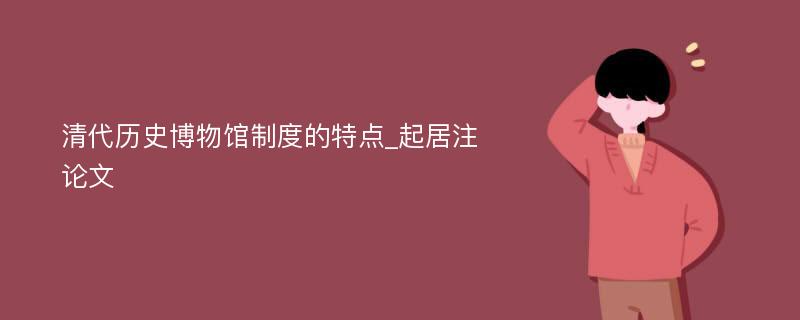
清代史馆制度的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代论文,制度论文,史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8)12-0089-08
长期以来,研究清代史学的学者一直都比较关注清代私家修史的成就,论著频出。与之相比,人们对清代史馆制度的研究明显不够,对清代史馆制度特点的探讨,更是鲜见。① 实际上,史馆制度是清代修史制度的核心,也是影响清代史学面貌及史学特征的最主要因素。分析清代史馆制度的特点,对于深入认识清代官方史学的本质乃至清代政治文化的特征,无疑会有很大的帮助。
一 史馆格局:稳定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主干与辅助相配套
设馆修史在中国有较早的历史。自唐以来,官方就通过一定的机构,把修史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唐代设立史馆,宰相监修,修纂国史和实录,对后世史馆制度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唐代史馆的形式还非常单一,还没有形成覆盖各个修史领域的史馆规模。[1]到了宋代,设馆修史的形式丰富起来,各种名目的史馆开始出现,修史领域扩展,规模扩大。但是,宋代的史馆主要是常开和例开之馆,史馆格局尚不够完善。[2]时至清代,统治者充分吸取了前朝设馆修史的经验和教训,史馆的设置趋于完备,格局更加合理,更有利于统治者通过修史来达到自身统治的目的。
和前代相比,清代史馆的形式增加,有常开、例开、阅时而开以及特开四种形式[3](p5),并形成了以常开、例开史馆为主干,以阅时而开和特开史馆为辅助的史馆格局。常开史馆持续开设,常开不闭,一直进行修史活动,这样的史馆有国史馆、起居注馆、方略馆等;例开史馆定期开设,届时而开,书成馆撤,实录馆、圣训馆、玉牒馆、律例馆等属于此类;阅时而开史馆根据具体情况开办,修纂具有明显接续性系列的史籍,会典馆、一通志馆即属此类;特开史馆是为了修纂某部史书而专门开设的史馆,每修一书,必开一馆,书成馆闭,不再重开。清代特开史馆非常之多,《明史》馆、《八旗通志》馆、“三通”馆、《明史纲目》馆、《明鉴》馆、《通鉴辑览》馆、《西域图志》馆等等,不一而足。这四类史馆在顺康时期就已经形成并巩固下来,共同构成了清代史馆稳定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主干与辅助相配套的整体格局。这样的史馆格局,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是仅见的。
清代史馆中的常开和例开之馆,是史馆中最具稳定性的部分,也是清代史馆的主干。这些史馆的开设,保证了清代官方史学中最核心内容的修纂。在统治者看来,本朝国史、帝王实录几乎是皇朝历史的全部,能够保证这类史籍按部就班地修纂,也就保证了对历史自始至终的解释权。对于国史、实录等史籍,清代统治者相当重视。康熙年间开国史馆修纂国史,目的就是“昭示奕祀”[4](卷一四五,康熙二十九年三月乙未),“用扬列圣之鸿谟,并及诸臣之劳绩”[5](卷一一,雍正元年九月丙午)。清朝列位帝王都对国史修纂给予极大关注,乾隆提出“国史修纂,所以彰善瘅恶,信今传后”[6](卷一一四二,乾隆四十六年十月癸酉)的原则。在他看来,修纂史书的目的在于传之后世,垂鉴将来,所谓“盖史者,所以传万世、垂法戒”[6](卷一一五四,乾隆四十七年四月辛巳),当代国史所担负的资治、垂训、警世的作用,是其他任何史籍所不能替代的。基于此,乾隆要求国史修纂既要“据事直书,而其人贤否自见”,又要贯彻“《春秋》华衮斧钺之义”。[6](卷七三九,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丁卯)国史馆对国史连续不断的修纂,就为清廷始终如一地解释历史和阐述现实作了资料和观念上的准备。
和国史一样,实录的纂修在统治者看来同样意义重大。康熙在为《太祖实录》作序时称赞努尔哈赤“肇开一统无外之规,度越古今,昭垂无极”,编纂《太祖实录》,目的就是“朝夕式观,以申继序绍庭之志,其在我后嗣子孙,循省是编,于栉风沐雨之勤劳,可以知积累之艰焉,于文谟武烈之显承,可以识燕贻之厚焉”。[7](卷首,康熙序)雍正为《圣祖实录》作序,认为“后之绍作君作师之任,求治统道统之全者,于是乎在”[4](卷首,雍正序)。在他们看来,实录就是后代帝王进行政治治理的必读之书,因为其中包含着前代帝王的统治经验。不间断的实录修纂,就是要皇族之后世子孙不断从中吸取经验,以为治国之资,即“濯识创业之辛勤,详考夫拓地开基以及于用人行政,凡大经大法,允为世守章程,即一动一言,莫非臣民轨则”[7](卷首,康熙朝进实录表)。可以说,实录是维系皇族治国安邦精神的纽带,不绝于书的关于后世帝王翻阅前朝实录从而获得治国经验的记载就是最好的说明。
清代统治者还特别重视方略的编纂,这是因为通过纂修方略,可以宣扬皇朝武功,所谓“我朝圣圣相承,功烈显铄,方略诸编,皆奉敕撰纪,以著其事之始末。威德远扬,洵书契以来所未有”[8](卷九九,艺文略三)。以方略宣扬皇朝“宏功伟绩”[9](p880~881),在清代成为一个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传统。
总之,常开和例开史馆编纂的史书,内容涉及清代现实政治生活的最主要方面,在维护皇权、张扬文治武功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乾隆间编纂《国朝宫史》,设“书籍”一门,将乾隆二十六年以前官修的重要书籍著录下来,分为16类,其所作的排序耐人寻味,“首登实录,以彰功德之原;次纪训谕,以昭诒谋之大;于御制仰圣学之高深,于方略述成功之懿铄。若夫表彰六经,厘定诸史,灵台占荚之学,职方益地之图,有典有则,厥功懋焉”[10](p485)。显然,编实录是为了彰显前朝丰功伟业的由来,纪训谕是为了昭明帝王谋略的博大,纂御制诗文是为了宣扬皇上学问的高深,撰方略是为了记述朝廷武功的美盛。很明显,这种排序所体现的是皇权中心的思想。而能够最充分体现这一思想的史书,都是由常开和例开史馆修纂的。我们说清代史馆具有稳定性,不仅是指史馆表面的常开不闭或有规律开设,更重要的是指清廷通过修纂史书始终保持官方历史书写的主动权,为皇权服务。
和常开、例开史馆相比,阅时和特开史馆具有灵活性的特点,是常开、例开这类主干史馆的辅助。它们不受任何时间、地点的限制,可以随时随地为配合政治形势而开设。在保持常开、例开史馆稳定开设的同时,清廷常常利用特开史馆适时进行史书修纂,以配合某种政治活动或思想宣传。像乾隆时期为了崇奖忠贞、风厉臣节,命史臣设馆编纂《胜朝殉节诸臣录》,“一体成书,与《明史》相附而行”[6](卷一零零二,乾隆四十一年二月庚戌),及时通过历史著述将自己的政策合法化。再如为了从理论上总结预立太子招致祸乱的历史教训,乾隆还下令组织史臣编纂《古今储贰金鉴》,“始于周平王,终于明神宗太子常洛,各胪事迹,以为后世立储之戒。首载圣谕,贻谋我国家万世共守家法”[11](p84),将自己的建储理论以史学的方式表达出来,并用史学的方法否定了册立太子这一历史形成的制度。又如咸丰、同治间,慈安、慈禧两宫垂帘听政,为说明垂帘听政的合理,设立史馆,命史臣将“历代帝王政治及前史垂帘事迹……择其可为法戒者,据史直书,简明注释,汇为一册,恭呈慈览”[12](P126)。由此可知,特开史馆有灵活多样的优势,它可以根据某种政治需要开馆修书,从而辅助常开、例开史馆更好地为政治统治服务。
清代史馆制度上这种稳定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主干与辅助相配套、常开与特开相照应的特点,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也正因为此,清代史馆不仅编纂出数以千万卷计的部帙浩繁的史书,而且还很好地配合了专制统治,通过史馆修史这一形式,用一个统一的历史叙事框架,将清廷的各项政策合法化,从而形成一个统一的符合统治者意志的价值观念。也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史馆成了专制集权可资利用的工具。
二 政治干预:皇帝全面掌控,一切仰承圣裁
自唐代正式确立史馆修史制度以来,帝王干预修史的记载就不断出现。唐高宗时修纂国史,高宗皇帝认为对太宗李世民的记载“多不周悉”,指示监修国史刘仁轨等“必须穷微索隐,原始要终,盛业鸿勋,咸使详备”[13](p1093)。中国古代本来有帝王不亲观国史的传统,但唐朝皇帝不顾史臣的反对,打破这一传统,翻阅实录,并对某些内容的写法提出批评。但是,唐代君主对史书的控制主要依靠的还是宰相兼修、重臣把关,皇帝亲自过问并不是普遍现象。到了宋代,随着专制皇权的加强,皇帝对于史事的控制日趋严密,阅视时政记、国史甚至起居注的记载常常见诸史册。对此,欧阳修曾上书提出批评:“自古人君皆不自阅史,今撰述既成,必录本进呈,则事有讳避,史官虽欲书而不可得也……其日历、时政记、起居注并乞更不进本。”[14](p850)皇帝阅看本朝历史受到大臣的批评,足见这一问题的严重。尽管如此,宋朝皇帝对史馆修史的干涉,还主要体现在删改史实上,诸如随意删除起居注、时政记中不利于自己的条文,多次重修实录等。[2](p193~195)对于史书修纂的项目、修史的指导思想、史书的体例等问题,过问不多。元、明帝王对修史亦有干涉,其范围、程度和形式都与宋朝差别不大。可是,到了清代,帝王对史馆修史的干涉明显加强,举凡修史的各个环节,大到修史项目的确定、修史指导思想的确立,小到体例的安排、字词的推敲,再到史馆的管理,无不过问,“达到了亲自全面干预修史活动的最高峰”[3](p10)。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首先,很多修史项目由皇帝主动发起修纂。清代帝王,为使修史更好地为自身统治服务,常常自己设计修史项目,谕令设馆纂修。如顺治十二年正月,为了推行教化,顺治皇帝谕令设立大训馆,修纂《顺治大训》,他说:“朕惟平治天下,莫大乎教化之广宣;鼓动人心,莫先于观摩之有象……兹欲将历代经史所载,凡忠臣义士、孝子顺孙、贤臣廉吏、贞妇烈女及奸贪鄙诈、愚不肖等,分别门类,勒成一书,以彰法戒,名之曰《顺治大训》。”[15](卷八八,顺治十二年正月辛亥) 并要求史官“协力同心,殚思博采,务令臣民皆可诵习,观感兴起,无负朕倦倦化导之意”[15](卷八八,顺治十二年正月辛亥)。圣训这类典籍,也是顺治帝倡议修纂的,顺治十二年四月,谕内三院:“《实录》业已告成,朕欲仿《贞观政要》、《洪武宝训》等书,分别义类,详加采辑,汇成一编,朕得朝夕仪型,子孙臣民,咸恪遵无斁,称为《太祖圣训》、《太宗圣训》。”[15](卷九一,顺治十二年四月癸未)于是成立圣训馆,编纂帝王圣训。乾隆皇帝更是善于发起修史项目,广泛特开史馆,修纂史书。他阅读明朝《宫史》,受到启发,决定修纂《国朝宫史》;[10](卷首,圣谕)阅读朱彝尊的《日下旧闻》一书,决定对之进行补正,令纂修《日下旧闻考》。其他如《盛京通志》、《盘山志》等书,皆是因为乾隆巡幸所至,遂产生编纂意图,设馆所修。嘉庆帝也效法列祖列宗,在披览范祖禹的《唐鉴》时,深感该书有资于治道,决定设立史馆,仿照《唐鉴》,编纂《明鉴》,“宜仿《唐鉴》体例,辑为《明鉴》一书,胪举大纲,搜采编次。其论断即令派出编纂诸臣,轮流纂拟,进呈后经朕裁定,勒为成书,刊刻颁行,用昭法戒”[16](卷二七零,嘉庆十八年六月乙卯)。
其次,形成史书修纂次第进呈御览的制度。为了对史书的内容、体例、字句等进行把关,清代帝王要求一些重要史籍每修若干卷就要进呈御览,不再等到全书完稿后一块审阅。康熙二十三年,清圣祖要求明史馆将《明史》已修成者,“以次进呈”,“可徐徐审阅,考镜得失,不致遗漏”。[4](卷一一四,康熙二十三年三月丁亥)这是康熙明确打破“告成呈览”的旧例,提出“以次进呈”的新方法。从此以后,对于重要的官修史籍,皇帝都要求史馆总裁“次第进呈”,随时阅览。乾隆七年,六部纂修则例,清高宗要求“次第进呈,朕皆逐一详览,其中或有更正,或有删除,俱照新定之书遵行”[17](p357)。明显强化了对修史工作的控制。乾隆十二年,修纂《大清会典》,清高宗又明确提出“将稿本缮成一二卷即行陆续呈奏,朕敕几多暇,将亲为讨论,冀免传疑而袭谬,且毋玩日以旷时”[18](p28)。乾隆十四年,大学士奏请编纂《平定金川方略》,提出十五条修纂原则,其中有一条就是“每成一卷,先进副本,恭候钦定,再缮正本”[6](卷三三八,乾隆十四年四月甲申),次第进呈已成史馆惯例。在官修的各类史籍中,只有起居注号称帝王不予观览,康熙曾言:“记注册,朕不欲亲阅。朕所行政事,即不记注,其善与否,自有天下人记之。”[9](p949~950)而事实上,对于哪些史事可以纂入,哪些不能纂入,皆由皇帝掌握。乾隆时期传出皇帝阅览起居注的所谓谣言,清高宗还出来辟谣:“至所称起居注册档,不应进呈御览等语,则自皇祖、皇考以及朕躬,从未披览记注,不知出于何人之讹传也!盖人君政事言动,万国观瞻,若有阙失,岂能禁人之不书?倘自信无他,又何必观其记载?当时唐太宗索观记注,朕方以为非,岂肯躬自蹈乎?”[19](p26~27)真是无风不起浪,欲盖而弥彰。其实自雍正开始,“起居注止载发抄之谕旨,更属无用”[20],阅与不阅,都无所谓了。
第三,对史书修纂内容进行全面指导。清代帝王对官修史书的指导具体而详细,从修史指导思想到史书字词错误,无不涉及。康熙、雍正都曾对《明史》编修提出指导性意见:“征事务求其实,持议必得其平。举政治之大端,而细致民谣皆所不录;准情理之至当,而矫诬附会在所必严。褒贬符舆论之公,繁简合文体之正。勿为苛刻之论,勿用无稽之言。毋胶执己见以遂其偏私,毋轻听传闻而涉于疑似。”[21](p339)这是从指导思想上为《明史》编修指明方向。雍正时律例馆纂修律例将竣,雍正指示史馆会同吏、兵两部,再次“逐一细查详议,应删者删,应留者留,务期简明确切,可以永远遵守。仍逐卷缮写,并原书进呈,朕亲加酌量,刊刻颁行”[21](p354)。这是更加具体的干涉。乾隆对官修史书的干预比之雍正更加细致、全面。乾隆时修纂《大清会典》,皇帝起了发凡起例的作用。乾隆还认为宗人府系宗室衙门,不应与文武衙门并列,此次纂修《会典》,即将宗人府另列一卷居首,其文职衙门从内阁开始依次排列。康熙、雍正《会典》载大学士员缺无定,此次纂修,俱照定员载入等等[22],均涉及体例问题。对于《大清会典》中的字词,乾隆帝也进行具体干预,如“婚礼典则”内有“王妃”字样者,均指示改为“福晋”。对于清文与汉文的对译,乾隆力主文义相符,如清文“伊尔希达”、“噶喇衣达”,汉文有时译写成“副管”,有时译写成“翼领”,乾隆谕令“伊尔希达”统一写成“副管”,“噶喇衣达”统一写成“翼领”。[22]其他如对国史立传“以人不以官”[23](卷一零四九)的指示,刊正辽、金、元三史所记人名、地名错误的谕旨[23](卷一零五零),对国史馆所纂《王鸿绪列传》应载入郭琇弹劾之文的要求[23](卷一零五零),对《续文献通考》馆所进《职官考》内所载职官错误的订正等等[6](卷六九一,乾隆二十八年七月壬申),均具体而详尽。嘉庆以后,虽然清廷日益走向衰落,但对史馆修史的干预依然很强。道光时纂修《仁宗实录》,“夫章程一秉夫鉴裁,即字体一遵夫指示”[16](卷首,进实录表)。咸丰时纂修《宣宗实录》,依然是“凡规条咸秉夫鉴裁,即点画亦遵夫指示”[24](卷首,进实录表)。说明即使到了晚清,清廷依然要对官修史书进行干预,使之符合自身的政治意愿。
第四,对史馆的管理亲自过问。清代帝王不仅关注官修史书的内容,而且关注史馆的管理,一旦发现问题,便出面协调,责令改正。乾隆时期,开馆较多,问题多有,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纂修人员,皆怠忽成习,经历年久,率多未成”,乾隆帝对此非常不满,谕令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之大臣,“按月察核,倘仍前怠玩,责有攸归”,并规定,除律吕正义馆、藏经馆、文颖馆之外,“其余各馆缮写汉文,请照《明史纲目》馆每员每日一千五百字;缮写清文,请照玉牒馆每员每日八百五十字;校对数目请照实录馆每员每日二十五篇”,各馆在每月初五以前将前一月纂辑、缮写、校对的数目,详细造册,咨送上谕事件处进行查核。[6](卷二二一,成隆九年七月壬寅)这是通过制度规定和监察部门来提高修书效率。嘉庆时期国史馆纂修《大清一统志》,向各直省咨取资料,令各地方“将建置沿革、职官、户口、人物一切裁改各事宜,限半年内查明送馆,勒限纂修”。但五年过去,各地资料仍没有汇齐,嘉庆帝对这种把史馆事务“视为不急之务”的现象非常不满,“著各该督抚分饬所属,查照该馆咨取事宜,迅速详查,造具清册送馆,毋得仍前延玩”[16](卷三一二,嘉庆二十年十一月己亥)。总之,帝王总是利用自身的权威来协调史馆事务,从而保证史馆修史的正常运行。
清代帝王对史馆修史活动的全面干预,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空前强化密切相关,是专制集权在史学领域的具体体现。一方面,他们对史学高度重视,发起、鼓励设馆修史,形成了兴盛一时的官修史书局面。另一方面,他们又从思想、体例乃至文字、语言等方面对史馆修史进行指导,遏制了史学思想的发展,抹去了史学本身所应具有的批判现实的锋芒。
三 史官构成:维护满人特权,满汉纂修官共局修史
清朝作为一个由满洲贵族建立的政权,无论是政治统治抑或文化形态,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这个特点表现在官方史学上,就是在史馆中“保证满人参与修史”[3](p15)。
在常开的起居注馆、国史馆、方略馆中,清廷都规定了满、汉官员的数目,比如起居注馆,“起居注官,满洲十人,汉十二人。主事,满洲二人,汉一人。笔帖式,满洲十四人,汉军二人”[23](卷二一)。国史馆,“总裁,特简,无定员。清文总校一人,满洲侍郎内特简。提调,满洲、蒙古、汉各二人。总纂,满洲四人,蒙古二人,汉六人。纂修、协修无定员。校对,满、蒙、汉俱各八人”[25](p890)。方略馆,“总裁无定员,以军机大臣领之……提调,满洲二人,汉二人。收掌,满洲二人,汉二人。纂修,满洲三人,汉六人”[26](p155~156)。可以看出,在这些史馆中,满、汉员额基本是对等的,而且满员列于汉员之前。尽管这些数字在实际运作中会有变化,但一直保持着满、汉员额的大体一致。像国史馆,虽然规定总裁无定员,但在实际任用上,“向来满、汉总裁各一员,满、汉副总裁各一二员不等”[27](人事类,案卷号736)。到光绪时期,“国史馆最终形成了总裁、副总裁各二名,满、汉员缺对等的定制”[3](p34)。方略馆也大致如此。可以说,无论满人有无史才,在史馆员缺中都要占到几乎一半的数目,甚至有的还更多。此外,为体现对蒙古族的重视,坚持对蒙古族一以贯之的友好争取,像国史馆这样重要的史馆,还设有蒙古员额。
在一些非常设的重要的史馆中,也基本上仿照常设史馆的数目来确定满、汉员额,同样要保证满人参与修史的权利,这一传统一直保持到晚清,比如光绪朝修纂《大清会典》所用员额,总裁,满、汉各二人;副总裁,满四人,汉二人;提调官,满二人,汉一人;总纂官,满、汉各四人;纂修官,满十九人,汉二十二人[28]。在史馆的管理层,满人数目超过汉人。
清廷以满人修史,并不是因为满人有较高的史才,相反,相对汉人来讲,满人的文化程度是比较低的,真正具有良史之才的人也是非常少的。之所以在众多史馆中规定满洲员额,主要还是和清廷一直坚持的优容满洲人的政策紧密相连的。有清一代,在各个方面都规定了满洲人的特权。在官员的任用上,同样要维护满人特权,最主要的就是通过特有的官缺制度来实现,《大清会典》规定:“凡内外官之缺,有宗室缺,有满洲缺,有蒙古缺,有汉军缺,有内务府包衣缺,有汉缺。”[29](卷七)将所有官缺作如上划分,是清代官制的一大特点。这种制度明确规定各族的所得官缺,既防止了争斗,又维护了满人在任官中的特权。在各类重要的官缺中,满、汉都是按比例设定的。据有人统计,六部尚书,满、汉各1人,左右侍郎,满、汉各1人;六部各司郎中,满74人,宗室4人,汉50人;各司员外郎,满95人,宗室8人,汉51人。[30](p126)由此看来,清廷在史馆中规定满人员额,实际上就是官僚任官制度在史学领域的一种反映。史馆虽然不像其他官僚机构一样具有完整的人事和财政权力,但它却明显地渗透着清代专制官僚体制的各种因素。
以本民族成员参与官方修史,并不起于清朝。历史上很多少数民族政权,都在官方修史活动中任用本民族的成员,比如辽朝,在记注官和修史官中都任用部分契丹人。[31]金朝,在国史院各级史职中任用女真人。[32]元朝修辽、金、宋三史,任用蒙古重臣担任监修。可见,清朝实际上是继承了前代少数民族政权的做法,在修史活动中体现本民族的特色和利益。所不同的是,清代对本民族史臣在史馆中的员额作了严格规定,用制度化的方式固定下来,这是前朝所没有的。
清代维护满人特权,以满人参与修史,一方面是想通过这种做法,将修史大权牢牢控制在满洲统治者手里,使之更方便地论证自己取得统治的历史和道德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就是通过共同修史,提高满人的文化素养和史学修养,促进文化的融合。官方修史兼用满、汉史臣,既反映了不同文化的冲突,又体现了不同文化的融合。
四 史无专官下严格而又灵活的修史运作机制
清代,史无专官,史馆中的史官,绝大多数都是由翰林院、内阁、军机处以及各部院衙门派充,由原衔兼任,薪俸也由原供职单位支付。史官置身官僚体系的运作之中,其迁转、任免和黜陟,均由朝廷责成原派充衙署和吏部协同处理。史馆没有完备的财权和人事权,再加上多数史馆又是临时设立,书成馆撤,因此,没有一套严格的修史运作方式,很难成功完成卷帙庞大的史书修纂任务。在这方面,清代史馆有一套成熟的运作方式,从史官选任、对外协调、史馆督察到资料征用,都有制度化的规定,既严格,又灵活。
清代史馆的组建,有一套程序。一般是由皇帝特命,或大臣提出,奏明皇上,并拟定组成史馆之各级史官的名单,由皇上钦定。一般总裁、副总裁由皇上亲自指定,其他人员则由总裁、副总裁等一起拟定。乾隆十二年二月,清高宗谕令内阁组建会典馆,重修《大清会典》,内阁大学士果毅公讷亲开列出内阁大学士、各部院满汉尚书、侍郎、内阁学士、詹事府詹事等职名55人,进呈乾隆,“恭请皇上于大学士、尚书等内钦点总裁四员,部院侍郎、学士、詹事等内钦点满、汉副总裁五员”,结果清高宗钦点内阁大学士讷亲、张廷玉,礼部尚书王安国、兵部尚书班第4人充总裁官,吏部左侍郎蒋溥、户部左侍郎傅恒、兵部左侍郎舒赫德、兵部右侍郎王会汾、刑部左侍郎钱陈群5人充副总裁官。[22]总裁、副总裁确定后,他们首先要做的工作是拟定所需纂修人员名额,行文翰林院及各部院衙门,让他们拣选“学问淹博,熟谙掌故之员”,缮写名单,汇总到总裁手中,由总裁统一拟出名单,由皇帝过目后确定下来。以上组建程序保证了专制皇权对史馆的完全控制,保证了帝王意志在史馆内的贯彻执行。虽然史无专官,但能够靠制度化的系列运作不断组织出一个又一个史馆,保证官方修史的连续进行。
史馆的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确定总裁、副总裁以及纂修人员外,还需要总裁协调与各个衙门的关系。清廷有明确规定,凡史馆组建,所需一切物质条件,都实行供给制,各衙门必须给以大力支持,房屋由内务府提供,桌饭银两工食由户部支领,修史所用箱柜、桌椅以及修理、裱糊等由工部负责,开馆由钦天监选择吉日,修成恭进御览必须由礼部参与。[33]对于一个没有财权和人事权的史馆来说,一部史书的修纂需要涉及官僚机器的各个部门,且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没有清廷的重视和合理的制度约束,难以达到如此完备的状态。
有清一代,凡较大的史馆,都制定“馆规”,按章行事,有严格的考勤考绩和奖惩制度。这些规章制度,或曰“规条”,或曰“章程”,或曰“条例”,对馆内各机构的职责、纂修任务、事务协调等都有明确规定。“在馆办事宜有成规。总裁官督率纂修各官,每日必及辰而入,尽申而散。庶几在馆办事,俱有成规。不独勤惰易稽,年限便于核定,且互相讨究,可以斟酌得宜,彼此观摩,亦见智能交奋。”[6](卷二八二,乾隆十二年正月丙申)在第一历史档案馆,笔者看到了道光三十年的《实录馆新定规条》,该《规条》共有12款,对馆内各个部门的职责、各部门办事的程序、纂修的进度、考勤等都做了具体规定。在涉及纂修程序和进度方面,就规定:“成卷后先呈监修总裁、总裁恭阅。其汉本未成时,满纂修先将清字谕旨及应载事件敬谨译出,务与原本清文吻合,交与汉纂修汇辑。书成后若系汉文遗漏,惟汉纂修是问,若系原奉清文未经译交,致有遗漏者,惟满纂修是问。”誊录官缮写史稿,“汉誊录官每人每日写一千字”,“满洲、蒙古誊录,每人每日各写五百字”,“凡誊录领书交书时均记明档簿,令本员自行画押。有字画草率及挖补过多者,书即驳回另缮。若如式者,收掌官收送校对处细校”。[34]笔者还看到了光绪三十四年国史馆制定的《改定史馆章程条例》[27](编纂类,案卷号1)和宣统三年的《厘定史馆章程》[27](编纂类,案卷号470),《条例》和《章程》涉及人员安排、经费使用、督察纂修以及查阅资料等各方面的情况。
清代史馆,特别重视考勤考绩,馆中都设有“考勤簿”和“功课册”。实录馆就规定:“凡总纂、纂修、协修、收掌、校对等官,毋令擅入擅出。每日到馆,勿使旷误,逐日画到,由提调官加押存查。”[34]国史馆的考勤几经变化,开始时议定纂修官每月必须到馆十四五日,月月统计。后来改为半年统计一次到馆天数,凡半年到馆不满七十日者,下半年补足。全年到馆不足一百四十天的,按日扣除其桌饭钱。[27](庶务类,案卷号1068,事宜单)再后来则采用“堂期考勤”,即规定每月三、六、九为堂期,届时到馆由考勤人员登记在册。除此之外,国史馆还设立“卯簿”,在每月朔、望日点卯,登记在册。[27](人事类,案卷号945)另有“加班考勤簿”,记录加班人员到馆时刻。除考勤外,修书各馆对考绩都很重视,国史馆设有各种“堂期功课档”和“月功课表”,登记编纂、校对等人员交来的史稿数量、内容,“在功课上注明某日交功课若干页。仍不时核对,以免舛错”[27](编纂类,案卷号1)。实录馆规定:“除总纂、纂修、协修功课应缴监修总裁、总裁查核外,凡收掌、校对、翻译、誊录及供事人等,功课疏密,差使勤惰,应行记功记过之处,比责成提调官记明加押,候书成议叙呈堂公核。”[34]玉牒馆“每月均将本月功课上报上谕处(即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33]。
清代对修书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处罚相当严厉,“各馆修书,纂修官文理错误者,罚俸三月,总裁罚俸一月。校对官不能对出错字,校刊官板片笔画错误,不能查出者,亦罚俸一月”[23](卷一一二)。嘉庆十九年,国史馆进呈御览之《和珅列传》,因对和珅的罪行记载不详,总纂官席煜被革职回籍。还有在《圣训》中将先帝庙号笔画写错者,更是牵连多人罚俸、革职甚至发配。[23](卷一一二)所有这些,都对纂修官是一种震慑,使他们不敢懈怠。对于修书勤奋人员,则给予激励。道光三十年十月,咸丰帝看到实录馆人员纂书辛苦,云:“现值天气严寒,实录馆人员朝夕恭纂书籍,著加恩于例支柴炭外,十一月、十二月、正月,每月赏银五十两,在广储司支领。”[35](卷二零,道光三十年十月庚申)除了平时的奖励以外,激励纂修官的主要还是议叙。清代史馆的议叙形式多样,有临时议叙者,有修若干年议叙者,有书毕议叙者,而以书毕议叙者为最多。国史馆实行所有人员五年一次考课议叙制,在堂期考勤、月功课考绩基础上进行议叙。[36]实录馆在嘉庆时实行中期议叙与书毕议叙相结合的方式,往往给以优叙。
资料是纂修史书的前提,清代在制度上保证了史馆调取资料的便捷。首先,清代所有官方档案深藏宫禁,密不示人,就连“九卿、翰林部员,有终身不得窥见一字者”[37](卷二,中书入阁观书),但只要史馆修史需要,可以随时调取。就连一般大臣不得观阅的实录,清廷也规定“各馆修书处有请领实录校对他书者,该馆出具印领,赴内阁恭请,满本房检明卷帙,注册发给”[38](卷二),从制度上保证了资料的供给。其次,调取资料手续便捷。各衙门必须积极配合史馆,需咨送者,按式造送。需史馆咨取者,各衙门查点齐备,以便随时咨取。光绪年间纂修会典,理藩院就抄录造送拟入会典源流册、拟入会典案件册。[39]玉牒馆也有“为咨查三额附卒年行理藩院事”[33]等向相关衙门咨取资料的记载。另外,各地衙门有义务为修史准备资料。乾隆初年续修国史,要求地方政府积极向国史馆报送材料,“将雍正十三年间诸王文武群臣谱牒、行述、家乘、碑志、奏疏、文集,在京文臣五品以上,武臣三品以上,外官司道总兵以上,身后具述历官治行事迹,敕八旗直省,查明申送史馆,以备采录传述”[6](卷一五,乾隆元年三月癸丑)。光绪年间国史馆续办儒林、文苑、循吏、孝友列传,曾向各省大量咨取应立传人物之事迹以及各种官私书籍和资料,其中一份移会江苏学政,“明示各学教官,令其采访呈上,由本省督抚设法运送到馆。所采之书,自顺治初年起至同治末年止。并望示知各地方官一体筹资录送,以昭信史而阐幽光”[40]。为征求人物、书籍,国史馆甚至要求地方官“访察举报,张贴告示,晓谕民众,俾绅耆生监等各举所知”[40],很有些全民动员的意味。总之,由于“钦定”、“圣裁”的作用,史馆具备了很多“特权”,从史官的选任、史馆的管理再到资料的征用,各个环节都井然有序,有条不紊。虽史无专官,却运转正常。
从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清代的史馆制度建设非常健全,对修史实行了有效的控制和管理,这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都是仅有的。由此保证了官方大规模修史的实现,为官方史学的繁荣打下了基础。其次,清代史馆制度带有浓重的民族特色,史馆中满汉员额的同在,史籍中满汉甚至蒙文文本的并存,都打上了民族文化的印痕,既反映了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也反映了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第三,官方设馆修史有着鲜明的帝王立场,清廷试图通过史馆这样的修史机构,彻底垄断史学,把对历史的解释权和对现实的评判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在这一过程中,皇帝往往充当了历史判官的角色。第四,清代史馆是在专制皇权日益强化的情况下形成的,史馆的组建、史官的选任、修史体例与内容的确立,无不渗透着专制皇权的政治意图和文化理念。由此导致官方史学热衷于宣扬纲常名教,彰显皇朝的文治武功,缺乏批判意识和批判精神。它严重限制了史馆内纂修官的史学才华,把史官变成汇编史料的机器。整个清代,官修史籍相当丰富,但资料汇编为多,独立创见鲜少,这不能不说是设馆修史的悲哀。
注释:
① 乔治忠《清朝官方史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是第一部研究清代官方史学成就的著作,该书侧重论述的是帝王史学思想、官修史书的学术成就等,极有价值。其中也涉及到修史制度,但对史馆制度本身的问题尚未充分展开论述。另外,研究清代史馆的论文还有陈捷先《清代起居注馆建置考略》(《清史杂笔》,台北学海出版社1977年版)、乔治忠《清代国史馆考述》(《文史》第39辑)、王清政《清代实录馆考述》(《江汉论坛》1999年第2期)、邹爱莲《清代的国史馆及其修史制度》(《史学集刊》2002年第4期)、王记录《清代史馆的人员设置与管理机制》(《史学史研究》2005年第4期)等。
标签:起居注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清朝论文; 历史论文; 明史论文; 康熙论文; 乾隆论文; 唐鉴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二十四史论文; 宋史论文; 元史论文; 晋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