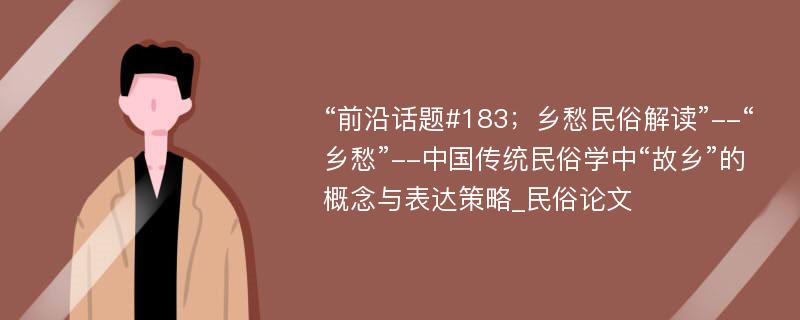
“前沿话题#183;乡愁的民俗学解读”——对象化的乡愁:中国传统民俗志中的“家乡”观念与表达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愁论文,民俗学论文,中国传统论文,民俗论文,家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214(2015)02-0005-06 主持人语: 作为一种特殊的情绪或心理现象,乡愁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从古至今,在许多群体或个体身上都有或多或少的表现。这是一种因主体与其故园分离而造成的思念与忧伤情绪。由于主体所处社会历史环境的不同,其与故乡分离的原因也有这样那样的差别:有的是因战乱、灾祸等破坏性力量而导致的迫不得已的离散,有的是因经商、读书、仕宦等主动选择而造成的分别。今天,随着现代化、城市化浪潮的加剧,乡愁的产生原因中,又多了一种由于传统生活方式的急速变化乃至消亡而生发的焦虑和失落。 不同的产生原因,又使得乡愁的表现形态及忧伤程度有所不同。与故土的被迫离散所导致的乡愁,是漫无边际、无可把握的思念与巨大悲怆;主动离别造成的乡愁,是乡国万里却始终对重返故园怀着希望的忧思;而现代化所引起的乡愁,则是在以发展为主题的历史潮流中眼见传统田园生活消亡却无可奈何的怅惘。但不论其表现形式和程度有怎样的差别,乡愁中所蕴含的对传统、对家园的真挚情怀又是高度一致的。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种情怀,把每一个个体与历史、与特殊的地方、特殊的人群连接了起来,对使人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中的成员的基础起着丰富和强化作用。 当下的中国,由于面临巨大的社会转型,“乡愁”正成为在各个领域备受关注的概念和话题。作为一门曾被认为是受现代性怀旧(乡愁)情绪影响而产生的学问,民俗学向来与“乡愁”问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不仅表现在它的诸多研究对象如歌谣等当中有大量抒写离散与乡愁的内容,也表现在它始终对古老传统的价值有特殊的认识,并对各种传统的衰落或消亡怀着特殊的敏感与关怀。有鉴于此,我们组织了这组有关乡愁问题的讨论,这既符合民俗学的题中之义,也是为了促使我们的学科更加积极地参与社会文化重要话题的讨论。 本组三篇文章,以民俗学的视角,从不同方面对乡愁问题进行讨论。其中,既有关于古代因家园离散而形成的浓郁乡愁的表现形式和处理方式的探讨,又有对当代中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乡愁问题与解决途径的思考。我们期望通过这些讨论,既能够对乡愁的多种面向及其表达形式加以展示和分析,又能够结合古村落保护等民俗学者广泛参与的工作,为如何缓解当下诸多处于衣食无忧状态的人们心中新出现的集体乡愁,提供有价值的参照。 需要指出的是,今天的民俗学,早已脱离了以往把民俗看作“遗留物”的、“向后看”的老路,而以直面当下的情怀来定位自己的学术取向。因此,我们对乡愁的关注,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在快速现代化的时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搭建更好的桥梁,从而为推进社会的良性发展贡献自己学科的力量。 ——安德明 中国历代民俗志,大多都是作者对其故乡或长期居留之地民俗文化的记录和描述,其中,有不少是作者因战乱等原因与故土离散之后的一种回忆式书写。这种借助记忆构建的民俗志,在保留当时生活文化方面珍贵资料的同时,也集中表达了作者浓厚的乡愁以及对故园美好生活的理想化想象。而这两方面的特点,又清楚地体现在这类民俗志的叙述策略上:家乡与家乡民俗,在其中既是作者倾注了强烈感情的对象,又被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一种对象化的方式呈现给读者——包括与他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同乡人,以及可能超出其家乡范围的更多的异乡人。本文将以《荆楚岁时记》、《东京梦华录》和《梦粱录》为例,对这类民俗志所表现出的有关家乡民俗的观念、态度和表达策略,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中国古代民俗志书写传统进行讨论。① 一、基于乡愁的家乡民俗志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谓“乡愁”,主要是指“家园文化与离散现实的冲突……所触发的带有悲剧意味的情思与感触”,是“一种血脉亲情、故园意识,是时空距离导致的人的怀旧感伤情绪,以及人生不能自主、不能预料的有关生命时光的咏叹等”。②民俗志,与民俗学和人类学研究者所熟知的“民族志”属于不同概念。后者既是一种基于现代学科理念对特定社会文化进行观察、记录与解释的综合研究方法,大体等同于“田野作业”,又是一种成果展示形式,即在田野作业基础上对调查与研究结果的书写和报告,其对应的英文是ethnography;而前者则是指有关某个地区一类或多种生活文化传统的描写和记录,其中并不必然包含现代学科的理念和方法要求,却往往因资料价值以及所体现的特定语境下书写者有关民间文化的态度而受到民俗学研究者的重视,英文大体可以译为folklore record。就中国古代的情形而言,各种民俗志的资料,有的来自作者的实地调查与搜集,也有的来自对不同文献中相关民俗材料的辑录。本文所谓“家乡”,既包括民俗志作者从小生长、生活的地方,又指其成年后移居其间并长期居住和生活的地方,即“第二故乡”;它所涉及范围的大小,也因作者写作时所处环境参照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对那些因各种原因离开自己家乡的写作者而言,它往往至少是一座城市,或者是包含了诸多城市和村落的更广袤的地区。以此推之,作为本文主要概念之一的“家乡民俗志”,指的是作者以其家乡生活文化传统为主要内容而做的记录和书写。 《荆楚岁时记》是较早出现的由当地人书写家乡民俗的专书。学界一般认为,它是作者南朝梁的宗懔在国破被俘至北朝之后所作,“他在北朝里面生活,是很不习惯的。他在自己身处异乡的感受中,在通过新朝看旧朝的不同经验中,撰写《荆楚岁时记》……”③也有研究者否认此书乃作者被掳往北朝之后的思乡之作,而认为它作于作者在梁朝为官之时,甚至“有很大可能是为定都荆州而作的文化宣传”。④本文在此遵从前一种看法。而即使就后一种推论而言,《荆楚岁时记》也具有明确的家乡人写家乡生活的特点,其因特定政治事件刺激而把所在地区生活文化对象化的处理,以及由此体现的特殊乡愁——虽身在故园又“因分离牵挂之情或土地人民乃至天地人际关系而产生的种种忧患意识与现实诉求”⑤,同本文所探讨的主要问题并不矛盾。 相比之下,《东京梦华录》和《梦粱录》因有作者自序交代,写作背景相对明确,都是作者在其长期生活的城市——汴梁和临安——为他国所破之后回忆往昔生活之作。虽然《梦粱录》作者自序所署写作时间“甲戌”,按推断当属南宋度宗咸淳年间,但据其序中所云:“矧时异事殊,城池苑囿之富,风俗人物之盛,焉保其常如畴昔哉!缅怀往事,殆犹梦也,名曰《梦粱录》云。”学界一般均认为这一时间标记可能是由于传抄失误所致,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作者别有深意的处理结果:“序无纪元,而但书甲戌,若在咸淳,则故都尚无恙也。阅一甲子,则当在元顺帝时,斯时元之为元,不犹夫宋之季世也哉?汴亡而《梦华》作,其地已沦异域,孟氏特仿像而得之;今兹所纪,则皆耳目所素习者,钟虚不移,井邑如故,凡夫可欣可乐之事,皆适成可悲可涕之端,作者于此,殆有难乎为情者焉。”(卢文弨抱经堂文集“《梦粱录》跋”) 二、求同存异的观念基础、记录遣怀的宗旨和对故园文化对象化的处理 这类志书的写作目的,在《东京梦华录》作者序中有十分清晰的表述: 一旦兵火,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来,避地江左,情绪牢落,渐入桑榆。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近与亲戚会面,谈及曩昔,后生往往妄生不然。仆恐浸久,论其风俗者,失于事实,诚为可惜,谨省记编次成集,庶几开卷得睹当时之盛。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涯者,仆今追念,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目之曰《梦华录》。 可以看出,作者写作此书,一方面是为了追念当年盛况,抒发对离散家园的深切怀念,排遣和表达挥之不去的浓郁乡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使过去的生活传统得以记录和保存,而不至于亡佚。同时,可以推断的是,作为身处异乡的避难者,作者通过展示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故园文化传统,客观上也能够起到促进与所在地区人民及其文化相融合的作用。 具体而言,对自己故乡风俗的书写,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同作者当下所居住地域文化的对比而展开的,这体现了作者在“我”与“他”的差别中显示“我”的特殊性,以及通过这种特殊性来与他者进行沟通、并争取融入他者的努力和追求。而这种努力的一个前提,源于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认识或信念,即“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这种对于不同地域文化差异性的认识和承认,是中国古代十分重要的思想,也构成了不同地域、人群和文化相互之间共存、共处的基本原则。尽管具体表现各有不同,每一个地区、人群的具体生活实践和文化现象,却都可以被纳入“风俗”这个更大的分类范畴,因而都是可以容忍和理解的。对各种有关异乡风俗习惯的著述来说,承认风俗差异性,也为更大范围的读者接受、理解和欣赏相关记述、进而接纳作者及其文化传统奠定了基础。而像《荆楚岁时记》这类由前朝遗民在新朝所著的回忆之作,尽管有寄托故国情思的目的,却也由于所述风俗符合有关文化差异性的认识以及基于这种认识的政治统治思想而得到了新朝统治者的允可,因为,“古者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故明王修道,一民同俗,上爱民为法,下相亲为义,是以天下不相遗,此明王教民之理也。”(《晏子春秋》“内篇·问上”)同时,“尚书:‘天子巡守,至于岱宗,觐诸侯,见百年,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俗。’孝经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传曰:‘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户异政,人殊服。’由此言之:为政之要,辩风正俗,最其上也。”(《风俗通义》“序”)也就是说,民俗被统治者当成了解社会和治理国家的重要资源来对待,而承认民俗的差异性,又是正确对待这种资源的前提。以此为基础,才能进行不同区域、不同层级文化之间的沟通、交流和相互影响,最终达到更大范围文化的融合与统一。 或许正是由于本着记录和保留文化传统的目的,尽管家乡与家乡文化寄寓着作者丰富的情感,但相比于直抒胸臆的诗文创作,家乡民俗志中作者深厚、浓烈的乡愁,往往是隐匿在客观、冷静的描写当中,被对象化为看似客观呈现的岁时仪式和市井活动。“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记得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李后主词作中有关离散情怀的这种悲怆表达,除了在《东京梦华录》和《梦粱录》自序中有所体现之外,在风俗志的本体部分,几乎丝毫不见痕迹。这大概同“述而不论”的传统史观影响不无关系,一定程度上具有强化所写内容真实可信性的作用;而由于这类文字并不明确表现强烈的怀旧情感,无论是对身为“前朝遗民”的部分写作者的政治安全还是对新朝王权的稳固来说,它都成了可以接受的稳妥的表达形式。 由于贯穿其书写始终的叙事策略,是把作者所熟悉并曾参与其中的故乡风俗,以及基于这种风俗的乡愁加以对象化的处理,因此,以冷静、客观的态度来呈现故国风情,成了这些著述的主要取向。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这些作者在根据个人经历实录或广泛搜罗文献资料加以疏证的基础上,对文字采用了相似的处理方式,即保持“语言鄙俚,不以文饰”的特点,从而使得“上下通晓”。(《东京梦华录》序)尽管由于这种追求,《梦粱录》受到了一些诟病,认为它“用笔拖沓,不知所裁,未若泗水潜夫《武林旧事》之简而有要也”,(朱彝尊曝书亭集“《梦粱录》跋”)但大多数的评论者,还是读懂并接受了它充分注重并着意表现民俗语言特征的做法,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云:“是书……详于叙述,而拙于文采,俚词俗字,展笈纷如,又出《梦华录》之下。而观其自序,实非不解雅语者,毋乃信刘知几之说,欲如宋孝王《关东风俗传》,方言世语,由此必彰乎。” 在书写中注重民俗语言特征的做法,以及《东京梦华录》作者在自序中所表现出的求真精神(“然以京师之浩穰,及有未尝经从处,得之于人,不无遗阙。倘遇乡党宿德,补缀周备,不胜幸甚。”)无意中表现出了与现代民俗学所强调的田野记录原则相吻合之处。或许我们可以说,这些先辈民俗志作者所开创的传统,构成了我们后世研究者所遵循的规范之一。 三、家乡民俗志的记述与表达策略 从具体的记述和表达策略来看,这类家乡民俗志又都具有这样一些特征:按照时间顺序或以时序与空间秩序相结合的方式来展开;概括描述与个人经验记录的融合;冷静描写与热情歌咏的结合;对官方礼仪与民间生活实践的一视同仁。 按时间或时间与空间分布相结合的顺序来展开记述,是古代许多民俗志书共有的特征,家乡民俗志的写作也都体现了这一特征。《荆楚岁时记》作为一部岁时民俗专书,⑥其记述体例即是遵循时序,细致记录、疏证了从正月元日至十二月除日的二十余项重要节俗。这种以时序为脉络的写法,是对中国一向重视的时间记述传统的延续,也开创了后世岁时著作以时序为线索来展开的叙事方式之先河。⑦《东京梦华录》和《梦粱录》中,就都有大量篇幅,是按照时间线索对重要节俗的描述。除此之外,这两部有关帝都民俗的志书,还对都城一般的市井习俗、商贸活动和宫廷、官府的重要礼仪,按照城市布局,进行了详细描写,极力渲染和描绘了故都的繁盛,客观上又衬托出对繁华不再的无比怅惘。 在记述各种风俗之时,作者往往是以概括的笔法,来追忆过去家乡的生活文化,从中可以看出力求客观的、把自己的生活传统对象化的努力。例如, 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春秋》谓之端月。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立春之日,悉剪彩为燕戴之,帖“宜春”二字。 (《荆楚岁时记》) 每日交五更,诸寺院行者打铁牌子或木鱼循门报晓,亦各分地分,日间求化。诸趋朝入市之人,闻此而起。诸门桥市井已开,如瓠羹店门首坐一小儿,叫饶骨头,间有灌肺及炒肺。酒店多点灯烛沽卖,每分不过二十文,并粥饭点心。亦间或有卖洗面水、煎点汤茶药者,直至天明。其杀猪羊作坊,每人担猪羊及车子上市,动即百数。如果木亦集于朱雀门外及州桥之西,谓之果子行。纸画儿亦在彼处,行贩不絶。其卖麦面,每秤作一布袋,谓之“一宛”,或三五秤作一宛,用太平车或驴马驮之,从城外守门入城货卖,至天明不絶。更有御街州桥至南内前趁朝卖药及饮食者,吟叫百端。 (《东京梦华录》卷三) 仲春十五日为花朝节,浙间风俗,以为春序正中,百花争放之时,最堪游赏,都人皆往钱塘门外玉壶、古柳林、杨府、云洞,钱湖门外庆乐、小湖等园,嘉会门外包家山王保生、张太尉等园,玩赏奇花异木。最是包家山桃开浑如锦障,极为可爱。此日帅守、县宰,率僚佐出郊,召父老赐酒食,劝以农桑,告谕勤劬,奉行虔恪。天庆观递年设老君诞会,燃万盏华灯,供圣修斋,为民祈福。士庶拈香瞻仰,往来无数。崇新门外长明寺及诸教院僧尼,建佛涅胜会,罗列幡幢,种种香花异果供养,挂名贤书画,设珍异玩具,庄严道场,观者纷集,竞日不绝。 (《梦粱录》卷一) 但由于这些著作,均是在个人经验基础上的实录,其中又无可避免地带有个性化体验的色彩。例如,《荆楚岁时记》在记述正月初七习俗时提到:“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镂金薄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又造华胜以相遗;登高赋诗。”其中的“登高赋诗”,显然是作为文人墨客的作者个人或相关群体经历的体现,而并非普遍流行的一般习俗活动。这种个体化的经验记述,在《东京梦华录》中尤有突出的表现: 冬至前三日,驾宿大庆殿……是夜内殿仪卫之外,又有裹锦缘小帽、锦络缝宽衫兵士,各执银裹头黑漆杖子,谓之“喝探”。兵士十余人作一队,聚首而立,凡十数队,各一名喝曰:“是与不是?”众曰:“是。”又曰:“是甚人?”众曰:“殿前都指挥使高俅。”更互喝叫不停。或如鸡叫。置警场于宜德门外,谓之“武严兵士”。 (《东京梦华录》卷十) 与该书大多概述性的文字不同,这段生动描写具有明显的个人特殊体验痕迹,尤其是在警卫口令中明确提及“高俅”的名字。实际上,综合全书来看,作者孟元老在述及各种民间习俗的时候,往往都是概括性的描述,而每当论及宫廷礼俗,却大都表现为对一个场面或一次特殊事件的记录,这或许同他对这些事件的了解不够有一定关系。如赵师侠在该书跋文中所指出的:“幽兰居士记录旧所经历为《梦华录》,其间事关宫禁典礼,得之传闻者,不无谬误,若市井游观,岁时物货,民风俗尚,则见闻习熟,皆得其真。与顷侍先大父与诸耆旧,亲承謦欬,校之此录,多有合处。” 相比之下,《梦粱录》对同类活动的描写,则更为概括,尤其是其中的“殿前都指挥使”,由《梦华录》中特指的“高俅”变成了泛指的“某某”: 更有裹绿小帽、服锦络缝宽衫兵士,十余人作一队,各执银裹头黑漆杖子,谓之“喝探兵士”,聚首而立,凡十数队。各队一名,喝曰:“是与不是?”众声答曰:“是。”又曰:“是甚人?”众声应曰:“殿前都指挥使某人。”及喝五使姓名,更互喝叫不停声。或作鸡鸣,是众人一同喝道。自初更至四更一点方止,此谓之“禁更”。前人诗咏之曰:“将军五使欲来时,停着更筹问‘是谁?’审得姓名端的了,齐声喝道不容迟。”又置警场于丽正门外,名为“武严兵士”,以画鼓画角二百,其角皆以彩帛如小旗脚结其上。 (《梦粱录》卷五) 《梦粱录》不仅对各种风俗的记述都极为概括,书中还引用了大量的诗词、谣谚和典籍等,对相关习俗进行综合的疏证。例如,“五日重午节……兼之诸宫观亦以经筒、符袋、灵符、卷轴、巧粽、夏橘等送馈贵宦之家。如市井看经道流,亦以分遗施主家。所谓经筒、符袋者,盖因《抱朴子》问辟五兵之道,以五月午日佩赤灵符挂心前,今以钗符佩带,即此意也。杭都风俗,自初一日至端午日……或士宦等家以生殊于午时书‘五月五日天中节,赤口白舌尽消灭’之句。此日采百草或修制药品,以为辟瘟疾等用,藏之果有灵验。杭城人不论大小之家,焚烧午香一月,不知出何文典。”(《梦粱录》卷三)对一些习俗,作者往往试图通过文献来解释其来源;有些习俗,无法清理出相应线索的,则说“不知出何文典”⑧。这使得该书已超出一地民俗志书的性质,更像一部综合的区域风俗考证著作。 “直陈其事”的客观记述方式,显然有益于加强书写的客观性和可信度,然而,即使是在《梦粱录》这样一部看似冷静描写和考证的著作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字里行间跃动的个人好恶,以及对故土人文的自豪与难以抑制的赞美之情: 自淳咸年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裹奇巾异服,三五为群,斗美夸丽,殊令人厌见,非复旧时淳朴矣。但杭城人皆笃高谊,若见外方人为人所欺,众必为之救解。或有新搬移来居止之人,则邻人争借动事,遗献汤茶,指引买卖之类,则见睦邻之义,又率钱物,安排酒食,以为之贺,谓之“暖房”。朔望茶水往来,至于吉凶等事,不特庆吊之礼不废,甚者出力与之扶持,亦睦邻之道,不可不知。 (《梦粱录》卷十八) 类似的情绪,在《东京梦华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凡百吉凶之家,人皆盈门,其正酒店户,见脚店三两次打酒,便敢借与三五百两银器。以至贫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银器供送。有连夜饮者,次日取之……其阔略大量,天下无之也。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之万数,不欲繁碎。”(《东京梦华录》卷五)特别是其中所谓“其阔略大量,天下无之也”,自豪与赞美,溢于言表。而由于这些著述总体的风格是客观化的描述和抽绎,因此,这种偶然的情感流露,显得既自然又格外真挚。 《东京梦华录》和《梦粱录》两书,又均有这样的特点:既记述皇宫官宦礼仪,又记述民间礼俗,二者在著述中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同作者过去的官宦人家身份的影响有关,客观上也体现了对文化规律的遵循,即一种文化传统往往是为民族内部所有成员共同遵守和传承,尽管其具体活动形式会有所差异。作为前朝遗民,这些作者通过记录作为前朝重要标志的皇室礼仪来表达对前朝的留恋,似乎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另一方面,对于皇宫种种礼仪的津津乐道,或多或少也体现了他们自高身份的心理——尽管成为了离乡背井的“遗民”,但他们曾经是有地位的人,熟知过去的上层礼仪。这对处于陌生异地、深怀乡愁的作者而言,不仅具有精神安慰的作用,也可能成为他们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与人际关系的资本。当然,尤为重要的是,它还具有通过上层阶级的活动来规范节序仪式的意义,也就是说,通过细致描写皇室的一系列活动,使有关时间规律的仪式化行为得到更为明确、更为强化的认识。 以上特征的存在,使得这些著述在表面客观、冷静的呈现当中,总是带有个人体验的色彩,带有或深或浅的主观情感的印记。就像有的文学评论者所指出的:“故乡的原型意象,情感的物化,如日月星辰、井泉山河、雨雪雷电、田园花木、门窗庭除、禽鸟牲畜、家具摆设、酒食酿器、稼禾炊烟、器乐歌舞乃至祭台墓冢等等,‘一箪食,一瓢饮’,一草一木,无不构成中国乡愁文学作品内容中的常态原型意象。”虽然没有直抒胸臆地言愁、言恨,但是一草一木总关情,在对故乡生活文化传统极力克制的描写和对象化的处理当中,乡愁与离散之情反而沉淀得更为深沉,更为隽永。 与故土的离散,为身为离散者的民俗志作者提供了一个在对比中反观自己家乡的不同视角,进而使家乡成为了一个“对象化”的存在,一个可以从一定距离之外加以观察、描述和表现的客体。这种对比的视角和相应的叙述策略,成为了中国历代民俗志所沿用的一种书写模式。在现代民俗学兴起之后,许多中国民俗学者自然而然地采用了以家乡民俗为研究对象的做法,并由此形成了这个学科中的一个长期而连贯的重要流派,究其根源,可以说,同古代民俗志中有关家乡书写的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①本文曾在台湾东华大学中国语文学系主办的“2014海峡两岸民俗暨民间文学学术研讨会”上宣读,衷心感谢论文评议人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叶涛研究员的精彩点评和给予的修改意见。 ②张叹凤:《中国乡愁文学研究》,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1年,第43—44页。 ③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见钟敬文著,董晓萍选编:《钟敬文文选》,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2页。 ④李道和:《民俗文学与民俗文献研究》,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8年,第198—201页。 ⑤张叹凤:《中国乡愁文学研究》,第43页。 ⑥张紫晨:《中国民俗学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185页。 ⑦萧放:《〈荆楚岁时记〉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2、154页。 ⑧在这里,作者似乎显示出一种偏见,即认为所有风俗皆产生于某一重要文献的影响,却忽略了不少文献实际上往往来自于对习俗的总结。标签:民俗论文; 乡愁论文; 东京梦华录论文; 梦粱录论文; 传统民俗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风俗文化论文; 民俗学论文; 文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