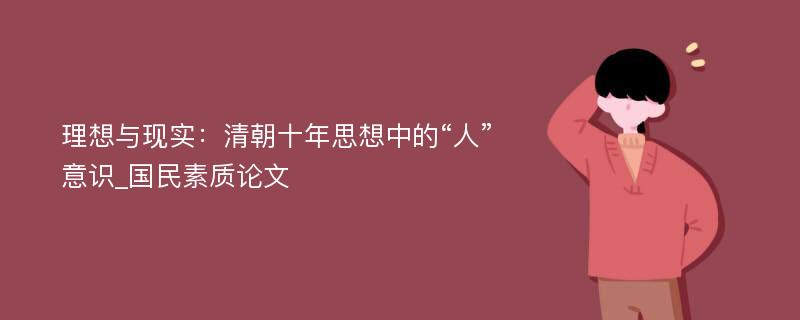
理想与现实:清季十年思想中的“民”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论文,现实论文,理想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关于晚清思想的研究中,很多人注意到“国家”意识的彰显①,而对“民”意识的兴起及其相关问题却很少研究。晚清最后十年,不仅“民权”、“民智”、“民力”等戊戌前后流行的名词继续风行,“民生”、“民族”、“平民”、“国民”等由“民”组合的词语也被广泛使用,一些富有影响力的报刊如《新民丛报》等更直接以“民”命名;当时中国各种思想各派主张,很少有不与“民”发生紧密联系的。若说“民”意识在清季十年处于思想论说的中心,或不为过。
基本上,晚清人多说“民权”而少言“民主”,然两皆外来观念,有时背后的外文原词还是相同的。沟口雄三和黄克武曾着力于这两个词的当时涵义和思想渊源②。徐宗勉等所著《近代中国对民主的追求》主要从政治体制考察民主在近代中国的进展③,成为后来不少研究者的共同倾向。熊月之则把时代思潮和人物思想相结合,进一步叙述了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发生、发展历程,明确提出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即“由爱国而民主的特殊道路,使得近代民主思想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特点”。④
对于“民”的认识是思考“主”的基础,“民”意识与民主思想的发生、发展关系密切。以前不少相关研究侧重从概念上区分传统的“民本”与外来的“民主”,其中隐含的以近代西方“民主”为切入视角的特点,容易使一些与西方“民主”不一致或不“接轨”的看法成为视而不见的材料,实际被排斥于史学言说之外。而这些看法很可能恰好说明了中西差异,提示出中国走向“民主”的独特路径。
沈松侨的《国权与民权:晚清的“国民”论述,1895—1911》⑤一文是近年出现的力作,他从实质和形式两个层面考察“国民”概念的形成过程及主要内涵,对“国民”在中西方不同语境中概念分歧的分析和对“国民与国家”关系的讨论,都很见功力。但此文的理论色彩较强,偶尔不免显出“思想”掩盖“人”的倾向。
尽管既有的相关研究数量已不少,一个较全面的晚清“民”意识兴起的动态样貌仍有待重建。这首先需要沿着当时思想脉络的展开,真正侧重“民”意识这一问题本身进行更深入的考察,而不一定要沿着以政治倾向为标准区分出来的派别进行追索。本文仅据习见的当时报刊材料简略梳理“民”意识兴起过程中呈现的理想和现实两面的冲突,以及时人对此的因应主张,希望能多少推进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对晚清人而言,“民”主要指涉包括士农工商的“四民”,且往往是与“官”对应的基本也就是后人称为“被统治者”那个广大的群体。不过,在这个梁启超所谓“过渡时代”里⑥,各种观念主张也都呈现一种“过渡”的状态:通常涵义不很确定,不同的人使用同一名词,其所指谓可能相差很远;而那些具有“新兴”意味的观念,更因其思想资源的差别而饱含歧异。在很大程度上,“民”或“民意识”也具有这样的特点:它既是传统的“以民为本”观念中那个民,也是新引进的“公民”或“国民”观念中的民;两相比较,后者显然有着更多后天的或附加的成分。而时人在表述时通常并不明言其究竟何所指,他们对这类新旧涵义兼具的词汇也未必先区分而后使用,有时根本就混用之。这也说明,尽管“民”的涵义正处于扩张之中,对当时人来说,其在具体的上下文里仍是一个不必特别界定就可以让人明白的词汇。
在这样的情形下,如果像一些“思想史”学者那样先界定出一个边界清晰的概念,再根据这特定的概念去选择材料进行论述,虽然可能看上去清楚明晰,也许真可能如陈寅恪所说的那样,“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⑦。一个由后人界定出来的是什么、不是什么的“民”意识,可能最不接受的是被我们“研究”的当事人。或许研究历史应该反过来,考察当事人当下究竟关心什么,他们真正希望表述什么,以及他们实际表述了什么。⑧ 本文基本遵循时人的表述习惯,仅在不区分或界定便可能混淆时予以适当说明。
一、“民”在清季言论中的地位提升
按照近代被频繁征引的顾炎武的意见,“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而“保天下”则“匹夫之贱与有责”。庚子之后,中国被“瓜分”的可能性日增,时人在口说“亡国”之时,心中想到的恐怕是顾氏笔下“亡天下”的情形。在时局的迫压下,此前那种主要依赖政府和上层社会的“保国”方式越来越被质疑,而以前不被看好的中下层社会渐受看重,“民”的地位得到大幅提升,“民”在国家中所处的地位也受到特别关注。这一倾向既受到甲午后“开民智、兴民权”努力的推动,也与西方近代“国家”观念的输入直接相关。
在这一时期西方国家思想的传播中,最有影响的是梁启超⑨ 。1901年,他发表了《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从十一个方面对“中国旧思想”和“欧洲新思想”进行了比较,认为中国旧思想主张君主为国家之主体,国家与人民全然分离,人民之盛衰与国家之盛衰无关;而欧洲新思想则主张人民为国家之主体,国家与人民一体,人民之盛衰与国家之盛衰如影随形。⑩ 人民在国家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已经得到明确的关注,并开始作为在思想上区分中西新旧的标准,国家非一人一姓、一朝一代之私产而是人人有之的观念得到广泛的认同。
1901年5月, 《国民报》创刊号发表题为《原国》的文章说:国家譬如一个公司,人民是股东,君主是会计,官吏是司事,“聚股东、会计、司事各人而谓之公司,聚人民、君主、官吏各部而谓之国,其义一也”。国家人人有之,人人对国有应尽之义务和应得之权利,任何人不能有专制之权。(11) 稍后欧榘甲在《新广东》中也说:“中国者四万万人之公司也,四万万人者中国之股东也,朝廷者中国股东之掌柜也。凡生于中国之一人,即有中国之一份,中国之事,皆其身内之事,非在身外之事,无所不当亲理,无所不当干涉。”(12)
与“公司”和“股东”关系相似但在意义上更进一层的,是从“主人”和“产业”的关系上去看待人民和国家关系。1903年《江苏》杂志的一篇文章提出:“人民为国家之主人,国家为人民之产业。”“人民与国家有密接之关系,亡则人民与国家俱亡,存则人民与国家俱存,从未有国家亡而人民存,人民与国家离为二体者。”(13)
无论是“公司”与“股东”关系的比喻,还是“主人”和“产业”的表述,都意在强调人民是国家的“主体”,对“国家”具有所有权,对“国家”事务具有支配权,这与中国传统中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基础上所强调的“民贵君轻”、“民为邦本”、“载舟覆舟”等思想,有了大不相同的意味。
关键是作为“主人”的人民决定着作为“产业”的国家的兴衰存亡。有人提出,中国之所以面临“亡国”危机,主要原因是国家与人民相分离,因“主人”缺位而导致“产业”衰败。能不能改变当下的窘境,取决于人民能否切实履行作为国家“主人”的政治责任:“吾国民以为不能行,斯不能行矣,吾国民以为能行,断无不能行者,能与不能,全属诸我。”(14)
在国家形势危若累卵的情况下,把国家兴亡寄于人民,以为“国民欲其亡则亡,欲其兴则兴”的思想被反复加以强调(15),“亡国”的忧患更促进了“民”的地位提升。杨度就说:“中国之价值,必由我国民自评之而自定之。如以为犹可存也,则中国斯存矣;若以为将遂亡也,则中国斯亡矣。”(16) 《湖北学生界》的一篇文章也说:“吾以为我国民而听其亡也,则虽合地球之人类欲存我而不可得也;我国民而能自强也,则虽合地球之人类欲亡我而亦不可得也。”若“举国之人皆有‘我即国,国即我’之理想,深入于脑中,牢固而不可拔”,亡国的可能性就不大了。(17)
把国家兴亡寄于人民,也隐喻着相当一些士人的共识,即政府在救亡方面已难以依赖。国家危机通常是政府的责任,而清政府在一系列问题的处置上给人留下了轻视国民、看重外人的印象。连思想相对“温和”的黄遵宪也批评政府推行的改革是“徒以之媚外人而骗吾民”(18),而激进者就直接攻击清政府“为外族作伥,制吾人死命”(19)。张锺瑞批评政府说:“欲言对外,彼亦干涉;欲言治内,彼亦限制”,“若欲自振,则即非破坏此非平民的政府不为功”。(20)
产生这种思想的背景是,门户开放以后,外国资本大量进入中国,民间的工商业常感觉受到政府和官吏的掣肘,而外国资本反而能借中国官力以压制中国工商业。清政府实行新政的许多“富强”措施都不能不借外债,但这也成为反对者攻击的口实。曾鲲化就说:“凡官办铁路,无一不与外人有密切之因缘,即无一不得丧权失利之恶果。”(21) 苏杭甬铁路之争更被诠释为“政府强人民以借外债,人民保国权以拒外款”。时人明言:“今日时局,我国民实立于两敌之间:外人挟政府以制我国民,政府复挟外人以制我国民。我国民处此二敌,又何所挟哉?一言以蔽之曰:以国民挟国民而已。”(22)
外人、政府和国民的三重关系体现出权势结构的转移,即外国势力已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一部分,而政府与人民不但未能“一致对外”,反被视为既并列而又对立的力量。许多流传的话不一定有确切的出处,有的甚至可能是出自革命党方面的有意宣传,但仍能反映相当一部分人的心态。当时社会上流传着“百姓怕官府,洋人怕百姓,官府怕洋人”的说法,多少表现出对三方相互制约关系的一种认识。庚子后流传的慈禧太后所谓“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及“与其与奴隶,不如赠朋友”的话。(23) 更使得一些人意识到,外人之所以能够挟制国人,正是因为有此“卖国”政府在。
官府由官吏组成,因此,官吏形象的恶化,也意味着官府形象的恶化。在时人眼中,整个官僚群体显得守旧落伍,无所作为,唯利是图,不论是维新派,还是守旧派,中国的官员都是“奴隶”,只是投靠的“主人”不同,并无实质性差异。官僚已被整体地负面化,显然无法承担救国的责任,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不能依赖政府。有人提出,若国民“必恃今日之政府官吏以图存”,则中国必亡;若国民“知今日之政府官吏,为列强所擒之纵之威胁之具,必不足恃以图存”,则中国不至于亡。(24)
梁启超在1903年指出,庚子后,“国民犹喁喁然企踵拭目,若不胜其望治之心者”,然而结果是失望。他语重心长地对国民说:“我国民依赖政府之恶梦,其醒也未!我国民放弃责任之孽报,其知也未!”国民就像“孤军被陷于重围,非人自为战,不足以保性命”。自今以往,不能再“想望政府、崇拜政府、责备政府、怨詈政府”,必须依靠自己,“求所以自立于剧烈天演界之道”。(25) 在清政府自身已可能是亡国因素的情形下,救亡图存只能在政府之外另辟蹊径,其责任相应地落到国民的肩上。
同时,“民”的地位提升也受到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20世纪既被认为是一个“多数势力发生之时代”(26),则“保国”不再是少数精英的职责,而成为多数人的责任。为因应国际困局,需要调动和发挥多数人的作用。在这种思路的刺激下,虽然时人议论中仍不乏对“志士”、“英雄”的呼唤,但总的来看,对英雄事业的推崇逐渐被对民众作用的讴歌所取代。杨度引日本人的话说,今日虽有汉高祖、明太祖,也不能以数十万乌合之众而取天下。故他以为,“若犹欲以历史上数千年之所谓英雄事业,行于今日之世界者,非特其理不可也,吾知其势亦必有所不能”。盖“一二霸者之雄心,何足以敌亿万民族之涨力也”。(27)
与“民”的地位提升相伴随,时人对社会上层和中下层群体的认知也出现变化。当时较有影响的上层读书人,不论是在朝还是在野,不论趋新还是守旧,不论在道德方面还是功业方面,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质疑和批判,时人对“士”的失望有非常明确的表述。有意思的是,作出这类表述的仍是读书人本身。在上层群体无可望的情况下,原来处于中下层的群体逐渐受到时人的关注,这些读书人开始寄希望于下层百姓。像宋恕这样的多愁善感之士也慨叹“士大夫之品评无据,远不如种田挑担人之有真是非”;他甚至说出“由贫民来定道统”这样的惊人之语。(28)
上层社会甚至不再被视为领导人才的摇篮,新政治领袖的产生更多被寄望于下层社会。《国风报》的一篇文章说:“细审中国之国情,其门地愈高者,愈难于出人才;其门地愈低者,愈易于出人才。故今后政治家之发生,必为平民的而非阀阅的。”尽管还有“寡识之士”欲于阀阅中求政党之领袖,作者却认为只能求之于平民社会,盖今日“中国而无政治家之出现也则已,苟其有之,必为平民的之政治家”也。(29)
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思想很快给中国社会变革的认识注入了新的理念。梁启超指出:若“一国之民,举其前此之现象而尽变尽革之”,则“其所关系者非在一事一物一姓一人”,与君主没有多少关系。与以往相比,现时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不是“王朝革命”,而是“国民变革”。(30)
在革命思潮兴起后,以革命手段推动社会改造不仅被认为是国民的分内之事,而且非国民莫属。邹容明确提出:“革命者,国民之天职也,其根柢原于国民,因于国民,而非一二人所得而私有也。”(31) 汪精卫也把革命党定位为“民党”,指出“革命之主义,非党人所能造也,由平民所身受之疾苦而发生者也”。(32) 正是人民作为国家主人这一思想的确立,使当时的中国革命被定格为既以国民为目标又以国民为动力的国民革命。对思考革命的激进者而言,更是只能依靠下层民众。朱执信就说:历史上“中国革命运动之力不出于豪右之族”;今后革命“亦必不出于豪右,而出于细民”。(33) 林懈也指出,历史上办大事的豪杰都是穷苦出身,“倘使他们一个个都是富家翁,却那里肯出来干这些杀头的事体呢”?(34)
1905年,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说自己倡导的“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其他的各种学说“皆此三者之充满发挥而旁及者耳。”(35) 事实上,不只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国的各种思想各派主张,很少有不与“民”发生紧密联系的。这一点,只需看当时由“民”组合而成的词语被广泛使用的程度即可知一斑。因此,说“民”意识的凸显在20世纪前十年呈现了一种时代性的关注转移,或不为过。
“民”在清季言论中的地位提升,意味着它对于国家所担负的历史责任较前大大加重了。时人想借制度上的设计和社会生活中的倡导,通过对政府和民众、个体和群体、社会上层和下层等关系进行调整,就能调动和发挥大多数国民的作用,兴民权以振国权,合民力以成国力,实现国家的救亡图存。然而,在对“民”寄予厚望之后,回到中国的现实,不少人对现实中国国民能否承担这种责任表现出很大的怀疑。虽然理论上的设计一度带给他们巨大的鼓舞,但现实状况又使曾经抱有的热烈期盼大打折扣,积极与消极、欢欣和失落两种情绪形于言表。
二、并不理想的现实之民
“民”在晚清思想言论中出现明显的地位提升,受到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和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但更主要是在时局刺激之下,思想界围绕“保国”目标,对中国政治力量和社会阶层重新加以评估的产物。因此,“民”的地位提升,既是就它自身在不同时代的地位作纵向比较而言,又是和同时代其他政治力量和社会群体横向对比的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虽然对不同群体的社会评价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关注重心的下移,但在思想言论中,“民”常具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民”包容了当时的士农工商等各个社会阶层,狭义的“民”则把官、甚至士等某些社会阶层排斥在外。梁启超曾对当局者说:“狭义言之,则诸君官也,民之对待也”;而“以广义言之,则诸君亦国民之一分子也”。(36) 虽然“民”本身并不能等同于得到肯定性评价较多的中下层社会群体,但一般人使用这一概念却越来越接近于社会中下层而疏远于社会上层。
然而,趋新思想家很快发现,他们所期望的“国民”难觅踪影,而“奴隶”却在在皆是,国人不论上下贵贱在所难免。“国民”和“奴隶”的对立是20世纪初年一个非常流行的对比性分析,两者呈现一种非此即彼的状态。《国民报》的一篇文章即认为,中国问题不是官僚或某一社会群体带有“奴隶”性,而是全体国人“不论上下,不论贵贱,其不为奴隶者盖鲜。试观所谓士、所谓农、所谓工、所谓商、所谓官吏,有如吾所谓国民者乎”?若“举一国之人而无一不为奴隶,即举一国之人而无一可为国民”。(37)
“国民”和“奴隶”的差别首先表现在与国家的关联上,如《浙江潮》上一篇文章所说:“凡立于一国之下,而与国家关系休戚者,则曰国民;立于一国下,而与国无关系休戚者,则曰奴隶。”(38) 《国民报》也说:“奴隶之所顾者为一人一家之事,国民之所顾者为同国同种之事。奴隶之遇事也,有畏葸苟且之心,故在家则诿之父兄,在朝则诿之君相,是率一国之人而无任事者也。国民之遇事也,有勇往冒险之心,故一国之事即一人之事,一人之事即一国之事,是率一国之人而皆任事者也。”权利和责任是国民和国家发生联系的纽带:“奴隶无权利,而国民有权利;奴隶无责任,而国民有责任。”所谓权利,主要是“参预国政之权利”;而所谓责任,即体现“一人之事即一国之事”上面。(39)
时人认为,国民要行使对于国家的权利,履行对于国家的责任,从个体方面讲,必须具备独立和自觉的性质。邹容就明言:“国民独立,奴隶服从。”他认为,国民者,“有自治之才力,有独立之性质,有参政之公权,有自由之幸福,无论所执何业,而皆得为完全无缺之人”。而奴隶则“既无自治之力,亦无独立之心,举凡饮食男女,衣服居处,莫不待命于主人,而天赋之人权,应享之幸福,亦莫不奉之主人之手”。(40)
当然,这两个非此即彼互相对立的概念主要是精神层面的,用时人的话说,即奴隶根性和国民精神的对立。所谓举国之人皆“奴隶”也更多体现于此。这样的整体负面特性,下层社会自不能免。且这种“奴隶”性不仅表现在政治层面,如沈松侨所指出的,民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消极被动”地位的状况,“已内化而为一般民众的意识结构与行为模式”。(41) 时人注意到,有些国人对“平等、自由、民权”等理念不但不响应,且“仇之攻之尤甚于民贼独夫”。(42) 显然,在对“民”寄于厚望之后,回到中国的现实,不少人发现状况并不乐观。
一位署名“辕孙”的人便说:其实“专制君主之压制国民不足畏,腐败官吏之鱼肉国民不足畏,所可畏者国民之奴隶根性耳。奴隶之劣性不去,则必以逼勒我赋税以供专制君主之快乐为天职,朘削我膏脂以充腐败官吏之私囊为义务。此心不变,则其国永亡”(43)。《国民报》上题为《原国》的文章论“人人对国有应尽之义务”说:“既为一国之人,即无所逃于一国之中。”从上面“抑人民之自由,抑人民之平等,而使之流离困苦,不得其所者”是“贼国”;一般人“任一国之陆沈,而理乱不知,黜陟不闻”则是“忘国”;两者性质相类,“忘国贼国厥罪惟均,皆国之蠹也”。(44) 换言之,中国的危亡固然可能因政府无能,但国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国民“奴隶”说所反映的对民众素质的担忧在20世纪最初几年相当普遍。那时距甲午后提出“开民智”还不到十年,而“开民智”本身大体带有言甚于行的晚清共同特点;即使付诸行动而确实有效,时间也还太短,故“民”之素质“不高”应是正常现象。(45) 本来“开民智”的提倡已提示着“民智”不适应时代要求而需提高之意,当时很少有人对此产生疑问,反倒是一般认为守旧的叶德辉站在人民立场质问“开民智”的提法说:“试问今日之民,谁肯居于不智?又试问不智之民,何必更伸其权?”(46) 叶氏的后一问实点出这些启蒙者的尴尬:被时人寄予厚望、赋予重任的,正是同样被他们视为近于“奴隶”的“不智之民”!
此前很多人以为中国对外竞争失败是技不如人,对国人素质的关注引申出新的看法,即中国的问题不仅是“技不如人”,而且是“人不如人”;则中外竞争不仅输在“对外”一面,而且输在“自我”一面。如严复所说,中国若仅在形式上模仿西方,“有火器者遂能战乎?有警察者遂能理乎?”(47) 因此, 提高“民”之素质以造成“新民”,才是行动的方向。梁启超说:人们动曰某甲误国,某乙殃民,政府失机,官吏溺职,虽未必不是事实,但政府成于国民,官吏出自民间,“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政府官吏,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他将政府和官吏的负面表现归结于“民”的整体素质不高,认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48)
从“开民智”到“新民”的思路是延续的,表明尽管中国老百姓素质不理想,但“国民”是可以培养的。但是这里有一个明显的矛盾,政府已被认为不能救亡,包括士人在内的上层社会也不可靠,那谁来“开民智”?谁来“新民”?梁启超虽曾明言“新民云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则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但他在同一文中也说,“中国群治不进,由人民不顾公益使然也。人民不顾公益,由自居于奴隶盗贼使然也”。虽然后者是“由霸者私天下为一姓之产而奴隶盗贼吾民使然”。(49) 但梁氏大致仍赞同当时流行的国人“奴隶”说。从常规的逻辑看,以素质近于“奴隶”的国人进行自我教育,其“自新”效果恐难期待。若“民”之素质有待外在力量来提高,则不仅返回到“开民智”主张背后隐伏着的精英倾向,也提出了进一步的问题:谁来承担这个责任?
三、新民抑或新政
时人心目中亡国亡天下的危险已很紧迫,而政府和上层社会又不可靠,需要承担国之兴亡责任的一般民众状况也不理想。面临这样一种“民”的现实,解决之道似乎只能是民的提高;对一些人而言,这可能意味着要以士的提高为前提;同时,不少人开始重新发现政府的作用,认为政府的改良也不失为一法;还有人认为,只有以革命造新政府来一举解决所有困惑。(50)
在严复版的“天演”观念流行之后,人们最担心的是中国在世界竞争中的胜败,及其可怕的后果——亡国。《东方杂志》一篇文章说:所谓“国民”,是能以个人之力“成立国家,使其群日竞争于优胜劣败之场,而不为天行所淘汰耳。能如是者,是之谓民,是之谓国;不能如是者,不足谓之民,即不得复名为国”(51)。既然国与民的关联如此密不可分,民的素质直接影响到国的前途,救国也就不仅是“对外”的问题,首先涉及的是“内部”的社会变革。而对国民状况的不同认识,又导致了在选择中国社会改造方案上的分歧。
关于中国的改造从何处下手,实际上存在着首先改造民众和首先改造政府两个思路。后者虽包括改良和革命(即更换政府)两种非常对立的政治主张,但其共同点在于都认为民众暂时难以改变,致力于政府是更为快捷的取径。若套用梁启超“新民”的说法和思路,这类主张也可以名为“新政”。对下层民众素质的不满意使得许多人重新思考政府的作用,所谓“立宪派”和“革命派”在这一点上恰有其共性。“新政”主张将通常对立的改良和革命取向涵盖在内,这样一种异中有同的思想现象非常值得注意。
梁启超的《新民说》发表后,署名“飞生”者即对其新民以新社会新政府新国家的主张表示质疑。飞生认为,国民性质或出于天然,或受自地理,或源于历史的遗传影响,养成于千百年,绝非通过十年、数十年的改革所能奏效。“故自理论上言,则有新民固何患无新政府;而自事实上言,则必有新政府而后可得新民也”。因为政府是人民的代表,“代表其群者必其贤智之过于其群者也。贤者教不贤,智者教愚,则政府者固有新民之天职在”。这样,问题在于政府是否“贤且智”。若答案是肯定的,则政府自可承担教民之责;若政府不能担任其天职,就应考虑“易而置之”。如果政府和人民双方都需要提高,致力于改变“少数短年易变之政府”在效能上仍胜于改新“多数积重之民俗”。(52)
署名“竞盦”者提出,政体与国民是相互依赖、互为因果的关系:“政与民互为因亦互为果,政因民而日修,民亦因政而日化。政体之善者,必适合国民之程度,而又能谋将来之发达,使民日进于文明。”虽说互为因果,这里明显侧重的是政体对国民的作用。而署名“汉驹”者认为,为培养人民的政治能力,须使之逐渐熟悉政治上的操练,而要有这方面的经验,“非铸成一与人民至切近之政治模范,以为人民观念之物,以为人民操练经验之地不为功”。应建设一新政府,以为“开浚人民之政治思想,培养人民之政治智识,习练人民之政治能力之一大机关”。而署名“铎人”者论改革的次序说,“以数千年因循之古国,而欲振起其自觉心,固莫如使之耳目一新。新吾民,固莫如有新政府”。盖“必先造新政府,然后可以行新制度,断未有求旧政府而可以立新制度者”。(53)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这几位大体是主张更换政府即倾向于革命的。但类似思想同样存在于主张改良、立宪者,署名“崇有”者就认为,中国的“乡僻愚民,随地皆是”,其“勇于私斗,怯于公战,虽为驭之不得其道,而求其大原因,则在人民无国家思想,故视胜败荣辱与己若毫不相涉。夫民无国家思想,非民之罪,政体实为之”。他引孟德斯鸠关于“不使人民参预政事,则人民与国漠不相关”的话为据,提出“国家欲得民之死力,非授以政权不可”。具体落实在“施以普及教育之道,约以设立议院之期”。(54)
而政闻社的宣言更明确说:今日之恶果皆政府造成,只要改造政府,则恶根拔而恶果便会一一消除。该宣言一方面提出国民必须具备三种资格然后能实行立宪政治(即“勿漠视政治,而常引为己任”;“对于政治之适否,而有判断之常识”;“具足政治上之能力,常能自起而当其冲”),另一方面也说,“必先建设立宪政治,然后国民此三种资格乃能进步”。(55) 该文的基本立意是以立宪改造政府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似乎把先改造国民和先改造政府两种思路都包括在内。类此把一些看似冲突甚或对立的观念包容在一起是当时较普遍的现象,上述这些看重政府作用者并非都不看重民的作用,有些根本就是前引民意识兴起的表述者。一方面,这些杂志论说多为仓促完成,充满情绪性;另一方面,他们自己或并未觉得这些观念是相互矛盾的,有时反而看作一种互补的关系。这多少反映出时人希望一举解决所有问题的紧张心态。
在这样的心态下,一些猛烈抨击专制政体之人,仍特别看重作为一种手段的“专制”的有效性。今日译为“义务教育”之词,当年更多译为“强迫教育”。这不仅是外文字义的理解问题,当时人就是多从“强迫”的中文角度看问题。如署名“云窝”的作者就说:“专制政体不容于今世界,而教育则欧美列强悉用强迫主义者,何以故?非此不能使全体国民人人尽受教育,而均一其进化之程度也。吾祖国民智未开,其用强迫主义也当尤重。”(56) 他们不仅从字面上看重“强迫”的必要,更因此看到“专制”的效能。
急于“见效”是当时的共同倾向,署名“穀生”者就怀疑“立宪而后中国可兴”的可能性,一方面“今之国民,有立宪资格者,能有几人?无立宪国民,又将谁与立宪”?而列强侵略日亟,也未必给中国时间以“从容立宪”。故他认为只有“中国兴而后可立宪”。他既斥责中国自秦以来,只有寡人专制之政而无教,所谓教都只是政体的附庸;同时又主张利用这既存的权势,“即专制之政教,而因以为功。其最初之术,则以专制之力,行强迫教育之制,其次若工业、若路矿、若官制、若服色,其不适于生存者,一以专制之力划绝之,其有合于强国者,一以专制之力提倡之。至若民风习俗,万不能以专制政令易之者,则以专制之教间接而行之”。这样“自上而下,雷厉风行,不出十年,中国其庶乎可立宪矣”。(57)
榖生提到的“国民资格”是那时一个重要的争议性问题,很多不同政治主张都建立在对此问题的认知和判断之上。多数人都认识到开民智、培民德的“新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中国所面临的外部危机不允许一个长期持续的努力。为了效率,尽管“民”的地位被充分认同,但实际操作似又不能不围绕“政”展开。《外交报》一篇文章说:“欲求治其病之方,当分治本与治标二者。以理论之,固须治本。然开民智、培民德、殖实业,非数十年不可。倘药未奏功,而其人已死,可奈何?”(58) 《外交报》在当时的整体倾向是偏于温和改良的,但也已感到时不我待, 其余人的急迫就更可想而知了。
梁启超曾经一度也倾向革命,他那时认为:中国人“居于奴隶盗贼,由霸者私天下为一姓之产而奴隶盗贼吾民使然”。如果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就有利于社会改造和增进“群治”。立宪国之政党政治也未必皆秉公心公德而不计私名私利,但“专制国之求势利者,则媚于一人;立宪国之求势利者,则媚于庶人”。政党政治分在野党与在朝党,两者都要努力使“民悦”而得多数,最后得益的仍是“群治”。(59) 这样,为了实现立宪救国,即使破坏也在所不惜。
而黄遵宪的看法则不同,他概括自己和梁启超主张的异同说:“公以为由君权而民政,一度之破坏终不可免,与其迟发而祸大,不如速发而祸小。仆以为由野蛮而文明,世界之进步,必积渐而至。实不能躐等而进、一蹴而几。”黄认为,中国人自古以来习惯于受治于人,对于人群不知有义务,对于政府不知有权利,毫无政治思想可言,不仅不能适应分权授政,甚至会出死力抗拒改革。“以如此至愚极陋之民”,难望其做新民以新中国。只有在人人能独立能自治并能群治以后才谈得上开议院,故中国改为立宪政体的进程只能以渐进的、自上而下的方式推进。(60)
梁启超在1903年访美之后,对国民资格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伯伦知理和波伦哈克关于共和政体基础的论说给他以极大的震撼,梁氏坦言:醉心共和政体有年,“今读伯、波两博士之所论,不禁冷水浇背,一旦尽失所据,皇皇然不知何途之从而可也。如两博士所述,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我同胞虽一不具,且历史上遗传性习,适与彼成反比例,此吾党所不能为讳者也。”若中国一定要实行共和,“无论其行而不至也,即至矣”,也可能像法国或南美诸国一样。这使他对在中国实行共和制产生了极大的疑虑,思想上有了根本性的转变。(61)
亓冰峰已注意到,梁启超类似“冷水浇背,一旦尽失所据,皇皇然不知何途之从而可”的说法有两次,前一次是他在《三十自述》中回忆初见康有为,“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师子吼”,当时他也感到“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62) 两次措辞的相类很能提示梁氏这一次思想转变有多么彻底,而最基本的一点,恰是伯、波两博士所述国民应有之资格,他的中国同胞不仅一样不具,且与之相反。
在思想大变之后,曾经对国民不失希望的梁启超逐渐靠近了对国民不抱希望的黄遵宪,转而批评革命主张,且其口吻也与黄批驳他自己的非常相似。梁启超曾叹息道:“夫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是多数政体之总称也,而中国之多数、大多数、最大多数如是如是,故吾今若采多数政体,是无以异于自杀其国也。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吾今其毋眩空华,吾今其勿圆好梦。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63) 他后来回顾说,当初办《新民丛报》时,“承团匪之后,政府创痍既复,故态旋萌,耳目所接,皆增愤慨。故报中论调日趋激烈。壬寅秋间,同时复办一《新小说报》,专欲鼓吹革命。鄙人感情之昂,以彼时为最矣”。后见“留学界及内地学校,因革命思想传播之故,频闹风潮”;又见“无限制之自由平等说,流弊无穷。惴惴然惧又默察人民程度,增进非易。恐秩序一破之后,青黄不接,暴民踵兴,虽提倡革命诸贤,亦苦于收拾”;加以外国威胁未减,“恐事机一发,为人劫持,或至亡国”,“于是极端之破坏不敢主张矣”。(64)
这部分也是康有为的主张,康氏本认为,欧美各国“法至美密,而势至富强者何哉?皆以民为国故也。人人有议政之权,人人有忧国之责,故命之曰公民”。反观中国,“乃以四万万人之大国,无一人有国家之责任者”。这正是中外胜负强弱之基础,“故有公民者强,无公民者弱,有公民虽败而能存,无公民者经败而即亡”。所以中国要变法,“第一当立公民”。(65) 稍后他反对革命,仍以为中国闾巷小民自古至今,不过“但求饱食暖衣而已”,其“苟不致饥寒交迫,穷极无赖,即断不生作乱之思想。至于何者为自由,何者为不自由,彼初不知之”。故以自由之说导中国细民革命,就像给猴子穿衣服一样无益。(66)
章太炎注意到康氏的理论基础是中国人程度不够,他反驳说:“长素以为,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革命以后,必将日寻干戈,偷生不暇,何能变法救民,整顿内治。夫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之民,不可革命,而独可立宪,此又何也?”但若以此反驳,则“吾曰不可立宪,长素犹曰不可革命”的基础并未改变。所以他主张“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佗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盖“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而亦由竞争以生此智慧”;用今日的话说,人民可以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只要“以合众共和结人心”,革命“事成之后,必为民主”。故“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并非只能破坏,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67)
类似在游泳中学习游泳的主张渐为人采纳而推广,包括提倡立宪之人也有类似的设想。有署名“觉民”者说,实行宪政必须全国人民具有政治知识和自治能力,但以中国所面临的岌岌可危的对外环境,“若必待吾国民具有立宪之资格,而后始举行宪政,恐彼其时中国之名词,已不复存于世间,而为历史上之古迹矣”。综合民智幼稚、民力绵薄的实情和宪政不能须臾缓的形势,他主张由政府分权,“诚心立宪”,实行“和平之改革”;与此同时,以教育的方式来“培养而助长”国民的知识与能力,“数年以后,度不难及立宪国民之程度”。(68)
当然,也有人恰因中国人民没有立宪资格而主张革命,他说,“立宪则必以人人能守自治之法律,人人能有担任宪政之资格”,今人“以数千年遗下懦弱疲玩之社会性质,俯首屏息于专制政体之下”,欲其自动勃焉而兴“以进于光明伟大立宪国之国民,吾恐迟之十年数十年后,仍不能睹效于万一,而中国之亡,已亟不能待”。这位作者的时不我待心态与前者一样,但方针则相反,他主张不如由“一聪明睿知之大人”率领“数千百铮铮之民党”实行革命,“及大功告成,天下已定”,而后逐步实行共和主义之政策。(69)
不论中国人是否能在实行共和中养成共和国民资格,双方关于中国之民的素质不高、尚不具“国民资格”一点还是有相当程度的共识。且如前所述,尽管主张革命和立宪的双方存在着实行革命推翻现政府与依赖现政府推进改革的分歧,但首先改造政府的思路既存在于主张立宪的群体之中,也存在于主张革命的群体之中,超越了政治目标的分野。进而言之,把“民”视为国家兴衰存亡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应该由此实现国家的救亡图存,更是较多人分享的共识。当时思想界的各派主张,都可在此一大的路径下找到各自的着力点。就此而言,晚清思想史的研究,尚存在着一条超出以政治区分派别的研究路向。对时人心目中存在的派别之分当然要予以充分的尊重,但也要重视派别之间和派别之内观念主张的多歧性,就各人的具体观念主张本身进行探讨,不必非要确定立言者属于什么派别。
其实革命和立宪论争双方并非处于绝对对立的位置,汪东当时就说:“革命与立宪,要非绝对的名词也。夫立宪为专制改良的政体,而革命者,即所以求此政体之具也。求共和立宪以革命,求君主立宪亦以革命。”(70) 沈松侨近年经过认真考察后也说,立宪和革命“两派人士,取径固有参差,策略不无轩轾,原其本心,要皆以塑造深具权利、义务观念,享受自由、平等,并能积极参与国家政治事务之中国新‘国民’为旨归。”(71)
有上述共同点当然不排除双方存在巨大而明显的分歧这一基本事实。反对立宪者以“民”为依据攻击主张立宪者,主张君主者以“民”为依据攻击主张共和者,有时此“民”不同于彼“民”,相关的思想论争呈现为一幅“民”与“民”相争战的图画。这才使得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手段和改造社会的“终极”力量而寄予厚望的“民”本身成为新的有待于解决的问题。
实际上,感觉到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是清季相对普遍的现象,梁启超1901年论康有为的“哲学”时,便有一节的题目是“理想与现实之调和及其进步之次第”。他发现,康有为的很多理想“与现在之实际”呈现“悉相冲突”的状态,而康氏则以“《春秋》三世,可以同时并行”的方式来解决。也就是将原来依时间顺序展开的据乱、升平和太平三世转化到同一时段的空间之中,且允许其并存:“或此地据乱,而彼地升平;或此事升平,而彼事太平;义取渐进,更无冲突。”这是否真为康有为的思想且不论,但它的确体现出时人希望在各种极其复杂相互纠缠的冲突因素中寻求某种解决的愿望。(72)
在“民”意识兴起的同时,“民”与“国”的现实都充满了各式各样必须面对又难以解决的问题,即使对于先造成新国民还是先造成新政府这一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同一个人的回答有此一时彼一时的现象,甚至同一个人对同一个问题上的看法表现出此一方面不同于彼一方面的状况,形成了一种思想的纠结徘徊。这反映出在社会变革万端待举、千头万绪的情况下,时人从不同的关注出发提出的各种救亡之术既互为条件又互相掩盖,是晚清思想中非常值得注意的特点。
内外交困的现实和纠结往复的复杂因素不断加重着时人精神的苦闷和心理的焦灼,而寻求毕其功于一役、实现彻底解决的意识日益强烈,对中国改造问题的态度也渐趋激烈。梁启超在1903年访美后已倾向于“调适思想”,希望更能针对中国的现实而思考因应之方策。(73) 但已完全不赞成革命的他在辛亥革命前夕也不能不承认:“在今日之中国而持革命论,诚不能自完其说;在今日之中国而持非革命论,其不能自完其说抑更甚。”(74) 不赞成而又找不到足够的理由反驳,恰折射出那一时期积重难返的中国社会陷入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深刻困境。
可以说,清季十年思想言论中“民”的形象呈现“名”和“实”的不同,具有理想和现实两个层面。时人对下层民众的讴歌,其实只是对理想中的“民”的歌颂,他们在制度设计中寄望的“民”和现实生活中面对的“民”常常是两种面貌。那么,如何弥缝其间的差距?如何使“现实之民”达到“理想之民”的标准?或又如何以“理想之民”改造“现实之民”?这些都成为思想界必须直面的问题。辛亥革命造成的政治鼎革并未如时人想像的那样一举解决问题,新文化运动时期有关“国民性”改造的思考,仍与清季要想“新民”的种种努力相关,这方面的讨论只能俟诸另文了。
注释:
① 如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② 沟口雄三:《中国民权思想的特色》,黄克武:《清末民初的民主思想:意义与渊源》,均收入《中国现代化论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91年,第343—362、363—398页。
③ 徐宗勉、张亦工等:《近代中国对民主的追求》,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④ 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575、16页。
⑤ 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3本第4分,2002年12月,引文在第725、685页。
⑥ 参见梁启超《过渡时代论》,1901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27—32页。
⑦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7页。
⑧ 参见罗志田《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不改原有之字以开启“相异的意义体系”》,载《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4期。
⑨ 参见张佛泉《梁启超国家观念之形成》,载《政治学报》(台北)第1卷第1期,1971年9月;巴斯蒂《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翻译》,载《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
⑩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1901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12—22页。
(11) (未署名)《原国》,《国民报》第1期,1901年,我所用的是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8年影印的《国民报汇编》本,第6页。
(12) 欧榘甲:《新广东》,1902年,引自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以下简作《辛亥前十年间时论》),三联书店,1960、1963、1977年,第1卷上册,第279页。
(13) 汉驹:《新政府之建设》,《江苏》第5期,1903年,第3页(文页。按该刊有时以文分页,有时以栏分页,有时以类分页,且常跨期延续,笔者尽可能区别标出)。
(14) 汉驹:《新政府之建设》,《江苏》第5期,1903年,第5页(文页)。
(15) (未署名)《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报》第1期,1901年,《国民报汇编》,第31页。
(16) 杨度:《〈游学译编〉叙》,1902年,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7页。
(17) (未署名)《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湖北学生界》第3期,1903年,第1、7页(文页)。
(18) 黄遵宪致梁启超,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吴振清等编校《黄遵宪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12页。
(19) 汉驹:《新政府之建设》,《江苏》第6期,1903年,第6页(文页)。
(20) 张锺瑞:《对于要求开设国会者之感喟》,《河南》第4期,1908年5月,引自《辛亥前十年间时论》第3卷,第280页。
(21) 曾鲲化:《论官办铁路之恶结果》,《东方杂志》第5年第8期,1908年9月,第53页(栏页)。
(22) 击椎生:《苏杭甬铁路与滇川铁路之比较》,《云南》第12期,1908年2月,引自《辛亥前十年间时论》第3卷,第106页。
(23) (未署名)《中国灭亡论》,《国民报》第2、3、4期,1901年,《国民报汇编》,第44页。
(24) (未署名),《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报》第1期,1901年,《国民报汇编》,第33页。
(25) 梁启超:《敬告我国国民》,1903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四》,第24页。
(26) 雨尘子:《近世欧人之三大主义》,《新民丛报》第28期,1903年3月,引自《辛亥前十年间时论》第1卷上册,第343—344页。
(27) 杨度:《〈游学译编〉叙》,1902年,《杨度集》,第79页。
(28) 王汎森对此有精到的分析, 参见其《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载《台大文史哲学报》第56期,2002年5月,宋恕之语也转引自同文。
(29) 柳隅:《阀阅的之政治家与平民的之政治家》,《国风报》第2年第5期,1911年3月,引自《辛亥前十年间时论》第3卷,第782、784—785页。
(30) 梁启超:《释革》,1902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43页。
(31) 邹容:《革命军》,1903年,引自《辛亥前十年间时论》第1卷下册,第665页。
(32) 汪兆铭:《论革命之趋势》,《民报》第25期,1910年2月,第3页(文页)。
(33) 朱执信:《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民报》第5期,1906年6月,第16—17页。
(34) 林懈:《国民意见书》,《中国白话报》第5—8、16—18期,1904年2—8月,引自《辛亥前十年间时论》第1卷下册,第920—921页。
(35) 孙中山:《〈民报〉发刊词》,1905年,《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288—289页。
(36) 梁启超:《敬告当道者》,1902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36页。
(37) (未署名)《说国民》,《国民报》第2期,1901年,《国民报汇编》,第12、15页。
(38) 余一:《民族主义论》,《浙江潮》第1期,1903年,第4页(文页)。
(39) (未署名)《说国民》,《国民报》第2期,1901年,《国民报汇编》,第8—9页。
(40) 邹容:《革命军》,1903年,引自《辛亥前十年间时论》第1卷下册,第671页。
(41) 沈松侨:《国权与民权:晚清的“国民”论述,1895—1911》,第696页。
(42) 竞盦:《政体进化论》,《江苏》第3期,1903年,第49页。
(43) 辕孙:《露西亚虚无党》,《江苏》第4期,1903年,第10页(文页)。
(44) (未署名)《原国》,《国民报》第1期,1901年,《国民报汇编》,第6页。
(45) 关于这方面的努力, 可参阅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46) 叶德辉:《与南学会皮鹿门孝廉书》,《郋园书札》,长沙中国古书刊印社1935年《郋园全书》汇印本,第11页B。
(47)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559页。
(48) 梁启超:《新民说》,1902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2页。关于梁启超的“新民说”,可参考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8、9章;狭间直树:《〈新民说〉略论》,收入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68—94页。
(49) 梁启超:《新民说》,1902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3、58页。
(50) 改良与革命的提出和论证当然还受到各种社会、思想和政治因素的影响,这里只是指出其与“民”意识的关联而已。
(51) 蛤笑:《论地方自治之亟》,《东方杂志》第5年第3期,1908年4月,第35页(栏页)。
(52) 飞生:《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浙江潮》第8、9期,1903年,第6—9页(文页)。
(53) 竞盦:《政体进化论》、汉驹:《新政府之建设》,《江苏》第1期,1903年,第29页;第5期,1903年,第7页(文页)。铎人:《对于宪政之民心与立宪之不可得和平》,《民心》第1期,1911年3月,引自《辛亥前十年间时论》第3卷,第815页。
(54) 崇有:《论中国民气之可用》,《东方杂志》第1年第1期,1904年2月,第6—7页(栏页)。
(55) 《政闻社宣言书》,《政论》第1期,1907年10月,引自《辛亥前十年间时论》第2卷下册,第1055—1059页。
(56) 云窝:《教育通论》,《江苏》第3期,1903年,第14页(文页)。
(57) 榖生:《利用中国之政教论》,《东方杂志》第2年第4期,1905年5月,第78—81页(栏页)。
(58) (未署名)《论外交治本之法》,《外交报》第49期,1903年7月9日,引自《辛亥前十年间时论》第1卷上册,第321页。
(59) 梁启超:《新民说》,1902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58—59页。
(60) 《黄遵宪致梁启超》,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黄遵宪集》,第506、511页。
(61)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1903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85—86页。
(62) 亓冰峰:《清末革命与君宪的论争》,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0年,第95—96页。
(63)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1904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第124页。
(64) 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1912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3页。
(65) 康有为:《公民自治篇》,《新民丛报》第5、6、7期,1902年,引自《辛亥前十年间时论》第1卷上册,第173—181页。
(66) 康有为:《革命驳议》,《苏报》,1903年,引自《辛亥前十年间时论》第1卷下册,第694页。
(67) 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黄帝魂》选录,1903年,引自《辛亥前十年间时论》第1卷下册,第759—760页。
(68) 觉民:《论立宪与教育之关系》,《东方杂志》第2年第12期,1906年1月,第243—249页(栏页)。
(69) 汉种之中一汉种:《驳“革命驳议”》,《苏报》,1903年6月,引自《辛亥前十年间时论》第1卷下册,第691页。
(70) 寄生(汪东):《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民报》第2期,1905年11月,第1页。
(71) 沈松侨:《国权与民权:晚清的“国民”论述,1895—1911》,第711页。
(72) 按梁启超在文中说康“先生教学者常言‘思必出位,所以穷天地之变’”,这个主张对今文经学而言实在是石破天惊的出位之思!参见其《南海康先生传》,1901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84页。
(73) 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2006年新版。
(74) 梁启超:《粤乱感言》,1911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七》,第66页。
标签:国民素质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国民报论文; 奴隶论文; 国民论文; 亡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