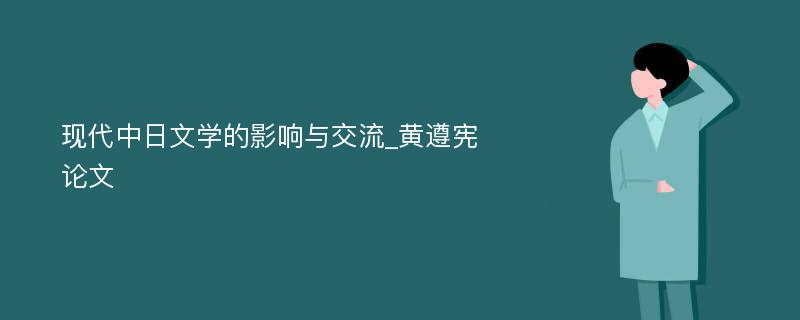
近代中日文学的影响与交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中日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日文翻译及黄遵宪
近代时期中国文坛的一个显著征象是,翻译文学不仅是翻译西洋作品,且相当部分也翻译东洋作品——日本人的书,或将日本人翻译的西洋作品加以转译。这是由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大大激发了中国人,使中国的一批开明人士欲从日本道路中引出中国的经验教训,而大批留日学生的出现,对中日文化与文学的影响交流,又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对此,梁启超《论译书》一文道出了其中真谛:
日本自杉田翼等始以和文译荷兰书,泊尼虚曼孑身逃美,归而大畅斯旨。至今日本书会,凡西人致用之籍,靡不有译本,故其变法灼见本原,一发即中,遂成雄国。(注:载《时务报》《变法通议》(1897)。)
大量日文翻译作品的涌现,自然对中国文坛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与影响,胡蕴玉《中国文学史序》说:“日本文法,因以输入;始以译书撰报,以存其真;继也厌故喜新,竞摹其体。甚至公牍文报,亦效东籍之冗芜;……”(注:《南社》第八集。转引自《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第4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胡氏所言, 透出日本书的翻译对当时文坛的冲击与影响。
近代翻译作品中,通过日文转译的西方(包括俄国)文学作品为数不少,这些作品往往先由日本人将英文(或其他欧洲语言)译成日文,而后中国译者再据日文转译成中文。如俄国诗人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中译名为《俄国情史》(戢翼翚译),根据日译本《露国奇闻花心蝶思录》(高须资助译)转译而来;又如,《忧患余生》(吴梼译)乃转译自日译本《犹太人之浮生》(二叶亭四迷译),而原作名为《该隐和阿尔乔姆》;再如,周树人的译作《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均系法国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的作品,但周树人是据日译本转译而成。包括当时文坛的一些小说创作,有些也是据日译欧美和俄国作品而写,如罗普的《东欧妇女豪杰》即是一例,先将欧洲(俄国)作品中的豪杰事迹据日译本翻译出来,同时揉入中国的色彩与成分,于是便成了中国式的“东欧女豪杰”了。这种一转再转的所谓“创作”(其实是“变相的翻译”),许多都走了日译本的“捷径”,对促进中外文学交流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所论很能说明问题,他指出,“近来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已”,这里所谓“新语”,包括了从欧美与日本两处输入之“外来语”,而尤以日本为多——或自日本书直译,或从由日本之西译书转译,这些“新语”的输入,客观上无疑丰富、充实了当时文坛(包括学术)的语汇。王氏说:“故我国学术而欲进步乎,则虽在闭关独立之时,犹不得不造新词,况西洋之学士骎骎而入中国,则言语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势也。”其解决之办法,即“新语之输入”也(注:《王国维学术经典集》(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类似现象,刘师培在《论近世文学之变迁》一文中也有述及,他说:
文学之衰,至近岁而极。文学既衰,故日本文体,因之输入于中国。其始也,译书译报,据文直译,以存其真。后生小子,厌故喜新,竞相效法。
毫无疑问,这里所指,不仅是词汇、语言,其中既包括句法,也包括文体结构。这方面的显著例子,为梁启超氏,他自己承认,自赴日以后,广搜日本书读之,从而使思想与言论均有所变化,文体也明显地改变了——长句增多了,句法表现丰富了,文体结构形式也自由了。胡适说他,“不避日本输入的名词”,文章“最不合‘古文义法’”(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载《胡适文存》。),意指他受外来影响后,文体、文风改变最大。梁氏特别欣赏日人德富苏峰的文章,认为他“善以欧西文思”入文,为“文界开一别生面者”,“余甚爱之”(注:梁启超《夏威夷游记》,载《饮冰室合集》。),明确表示要仿效德富苏峰,以欧西文思入文章之中。
日本的假名文字此时也引起了中国一些开明人士的注意与兴趣,觉得它在表达上有其优越之处。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学术志》对此作了阐述。他说,假名文字有利于表达人的情感,“其用之书札者,则自闾里小民,贾竖小工,逮于妇姑慰问、男女赠答,人人优为之”;有利于直抒胸臆,“其被之歌曲者,则自朝廷典礼、士官宴会,逮于优人上场、妓女卖艺,一一皆可播之声诗,传之管弦”。有利于描绘形象、记述见闻,“若裨官小说,如古之《荣华物语》《源语》《势语》之类已传播众口,而小说家簧鼓其说,更设为神仙佛鬼奇诞之辞、狐犬物异怪异之辞、男女思恋蝶亵之辞以耸人耳目,故日本小说家言充溢于世。而士大夫间,亦用其体以述往迹,纪异闻。”(注:参见王晓平《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第279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正因为假名文字这种特殊功能——可使语言与文字相合,因而黄遵宪极力予以推崇,并热切希望中国的文字也能走言文合一的道路,真正改变古代言文分离的状况。不过,这里须指出的是,其实日本本部在黄遵宪其时并未达到言文合一的理想状态,只能说正处于向这个方向改变的过程之中,黄遵宪预见到它的作用与意义,意图以此促动与影响中国文坛,使之发生变革。
黄遵宪曾被清政府任命为出使日本国的参赞,在日本呆了四年多时间,此期间,他的所言所行,所撰所著,均与日本文化(与文学)交流有关,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为近代中日文化(及文学)影响与交流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在日本期间,黄遵宪结交了许多日本朋友,其中包括政治家、学者、诗人、书法家、医生、僧侣等,他与他们或过从甚密,或诗文往来,一时间,使中日文化交往呈现热况。王韬在《日本杂事诗序》中这样写道:
公度,岭南名下士也。……既副皇华之选,日本人士,耳其名仰之如泰山北斗,执贽求见者,户外屦满。而君为之提倡风雅,于所呈诗文,率悉心指其疵谬所在。每一篇出,群奉为金科玉律。此日本开国以来所未有也。
《日本杂事诗》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上自神代,下及近世,其间时世沿革,政体殊异,山川风土,服饰技艺之微,悉网罗无遗。”(日人石川英《日本杂事诗跋》)诗集面世后,日本的刻本甚多。读《日本杂事诗》,我们可以发现许多黄遵宪与日本友人往来与结下情谊的记载,同时也能了解到日本历史与自然山川风貌,有助于对日本的认识。黄遵宪还写了《日本国志》,为中国人了解日本的历史、文化与国情,为中日文化交流起了良好作用。
《日本国志》共四十卷,分十二志: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工艺志。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国志》不仅是中国人编纂日本国志之创始,且也是日本国史志之首例,殊属难能可贵。《人境庐诗草跋》中黄遵宪自称道:“……亟自刊行者,意在借观邻国,作匡时之策也。”拳拳之心,溢于辞表。《日本国志》问世后,“海内奉为瑰宝,由是诵说之士,抵掌而道域外之观,不致堕五里雾中,厥功洵伟矣。”(注:狄葆贤《平等阁诗话》。)“甲午战后,此书乃大流行。……这书对于日本,理解深刻,取材正确,学术志、礼俗志,源源本本,择精语详,到现在还值得一读。”(注:梁容若《文学十家传·黄遵宪评传》。)此书虽无专门的文学志,然我们却能从“学术志”中得到一些有关文化与文学的信息,例如关于“言文合一”主张等。
黄遵宪在日本期间,不仅了解、记述有关日本的历史、文化与国情现实,且常将中国文化(古代文化)介绍给日本友人。例如有一次,当日本友人谈及中国小说传至日本甚少时,黄遵宪即向日本友人推荐了《红楼梦》,并热情介绍此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磨者。”“论其文章,直与《左》《周》《史》《汉》并妙。”(注:《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后日本友人也向黄遵宪介绍了日本小说《源氏物语》,谓其与《红楼梦》作意相似。
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与《人境庐集外诗辑》中还保存了数十篇赠和日本友人的诗作,记录了他与日本友人之间的友谊交往。值得注意的是,黄遵宪还应日本友人之请为他们的著述撰写序跋,这些序跋对日本友人的文学创作及学术研究褒贬分明,切中肯綮,深得日本友人首肯与赞赏,为中日文化交流史留下了佳话。
二、文坛革命与日本影响
近代时期中国文坛上的小说革命,实际上与受日本影响关系密切。1896年,康有为曾刊印了一本自编的《日本书目志》,他认为,这些著作与日本的改革极有关系。《书目志》共分15类,其中包括了文学,还特别把小说单列一类,说明在康有为看来,小说具有与其他学科(例如政治、法律等)等量齐观的价值——这表明,向日本小说学习,变革中国小说的观念,在康有为身上已有所体现,且康氏主观上将小说置于了与政治密不可分的地位。1897年,严复、夏曾佑在《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中提出:“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至于梁启超——这位力倡“小说界革命”的主帅,更是受日本影响,从日本变法维新的成功中悟出了小说的作用,他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说道:“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可见,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以及伴随这一成功而发生的文坛变革——小说的重要作用,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中国文坛,导致发生了梁启超首创、力倡,并有众多激进、开明人士群起响应所形成的中国近代文坛一场规模不小的小说界革命。当然,这里需要指出,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小说界革命”人士,没有一味仿效日本文坛的小说创作现状,而是结合中国社会现实有所选择地鼓吹政治小说,认为政治小说功利性最强,它在日本明治维新的自由民权运动中发挥过较大作用,因而相信它在中国社会变革中也能起重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梁启超将小说的作用提高到了可以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新学艺、新人心、新人格的高度,认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注:见《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载《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版。),则不免夸大了文学的社会作用,此乃是日本文坛的启蒙思想家们所未敢言或不曾言及的。
梁启超等人主动学习、仿效日本文坛,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封闭体系,无疑是一大冲击,使原本完全封闭的中国文坛,开始了开放或半开放,自此,有意识地吸收外国文学,成了一种风气或时尚。同时,文学本身的内容及表现形式也发生了剧变,民族忧患意识、苍凉悲壮格调、言文合一形式,逐渐成了文坛的一大“景观”,开始替代了传统的文学框架及其表现形式,这是中国文学从传统走向近代(甚至现代)的重要标志。
这当中,我们还应指出,梁启超提出的所谓“写实派”、“理想派”两种概念,也有受日本文坛影响的成分,而非纯出于欧洲的写实主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日本文坛上有以坪内逍遥为代表的写实主义和以森欧外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他们两派在日本文坛发生的论争,对曾旅日并充分感受日本文坛气息的梁启超,无疑有着较大影响,他由此而有“写实派”“理想派”的观念,实在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当然,必须指出,梁启超及其同人在中国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并非对日本明治文坛的单纯摹仿与照搬,而是受影响后针对中国文坛实际状况提出来的,且与日本文坛的改革有着很大的差别。当然,梁启超受日本文坛政治小说影响而夸大小说的社会作用,大肆鼓吹政治小说的功能,有其偏激之处,这是过分抬高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将其摆到了不恰当的地位;此外,日本文坛政治小说本身的说教重于人物形象表现,也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了“小说界革命”,梁启超自己创作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即犯了这个毛病,小说在写法上不少处类同报章论文,缺乏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描写。
其实不光是“小说界革命”,即便“诗界”与“文界革命”,也同样有着日本影响的成分。如“诗界革命”学习日本诗坛的“欧洲意境”——即学习或借鉴日本诗歌中的“欧洲意境”,和由日语翻译的欧洲诗歌,以及由诗歌形式受日本口语化文学影响而提出的“言文合一”主张;“文界革命”所提倡的“新文体”,在结构条理明晰、叙述平易畅达、语法语汇表达等方面,以及引进外来语上,也多少受了日本文坛的影响。比如黄遵宪的诗《锡兰岛卧佛》《今别离》《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等,其中内容和词句上分别述及了宗教(佛教)、近代科技(轮船、火车、无线电、照片)、自然科学(植物学、化学、生理学)等,与“欧洲意境”——西方思想、学理相似,此乃是受日本诗坛中介影响的结果。(当然,黄遵宪也有旅欧美之经历,但《日本杂事诗》主要写于日本。)此外,黄遵宪倡导“言文合一”,某种程度上也是受了日本言文一致运动的影响启发,因黄遵宪离日本时,日本文坛的言文一致运动已取得很大成绩,这不能不使之黄遵宪受到濡染,况且黄遵宪早在二十来岁时即已有此念——“我手写我口”,只是当时尚显得幼稚,不成熟而已。至于梁启超倡导的“新文体”之受日本明治文坛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梁启超曾读过日本启蒙思想家柴四郎、德富苏峰等人的多部著作,并有很高评价,他还亲自将柴四郎的《佳人奇遇》、德富苏峰的《烟士披里纯》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这就很自然地要受到他们所著文体的感染。梁启超既然深感读日本学者之文“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便自然要努力效法并提倡了,他在《夏威夷游记》中曾对德富苏峰“善以西文思入日本文”大为赞赏,认为“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此足可见“文界革命”深受日本文坛影响之一斑。
这里还应简单提及周树人(鲁迅)受日本文学影响的情况,他曾在《我怎样做起小说》一文中明确表示(注:这里应称“鲁迅”,因《我怎样做起小说》一文写于1918年之后。),日本的夏目漱石和森欧外曾是他喜爱的作者,其中夏目漱石尤为他所佩服。夏目漱石的文学理论也多少影响了周树人。此外,森欧外等人在日本掀起的浪漫主义运动,尤其是他们所翻译的大量欧洲浪漫主义作品,如歌德、拜伦、卡莱尔、海涅等,以及随之出现的浪漫主义诗人的传记——《拜伦——文艺界之大魔王》《雪莱》《诗宗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也深深吸引了周树人,使他情不自禁地欲向中国文坛翻译介绍欧洲浪漫主义诗人及其作品,以兴起中国文坛的浪漫主义运动。于是乎,上述浪漫主义作家(诗人)的传记便成了他撰写《摩罗诗力说》的原材料。这部《摩罗诗力说》中所极力宣扬与推崇的摩罗诗人之主张与行为,乃是向当时黑暗中国投出的利剑与匕首,旨在启发引导国民之觉醒与反抗,而书中对欧洲摩罗诗人与中国诗人(如屈原)的比较对照,则显然体现了作者早期的中外文学之比较意识,虽然这种比较尚不属于纯文学范畴,而多少带有政治与社会色彩——因为撰写此著,更多的成分乃在于以此唤醒国人,以拯救中华民族。
另外,还要提及的是,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组织春柳社,编写、演出西方戏剧,某种程度上,也是受了日本(演剧界)影响的结果。
1905年至1906年间,留学日本东京的部分中国青年组织了中国第一个民间演出团体春柳社,他们感慨自己国家文艺的衰弱,力图以自己的努力,振兴戏剧,《春柳社演艺部专章》中写道:
近号文明者,曰欧美,曰日本,欧美优伶,靡不学博洽多闻,大儒愧弗及;日本新派优伶,泰半学者,早稻田大学文艺协会有演剧部,教师生徒,皆献技焉。(注:《北新杂志》第30卷,1907年。)
1907年,春柳社排演了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第三幕,继而又改编上演了林纾翻译的《黑奴吁天录》,以及《热泪》《猛回头》《社会钟》等剧。这些戏,在编剧、表演等方面,都曾受到当时日本新派剧的影响:《茶花女》的排练、上演,得到过日本朋友藤泽浅二郎指导;《热血》《猛回头》《社会钟》等剧是日本作家田口掬町、佐藤红绿的作品(或译编、或改编);春柳社的演员们在演剧的表演技巧上,则不少人有意无意模仿、学习了日本新派剧的著名演员。(注:参见《中日近代文学交流史稿》,王晓平著。)
最后,值得提一笔的是,在中日文化与文学交往中,除了王国维曾对日本学界研究中国古典戏曲产生影响并留下佳话外,近代著名学者俞樾与日本文人学者间也有过文字交往。他编选的《东瀛诗选》出版后,在日本引起一定反响,这本《东瀛诗选》,乃是出于日本友人的请求,其时他正在患病,但他念及“与东瀛诸群子结文学因缘,未始非暮年之一乐也”,便欣然接受了这一差事。这部《东瀛诗选》是日本汉诗的第一部总集,出版后在日本很受欢迎,“纸贵瀛东,共相传播”(陈家麟《东槎闻见录》)。与《东瀛诗选》问世的同时,俞越还写了《东瀛诗纪》,收入其所著《春在堂全书》中,“纪”中记录了每位诗人的师从渊源,由此可一窥日本汉诗三百年的发展轨迹,同时,“纪”中对每位诗人诗作本着知人论世的精神作了品评。此外,俞樾还有记日本儒者、文人的笔记小说如《先哲丛谈》,搜录日本境内神鬼妖狐奇闻异事的笔记如《右台仙馆笔记》,这些著作反映了俞越对日本文化的浓厚兴趣,也是中日文化(文学)交流的产物。(注:参见《中日近代文学交流史稿》,王晓平著。)
三、日本的中国文学翻译与研究
中国文学的传入日本,较之欧美,时间上要早得多,这是由于历史和地理条件的缘故。早在唐代(甚至更早),日本岛一些文化使者(及留学生)即已将中国的许多文学典籍传入日本,其中包括《论语》《诗经》《楚辞》《文选》等,在日本产生较大影响。
进入十九世纪中下叶,日本对中国文学典籍已不是简单的翻刻、诵读,而是开始专门研究,出现了研究论文及著作。以楚辞来说,生活于十九世纪中下叶的学者冈松甕谷撰写了《楚辞考》一书,该书取证王逸、朱熹、洪兴祖及林云铭的论点说法,并参以己见,是一部有一定价值的论考性著作(注:参见《楚辞资料海外编》第400~411页,《楚辞研究集成》之一,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嗣后,有西村硕园的《屈原赋说》,该书虽仅完成上卷(十二篇),但它作为一部楚辞概说书,在日本占有甚高地位。对此两部《楚辞》研究著作,当代日本楚辞专家竹治贞夫说:“进入明治时期后,真正以汉文进行的楚辞研究,是冈松甕谷的《楚辞考》和西村硕园的《屈原赋说》。与其他古典名著研究相比较,这未免有些寂寥之感,可是,前者作为楚辞注释,是温雅之中含有卓见的佳作,后者作为楚辞概说,其考证的精密和规模的宏大,至今尚未见出其右者”。(注:引见《楚辞资料海外编》第414页。)
至于日本在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古典小说及戏曲的研究(尤其古典小说),成果就更多些,不过其中相当部分是改编翻译。
明治十六年(1883年)出版的菊地三溪的《本朝虞初新志》,即是仿效《聊斋志异》体裁编写的。石川鸿斋的《花神潭》(明治二十一年即1888年)及《夜窗鬼谈》(明治二十二年即1889年),明显受《香玉》等篇的影响。森欧外的妹妹小金井君子翻译的《皮一重》,即《画皮》,收入森欧外编著的《翳草》(《ガけ草》)一书,译文是就原著文笔作部分润色,为拟古风体,这是近代作家翻译《聊斋志异》的最初译文。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中国怪异文学在日本很盛行,大家都喜读《聊斋志异》。国木田独步翻译的《竹青》《王桂庵》《石清虚》《胡四姐》四篇译文,载于《近事画报》杂志(昭和元年以后改造社收入镰仓文库的《独步全集》),这是以现代语翻译《聊斋志异》的最早的译文。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近事画报社编译出版的《支那奇谈集》,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聊斋志异》的篇目,共一百一十九篇(包括独步的四篇译文在内),译文皆忠实原著,而《香玉》中的诗句采用七五调韵文译出,尤引人注目。诗人蒲原有明翻译的《香玉》《木雕美人》《橘树》《蛙曲》《鼠戏》《戏缢》《诸城某甲》七篇,载于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国木田独步编辑的《文艺杂志》的“新古文林”,其中以小金井君子的译文独具异趣,语言优美。上面介绍的都是日本有名的译文。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出版的秋,秋郊的《花神绮话》一书中,收有《香玉》《劳山道士》《瑞云》《恒娘》《画皮》《陆判》《白于玉》《续黄粱》《黄英》《申氏》《青凤》《书痴》《瞳人语》十三篇作品的翻译本,为翻译中的精品。……在日本,《聊斋志异》最早的译本是神田卫民译的《艳情异史》,1887年由东京明进堂出版。
明治时期,《红楼梦》在日本开始受到普遍重视。1872年,《绣像全图增批石头记》的日本版出版,说明《红楼梦》开始拥有更多更广泛的读者。
1892年(日本明治二十五年,清光绪十八年),是“程甲本”刊行100周年,在日本红学史上这是有重要意义的一年。 这一年发生了三件重要事情:
(1)4月,森槐南译了《红楼梦》第一回楔子,发表在《城南评论》二月号,这是《红楼梦》首次被译成日文。
(2)6月,诗人岛崎藤村译的《红楼梦》第十二回《风月宝鉴》发表在《女学杂志》三二一号上。
(3)11月, 森槐南著《红楼梦评论》发表在《早稻田文学》二十七号,这是第一篇日本人写的《红楼梦》评论。
虽然森槐南的译文比德国传教士郭实猎1842年5 月以英文撰写的《红楼梦》主要情节介绍以及其他一些零星的英法译文晚,但是《红楼梦》在日本的流传和影响则是西方国家所不能比的。在日本存在着许多精通中文的学者文人,在没有译本的情况下他们也能直接阅读原著。
日本在明治二十年到四十年间(1887~1907年),以《红楼梦》的日译为开始,《红楼梦》翻译研究在日本逐渐繁盛起来,日本人开始表现出对这部中国名著的极大兴趣。菊池三郎在《中国文学入门》中回忆到:“说到这位林黛玉,幕末、明治的日本人大概都是知道的,我的父亲在谈话中曾说到林黛玉是美女的典型一事至今还留在我关于童年的回忆里。”
日本对《红楼梦》的评论研究始于森槐南。他于1892年11月在《早稻田文学》二十七号上发表了《红楼梦论评》,开了日本红学研究的先河。从明治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宫崎来城、古城贞吉、笹川临风、依田学海、奥村梅皋、狩野君山都发表了评论文章。宫崎晴澜、永井甃石等都有咏《红楼梦》的汉诗。当时的作家,如尾崎红叶、山田美妙、二叶亭四迷、森欧外等人,家中藏书都有《红楼梦》的几种不同版本。
在国外研究《红楼梦》的学者中,日本学者进行了最为细致、系统的工作。日本学者选题广泛,“举凡小说的主题思想、艺术结构、语言文字,以至版本流行、资料考据等方面,都有论及。”(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
以上是辑录自《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一书中有关中国近代时期日本翻译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概况。(注:《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宋柏年主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
中国古典戏曲在日本的研究,起步较早。1897年,笹川临风即问世了一部《中国小说戏曲小史》(其中也涉及了小说),这要比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早了十多年,可见,对中国戏曲史的研究,日本还早于中国。至于对中国古典戏曲的翻译,时间要更早些,十九世纪初叶,已有《西厢记》《窦娥冤》等译本问世了(注:参见《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第372页。)。不过,话说回来, 虽然戏曲史著作的产生日本早于中国,但日本真正的中国戏曲研究,却是受了王国维的戏曲研究论著影响后兴起的,尤其王国维辛亥革命后流亡日本,在日本学界影响甚大,以至形成了竞相翻译、介绍、研究中国戏曲的热潮。有关这方面情况,日本人盐谷温在其《中国文学概括讲话》第五章中作了形象描述:
王氏游寓京都时,我学界也大受刺激,从狩野君山博士起,久保天随学士、铃木豹轩学士、西村天囚君士、亡友金井君等都对斯文造诣极深……呈万马骈镳而驰骋的盛况。(注:转引《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第373页。)
同样,日本著名汉学专家铃木虎雄也因受王国维影响,萌生了研究词曲之念,开始试训释《琵琶记》,并常向王国维请教难解之处以及有关的典籍、掌故、风俗等,1913年他还专门译介了王国维的《古剧脚色考》一书。而王国维也有《译〈琵琶记〉序》一文面世,这是专为日人西村天囚所译《琵琶记》而撰,文中指出了只取科白不取曲辞之弊,认为是买椟还珠行为,同时序文充分肯定了日本学者译汉籍、知汉文学的成就,认为“非欧人所能望”。
王国维与日本学者的学术交往,以及受王国维影响,日本学界掀起翻译研究中国古典戏曲的热潮,为中日文化与文学交流留下了佳话。
标签:黄遵宪论文; 王国维论文; 文学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中日文化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聊斋志异论文; 读书论文; 梁启超论文; 香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