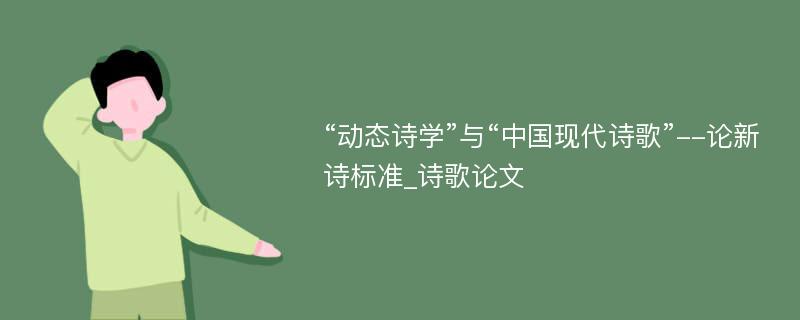
“动态诗学”与“现代汉诗”——再谈“新诗标准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新诗论文,再谈论文,标准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诗学家陈仲义先生《感动 撼动 挑动 惊动——好诗的“四动”标准》一文的发表,引发了新一轮有关“新诗标准问题”的热烈讨论。仅新世纪以来,大体同样的讨论就已有两次,分别由2000年《诗刊》下半月刊和2004年10月《江汉大学学报》发起组织,响应者不少。在此之前,1997年由诗学家王光明先生发起,福建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联合举办的“武夷山·现代汉诗诗学国际研讨会”,以“现代汉诗的本体特征”为主题,所开启的在“现代汉诗”命名范畴下有关“诗歌本体”问题的理论研讨,以及由权威诗歌理论刊物《诗探索》于1996年至2002年之间,连续多次组织的有关“‘字思维’与中国现代诗学”的大讨论,实际上也都是对诗歌“标准”问题的一些分延性的深入探讨。短短十余年内,对大体同一命题的不断切入,且不断形成热点,只能说明,这一看似总是“不得其门而入”的诗学命题,确实是新诗理论研究始终绕不开去的大难题,试图对此大难题有所解决的愿望,也显得越来越迫切。
一个命题反复被重新提及,又反复以无可总结而结束,再等待新的提及,是否是个“伪命题”?至少,仅就现实中的新诗创作来看,这样的讨论对其几乎产生不了什么作用,诗人们想怎样写照样怎样写,而当我们感到对此已无话可说的时候,诗歌自己却早已发生了新的变化,展示出新的景观。于是难免让人对这一命题的根由提出质疑:它何以存在又有何意义?
由此推论,就涉及到对新诗之“伪”的追索。新诗自诞生之日至今,有关“新诗只有新没有诗”的指认便从未断过,乃至有更极端者认为新诗的存在是一个百年“大谎”。极端者之言显然不足为论,但前者的说法却颇值得引入对“新诗标准问题”之真伪的推论。也就是说,假设承认新诗百年,从驱动到结果,其总体发展态势,确实只是唯新是问,任运不拘,谈不上或还顾及不上诗之本体的建设与发展,则有关“新诗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暂时失去了立论的依据。反之,若认为新诗百年,已经在创作实践中具备了本体意义上的诗质的认同,此一立论才具有学理上的合法性。
如此强词夺理般的机械推论,只是为重新认知新诗的现实存在及其与“标准”问题的关系理清思路。
新诗百年,从外在形式看去,除了分行和字数少之外,似乎再无文体标志可辨识。即使是分行即如何建行本身,也无可通约的标准可言;字数的简约也多以只在字数,而并未完全达到审美意义上的简约。尽管在新诗发轫的第二个十年开始,便已有闻一多“新诗格律化”主张的提出和“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鼓吹,以及后来卞之琳、林庚、冯至等前贤对新诗技巧与形式的惨淡经营,以求找到新诗“自己更完美的形式”,[1] 寻求新诗形式的规范及至定型,但最终还是被后来各种各样的“新”所淹没不计,以至到今天依然需一再重涉那个从一开始就不断涉及的“标准”问题。
然而有意味的是,若单从结果来看,正是这样无所不自由的写法,却支撑了百年新诗的强势发展,从而为我们民族的精神空间,撞开了新的天地,继而成为百年中国人,从知识分子到平民百姓,尤其是年轻生命之最为真实、自由而活跃的呼吸和言说,也同时成为东西方精神对话的有效通道。尤其是近三十年来中国内地的现代主义新诗潮运动,更是在不断消解狭隘的阶级利益与狭隘的民族利益的困扰,顽强对抗封建残余与意识形态暴力的迫抑的奋争中,最终以独立的现代精神人格和独特的现代艺术品质,走向世界,与世界文学接轨,成为20世纪人类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可以发现,任何时候对新诗的任何发问,都要首先面对并认清上述悖论,而有关“新诗标准问题”的讨论,更是只能在这样的悖论前提下予以展开。
接下来的问题是:新诗不成熟的“肉身”与早熟的“灵魂”,何以能越百年而自由共生协调发展?亦即唯“新”是问的新诗,何以取得依然属于“诗”的审美品质与审美效应?被称之为“新诗”的诗性之“性别”又属之为何?
二
新诗之“新”,比之古典诗歌的“旧”,看起来是外在形式的区分,实际上是两种不同诗歌精神亦即“灵魂”的分道扬镳。尽管,当年胡适先生确实是经由诗的语言形式方面为新诗的创生打开的突破口,但不要忘了,包括新诗在内的所有新文学的发生,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借道而行”的产物,本意并不在美学意义上的语言、形式之“道”的探求与完善,而在借新的“灵魂”的诗化、文学化的高扬,来落实“思想启蒙”与“新民救国”之“行”的。换句话说,推动新诗发生与发展的内在心理机制之根本,是重在灵魂而非形式的,由此渐次形成的诗歌欣赏习惯,也多以能从中获取所谓“时代精神”的响应为标的,并渐次成为新的欣赏与接受程式。这也便是新诗百年,总是以内容的价值及其社会影响力作为压倒性优势,来界定诗歌是否优秀与重要的根本原因。而新诗的灵魂也确实因此而得以迅速成熟和持续高扬,乃至常常要“灵魂出窍”,顾不得那个“肉身”的“居无定所”了。
显然,新诗的诗性,从一开始就完全不同于古典诗歌。时至今日,诗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我们存在的家,“诗歌是语言的如何说的历史,而不是说什么的历史”[2] 等观念,几乎已成为一种常识为人们所普遍认同。但落实于具体的诗歌写作,在年少的新诗这里,却总是以“说什么的历史”带动或改变着“如何说的历史”,“灵魂”扯着“肉身”走,变动不居而无所不往。这里的关键在于,百年新诗所处历史语境,实在是太多风云变化,所谓“时代精神”的激烈更迭,更是任何一个历史上的百年都无法比拟的,以致回首看去,百年新诗历程更像是一次“急行军”而难得沉着,更遑论“道成肉身”式的自我完善。
对此,我曾在《拓殖、收摄与在路上——现代汉诗的本体特征及语言转型》一文中,形象化地将古典诗歌的写作比喻为“在家中”的写作,将新诗的写作比喻为“在路上的写作”,进而指出:“‘在路上’的写作与‘在家中’的写作有着本质的不同。原因是,‘在路上’的生命状态对艺术的诉求,和‘在家中’的生命状态对艺术的诉求是不一样的。‘在家中’的写作,无论是出世的还是入世的,是‘仙风道骨’还是‘代圣立言’(‘圣’与‘家/国’同构,‘言’即‘志’),都有一个较稳定而可通约的文化背景作凭借,因而其言说总是具有一定的公约性和可规范性的,写作者也在有意与无意间追求这种公约和规范;‘在路上’的写作,则完全返回自身,返回当下的个在生命体验,且因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性和变化性,无法再有‘规范’可言,写作者也不再顾及这种‘规范’,亦即写作本身也成了一种处于变动不居的、‘在路上’的状态。”[3]156-183
现在看来,这种“在路上”的状态以及对此状态的个性化表达,本身已构成了新诗诗性的一部分,而且是其主要的部分。敏锐,新奇,活力,有效,这些作为新诗不断发展与跃升的主要驱动力,同时又转换为新诗诗性审美的主要指标而为人们所认同。而所谓“变动不居”本来就是新诗的本质属性之一,由此带来的写作现象就是不断地标新立异及无标准的自我标榜。而以“移步换形”且繁乱无定的语言形式来表现同样“移步换形”且繁乱无定的“时代精神”,或许正是身处百年文化大语境下的必然选择?
由此看去,以“新诗”为命名下的诸多诗学问题,都可以以“动态诗学”(笔者生造的一个命名)为绾束——“新”与“动”以及“自由”,遂成为理解和阐释有关新诗问题的第一义的关键词。离开这三个关键词的基点,怎样说,都是一本糊涂账。
不过,内容之“道”与语言形式之“肉身”的纠结与撕扯,却依然是年少的新诗从未了断且始终挥之不去的根本问题。有如成长的法则不能替代成熟的法则,年少的新诗之过渡性的唯新是问,也不能因此就“过渡”个没完。新诗无体而有体:各个有体,具体之体;汇通无体,本体之体;本体不存,具体安得久存?这是新诗一直以来的隐忧。而当下的诗歌现实是,经由百年“急行军”式的、无所不至的探索,几乎已踏平了诗性生命存在的每一片土地,造成整个诗性背景的枯竭和诗性视野的困乏,成为一种无边界也无中心的散漫集合。或许当下时代依然还是更趋向于多样性而不是完美,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实现自己的潜能,甚而还包含着更多的没有开发的可能性。但必须要同时提醒的是,在它具有最强的变化能力的同时,更需要保持一种自我的存在——本质性的存在。
于是,如何将“唯新是问”的价值属性,适时导入“如何新才好”的价值轨道,便成为新诗诗学的一个新命题。而这一命题是否成立的前提,是先要判断在“新诗”命名范畴下的现代汉语诗歌的发展,是否已临近一个由年少而步入成熟的“转换期”?
三
“新诗”的前身是“白话诗”,之后又有了“自由诗”的命名。与三种命名下的诗歌精神相伴行的,是由“白话”而“国语”而“现代汉语”的语言嬗变。诗因诗人的特殊语感而生。一时代之诗人的语感,必受一时代之语言形态所影响,进而再经由诗人们的语言创造,反过来影响一时代之语言形态的变化。这种相生相济的互动嬗变,在百年中国大语境下,无不和“现代”这又一个关键词息息相关。实际上,尽管我们一再将整个近百年的汉语新体诗歌写作习惯性地统称为“新诗”,但同一指称下的“新诗”,无论是其“灵魂”还是其“肉身”,早已大为不同——尤其是在“现代性”这一点上。可以说,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台湾“现代诗”的发轫及其后的滥觞,到20世纪70年代末大陆中国现代主义新诗潮的一发而不可收拾,所谓“新诗”百年,已然明显划分出两个大的时代板块,即“新诗时代”和“现代汉诗”时代。
作为正式的学理性命名,“现代汉诗”的提出,以及对此作出全面深入的理论性阐释者,是当代诗学家王光明先生,并通过他的有关专著《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建构起一整套理论体系,影响甚大。现在看来,这一命名及其影响,是具有突破性意义的。这一意义的关键,正在于正式而名正言顺地将“新诗”和“现代汉诗”区分开来,从而也就从学理上,就如何将“唯新是问”的价值属性适时导入“如何新才好”的价值轨道这一命题,提供了一个适当的切入点。也就是说,只有先行将有关“新诗”之“新”的言说,适时导入“现代汉诗”之“现代”的言说,并重新梳理“新”与“动”以及“自由”三个关键词的正负价值在性之后,有关“如何新才好”亦即“新诗标准问题”的讨论,才不至于再次成为一本说不清还得说的糊涂账。
那么,拿什么来判断年少的新诗,确然已进入了一个新的生长发育期,不能再像以往那样“自由散漫”,也可以不再像以往那样“任运不拘”?或者说,“新诗”向“现代汉诗”的转换,是以什么为指标来作为其“临界”的判别呢?就此,以笔者学力所限,暂时只能大而化之地想到三点:其一,现代汉语之阶段性的基本定型;其二,现代中国文化语境之阶段性的基本定型;其三,体现在诗歌及整个文学艺术中的现代意识和现代审美精神之阶段性的基本定型。我想,假如这三个“基本定型”可以成立,我们就可以告别“新诗”之“新”的反复困扰,进入“现代汉诗”的命名范畴里,展开对所谓“标准”问题的有效讨论。
这就要说到“自由”,因为有关“标准”的讨论,必然同时也是对有关“自由”如何约束的讨论,尽管我们也知道,完全没有约束的自由实际上反而是不自由。现代诗的自由,不仅是解放了的语言形式的自由,更是自由的人的自由形式。对于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百年中国文化进程而言,自由是无比珍贵的,也是来之不易的,我们不能没有自由,但今天的我们更要学会如何“管理”自由;有如我们不能没有真实但也不能仅仅为了真实性而放逐了诗性——诗形的散文,诗形的随笔,诗形的议论,诗形的闲聊,以及等等,惟独缺少了诗性。时至今日,当多元已成为价值失范的借口,自由已成为不自由的焦虑,对“自由”的“管理”,便成为无可回避的问题。具体到诗歌本体上来说,如何在自由与约束的辩证中,寻找新的形式建构与语言张力,遂成为“现代汉诗”命名范畴下,必须要面对的首要命题。正如王光明所指出的:“……即使是自由诗,也不能永远以不讲形式为形式,甚至不能以‘每一首诗都有自己的形式’为借口,那是矜才使气,而不是写诗。诗永远要在自由与约束的辩证中寻找张力……没有基本形式背景的诗歌是文类模糊、缺少本体精神的诗歌,偶然的、权宜性的诗歌,是无法被普遍认同和被传统分享的诗歌,正如未被形式化的内容是粗糙的素材或灵感的火花一样。”[4]
如此绕了一大圈,是想证明:有关“新诗标准问题”的讨论,既是“伪命题”,又不是“伪命题”;对于“新诗”之命名范畴来说或许是个“伪命题”,对于“现代汉诗”之命名范畴来说就不是“伪命题”。也就是说,只有在进入“现代汉诗”这一新诗发展的新阶段,才能越过前述悖论的困扰,使有关“标准”问题的思考,真正落在实处,具有现实意义。当然,这里的“现代汉诗”,是指建立在诗歌本体意义上而非单纯诗歌史意义上的“现代汉诗”。借用诗评家荣光启在其《“标准”与“尺度”:如何谈论现代汉诗》一文中的话,可分解为“不仅‘现代’,而且有‘汉语’的品质,而且是‘诗’”。[5]
就此,越过“新诗”这道坎,我们似乎可以心安理得地来尝试有关“现代汉诗”之“诗歌标准问题”的讨论了。
四
新诗先脱“古典”之身而成幽灵,再得“现代”之体而寻典律——“现代汉诗”的确立,为新诗的诗体建设,提供了可能的平台。至少在这二三十年的诗歌进程中,包括笔者在内,我们其实都一直在这个平台上说话,说与“标准”问题或切近、或分延、或困惑的相关话题。为此,在我试图想就这一话题说出一点新的东西之前,我得先看看我已就这一话题说出过些什么,它们是否还有效于当下,以确定我确实还有新的可说,或者有无必要再说什么。
就个人研究所限,对“现代汉诗”之诗美标准的思考见诸于文本表述的,大体梳理下来,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观点尚值得重新复述:
(一)关于“诗美三层次”的论述
此观点见于:1993年发表于《诗歌报》月刊第6期及台湾《文讯》杂志10月号总96期的《诗美三层次》一文。文章出于普及性的目的,将一切诗美,简单归纳为三个层次去审视:情趣,精神,思想。并以此从诗歌创作/发生和诗歌欣赏/接受的双向角度,给出了一个“尺度”公式:
情趣(色、形)→自文字(语感)→动情→入道→第一层次;
精神(气、韵)→自人格(生命感)→动心→入神→第二层次;
思想(骨、魂)→自哲学(宗教感)→动思→入圣→第三层次。
同时辅助说明:无论情趣、精神、思想,皆有大小之分。有无是一回事,大小是另一回事;有无成真伪、定品位,大小则成风格、定流派。三者或缺或盈或大或小,不同比例成分之组合,遂成不同诗质。由此建立一尺度体系,作者可自审自度,读者亦可为评为释。[3]111-116
(二)关于“诗性”“诗形”与“非诗”的划分
此观点见于1999年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第6期的《诗性、诗形与非诗》一文。文中首次提出将现代汉语诗歌作品分为“具有诗性的诗”和“徒具诗形的诗”两种不同性质的文本样式,以明确真正可称之为“现代汉诗”的基本标准,并将这一标准初步指认为:
1.具有独立的、自由的鲜活人格。作为超越社会层面的私人宗教,以本真的生命体验,深入时间内部、生存内部,开启新的精神光源,拓展新的精神空间。
2.具有独特的审美体验。作为人类最敏感的“艺术器官”,这种体验必须是原创性的、不同于任何他在的,最终必须要求富于新奇感、惊异感、意外感,成为一次原发性的“灵魂事件”,于瞬间开启对生命与存在之奥秘的特殊体悟。
3.具有独在的语言质素。作为诗性文体的最本质凭恃,这种语言质素的要义在于:(1)是恢复了语言命名功能的;(2)是超语义的;(3)是与精神同构而非仅作为载体的;(4)是造型性的而非通讯性的;(5)经由出人意料的组合而脱离语言习惯与语言制度,进而成为有意味的语言事件的。[3]89-93
(三)关于“现代汉诗语言应遵循‘守常求变’法则”的论述
此观点见于2002年发表于“北京香山·2001·中国现代诗学国际研讨会”的《现代汉诗语言的“常”与“变”——兼谈小诗创作的当下意义》一文。文中指认“现代汉语诗歌之语言变数太多,居无定所,只见探索,不见守护,以至完全失去了其本质特性的参照,正成为一个越来越绕不开去的大问题。”由此提出当代诗歌发展应遵循“守常求变”、“变”中求“常”、守护中求拓进的语言机制,和重视“常态写作”,重涉“典律之生成”的诗学命题。并从“简约是中国诗歌最根本的语言传统,也是中国文化及一切艺术的精义”的理念出发,强调作为审美意义而言的“简约”这一点,应该视为诗歌语言形式的“底线”来加以守护。并由此重估小诗创作的美学价值,提倡“为诗减肥”,推动新的小诗运动。[3]40-52
(四)关于“‘口语’与‘叙事’等语言策略”的论述
此观点见于2007年发表于《星星》诗歌月刊(上半月)第9期的《怎样的“口语”,以及“叙事”——当下“口语诗”问题之我见》一文。文章一方面充分肯定90年代以来的当代先锋诗歌,“转换话语,落于日常,以口语的爽利取代书面语的陈腐,以叙事的切实取代抒情的矫饰,以日常视角取代庙堂立场,以言说的真实抵达对‘真实’的言说,进而消解文化面具的‘瞒’与‘骗’和精神‘乌托邦’的虚浮造作,建造更真实、更健朗、更鲜活的诗歌精神与生命意识”,一方面指出由此而生的“严重的‘族系’相似性和‘同志化’的状况,并将个人语境与民间语境又重新纳入了制度化语境和共识性语境,造成普泛的同质化的诗歌立场,而这本是引入‘口语’与‘叙事’策略的初衷所主要要反对的东西。”由此给出另一向度的语言策略,以探求将“口语”与“叙事”的负面降到最低,使之发挥真正有价值的诗歌美学作用的可能。并将其概括为三点:
1.抒情性写作的智慧化(相对于抒情性写作的激情化所带来的虚浮造作及滥情);
2.“口语性”写作的寓言化(相对于“口语性”写作的过于写实化);
3.“叙事性”写作的戏剧化(相对于“叙事性”写作的“指事”化弊端)。[3]80-88
以上四点,现在看来,将其重新纳入有关“现代汉诗”之“标准”的讨论,似乎依然有效而并不过时。至于新的思考,目前只想到一个有关现代诗歌本质的再认识的问题,或可有益于“标准”问题的讨论。
先回到荣光启对“现代汉诗”定义的精当拆解:“不仅‘现代’,而且有‘汉语’的品质,而且是‘诗’”。就“现代”而言,应该说,在包括台湾和海外在内的当代汉语诗歌写作中,已属普及性的常识。我们再也无法握住那只“唐代的手”,只能在现代汉语及现代文化语境下,来言说我们中国人的现代感和现代诗性生命意识。对“汉语”的诗性特征以及当代诗歌写作中的“汉语性”的再认识,也不乏普遍的重视,乃至有诗人认为“汉语是世界上少数直接就是诗的语言。”[2] 这里最关键的是对“而且是‘诗’”这一判语的认定。实则有关“新诗标准”的讨论,说到底,就是对什么样的诗歌作品是真正符合诗的、特别是“现代汉诗”的基本品质的讨论。再具体点说,是对构成这一基本品质的基本元素的讨论。而这,也是最难以沟通和统一认识的核心点。是以大多数有关“标准”的言说,都属于在此核心问题之外绕圈子的话,或分延及子问题的思考。对此,我只能结合古今诗歌的共性与差异性的相切地域和联结地带,勉强总结出一个“四象标准”,求证于同道方家。
所谓“四象”:一为“意象”;二为“思象”;三为“事象”;四为“音象”。
其一,诗是意象思维的结晶。意象是诗歌语言的根,诗并非因为有特殊的话题要说,才开启特殊的说法,而是因为有特殊的语言风景的诱惑,方说出那个特殊的话题。诗以沉默为本,不得已而说,说不可说之说;诗以语言为行迹,而诗心本无言,只求意会,会存在无言之境,遂取意象而言,言言外之意——这一诗歌本质的核心属性,无论古典还是现代,大概都是首要之取。
其二,诗是诗性生命意识的表征,所谓“诗言志”,有关“灵魂”与“精神”的诗。在现代诗的创造中,一首好诗,既是一次新奇而独特的语言事件,也是一次新奇而独特的灵魂事件,包括新奇而独到的人生感悟和新奇而独立的生命体验。用通俗的说法,这就是诗的思想性。但诗是对思想的演奏而非演绎,即让语感代思想去寻找更深藏隐蔽的思想。故还得诉诸于“象”,是为“思象”。仅从发生学而言,也可等同于“心象”,以及一些诉诸于形象化或感性化的意绪、理趣与顿悟等。
其三,诗同时也是生活事件的见证,所谓“诗言体”(于坚语),有关“存在之真”与“身体之惑”的诗。现代社会中人的生活和人的命运,无不充满了各种的变数,乃至比虚构的文学还要富于戏剧性和故事性。加之物质世界的日益凸显等现实因素,迫使当代诗歌必须脱身单纯抒情的“精神后花园”,转换话语,落于日常,及物言体,引“叙事”为能事,拓展其表现域,是必然的出路。由此,对“事象”的经营便发为“显学”,也便成为现代诗与传统新诗最为不同的本质属性之一。诗有虚实,意象为虚,叙事为实,虚实相济,方生诗意无穷。但“叙事”不是“说事”,而是对“事”的“说”,故也还是要回到“象”上来说:意象性的说,戏剧性的说,寓言性的说——诗性的说,说“事”不可说之“说”。
其四,诗是有造型意味和一定音乐性的语言艺术。汉语自“白话”起一直“现代化”到今天,确实已经和古典汉语分身为两个截然不同的语言谱系。新诗引进西语的逻辑句法及文法,讲求因承结构和散文化,诗思的开展,大都由篇构而句构而字构(与古典诗词刚好相反),字词皆拘役于整体结构,是以大大消减了音乐性的存在。但汉语天生是一种富有音乐性的语言,并未因现代化而完全丧失其基因。在新诗和现代诗的许多优秀作品中,都不难发现,其实依然不乏音乐性的存在,只是已内化为一种语感中的呼吸——根据心境、语境、意境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韵律与节奏感。显然,这种现代“内化”性、潜在性的音乐感,已非传统诗学意义上那种可直接感受到的音乐性,故称之为“音象”。
以上“四象”,也和前述“诗美三层次”一样,呈现在具体的诗歌作品中,或缺或盈或大或小,不同比例成分之组合,遂成不同诗质诗品。由此建立另一尺度体系,或可和上述诸观点一起作为参照,有助于当前诗歌“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入展开。
五
然而最终,作为诗歌理论与诗歌写作双栖的诗爱者,对有关诗歌“标准问题”的讨论,我还是深感迷惑。
首先“标准”这个词本身就很麻烦,尤其是拿来用于对诗的言说,非常别扭。诗贵自然——如生命之生成,不可模仿;如自然之生成,不可规划。创造性的诗歌写作,是一种生育形态而非生产形态,不是像工厂那样,旧产品不行了,引进一套新技术新设备新的生产线,就马上可以生产出一种新的产品来。而一位好的现代诗人也无须事先认领什么“标准”才去写诗,他会主动地理解现代诗的诗体形式,尽管这形式在现代诗中是如此的自由无定,似乎没有了任何的文体边界,但若下心体会,这个“自由”还是有它基本的、区别于其他文体的语言形式,以及基本的不可或缺的诗美元素,且已潜移默化为诗人写作的经验之中。同时,一首诗必须有它自己的生命,由自己内在的生命波动与压力所驱使,尤其在现代诗这里,“成就最高的诗往往拒绝接受任何一种韵律或既成的模式,因为形式只能由诗人的创作动力来决定,当这种动力迸发时就会采取适当的表达形式。”[6]
说到底,谁能“标准”闪电的样式和花叶的绽放呢?或换一个角度,从诗歌接受方面而言,谁又能在今日文化语境下,实现调千口而适百家的美好愿望呢?
于是重新想到我所生造的那个“动态诗学”的命名。
新诗是一个伟大的发明,一个自在自足并富有生殖力的伟大新生命。新诗肯定会按照现在已普世性的运行惯性或叫做传统(新的诗歌传统)发展下去,不可逆转。而包括“诗歌标准”讨论在内的一切有关新诗或现代汉诗的理论言说,都可能只是一种“动态诗学”式的后设性自圆其说,且不再幻想有多大作用于实际的诗歌发展;或许有一定的提醒作用,或对诗歌爱好者提升一点欣赏水平,但都无关紧要——正如魏天无在《新诗标准:在创作与阐释之间》一文中所指出的:新诗标准问题属于批评而非创作范畴,其目的不是为了束缚而是为了释放诗歌中“异己”与“抗议”的声音与力量。并由此提供多元化阐释空间。[7]
也许,只有真正认领了这样的可能与局限,我们才能真正说出点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