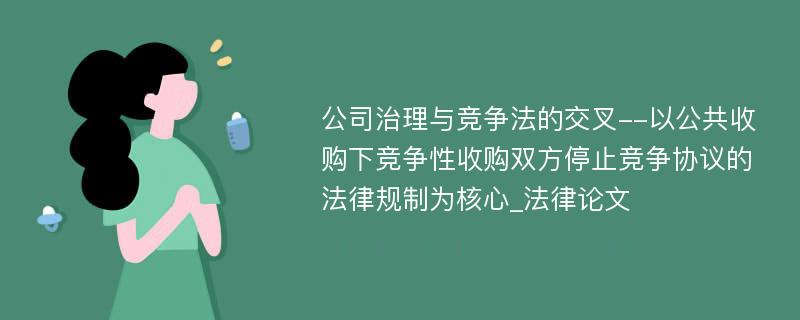
公司治理与竞争法之交错——以公开收购下竞争收购者间停止竞争协议之法律规制为核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竞争论文,公司治理论文,规制论文,竞争法论文,协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次
一、问题提出——公司控制权市场中可能产生的竞争法议题
二、公司控制权市场下公司法与竞争法的交错——公司本质理论下的观察
三、竞争收购者问的停止协议是否应受竞争法规范?——美国法下的分析
四、公开收购下公司控制权市场的特性分析
五、我国台湾地区现行法下竞争收购者间的停止协议是否应受到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的规范?
六、结论
一、问题提出——公司控制权市场中可能产生的竞争法议题
近年来,公司治理议题为公司法学界关注的焦点,各方亦无不努力希望藉由各种机制,促进公司治理目标的达成。在台湾,① 从外部董监事制度的引进、董监事责任的确立、审计委员会的设置、股东会与股东权强化等内部治理机制的建构,到制定“企业并购法”、增修“证券交易法”等强化“公司控制权市场”等外部治理机制,台湾公司治理相关架构已逐步完善与确立。
其中,公司控制权市场(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对于公司治理的正面意义亦为各方所肯认。透过公司控制权市场的运作,使公司控制权能移转至更有效率的经营团队,从而达成公司价值极大化的目标。而“公司控制权移转”的方式很多,台湾于2002年修正“证券交易法”(以下称台湾“证交法”)新增的第43-1条“公开收购”(tender offer)为其中之一,近年来也颇为常见。
本文拟研究公开收购下,公司控制权市场各方参与者间所可能从事各种竞争与合作行为,是否应受到台湾“公平交易法”(以下称台湾“公平法”)下“联合行为(collusion,近似内地《反垄断法》下之垄断协议)”的检验,② 以及其检验标准为何等问题进行分析,以进一步了解台湾“公平法”与公司、证券法规间的交错关系。
一般而言,倘论及公司控制权市场下,竞争法与公司、证券法规间的关联性时,论者多能立即联想公司间进行并购时,除应符合公司、证券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外,还应该受到“竞争法”下反垄断的相关规范,除此之外,恐怕再难想象其间还有其他关联性了。然以下案例或者可以引发吾人不同的思考面向。
1988年年初,美国Campeau与Macy两家公司对Federated百货公司发动竞争收购,双方都势在必得,导致收购价格不断上升。同年四月初,Campeau与Macy这两家竞争收购者深觉如此竞争下去,将使两败俱伤,故双方达成协议,由Macy放弃竞价,以交换Campeau承诺支付Macy为参与此一公开收购所支出的成本,包括律师、财务顾问等费用共计6千万美金,Campeau同时承诺在取得Federated经营权后,将同意出售Federated的两个部门给Macy公司。此一协议使Campeau与Macy两家公司皆大欢喜,但却惹恼了Federated的股东,股东们认为竞争收购者间的停止竞争协议,破坏了竞价的市场竞争机制,造成股东的损害,故以协议行为违反美国Sherman Act(以下称《谢尔曼法》)为由提起诉讼。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本案中,认为《反托拉斯法》不应涉入公司控制权市场,本案应受证券相关法规规范,而现行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以下称美国《证交法》)允许此一协议,从而判定原告败诉。③ 倘此类案例发生在台湾又将如何呢?
由本案衍生的另一个问题是,倘目标公司Federated百货的经营团队为防止敌意并购者收购成功,从而导致其经营权丧失,故采取各种“防卫措施”(defensive tactics)以逼退敌意并购者,例如Federated经营团队与收购者间约定,由Federated以高价买回收购者所持有的Federated股份(即为美国实务上常见的greenmail)。Federated经营团队此一行为亦可能产生如同前述Finnegan一案中Campeau与Macy间停止竞争协议所造成的限制竞争结果,所不同的仅在于协议的当事人由竞争收购者间转为目标公司经营团队与收购者而已。
关于目标公司经营团队面对敌意并购时得否采取防卫措施、与采取何种强度之防卫措施,美国向以公司法下之“受托义务”(fiduciary duty)作为公司经营团队行为的司法审查标准。而受托义务于此时为调和以下两种利益冲突之重要工具:一方面目标公司经营团队面临控制权可能丧失的“终局契约阶段”(end-game period),往往希望藉由防卫措施,拉高并购者的并购成本,达到限制竞争的效果,进而逼退敌意并购者;另一方面,目标公司股东面对敌意并购者之收购行为,由于缺乏集体行动的可能性,所以各自为自利行为的结果,反而造成整体的不利益,此时,就必须由经营团队从公司价值极大化的高度,击退无效率的并购者,或藉由防卫措施的使用,拖延敌意并购者的公开收购时间,以便吸引更多的竞争收购者加入竞价,从而达到增加竞争的效率结果。美国透过法院判决的不断累积,已形塑出敌意并购下董事受托义务的标准,以美国德拉瓦州为例,知名的Unocal test即以合理性原则及比例性原则,作为审查标准,其中合理性原则要求董事仅能对具威胁性、对股东不利的敌意并购采取防卫措施,比例性原则则要求董事采取防卫措施时,不能产生阻却所有并购要约的效果。④ 又Revlon test下,法院甚至赋予董事有寻求其他更佳并购者的义务。⑤ 也就是说,在公司价值极大化的目标下,董事防卫措施的实施仅能排除对公司有害的敌意并购,必要时董事也有促进公司控制权竞争的义务,显然,美国公司法下的受托义务亦隐含有竞争法的原理原则。
然而敌意并购者间之停止竞争协议行为,虽也有限制竞争的可能性,但除非敌意并购者为目标公司的控制股东从而对目标公司与其少数股东负有受托义务,否则其行为将无法以受托义务绳之。也就是说,从目前美国法规范与法院实务上观之,目标公司经营团队的各项防卫措施,美国法上以受托义务为检验标准,以防止不当限制竞争的防卫措施的产生,而美国法下对于竞争收购者间的限制竞争行为却不加规范,显见其立法上与法律适用上的不平衡。
限于篇幅,本文拟以前述Finnegan一案为模型,论述公开收购下,竞争收购者间的停止竞争协议是否该当台湾“公平法”下的限制竞争行为中之联合行为,并以此作为研究竞争法与公司、证券法规之间关联性的起点。
二、公司控制权市场下公司法与竞争法的交错——公司本质理论下的观察
一般多认为,竞争法、公司法与证券法规,此三法规的规范目的不相同,各有管辖场域、互不相干涉。台湾“公平法”的规范目的在于维护交易秩序、保护消费者利益,并以调整整体效率与配置公平为核心;⑥ 而“公司法”则以一公司组织内部利害关系人间的权利义务配置与利益冲突为规范核心;至于“证券交易法”,则主要规范以有价证券为金融工具的资本市场,以促进证券市场效率、衡平市场参与者的关系为重点。虽然“公平法”与“证交法”均为以“市场”为规范对象,但或有论者认为“公平法”所规范的“商品或服务市场”,与“证交法”所规范的“有价证券市场”不同;也就是说,公司所生产制造的商品或服务所构成的市场受“公平法”规范应属无疑,但公司所发行的股份与其所制造的商品或服务不同,应不受“公平法”的规范。各法规彼此之间,各有管辖场域、互不相干涉。
但此一看似清楚明白的法规范管辖场域界限,近年来在美国却受到不少质疑。最主要系受到美国公司法学界关于“公司本质理论”(the nature of the firm)改变的影响。现今美国公司法学界多采“公司契约理论”(contract theory),⑦ 认为公司为一连串明示或默示契约所形成的“契约连锁点”(nexus of contracts)。⑧ 在此一概念下,公司系藉由各种各样的合同关系与市场参与者进行资源的交换,这些市场参与者包括上下游供货商、消费者、股东、债权银行、高管人员、职工等。则什么是“公司内契约”,又什么是“公司外契约”呢?公司规模与影响力,透过分割、外包(outsourcing)、融资租赁(financial leasing)、转投资、合并、策略联盟或合资等方式,或大或小,公司内外的分界逐渐模糊,因之,以公司内外作为区别公司法与其他规范的依据,即失其依恃。不仅理论上无从区辨公司内外,过往被称为“黑盒子”的公司组织,伴随着资本市场对于公司治理的要求、揭露规范的重视与科技的发达,原本外人难以一窥其堂奥的情况,已逐渐改变。
当然,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在公司契约论下,合同订立自由、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界限,与法规范介入的必要性与强度为何。也就是说,既然认系“合同”,则法规范介入的正当性为何?
以台湾法规范为例,公司与员工间的劳动合同,由于存有人力资源的“专属性投资”(firm-specific investment)、缔约地位不平等,及信息不对称等特性,全然放纵当事人自由订立合同或依寻市场竞争机制,往往造成“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的结果,故有“劳动法”等相关法规加以调整,而“公司法”涉及职工者也不在少数,例如台湾“公司法”第235条员工分红,⑨ 以及第267条第1款“职工优先认股权”等,⑩ 均透过“公司法”以强制规定的手段达到公司价值极大化的目的;至于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所形成的市场,一般则认为并非商业化的商品或服务,同时为了保护劳工赖以为生的劳动力,其关于集体劳动合同的谈判,系以限制竞争为手段以达成维持职工与用人单位间的力量对等,原则上不受“竞争法”的规范。(11)
又以公司与银行间的授信契约为例。银行作为公司的债权人,受股东仅负有限责任的影响甚深,纵使银行可以透过契约条款调整可能产生的风险,且银行与公司间往往被视为力量对等的契约当事人,然契约本身亦有其成本,为降低公司取得借贷资金的成本,台湾“公司法”即规定第167条“禁止公司买回自己之股份”、(12) 第237条“盈余公积之提列”等。(13) 此外,即使一般认为契约自由性质最强的公司与银行间的授信契约本身,近年来也受到我国台湾“公平交易委员会”对于其经营行为可能涉及台湾“公平法”规范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关注。(14)
也就是说,过去认为界限分明的公司内与公司外的法规范划分方式,已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应是,倘公司为契约的连锁点,则在契约自由与市场价格机制功能的局限性下,法规范应否介入与如何介入,才是应予关注的焦点。
三、竞争收购者间的停止协议是否应受竞争法规范?——美国法下的分析
关于竞争收购者间对于停止竞争的协议行为,是否会生限制竞争的效果,从而应予限制。此一议题在美国的研究,尚不多见,学者Rock分析,这可能与在美国同时讲授“公司法”与“竞争法”的学者为数不多有关。本文亦认为,亦可能系受到以下两因素影响。
首先,“公司契约理论”成为公司法学界的通说也不过是近十几年的事,(15) 学者透过契约理论逐渐解开公司组织的“黑盒子”,并且重新审视公司组织的本质以及其与其他市场参与者间的关联性。因之,过去将股份买卖视为公司内部事务而认为不受竞争法管辖的看法,才逐渐受到挑战。
其次,关于“公司股份”是否为美国《谢尔曼法》的规范客体,美国联邦巡回法院曾有不同意见。首先,联邦第三巡回法院于1985年Kalmanovitz v.Heileman一案中认为,公司股份并非《谢尔曼法》第1条所谓的“trade or commerce”,是故股份买卖应不受竞争法的管辖;(16) 然联邦第二巡回法院于1990年Finnega一案中却采肯定见解,认为否定说将不当地限缩《谢尔曼法》的适用范围。(17) 联邦最高法院于驳回本案上诉理由书中认为,第二巡回法院于本案的判决并未与联邦最高法院的见解抵触,亦未与其他巡回法院的见解相冲突,故维持本案二审判决。(18) 意即,公司股份为《谢尔曼法》所规范的“trade or commerce”此一争议问题,在Finnegan一案中业已确立。
此外,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2007年Billing v.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 Ltd.一案中,亦可视为最高法院再次确认股份为竞争法的管辖客体。本案中系一群购买IPO股份的投资人以销售IPO股份给他们的证券承销商为被告,主张承销商之间约定仅能出售IPO股份给同意“laddering agreement”或“tying agreement”的投资人的协议行为,违反《谢尔曼法》第1条与《Clayton Act》(有译为《克莱顿法》)第2条。(19) 本案中,法院与诉讼当事人已经未对公司股份是否应受竞争法管辖的问题予以着墨,双方当事人的论辩与法院判决均集中在分析竞争法之“默示除外原则”(doctrine of implied revocation)于股份买卖及证券市场的适用判断。所谓“默示除外原则”,系指倘于具体个案中,适用竞争法将会破坏其他部门法,例如联邦证券法规,对于该行为或市场的规范目的,亦即竞争法与其他相关法规间存在“明显冲突”(plain repugnancy)时,纵使联邦证券法规并未明文排除竞争法的适用,法院仍应基于“默示除外原则”排除《反托拉斯法》的适用。(20)
以下分别就第一“公司股份是否为《谢尔曼法》的规范客体”,与第二“联邦证券法规对于公司控制权市场的规范,是否应优先于(preempt)《谢尔曼法》的适用,以及证券法律法规是否肯认竞争收购者的停止竞争协议的存在”两大议题,分析介绍美国实务见解的演进与学者看法。
(一)公司股份是否为《谢尔曼法》的规范客体?
1.美国联邦第三巡回法院于Kalmanovitz v.Heileman一案的判决
关于公司控制权市场是否受反托拉斯法的管辖,早期美国联邦法院判决多采否定说,以最具代表性的Kalmanovitz v.Heileman一案为例,(21) 联邦第三巡回法院援引联邦最高法院1940年于Apex Hosiery Co.v.Leader一案,(22) 认为《谢尔曼法》第1条所谓的“trade or commerce”,系指“commercial 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ing of goods or services”,而本案中投资人间买卖股份的行为,并不符合法规范所定义的“商品或服务”(“the purchase or sale of stock by investors does not fit easily within the definition of goods or services as used by the antitrust laws.A seller of shares of a particular company is not engaged in the business of selling shares as an ongoing trade or business”)。(23)
2.学者评论
对此,有学者批评认为,联邦法院的前述判决,事实上是不当地限缩了美国国会关于《反托拉斯法》的立法意旨。也就是说,美国国会系基于美国宪法之“商业条款”(the commerce clause)对于“州际商业”(interstate commerce)的广泛立法权限的前提下制定《反托拉斯法》,故除非立法者另有指明外,应无理由排除公司控制权市场的适用。(24) 事实上也有不少联邦法院判决肯认《反托拉斯法》下“trade or commerce”的定义,应该涵盖所有国会基于商业条款下的权限范围,(25) 而很显然的是,国会的立法权包含州际的公司控制权市场,此亦为美国国会得以制定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与1968年针对公开收购的《the Williams Act》(以下称《威廉斯法》)的原因。
Rock进一步指出,第三巡回法院于Kalmanovitz一案中援引194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Apex Hosiery一案的判决,而该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将商品或服务的概念引入《反托拉斯法》之适用中,其目的必非在限制《反托拉斯法》的适用范围,其目的系将《反托拉斯法》的管辖范围——“商业活动”(commercial activities)与非《反托拉斯法》的管辖范围——“政治或劳工活动”(political or labor activities)予以明确划分。(26) 也就是说,第三巡回法院在未提出何谓《谢尔曼法》下适用的“商品或服务”的明确标准下,即认定股份并非商品或服务,从而作成公司控制权市场并非《反托拉斯法》管辖范围的判决,不具合理性,(27) 其亦错误解读联邦最高法院关于《谢尔曼法》下“商品或服务”的见解。
3.美国联邦第二巡回法院于Finnegan v.Campeau Corp.一案的判决
除学者对前述第三巡回法院于Kalmanovitz一案中认定公司股份并非商品的见解有所批评外,晚近美国联邦第二巡回法院于Finnegan一案中亦采反对见解。(28) 第二巡回法院认为,本案一审法院于判决中引用第三巡回法院在Kalmanovitz中对于Apex Hosiery一案中最高法院的判决系属误解。也就是说,第二巡回法院认为,公司股份为《谢尔曼法》第1条“trade or commerce”衍生而来的“goods or service”应属无疑,并不因为公司股份为“无体物”(intangibles)而非“有体物”(tangible commodities)而被排除在商品的认定范围之外。第二巡回法院同时认为,联邦最高法院于数件案例中,对于商品的定义系采较为“宽泛”(boarder)的定义,例如United States v.Socony-Vacuum Oil Co.一案中,最高法院认为限制州际货物交易价格的“合同”应该受到《反托拉斯法》的管辖;United States v.Philadelphia Nat'l Bank一案中,最高法院认为“银行”并不会因为所提供者为信用或其他无实体的服务而非有实体的商品,而排除《反托拉斯法》的适用。
(二)美国联邦证券法规对于公司控制权市场的规范是否应“优先”于(preempt)《反托拉斯法》的适用?
1.实务见解
美国联邦第三巡回法院于Kalmanovitz一案认为,倘于公司控制权市场下适用《反托拉斯法》,将会破坏联邦证券法规对于公司控制权市场的规范目的,故即使联邦证券法规并未明文排除《反托拉斯法》的适用,法院基于“默示除外原则”,仍应排除《反托拉斯法》的适用。联邦第三巡回法院同时认为,所谓的“公开收购”,通常系指任何人(an individual)或一群体(group),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对于目标公司的股份进行要约收购的行为。(29) 也就是说,公开收购本质上并不排除数人透过公开收购的方式共同取得目标公司的股份,因之,倘本案行为受《反托拉斯法》的规范,将会破坏或妨碍美国证券交易法规的规范目的。
联邦第二巡回法院于Finnegan案中,(30) 亦采相同见解。第二巡回法院首先说明,本案关于竞争法是否适用于证券交易法相关案件中的问题,将依联邦最高法院于“Silver”、(31)“Gordon”,(32) 与“United States v.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33) 三个案件中所确立之“默示除外原则”判断之。联邦法院认为,默示除外原则排除竞争法于具体个案下的适用并非常态情况,而仅于竞争法与其他相关法规存有“明显的冲突”时,始有此一原则的适用。(34)
简言之,当竞争法与其他规范没有冲突时,则不应排除竞争法的适用;而当竞争法与其他规范有冲突时,则应排除竞争法而优先适用其他法规范。所以重点即在于,何种情况始构成所谓“竞争法与其他相关法规间的明显冲突”?第二巡回法院藉由对于前述三个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分析,来确定默示排除原则于本案的适用情况。
Silver 一案中,纽约证券交易所拒绝继续提供非会员连接使用交易所的报价系统(stock ticket service),联邦最高法院以美国证管会(SEC)欠缺对于证交所此一系争行为的监督权为由,认定并无竞争法应予排除适用的情况。(35)
Gordon一案中,最高法院以SEC依照1934年《证交法》的规定,对于纽约证券交易所有关制定固定佣金费率的行为具有管辖权,且相关费率的制定必须经过SEC的许可,从而认定纽约证券交易所此一系争行为应专属SEC管辖,竞争法于此应默示排除适用。(36) 法院认为,竞争法的目的在于保护竞争,然倘于本案中适用竞争法,将可能破坏SEC基于健全证券市场发展所制定的相关政策与法规范。(37)
于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一案中,最高法院认为,证券商公会制定有关销售共同基金的行为规范,依相关《证券法》的规定,应受SEC的管辖与允许后,始得有效拘束公会会员,故本案亦无竞争法的适用。(38)
综合前述三个判决,可知联邦法院在判断具体案件中竞争法是否应默示排除适用的重点在于,倘其他法规范或主管机关对于系争行为已有严密的法规范或监督,且该规范允许系争行为,而竞争法禁止该行为时,竞争法即应无适用的余地。
回到Finnegan一案,关于系争行为—竞争收购者间的停止经营者竞争协议行为—是否应受竞争法规范之关键点,则在于此一停止竞争协议行为是否已受《证券法》与证券专责机关的完整规范与监督,且在该法规范下是否允许系争行为,而倘竞争法禁止此一行为则将破坏证券法的有效实施时,也就是证券法规与竞争法有明显冲突时,竞争法应予排除适用。
对此,第二巡回法院认为应有“默示除外原则”的适用。其认为竞争法与国会于1968年为规范“公开收购行为”所制定的《威廉斯法》的立法目的明显不一致,且为使威廉斯法与其他证券法规得以顺利实施,竞争法的排除适用将是必要的。(39) 兹分述第二巡回法院的理由如下:
(1)《证券交易法》允许收购者基于共同取得目标公司股份所为的合意行为。第二巡回认为,《威廉斯法》中第14(d)条赋予SEC制定相关规范以保护公开收购时目标公司股东应知悉相关信息权利。根据此一授权,SEC要求公开收购者必须申报Schedule 14 D-1,其中公开收购者应申报事项中,包括“...Describe any contract,arrangement,understanding or relationship...between the bidder...and any person with respect to any securities of the subject company(including...joint ventures...),naming the persons with whom such contracts,arrangements,understandings or relationships have been entered into...”(40) 也就是说,倘公开收购者与其他公开收购者之间有任何协议时,均应予以揭露。
此外,第二巡回法院亦指出,依据美国《证交法》第14(d)(2)条规定,(41)“When two or more persons act as a partnership,limited partnership,syndicate,or other group for the purpose of acquiring,holding,or disposing of securities of an issuer,such syndicate or group shall be deemed a‘person’for purposes of this subsection”。也就是说,倘二人以上基于共同取得目标公司股份的目的而为结合时,无论所采取的结合形式为何(例如以契约方式),在本条规范下均被视为同一人。
基于此,第二巡回法院认为,在《证交法》的规范下,本来就允许收购者间进行协议行为以共同取得目标公司的股份。而针对本案原告主张应将收购者的协议行为区分为系在开始公开收购程序前所为的共同收购协议,或系在公开收购进行中所为的停止竞争协议,而主张公开收购程序前所为的协议行为,始为相关证券法规范所允许,第二巡回法院则认为,《威廉斯法》与SEC相关规则并未将收购者间的协议行为予以区别,故原告此一主张无理由。(42) 第二巡回法院进一步认为,倘公开收购进行过程中,竞争收购者间达成协议行为,此时只要依证券相关法规完成更新申报内容的程序,(43) 即已达到保护投资人之立法目的。(44)
(2)SEC有权制定相关规则以禁止竞争收购者间停止竞争协议,但SEC并未制定。此外,本案原告亦主张SEC并无权限同意或禁止如同本案竞争收购者间的停止竞争协议,盖证券法规仅授权SEC就公开收购的信息揭露部分制定相关规则,是故原告主张竞争收购者间的停止竞争协议应回归竞争法的管辖,第二巡回法院也否定原告此一主张。第二巡回法院认为,从SEC陆续制定了许多公开收购的相关规则,例如目标公司的股东“有撤回其应募之权”,以及公开收购必须对目标公司所有股东为之,而不能仅对特定股东为之的规范来看,这些规范本质上与信息揭露并无直接的关联性。(45) 也就是说,SEC有权制定禁止竞争收购者间的停止竞争协议的相关规则,而其系有意地选择不禁止竞争收购者间的停止竞争协议时,法院法基于默示排除原则应予尊重。(46)
(3)倘禁止竞争收购者间的停止竞争协议,将会打击市场参与者进行公开收购的诱因,从而违反《威廉斯法》的立法意旨。第二巡回法院指出,美国国会系在体认公开收购作为一有效监控目标公司经营团队经营效率的手段,从而不应被压抑的前提下,制定《威廉斯法》。(47) 竞争法介入禁止竞争收购者间的停止竞争的协议行为,将会打击公开收购活动的进行,且将破坏《威廉斯法》期能达到寻求目标公司、目标公司股东、目标公司经营团队与公开收购者间权利义务平衡的政策中立原则(neutrality)。第二巡回法院认为,倘竞争法介入干预,将使目标公司股东取得短期优势,且从长期来看,会因公开收购数量之下降而导致目标公司现任经营团队继续掌握公司控制权,(48) 此绝非立法者所乐见者的结果。(49)
基于前述理由,联邦第二巡回法院在Finnegan一案中,虽肯认公司股份为《谢尔曼法》第1条“trade or commerce”衍生而来的“goods or service”,但最后仍以“默示除外原则”判断本案应受《证交法》而非《反托拉斯法》的管辖。本案原告Finnegan针对第二巡回法院关于“默示除外原则”之适用问题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之声请,联邦最高法院最后以第二巡回法院适用法律并未违反最高法院的见解为由驳回本案原告之上诉的声请。(50)
2.学者评论
(1)对第三巡回法院的判决评论。Professor Rock则认为,第三巡回法院于Kalmanovitz一案中之见解显然对于本案中原告的主张有所误解。本案原告所主张被告违反竞争法的行为,并非数人约定共同进行收购要约之“联合公开收购行为”(join bidding),而系公开收购下的竞争收购者间的停止竞争的协议行为。Professor Rock进一步分析认为,此两种共同行为看似相近,实则不同。后者为竞争者间的价格约定(price-fixing),为典型的限制竞争行为(naked restrains of trade),在《反托拉斯法》的评价下,往往会被认定为“当然违法”(per se illegal),除非有“合理原则”(the rule of reason)的适用;而前者则可能产生促进竞争的效果(procompetitive),例如联合公开收购行为可能有促使规模较大的公司也可能成为公开收购下的目标公司,使得原本不可能透过一己之力参与公开收购竞争的市场参与者,透过合作而参与,从而增加了公开收购下的竞争机制。(51)
Rock进一步分析,由于包括《威廉斯法》在内的联邦证券法规,并未明文排除《反托拉斯法》的适用,故依联邦法院向来的见解,默示排除原则的适用应予以相当的限缩,(52) 仅于《反托拉斯法》与证券法规间有“明显抵触”,而适用《反托拉斯法》将会破坏证券法规规范范围的计划时,始得排除《反托拉斯法》的适用。(53) 而于本案中,联邦证券法规的规范目的,与《反托拉斯法》并无冲突,《威廉斯法》中特别强调公开收购过程中的信息揭露机制,事实上也是为了强化竞争机制所作的降低交易成本的安排。是故学者认为,《反托拉斯法》于本案仍应予适用。
亦有学者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United States v.Philadelphia National Bank一案中判决,(54) 来反驳法院于Kalmanovitz一案的谬误。Philadelphia National Bank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特别指出,本案的关键点在于,《反托拉斯法》是否适用于银行合并案中,特别是在美国国会于1960年针对银行业的合并,制定有1960年《银行合并法》(the 1960 Bank Merger Act)。法院最后强调,纵使银行之合并行为应受《银行合并法》的规范,然而该法并无明文排除《反托拉斯法》适用,同时适用克莱顿法亦不会与银行合并法产生冲突或抵触。(55) 也就是说,即使国会以特别法对于银行的合并行为进行广泛的管辖,只要该法与竞争法并无冲突,即无排除竞争法适用的理由。
(2)对于第二巡回法院的评论。Fried等教授亦认为,从Finnegan一案来看,美国《证交法》与竞争法的规范目的本来不同,两法系在解决与处理不同的问题,而非有所冲突,是故应无竞争法应默示排除的情况。(56) 其认为,竞争法的目的,主要系在防止限制竞争行为影响市场竞争秩序;而《证交法》的规范目的,则系透过信息公开以防止市场诈欺行为,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是否会造成限制竞争或不公平的情况,向来非其所关注。(57) 是故,SEC之所以选择未制定相关规则以禁止竞争收购者间的停止竞争行为,并非有意侵入其他部门法的规范范畴而创造一个不受竞争法规范的交易市场,其系在证券相关法规的规范目的下,制定相关的规则。
3.本文见解
首先,本文认为应予以厘清的是,第二巡回法院所称介入禁止竞争收购者间的停止竞争协议将减少公开收购的数量,是否属实。纵使为真,但仅为公开收购的数量增加,但质量未增加的情况,是否为立法者所乐见?本文认为答案应是否定的。如同第二巡回法院于判决中所言,立法者认为公开收购为汰换公司无效率经营者的重要工具,显然立法者希望鼓励的是能促进效率、增加公司价值的公开收购行为,同时遏制效率减损的公开收购,而非一味地追求数量的增加。本文认为立法者期待寻求目标公司股东、经营团队,与并购者间的权利义务平衡,也应在促进有效率并购行为发生的前提下开展。否则,倘仅追求利害关系人间之形式上的平等,则立法者也无必要在《威廉斯法》下,赋予目标公司股东可随时“撤回其应卖之权利”,同时要求收购者必须遵循相关信息揭露原则与程序、必须以相同价格购买原则等规则之制定。也就是说,立法者显然了解公开收购下各个参与者间所形成的公司控制权市场,必定存有其特殊性,使得此一市场无法单靠参与者间的行为,自动地达成效率的目的,为了矫正此一市场失灵、促进市场的有效率运作,才有订立包括信息揭露以内相关规范的必要。
其次,竞争收购者间的停止竞争协议就如同一般典型的围标行为——“水平价格联合行为”(horizontal price-fix),均会因限制竞争而产生资源配置无效率,以及财富分配不公平等问题,则在围标行为多半被视为“当然违法”的情况下,除非另有坚强的理由,否则法规范似无由给予竞争收购者间的停止竞争协议不同的对待。也就是说,究竟是何理由可以正当化公司控制权市场不受竞争法的规范,还是公开收购下的公司控制权市场应其特殊性,反而更应维护其市场竞价机制?本文以下即从公开收购下公司控制权市场的特性进行分析,并进一步分析公开收购下的公司控制权市场与一般的围标行为的异同为何,以及竞争收购者的停止竞争协议所产生的资源效率或财富分配结果为何。
四、公开收购下公司控制权市场的特性分析
本文认为,由于公开收购下的公司控制权市场有以下的特性,故维护此一市场的竞争机制、防止竞争收购者间进行破坏竞争的协议行为,将是十分必要的。
(一)公开收购下目标公司股东的应卖压迫效果
一般而言,并购者以公开收购方式进行目标公司的股权收购时,收购价格自然会较市价为高,但却未必会高于目标公司股份的现在价值(即目标公司在现任经营者手中所产生的价值)。而只要收购价格比股份现在价值(value)低,纵使高于股份市价(market price),此一并购仍可能会造成价值减损的结果。面对此一情况,为了达成效率极大化的结果,目标公司的股东应拒绝应卖,不让经营较现任团队更无效率的并购者取得公司的经营权。然无论美国或我国台湾许多研究结果皆显示,目标公司股东仍相当有可能会同意以低于股份价值的收购价格,应卖其股份,(58) 此即所谓“应卖压迫效果”(coercive effect)。
兹分析此一应卖的压迫效果产生原因如下:(59)
1.首先,目标公司股东未必知悉股份的真实价值。在收购价格高于市价的情况下,必有股东会因此而将股份应卖于并购者。同时,何时发动公开收购的时间点取决于并购者,根据美国的经验可知,并购者往往于目标公司股价处于相对低档时进行公开收购,股东应卖的诱因因而增加。
2.就算某些股东知悉此一收购价格低于股份真实价值,此一讯息亦未必能在股东间充分传播,也未必能获得多数股东支持,并且以一致地行动拒绝应卖,来抵制并购者的低价并购;(60) 同时,并购者无须取得目标公司全部股份才能获得控制权,在股权较为分散的公司,并购者往往只要取得20%的股权,再透过委托书征求等其他机制的配合,即可有效控制目标公司股东会与董事会。
3.同时,股东间对于股份价值高低或有不同意见,也就是说,可以预期的是,只要收购价格高于市价,总是会有股东应卖其股份,个别股东很难影响公开收购的结果。
4.因此,在预测其他股东极可能会应卖股份导致收购者公开收购成功而取得目标公司控制权的情况下,对于知悉收购价格事实上低于股份价值的股东(假设为A股东)而言,即陷入是否要应卖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A股东一方面明知收购价格低于股份价值,其不应该应卖;另一方面,A股东会发现倘其不应卖而成为公开收购成功后目标公司的少数股东时,其将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理由有二:
首先,A股东知悉收购价格低于真实价值,表示并购者并非较有效率的经营者,所以倘其不应卖,则其在目标公司股份的价值亦将低于公开收购前的价值。如此一来,A股东不仅没有取得高于市价的收购价格,其所持股份价值也将低于公开收购前的价值,对A股东而言,不应卖将面临双重损失。
其次,收购者在以公开收购方式取得控制性持股后,往往会接续进行目标公司与并购者间的合并,并且多会以现金作为对价,进行第二阶段的“逐出式合并”(cash-out merger)。由于收购者已经取得目标公司的控制权,其对于此一目标公司与并购者间的合并条件,例如合并时间点与合并价格,具有决定的实力,并购者也有相当动机,选择对自己较有利的时间点与条件与目标公司进行合并。例如,并购者会选择目标公司股价较低的时刻进行合并,甚至刻意操弄目标公司的盈余以创造目标公司的低市值。
综上所述,未必知悉股份真实价格的股东,极有可能会因为公开收购价格高于市价而应卖其股份;而知悉公开收购价格低于股份价值的股东,会发现不应卖相较于应卖,其个人的财富将会减少,从而必定会做出应卖的决定。也就是说,因为收购价格低于股份价值,虽然此一股东会希望此一公开收购破局,但由于体认到“集体行动问题”(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其会希望在他应卖下,其与股东都不要应卖,因为如此一来,一方面可以使公开收购破局,一方面可以防止万一公开收购成功时,他也不会因为变成目标公司的少数股东而受到更差的待遇。当然,一旦目标公司股东都这么想时,无论收购价格是否高于股份价值,收购者的收购势必马到成功。这不仅将造成目标公司股东的损失,亦可能使公司控制权流向会减损公司价值的经营团队的手中。但倘此时有竞争收购者出现,则目标公司股价即有可能因为竞价机制而往上攀升,使公司控制权有机会流向较有效率的经营者手中,目标公司股东也可以因此获得较高的利益。
以上分析可以说明,为何证券市场单单仅以“揭露”原则为规范模式,实无法有效达成健全证券市场、促进公司价值极大化的目的,本文认为促进公司控制权市场的竞争机制,在第一阶段透过竞价机制,促使可以极大化目标公司价值的并购者出现,应是另一个可以思考的方向。
(二)公开收购下竞争收购的效率结果分析
1.对目标公司股东、竞争收购者、目标公司,与目标公司经营团队的影响
如前述Finnegan实例可知,竞争收购者间的协议行为会产生以下的利益冲突结果。首先,对于达成协议的竞争收购者而言,当然有利,借此停止竞争的协议,压制可能节节高升的收购价格,降低并购成本。然而,对于目标公司股东而言,却丧失其可透过公开收购的市场竞价机制,以获取较高价金的机会。
竞争收购者间的停止竞争协议,不仅会大幅降低目标公司股东的利得,(61) 也由于破坏公开收购下的价值竞争机制,使得最后取得公司经营权的收购者,不一定为在价格竞争中出价最高者,也就是说公司的控制权将无法确保移转至能将公司资产运用最大化的经营者的手中,从而影响目标公司价值极大化的结果,甚或可能使公司资产落入比现任经营团队更差的并购者手中。
简言之,公开收购制度的核心价值,除欲使目标公司的股东有机会于并购者以公开收购方式取得控制性持股的交易时,能分享其股份高于市价的溢价收入外,另一个重要的目的在于,公开收购方式有机会创造竞争性公开收购,使公司控制权透过市场价格机制,达到有效率移转的结果。
2.对于“财富分配”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竞争收购者间的停止竞争协议行为将会产生“财富分配”(distributional effects)与“资源配置效率”(allocation effects)两种竞争法所关注的影响。(62)
先从财富分配的角度分析。倘竞争收购者以协议方式停止竞争,则目标公司股东与收购者间即产生财富分配的利益冲突问题。也就是说,收购者间保留了原本将移转至目标公司股东的利益。收购者间的协议在财富分配议题上所产生的事后效果十分明确,然而,收购者的协议对于财富分配的事前效果有何影响,美国学者间却有不同看法。Easterbrook & Fischel认为,倘不允许竞争收购者间为停止竞争的协议,则可能会降低公开收购的数量,但Bebchuk与Gilson则认为,停止竞争协议的禁止并不会影响公开收购的总体数量。(63) 关于此部分,详见本部分第四点的论述。
再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分析。以下兹举一例说明,为何竞争收购者间的停止竞争协议将有遏阻其他竞争收购者加入竞争的效果,而且可能造成可将目标公司极大化的收购者无法取得公司控制权的不当结果。
假设目标公司Target目前股价为20元,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为100股,公司大股东Controller持股20股,平时借由委托书等方式可以实质控制公司运作。现有三组人马欲对Target进行公开收购,即Bidder A、Bidder B与Bidder C,各分别持有15股,而根据Target股权分散程度,任一股东只有持有35股以上,即可稳定地掌握公司控制权。假设在一允许竞争收购者间进行停止协议的法规范管辖范围内,Bidder A出价每股25元,Bidder B出价每股30元,Bidder C出价每股32元,且各自均先表明收购5股(收购者不一定会在第一次出价时即表明预购买取得控制权的必要股数,而可能会先观察市场反应与竞争对手的出价行为,同时对于之后的收购策略预留弹性空间)。倘今Bidder A与Bidder B达成停止竞争协议,由Bidder B继续参与竞争收购,而Bidder A所持股份将支持公开收购结束后,Bidder B当选公司经营团队,以交换Bidder B将填补Bidder A因此所受的损失(假设为50元)并承诺在成为公司经营团队后,将Target两个部分转售于Bidder A。且为确保决议的有效实施,双方成立表决权信托(voting trust),以便日后共同行使投票权。此时,Bidder A与Bidder B合计持有target股份已达30股,只要透过公开收购再取得至少5股即可达到控制target所需的35股。而倘Bidder C预与A、B一较长短,则其至少必须取得15股以上,倘Bidder C仍维持原本每股32元的出价,则Bidder C取得控制权的成本至少为480元。而竞争收购者A与B间的合作协议,将使Bidder B只要再取得5股,即可掌握公司经营权,显然此时Bidder B可以轻易地出高于Bidder C的每股收购价格以取得其所需的股数。其结果是,Target的控制权未必能由最有效率的经营者所取得。
当然,容有疑问的是,前例中,有无可能是由Bidder A或Bidder C间达成协议呢?此时是否反而有促进效率的结果?进一步说,竞争收购者间是否可以透过契约达到资源配置优化的效率结果?本文认为,此时契约调整资源配置的功能极为有限。理由如下:
首先,以本例而言,倘Bidder C不愿意于并购后将Target的两个部门释出给Bidder A,则两方的契约可能即无由成立。
其次,由于公司控制权市场中关于公司价格会产生所谓“偏好不确定”(preference uncertainty),所以此时以利用市场竞价模式将比契约模式更可以达到资源配置优化的结果。盖公司控制权市场与大豆等一般商品市场有所不同。大豆市场是由较多的买家、卖家所产生、商品数量庞大,也具有高度的可取代性,商品透过多次不断重复的交易,形成一个客观存在的市场价格,此一市场参与者仅为价格的接受者(price takers)。此时任一卖方与任一买方以一对一的契约进行交易时,卖方很容易知道其商品是否以极高价出售(亦即是否贴近或超过市场价格),卖方也可以以交易成本极低的方式,在市场中找寻其他买方。此时,契约机制即可协助卖方将资源转让于极佳的受让者手中。
而公司控制权市场则有所不同。首先,此一市场的参与者是有限的,市场上的每一家公司均有其独特性,很难找到完全相同的两家公司。其次,公司控制权市场较难产生一个客观存在的市场价格。盖一公司的市场价格相当程度取决于买卖双方关于目标公司价值之认定,而公司价值的高低系透过经营团队对于公司资产配置安排所决定。也就是说,公司价值的高低会受不同经营团队的经营、与不同组织进行不同的资源整合等因素影响。亦即,公司控制权市场下,不同并购者对于公司价值将有不同评价,且其间的差距可能颇大。
因之,在此公司价值不确定的情况下,倘以契约方式进行公司控制权交易,卖方往往会陷入“我不知道卖价是否极高,只知道比我高”的情况,契约机制使价格极大化的期待即受到相当的限制。而从效率角度,吾人期待的是以极低的交易成本,促使资源朝向极佳的方向流动的规范设计,透过竞争收购的机制,可以使所有可能的市场参与者,在交易成本极低的情况下,揭露其对公司价值的评价,从而增加公司资源配置极大化的可能性。(64)
另应补充说明的是,由前述目标公司Target之例吾人亦可知,即使在公开收购的竞争机制下,出价最高的收购者有时也未必为可将目标公司价值极大化的经营团队。盖收购者在公开收购时出价的高低,除了取决于并购者对于目标公司价值高低的评价外,亦受各收购者在公开收购之前所取得目标公司股份数量的多寡与总成本多少(取得股份之总支出)的影响。也就是说,并购者在公开收购前持有目标公司股份的数量越多、成本越低者,该收购者在公开收购时的优势越强,盖此时取得控制权所需的股数较少,即可以较高的单位价格取得其所需的股数。也就是说,收购者的总成本决定谁最接近价值极大化者,能支出总成本越高者,其越接近价值极大化者;然公司控制权的取得系取决于所得掌握的股数多寡(包括自己持有的股数或透过契约或信托支持自己的股数)。股份取得的总成本与所得掌握的股数间并无必然的关联性,盖公司股份涨涨跌跌,取得股数最多者不一定总成本最高,故不一定为价值极大化者;而取得成本最高者,未必持股最多,从而不一定能成为经营者。如此说来,公开收购下出价最高者,并不一定是价值极大化者,则吾人是否仍有维护公开收购下竞争机制的必要性?本文认为在限制或促进竞争的两种政策选择上,仍是以后者为较佳的规范模式,理由如下。
首先,竞价机制仍是协助确定股份等此类具有偏好不确定的商品,寻找出能极大化股份价值的市场参与者的重要工具。维持竞争机制,可以促使能支付最高成本的收购者,较有机会取得目标公司的控制权,也就越贴近价值极大化的效率目标。盖如前例,竞争收购者透过停止竞争的协议,可能因此降低其取得目标公司股份的总成本。此外,也可以降低公司控制权市场中,出现并非真心取得Target经营权的收购者,其系仅欲藉由等待与其他并购者间的合作协议以取得好处的投机者。此类投机参与者的存在,将严重破坏市场的价格机制,同时增加市场参与者的“竞租行为”(rent-seeking)。
另外一个值得附带一提的问题是,是否只要确保公司控制权市场的竞争,就可以确保结果必为有效率的,也就是说目标公司的控制权即会由效率极大化的并购者所取得呢?其实不然。如前所述,由于公开收购者以高于股份市场价格进行收购,多系运用两阶段并购策略(two-tier merger),致使目标公司股东在集体行动困难所产生的囚犯困境的情况下,往往会产生应卖的压迫效果。也就是说,纵使并购者的出价低于公司目前的真实价值,目标公司股东在追求个人价值极大化的情况下,仍会应卖其股份,则公司控制权则可能流向无效率经营者的手中。此不仅仅产生财富分配的问题,也会造成资源配置无效率的情况。然,透过健全公开收购市场有效率的竞争机制,也可能某一程度地矫治前述目标公司股东选择扭曲现象。简言之,本文此处所欲强调者为,要促进公司控制权市场成为公司治理的有效工具,尚须有许多措施的配合,而控制权市场竞争机制有效率维持,将是十分重要的一环。
(三)公开收购与其他订价、竞价形态的异同
如前所述,以一对一的契约方式欲达到资源配置极大化的目标,往往有其局限性,故市场会根据标的物的属性不同与市场参与者的属性不同,设计出不同的商品定价或竞价方式。
例如,有些商品系属卖方订有牌价者(posted price),如牛奶、药品的零售市场。属于此类的商品与市场,大多属于商品内涵较为简单,而且买方数量较多且单次商品需求量低者,故买方对于商品的价格并无议价的能力。又或者在工程招标案中,往往采取的是密封式投票(sealed auction),而取最低标或最有利标。前述两种市场倘发生市场参与者的水平价格拘束行为,无论在美国或我国台湾,吾人常见竞争法介入的身影。
而公开收购的定价与竞价方式,则比较类似一般所称的英国式拍卖法(oral ascending bid),亦即竞标者出价由下往上喊,喊价最高者得标。公开收购也是,收购者在目标公司的股份市价(相当于拍卖中的底价)的基础上,往上竞价,由出价最高者取得其所需的股份。此外,由于前述公开收购对于目标公司股东所造成的应卖压迫效果,公开收购往往成功。
市场参与者依循标的物不同的特性,设计出不同类型的竞价模式,每一种竞价模式均有其优缺点,本文研究目的不在讨论以公开收购的方式是否为最符合效率的控制权移转方式。然而根据研究,公开收购所采取的英国式拍卖法较容易发生竞争收购者间的协议行为而破坏其竞争机制。(65) 主要原因如下。
在具有牌价的商品市场中,卖方倘欲以联合行为约定商品的价格,例如约定不以一定价格出售商品,此时参与协议者往往会面临如何确保其他参与者亦能遵守协议的困境。盖此时任一参与者基于自利动机,往往会有违反约定的倾向,以便自己能在其他参与者以较高价格出售商品时,反而能以较低的价格卖出较多的商品以取得高额利润。此外,属于此类的商品与市场,大多属于商品内涵较为简单,而且买方数量多且单次商品需求量低者,故买方对于商品的价格亦无议价的能力。(66) 是故,参与者所为违反约定的行为,往往不容易被发现。所以,参与协议者为确保其他参与者均能遵守协议,必定会产生相当的监督成本与剩余损失(residual loss)。
而在公开收购下,由于各收购者系藉由合作而取得原本在竞价机制下,应给付目标公司股东的利益,而将保留的利益分配给参与合作的收购者,也就是说,参与合作的收购者因合作而利益,与前述于具有牌价的商品市场中,个别参与者系因不合作而取得利益有所不同。故显然,公开收购下的收购者较有动机遵守协议内容。此外,公开收购系在一段时间内,对于同一目标公司股份所为的竞价行为,各个收购者的投标行为如何一目了然,其违反约定的动机自然也较低。
也就是说,在吾人首先肯认竞争收购者间的协议行为会对资源配置与财富分配产生不良的影响的情况下,倘公开收购市场下竞争收购者多有动机进行协议行为,且此一协议行为的成本极低,则在如牛奶、药品等市场或工程招标中,竞争法均关注其市场参与者的联合价格拘束行为的情况下,则更容易受参标者协议行为影响的公开收购市场,是否亦应受相关法规范管制,则值得吾人深思。
(四)倘规范上促进公开收购下的竞争收购,是否会使公开收购发生的数量与几率降低?
Easterbrook & Fischel两位美国公司法学界的知名学者,于1981年哈佛法学评论的论文“The Proper Role of a Target's Management in Responding to a Tender Offer”中,关于公开收购下竞争收购将不利于并购效率的论述,(67) 引发了美国公司法学界的一番论战。Professor Bebchuk与Gilson针对Easterbrook & Fischel前揭文,分别于1982年先后发表文章予以评论,(68) 并认为公开收购下的竞争收购有利于并购效率。而Easterbrook & Fischel亦于1982年为文回应,并与Bebchuk的第二篇评论刊于同期的Stanford Law Review中。(69)
首先,双方均认为,公开收购作为公司治理的外部手段,对于市场参与者个体与整体财富的极大化均有其好处,所以应鼓励与促进公开收购的产生。然而,一旦有收购者(the initial bidder)对目标公司进行公开收购时,法规范是否应促进其他竞争收购者的出现(无论是否为目标公司的经营团队所引动者),双方则有不同看法。
Easterbrook & Fischel采否定说,其认为,公开收购的相关规范倘有利于竞争收购的形成,则将使市场上潜在收购者(prospective acquirer)丧失搜寻适合进行公开收购目标公司的诱因,从而最终将导致公开收购数量的减少。盖竞争收购者的出现,将使最初收购者所支出的搜寻目标公司的成本无法回收。基于这样的观察,Easterbrook & Fischel认为,相关法规范应作限制竞争收购产生的设计,包括目标公司的经营团队在面临公开收购时,应依采取消极做法,不应采取防卫措施。这样的见解,很明显地影响了第二巡回法院于Finnegan一案的判决结果,法院于判决中即认为,倘不允许竞争收购者为停止竞争的协议,将会妨碍公开收购的产生。从而第二巡回法院认为,允许竞争收购者间的停止竞争协议的法规范,始有益于目标公司股东与社会整体效率。
Bebchuk则力驳上述论点,其除系基于前述分析认为目标公司股东在公开收购时将面临应卖压力,从而主张应促进公开收购下的竞争收购的产生,Bebchuk亦认为竞争收购者的出现,并不会使最初收购者的搜寻成本无法回收,相反地,最初收购者反而可能因为竞争收购者的出现而增加其获利。
本文同意Bebchuk的主张,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首先,最初收购者的搜集成本是有限的。盖收购者往往会委请投资银行或顾问公司进行目标公司的搜寻与分析,而此一费用通常系以成功报酬(successive fee)的方式设计,也就是说,倘收购成功时,收购者再行支付较高的顾问费用,且此一费用往往相当具有弹性。(70)
其次,公开收购者在进行公开收购前,多半已先持有目标公司的部分股份,此举一方面可以增加取得控制性持股的可能性,此外尚可为避险(hedge)之用。亦即,倘其收购因尚有出价更高的收购者存在,而使其收购失败时,其亦可将其所持有目标公司的股份卖于出价更高的收购者,从而赚取其间的价差。
再次,最初收购者所为的出价分析,基本上也很难为其他竞争者所引用,至多仅能唯一参考指标而已,也就是说,此处最初收购者所为出价评估的外部效益较少。盖倘收购者系因认为其取得目标公司控制权后,将可增加目标公司的价值而为公开收购者,此一收购所为的出价,基本上将因各个收购者的状态、所营事业、目标公司的资产与营业可与收购公司的整合程度等因素而有所不同;倘收购者系因市场低估目标公司股份价值而为公开收购者,也就是说,其系为赚取差价而非意在长期持有目标公司的控制权,则竞争收购者所带动的竞价效果,反而可以使其迅速获利。
Easterbrook & Fischel尚认为,由于最初收购者将适合的公开收购标的——目标公司——从众多的公司挑选出来,从而减少其后竞争收购者搜寻的成本。这种可能性不能说完全不存在,但应属有限。盖在系为取得目标公司经营权而为之公开收购下,不论是最初收购者或其后的竞争收购者,多半都是与目标公司所营事业相关的公司,例如系为垂直或水平关系,彼此间无时无刻不在注意彼此的动向、布局、股价变动与股权变动的状况。也就是说,潜在的目标公司与收购者往往都不是一夕之间突然出现的。所以要说某一公司成为目标公司是因为最初收购者慧眼独具的结果也许是言过其实的。
基于以上论述,本文认为,部分学者主张公开收购下的竞争收购将减少公开收购的数量,恐言过其实,且未必与现实状况相吻合。本文认为在实际的运作上,最初收购者纵使未能收购成功,亦往往能从过程中获取相当的补偿,甚或利得。
(五)小结:公开收购下公司控制权市场的竞争机制是否应予维护?
本文认为,在公开收购下所形成的公司控制权市场,由于存有买卖双方有限、价值(偏好)不确定、应卖压迫效果、竞争收购者间进行协议行为的动机高且成本低、可能产生资源配置无效率与财富分配不均等特点,是故规范设计上,应以维护市场竞争机制为原则,始为对所有市场参与者均有利的较佳选择。
五、我国台湾地区现行法下竞争收购者间的停止协议是否应受到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的规范?
至此,本文研究认为,法规范应促进公开收购下公司控制权市场的竞争机制,并且对于竞争收购者间的限制竞争行为应以法规范予以适度限制。本部分首先分析,在现行台湾“公平法”与“证交法”的架构下,竞争收购者间的停止协议行为是否应受限制,再分析立法论上的可能性。
(一)现行法下之分析
是否有台湾“公平法”第46条除外不适用(豁免适用)本法规定的情况?
在台湾法的适用上,是否亦会产生如同美国法院因“默示排除原则”而认应适用“证交法”而排除“竞争法”的情况?此即应分析台湾“公平法”第46条规定“事业(内地《反垄断法》用语为经营者)关于竞争之行为,另有其他法律规定者,于不抵触本法立法意旨的范围内,优先适用该其他法律的规定”以及台湾“公平法”第9条第2款规定“本法规定事项,涉及他部会之职掌者,由‘台湾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员会’商同各该部会办理之。”
台湾“公平法”第46条曾于1999年修正为现行条文,(71) 其修正理由为“扩大本法之适用并确定竞争政策优于其他政策”。此一修正确立台湾“公平法”为“经济基本法”的立法意旨,其他法律须在不抵触本法的立法意旨的范围(调和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促进整体经济利益)使得排除适用“公平交易法”。学者并认为,本条规定使得“公平会”对于其他法律关于竞争行为的另行规定,拥有检视其具体适用是否与台湾“公平法”的立法目的兼容的审查权。(72) 也就是说,在本条规定修正前,经营者合乎其他法律的行为当然排除“公平法”的适用,但本条规定修正后,我国台湾“公平会”拥有该经营者行为是否排除“公平法”适用的审查权。(73) 在现行台湾“公平法”第46条的适用下,倘经营者的竞争行为应有其他法律规范,且其他法律规范并无抵触“公平法”的立法意旨,才可优先适用其他法律。否则只要其他法律无规定,或者其他法律的规定与“公平法”有所抵触,均应适用“公平法”。由此可知,台湾法下关于“公平法”与其他法规范间适用问题的处理方式与美国有极大的不同。
是故,竞争收购者的停止竞争协议行为在台湾“公平法”第46条下,与证券相关法规的适用关系有以下的可能性:(1)倘竞争收购者的停止竞争行为为“公平法”所禁止,亦为证券相关法规所禁止,则应非第46条的适用问题,而仅生法规范竞合与机关协商执法的问题。(74)(2)倘竞争收购者的停止竞争行为为“公平法”所禁止,但为证券相关法规所许可,则应依第46条判断证券法规是否有抵触“公平法”的立法意旨,在未抵触的范围内,应优先适用“证券法”,否则即应适用台湾“公平法”。(75)(3)倘竞争收购者的停止竞争行为为“公平法”所许可,则无论是否为证券相关法规所许可,均无台湾“公平法”适用的问题,自亦无第46条的问题。
至于在判断前述第(2)点台湾“公平法”与其他法规是否抵触的标准上,有学者认为台湾“公平法”第46条系授权“公平会”在个案中“站在以市场竞争制度为基本原则的立场,尝试调和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并以‘促进整体经济利益的最大发展’为最终目的。”(76) 亦即,在此前提下,判断究竟是“执行‘公平法’或优先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更能促进整体经济利益的发展?”(77) 至于具体判断标准上,除了本条修正理由中所谓“应考虑特别法与普通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其他法律的立法时间与立法目的”等因素外,学者亦提出其他判断因素,包括市场集中度与市场进入的障碍、参与竞争者的数量与市场绩效、市场规模、竞争素质(价格、质量、服务)、交易成本、生产效率与资源配置效率、消费者福利、其他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例如对于人身安全、环境保护、国防机密)、(78) 其他法律是否已经有维护竞争秩序的内涵,(79) 以及其他法律的管制机关的管制有效性与能力等因素,(80) 均应加以考虑。
综上所述,关于公开收购下竞争收购者间的停止竞争协议是否违反台湾“公平法”的判断,应依循以下两个步骤处理之:首先,此一行为是否为“公平法”所禁止?其次,此一行为是否为证券相关法规所禁止?兹分述如下。
1.公开收购下竞争收购者间的停止竞争协议是否为“公平法”所禁止?
也就是说,竞争收购者间停止协议行为是否属于“公平法”第7条“联合行为”,(81) 从而应在第14条禁止之内?(82)
台湾“公平法”下所谓联合行为,依学者见解,系指经济上企业主体从事阻绝或减少市场竞争的共同行为而言。(83) 有鉴于联合行为将产生限制市场竞争的结果,可能造成资源配置的生产无效率,以及夺取消费者剩余的配置无效率问题,故台湾“公平法”第7条首先规范联合行为的定义,并于第14条明定关于联合行为系采“原则禁止、例外许可”的原则。
(1)股份是否为“公平法”第7条所称之“商品或服务”?
由条文观之,台湾“公平法”第7条关于联合行为的规定,似系以“商品或服务”作为适用条件。由于美国实务见解的启示,使得吾人亦必须就公司股份是否为“商品或服务”进行探究。
亦即,台湾“公平法”第7条以“商品或服务”作为联合行为构成要件的必要性与意义何在?倘从“公平法”第1条所确定本法的立法目的——“维护交易秩序”,来思索“商品或服务”的意涵,则吾人是否可以想象有任何可以被交易的标的物,并非“商品或服务”?又或者本条所谓之“商品或服务”系有其特定范围?其范围又是如何?“商品或服务”是否为一个实质存在的条件?而学者普遍认为作为第14条联合行为的补充规范的第19条第4款,(84) 却未与“商品或服务”结合的理由又何在?
如前所述,美国联邦巡回法院间对于公司股份是否为竞争法所规范的商品或服务虽曾存有不同见解,但现似乎已采肯定见解。而公司股份是否属于台湾“公平法”第7条下所称的“商品或服务”,截至目前,似尚未见有相关实例,故无法确知台湾主管机关与法院对此看法为何。然本文认为,公司股份应可认系台湾“公平法”第7条所称之“商品”。理由如下:
首先,倘依前述美国第二巡回法院于Finnegan一案中的见解,股份为具有财产价值、可为转让的商品。再者,台湾“公平法”并未排除公司股份作为商品而不受“公平法”的检验。亦有学者解释第7条第2款的“商品交易”认为,指就“广义的商品,包括有体物及无体物,以其经济价值有偿为对价交换行为”。股份当属涵括在此一解释之内无疑。至于倘有认为股份虽系商品,但应由证券相关法规规范,则属“公平法”第46条适用的问题,与本条的分析无涉。
其次,根据本文第三部分的分析可知,在公开收购下,竞争收购者间为具有竞争关系者,其透过停止竞争的协议,限制了目标公司股份此一商品的价格,将严重影响目标公司股价透过公开收购竞价机制的形成,从而产生台湾“公平法”所关注的资源配置无效率与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倘有认为公司股份并非台湾“公平法”所规范的对象,公司控制权市场并非台湾“公平法”所规范的市场,则应提出合理的论述,说明为何此一市场内的竞争行为不受“公平法”的检验。
(2)是否为经营者在同一产销阶段的水平联合?
依台湾“公平法”第7条第2款的规定,经营者在同一个产销阶段之“水平联合”,始该当第7条的联合行为。就公开收购下因股份收购与应卖所形成的市场而言,竞争收购者当然属于同一产销阶段——均为目标公司的股份需求者,且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应无疑义。
而本条第1项所谓“与有竞争关系之他事业共同决定商品或服务之价格,或限制数量、技术、产品、设备、交易对象、交易地区等,相互约束事业活动之行为而言”,依学者见解,此处所谓“约束事业活动”即为限制竞争之意,而“价格、数量、产品”等系为立法者用以说明联合行为限制竞争之内容与常见之类型,故仅为例示之联合行为类型。(85) 本文认为,倘系所有的竞争收购者均参与停止竞争之协议,则此一协议即为价格之联合行为;纵使并非所有的竞争收购者均参与协议,也就是说对于最后的收购价格未必有绝对之决定,但如前所述,其将减少未参与协议之其他竞争收购者胜出的机会,或者吓阻其他竞争收购者之出现,是故,仍会造成限制竞争之结果。
(3)是否足以影响生产、商品交易或服务供需之市场功能?
“公平法”第7条第2项尚以竞争收购者之协议行为必须“足以影响生产、商品交易或服务供需之市场功能”,使足该当联合行为。此时之判断标准为何呢?也就是说,公开收购下目标公司股份之收购与应卖行为,是否会受到竞争收购者间之停止竞争协议之影响?
台湾姜炳俊教授引介德国Emmerich教授见解认为,“(德国)通说在实务上所要求的‘市场效果实查’并无必要。事业基于理性缔结联合行为合意,必然是衡诸其对市场之认识,可望发生一定的市场影响效果,若局外人必须就此举证,显然不合事理。只有在当事人限制竞争之目的无法证明时,才有审查对市场影响之必要,然而在此情形下,通常事业在合同缔结时早已将限制第三人竞争之效果计算在内,结果只要符合限制营业竞争之要件便可认为有影响市场关系之效果”。(86) 故有学者认为,Emmerich教授的“推定市场影响存在论”较符合台湾规范适用,亦即联合行为之成立只要符合第7条第1项之要件,“公平会”无须对于本条第2项之市场效果为审查,而由当事人举证其行为对市场无影响而主张免责。(87)
台湾黄铭杰教授亦指出,关于独占地位之滥用、结合及差别待遇等垂直竞争限制规范上,必须以“市场占有率”作为判断该等行为是否足以影响市场功能之“市场(支配)力”之工具;然对于联合行为,则应认为“当事业决意组成联合行为时,实际上即可推论其共同拥有足以影响市场功能之市场力或占有率”,(88) 盖倘参与联合行为之经营者无法确信该联合行为将有其足以影响市场功能之效果,则此联合行为反而将使交易相对人转而向其他未参与联合行为之事业进行交易;也就是说,倘事业不能成功地因为联合行为而影响(限制)市场其他参与人之行为,参与联合行为的事业反而将因此受损害。
黄教授同时强调,虽然并非所有的联合行为均应适用此一推定市场占有率理论而以“当然违法”绳之,某些联合行为尚应经所谓“合理原则”(the rule of reason)之审查,但对于限制价格、产量、分割市场此等“恶质卡特尔”,由于其实施之目的,即在透过对于商品或服务价格等“竞争参数”之控制,达到限制竞争之目的,故应属当然违法的联合行为。而欧盟因考虑此类行为限制竞争之本质与竞争法执法的成本与效益,亦明白表示倘事业之整体市场占有率未达10%时,其联合行为不会对竞争产生实质之限制的同时,亦强调限制价格、产量、分割市场等恶质卡特尔并不适用此一除外原则。(89)
另外,台湾吴秀明教授认为,可参考德国法上之“可察觉性”理论,将联合行为是否影响市场功能以“量”与“质”之标准,综合判断之。所谓“量”的标准,乃系于划定相关市场后,测定参与联合行为之经营者在该市场之市场占有率为何,德国实务上系以市场占有率5%作为认有影响市场功能之门槛;而所谓“质”之标准,则系衡量经营者以联合行为限制竞争参数在本质上会对限制竞争之程度与倾向有多高为断,也就是说“愈属核心限制竞争手段(如订价)之排除,被认为影响市场功能之可能性也就愈高”。
此外,台湾实务界与学界亦特别指出,经营者在采购或工程招标等案件中之联合行为有其特殊性。依台湾“‘公平会’1998年11月18日第367次委员会议决议”,认为投标厂商之围标行为“因悖于参标者应经由公平自由竞争机制以决定得标者以及得标价格之招标制度机能,故该围标行为本身即属直接限制竞争之行为,毋庸具体论究围标行为所足以影响之市场范围层级;凡可能参与投标者达成相互约束事业之合意时,即得认该围标行为足以影响各该招标市场之竞标机能”。(90)
综上所述,台湾实务界与学术界关于台湾“公平法”第7条第2项“足以影响生产、商品交易或服务供需之市场功能”之认定标准,见解并不完全一致。然大致有以下两种意见:第一,采“可察觉性理论”。以联合行为之质——限制竞争参数之内容为何,与量——参与事业之市场占有率高低,来判断系争联合行为是否足以限制竞争。第二,采“市场影响推定论”。先论该联合行为是否为限制价格、产量等恶质卡特尔,倘是,则应推定该联合行为即符合影响市场功能之要件,而由经营者举反证免责。
此两种分类是否适用于所有联合行为之分析,本文不敢妄论,但在竞争收购者间之停止竞争协议中,本文认为,在所有竞争收购者均参与停止竞争协议的情况下,因系恶质卡特尔,且必定造成如工程围标般限制竞争的影响,此时应毋庸考虑市场占有率,应即认定为当然违法的联合行为;然在非所有竞争收购者均参与协议时,本文认为此时仍应推定该联合行为具有市场影响力,而由经营者以市场占有率等因素提出反证免责。
又竞争收购者间之停止协议行为是否可能该当“公平法”第19条第4款之“以胁迫、利诱或其他不正当方法,使他事业不为价格之竞争、参与结合或联合之行为”之不公平竞争。例如,倘一方以补偿他方参与公开收购所需之费用,同时给予其他之报偿,以作为他方不为竞争之条件时,是否该当本款?
本条于个案中依具体情况可能有所不同,但应注意者,学者虽认为台湾“公平法”第19条为第14条之重要补充规范,然两者之重要差异,在于第19条系规范一方意志强加在他方行为之结果,而第14条则系在规范竞争者间之合意行为。(91) 由于第14条与第19条之法律责任不相同,(92) 故在法条适用上应注意两者间之差异性。
2.公开收购下竞争收购者间之停止竞争协议为证券相关法规所允许或禁止?
台湾证券相关法规并未明文规范竞争收购者之停止竞争协议行为,故本文拟从证券法规对于公开收购法制的核心规范、相关法规对于公开收购下之竞争机制之态度,以及公开收购下之“共同取得”制度的意义与内涵三方面,来说明证券法规对于停止竞争协议行为所可能采取的态度。
(1)台湾公开收购法制之立法目的与核心规范
台湾在1988年修正“证交法”时,增订第43-1条,加入关于公开收购之相关规范,在当时尚无实际案例的情况下,相关立法主要系参酌其他国家之立法经验。而各国公开收购法制或有不同,但大都一方面肯认公开收购为一有效之公司治理外部机制,一方面从各国实证经验可知,公开收购市场倘放任不管,将严重影响证券市场之效率,是故“信息公开原则”与“保护目标公司股东”即为各国公开收购法制的两大核心。台湾地区立法也大致遵循此一方向。2002年修法时,再增订“证交法”第43-2条至第43-5条,并授权证券主管机关制定“公开收购公开发行公司有价证券管理办法”(下称“公开收购办法”)以及“公开收购说明书应行记载事项准则”两个行政规则。
(2)证券法规对于公开收购下之竞争机制之态度
本文认为,台湾证券相关法规,对于维护公开收购下之竞争机制应系采肯认态度。理由如下:
首先,台湾证券主管机关——“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期货局(下称‘证期局’)”,根据台湾“证交法”第43-1条第4款所颁布之“公开收购办法”第7条第2款规定,“对同一公开发行公司发行之有价证券竞争公开收购者,应于原公开收购期间届满之日五个营业日以前向本会办理公开收购之申报并公告。”显见台湾证券法规,肯认竞争收购之价值。刘连煜教授对此分析认为,“……法令之所以允许二个以上之主体竞争公开收购,除了系为维持公平竞争之机会外,也因竞争收购关系,可为标的公司之股东带来更高之出价,对股东更为有利”。(93)
其次,为进一步强化竞争收购之效果,前述“公开收购办法”第18条规定,原则上公开收购期间为10至50日间,倘“有第七条第二款之情事(按:即有竞争收购之情况)或有其他正当理由者,原公开收购人得向本会申报公告延长收购期间……”此一允许原公开收购人得延长收购期间之规定,目的即在给予原公开收购人可再为竞价之机会。
最后,“证交法”第43-5条第3款规定,倘公开收购人未能于收购期间内完成预定收购数量者,除有正当理由并经主管机关核准者外,其于一年内不得就同一目标公司进行公开收购。本条设置之目的,在于避免有心人士藉公开收购扰乱其他公司之正常经营,也就是以公开收购之名,行影响市场价格之实,(94) 或藉此来要挟目标公司经营团队给予好处以获取一己之利。然“公开收购办法”第24条规定,则将“参与竞争收购”作为前述“证交法”第43—5条第3款之公开收购人得在就同一目标公司进行公开收购之“正当事由”。显见,主管机关意在为目标公司创造竞争收购之可能性。
由以上相关规定可以得知,主管机关显然相当肯认竞争收购的正面价值。依循此一逻辑,维护公开收购下之竞争机制则十分重要。
(3)公开收购下之“共同取得”制度的意义与内涵
如前所述美国联邦法院判决认为,由于《威廉斯法》明文规定两人以上“共同取得”目标公司之股份时,应视为同一人,且应予以申报,从而美国法院认为,由于联邦证券法规范下的公开收购行为,本身即容认数人协同进行公开收购,故倘《反托拉斯法》介入,则将破坏联邦证券法规的设计,此时,纵使证券法规并未明文排除反托拉斯法之适用,反托拉斯法基于“默示排除原则”而无所适用。
然在台湾法下,台湾“证交法”第43-1条第1款与第3款的“共同取得”制度,是否应得出与美国法院相同之见解?也就是说,竞争收购者间之停止竞争协议与数人之联合公开收购协议是否有所不同?本文持与美国法院不同之见解,且认为竞争收购者间之协议行为,应与共同取得制度下之协议行为有所区别。理由如下。
首先,本文认为,竞争收购者间之停止竞争协议与联合公开收购协议所产生之效率结果有所不同。前者除了明确地造成目标公司股东原可依竞争机制取得较高溢价利得之减损外,也可能使目标公司之控制权无法透过公开收购方式移转到可将公司价值极大化之收购者手中。
而至于联合公开收购协议,却较有可能达到“促进竞争”(procompetitive)之效果。例如联合公开收购行为可能促使较大规模的公司也有机会成为公开收购下的目标公司,使得这类公司有机会藉公司控制权市场作为外部公司治理的工具;或者使得原本不可能透过一己之力参与公开收购竞争的市场参与者,透过合作而参与,从而增加了公开收购下的竞争机制;或者联合公开收购的参与者各自对于目标公司的部分资产或营业具有优势的管理能力或可与其各自目前的资产或营业予以结合,以发挥更佳的综效。
综上分析可知,竞争收购者间之协议行为与共同取得制度下之协议行为,两者在限制竞争或促进竞争之效果上,有相当程度之不同,从法规范的角度言,应予分别处理。
再者,台湾“证交法”下之“共同取得”制度,其目的并非在鼓励或促进潜在竞争者或现实竞争者进行公开收购事前或事后之共同行为。
台湾“证交法”第43-1条第1款规定,“任何人单独或与他人共同取得任一公开发行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超过百分之十之股份者,应于取得后十日内,向主管机关申报其取得股份之目的、资金来源及主管机关所规定应行申报之事项;申报事项如有变动时,并随时补正之”。又同条第3款规定,“任何人单独或与他人共同预定取得公开发行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达一定比例者,除符合一定条件外,应采公开收购方式为之。”此外,依主管机关颁布之“‘证券交易法’第43-1第1项(款)取得股份申报事项要点”第2点规定,“证交法”第43-1款第1项所谓“任何人取得公开发行公司已发行股份”,系指“包括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利用他人明意持有者”;所谓“与他人共同取得股份”,依前述要点第3点,系指“以契约、协议或其他方式之合意,取得公开发行公司以发行股份”。
本文认为,“证交法”有关股份“共同取得”的情况应予申报,以及强制公开收购门槛的股份应合并计算的规定,其目的乃系考虑,大量股权取得之管理,对于公开收购制度下的信息揭露义务与目标公司利害关系人之权益保障,均有重要影响,(95) 为避免有心人士,利用他人名义持股或以与他人协议由他人取得股份的方式,藉以逃脱相关信息揭露及公开收购进行之程序规定,从而有本条之设置。
也就是说,“共同取得”制度之目的,并非在于鼓励或促使市场参与者进行联合公开收购行为;“证券交易法”对于“共同取得”之容认态度,并不表示其亦容认市场参与者藉由共同取得之协议或行为,以达成限制竞争之目的。盖如前述,“证交法”与主管机关十分肯认公开收购下的竞争价值与市场机制之重要性,故倘系认为因“证交法”规范有“共同取得”,从而认定“证交法”允许市场参与者得藉由共同协议以达成限制竞争之目的者,则应属对于本规范之错误理解。
3.小结
综上所述,本文获致以下结论:
第一,本文认为台湾现行之证券相关法规,对于竞争收购者间之停止竞争行为并无明文规范。此可能亦与证券法规向来之立法目的与规范范围,并未曾考虑并购者间之合纵连横行为可能会产生限制竞争或不正当竞争之可能性有关。在台湾“公平法”为台湾经济基本法的前提下,竞争收购者间之停止竞争协议应回归“公平法”之管辖应无疑义。
第二,纵有论者认为台湾“证交法”的相关规范应系容认竞争收购者间之停止竞争协议存在,如前所述,在特定行为为台湾“公平法”所禁止而个别管制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尚必须检验台湾“证交法”允许此一停止竞争协议是否不抵触台湾“公平法”之立法意旨。就此,本文认为,倘“证交法”有任何允许竞争者间之停止竞争协议之意,此一规范亦将因违反台湾“公平法”之立法意旨,而应依“公平法”第46条之规定不予适用。
第三,从“竞争法”之角度而言,应区别公开收购开始后之竞争收购者间之停止竞争协议行为,与公开收购开始前即为之共同取得股份之联合收购协议行为。盖前者关于限制竞争之动机、可能性与危险性显然较为明显,而后者则较可能产生“促进竞争”之效果,从而可能不符合台湾“公平法”第7条关于联合行为之要件。
也就是说,共同取得下之联合公开收购行为将可能产生促进竞争与限制竞争的效果并呈的情况。此时,究应如何判定其是否有“足以影响生产、商品交易或服务供需之市场功能”?本文认为,台湾“公平会”过去处理关于工程招标案件中“联合承揽”是否构成联合行为的相关判断准则,值得参考。
以下就台湾“公平会”函释(81)公2字第00376号之内容,择要摘录如下:
首先,实务上工程招标所为之“联合承揽”是否构成“公平交易法”第7条所规定之“联合行为”,不能仅从名称加以认定,仍须具体认定其是否符合该条之要件,包括:(1)是否足以影响生产、商品交易或服务供需之市场功能;(2)二以上之经营者是否“具有竞争关系”;(3)是否共同决定价格等。如不符合以上三要件及其他联合行为之要件,纵名为“联合承揽”或“共同承揽”亦非“联合行为”,而无“公平法”之适用。
其次,联合承揽事业,如符合下列第1项之基准,且符合第2项[2之(1)(2)(3)须同时具备]或第3项基准之一者,不构成联合行为,但发包机构不得有涉及不公平竞争之行为:
1.须个案联合承揽。联合承揽按每件工程分别成立,其联合承揽关系于工程完工后即消灭者。
2.关于是否影响市场功能之要件。(1)具有市场地位之发包机构(如政府机构、公营事业及其他具有独占地位之事业),要求投标或承包事业所为之联合承揽。(2)发包单位衡量国内外水平及供需关系等因素认为有联合承揽之需要,且于招标须知中载明联合承揽相关规定者(联合承揽人不足影响市场功能)。(3)非投标或承揽事业所积极发动,而系被动配合第(1)项发包单位之要求,依第(2)项规定而为之联合承揽,且意图不在限制竞争,且无使发包单位受损之虞者(即意图不在于共同决定价格及其他交易条件以限制竞争)。
3.关于“竞争关系”之要件。在未联合投标之情形下,联合承揽团体中之个别事业各自均不符发包单位之投标资格者。二以上事业因组成联合投标团体而符合投标资格,因此增加投标事业或联合投标团体之竞争者。
前述关于工程招标案件联合承揽是否构成联合行为的判断基准,倘适用于联合公开收购行为时,应注意之事项仍有待进一分析,但综观台湾“公平会”此一函释可知,“公平会”允许工程招标案件中的联合承揽行为的基本核心准则在于,此联合行为的目的是在促进竞争,或是限制竞争,此一基本原则在吾人进一步分析应如何判断促进竞争之联合收购协议行为时,仍深具参考价值。
(二)立法论下的可能性分析——应由“公平会”或“金管会”管辖?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文认为,公开收购下竞争收购者间之限制竞争协议确系应受法规范,且依本文对于台湾“公平法”与“证交法”之分析得出,现行法下应由台湾“公平法”之专责单位我国台湾“公平交易委员会”依台湾“公平法”第14条联合行为之禁止加以处断之结论。然立法论上仍可思考,应由主管台湾证券市场之我国台湾“金融管理监督委员会证券期货局”,或者我国台湾“公平交易委员会”为管辖机关较为合适,或者是否应由“证交法”另行增订关于公司控制权市场之竞争规范以为“公平法”之特别法,均值讨论。盖此乃涉及公司控制权市场之竞争秩序问题,且现行“证交法”亦有联合公开收购行为的相关规范,例如“证券交易法”第43-1第1项(款)“取得股份申报事项要点”第2点规定,“取得人与他人共同取得股份者,如有书面合意,应将该书面合意并同向主管机关申报”。
倘从现行台湾“公平法”与其他法规范间之关系观察之,亦不乏由台湾“公平会”以外之其他专责机关处理特定市场的竞争问题。例如我国台湾“公平会”函(88)公2字第88044951001号,说明“按有关围标行为之规范,现行‘政府采购法’第87条至第92条定有明文;复依本会与‘公共工程委员会’,就台湾‘公平法’与‘政府采购法’之适用问题协商会议决议:(一)政府采购争议事件涉及竞争秩序之行为,发生在‘政府采购法’施行前者,依‘公平法’……(四)政府采购争议事件涉及竞争秩序之行为,发生在‘政府采购法’施行后者,由当事人循‘政府采购法’途径解决”。据此,倘相关疑义系发生于1999年5月27日“政府采购法”施行后者,建请贵处另行函请我国台湾“公共工程委员会”解释。也就是说,关于政府等公部门采购涉及竞争秩序之问题,“政府采购法”为“公平交易法”之特别法,并以我国台湾“公共工程委员会”而非我国台湾“公平交易委员会”为专责机关。
本文对于涉及公司控制权市场之竞争规范,于立法论上应由何法或何机关为管辖尚无定论,倘依台湾现行法规则应为“公平法”与“公平交易委员会”无疑。然应注意者,台湾“公平法”第9条第2款之规定:“本法规定事项,涉及他部会之职掌者,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员会’会同各该部会办理之。”
六、结论
本文以美国Finnegan v.Campeau Corp一案所引发公开收购下敌意并购者之停止竞争协议所涉及的市场竞争问题,以及竞争法与证券法之交错问题谈起,分析美国法院判决之演变与分歧,以及学说见解,得出法规范应维护公司控制权市场之竞争机制之初步研究结论。
此一议题之讨论深具实益。一方面可以促使公司法与竞争法学界与实务界,重新思考公司控制权市场之特性、其对于公司治理与价值极大化之重要性,以及各个利害关系人于此一市场中之行为对于其他利害关系人与公司价值之可能影响。另一方面,台湾虽然尚未出现类似Finnegan之案例,然如本文分析,在台湾资本市场逐步与全球接轨、相关敌意并购手段之法律规范逐渐完善,以及台湾控制权市场有逐渐实行市场竞价机制趋势之际,未来类似Finnegan之案例极有可能在台湾发生。台湾相关法规范应如何正确适用、立法上应有何亟待完善之处,即有深入研究之必要。
公司控制权市场下就应如何调和公司、证券法与竞争法间之适用关系,不仅关乎一国公司治理的良窳,亦系对于竞争法制之挑战。本文期抛砖引玉,引发公司法与竞争法学界与实务界对于本议题之进一步关注与研究。
作者感谢台湾大学黄铭杰教授提供宝贵意见,感谢中国政法大学方立维博士于本文使用内地法规用语上之建议。
注释:
① 本文所称“台湾”均指我国台湾地区。——编者注
② 我国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第7条:“本法所称联合行为,谓事业以契约、协议或其他方式之合意,与有竞争关系之他事业共同决定商品或服务之价格,或限制数量、技术、产品、设备、交易对象、交易地区等,相互约束事业活动之行为而言。前项所称联合行为,以事业在同一产销阶段之水平联合,足以影响生产、商品交易或服务供需之市场功能者为限。第一项所称其他方式之合意,指契约、协议以外之意思联络,不问有无法律拘束力,事实上可导致共同行为者。同业公会藉章程或会员大会、理、监事会议决议或其他方法所为约束事业活动之行为,亦为第二项之水平联合。”我国台湾“公平法”第14条:“事业不得为联合行为。但有左列情形之一,而有益于整体经济与公共利益,经申请中央主管机关许可者,不在此限:一、为降低成本、改良质量或增进效率,而统一商品规格或型式者。二、为提高技术、改良质量、降低成本或增进效率,而共同研究开发商品或市场者。三、为促进事业合理经营,而分别作专业发展者。四、为确保或促进输出,而专就国外市场之竞争予以约定者。五、为加强贸易效能,而就国外商品之输入采取共同行为者。六、经济不景气期间,商品市场价格低于平均生产成本,致该行业之事业,难以继续维持或生产过剩,为有计划适应需求而限制产销数量、设备或价格之共同行为者。七、为增进中小企业之经营效率,或加强其竞争能力所为之共同行为者……”
③ See Finnegan v.Campeau Corp.,722 F.Supp.1114(1989),915 F.2d 824(1990),499U.S.976(1991).
④ 493 A.2d.946(Del.1985).
⑤ 506 A.2d.173(Del.1985).
⑥ 赖源河编审:《公平交易法新论》,元照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27~34页。
⑦ William T.Allen,Contracts and Communities in Corporate Law,50 Wash.& Lee.L.Rev.1935,1400(1993).
⑧ Frank H.Easterbrook & Daniel R.Fischel,The Corporate Contract,89 Colum L.Rev.1416,1418(1989).
⑨ 我国台湾“公司法”第235条:“股息及红利之分派……以各股东持有股份之比例为准。章程应订明员工分配红利之成数……”
⑩ 我国台湾“公司法”第267条第1款:“公司发行新股时……应保留发行新股总数百分之十至十五之股份由公司员工承购。”
(11) 刘孔中:《公平交易法》,元照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15页。
(12) 我国台湾“公司法”第167条第1款:“公司……不得自将股份收回、收买或收为质物……”
(13) 我国台湾“公司法”第237条:“公司于完纳一切税捐后,分派盈余时,应先提出百分之十为法定盈余公积。但法定盈余公积,已达资本总额时,不在此限。除前项法定盈余公积外,公司得以章程订定或股东会议决,另提特别盈余公积……”
(14) 参见“台湾‘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员会’对于金融业经营行为之规范说明”(http://www.ftc.gov.tw/,浏览日期2007年12月23日)。
(15) 前引⑦,Allen,1400。
(16) 769 F.2d 152(3d Cir.1985).
(17) 本案中,第二巡回法院肯认公司股份为谢尔曼法的管辖客体,但以谢尔曼法于本案中因“默示除外原则”,而应适用美国联邦证券法而非谢尔曼法,从而判决Federated之股东Finnegan等人败诉。
(18) 499 U.S.976,111 S.Ct.1624(1991).
(19) 127 S.Ct 2383,2387(2007).
(20) 915 F.2d 824,828(1990)(quoting Gordon,422 U.S.at 682,95 S.Ct.at 2611).
(21) 769 F.2d 152(3d Cir.1985).
(22) 310 U.S.469(1940).
(23) 769 F.2d 152,156-7(3d Cir.1985).
(24) Edward B.Rock,Antitrust and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77 Calif.L.Rev.1388(1989).
(25) See e.g.McLain v.Real Estate Bd.of New Orleans,Inc.,444 U.S.232,241(1980); Tarleton v.Mcharry Medical College.717 F.2d 1523,1529(6th Cir.1983).
(26) 前引(24),Rock,1390。
(27) Id.,at 1389.
(28) 915 F.2d 824,827-828(1990).但应注意者,第二巡回法院最后仍以驳回原告之诉,理由为证券相关法规于本案应优先适用。Id.,828-832.
(29) Kalmanovitz v.G.Heileman Brewing Co.,769 F.2d 152,158(3d Cir.1985).
(30) 915 F.2d 824,827-828.
(31) 373 U.S.341,83 S.Ct.1246(1963)
(32) 422 U.S.659,95 S.Ct.2598(1975).
(33) 422 U.S.694,95 S.Ct.2427(1975).
(34) 915 F.2d 824,828(1990)(quoting Gordon,422 U.S.at 682,95 S.Ct.at 2611).
(35) Id.,at 828-829.
(36) Id.,at 829.
(37) 422 U.S.at 661,668-669.
(38) Id.,at 829.See also 422 U.S.694,734(1975).
(39) 915 F.2d 824,829(1990).
(40) 17 C.F.R.§ 240.14d-100(1989).
(41) §14(d)(2)of the 1934 Act,15 U.S.C.§ 78n(d)(2)(1988).
(42) 915 F.2d 824,830(1990).
(43) Id.
(44) Id.
(45) Id.,at 831.
(46) Id.,at 831.
(47) Id.,at 831.
(48) Id.,at 832.
(49) Id.,at 831.
(50) 499 U.S.976,111 S.Ct.1624(1991).
(51) 前引(24),Rock,1393。
(52) 盖默示排除是美国法院判决对于反托拉斯法适用范围的解释结果,倘适用上太过宽泛,势必将破坏立法者旨意。倘立法者有意排除某一特定市场于反托拉斯法的适用,其可在反托拉斯法或其他相关法规范上作如此限制。谢尔曼法明文排除适用的规定,例如15 U.S.C.§1108(1995)(exempting newspaper agreement from antitrust law)。
(53) 前引(24),Rock,1391-2。
(54) 374 U.S.321(1961).
(55) Id.,at 305-51,354.See Joshua M.Fried & R.Preston McAfee & Melanie Stallings Williams & Michael A.Williams,Collusive Bidding in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79 Neb.L.Rev.48,56(2004).
(56) 前引(55),Fried,70。
(57) 前引(55),Fried,70。
(58) See generally Lucian Arye Bebchuk,The Pressure to Tender:An Analysis and A Proposed Remedy,12 DEL.J.CORP.L.911(1987).
(59) 朱德芳:“效率、并购与公司治理——以敌意并购法规范为核心”,载《中原财经法学》2006年第17期。
(60) See Reinier R.Kraakman ET AL,THE ANATOMY OF CORPORATE LAW,160.
(61) 世界各国的统计数据显示,竞争收购要约下的收购价格通常比仅有一单一收购者的情况来得高。See Bradley,Desai & Kim,Synergistic Gains from Corporate Acquisitions and Their Division Between the Stockholders of Target and Acquiring Firms,21 J.Fin.Econ.3,21025(1988).
(62) 前引(24),Rock,1372-73。
(63) See Lucian A.Bebchuk,The Case for Facilitating Competing Tender Offers,95 Harv.L.Rev.1028,1034-41(1982); Lucian A.Bebchuk,The Case for Facilitating Competing Tender Offers:A Reply and Extension,35 Stan.L.Rev.23,30-39(1982); Frank H.Easterbrook & Daniel R.Fischel,The Proper Role of a Target's Management in Responding to a Tender Offer,94 Harv.L.Rev.1161(1981); Frank H.Easterbrook & Daniel R.Fischel,Auctions and Sunk Costs in Tender Offers,35 Stan.L.Rev.1,7-9(1982); Gilson,Seeking Competitive Bids Versus Pure Passivity in Tender Offer Defense,35 Stan.L.Rev.51,52-62(1982).
(64) 这也就是像古董等亦具有偏好不确定之商品,亦多采竞标方式决定价格之原因。
(65) Robert Marshall & Michael Meurer,Bidder Collusion and Antitrust Law,72 Antitrust L.J.83,85(2004).
(66) 前引(65),Marshall,86。
(67) Easterbrook & Fischel,94 Harv L.Rev.1161(1981).
(68) Bebchuk,The Case for Facilitating Compering Tender Offers,95 Harv.L.Rev.1028(1982); Gilson,A Structural Approach to Corporations:The Case Against Defensive Tactics in Tender OFFERS,33 Stan.L.Rev.319(1981).
(69) Easterbrook & Fischel,Auction and Sunk Costs in Tender Offers,35 Stan.L.Rev.1(1982); Bebchuk,The Case for Facilitating Competing Tender Offers:A Reply and Extension,35 Stan.L.Rev.23 (1982).
(70) 前引(68),Bebchuk,1036-7。
(71) 我国台湾旧“公平法”第46条为:“一、事业依照其他法律规定之行为,不适用本法之规定。二、公营事业,公用事业及交通运输事业,经“行政院”许可之行为,于本法公布后五年内,不适用本法之规定。”
(72) 前引⑥,赖源河编审,第112~113页。
(73) 吴秀明:《竞争法制之发轫与展开》,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376页。前引⑥,赖源河编审,第120页。
(74) 洪礼卿等人主持:“‘公平交易法’第46条修正后之适用问题研究”,载《“公平交易委员会”八十九年度合作研究报告十二》,第20页(2000年12月)。
(75) 另应注意者,有学者指出,“公平法”第46条之除外规定范围,仅限于“公平法”下的反托拉斯法部分,而不能排除本法不正当竞争部分,否则将造成“鼓励事业从事不正竞争”之结果。前引⑥,赖源河编审,第103页。
(76) 前引(73),吴秀明书,第377页。
(77) 前引(73),吴秀明书,第377页。
(78) 前引(74),洪礼卿等人主持,第78~81页。“公平法”学界似乎以“公平法”立法目的多元价值论为主流。前引⑥,赖源河编审,第34页。论者认为,现行“公平法”为一涵盖防止限制竞争、不正竞争与消费者保护三种性质之法律。其并建议,关于限制竞争部分,应以经济效率为主要目标,倘效率之有无不甚明显时,则可考虑其他次要目标,如保护中小企业、财富分配、消费者利益等;不正当竞争部分,则应先以营业之善良风俗为考虑,而以明显的效率提升或消费者利益,作为阻却违法的事由;消费者保护方面,则应以消费者保护为基本诉求,倘涉有重大消费者利益,如安全、健康等,则应认为其高于效率与营业者之利益。
(79) 前引(74),洪礼卿等人主持,第80页(2000年12月)。论者认为,倘其他法律已经明显植入竞争导向的新经济政策,则该法可视为“公平法”之补充,如果该法已经适当地反映了“公平法”之立法目的,则“公平会”采取低度审查即可。
(80) 前引(73),吴秀明书,第378页。吴秀明教授认为,倘其他管制机关之人员、专业经验、经费等管制资源较多、管制效率较佳时,“公平会”对相关事宜宜采低度审查,或径行认定其他法律之规定不抵触本法之意旨;但倘若其他管制机关并无足够之管制资源、管制成本过高,或明显懈怠或根本不为管制时,“公平会”仍得予以管制。
(81) 前引⑩,我国台湾“公平法”第7条。
(82) 前引⑩,我国台湾“公平法”第14条。
(83) 前引⑥,赖源河编审,第231页。
(84) 前引(73),吴秀明书,第115页。我国台湾地区“公平法”第19条:“有左列各款行为之一,而有限制竞争或妨碍公平竞争之虞者,事业不得为之:一、以损害特定事业为目的,促使他事业对该特定事业断绝供给、购买或其他交易之行为。二、无正当理由,对他事业给予差别待遇之行为。三、以胁迫、利诱或其他不正当方法,使竞争者之交易相对人与自己交易之行为。四、以胁迫、利诱或其他不正当方法,使他事业不为价格之竞争、参与结合或联合之行为。五、以胁迫、利诱或其他不正当方法,获取他事业之产销机密、交易相对人数据或其他有关技术秘密之行为。六、以不正当限制交易相对人之事业活动为条件,而与其交易之行为。”
(85) 前引(73),吴秀明书,第61、65页。
(86) 前引⑥,赖源河编审,第253页。
(87) 前引⑥,赖源河编审,第253页。
(88) 黄铭杰:“联合行为成立与市场界定、影响市场功能认定间之理论与论理(下)——评‘最高行政法院’92年度判字第1336号判决”,载《台湾本土法学杂志》2005年第69期。
(89) 参见前引(88),黄铭杰,第19、22页。
(90) 学者见解请参阅黄铭杰:“联合行为成立与市场界定、影响市场功能认定间之理论与论理(上)——评‘最高行政法院’92年度判字第1336号判决”,载《台湾本土法学杂志》2005年第68期;前引(73),吴秀明书,第76页。吴秀明教授认为,此时亦非不能以量之观点认定市场功能之影响。
(91) 前引(73),吴秀明书,第84页。
(92) 前引(73),吴秀明书,第83页。
(93) 刘连煜:《新证券交易法实例研习》,元照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90页。
(94) 吴光明:《证券交易法论》,三民书局2006年版,第75页。
(95) 前引(94),刘连煜书,第174、17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