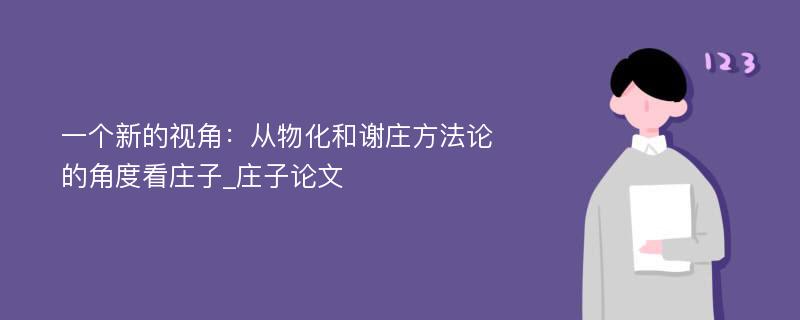
一个新的视角:从“物化”说看《庄子》——兼及解庄方法论的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庄子论文,视角论文,透视论文,庄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庄子》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朵奇葩。对《庄子》的研究自《庄子》诞生起就已形成一种专门的学问——庄学。当庄学研究形成热潮,并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时,我们有必要检讨庄学史,汲取其精华,发现其不足,避免研究中不必要的重复。这样,我们便有必要对历史上的解庄方法作一细致梳理,并寻找新的研究视角。在此基础上,我们方能推陈出新,为新时代的庄学研究注入新鲜血液。
一、古人的理解
先秦经传诸子中文哲、诗思融合的形态常常被生硬地割裂。《庄子》也难逃厄运。其诗心玄理妙合为一的“物化”说仅被视为哲理的解悟,而其诗性的特质自此被遮蔽。古人在哲学层面阐释“物化”,集中在玄学、佛学、理学、禅学几个层面。这里有五种代表性看法。
第一种是“人生幻化论”,以西晋郭象为代表:
夫时不暂停,而今不遂存,故昨日之梦,于今化矣。死生之变,岂异于此,而劳心其间哉!方为此则不知彼,梦为胡蝶是也。取之于人,则一生之中,今不知后,丽姬是也。而愚者窃窃然自以为知生之可乐,死之可苦,未闻物化之谓也(注:郭庆藩辑、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13、114页。)。
郭象认为庄子的“物化”实际说的是人生的“幻化莫测”状态。此不知彼,今不知后,生不知死,一切都是幻灭。郭象以玄学观念解庄,开拓了庄子研究的新气象,掀起了庄子研究的高潮。但也从根本上曲解了庄子“物化”思想。因为庄子虽认为物化世界是虚幻的,但又指出了超越的“道化”向度。郭象抛弃了“道化”的存在论前提与超越指向,在悲惋人生虚幻中,将世界经验为滔滔不返。这种看法本质是线性时间观与历史的单线条思维。这与庄子“处道之环中,应万物之无穷”,真人体道,回归道的历史圆环说大异其趣。在人生幻化论指导下,郭象以“适性逍遥”的及时享乐哲学取代了“道化”的超越之思。这样,郭象从庄子“物化”说改造而成的“独化”、“自化”论看似对庄子的重大发展,但本质上已偏离了庄子的真精神。
第二种是“精神不灭论”,以东晋慧远为代表:
神也者,圆应无生,妙尽无名,感物而动,假数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灭;假数而非数,故数尽而不穷。有情则可以物感,有识则可以数求。数有精粗,故其性各异;智有明暗,故其照不同。推此而论,则知化以情感,神以化传;情为化之母,神为情之根(注:慧远:《形尽神不灭》。)。
在慧远之前,已有玄学化僧人支遁注《逍遥篇》驳斥郭象“适性逍遥”观。慧远进而从佛家“神不灭”观出发,否定郭象庸俗化享乐哲学。慧远指出,神无生、无名,不同于物的情、识。物因有情可感,有情则有生灭迁化,情是造成物生死的原因;物因有识而可数(理)求,有数(理)就有精粗明暗,数(理)就是造成物蔽于所见的原因。“神”则与“物”(形)不同,它参与大化,却不因物的生灭而生灭,它是永恒的存在,是物情得以存在的根源。
应当说,佛教的“神”寄于“化”而不随“形”化的“本根”超越观与庄子的“道”托于“化”而不随“物”化的“本根”超越观是基本一致的。道的莫测变化就是“神”,它寄托于物化,其本身却不化,这就是物的“本根”。这的确类似于佛家超越了生死轮回的“神”或“真如”。正因此,早期的佛教徒常借用庄子术语来解释佛教难于被国人理解的抽象观念。
不过,佛教心向往之的“神”或“真如”与庄子的“道”却有根本分歧。佛家“神”或“真如”与“物情”相隔,二者关系是“彼岸”与“此岸”的对立关系,庄子“道”与“物情”相通,物只要不失其情,就能冥合于道。故庄子“道”先天“有情”,佛家“真如”却先天“无情”。庄子的“道”、“神”、“情”具有自然论、境界论色彩,佛家“神”、“真如”具有神性论、宗教论色彩。慧远对“物化”说的“神性论”发挥,是“以佛解庄”、“以庄释佛”的必然结果,其隐含的“形神”观对后世艺术影响深远。
第三种是“物理自然论”,以唐代成玄英、宋人林希逸为代表。成玄英曰:
夫新新变化,物物迁流,譬彼穷指,方兹交臂。是以周蝶觉梦,俄顷之间,后不知前,此不知彼。而何为当生虑死,妄起忧悲!故知生死往来,物理之变化也(注:郭庆藩辑、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13、114页。)。
成疏与郭注相同处在于强调“物化”的变易性,成疏的重要发展是提出“物理”一词。《鹖冠子·度万》:“庞子曰:‘愿闻其人情物理。’”此处“物理”尚指物之常性。但成玄英处,“物理”却具有本体论的意义。所谓“道者,理也”,“天道,自然之理也”,“真实之道,则自然之理也”。成玄英还多处用“实理”、“虚通之妙理”、“重玄妙理”来对“理”进行规定说明。这样,“理”即实即虚,非有非无,它乃本然源发,先天具足。一切事物、变化皆从“理”中流出,“理”为“一”,“物理”,“天理”、“真常之理”无有不同,而从“理”流出的物事、现相变化却有“万殊”,这也即“理一分殊”说的由来。
成玄英重“理”,并将“理”上升到本体论高度,以代替庄子的“道”。庄子的“道”是美、法、理、情、信的多层次统一,而“物”则是道的具体化,也相应地富有“道”的丰富内涵。成玄英将“理”抽象出来,并视为唯一绝对的东西,便将庄子形上化了。而且,庄子的“物化”除具有物形或物理变化的自然层面含义外,还具有圣人“知其不可奈何而安知若命”、“乐天知命”的生存境界与超脱心态含义,这是一种超越了自然的生与死、社会的时与命、个体的情与欲限制的自由心境,是一种与道徘徊,自由逍遥的诗化人生境界,显然与成玄英纯粹从抽象层面解释的“自然变化”观有巨大差别。
第四种是“宇宙气化论”,以宋人陈景元、褚伯秀、陈碧虚为代表。陈景元曰:
周蝶之性,妙有之一气也。昔为胡蝶乃周之梦,今复为周,岂非蝶之梦哉?周蝶之分虽异,妙有之气一也。夫造化之机,精微莫测,傥能如此,则造化在己而迁于物,是谓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注:崔大华:《庄子歧解》,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109页。)。
这种观点与成玄英“理化”说有相通处,只不过以“气”代“理”、“道”,而体现出一种自然哲学的色彩。但其自觉地为“物化”寻找本体论依据,并从万物同源于“气”的高度解释“觉梦如一”、“周蝶不分”的心理现象。这有向自然科学发展的倾向,是对《庄子》中已有的自然科学观的继承发挥。
第五种是“境界顿悟论”,以宋刘辰翁、清刘凤苞为代表。援禅释庄,重顿悟禅机,体验境界。刘辰翁以为“蝴蝶梦”道出了“人牛俱失之机”,刘凤苞云“以物化作结,见彼此幻形,还他空空无著”,这正是一种庄禅互渗的透彻玲珑之境。禅机顿悟说激活了庄周“物化”之梦中的诗心灵境,为渐显枯燥迟滞的庄学研究注入了清新之气。当然,这种观点是以佛家的“空观”为其底蕴,这与庄子以道的“情”、“信”为底蕴显然有很大差异。因为“道”并不是完全的“空”、“无”,而是“有”与“无”统一,道虽看不见却具有实在性及诸多特性,这也就避免了如佛家那样将世界看作空幻的悲观论调。
悟诗如参禅,诗道同禅道。严沧浪云,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而诗道亦在妙悟。与“以禅解庄”相映成趣的是“以文解庄”论。清宣颖、刘凤苞等既以禅解庄,而更以文解庄。宣颖《庄解小言》:“庄子之文,长于譬喻,其玄映空明,解脱变化,有水月镜花之妙,且喻后出喻,喻中设喻,不啻峡云层起,海市幻生,从来无人及得。”刘凤苞《南华雪心编》:“南华泄天地之秘者也,其光之灿烂,如日月星辰之悬象而著明;其气之鼓荡,如风云雷雨之顺时而布令;……合天地有象有声以为文,以是为文之至。”庄子文章的诗心灵性、跳荡奇谲,宣、刘二人可谓得之深矣。
以禅解庄,以文解庄不仅昭示着哲学之智性向文学之灵性的转变,并且为庄学研究开辟出一片崭新的天地,也为重回“物化”诗境提供了可能。同时,也应看到,自魏晋后的诸家解庄中,唯郭象达到了自成一体的理论高度与思之独创。但郭象之“思”终究沦为现成的智识,而非庄周源发的诗性生命感悟。明清以来的以禅解庄、以文解庄虽在“思”中接近庄子的“诗性”,但尚缺乏自成一体的理论创新。
二、近人的阐释
近代以来,因中国倍受西方列强欺凌的屈辱地位,让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误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失败,并由此走上了否定传统文化的道路。应当看到,中西文化互有优长,固守传统与全盘西化,都只能是误入迷途的两个极端。但要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在近现代的大部分时间内,却成为不可能。这样,笼罩于西学强势语境下的近现代庄学研究,基本上就成了西学改造中国文化的试验场。中国传统重“天人合一”整体和谐的一元化通感思维也变而为重“天人二分”逻辑思辨的二元对象思维。当西方二元化的主客对立说介入时,《庄子》“物化”论的背景旋即改变。虽然,有许多学者谈到了《庄子》的物化人生观、物化艺术观,但气味已和庄子迥异。这里,我们先来看几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种是“逻辑实证论”,以崔大华、崔宜明为代表。崔大华认为:“《庄子》中的这类‘物化’描写还有很多,但基本上不外乎这样三种观念成份:一是诡谲荒诞的寓言或神奇传说;二是没有证验的、不确切的生活经验;三是缺乏具体环节和思维过程的哲学洞察。”(注:崔大华:《庄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110页。)崔大华从黑格尔“运动的本质是成为空间和时间的直接统一”(注:崔大华:《庄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110页。)理论出发,将庄子的“化”释为“万物生成和存在的形式”,是成为时间和空间本质的运动。认为《庄子》的“物化”不符合生活的客观逻辑,缺乏科学的实证环节,所以是荒诞、不切实际的东西。崔宜明则以严密逻辑与理性思辨为基础,提出“化”就是“理”与“必然性”的看法,并认为客观存在之理的“化”与带主体自由品格的“观”是对立统一的(注:崔宜明:《生存与智慧——庄子哲学的现代阐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6页。)。以“理性思辨”分析庄子“物化”说是二崔的一个显著特点。
二崔的重要贡献是以西方逻辑实证精神对庄学作出了系统梳理。但这种以逻辑实证主义和主客符合论为真理的对象化思维模式,与庄子以道化的存有论为前提的真理观迥异。因为在庄子看来,世界、人生、文学都不过是道在物化中的自行绽放,万物、作品的“美”也都只是道的自行闪现。美、善、真都并不以我与世界是否相“符合”为前提,而是有一种先在的原始生命统一性。
第二种是“艺术境界论”,以徐复观、陈鼓应为代表。如徐复观认为:“庄子在心斋的地方所呈现出的‘一’,实即艺术精神的主客两忘的境界。庄子称此一境界为‘物化’,或‘物忘’。这是由丧、忘我而必然呈现的境界。(蝴蝶梦)这是主客合一的极至。因主客合一,不知有我,即不知有物,而遂与物相忘。”(注: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3、37、56页。)此种观点与“逻辑实证论”相反,而将“物化”、“蝴蝶梦”看成纯精神层面的艺术活动或艺术的“心态”与“心境”,即所谓“最高艺术精神之投射”,“艺术精神的主客两忘的境界”(注: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3、37、56页。)。徐复观指出,《庄子》中的天地万物都是“有情的”,都有“人格的形态”,都被赋予了“观照者的内地生命”(注: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3、37、56页。)。物化就是人生观照世界、生命的一种审美化、艺术化方式,物、对象都是人性纯洁的直接流露,是道德的具体化、具象化。二人的贡献在于重新发现庄子“物化”说中蕴藏的艺术精神和境界人生,突出了人的自觉性与能动性,避免了科学实证主义的偏狭。其缺点在于,把“物化”看作纯主观,远离现实的心灵活动,导致了绝对神秘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误解。
第三种观点是“艺术创作论”,以张少康、刘绍谨等学者为代表。如张少康:“庄子认为只有达到‘虚静’,才能排除一切主观和客观杂念对自己的干扰,才能智照日月,洞鉴万物,深入领会创造对象的外在形态特点和内在规律,集中精力进行复杂的创造活动,使创造者与被创造者融合为一,使主体和客体进入到‘物化’的状态,这时就能创造出与自然同化的技艺产品来,这个道理和艺术创造是一致的。”(注: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9页。)他们着重指出了物化在人生境界或艺术创作层面的心理学内容,注重揭示“物化”境界与“虚静”心理的关联,将“物化”看作主体心灵与客观自然融合的最佳状态。并指出,“物化”在庄子那里是与技艺创造、寓言形式相联系的,其对文学的“虚静”、“神思”说影响深远,物化的境界就是马克思的“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是“人化自然”,是合于康德“无目的而合规律”的审美创造。张先生更进而描述了《庄子》中隐藏的“虚静”心理→“物化”创作→“天籁”境界的文学创作道路。张、刘二人的贡献在于重新发现了庄子的文学价值,是将哲学庄子转向文学庄子的一次有益尝试。但以“人化”解读“物化”,并未脱离“人本主义”嫌疑,而与庄周“齐物论”相违。
从以上分析见出,近代学者在西学笼罩的视野中阐释庄子,有别开生面、新意迭出的见解。但因急于用西方科学主义、逻辑主义将《庄子》进行现代化转换,故难免有生吞活剥的偏差。而又因文化视角的“它者”转换,使《庄子》中被传统遮蔽的东西,获得了意外生机。这种生机就是从《庄子》中发掘出了被传统自然观压抑太多的“人”,这种人是具有自由精神、理性思辨、超越境界、艺术气质、独立品格的生命个体。当然,这种“个体”因染上了太过浓厚的主体主义与认识论、工具论色彩,由此也在某种程度上被放大、变形。但毕竟,西方文化的“它者”视角,为《庄子》及其“物化”诗境的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
三、新的解读
实际上,在西学介入前,就已有部分中国传统学人在深思,如何从一元的单维文化视角中转换出来,而赢得多种文化视角的透视。这种多元文化观照的实践就是带有涵容谅解与历史还原精神的“以庄解庄”方法论的出现。自清中叶以来,这种解庄方法突破了儒学、理学、禅学、朴学的遮蔽,也化解了从西方传入的主客认知论、实践工具论、逻辑实证论的滞碍。其代表人物有林云铭、郭庆藩、闻一多、曹础基、栾栋等。
清林云铭《解庄杂说》:“《庄子》旨近老氏,人皆知之;然其中或有类于儒书,或有类于禅教。合三氏之长者,方许读此书。”(注:谢祥皓、李思乐:《庄子序跋论评辑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7、300页。)林氏看到了《庄子》本身的异质性,指出解庄不能局限于某种文化的单维视角,而应合老氏、儒学、禅教三者之长,差异共存,多方观照。他认识到这种差异共存的多元解读仍不足化解传统学人陷于一偏的弊端,故其后又提出:“《庄子》为解不一,或以老解,或以儒解,或以禅解。究竟牵强无当,不如还以庄子解之。”(注:谢祥皓、李思乐:《庄子序跋论评辑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7、300页。)既然学者免不了受儒学或禅教左右,何不如搁置成见,而以“虚静”、“明彻”、“无我”之心直面庄子本身。这与胡塞尔等西方学者提倡的“现象学还原”即“停止判断”、“悬搁成见”等方法论有诸多相似之处。当然,林云铭的以庄解庄,尚还未形成一种现象学还原的成熟理论与方法论,而只是一种自觉或不自觉方法实践,并主要植根于庄学自身的土壤,即庄子化通彼此是非的“物化”观。
其后,郭庆藩、闻一多都从实践上对“以庄解庄”的精神与方法多所推进,但终未形成自觉的理论升华。曹础基《庄子浅注》是建国后第一部庄子注书。该书浅显易懂,评点校注甚见功力,但其真精神却是潜藏于传统校勘考据中的“以庄解庄”新方法的运用。在《浅注》(新版)中,曹先生摒弃了近人对“物化”进行随意比附、刻意穿凿的做法,力图在庄子言说的本真语境及思想脉络中还原庄子。曹先生看出了“物化”说具有源发层面(道化万形)与事实层面(物物互化)的重要区别,更觉察了物化中道、物、人、文的内在关联,指出了世界从根本上说来是道之物化中的整体存在。但尚有不足的是,“以庄解庄”与“物化”说的内在关联仍未得到阐释。拙文《〈庄子〉物化思想初探》(注:何光顺:《〈庄子〉物化思想初探》,《广西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则提出对庄子“物化”论的理解必须与其“道化”论相联系,并指出“物化”是庄子阐释生存和化解各种矛盾的方式,其实质是“道化”境界的过渡。
从清林云铭到当代学人,虽从不同角度实践着以庄解庄的方法,却一直未能对该方法进行理论升华及对《庄子》中潜藏的核心概念“物化”说与“以庄解庄”方法联系。林云铭对“以庄解庄”的提倡暗含着排除成见、虚心静观的“物化”说的影子,但这种潜在的东西却尚未得到本质的充实,也不可能上升到“理念论”与“方法论”的高度。这不能不说与传统文化的藩篱尚未得到根本突破有甚大关系。
栾栋教授是近年来致力于融贯古今,会通中西,并对庄子“大化”(物化)说有独到见解的学者之一。栾先生认为,庄子“物化”说源于《周易》“易化”法,而又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周易》重“通变”、“几神”,以化通天地神人的“大化”精神是庄子的文化母胎。“大化”观是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先秦易学、老、庄的根本切入点。栾先生进而在传统文化的历史背景与中西文化融通的当代语境中,对“以庄解庄”方法作了理论的提炼与升华。可以认为,“以庄解庄”是对庄子化通天地神人的“物化”说的回归。概括说来,“以庄解庄”方法论主要包括三层含义:
第一,“以庄解庄”是在内、外、杂篇比对、训释的基础上,达到对传统“以它平它”思想方法的突破。“以它平它”思想最早见于《国语·郑语》,其核心在于强调异质和谐中才会有文明的诞生和学术的繁荣,但流弊所及,也造成各家思想无原则调和。如郭象将庄学融入名教,慧远将“物化”等同佛家“法性”,苏轼发明庄子实助孔教说等,都是对庄子原始思想的偏离。人们习惯于将庄子归入道家流派,也就是说,《庄子》确与其他门派存在差异,但《庄子》的动态与分裂使其本能地抗拒着任何体系、形态的固化努力,差异性研究不能完全涵容《庄子》。实质上,庄子和而不流,流而不派。和而不流,是指庄子在众多差异性裂变中取得和谐平稳,但不随波逐流;流而不派,是指庄子思想动荡周流、变化开阖,却不画地为牢。不过,用“以庄解庄”突破“以它平它”,并不意味着用“同一性”来代替“差异性”。应看到,《庄子》内、外、杂篇本身已形成不断吸纳又不断稀释的思想动态群落与天然生态圈。以“大化观”(“物化”观)打通同一性与差异性的障壁,是庄子思想的内在要义。庄子不以同一性,而以动态的活泼性,以生生不息的“大化”说克服其寓言中隐藏的差异性、变化性。“以庄解庄”是对“以它平它”说的突破,是立足庄子思想本身,对庄子作出的历史还原。
第二,“以庄解庄”是对庄学研究史的溯本求源,是对学界将庄学现代化、时髦化的有力反拨。庄子思想核心在“化”(物化),其终极在“道”,其底蕴在“自然”。化“是非”于“无是非”,化“不平等”于“平等”,化“人为”于“自然”,化“彼我”于“齐一”。《庄子》内篇是这种思想的原始面貌,而外杂篇及历代学者注庄解庄多不同程度偏离了庄子原始面貌。“以庄解庄”意欲揭去庄学研究中为庄子蒙上的层层面纱,还先秦庄学的本真,进而对先秦庄学作出细致梳理,对庄子自作、庄学儒派、庄学黄老派、庄学名法派及庄学嫡派作出恰当分界,最终以《庄子》内篇原始精神为基点,导出庄学合理外延,并据此判定外、杂篇在庄学中的恰当位置。这种溯本求源的追寻就是“以庄解庄”方法论的具体化。同时,这种方法论对时下将庄子黑格尔化、海德格尔化、后现代化等解庄偏颇有很强的针砭作用。
第三,“以庄解庄”是对庄子矛盾思想的开合启蔽,是对庄子研究者将庄子原点化和读者化的双重解脱。在庄学研究中,往往有两个极端:一是将《庄子》压缩为“道”的原点,一是将《庄子》读者化,认为读者尽可各取所需。这两个极端的缺点在于将《庄子》固化,遮蔽了《庄子》源发动态与生态性,为歪曲偏解《庄子》留下口实。实际上,《庄子》内外杂篇孕育的矛盾动态思想本身已成为循环无端,氤氲化育的缘境,从而化解了将《庄子》原点化和读者化中的固执偏差。以庄解庄,就是学者当深入《庄子》思想矛盾的深处,探析《庄子》动态缘境的成因。“以庄解庄”力求保护《庄子》原发动态性,让《庄子》在开放中永葆活力。
在20世纪末的重新解读中,《庄子》“物化”说的原发生成、人生境界、艺术精神、文学特质等诸多内蕴日益凸显。纯哲性反思向纯诗性超越的转渡,已形成一条隐隐约约的林中路。哲学和文学交流融合的时代悄然来临。同时,与“物化”说相辅而行的“以庄解庄”理念与方法论已日趋成熟。这种新方法论对于打通文化“同一性”与“差异性”障壁,消解学术“溯源派”与“现代派”隔阂,反拨文本“原点化”与“读者化”弊端可谓匠心独运。以“大化”(“物化”)说为视角,以“以庄解庄”为方法的解庄方法论,已从根本上突破了庄学自身,成为复兴传统文化,融汇中西学的一座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