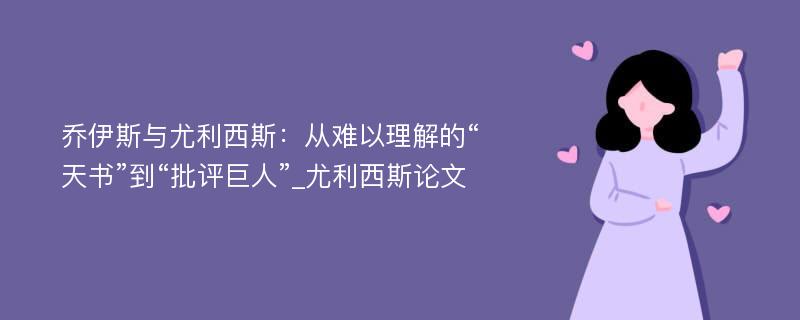
乔伊斯与《尤利西斯》:从天书难解到批评界巨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书论文,巨子论文,难解论文,西斯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0062(2006)05-0049-12
在谈到《尤利西斯》时,乔伊斯曾经对他的一位崇拜者说:“我在书中设置了数不尽的谜团,足够那些教授们忙乱几百年了。”①乔伊斯并没有开玩笑,他果然按自己的构想做了。《尤利西斯》问世后,它与传统小说迥异的形式和内容,其中无数迷雾般的怪词怪语、联想暗示以及形形色色的文字游戏,不仅让一般读者摸不着头脑,就是专家学者也感到茫然无绪,难于卒读。于是,读书界、学术界一片哗然,有人热烈赞扬,更有人愤怒抨击。从那时以后,学者们开始钻研,《尤利西斯》遂逐渐开始被破解,后来读解和研究的人越来越多,研究的内容也越来越深入。今天,对这部作品和乔伊斯的批评已经像莎士比亚批评一样,变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甚至一种产业;乔伊斯的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和音乐剧;还有专门研究他的期刊和杂志;世界各地经常有若干以他为专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人们还把《尤利西斯》所写的6月16日定名为“勃鲁姆日”,每年这一天前后,世界许多地方都要举行各式各样的纪念性学术活动。一个作家能够引起国际社会如此高度的重视,在中外文学史上着实不多见。乔伊斯和《尤利西斯》批评可以说走过一条由极少数人问津到逐渐发展为文学评论界关注热点的轨迹。
一、天书:从瞠目结舌到破解
《尤利西斯》于1922年2月2日在巴黎出版后,立即引发了轩然大波。面对着一部与传统小说完全不同,看起来毫无章法,读起来不知所云的天书,批评家们简直无所措手足,于是,恶评迭起。一篇题为《〈尤利西斯〉的丑闻》的文章说,这部书有三分之二是杂乱无章的,居然有整章没有标点符号和其他说明,叫人根本摸不着头脑,作品的内容全是些无聊和淫秽的东西,充斥着腐败变质的材料,可以说是斯文扫尽。作者无疑是一个乖戾的疯子,他所创作的不过是茅厕文学而已。②一位论者说,这一蓝皮本的书看起来像一本电话簿,它不是要卖给读者的,而是为收藏家准备的,那些买它的人不过是为了收藏获利。③有人说,乔伊斯是欧洲社会道德的叛徒;④有人说,乔伊斯是使整个都柏林蒙受羞辱的无耻之尤。⑤这些具有攻击性的言论大致代表了西方社会对这部作品最原始的一般反应。创作界的反应也很差。作家们对这部作品充满反感甚或敌意,弗吉妮娅·沃尔芙说,这是一本“没有教养的”书,一本“自学成材的工人”写的书,仿佛“一个惴惴不安的本科生在搔痒痒”;埃德蒙·高斯说,这本书写得“乱七八糟,趣味、文体、所有一切都臭极了”;保尔·克洛岱尔说,这是一本“恶魔般的”书;纪德说,这本书是一个“假冒的大作”。⑥第一篇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的评论是爱尔兰作家尚恩·莱斯利爵士,在伦敦《评论季刊》上发表的文章,但这篇评论的基调仍然是较为负面的。莱斯利抱怨说,《尤利西斯》在总体上是无法阅读的,也是让人不愿引用的,书中的内容“与高雅的趣味、美好的道德格格不入”,它的主要目的是要“愚弄读者甚至优秀的批评家”,它完全是“没有道德观念的”、混乱的、没有形式的。⑦
《尤利西斯》从1915年开始构思到1922年出版,经历了7年时间。1918年,美国杂志《小评论》开始连载这部尚未完成的作品,从1918年3月到1920年9-12月,《小评论》分23期连载了这部作品的1-14章。由于庞德的协助,伦敦的《自我主义者》也于1919年2月到1919年12月连载了部分章节。尽管在7年的创作过程中,乔伊斯总在不断增删修改已经写成的章节,但全书的基本轮廓和形式结构从一开始就是明确的,⑧只不过这些形式、结构和技巧的特征都隐匿在看似杂乱无序与谜团般的文字中。乔伊斯有意要让批评家和学者们用较长的时间和精力去破解他设置的迷宫,他认为这才是艺术家取得不朽的唯一途径。但他这些精巧的设计隐藏得相当深,不仅一般读者无由理解他的真意,就是精明的学者也难于透过文字完全把握其深藏的机巧。因此,不能完全不让批评界了解他的意图,于是,他采取了十分精明的做法,通过朋友和亲人缓慢地向外界泄露他的创作奥秘。1918年夏,乔伊斯初识弗兰克·勃金不久,就和他谈论了尤利西斯作为一个完满的文学形象的话题,并向他透露了自己正在写《尤利西斯》的信息:“我正在写一本以尤利西斯的漫游为基础的书,《奥德赛》是这本书的基本框架。只不过我这本书的时代是现在,书中所有人的漫游不超过18个小时罢了”,“我的这本书是一部现代的《奥德赛》,其中的每一章都和尤利西斯的漫游相对应”。⑨1920年9月间,他把《尤利西斯》的创作提纲寄给了友人卡尔洛·里纳提 (Carlo Linati);1921年11月前后,又将《尤利西斯》的创作提纲借给了认识不久的拉尔博。⑩这两个提纲虽然不尽相同,但都包含了一些十分关键的词语,对理解这部作品的题旨、结构、人物具有重大提示作用。这两个提纲后来都公诸于世,第一个提纲即所谓的“里纳提提纲”(Linati Schema),第二个提纲即所谓的拉尔博提纲(Larbaud Schema)。(11)第二个提纲很快就在乔伊斯友人的小圈子里流传,并为拉尔博于1921年12月7日在巴黎莎士比亚书局文人聚会上所做的公开讲演以及后来所写的评论提供了可靠的材料,使他可以对《尤利西斯》奥德赛式的结构、人物、主题和各种独特的技巧做出明晰的阐发,从而对后来的《尤利西斯》读解和批评产生了重大影响。(12)这两个提纲也为斯图亚特·吉尔伯特(Stuart Gilbert)于 1930年出版的《乔伊斯的〈尤利西斯〉》(James Joyce's Ulysses)提供了重要依据,而这本书对于广大读者理解《尤利西斯》是极为重要的一本参考书,也是乔伊斯批评中公认的一部经典之作。
吉尔伯特是乔伊斯的密友之一,曾在乔伊斯的支持下对《尤利西斯》的法译文做过校订。由于他对《尤利西斯》的热情和理解获得了乔伊斯的欢心,乔伊斯曾向他解说《尤利西斯》的结构和一些章节。正是在乔伊斯的具体帮助下,他率先出版了研究此书的第一本专著。这部专著最先向学术界较为详细地阐释了《尤利西斯》在总体上暗藏的荷马式结构,与《奥德赛》加以对照,逐章指出了相关的主题、母题、颜色、关联等,并对一些晦涩的文句做了注释。同时,此书也指出乔伊斯一些重要观念的来源(譬如,贝拉尔的《腓尼基人与奥德赛》和辛奈特的《佛教秘义》等)。吉尔伯特这部著作对后来大量《尤利西斯》读解类著述影响甚大。(13)
吉尔伯特这本书之后,《尤利西斯》在学界已经不再是“天书”了,批评家们开始循着吉尔伯特的指点,从各个层面对其加以深入探讨;与此同时,一些学者继续从读解的角度进一步钻研,产生了一批重要成果。三四十年代影响颇大的有两部著作,即弗兰克·勃金(Frank Budgen)的《乔伊斯和(尤利西斯)的创作》(James Joyce and the Making of Ulysses,1934)和哈利·列文(Harry Levin)的《乔伊斯导读与评点》(James Joyce:A Critical Introduction,1941)。六七十年代又出现了两本十分重要的笺注性著作,即美国学者韦尔登·桑顿(Weldon Thornton)的《〈尤利西斯〉中的暗示:注释性条目》(Allusions in Ulysses: An Annotated List,1961,1968)和唐·吉福德的 (Don Gifford)的《〈尤利西斯〉注释》(Ulysses Annotated:Notes for James Joyce's Ulysses,1974, 1988)。
勃金也是乔伊斯的密友之一,1918年乔伊斯寄居苏黎世,一面教书,一面创作《尤利西斯》,曾与勃金朝夕相处,并向他讲述了《尤利西斯》大部分章节构思的情况。勃金这本书既记录了一位艺术家与一位小说家之间的交往和友谊,又提供了这部小说创作中许多鲜为人知的第一手材料,既有传记成分,又从一个艺术家的眼光解析了这部作品形成的过程,正如著名学者克莱夫·哈特在这本书“导言”中所说的那样,“《尤利西斯》复述了《奥德赛》的故事,而勃金这本书则复述了《尤利西斯》的故事”。(14)毫无疑问,这本书对读者读解《尤利西斯》具有重大参考价值。列文的《乔伊斯导读与评点》是第一部美国学者解析与评点《尤利西斯》的专著。这本书不仅包含了对《尤利西斯》的解析和评点,而且对乔伊斯做出了明晰的评价,将其置于与乔叟、莎士比亚、密尔顿等英国文学大师同列的位置,为美国后来的乔学确定了基调。
韦尔登·桑顿和唐·吉福德对《尤利西斯》逐章逐句做了细致的笺注,在语言文字、典故征引以及篇章结构上用力甚多。这两本注释既有重叠又有区别。桑顿的注释紧扣文本,尽力发掘文本中具体字句的暗示与涵义;而吉福德的注释则较多关注文本间的指涉,尽力提供更多关于语境的阐释。桑顿的注释规模适中,比较适合初读《尤利西斯》的读者;而吉福德的注释则规模宏大,内容详实,不仅对普通读者有用,也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的便利,特别是其1988年的修订本,修订增补多达1000余处,这本书既对双关语、笑话、掌故、方言、俗语、外来语、混成词等种种语词给予明晰的解说,又对文中涉及的宗教、历史、哲学、文学、神话传说、民俗民风、歌谣俚曲、地名人名等给以了详细的阐释,在《尤利西斯》注释类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两部工具书都采用逐章逐条加以剖析的结构,可谓《尤利西斯》读解类著作中的双璧,读者可以同时使用,当能相互补充,相得益彰。(15)
此外,哈利·布莱迈尔(Harry Blamires)的《勃鲁姆日书》(Bloomsday Book,1966)也是一本非常实用的导读性著作。此书用简洁朴实的语言对《尤利西斯》的18章做了逐页梳理,把作品中的人物、事件、象征、语言游戏、征引等综合在一起加以解析,作者明确地说此书是为一般读者写的,按照他的预期,读者在这本导读的指引下,“首次阅读《尤利西斯》所获得的理解将是他在没有本书指引下数次阅读才能获得的”。(16)作者在30年后出版了此书的修订本(第三版),更名为《新勃鲁姆日书》,这个新版本不仅在内容上做了个别的修订,而且标注了三个当今通用的版本(盖勃勒1986年修订本、牛津大学1993年“世界经典”本、企鹅 1992年“20世纪经典”本)的相应页码,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对读者的导引作用远远超越了他30年前的预期。
这类破解性的著述对《尤利西斯》的读解真是功不可没,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它们开创性的努力,《尤利西斯》对广大读者来说,今天依然是无法理解的天书。
二、批评:从表层走向深入
《尤利西斯》问世之后,对这部“天书”真正有认识的只是与乔伊斯有交往的一个小圈子里的人,当然这些人也都是颇有建树的作家和批评家。作为早期的批评,他们的文章或讲演今天看来自然还不能说十分深入,但却筚路蓝缕,对后来的批评起了引领和催生的重要作用。
庞德是当时少数懂得这部小说的革命意义和价值的批评家之一,他指出,乔伊斯继承的是福楼拜的传统,但大大超越了福楼拜。《尤利西斯》有许多形式上的创造,例如,采用了荷马史诗的结构框架、奏鸣曲的形式和父子小说的线索等,这些重大的革新正是“我们的艺术向前发展的关键所在”,他说:“《尤利西斯》未必是每一个人都能赞赏的书,但却是每一个严肃的批评家必须阅读的书。”(17)庞德作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大宗师,在20世纪20年代的巴黎,对包括乔伊斯在内的许多现代主义作家曾给予积极的扶持和热情的指导。他是现代主义纲领的制定者和推动者。没有他的提携,《尤利西斯》能否诞生当是一个问号,而他的评论尽管简短,却指明了《尤利西斯》在现代主义文学中的革命性意义。
从另一个角度指出《尤利西斯》革命意义的是美国著名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威尔逊不仅对《尤利西斯》的结构、语言等形式因素做了比较细致的分析,而且着重指出这部作品在人物内心世界刻画方面的创新。威尔逊说,乔伊斯不仅能像福楼拜那样对外在世界做逼真的描写,而且能对人物的内心世界做逼真的描绘。《尤利西斯》是天才的创造,它“对普通人的意识做了最忠实的透视”。在《布法尔与佩居谢》中,福楼拜是通过“列数人有限的低劣和平庸”来表现人性的卑贱委琐,而在《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却通过内在心理的描写囊括了人所有的低劣和平庸。威尔逊说,乔伊斯是小说创作的“大师”,他创造了新的文学形式,为小说创作确立了可使其无愧于和诗歌、戏剧同日而语的最高标准。(18)
作为与乔伊斯双峰并峙的现代主义大师,T.S.艾略特早期的批评显然具有重大意义。他在 1923年11月《日晷》上发表的《〈尤利西斯〉、秩序和神话》一文中指出了《尤利西斯》在方法与结构上的重大革新:即其对《奥德赛》结构的借鉴、文体的创新和每一章中象征的运用。他认为,运用神话结构把“当代性与古典性加以持续对照”将会对“杂乱无章、百无聊赖的当代史做出全景式的审视”,从而赋予它秩序与形式,使其产生意义。他指出,乔伊斯对篇章结构这种操控和布局的杰出才能是后来者必将学习与借鉴的。《尤利西斯》使我们明白,在传统的叙述方法之外,还可以采用神话方法,而神话方法的采用,将使“现代世界的艺术创造成为可能”。(19)艾略特拈出《尤利西斯》中象征与神话结构作为现代主义小说的重要因素加以推崇,起到了一石二鸟的作用,既标榜了现代主义,又凸显了《尤利西斯》。
还有一些批评家从另外一些角度评说了《尤利西斯》的创造性。玛丽·考勒姆指出了《尤利西斯》鲜明的自传性,她说《尤利西斯》“是乔伊斯的自白,是一本最真诚、最狡黠地写就的自传性作品”。它史无前例地写出了两个男人的内心世界,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作家的全部生活和内心历程,这是前无古人的,连卢梭也没有完全做到。(20)吉尔伯特·塞尔德斯指出,《尤利西斯》的问世表明小说创作将开始一个“新的转向”,这部作品把亨利·詹姆斯和福楼拜创作的那类小说发展到了顶峰,它不仅是乔伊斯本人艺术生涯的顶峰,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精神生活的顶峰。乔伊斯在这部作品中“用近乎完美的技巧对小说的形式和结构所做的创新将对未来的作家产生难于估量的影响”,这部小说中还有数以百计的创新点可供后人借鉴,后来的小说家们将没有人能够完全避开它的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乔伊斯是最令人畏惧的,也是最令人赞赏的。(21)
庞德、威尔逊、艾略特等人的上述批评尽管未必深入,但他们着眼于《尤利西斯》的革命性与创造性,指出了这部作品与传统小说若干迥异之处,为其在现代主义小说史上经典地位的确立铺平了道路。
30年代之后,特别是从《尤利西斯》在美国解禁到七八十年代,这部作品的批评开始向纵深发展。在篇幅上,这一时期的批评不再是概括式、综合式的短评,相反,却出现了许多长篇的深度批评,批评的范围也大大拓展,从早期较多侧重形式开始向全方位评论挪移,批评家们开始从语言、文体、形式、结构、主题、政治、心理学、社会学等多侧面、多角度切入讨论,从而使《尤利西斯》批评获得了飞跃式的进展。
这一时期,对《尤利西斯》的形式、结构、文体和语言的深入探讨成为批评的一个热点。就叙事结构而言,一些批评家把《尤利西斯》看作一个巨大的空间结构,指出其运用意识流等技巧造成叙事的碎片化、空间化,对传统叙事结构是一个重大变革,例如欧文·斯坦伯格(Erwin Steinberg)在其《〈尤利西斯〉中的意识流及其他》(Th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and Beyond in Ulysses,1973)中就将《尤利西斯》看作爱森斯坦电影式的蒙太奇结构,指出乔伊斯运用意识流手法描述人物的心理过程,形成断裂的叙事碎片,是一种全新的叙事实验。而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在其《现代文学的空间形式》(The Spatial Form of Modern Literature)一文中则把《尤利西斯》看作一首意象主义诗歌,指出其总是要不断“打破读者对叙事连续性的正常期待,迫使他们从空间而非时间去观察叙事结构中诸种成分的并置”。(22)相反,卡伦·劳伦斯(Karen Lawrence)则从时间性的角度来分析《尤利西斯》的叙事结构,她的讨论集中在这部作品的文体变化与读者的反应上。在《尤利西斯文体的奥德赛》(The Odyssey of Style in Ulyss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中,她试图从一种新的时间角度来读解这部作品,她提出作品中文体的变化是一种修辞的实验,具有某种总体的方向,而这些文体上的变化在断裂的发展过程中迫使读者在自己的阅读期待中做出相应的调整。她认为,任何“拓扑性”和“目的性”的阅读都是无济于事的,这部作品从根本上是“反启示的”,乔伊斯“提出了种种意义的可能性,但却拒绝给出某种终极的启示”。(23)休·肯纳(Hugh Kenner)早在其1955年出版的《都柏林的乔伊斯》中就率先提出乔伊斯把戏仿、反讽等修辞手段作为重要创作技巧的事实,30年后又在其《尤利西斯》(Ulysses,1980,revised,1987)等著作中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进一步论述了这部作品的文体变化。他指出,《尤利西斯》前半部(前10章)采用了“初始的文体”,主要是大段的“内心独白”、“场景突转”和“无情的反讽”,而后半部(后8章)补入后,整部作品的文体就必须遵从“父子相逢”的荷马式结构,因此是“强制的”,这就必须强调一种同时关注两个人物行动的“叙事模式”,肯纳借用了戴维·海曼的“安排者”(arranger)的说法。(24)通过文本细读,说明这个“安排者”是一种“插入的意识”,既不是作者,也不是叙述者,甚至根本就不是一个“声音”,因为它并不“讲话”,读者完全听不到它,只能看到它冷漠的行动或表演。肯纳认为,这个“安排者”对整个小说具有巨大的操控作用,它“也许是《尤利西斯》中最激进的、最令人沮丧的创造”。(25)雷·戈特弗里德(Ray K.Gottfried)的《尤利西斯的句法艺术》(The Art of Joyce's Syntax in Ulysses,1980)集中讨论《尤利西斯》的句法,通过对其句法结构的精细分析,特别指出乔伊斯如何运用了亚里士多德所谓的“隐德来希”(entelechy)法,即如何通过本原的能动过程,实现句法中潜在的可能性。戴维·莱特(David G. Wright)则在《尤利西斯的反讽》(Ironies of Ulysses,1991)中对《尤利西斯》中反讽的运用逐章做了全面细致的讨论。他强调,大量反讽构成了这部作品崭新叙事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显著特征。罗伯特·马丁·亚当斯(Robert Martin Adams)则对《尤利西斯》中的象征做了深入的探讨,他的《表层与象征:〈尤利西斯〉的一致性》 (Surface and Symbol:The Consistancy of James Joyce's Ulysses,1962)是《尤利西斯》问世 40年来对这部作品评论中相当精彩的一部。作者钩沉索隐,对世纪之交都柏林与本书有关的档案记录、报章杂志、回忆访谈等方方面面的材料做了认真细致的爬梳,发现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新材料,并将这些新材料与文本相互比勘,从而将作品的表层与其深层的象征区别开来,在《尤利西斯》研究中,这部书不仅以材料搜求与文本分析见长,更重要的是它对作品深层的象征结构做了颇有价值的讨论,指出乔伊斯的独到处正是他编织了巨大的象征网,并在这一象征的网状结构中对人物的内在与外在世界做出了自然主义的描绘。
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的《詹姆斯·乔伊斯语言导引》(Joysprick: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nguage of James Joyce,1973)、科林·麦卡伯(Colin MacCabe)的《詹姆斯·乔伊斯和文字革命》(James Joyce and the Revolution of the Word,1978)等,都是以《尤利西斯》等作品的语言实验为中心内容的代表性著作。伯吉斯本人是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之一,他对乔伊斯的批评可以说更多的是亲切与亲和性。他这本讨论乔氏语言的著作,以广大普通读者为对象,文笔生动,语言平易,是人们阅读乔伊斯最佳的入门书之一。《詹姆斯·乔伊斯和文字革命》着力挖掘乔伊斯语言实验的革命意义,在这一层面上将其与莎士比亚等量齐观。20余年后作者在修订版中又增加了新的材料与见解,特别强调了乔氏语言革命的政治内涵,从而受到了伊格尔顿、洛奇等著名英国批评家的高度赞誉。
除著述之外,这一阶段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批评文集。克莱夫·哈特、戴维·海曼(Clive Hart & David Hayman)合编的《尤利西斯批评文集》(James Joyce's Ulysses:Critical Essays, 1974)和伯纳德·本斯托克(Bernard Benstock)的《〈尤利西斯批评文集〉》(Critical Essays on James Joyce's Ulysses,1989)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两部。就这两部文集而论,克莱夫·哈特和戴维·海曼合编的《尤利西斯批评文集》显然更胜一筹。这部文集选收了18位一流乔学家分论《尤利西斯》各章的文章,这些文章不限于一般的读解,而是通过精细的阅读,从文体、色调、视点、叙事结构、象征意义等不同角度,着重论述了这部作品在形式、技巧、结构等方面的特征,并兼顾了内容与意义方面的分析。从总体上看,每一章的论述都有独到之处,而全书能集众家之长,道人所未道,是《尤利西斯》批评文集中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一本经典之作。(26)
讨论乔伊斯和《尤利西斯》的现代性是这一时期批评的另一个热点。从现代或现代主义角度论述乔伊斯和《尤利西斯》较早的有威廉·廷达尔 (William Tindall)的《乔伊斯解释现代世界的方式》(James Joyce:His Way of Interpreting the Modern World,1950),这部著作集中分析《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从人性、家庭社会关系、现代人的心理、语言与文字、神话与象征等不同层面讨论了乔伊斯对现代世界与传统完全不同的解释方式,极富启发性。后来有海沃德·埃里希 (Heyward Ehrlich)编选的《詹姆斯·乔伊斯和现代主义》(Light Rays:James Joyce and Modernism,1984),此书选收了在拉特格斯大学召开的乔伊斯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的部分论文,同时又补充一些其他学者的文章。全书把乔伊斯置于现代文学、哲学、心理学、音乐、绘画的语境中,集中讨论其现代特色。为此书撰文的不仅有像莫里斯·贝雅(Morris Beja)、休·肯纳(Hugh Kenner)、扎克·波温(Zack Bowen)、莫顿·勒维特 (Morton P.Levitt)、埃尔曼等著名的乔学家,还有像莱斯利·费德勒(Leslie Fiedler)、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等以研究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闻名的批评家,更有像诺曼·奥布朗 (Norman O Brown)这样的现代主义心理分析学者和约翰·凯奇(John Cage)这样的现代主义音乐大师。事实上,关于这一论题的讨论一直延续到当代。
三、当代性:批评的新动向
20世纪后半叶出现的种种批评流派和理论热,不仅使乔伊斯和《尤利西斯》批评在规模上进一步扩大、在深度与广度上进一步开拓,也为过去 20年来的乔伊斯和《尤利西斯》批评带来了新气象,批评家们运用这些不同的理论工具对乔伊斯和这部作品提出了新的读解。
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的影响下,有大量的著作从心理分析的角度论述乔伊斯和《尤利西斯》。这类著述中重要的有谢尔登·勃利维克 (Sheldon Brivic)的《弗洛伊德与荣格之间的乔伊斯》(Joyce Between Freud and Jung,1980)。勃利维克从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心理分析理论立论,分析乔氏《尤利西斯》等作品。后来作者继续就这一领域做深入探索,相继写出了《创造者乔伊斯》 (Joyce,the Creator,1985)、《符号的面纱:乔伊斯、拉康和知觉》(The Veil of Signs:Joyce, Lacan,and Perception,1991)和《乔伊斯的觉醒中的女人》(Joyce's Waking Women:An Introduction to Finnegans Wake,1995)等,从而使自己成为从心理分析角度研究乔伊斯的重要批评家之一。勃利维克把乔氏笔下的人物及其行为全部置于弗洛伊德、荣格、拉康等人的心理分析框架中,从爱欲、创造、阉割、原型、符号等角度给以解析,获得了新的意义,譬如,他认为,作为《尤利西斯》“情节”的高潮,勃鲁姆与斯蒂芬“父子相遇”行为的完成来自勃鲁姆的“性心理动力”,倘若6月16那天没有勃鲁姆与莫莉做爱的性行为,勃鲁姆就不会产生成为斯蒂芬“精神之父”的心理动力。(27)理查·布朗(Richard Brown)的《乔伊斯和性》(James Joyce and Sexuality,1985,1989, 1990)集中探讨了乔伊斯对性的立场。全书以四章的篇幅结合《尤利西斯》等文本阐述了现代的爱与婚恋、新的性科学、性美学等问题。作者指出,莫莉和勃鲁姆二人分别实现与未实现的通奸是《尤利西斯》中颇有意义的事件,这体现了乔氏赞同自由恋爱未必一定要实践婚姻的现代观念;作者分析了勃鲁姆及乔氏对两性差异的强调,指出勃鲁姆性格中的“女人气”,并讨论了《尤利西斯》等文本中“第三性”即“雌雄同体”等问题。(28)莫德·艾尔曼(Maud Ellmann)在《〈尤利西斯〉中的鬼魂》(1990)一文中以第9章斯蒂芬关于莎士比亚与哈姆雷特的思考,以及第15章关于勃鲁姆在红灯区幽灵般游历的戏剧性文字为依据,从哲学与弗洛伊德、琼斯等人的心理分析理论出发探讨了父亲的鬼魂、死亡、欲望、自我等与斯蒂芬、勃鲁姆以及戏剧的关系,指出第15章中隐含着“歇斯底里起源于漫游的子宫”的说法,还认为“《尤利西斯》是一本写鬼魂的书;那里的鬼魂如同地狱里饥饿的精灵在吸食自我的血”。(29)
最近的这类著作以琼·金保尔(Jean Kimball)的《乔伊斯和早期心理分析家》(Joyce and the Early Freudians:A Synchronic Dialogue of Texts,2003)以及路克·舍斯顿(Luke Thurston)的《詹姆斯·乔伊斯和心理分析问题》(James Joyce and the Problem of Psychoanalysis,2004)为代表,前者从互文性的角度讨论乔伊斯在的里雅斯特期间,购买并阅读过的弗洛伊德、荣格和琼斯等心理分析家的三篇早期之作(30)与《艺术家青年时期的画像》、《尤利西斯》等小说之间的关系,作者侧重的是文本之间的“对话”,进一步发掘了从心理分析的理论与方法探讨乔伊斯文本的可能性。同时还对乔氏使用“暗示”等修辞手段做了弗洛伊德式的分析。后者的重点却不在文本,而在作者本人。舍斯顿讨论拉康、弗洛伊德等人与乔伊斯的关系,以拉康的理论为依据,分析乔伊斯的创作,他提出,尽管乔氏本人不愿承认心理分析对他的影响,(31)但他的创作本身却将他自身置于完全可以进行心理分析的文学大家的行列中。这些著作不仅对乔学者,而且对文学理论家和心理分析家都是很重要的参考书。
与心理分析的角度密切相关的是女性主义的角度,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大量从女性主义角度研究乔伊斯和《尤利西斯》的论著。乔伊斯曾经说过他“恨知识女性”的话,(32)但知识女性对乔伊斯及其作品却情有独钟。在对《尤利斯西》等作品的女性主义批评中,女性批评家的专著、编著、论文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博妮·凯姆·司各特(Bonnie Kime Scott)的《乔伊斯和女性主义》(Joyce and Feminism,1984)从当代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挖掘了乔伊斯作品中不同层面的意义,为当代乔伊斯批评提供了一个女性主义的框架。此书不仅论述了诸如哈利叶特·肖·威弗、阿德里安·莫妮耶等对乔伊斯支持甚多的女性,而且还论述了诸如玛丽·考勒姆、瑞贝卡·韦斯特、弗吉尼亚·沃尔芙等人对乔氏所作的女性主义批评。(33)苏塞特·汉克与埃琳娜·温克勒斯(Suzette Henke & Elaine Unkeless)编选的文集《乔伊斯作品中的女人》(Women in Joyce)把焦点设置在乔氏所创造的女性人物身上,从当代和女性主义的视角进行了解析,提出乔氏笔下的女性形象具有象征与原型的意义。凯洛琳·海尔勃朗 (Carolyn G.Heilbrun)在本书简单的“后记”中认为,乔伊斯并不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他对女性的认识受时代与现实的制约,不可能把女性看作“人性的一种范式”,只能按照世俗的眼光来描写女性,他看到了当时都柏林现实中女性生活的艰辛,但却不可能对这一现实做出深刻的剖析与批判,这种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减损了他的伟大。(34)汉克后来又写出了《乔伊斯和欲望的政治》 (James Joyce and the Politics of Desire,1990)一书,将心理分析与女性主义的角度结合起来,侧重讨论乔书中的语言、欲望和性差异,说明乔伊斯怎样瓦解了支撑西方父权制文化数千年的语言确定性,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对乔伊斯笔下女性的评论较多集中在莫莉·勃鲁姆的形象上。戴维·海曼在《经验的莫莉》一文中指出,莫莉是生活创造的那种被动的女性,“她的声音”被擦去了,她的象征意义被减弱了,她只不过是勃鲁姆(乔伊斯)愿望与恐惧的投射。在勃鲁姆的眼中,她只是一个令人销魂的、懒散的、放荡的女人,一个爱打情骂俏的、有着裸露癖的女人,一个泼妇,一个充满肉欲的动物。他认为莫莉应该具有更大的生命力与意义,那种说她懒散和淫荡的观点是不公允的。(35)达西·奥勃莱恩在《莫莉·勃鲁姆的决定因子》一文中认为,乔伊斯塑造的莫莉之所以只有一维的动物性,来自乔伊斯本人与诺拉私生活中那种欲望、负罪感以及性受虐狂纠缠在一起的复杂的心理模式,那种对女性既鄙视又恐惧的态度其实来自爱尔兰天主教的清教传统。(36)温克勒斯在《世俗的莫莉》一文中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莫莉人格中的世俗性,指出那些看似男性的性征,譬如言语中要强、性行为中的控制与进攻性等其实恰恰体现了她的女性性征。而莫莉这类女性也并没有超越世俗和传统的规范。(37)海瑟·库克·凯娄发表在1990年《20世纪文学》冬季号上的一篇专文既不赞成把莫莉看成具有原型意味的妻子、母亲形象,也不赞成将她看成一个淫荡、邋遢的可怕女性形象,而认为莫莉不过是一个真实的普通女人,她对美好生活的理解与渴望同常人并没有两样。(38)詹妮弗·韦克发表在《乔伊斯季刊》上的文章则认为,无论从原型意义上的母亲、妻子抑或从好女人、坏女人的模式来解析莫莉都是不恰当的。她主张从消费文化的丰富性来看待莫莉。按照她的观点,整个爱尔兰是一个消费者,莫莉也是一个消费者,作为一个家庭主妇、一个女性,她在家中尽管未必勤劳,也不生产,但却是一个消费主体,她付出的脑力和心力尽管意义不是很大,但却不无价值。(39)
有相当一批著述讨论乔伊斯以及《尤利西斯》和意识形态、政治、民族、种族、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关系,其中不乏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的角度。布鲁斯·纳德尔(Bruce Ira Nadel)的《乔伊斯和犹太人》(Joyce and Jews: Culture and Texts,1989)通过大量的材料论述了乔伊斯和犹太历史、文化的亲和性,并对形成这一亲和性的原因做了深入的探索;奈尔·戴维森 (NeilR.Davidson)在《乔伊斯、〈尤利西斯〉及犹太身份的建构》(James Joyce,Ulyss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Jewish Ident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中指出,乔伊斯从青年时代起就了解并同情犹太民族的苦难,对犹太民族的文化精神充满了想像,这种想像力构成了他创作《尤利西斯》等作品的内在动力。戴维森还进一步从历史、传记、时代特征等方面讨论了乔伊斯对犹太精神之所以有深刻理解的原因。詹姆斯·费哈尔(James Fairhall)的《乔伊斯和历史问题》 (James Joyce and the Question of History, 1993)以《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为主要文本,从新历史主义等理论视角讨论乔伊斯如何从一个艺术家的立场来对待历史。作者把文学文本置于历史语境中,截取爱尔兰历史中从凤凰公园谋杀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段展示爱尔兰民族独立斗争的多事之秋,通过乔伊斯对待民族主义、殖民主义、阶级、性别等问题的独特态度,说明他试图从必然把握自由的历史意识。德莱克·阿特里奇(Derek Attridge)编选的《半殖民的乔伊斯》 (Semicolonial Joyce,2000)一书中,选收了11位乔学者讨论乔伊斯对待爱尔兰民族解放斗争既爱又恨的复杂立场,将他和他的作品置于西方殖民主义的历史语境中,具有鲜明的后殖民主义视角。
此外,西姆斯·芬尼根(Seamus Finnegan)的《詹姆斯·乔伊斯和以色列人以及流亡中的对话》 (James Joyce and the Israelites and Dialogue in Exile,1995)、约瑟夫·瓦兰特(Joseph Valente)的《詹姆斯·乔伊斯和正义问题》(James Joyce and the Problem of Justice,1995)、艾玛尔·诺兰(Emer Nolan)的《詹姆斯·乔伊斯和民族问题》(James Joyce and Nationalism,1995)、文森特·程(Vincent J.Cheng)的《乔伊斯、种族和帝国》(Joyce,Race,and Empire,1995)、特莱沃·威廉斯(Trevor L.Williams)的《乔伊斯的政治读解》(Reading Joyce Politically,1997)、凯思·布克尔(M.Keith Booker)的《尤利西斯、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Ulysses,Capitalism,and Colonialism:Reading Joyce after the Cold War,2000)、帕特里克·默吉(Patrick McGee)的《马克思之后的乔伊斯》(Joyce beyond Marx: History and Desire in Ulysses and Finnegans Wake,2001)等都是近年来较有影响的著述。这些著述或从民族、种族,或从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等角度读解乔伊斯,从标题一望可知。即使那些标题不甚明确的,也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譬如《詹姆斯·乔伊斯和正义问题》,虽然作者拈出了“正义”这一关键词,但他其实是就这一中心问题,从民族、种族、阶级、性等不同的角度对乔伊斯做政治和伦理化的解读。《乔伊斯的政治读解》从乔伊斯提出的“都柏林是一个瘫痪的城市”的命题出发,通过细读其作品,就爱尔兰和英国的关系、阶级差异、宗教霸权、家庭与性别关系不平衡的权利结构等角度,深入探讨了乔伊斯的政治立场,指出了乔伊斯深厚的人文主义关怀。《马克思之后的乔伊斯》是一个乔学者的论文集,其中既有旧作,也有新论,总体上似乎缺乏一部专著的严谨和周密,但其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却是一以贯之的。作者始终坚持要把乔伊斯置于政治经济和生产的总体语境中来分析,引导读者从文化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理解乔伊斯,从而看到乔伊斯对资本主义的种种价值观所持的批判态度。作者的政治信念是异常坚定的,对作品的分析也是十分恳切的,特别是最后从社会与文化革命理论对《守灵夜》所做的长篇剖析,为人们从一个崭新的视角理解乔氏这部作品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启迪。
还有大量著述从形式、艺术的角度讨论乔伊斯和《尤利西斯》。例如,乔学者扎克·波温的《乔伊斯作品中的音乐暗示》(Musical Allusions in the Works of James Joyce,1974)和《勃鲁姆古老甜蜜的情歌》(Bloom's Old Sweet Song,1995)就是从音乐与文学的角度研究乔伊斯的经典之作。特别是后者,它不仅从《尤利西斯》等小说的情节、结构、人物、主题、文体等角度分析乔伊斯对音乐的运用,考稽作品中与音乐有关的暗示的源流,而且结合作品就音乐与现代主义、音乐与宗教仪式、音乐与喜剧等方面做了有力的理论阐发。乔伊斯的作品不仅暗含了文学与造型艺术的种种关系,而且引发了许多造型艺术家的兴趣,开启了他们的想像。有的艺术家借用乔伊斯的观念创作作品;有的艺术家受其小说中某一点的触动产生灵感而创作作品;有的艺术家为乔伊斯和他的作品做漫画和插图。2004年勃鲁姆日前后在都柏林举办的展览,以“艺术中的乔伊斯”为题,展出了 60多位国际知名艺术家的作品,其中有马蒂斯为《尤利西斯》所作的插图;有曼·雷为乔伊斯所作的画像;有凯奇为乔伊斯所作的音像作品;有约瑟夫·博伊斯从《尤利西斯》获得灵感所作的绘画与雕塑。在形式和风格上则是五花八门,有观念艺术,有装置艺术,有立体派,有抽象表现派;有用猪油和鸟食塑造的艺术家半身像;有表达乔氏观念和思想的电动百叶窗和流淌着白兰地和红葡萄酒汁的床。整个展览显示了乔伊斯对当代造型艺术的巨大影响。展览之后,作为艺术家的乔学者克丽斯塔-玛利亚·海伊丝(Christa-Maria Lerm Hayes)出版了《艺术中的乔伊斯》(Joyce in Art: Visual Art Inspired by James Joyce,2004),这部著作不仅收为这次展览的精品,而且对其做了理论的探索,成为从造型艺术研究乔伊斯的一部最新最有代表性的力作。(40)托马斯·波克达尔 (Thomas Burkdall)的《乔伊斯的电影和小说》 (Joycean Frames:Film and Fiction of James Joyce,2000)是从影视方面研究乔伊斯的一部代表性作品。此书从电影语言、电影理论、造型艺术、现代主义等多个层面切入乔氏作品,把乔伊斯和爱森斯坦等电影大师相提并论,对文学与影视研究均有借鉴意义。(41)
四、插曲:版本之争的丑闻
《尤利西斯》批评中一个不能不提的事件是关于这部作品的版本之争。应该说,《尤利西斯》的版本之争是其批评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事件。1984年德国乔学者汉斯·盖勃勒(Hans Gabler)在对《尤利西斯》的版本做了大量细致的研究之后,与另两位学者出版了一个新的“校勘本”,盖勃勒在前言中称这个本子订正了1922年原本以及后来的各种版本中大约5000多处错漏,包括文字与标点的错误以及漏排的文字和段落等,譬如第15章中,斯蒂芬看到他母亲幽灵的那一段文字原版及后来的版本就漏掉了。这个校勘本1984年由纽约的花环出版集团(Garland Publishing)出版,随即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学者们开始参考、出版社争相出版这个新的“校勘本”,然而在其问世后的翌年,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学者约翰·基德(John Kidd)就对盖勃勒这个“校勘本”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基德认为,盖勃勒在校勘中带领他的一些学生主要依赖电脑对不同的版本加以比较,而没有能够真正地以原稿为底本去校勘,这种德国学派的校勘法自身是有缺憾的。基德指出,盖勃勒的这个校勘本中大量的所谓“校订”都没有原稿的依据,不仅把原先不错的改错了,而且更多地引进了新错误。基德把盖勃勒对《尤利西斯》的这种校勘称作“丑闻”,他的批评引起了乔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并且引发了乔学者对乔伊斯留下的大量笔记和手稿研究的兴趣,从而把对乔伊斯版本学的研究导向发生学的研究。(42)例如,曾经与盖勃勒一起编辑“校勘本”的爱尔兰乔学者丹尼斯·罗斯与另一位乔学者约翰·奥汉龙就声称,从乔伊斯的一个笔记本的部分资料中发现了他创作《尤利西斯》的新证据,公布了乔伊斯最初构思勃鲁姆这个主要人物形象的某些思考,并提出《尤利西斯》是乔伊斯为《画像》精心设计的姊妹篇的观点。(43)罗斯后来还出版了一个所谓的“读者版”(A Reader's Edition)的《尤利西斯》,对其做了大量的删改,特别是增加了许多原先没有的标点符号。按照他自己的解释,他的目的是要把《尤利西斯》从“学术象牙塔中偷运出来”,使其真正回到“市场”和读者大众中,因此,他这个版本的《尤利西斯》是“人民的《尤利西斯》”,是普通读者的《尤利西斯》。这个“读者版”的《尤利西斯》问世后像盖勃勒的“校勘本”一样引出了激烈的争论。(44)
事实上,乔伊斯留下的大量笔记、手稿《尤利西斯》1922年的原版以及后来的种种版本中都存在着不少难以确定的因素,需要花大力气去研究,因此围绕上述两个版本的争论几乎成了一场混战,加上“乔伊斯遗产委员会”(James Joyce Estate)就版权等问题的介入,使问题变得更复杂起来。从总体上说,乔学界对盖勃勒的校勘本尽管存在不同的看法,但依然认为它对《尤利西斯》研究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而罗斯对《尤利西斯》的删改大多出自他自己的“创造”(小部分依据了盖勃勒的校勘),他的创造似乎较多地离开了乔伊斯的本意,因此,学界对他的这个本子在总体上似乎还不认可。但无论如何,有关这部作品与乔伊斯其他作品在版本学与发生学等问题上的争论将会进行下去。换句话说,关于《尤利西斯》等乔伊斯作品的版本学与发生学的研究,在21世纪的乔学与《尤利西斯》批评中必将依然是一个重要的领域。
乔伊斯和他的《尤利西斯》从20世纪20年代初出现在世界文坛的地平线上之后,对世界文学史产生的影响之大无法用语言描述,对他和他的《尤利西斯》等作品的批评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产业。在新世纪里,乔伊斯和《尤利西斯》等作品的影响无疑还将在这份批评产业的不断膨胀中进一步增大。
收稿日期:2006-05-08
注释:
①Richard Ellmann,James Joy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revised ed.1982,p.521.
②参见The Scandal of Ulysses,Sporting Times,No.34,转引自Robert H.Deming,James Joyce:The Critical Heritage I,Routledge,1970,pp.192-193。
③参见A New Ulysses,Evening News,8,April,1922,p.4,转引自Robert H.Deming,James Joyce:The Critical Heritage I,Routledge,1970,p.194。
④参见James Douglas,Beauty-and the Beast,Sunday Express,28 May 1922,p.5。
⑤参见Dublin Review September 1922,clxxi,pp.112-119一篇未署名的文章。
⑥参见Richard Ellmann,James Joy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p.528-530。
⑦参见Shane Leslie,Ulysses,Quarterly Review,October,1922,ccxxxviii,pp.219-234。
⑧例如,与《奥德赛》对应的结构、时间和人体器官与艺术类型在各章中的对应和象征、一天的故事、百科全书式的内涵、两个民族(以色列和爱尔兰)的史诗、内心独白(意识流)手法和不同文体的运用等都始终没有改变。参见Stuart Gil bert.The Letters of James Joyce I,pp.146-147;参见Richard Ellmann,James Joyce,1982,p.521。
⑨参见Frank Budgen,James Joyce and the Making of Ulyss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15-18,p.20;参见 Richard Ellmann,James Joy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Revised ed.1982,pp.335-436。
⑩参见Frank Budgen,James Joyce and the Making of Ulysses,p.519。
(11)参见Don Gifford,Ulysses Annotate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p.12。
(12)关于拉尔博这一讲演前后的情况,参见Richard Ellmann,James Joyce,1982,pp.520-523。
(13)参见Stuart Gilbert,James Joyce's Ulysses,Vintage Books,1952。
(14)Frank Budgen,James Joyce and the Making of Ulysses and Other Writings,Oxford University Pr.1972,p.xix.
(15)参见Weldon Thornton,Allusions in Ulysses:An Annotated List,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8,1982; Don Gilford & Robert J.Seidman,Ulysses Annotated:Notes for James Joyce's Ulyss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1988。
(16)Harry Blamires,New Bloomsday Book,Routledge,1996,p.xi.
(17)参见Ezra Pound,James Joyce and Pecuchet,转引自Robert H.Deming,James Joyce:The Critical Heritage I,Routledge,1970,pp.263-267。
(18)参见Edmund Wilson,Ulysses,New Republic,xxxi,No.396,5 July 1922,pp.164-166。
(19)参见T.S.Eliot,James Joyce:Two Decades of Criticism,Seon Givens ed.Vanguard,1948,1963,pp.198-202。
(20)参见Mary Colum,The Confessions of James Joyce,Freeman,v,No.123,19,July 1922,pp.450-452。
(21)参见Gilbert Seldes发表在1922年8月30日Nation第cxv期2982号上的评论,pp.211-212。
(22)Joseph Frank,The Widening Gyre:Crisis and Mastery in Modern Literature,Indiana University Press,p.10.
(23)Karen Lawrence,The Odyssey of Style in Ulyss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p.7.
(24)参见David Hayman,Ulysses:The Mechanics of Meaning,Prentice-Hall Inc.1970,p.70。
(25)参见Hugh Kenner,Ulysses,1980,revise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7,"Arranger"一章。
(26)参见Bernard Benstock,Critical Essays on James Joyce's Ulysses,1989; Clive Hart & David Hayman,James Joyce's Ulysses:Critical Essays,1974。
(27)参见Brivic Sheldon,Joyce Between Freud and Jung,National University Publications,1980,pp.168-182。
(28)参见Richard Brown,James Joyce and Sexual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29)参见Derek Attridge(ed),James Joyce's Ulyss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96,86。
(30)这三本小册子是:弗洛伊德的《达·芬奇的童年记忆》、荣格的《父亲在个人命运中的意义》和琼斯的《哈姆雷特问题与俄狄浦斯情结》。
(31)关于乔伊斯对心理分析的不信任和反感,参见Richard Ellmann,James Joy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393, 436,466,472,510。
(32)这是乔伊斯对玛丽·考勒姆说的,批评家们熟知乔伊斯对女性的这一观点。参见Richard Ellmann,James Joyce,p. 529。
(33)参见Bonnie Kime Scott,Joyce and Feminism,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4,pp.1-8,120-132。
(34)Suzette Henke & Elaine Unkeless,Women in Joyce,University of Llinois Press,1982,pp.xi-xii,215-216.
(35)Thomas F.Staley & Bernard Benstock(ed),Approches to Ulysses:Ten Essays,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70, pp.103-136.
(36)Ibid.pp.137-155.
(37)Suzette Henke & Elaine Unkeless,Women in Joyce,University of Ullinois Press,1982,pp.150-168.
(38)Heather Cook Callow,Marion of the Bountiful Bosoms:Molly Bloom and the Nightmare of History,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36,Winter,1990,pp.464-476.
(39)Jenifer Wicke,Who's She When She's at Home? Molly Bloom and the Work of Consumption,JJQ 28.4,Summer 1991, pp.749-764.
(40)参见Christa-Maria Lerm Hayes,Joyce in Art:Visual Art Inspired by James Joyce.Lilliput Press,2004。
(41)参见Thomas Burkdall,Joycean Frames:Film and Fiction of James Joyce.Routledge,2000。
(42)1978年,花环出版社出版了250套63大卷《乔伊斯档案》(James Joyce Archive),后来,《乔伊斯季刊》(James Joyce Quarterly)又连载了各卷原本没有引出的卷号与名字,这样就为乔伊斯创作发生学研究进一步提供了可能。
(43)参见Danis Rose and John O'Hanlon,The Lost Notebook:New Evidence of the Genesis of Ulysses,Split Pee Smythe, 1989。
(44)参见基德与罗斯在《纽约书刊评论》上论战的文章,New York Review of Books,Vol.44,No.14,Vol.45 No.1, 1997-1998。
标签:尤利西斯论文; 乔伊斯论文; ulysses论文; 文学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读书论文; 奥德赛论文; 象征手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