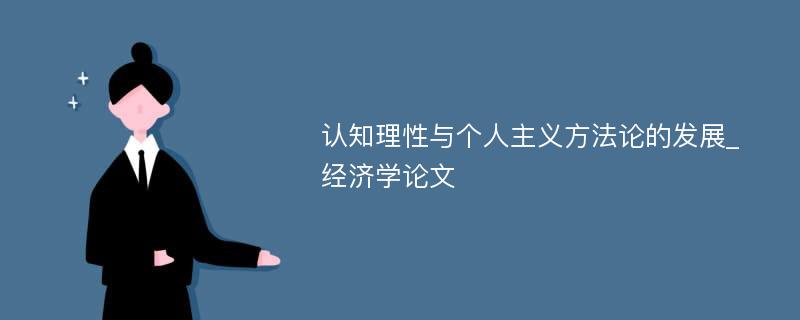
认知理性与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认知论文,理性论文,个体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EL Classification:A110,B250,D700
一、引言
经济学长期存在两种研究传统:均衡分析和演化分析。普遍认为,这两种传统各自的解释目标、方法论、基本假设、核心概念和解释逻辑等都存在根本性的差异,是两个不可通约的分析范式,即一种范式中的概念、描述、方法、意义在另一种范式中往往是失真、错位甚至丢失的。通俗地讲,一旦我们谈及均衡分析就不存在演化,反之亦然。一个形象的描述是,演化理论是研究尘埃如何落定,而均衡理论则是研究尘埃落定后的世界。但是,在复杂世界中,并不存在所谓泾渭分明的演化世界和均衡世界。事实上,尘埃永远都是不可能落定的,落定只是局中人的一种知识猜测。在理论上,这种两分法的研究传统难以避免地会产生诸多对立的学术命题。例如,制度变迁是有主体性还是无主体性?个体行为是有意识的理性最大化还是无意识的规则遵循?是个体主义方法论还是群体(集体)主义方法论?是目的论解释还是功能(或结构)论解释?是运用物理(机械)类比还是生物(有机)类比?是强调局中人对其所处互动场景的“知”还是“无知”?均衡理论的答案是主体性、理性最大化、个体主义、目的论解释、机械类比,而演化理论则给出相反的答案。
想要深入解答上述看似对立和矛盾的命题,经济学就不能再局限于原先“均衡—演化”对立的两分法传统。这需要均衡理论和演化理论某种程度的交流和互馈,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无涉、对立和不可通约。从科学发展史看,许多科学的进步恰恰是因为一些看起来不同、甚至对立的理论范式被证明在某种意义上是一致的,或者某种理论是另一种更一般性理论的特例(豪斯曼,2007)。
长期以来,一些杰出的经济学家都自觉地思考这种范式调和。我们既能够在马歇尔的均衡理论中挖掘出大量的演化思想①(马歇尔,2005),也能够在熊彼特的演化著作中发现其对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的信奉②(Hodgson,1993)。而当前经济学理论的许多前沿进展也是来自均衡理论和演化理论的调和与相互借鉴。例如,博弈论的一个重要进展就是放弃原有共同模型(common model)或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的假设,对每个行动者赋予一个依赖其历史经验的“主观认知”模型,弱化了个体理性假设,从而增加更多的演化信息,从原先的均衡行为分析转向趋向均衡行为的分析(Binmore,2001;青木昌彦,2001; Varoufakis and Hargreaves-Heap,2004; Schmidt,2006;丁利,2006)。类似地,演化理论也积极吸收均衡理论的思想。演化博弈和学习理论在演化经济学中广泛流行则体现了演化思想与均衡思想的交流与相互借鉴(Fudenberg and Levine,1998;弗罗门,2003; Brenner,2006)。近些年来,以Herbert Gintis和Samuel Bowles等为代表的桑塔菲学派尝试从跨学科的视角寻找人类行为分析的统一起点,将演化行为(或自动过程)和建构行为(或受控过程)置于统一的研究框架中(Gintis,2000,2007; Bowles and Gintis,2004; Fehr and Fischacher,2003)。
因此,不同范式间的比较和交流是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发展的重要源泉。两分法的学术传统已经严重束缚了经济学的理论发展。经济学不能再仅仅将演化理论和均衡理论视为绝对对立或完全不可通约,而是应该谨慎设定一些调和或交流的条件和场景,尝试建立两者的局部可交流或可转换的理论平台,促使两者相互吸收,从而丰富和深化各自的理论范式。当然,一个更为乐观的前景是能够建立一个契合演化理论和均衡理论的更为一般化的理论范式。
本文延续这种学术思潮,从范式调和的思路出发,探究经济学最为基础的“理性”命题,通过深入辨析建构理性和演化理性两种对立的理性范式,结合各种有关个体理性的最新研究,阐释一个更具有一般性的理性概念,进而为许多看似冲突的理论提供一个更为一般性的研究框架,增加各种理论的交流与互馈。
二、建构理性和演化理性辨析
(一)理性的两分法:建构理性和演化理性
社会科学对于理性做了许多两分法的归纳(Hamlin,2003)。例如,韦伯区分了“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和“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韦伯,2004);哈贝马斯区分了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和“交流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Boundon,1998);西蒙区分了“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和“过程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Simon,1978,1986)。这些分类都基于社会科学家对主客关系和主体间性的辨析和认识,为准确理解人类理性的内涵提供了重要见解。
在哈耶克(1967,1969,1979,1987)的启发下,Vernon Smith(2003)重新区分了两类理性:建构理性(constructivist rationality)和演化理性(ecological rationality)。两类都承认理性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它们对于理性内涵和实质的理解存在根本性的差异。
建构理性认为人类的理性能够创造和理解所有文明成果,因而,诸如道德、宗教、法律、语言、文字、货币和市场等一切的社会制度都源于人类有意识的发明和设计,都是人类根据理性原则精心设计的产物(哈耶克,1967)。因此,建构理性是一种唯理主义,认为个体理性推理是所有知识来源的基础,理性是超越任何经验知识的先验存在,所有的知识都可以借助个体的理性推理而演绎出来。在建构理性主义者看来,人类只应当相信那种能够通过理性被证明的东西,而所谓非理性或未被理性充分理解的事物要么在理性的重新检验下获得存在的合法性,要么就被抑制和铲除。应该说,作为启蒙运动的重要哲学思潮,建构理性将人类的理性推至世界本体的高度,大大强化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从而将决定人类社会命运的权利从神的世界拉回到人的世界。这无疑大大增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信心,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能动性。
演化理性认为,人类的理性不是先验存在的,而是在漫长的生物和文化演化中演进出来,它不是孤立或超越所有历史文化背景的,而是内嵌于各种习俗、惯例、法律、制度、语言、历史等文化制度中的(哈耶克,1979; Smith,2003)。不同的文化制度将型构或演化出不同的理性内涵,理性本身是内嵌于一个更为宏大的演化过程中,并且也和其它知识共同演化。因而,理性并不具备构成其它知识来源的优先权。一旦意识到人类理性的这种局限和困境,我们便不能像建构理性主义者那样将人类所有的难题都寄希望于个体理性,我们不能抛弃所有未被理性证明或理性不及的传统,更不能武断地依赖理性去建构未来。诸如道德、语言、法律和市场等社会制度也就不是由人类理性预先设计的,而是由人类在长期的社会互动过程中演化而来的。因此,演化理性弱化了个体理性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转向对个体间社会互动过程的重视。
实际上,这两种理性观长期存在于社会科学研究中,并构成研究者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两种主要方法论。在经济学中,信奉理性选择的新古典经济学则是建构理性主义的典范,而信奉自然选择的演化经济学则是演化理性主义的典范。前者包括一般均衡理论、博弈论、信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增长理论等所有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后者则涵盖了德国历史学派、老制度学派、新熊彼特主义、奥地利学派等非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畴。长期以来,新古典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的紧张关系主要源自各自坚持不同的理性观。
(二)传统经济学的简化:完全建构和完全演化
可以用一个连续的坐标轴来描述理性的特征。轴上有两个极端点,其中一端是完全的建构,另一端则是完全的演化。前者具有高度的目的性和主体性,个体行为是有意识的目标最大化,后者则是完全的功能性和无主体性,个体行为是毫无意识的规则遵循。长期以来,传统经济学中所谈的建构理性和演化理性通常都是指完全的建构和完全的演化,即个体要么具有无限的意识和目的,要么就是毫无意识和目的。通俗地说,前者是完全设计,后者则是完全无为。应该说,这两种理性观都是理论上的简化和抽象,并且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均衡理论和演化理论各自独立发展。但是,这样的理性假设却使得两种理论都远离现实,只能揭示某些特殊的现象。而且,这种完全对立的理性观也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会导致均衡理论和演化理论完全对立;相反,它却促使均衡理论和演化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的趋同。
基于完全的建构理性,传统均衡理论将理性赋予无所不能的个体,所有的选择都是由个体理性获得。即便是在多人不完全(incomplete)信息博弈中,通过海萨尼程序③(Harsanyi procedure)都能转化为不完美(imperfect)的完全信息博弈(Montetand Serra,2003)。因此,严格地讲,在经典博弈论中,所有的非合作博弈都是完全信息的博弈。这意味着博弈局中人之间共享一个心智模型,并且局中人和研究者(模型构造者)也共享一个心智模型,经典博弈是一个单一心智的模型。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博弈可以被认为是一个人的博弈,即无论是研究者还是局中人,都能够通过理性的算计而在事前算出博弈的解。传统均衡理论实际上是将所有的社会经济难题交给一个建构理性主义者来计算和求解,而且由于这个建构理性主义者无所不知,它实际上是一个神。通过将理性赋予个体,传统均衡理论想证明人类能够控制自己的命运,然而,由于不对理性做任何实质上的限制,它实际上又将人视为神。在这个意义上,传统均衡理论不是对现实世界中人的描述。
相反,许多传统演化理论实际上是将理性赋予超越个体的结构或系统,所有的制度都不是源自个体选择,而是源自超越个体的自然选择。由于将个体行为视为完全无意识的规则遵循,个体不具有任何的认知能力,而是类似于生物学中的基因,人类社会演化也类似于生物演化。人类社会演化被降格为与所有普通生物演化一样,支配社会演化的不是人的认知或智慧,而是自然法则。而且,由于相信自然法则是一种“优胜劣汰”的程序,人类社会总会朝着一种进步的方向演进,人类社会的所有难题都能在这种程序中得到解决。这实际上是给自然选择赋予无限的力量和理性,也是将自然选择等同于无所不能的神。
无论是基于完全演化理性的演化理论,还是基于完全建构理性的均衡理论,都不是对现实世界的描述。前者信奉“自然为人立法”,后者信奉“人为自然(或社会)立法”。由于没有对自然选择和个人选择的力量做任何限制,这两种理论在本质是相通的,即都信奉一种超越经验世界的理性,只不过前者将理性诉诸于无所不能的自然选择,后者则将理性诉诸于无所不能的个体选择。而实际上,这两种理论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即自然选择的结果可以通过个体理性选择模型获得,而个体选择的结果也可以通过自然选择的演化模型获得。例如,复制者动态模型中的类型频数分布可以被视为个体选择的混合策略,反之亦然。
类似地,Alchian(1950)著名的“赛车手”的例子证明了均衡理论和演化理论的相似性。Friedman(1953)强调,自然选择(或市场选择)将导致“只有理性最大者才能生存”,因此,可以假设个体“好像”(as if)是理性最大化者。Becker(1976)认为,无论个体是否为理性最大化者,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需求曲线总是向下倾斜。这些观点实际上都将自然选择等同于个体理性选择,信奉一种先验的凌驾于人类的理性。因此,完全建构理性和完全演化理性会导致均衡理论和演化理论的趋同。正如阿尔钦、弗里德曼和贝克尔等宣称:他们是新古典演化主义。
(三)拓展个体理性假设的必要性
正如上文所述,所谓的完全建构和完全演化都是一种极端假设,围绕这两种假设而构建的均衡理论和演化理论本质上是相通的,并且能够相互转换,它们都不是对于现实世界中人的描述。当然,任何理论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抽象,而且,正如Friedman(1953)认为的,理论的有效性依赖于其预测结果的准确性,与理论基本假设的真实性无关。这意味着,即便理论对于个体的假设是不真实的,只要该理论所推导出的预测或结果与现实一致,理论就有效。因此,尽管完全建构理性的个体假设是不真实的,新古典理论在一些领域中却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
但是,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发展,许多经济现象系统性地背离了新古典模型的预测。例如,“偏好逆转”(preference reversals)、“锚固效应”(anchor effect)、“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现状偏见”(status quo bias)和“镜像效应”(reflection effect)等(Kahneman & Tversky,1979)。Simon(1986)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在许多领域中的成功解释和预测实际上是不依赖于“理性最大化”的个体行为假设,而是依赖于许多有关个体所处环境的辅助假设(例如,有效的市场体系、法律体系和产权体系等)。在西蒙看来,这些辅助假设恰恰表明了个体决策受制于决策的过程、程序或背景,因此,过程理性或有限理性能够更好地解释一些经济现象(Simon,1991)。
同样地,一些现代演化经济学家也明确拒绝将社会经济系统演化简单类比于生物演化(Foster,1997; Witt,1997)。尽管Hodgson(2002)认为“自然选择理论能够为一切开放系统的演化提供一般性的解释框架”,但他依旧强调“必须将自组织等复杂系统理论内嵌于自然选择理论中,才能更加准确地解释社会经济系统的复杂性”。何梦笔(Herrmann-Pillath)(2004)明确指出,生物演化不存在认知主体,只是由遗传物质储存信息进行,而社会经济系统演化存在认知主体,是认知主体的知识积累过程。因此,个体不是基于完全演化理性或毫无能动性的,心智或认知是个体行为的重要特征,经济学必须为个体心智留有余地。
因此,经济学不能再信奉弗里德曼有关个体理性假设的“工具主义”辩护,仅仅将个体理性假设视为理论构造的一个逻辑环节,而不探讨理性假设自身的本体属性和经验内涵。事实证明,这种对个体理性假设有效性的忽视,已经严重阻碍了经济学对现实的解释力。无论是完全建构理性,还是完全演化理性,都是人类理性的特殊特征,它们都很难构成经济学理论的一般性基础假设。经济学理论的发展首先必须拓展现有流行的个体理性假设(包括完全建构和完全演化),深入挖掘个体理性的实质内涵和外延,在一个更具有一般性和有效性的理性假设下建构其理论体系。一旦拓展了个体理性假设,许多原先被认为是相互冲突的理论则可能被证明是兼容和互补的。
三、理性的认知特征:来自行为经济学、文化演化理论和脑神经科学的启示
近年来,借鉴认知科学中有关人类行为的研究,已经成为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流行趋势。产生了诸如行为经济学、神经元经济学、心智经济学、语言经济学和跨学科综合经济学等基于认知科学的新经济理论。尽管这些新兴的理论从各自不同视角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但是,它们都毫无例外地反对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并且一致强调认知因素对个体理性的影响,主张从个体的认知过程来理解个体行为。限于篇幅,本文重点探讨三个研究领域对理性认知特征的启示,即行为经济学、文化演化理论和脑神经科学,并且阐释各自领域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它们也是推动现代经济学理论发展最为重要和典型的三股力量,分别体现了“个体心理”、“社会文化演化”和“生物演化”等三个认知维度对个体经济行为的系统性影响。当然,这三个领域也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是相互吸收和相互渗透的,共同聚焦于人类行为的分析。
(一)行为经济学的启示
行为经济学主要运用心理学的知识来阐释认知心理对个体行为决策的系统性影响,它认为个体的行为决策在许多场景中都不遵循新古典经济学的期望效用法则,即消除性(cancellation)、传递性(transitivity)、占优性(dominance)和不变性(invariance)④(Kahneman & Tversky,1979)。而新古典经济学对于个体理性的定义便是遵循这些法则。这四个法则的重要性依次递增,其中,偏好的不可变性是最为核心的法则。Tversky和Kahneman(1986)认为,个体的偏好不是孤立不变的,而是受到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s)的影响,即受到有关决策问题的描述方式、决策背景和决策程序等的影响。这意味着个体偏好是从相关的决策框架或者背景中引致形成的,决策背景的变化可能导致偏好的变化。在他们看来,个体的行为决策可以分为前后两个过程:其一是形成框架(framing)和编辑(editing)过程。这也是决策背景的形成过程,类似于博弈规则和博弈结构,它规定了决策问题的描述方式、个体可能的行动集合、收益集合和环境的不确定性程度等。而决策背景的形成主要受到习俗、惯例、个体经历和预期等的影响;其二是评价过程,即对各种行动的前景进行评价,包括通过价值函数对于行动结果的价值进行评价,以及通过概率函数对状态发生的概率赋予权重。
Tversky和Kahneman(1991)指出,无论是价值函数还是概率函数,都受到个体认知心理状态的影响。价值函数具有以下三个主要特征:其一是“基点依赖”(reference dependence)。个体对某一行动结果的评价依赖于个体事前所处的基点(例如,要素禀赋、产权结构和社会结构等),基点变化会导致个体偏好的变化;其二是“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即相对于获益,个体对于损失赋予的效用权重较大。效用函数是一个S型的曲线,它在获益处是凹函数,而在损失处是凸函数,并且损失处的曲率比获益处的曲率陡;其三是“敏感度逐渐缩小”,即获益和损失的边际价值都随着数量的增加递减。因此,价值函数是一个不对称的S型曲线,高于基点处是凹函数,低于基点处是凸函数。而概率函数则具有“次确定性”(subcertainty)和“次比例性”(subproportionality)等特征。⑤
Kahneman(2003)认为,在某些情况下,⑥新古典的理性原则是适用的,但是,在更多的现实决策中,个体的行为是遵循上述的决策过程,而且,在复杂的世界中,许多规则会对决策背景、行动结果和场景概率的评价产生影响。因此,所谓的个体理性不应该是一个孤立和超越一切的逻辑体系,而必须是包含个体认知心理的稳定评价体系。
行为经济学所蕴含的理性观将个体理性从凌驾于万物的“神”的世界拉回到现实中“人”的世界,从而表明个体理性是有限的,它受到个体认知心理状态的影响,并且内生于各种决策背景中。
(二)文化演化理论的启示
近些年来,对“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的跨文化经验研究促使许多经济学家开始关注文化演化对个体行为的影响(Henrich,2000; Henrich et al,2001; Henrich,2003; Gintis,2007)。
在以往的研究中,“最后通牒博弈”实验通常被实验经济学家用来证实“现实中的个体行为系统违背了新古典的理性法则”。由于大多数实验的参与者是同一学校的学生,这些实验很难检测到文化对个体行为的影响。经济学家们通常认为,这些偏离新古典预测的行为与文化无关。他们更倾向于将这些行为解释为人类拥有先天的“公平”和“利他”偏好。
Henrich(2000)首先对秘鲁的土著Machiguenga和美国洛杉矶进行“最后通牒博弈”的跨文化研究。研究表明,在“最后通牒博弈”中,Machiguenga和洛杉矶的“建议者”提供给“接受者”的分配份额均值分别是26%和48%,最常见的分配份额分别是15%和50%;当分配份额低于20%时, Machiguenga的“接受者”几乎都接受,而洛杉矶的“接受者”则都拒绝。Henrich指出,在Machiguenga的文化背景中,“建议者”并不认为他们有义务为“接受者”提供相同比例的份额(即50%),同样地,“接受者”也不期待能够从“建议者”中获得同等比例的份额,因此,他们也不会因为不平等的分配份额而惩罚“建议者”。对于Machiguenga人而言,15%就是一个公平的分配比例。相反,在洛杉矶,50%才是一个公平的分配比例。在Henrich的推动下,由12名专家组成的团队在五大洲的12个国家的15个小规模社会中进行“最后通牒博弈”实验(Henrich et al.,2001)。研究数据表明,各个社会的博弈行为存在显著的差异。例如,分配份额均值处于26%和58%之间,常见的分配份额处于15%和63%之间。计量分析表明文化的差异能够解释68%行为的差异。这些经验研究都强调,文化对于个体的某些偏好(例如,公平和利他)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
由于人类拥有较强的社会学习能力,较之于其它物种,文化在人类社会中能够更加容易地得到传承和演化,它对个体行为特征的生成产生重要的影响,甚至会通过影响个体的适应度进而影响基因的演化。一些经济学家尝试通过基因与文化的协同演化来解释个体利他偏好的生成和演化,希望在更加基础的理论层面上阐释人类社会的各种亲社会性行为(Bowles et al,2003; Henrich,2003)。
生物学群体选择理论认为,只要群体间的差异足够大,而群体内的差异足够小,群体选择力量就会大于个体选择力量,从而导致那些不利于个体却有利于群体的利他偏好获得演化优势(Wilson and Sober,1998; Whitman,2004)。但是,由于基因变异和迁徙等容易引起基因重组,在生物学模型中,利他偏好演化的条件实际上是相当苛刻的。Henrich(2003)认为,仅仅通过生物演化模型无法解释人类社会大量存在的各种利他行为,而是必须将文化演化过程考虑进去。一些诸如遵循者传递(conformist transmission)和声望偏见传递(prestige-biased transmission)和标准化遵循(normative conformity)等文化传递机制,能够降低群体内个体间的差异;同时,文化演化过程会产生多重稳定均衡,这能够避免因迁徙而影响群体间的差异程度。因此,通过重构个体的演化环境,文化演化能够促使那些有利于群体的特征获得演化优势,进而促使形成这些特征的基因获得演化优势,而后者又会强化前者的演化优势。因此,基因与文化的协同演化能够强化利他偏好的适应性。
Gintis(2003)指出,文化演化过程通常会产生规范内化(norm internalization)和亲社会性情感(prosocial emotions)。规范内化说明个体的某些行为已经被内化为个体的目的,而非达到目的的手段。个体采取该行为不是因为其结果能够给个体带来益处,而是因为该行动本身就具有某种价值。因此,这些行动不是基于工具理性,而是基于价值理性。亲社会性情感则意味着个体的效用函数包含着各种社会心理因素,它不仅仅是以自我福利为中心的,还包括对他人效用的关心。而具体的文化特征塑造了具体的规范内化和亲社会情感。
因此,从文化演化的视角看,个体理性是内嵌于文化过程中,受到个体的社会认知过程的影响,文化演化生成的各种规范和社会制度塑造了个体理性的某些实质内涵。
(三)脑神经科学的启示
近年来,脑神经科学研究发现,人类大脑是模块化的结构,某项具体的活动并不需要激活所有的脑系统,不同的大脑活动是通过不同的模块的脑循环(brain circuits)来进行;不同的被激活的脑循环能够产生不同的动机和不同的行为选择。因此,即使面对同一选择菜单,个体的偏好也可能不同(Camerer et al,2004,2005)。这种见解彻底挖掘了新古典经济学有关个体偏好稳定的假设。
人类大脑是长期生物演化的结果。在此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大脑演化出各种模块结构以便应对有机体内部机能和外部环境的各种变化。自然选择要求有机体必须有效地管理资源和能量,确保体内的动态平衡,这依赖于生物调节过程。通过生物调节过程,有机体的内部结构能够应对外在的环境变化,促使大脑演化(Martins,2008)。Damásio(1999)指出,所有复杂的生物调节过程都是利用简单的生物调节过程生成的。他区分了大脑中三个层次的生物调节过程。最为简单的生物调节过程是植物神经系统的协调过程,它包括新陈代谢过程、免疫系统反应和一些最简单的条件反射过程。最高层次的生物调节过程则是“情感”调节过程:当某些神经系统区域(例如,扁头体、扣带皮质、腹内侧前额叶皮质等)被刺激时,感觉皮质(sensory cortex)会触发情感反应。这些情感反应通过视丘下部、基础前脑、脑干等区域,引起肉体状态(bodily state)的变化。这些情感和肉体的变化都会记录在躯体感觉皮质中(somatic sensorial cortices),从而被永久性地保存下来。
Damásio还区分了两类情感:第一类是所有拥有完整神经结构的个体都拥有的基本情感(例如,害怕、生气、悲伤、高兴、惊奇和厌恶等),外界的刺激能够直接激活主管这些情感的脑区;第二类是更为高级的社会性情感(例如,同情、怜悯、尴尬、害羞、内疚和自豪等),它起源于第一类情感。除了依赖第一类情感所涉及的脑区外,它还依赖于另外一个脑区,即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区域。该区域的功能是对各种社会场景和目标进行分类。外界刺激必须先经过这个区域才能激活其它主管情感的脑区。因此,第一类情感是直接的生物调节,第二类情感是间接的生物调节。许多高级的认知活动都必须经过第二类间接的生物调节过程。
在此基础上,Damásio(1994,2003,2005)提出了著名的“躯体标记机制”(somatic marker mechanism),认为“情感”被躯体感觉皮质记录时会产生躯体标记,躯体标记会对“情感”进行评价并长期保留在躯体中,当遇到新场景时,躯体信号会指导有机体的行动。例如,有些产生负值情感的行动会被自动屏蔽。在Damásio看来,所有更为高级的理性算计过程实际上都事前受到躯体标记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发生在各个层次的神经系统中,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因此所谓的理性行为实际上是依赖于包括情感在内的各个层次的生物调节过程。
脑神经科学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人类较高层级的理性决策过程依赖于较低层级的生物调节过程。在大脑的演进过程中,“情感”引起的躯体标识机制比人类高级思维更早地在演化中形成,情感过程早于理性过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理性过程。高级的理性行为依赖于大脑各个层次的认知过程。这些认知过程有的是超越具体社会场景,有的则是依赖于具体的社会场景。
四、认知理性:一个更具有一般性的理性概念
如前文所述,经济学理论的许多新进展是,从认知科学的视角在不同层面上挖掘个体理性蕴含的认知内涵。一个显著的共识是,理性不应该是一套“生理无涉”、“心理无涉”和“文化无涉”的逻辑体系。即便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算计行为也是受到各种包括“个体情感”和“社会情感”等认知过程的影响。由于外在环境的复杂性和内在认知的有限性,个体理性通常处于完全建构和完全演化之间,是一种认知意义上的理性。“认知理性”是一个更具有一般性的理性概念,它涵盖了当前各种理性研究的主要特征。“认知理性”充分体现了当前经济学理论与认知科学结合的趋势。如果将个体行为建立在“认知理性”上,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假设就具有更多的经验基础,从而能够更加准确地描述个体的行为决策。“认知理性”还能够为许多看似冲突或者不相关的理论提供更为一般的研究框架,从而增加各种理论的交流与互馈。
(一)“认知理性”的内涵和外延
著名的社会学家Boudon(1998)最早提出“认知理性”的概念。但是,他仅仅从社会学的视角来解释,主要想尝试调和“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Boudon将“认知理性”定义为:个体X做出行动Z是因为他有足够的理由做出或相信行动Z,这些理由包括:(1)因为Z是达到C最好的途径;或者(2)因为X相信Z是达到C最好的途径,而且X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些足够的理由又包括:(2.1)Z是正确的;或者(2.2)Z是T产生的结果,而X有足够的理由相信T;或者(2.3)Z是好的,因为(2.3.1)Z值得所有人去做,或者因为(2.3.2)Z是由T产生的,因为(2.3.2.1)X有足够的理由相信T,因为……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Boudon所谓的“认知理性”实际上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简单组合。例如,定义(1)部分是“工具理性”,定义(2)部分是“价值理性”。他没有直接阐释“认知理性”的内涵,也没有论及“认知理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三者的理论关系。因此,Boudon的“认知理性”更像是一个同时贴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标签的名称。
本文的“认知理性”绝对不是一个标签式的概念。它是基于上述各种理论有关个体理性的经验研究,从认知科学的视角阐释个体理性的生成及其内涵。本文将“认知理性”的内涵描述为:拥有完整生物神经结构的个体(即正常人)通过生物调节过程、个体学习过程和社会学习过程等各种层次的认知过程,建立应对外界环境刺激的稳定认知模式,这种认知模式能够促使个体有效地处理各种有关内部机能和外部环境的能量、信息和知识,提高个体在各种演化环境中的适应性。这种认知模式就是认知理性,而由此认知模式形成的行为模式是“认知理性行为”。
简单地讲,“认知理性”是在认知有限性和信息有限性的双重约束下,由个体内在认知过程与外在环境互动生成的,具有演化适应性的稳定认知模式。其中,“认知约束”是一个重要的约束机制,也是主流经济学长期忽视的约束机制。个体各种认知模式的重要功能就是节约认知资源,提高个体处理各种能量、信息和知识的效率,从而确保个体内部机能和外部环境的动态平衡。人类长期演化生成的脑神经结构具有这种功能。除此之外,由个体的心理发展和社会文化演化形成的各种惯例、习俗、规范和制度也具有这种功能。因此,“认知理性”是一个外延比较丰富的理性概念,各种有效节约认知资源的行为模式都可能是一种认知意义上的理性。在某些简单的场景中(例如,行动集合、支付集合和信息集合都比较清晰),新古典的“工具理性”可能是有效节约认知资源的认知理性;而在一些复杂的场景中(例如,个体行动内嵌于各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中),遵循社会规范的“价值理性”,或者遵循拇指法则的“有限理性”则可能是有效节约认知资源的认知理性。
个体行动必须满足以下条件才符合“认知理性”:其一,个体必须拥有完整的生物神经结构,亦即个体是一个生理正常的人;其二,个体的行动必须具有稳定性和可重复性;其三,个体的行动必须能够节约某种认知资源;其四,个体的行动必须具有演化适应性。但是,“认知理性”并不要求个体的行动必须具有最大化的演化适应性。例如,在许多个体异质程度很大的环境中,个体的演化稳定行为是次优的。
(二)“认知理性”中的个体偏好、知识、约束和行为等特征
1.“认知理性”中的个体偏好特征
“认知理性”具有场景依赖性,即不同的场景(包括物理场景和社会场景)可能产生不同的认知模式,个体在不同场景中的行为模式可能会发生变化,从而导致个体选择偏好的变化。因此,在同一场景中个体偏好是稳定的,而在不同场景中个体偏好则可能发生变化。行为经济学和脑神经科学的大量研究揭示了这种偏好现象。如果偏好关系的形成高度依赖于选择环境,偏好没有独立性,选择环境的变化会自动促使偏好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无意识的,不会给个体造成任何逻辑混乱。如果偏好对选择环境的依赖程度较低,个体能够意识到偏好的变化,但在另一认知模式的支配下,个体仍然不会认为这种变化会有冲突。但是,如果两个场景因具有某种相似度而难以辨识,个体可能发生偏好冲突。个体可能搜寻另一个具有一般性的认知模式来解决这种冲突。如果不存在这种一般性的认知模式,个体只能通过各种认知过程(例如,个体试错和模仿)重新建立应对这种场景的偏好关系。
偏好的稳定性程度取决于个体认知模式。在某些由生物演化和文化演化形成的认知模式中,偏好可能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在某些由个体心理发展形成的认知模式中,个体偏好可能比较容易发生变化(例如,随着年龄和经历的增加,某些偏好会经常变化)。“认知理性”还具有多重动机,即偏好可能处于利己与利他的连续谱中。个体在不同的场景中可能采取不同的偏好类型。例如,文化演化形成的社会规范可能促使个体对群体内部成员的偏好是利他的,而对于群体外部成员的偏好是利己的。
因此,偏好可能是稳定和变化的,也可能是利己和利他的。具体的偏好特征取决于个体具体的认知模式。
2.“认知理性”中的个体知识
在“认知理性”中,个体是通过各种层级的认知过程来获取知识。不同的认知过程可能产生不同类型的知识。有些知识是由个体较为低级的生物调节过程获得,它对于所有人都是相似或相同的。例如,某些表示简单“情感”(害怕、生气、悲伤、高兴、惊奇和厌恶等)的表情。这些是由人类物种演化形成的基本共同知识,能够协调个体间一些比较简单的互动。个体还能够通过自我强化和自我试错等个体学习过程获取知识。这类知识包含着许多个体独有的、不为外人知晓的局部知识,通常具有较高的默会性。这种局部知识是个体间异质性的重要来源。个体还可以通过模仿、观察和文化传递等社会学习过程获取知识。这类知识包括许多由文化演化生成的各种社会行为规则,是文化群体的共同知识。这类共同知识有利于协调群体内个体间比较复杂的互动,是群体特征的重要标识,也是群体之间异质性的重要来源。当然,这三种认知过程不是完全独立的,有时是相互作用的。在许多情况下,个体学习过程与社会学习过程是交织一起的。许多共同或通用的知识通过个体自身的再学习过程,会形成个体新的局部或专用的知识。同样,随着个体局部知识的外溢,某些具有高适应性的局部知识也会逐渐成为共同知识。
3.“认知理性”中的个体约束
在“认知理性”中,个体除了受到如主流经济学说揭示的约束,例如,选择集、信息集、价格、时间和收入等约束,还受到“认知约束”。这些“认知约束”包括:有限计算能力、有限感知和记忆、有限注意力、有限意志、有限自控能力和有限自觉意识等(Simon,1987,1991; Salvatore,1999; Schandler,2006; Rubinstein,2007)。这些“认知约束”说明个体的认知资源也是一种稀缺的资源。个体的选择行为不仅仅会引起外在、显性的物质成本,还会引起内在、隐性的认知成本。在判断个体行为效率时,仅仅通过物质收益和成本是不够,还必须包含认知收益和成本。因此,当个体行为决策无法获得最优物质收益时,并不能被断定是非理性的,因为一旦考虑了“认知约束”,个体行为则可能是一种认知理性。
4.“认知理性”中的个体行为特征
在“认知理性”中,个体行为并不是独立和超越一切的逻辑推理,相反,它受到各种层级因素的影响,是内嵌于各种结构中的。这些结构包括宏观的社会文化结构和微观的脑神经结构,以及个体的认知心理结构。尽管个体行为受到这些结构的约束,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结构能够完全决定个体的行为。相反,个体能够通过认知过程与外界环境的持续互动,推动这些结构的演化。因此,个体既有能动性又受到结构性的约束。在个体行为分析中,“认知理性”并不排斥那些高于或低于个体层面的结构的存在,相反,它强调必须考虑到“认知约束”,并详细考察这些结构对个体行为的系统影响。
个体行为特征是多样的,它既可能是无意识的规则遵循,也可能是有意识的算计决策。行为的意识程度取决于认知过程的复杂程度,越复杂的认知过程消耗更多的认知资源,产生越复杂的行为模式。某些较为低级的生物调节过程会产生无意识的个体行为。例如,强化学习行为(Borgers and Sarin,1997)、参数化的自动学习行为(Arthur,1991)。比较复杂的一些认知过程会产生弱意识的个体行为。例如,许多基于传统惯例的学习行为(Brenner,1999,2006)。更加复杂的一些认知过程则会产生较强意识的个体行为。例如,随机信念学习(Brenner,2004)、贝叶斯理性学习(Jordan,1995)、神经网络学习(Heinemann,2000)和经历加权吸引学习(Camerer and Ho,1999)。
脑神经科学研究表明,所有较为高层级的认知模式都是依赖于较低层级的认知模式。个体的认知模式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特征。因此,个体行为模式也具有路径依赖特征。某些较为复杂的行为模式也是源自较为简单的行为模式。例如,通过增加参数的复杂性,简单的强化学习模型可以生成复杂的经历加权吸引学习模型(Brenner,2006)。
(三)“认知理性”对演化理性和建构理性的调和
如上所述,个体偏好既可能稳定也可能变化,个体行为既可能是无意识的规则遵循,也可能是有意识的算计决策。因此,“认知理性”既包含演化理性,也包含建构理性。演化理性和建构理性都是基于特定认知模式下的理性。当个体处于特定的认知模式中,即有关个体偏好、约束、收益、行动和信念等集合的知识都是个体不用耗费太多认知资源而能够知晓的,个体可能采取建构理性的行为,从而获取行动的最大化收益。反之,如果个体需要耗费较多认知资源才能获取上述相关知识,或者甚至对上述知识存在根本的“无知”,个体通常采取演化理性行为,遵循各种由生物和文化演化生成的规则系统。这些规则系统蕴藏着许多不为个体知晓却又具有演化适应性的知识。尤其是面对新环境时,个体起初通常会试探性地延用原先的社会规则。
就某一具体的场景而言,在初期,个体行为可能是演化理性,随着认知过程与外界环境的持续互动,许多由演化而来的默会、局部和未编码化的知识可能逐渐进化为显性、共同和编码化的知识,个体的认知模式也从简单趋向于复杂,个体行为逐渐从无意识转向有意识,理性逐渐从演化转变为建构。因此,随着知识的积累,认知理性也处于演化过程中。
五、认知理性的方法论辨析: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发展
如上所述,个体的认知理性受到各种层级的结构约束,例如,宏观的社会文化结构和微观的脑神经结构等。那么,“认知理性”的经济学方法论是什么?其基本分析单元是什么?是神经元、个体或者群体?这容易造成方法论上的困扰。如果将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单元建立在神经元上,那么“认知理性”是一种生物还原主义方法论,反之,如果是建立在群体上,“认知理性”则是一种群体或集体主义方法论。前者是一种基因决定论,后者是一种文化决定论。这两种方法论都受到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家的质疑和反对。他们认为,经济学的分析单元必须建立在个体行为上,因此,必须遵循个体主义方法论。
从其内涵可知,“认知理性”既不是基因决定论,也不是文化决定论。“认知理性”的基本分析单元也是个体行为,但是,它不排斥某些高于个体层级的整体现象(例如,社会结构),也不排斥某些低于个体层级的单元(例如,神经元或基因等)。个体行为既不是完全建构理性行为,也不是完全演化理性行为,而是一种认知理性行为。这种行为受到各种层级的认知过程的影响。这意味着无论是对神经元还是社会群体的分析,其目的都是为了阐述它们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因此,理论的基本分析单元或者分析起点是个体的认知理性行为,“认知理性”的方法论也是个体主义的,而且,这种方法论拓展了传统意义上的个体主义方法论。
(一)传统的个体主义方法论
在社会科学中,很少学科像经济学这样明确宣称信奉“个体主义方法论”。这个术语首先是由熊彼特提出来,经由米塞斯和哈耶克等人的发展,在上个世纪50年代后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进一步地,在波普尔及其学生Watkins的推动下,“个体主义方法论”引起了哲学领域的广泛讨论,并从经济学扩展到其它社会科学中(Hodgson,2007)。随后,在较长的时间里,社会科学领域掀起了“个体主义方法论”的热潮。
但是,长期以来,针对“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内涵和外延争议持续不断,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理解。在所有宣称遵循“个体主义方法”的阵营中,很多理论是相互冲突的。一些理论通常都宣称自身的方法论是“真个体主义”,并强烈批判对方的方法论是“伪个体主义”。例如,哈耶克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以及Vanberg对哈耶克的批判(Whitman,2004)。
1.建构理性下的个体主义方法论
这种方法论认为,个体是超越社会背景的独立存在体,所有社会现象都必须仅仅由个体的行动来解释,而不需要再附加其它社会制度因素。在此方法论中,每个个体都能够独立做出决策,别的个体只是他决策所依据的客观信息,不会改变他的内在偏好。个体间的差异都是一些可以度量和显示的外在特征,例如,策略集、信息集和支付集的差异。个体间不存在内在的本质差异,每个个体拥有相同无限的认知能力,采用相同的推理法则,都是只关心自身福利的经济人。个体间的互动关系仅仅是外在的经济利益关系,而且每个个体都知晓这些关系(例如,博弈结构和博弈规则)。通过理性的推理,每个个体都能够知晓个体间的互动结果。因此,只要定义好个体的策略集、信息集和支付集,所有的经济现象都能够由个体的理性行动来解释。
随着这种方法论在经济学中的成功,许多经济学家开始不满足于纯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将个体的策略集合扩展到许多非经济的行为中,尝试解释社会、政治、法律和文化等现象。这种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现象,促使“个体主义方法论”从纯粹的经济学领域进入了其它社会科学领域。在其它社会科学的运用中,个体依旧是凌驾于所有社会关系的独立存在体,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
2.演化理性下的个体主义方法论
哈耶克(1969)指出,如果建构理性的个体主义方法论是可行的,模型中的个体便能够直接推导出所有的由个体间互动形成的整体现象,亦即个体能够通过建构理性把握整体现象。这意味着模型的建立者能够掌握和建构社会整体知识。而这种自负恰恰是哈耶克(1987)所担心的。在他看来,个体主义方法论的首要功能就是拒绝这种对整体性知识的妄想。
因此,这种方法论认为,任何社会经济现象都不能仅仅由原子式的独立个体来解释,还必须包括个体间的互动关系(例如,制度)。这种互动关系是无法仅仅由个体的微观动机来解释的。因此,社会现象必须通过个体间的互动及其互动关系来解释。
(二)认知理性下的个体主义方法论
如果将上述第一种仅仅由个体行动解释的方法论称为完全的个体主义,那么,第二种还强调互动关系的方法论则可以被称为不完全的个体主义。基于认知理性,由于个体行为是内嵌于各种认知结构中的,所有的个体主义方法论都应该是不完全的。即使是基于建构理性的主流经济学,实际上也预设了特定的认知模式。例如,博弈论中除了假设个体是理性最大化者,还预设了博弈规则和博弈结构,而且假设所有参与者对这些知识的认知是相同的。
这种方法论主张不完全的个体主义。但是,较之于演化理性,它不仅强调那些由文化演化生成的各种社会互动关系或社会结构在解释社会经济现象中的作用,还强调各种由生物演化而来的脑神经结构和个体心理发展形成的心理认知结构在解释社会经济现象中的作用。因此,这种方法论承认各种高于或低于个体的结构的存在及其解释功能,但是,它反对直接从这些结构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相反,它认为,必须谨慎研究这些结构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并将这种内嵌于各种结构的个体行为作为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显然,这增加了理论的复杂性。在具体研究中,研究者必须对各种变量进行取舍,考察主要的影响因素。
基于认知理性,个体主义方法论并不具体限定个体的偏好特征和行为特征。个体的偏好既可以是利己的,也可以是利他的;个体行动既可以是无意识的规则遵循,也可以是有意识的算计决策。尽管各种经济理论对个体行为假设不同,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同属于个体主义方法论阵营。因此,哈耶克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实际上是本体论层面的,即对新古典个体本体属性的批判,如果纯粹从方法论角度上讲,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并非伪“个体主义”。在经济学中,许多方法论的争议通常源于本体论和方法论的混淆,将本体论的差异视为方法论的差异。“认知理性”从本体论的层面阐述个体的理性本质,为经济学提供较为一般性的本体假设。这既能减少许多理论间本体论的冲突,也能减少方法论的冲突。
由于某些具体行为模式受到特定社会场景的塑造,这种方法论强调经验研究的重要性。只有通过经验观测,经济学家才能够揭示这些行为特征,以及个体面临的认知约束和信息约束等。这意味着经济学家必须关注各种规则系统对个体偏好和行为的塑造,将理论研究置于更为广阔的学科背景中,将经验研究置于更为丰富的社会背景中,提高经济学的理论生命力和现实解释力。
六、结论及其对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启示
通过对个体理性假设的研究,本文得出如下一些结论:(1)理性既不是完全建构也不是完全演化的,经济学必须拓展个体理性假设;(2)经济学与认知科学的紧密结合是当前经济学理论发展的重要趋势,许多诸如行为经济学、文化演化理论和脑神经科学等理论都揭示了理性的认知特征;(3)“认知理性”是在认知有限性和信息有限性的双重约束下,由个体内在认知过程与外在环境互动生成的,具有演化适应性的稳定认知模式。它涵盖了当前各种理性研究的主要特征,充分体现了当前经济学理论与认知科学结合的趋势,是一个更具有一般性的理性概念,它也能够调和建构理性和演化理性的冲突。“认知理性”的个体偏好、知识、约束和行为特征具有多样性;(4)“认知理性”的理论基本分析单元是个体的认知理性行为,其方法论也是个体主义的,并且这种方法论拓展了传统观的个体主义方法论。
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转型过程中。这个演变过程的显著特征是,旧的社会形态尚未完全消失,而新的社会形态尚未完全明朗。经济主体处于传统与现代交织的认知模式中,其理性的内涵更加的丰富和多样。“认知理性”能够为研究中国经济现象提供合适的个体理性假设。它至少能够给中国经济学带来以下几点启示:(1)通过认知理性的视角,能够解释更多的中国经济现象。对于许多主流经济学无法解释的现象,我们不能简单视之为非理性,而是必须深入研究这些现象背后特有的各种社会制度及其对个体认知模式的影响,了解个体面临的具体认知约束和信息约束,从认知理性的视角来解释这些现象;(2)许多制度变革或创新不能沿用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假设,而是必须基于个体的认知理性假设,这样才能提高制度变迁的适应性;(3)中国经济学研究不能一味地照搬或遵循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对中国经济现象进行经验研究的同时,必须不断深化、提炼和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及其逻辑解释体系,从而能够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做出原创性的贡献。
注释:
①马歇尔指出,经济学家的麦加应该在经济生物学,但由于生物学概念比力学概念更加复杂,基础研究的书(即《经济学原理》)就必须更多地使用力学类比(马歇尔,2005)。
②霍奇逊(Hodgson,1993)指出,熊彼特一方面提出一个资本主义的演化理论,另一方面又始终信奉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他终身徘徊在这个矛盾之中。在这个意义上,熊彼特的演化思想是不彻底的,依旧保持着对均衡的眷念。
③所谓的海萨尼程序是指,通过引入自然对局中人类型的选择,而将原来不完全信息的博弈扩展为不完美的完全信息博弈(Montet和Serra,2003,pp.141-142)。
④“消除性”是指,不同行为如果在某一可能出现的场景中会产生相同结果,这个场景可以被消除或忽略;“传递性”是指偏好的可传递性,这是新古典理论最为基本的假设;“占优性”是指,如果一个选项在某一场景中优于另一选项,而在其它场景中至少和该选项一样好,那么这个选项便是占优选项,应该被选择。
⑤“次确定性”是指对较低的概率赋予较高的权重,而对于中和高概率赋予较低的权重,并且后者的效应比前者更加显著。例如,π(p)>p,但是π(p)+π(1-p)≤1;“次比例性”是指对于固定的概率r,π(pr)/π(p)<π(pqr)/π(pq)。
⑥例如,决策问题按照新古典的标准方式进行描述,或者概率和结果的评价是线性关系的。
标签:经济学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行为经济学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认知过程论文; 特征选择论文; 市场均衡论文; 自然选择论文; 博弈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