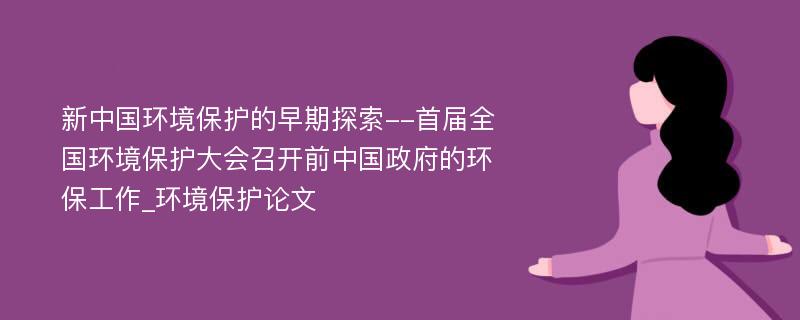
新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早期探索——第一次全国环保会议前中国政府的环保努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政府论文,新中国论文,环境保护论文,努力论文,事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X3;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10)04-0040-08
1973年8月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现代环境保护事业开始起步。有关新中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回溯性研究几乎都以这次会议为起点,对于此前的环保工作,由于资料缺失等原因,却极少论及或语焉不详。但实际上,如果没有此前中国政府在环保上所做的长期努力,现代环保事业是难以在1973年顺利起步的。
新中国环境保护的萌芽(1949~1957年)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工业化的展开和经济的发展,生态环境问题开始出现,但由于国民经济初入正轨,国家工业化刚刚起步,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只是在局部地区出现且程度较轻,因而环保意识尚未觉醒,政府并未明确提出环境保护的概念并制订相应的环保政策。不过,在经济建设过程中,相关部门曾经出台了一些具有环保功能的文件和法规,部分城市也采取了一些保护环境的举措。
在工业污染防治上,为了应对城市新建工业项目在规划、选址、设计、“三废”(废水、废气、废渣)处理等方面涉及的卫生问题,卫生部于1953年成立卫生监督室,在苏联顾问指导下,开展预防性卫生监督工作。这是中央政府成立的第一个环保性机构。因卫生监督工作中需要统一的卫生标准和法规作为依据,1956年卫生部、国家建委联合颁发了《工业企业设计暂行卫生标准》及《关于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中有关卫生监督工作的联合指示》。这两个文件对预防污染、保证饮水安全及城市合理规划发挥了积极的指导作用。1957年国务院第三、第四办公室发出《注意处理工矿企业排出有毒废水、废气问题的通知》,明确提出要注意防治工业污染。该通知已是一个实质意义上的环保文件。为了能更好地防治工业污染,1956年政府确立了“综合利用工业废物”的方针。该方针成为此后十余年间治理工业污染所遵循的基本方针。在上述方针政策的指导下,一些工业企业尤其是集中建设的156项大中型项目,采取了某些防治措施,如安装污水净化处理和消烟除尘设备等,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污染危害。在城市建设中,则比较注意合理布局,把污染企业尽量建在远离城市的地区,并在市区和工业区之间建有林木隔离带,以避免工业“三废”危害市区居民。譬如,1954年武汉制订的《武汉城市总体规划》已考虑到了城市的生态环境问题。“一五”期间开始建设的武汉钢铁公司和武汉肉联厂,厂址均选在了距市中心20公里以外的长江武汉段下游两岸。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锅炉厂、武汉汽轮发动机厂等大型机械工业企业,也分别建在近郊的工业区内。武钢的规划布局则注意到工业“三废”污染问题,将后勤生活区规划在厂区5公里以外,中间设计有绿化隔离带。[1]
此间,为了掌握环境污染的一手数据,少数城市的卫生部门曾经开展了污染源及污染状况调查。譬如,重庆市先后于1954年、1955年和1956年对长江、嘉陵江重庆段的水质基本状况、污染与自净能力,工业“三废”对两江的污染情况,以及粉尘和有毒气体、生产性噪音等进行过调查测定。① 此可谓中国环境状况调查的先声。
在环境管理上,1957年7月,南京市人民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新建厂矿在设计时应认真考虑处理废水、废气的措施,同时将此类设计图纸及有关资料送交卫生部门研究,只可惜其在实践中基本未予执行。[2]环境监测是适时了解环境状况、防控环境污染的重要手段。20世纪50年代,上海、淄博等城市开始开展环境监测工作。虽然方法不一、精度不高,[3]但正是在此基础上,我国的环境监测工作开始起步。
在城市环境整治上,一些中心城市在疏浚治理城市河流、外迁危害性较大的企业以及防治城市环境污染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1949~1952年间,北京市共修复旧下水道220余公里,清除旧沟淤泥16万立方米。1950年9月,北京市政府决定将易燃易爆工厂一律迁往南郊及其他地区。1951年,北京市政府又决定将永定门附近的木材厂及城区的皮革厂等迁往南郊,将易燃易爆及有碍卫生的工业企业集中在南郊沙子口、大红门、铁匠营一带。[4]福州市于1949~1953年间组织民工疏浚22条河道,共挖出污泥36万立方米,同时清挖了572条沟渠。[5]1952年兴起的爱国卫生运动对城市环境整治工作起到了促进作用。在城市环境污染防治方面,除了注意防治废水、废气污染外,一些城市曾专门为防治噪声污染出台了一些文件和法规。如1953年10月,北京市政府发布《关于减少城市嘈杂现象的通告》;1954年7月,市政府再次发出通告,要求继续减少城市噪声扰民;1955年5月,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减少城市嘈杂声音的规定》。[4](p.255)南京市则于1956年5月颁布了《关于减少城市嘈杂声音的规定》。[2](p.218)1956年6月,齐齐哈尔市颁布了《关于减少城市噪音的通告》。[6]
在保护资源上,1951年2月,林垦部出台《保护森林暂行条例(草案)》;1956年、1957年,国务院发布《矿产资源保护试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暂行纲要》;1956年中国建立了第一个综合性自然保护区——鼎湖山自然保护区,有关自然资源和生态保护的法规与制度已初具规模。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在植树造林和森林护育上取得了显著成就。1950~1957年间共造林23596.4万亩;1950~1952年间完成封山育林6210万亩;1956年一年封山育林即达5835多万亩。[7]这对保护生态环境、防止水土流失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国家工业化之初,新中国政府即能关注到环境污染问题并采取若干应对措施,很大程度上是学习苏联模式的结果。如1956年颁布的《工业企业设计暂行卫生标准》,即是模仿苏联1954年颁布的《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制订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环保工作正是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起步的,直到1957年之后才开始摆脱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综上,在这个阶段,中国政府在环境保护上做了很多的努力,尽管成效非常有限,如政府尚未形成环境保护理念,环保举措尤其是环境污染防治措施多是在“环境卫生”理念的指导下实施的,推行环保举措的机构也主要是卫生部门,但新中国的环保工作在此期间已开始萌芽发展。
在曲折中艰难发展的环保工作(1958~1969年)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在短期内造成巨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前期的零星环保举措也基本废弛,从而导致环境问题迅速凸显。“大跃进”运动结束后,政府曾经采取了一些环保举措,但随后因“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而名存实亡,环保事业的发展再次跌入低谷。本阶段环保工作的发展呈现出“中间高,两头低”的基本态势。
(一)“大跃进”运动造成的严重环境问题与中央政府的环保努力
“大跃进”时期,生态环境遭遇了建国以来第一次集中的污染与破坏。在工业领域,仅1958年下半年,全国即动员了数千万农民大炼钢铁、大办“五小工业”,建成了简陋的炼铁、炼钢炉60多万个,小炉窑59000多个,小电站4000多个,小水泥厂9000多个,农具修造厂80000多个。工业企业由1957年的17万个猛增到1959年的60多万个。[8]技术落后、污染密集的小企业数量迅速增加,使工业结构呈现出污染密集的重化工化趋势。与此同时,已有的环境保护规章制度受到批判和否定。在管理混乱、污染控制措施缺位的情势下,工业“三废”放任自流,环境污染迅速加剧。在农业领域,推行片面的“以粮为纲”政策,在急于求成思想和“向自然界开战”口号的激励下,全国范围内出现毁林、弃牧、填湖开荒种粮现象,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使环境问题迅速凸显。
针对出现的环境问题,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央政府曾经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以防治工业污染,制止乱砍滥伐,恢复林业经济的正常秩序。在恢复前期污染防治举措的同时,大力推行“综合利用工业废物”方针。1960年3月,中共中央在批转建筑工程部党委《关于工业废水危害情况和加强处理利用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工业废水处理利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必须积极进行工业废水的处理利用,新建企业都应将废水的处理利用作为生产工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设计和建设中加以保证。[9]与此同时,还提出了“三同时”思想。随后,工业部门提出了“变废为宝”的口号。1963年全国掀起了“三废”综合利用热潮,15个城市被确立为工业废水处理和利用实验研究基地。1956年颁布的《工业企业设计暂行卫生标准》被修订为《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并于1963年颁布实施。其间,对一些盲目建立的工业企业实行了关、停、并、转,混乱的工业布局得到了一定纠正。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中央政府一直没有忽视工业污染防治。1966年1月13日,国家经委拟定的《一九六六年工业交通企业支援农业的十项措施》再次强调,有害农业的污水、废气和废渣都要在1966年内抓紧进行处理,变有害为有利,变无用为有用。[10]此外,1960年初,国务院还批准颁发了《放射性工作卫生防护暂行规定》,对预防放射性污染作出了相关规定。在恢复林业经济正常秩序方面,1960~1963年间,政府先后下发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关于确定林权、保护山林和发展林业的若干政策规定(试行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和《森林保护条例》等相关文件和法规。1964年,林业部又提出了“以营林为基础,采育结合,造管并举,综合利用,多种经营”的林业发展方针。上述举措有力地促进了林业经济秩序的恢复,对弥补因滥伐林木导致的生态破坏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在自然资源和生态保护上,1962年和1965年,国务院分别发出《关于积极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指示》和《矿产资源保护条例》,并建立了一批综合性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和生态保护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
(二)1958~1969年间地方政府的环保努力
这一时期,地方政府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在环境保护尤其是工业污染防治上扮演了更为积极的角色,成为本阶段环保行政的重要特征。
1.一些地方政府成立了环保机构 成立环保机构是进行环境保护的重要组织保证。北京、天津、上海、黑龙江和新疆等少数省级行政单位,以及鞍山、武汉、哈尔滨、南京、南昌、齐齐哈尔、保定、青岛、吉林市等工业比较集中的城市,成立了“三废”治理利用办公室等环保机构。这些环保机构绝大部分成立于“大跃进”运动结束后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与卫生监督机构相比,这些机构环保内涵更加明确,与现代环保机构更为相像,是环保组织机构从“环境卫生”型向“环境保护”型转变的重要过渡形式。
2.出台防治污染的文件和法规 制订具有针对性的环保法规和文件是开展环境保护的重要制度保证。在防治工业污染过程中,一些省市因地制宜出台了相关文件和法规。如哈尔滨市1960~1965年间,先后颁布了8项强调管理工业“三废”、生活污水的文件和法规。[11]这些文件和法规从内容上来看,比中央颁布的文件更详尽、具体,也更有地区针对性;从颁布时间来看,也同样集中于国民经济的调整时期。
3.开展环境状况调查 开展环境状况调查是对环境状况作出客观评估并制定环保措施的基本依据。这一时期,中央基本没有直接组织环境状况调查,但北京、青海、黑龙江、重庆、鞍山、保定、武汉、佛山、吉林市、南海县等地,为了掌握本地环境污染状况,开展了以“三废”污染调查为主要内容的环境状况调查。从调查实施时间来看,这些调查基本分布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从调查实施机构来看,这些调查主要是卫生防疫部门实施的。这一方面表明环境保护方面的主导理念仍然是“环境卫生”理念,另一方面也表明即便部分省市设立了“三废”治理利用办公室之类的环保机构,但此类机构尚缺乏必需的行政权力和组织能力。
4.推行了若干环境管理措施 在地方环保行政的层面上,“三同时”思想得到了更为明确的表达。如上文所述,1957年,南京市发布的一个通知中已经显露出“三同时”制度的初步设想。在此基础上,1965年12月,南京市计划委员会、城建局、卫生局联合向市人民委员会报告,提出:“新建、扩建、改建单位的‘三废’处理设施应作为生产工艺的一部分,在设计、施工时一并安排,并将设计文件报‘三废’管理部门,会同卫生、公安、劳动部门签署意见。城建、设计、施工部门应加以监督”。[2](p.311)但“三同时”思想因多种原因而未能真正实施。
少数城市的环境监测工作进一步发展,已形成监测网络。如1963年齐齐哈尔市“三废”办公室会同卫生防疫站、市城建局规划科等单位,对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工厂、企业排水工程进行审查和水质化验,严格控制各种渗井的使用,开始开展初始的环境监测工作。在此基础上,1967年齐齐哈尔市污水处理办公室组织建立了污水监测监督网,设城市污水、西南工业废水、富拉尔基工业废水3片共10个点,定期检查检测。[6](pp.96,99)
(三)1958~1969年间环境保护的成效与环境状况的持续恶化
各级政府推行的环保举措在局部地区取得了一定成效。譬如,1963年10月,国家计委下达了在鞍山投资4564万元兴建49项废水、废渣、烟尘处理利用工程计划,并把鞍山列为全国“三废”处理、利用试点城市。1963~1966年间,鞍山市先后完成治理污染工程29项,完成治理投资额2744.7万元,其中污水处理工程17项、废渣处理工程2项、烟尘处理工程10项。这些措施有效地防治了一部分环境污染,环境质量有所改善。南沙河畔各矿选矿废水流失的精矿粉由每天615吨减少到110吨,每年可回收精矿粉18万吨,价值270万元,南沙河水质也由浊变清。鞍钢化工总厂建成的三套蒸汽脱酚装置,使废水含酚浓度由原来的每升97毫克下降到31.4毫克,每年回收酚盐834吨,价值89.3万元。高炉水冲渣工程以及渣砖、渣瓦厂的建成,使高炉废渣利用率达到50%,每年生产出渣瓦600万片、渣砖6000万块。鞍钢烧结总厂机尾除尘设施建成投产,使厂区降尘量由原来每月每平方公里611吨,下降到184吨。[12]1963年9月,东北局在鞍山召开“三废”工作现场会议后,吉林市先后办起11个小工厂,利用“三废”生产化工产品,每年创造价值800多万元。经过一系列努力,到1966年,吉林市每年处理工业废水3560万立方米,一占工业有害废水排出总量的23.5%;处理废气11亿立方米,占排出总量的33.5%;处理废渣70万吨,占排出总量的68.6%。回收和综合利用“三废”生产66种产品,产值4716.75万元。这些“三废”的处理和综合利用,减少了原料、材料损失,据估算每年创造价值近2000万元。1967~1972年间,吉林市每年处理利用工业废水42种,1.1亿多吨;废渣41种,60多万吨;废气16种,10亿立方米。到1972年以前,吉林市通过综合利用方法,共完成“三废”污染治理项目11项,投资1840万元,其中自筹25.2万元,重点是治理废渣。[13]除此之外,在“综合利用”、“变废为宝”等口号的号召下,许多工厂设计安装了“三废”治理设施,这也对防治点源污染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从全国情况来看,推行“三废”治理举措的地方和企业所占比重仍然较小②,且由于经验不足、技术落后以及执行不力等原因,大部分地方和企业的污染治理效果不佳,因此,即便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环境保护工作的成效仍然是非常有限的。另外,由于当时人们对“三废”治理重要性的认识不足,尤其是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产生污染的,谁要说有污染,有公害,谁就是‘给社会主义抹黑’”[14],这就进一步限制了污染治理的效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项环保举措基本废弛、地方五小企业再度兴起、片面的“以粮为纲”政策再度推行、林业发展遭遇第二次大挫折等等不利于环境保护甚至破坏环境的因素集中涌现,生态环境状况必然无可避免地持续恶化。
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部分地区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非常严重。在环境污染方面,随着工业结构的日益重化工化和工业规模的增大,到70年代中期,全国每天工业污水排放量达3000万~4000万吨,而且绝大部分没有净化处理直接排放,导致很多河流、近海污染。[15]譬如70年代初,大连湾污染严重,因污染荒废的滩涂5000多亩,每年损失海参1万多公斤、贝类10多万公斤、蚬子150多万公斤。海港淤塞,堤坝腐蚀损坏。[8](p.5)在生态破坏方面最突出的就是日益严重的水土流失。以湖北省为例,60~70年代,全省产林县由46个下降到32个,成林、过熟林蓄积量比建国初期下降50%。由于植被破坏,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期,全省水土流失面积约占土地总面积的1/4,流失面积超过百万亩的县有10个。[16]
环保意识开始觉醒与环保行政的加速发展(1970年~1973年7月)
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1970年6月26日,周恩来在接见卫生部军管会的负责同志时即指出:“卫生系统要关心人民健康,特别是对水、空气,这两种容易污染。”针对美日等国发生的工业污染问题,他又指出:“毛主席讲预防为主,要包括空气和水。要综合利用,把废气、废水都回收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不搞,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要搞”,而且“必须解决”。[17]此后,周恩来又多次强调要注意环境保护问题。据不完全统计,1970~1974年间,周恩来对环境保护共作过31次讲话,其中仅在1971年2月间就曾七次提到环境保护工作。[18]正是由于周恩来的高度重视,人们开始更加关注经济建设中的环境保护问题。同时,1971年后,周恩来主持国民经济的整顿工作,国内政治经济形势趋于稳定,也为人们能更多关注环境问题和推行环保举措提供了重要的社会环境。
20世纪60年代,西方工业化国家环境公害事件频繁发生,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为此,联合国决定于1972年6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联合国第一次环境会议,并向中国发出与会邀请。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中国派出了由国家计委、燃化部、卫生部和外交部共同组成的代表团参会。通过此次会议,至少参会人员开始意识到中国也存在环境问题,并得出了“中国城市的环境问题不比西方国家轻,而在自然生态方面存在的问题远在西方国家之上”的结论,[19]这是认识上的一大转变。此次会议对推动中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和第一次全国环保会议的召开,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在此过程中,中国环境保护意识也开始觉醒。
这一时期,随着周恩来的重视和环保意识的逐渐觉醒,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均开展了更为积极的环保工作,环保重点仍然是“三废”治理和综合利用,主要表现如下:
1.出现了成立环保机构的高潮 在周恩来的关怀下,1971年,国家计委成立“三废”利用领导小组。这是中央政府成立的第一个环保机构。1973年1月,又成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筹备办公室。在中央政府的带动下,北京、甘肃、湖北、广东、贵州、河北、河南、辽宁、云南、浙江、湖南、山东等省市新建或重构了“三废”治理利用办公室等环保机构。若再加上在20世纪60年代设立环保机构的天津、上海、黑龙江和新疆四省市区,到第一次全国环保会议召开前夕,已有16个省区市设立了环保机构。此外,长春、成都、大连、贵阳、南京、武汉、郑州、重庆、襄樊、宜昌等中心城市,也新建或恢复了环保机构。与此同时,1972年6月,成立了第一个跨省市的环保机构——官厅水库水资源保护领导小组。随后,又相继成立了关于保护黄河流域、淮河流域、长江流域、松花江流域、珠江流域、太湖水系等水域的环保领导小组。到1973年7月,在全国范围内已初步形成了涵盖中央、省、地市三级行政单位的环保组织网络。环保机构的成立为现代环保事业的顺利起步准备了重要组织条件,同时,也奠定了区域治理与流域治理相结合的环保基本格局。当然,由于环保机构基本隶属于同级政府,它们之间还缺乏上下级隶属关系,这是中国环保行政制度化之前所具有的重要组织特征。
2.召开会议研究污染治理问题 针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中央及部分地方政府曾召开若干会议,专门研究污染治理问题。1972年卫生部在上海召开了工业“三废”污染问题会议;同年4月,国家建委召开了“烟囱除尘现场会议”。在中央的带动下,各省市政府在传达会议精神的同时,也专门召开了此类会议。环保会议的召开,对人们加深对环境污染严重性和环保重要性的认识以及推行环保举措,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3.从中央到地方开展了更为广泛的污染调查 环境保护受到更多关注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从中央到地方开展了更为广泛的环境污染调查。尤其是在中央政府层面,从1972年起,国家卫生部曾组织相关省市对长江水系、渤海、黄海和东海海域进行了水质污染调查。这是中央政府组织实施环境状况调查的开端。在中央的重视下,北京、广西、贵州、山东、浙江、重庆、武汉、保定、长春、兰州、郑州、株洲、佛山等省市也纷纷开展环境污染调查,为人们认识到开展环境保护的紧迫性提供了重要事实材料。
4.环境管理措施得到进一步发展“三同时” 思想在中央政府的文献中首次得到了明确表述。在1972年6月国务院批转的《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关于官厅水库污染情况和解决意见的报告》中,提出了“工厂建设和‘三废’利用要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要求。[8](p.16)与此同时,北京市和云南省也分别作出了建设项目“三同时”的规定。[20]“三同时”制度逐渐成为一项重要环境管理手段。作为一种环境管理手段,主要污染点源的限期治理开始出现。1972年,北京市将位于居民稠密区、群众反映强烈的和平里化工厂、北京铅丝厂等11个工厂含酸、含苯废气的治理,作为限期治理重点项目。[4](p.272)1973年5月7日,湖北省革委会在转发《关于武昌东湖污染情况及治理意见》的报告中,要求武汉大学灭火剂厂、武汉第二制药厂、青山热电厂、武汉重型机械厂含酚废水,武汉仪表厂、武汉温度计厂、湖医的放射性废水,黄家湾六所结核病疗养院限期治理污染,否则应予以搬迁或停产。[16](p.76~77)此外,北京、广东、黑龙江、湖北、云南、山东、武汉、哈尔滨、齐齐哈尔等省市出台了更有针对性、内容更为详实的“三废”污染治理文件和法规;北京、安徽、云南、南京、齐齐哈尔等省市拨出专项资金用于污染治理;武汉市政府甚至制订了工业“三废”治理规划。
综上所述,1970年至1973年7月间,在中央的大力推动下,环保行政加速发展,人们的环保意识逐渐觉醒。这为1973年8月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的召开及环保工作的顺利开展准备了重要的组织条件,提供了环保经验、事实依据及思想基础。可以说,正是在周恩来的重视下、在联合国第一次环境会议的推动下、在前期环保努力的基础上以及在国民经济整顿的大环境中,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才得以顺利召开。
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召开前,中央及地方政府曾经做出过诸多环保努力,虽然这些努力非常零散,成效也比较有限,但环保工作并非一片空白,也并非乏善可陈。当然,由于环保意识并未觉醒,政府的环保举措主要是在“环境卫生”而非“环境保护”的理念指导下推行的,因而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环境保护。
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召开之前和之后的环保政策具有显著的历史连续性和继承性。从环保机构来看,第一次全国环保会议后中央与各地建立的环保局基本都是在“三废”治理利用办公室等环保机构基础上成立的;从环保重点来看,1973年之前政府环保工作的重点是“三废”治理和综合利用,这也正是1973~1978年间的环保重点;从环保理念来看,“预防为主”的理念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提出;从环境管理手段来看,第一次全国环保会议后制订的“三同时”制度、污染企业的限期治理等主要环境管理手段,已在此前的环保工作中提出并付诸实施;从环境治理格局来看,区域治理与流域治理相结合的格局也已在1973年前基本奠定。其他诸如环境监测、环境状况调查以及制定环保法规等也都在第一次全国环保会议前出现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事实上,现代环保事业正是在前期环保工作和经验的基础上开始起步的。从环保工作的生发机制来看,我国的环保工作从萌芽时期就表现出主要依靠中央政府推动的特征。这跟日本、美国等先进工业化国家的环保工作首先从地方兴起、在发展初期主要靠地方政府推动的特征有所不同。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当时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重要决策的制订与实施主要依赖于中央政府。同时,周恩来在环境保护上的远见卓识成为推动环保工作发展和现代环保事业兴起的关键因素,这也使周恩来成为新中国环保事业的奠基人。
[收稿日期]2010-03-08
注释:
① 重庆环境保护局编《重庆市环境保护志》,1997年,第3页。
② 譬如,1963年,南京市114家企业中只有13家相继上了废水治理设施,废水治理量仅占当年排放总量的0.5%。详见《南京环境保护志》,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