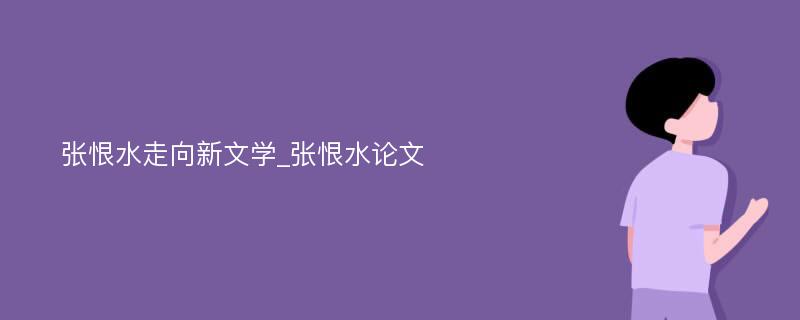
走向新文学的张恨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学论文,走向论文,张恨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学术界公认,张恨水是现代通俗小说天字第一号的代表人物,研究现代通俗文学必须要将张恨水作为一个不可迂回的重镇。但是,如果仅把视野局限于通俗文学的疆域,那么张恨水的文学史意义必将受到极大的遮闭;事实上,张恨水与新文学的关系,在今天看来,恐怕要比他的作品本身更富学术价值,因为它集中体现了现代通俗小说和新文学小说互动发展的轨迹,以及张恨水在其间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
现代通俗小说随着民国的建立而开始繁荣,因此亦称民国通俗小说。
民国通俗小说铺天盖地兴旺发达的势头,到五四时期在理论上遭受重创。但通俗小说的市场并未被夺去,此后它与五四新文学平行发展,范伯群先生称为“双翼齐飞”。事实上,新文学小说虽占据了文坛的制高点,被目为正宗,但在它周围汪洋恣肆的仍是通俗小说之海。新文学作家甚至不能将自己的亲人从通俗小说的市场上拉走,例如鲁迅的母亲看书,“多偏于才子佳人一类的故事,她又过于动感情,其结局太悲惨的,她看了还会难过几天,有些缺少才子佳人的书,她又不高兴看。”〔1〕鲁迅的日记和书信中多次记载为母亲购寄张恨水、 程瞻庐等人的小说之事。若以围棋为喻,新文学所占的是“势”,而通俗小说则占有大片的实地。
特别是社会长篇小说,均表现出“大规模描写中国社会”的气魄。这是中国古代、近代的通俗小说所没有的“现代性”极强的一种气魄。这种气魄对于当时尚处于幼年期的新文学无疑会产生强烈的压迫和刺激。到30年代,新文学才开始创作出《子夜》等一批“大规模描写中国社会”之作。
在这类描写细致,讲求写实,但对主题和结构不够重视并不时夹有“黑幕”气息的社会长篇小说与30年代崛起的新文学社会长篇小说之间,存在一些过渡性的作品,最典型的要数张恨水的《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
《春明外史》连载于北京《世界晚报》1924年4月16日至1929年1月24日。张恨水给这部小说的定位颇高,“用做《红楼梦》的办法,来作《儒林外史》”。〔2〕他一方面追求词章笔法的典雅, 尤其在回目及穿插诗词上用尽心思,另一方面十分注意刻划人物性格,描绘人物心理,摹仿西方小说用景物描写烘托意境的手法,尤其注意把主题集中于揭露社会和写出人物的命运悲剧,这就超越了一般的“黑幕小说”、“狭邪小说”和“才子佳人小说”的境界,从新、旧两个方面提高了章回小说。
《金粉世家》从1927年2月14日起连截于《世界日报》,1932年5月22日才结束。它的构思和酝酿时期,《春明外史》还在连载。张恨水有意要超过《春明外史》,他构思了整个故事,安排好大体情节,列出一张人物表,标明主要人物的性格及相互关系,从而一改《儒林外史》以来的“串珠式”、“新闻化”,使百万巨著成为一个结构性极强的整体。这种写作方法与不久以后的茅盾何其相似!《金粉世家》的倒叙式开头,“准开放式”结尾,西化景物描写,大量内心独白,都显示出通俗小说刻意调整自己姿态的努力。而这部小说的“封建大家庭批判”题材,也开启了新文学中《家》、《春》、《秋》等同一题材系列的创作。
与通俗小说中以《春明外史》、《金粉世家》为代表的“调整之作”相映成趣,新文学界的长篇小说,此时一方面找不到合适的感觉和姿态,在短篇的拉长中摸索,另一方面不免亦吸吮通俗小说的乳汁,其代表作家是张资平。五四新文学在叙述格局上的重要风格之一是出现了大量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我”,这在短篇小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在张资平的长篇小说中,却大多相反。他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飞絮》、《苔莉》、《上帝的儿女们》等,不但叙述手法与旧小说不分轩轾,——比如大量的“叙述干预”——而且艺术格调也向通俗小说看齐。郑伯奇说“资平的写作态度是相当客观的”,〔3 〕而张资平所推崇的“写实”之作乃是《留东外史》。〔4 〕这一时期新文学界推出的长篇小说仅有10部左右,除了张资平的作品外,老舍的《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与通俗文学阵营里“滑稽大师”程瞻庐的作品格调手法都差不多;王统照的《一叶》、《黄昏》以及杨振声的《玉君》,张闻天的《旅途》,都不能称得起严格意义上的长篇,与动辄百万言,充满大全景的通俗长篇相比,它们显得十分幼稚。比如《玉君》,当作一个中篇看还不错。陈西滢说它“文字虽然流丽,总脱不了旧词章旧小说的气味”,〔5〕而鲁迅认为它只不过创造一个傀儡, 其降生也就是死亡。〔6〕此话比较偏激,不尽符合作品实际, 但它的有力影响充分说明新文学阵营对自己的长篇创作评分大大低于短篇。所以长篇小说领域,通俗小说尽管总的姿态仍然偏旧,但却充满自信,稳步地调整着自己的方向。
新文学进入自己的第二个十年之后,兴奋点由“破”向“立”转移,开始发现和反思自身的问题。从1930年到1934年,开展了三次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承认了在与旧文学争夺读者上的失败。确定大众化的方向,当然并不意味着向通俗文学道歉和低头,相反在口头上也许更逞辞锋。但其实际取向的变化对新旧两派的发展的确是富于建设性的。
新文学最富探索性的短篇小说,逐渐消减先锋姿态,增加人物、情节因素来扩大阅读面。长篇小说则大获丰收,出现了茅盾、老舍、巴金等长篇小说艺术大师。这意味着新文学小说由注重抒情的时代进入注重叙事的时代。通俗小说由此亦获得了对叙事性创作的一种自信。
通俗小说的中兴期也是以出现一批“大家”为标志的。这些“大家”连同许多“名家”推出了成就明显高于调整期的大批比较优秀的作品。
在社会、言情小说领域,首推张恨水和刘云若。张恨水从1929年《啼笑因缘》开始,加快了改良章回小说的步伐。《啼笑因缘》的巨大成功使他实现了少年时代的名士之梦,进而使他思索如何让自己的创作更上层楼。在此后的《燕归来》、《小西天》、《满城风雨》、《似水流年》、《太平花》、《东北四连长》、《现代青年》、《如此江山》、《中原豪侠传》、《鼓角声中》、《夜深沉》等作品中,他的创作态度越来越严肃,越来越密切联系时代风云,灌注现代意识。在写作方法上也进行了各种改革尝试,虽然也有失败,但总体上是成功的,为通俗小说开辟了一条充满诱惑力的新路。
不过,在艺术观念和创作模式上仍有待突破。张恨水算是最为自觉的章回体改良作家,但他的改良,说到底仍是出于竞争的逼迫,是一种聪明的“识时务”,与老舍《茶馆》中的王利发颇为相近。他还没有清醒认识到章回体与现代艺术观念的脱节,所以他的改良颇有为章回体“补天”的意味。张恨水骨子里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坚信“中国是五千年文物礼仪之邦,精神文明,谅非西人所及。”〔7 〕他一直改良到抗战之前写《夜深沉》时,仍花费大量心血苦苦雕琢回目的工整典雅,如“立券谢月娘绝交有约/怀刀走雪夜饮恨无涯”之类。而在回与回之间,虽然早已摒弃了“且听下回分解”,但基本路数仍是“伏扣子”、“卖关子”,如“这是接好消息呢,还是接坏消息呢?”(第十五回结尾)“怪了,怎么他也会在这里呢?”(第九回结尾)完全可以加上“且听下回分解”而一点也不别扭。《夜深沉》一共四十回,据笔者统计每回最末一个字的四十个字中,共有23个“了”字,9个“呢”字,2个“的”字,2个“来”字,1个“呀”字,只有其余3个是实词。大量使用句尾虚词,意味着对段落结束的敏感与习惯。“了”字、“呢”字占80%,更显露出收场乏术,其重复之乏味还不如加上几句下场诗。张恨水尚且如此,其余的通俗小说在新文艺长篇小说灵活多变的结构模式对比下,大多显得呆板沉闷,这样写下去无疑是慢性自杀。通俗小说得以中兴的最核心秘诀就是大胆容纳了西方技法,“师夷长技以制夷”,现代化的马达一旦发动,是不可中止和逆反的,要生存,便有进无退。所以,艺术观念和创作模式两方面的局限决定了通俗小说的进一步变革具有迫切的必要性。
现代通俗小说进一步变革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是在战争的催化剂下转化成现实性的。
抗日战争的爆发,将民族命运问题推到了时代的最前景,造成了民族意识的空前统一。朱自清称:“抗战以来,第一次我们获得了真正的统一。”〔8〕文学组织,文学宗派,文学观念,文学形式, 文学格调,一时都趋向抗战的中军大旗。新旧文学两大营垒也都放下吊桥,欢聚一堂。1938年3月27日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张恨水列为理事之一,国统区通俗小说的荣辱兴衰系于一身。张恨水不负众望,抗战期间写出了20余部长篇小说,成为大后方销行最广、销售量最大的作品。这些作品中直接描写抗战的有《桃花港》、《潜山血》、《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游击队》、《冲锋》(一名《天津卫》,单行本易名为《巷战之夜》)、《敌国的疯兵》、《大江东去》、《虎贲万岁》等;描写大后方生活,揭露国统区黑暗的有《疯狂》、《八十一梦》、《蜀道难》、《牛马走》(一名《魍魉世界》)、《偶像》、《第二条路(一名《傲霜花》)等,此外还有《秦淮世家》、《水浒新传》、《丹凤街》(一名《负贩列传》)、《征途》、《赵玉玲本记》、《雁来红》等。这些作品绝大部分直接间接关乎时代,如他本人所说:“与抗战无关的作品,我更不愿发表。”在题材选择上,与新文学小说基本一一对应。在艺术风格上,更加明确而努力地向新文学靠拢。因此,在取得新的突破和成就的同时,也得到了一些教训。首先是沾染了同期新文学小说的一些通病,如机械图解政治观念、过分追求浅俗等;其次是贪于“进步”,有时未免如邯郸学步,把自己原来的优点也丢弃了。如张恨水早年小说往往奇峰迭起,悬念纷呈,而此时作品,特别是抗战小说,大都平铺直叙,呆板单调。有时退回言情的老套中去,新旧生硬相加,颇不和谐。成就与教训的起伏颠扑中,张恨水为通俗小说杀出了一条既光明又曲折的新路,尤其是以《八十一梦》为代表的讽刺小说,一方面继承晚清传统,另一方面借鉴新文艺观念,成为一种品位独特的艺术形式,对新旧两派小说均产生极大影响。后来的主流文学史虽然一直忽视张恨水,却从未能将《八十一梦》抹而去之。为通俗小说在主流文学史争得一席之地,首功当归于张恨水在抗战期间的创作,其意义已经不限于国统区了。
作为国统区旧派小说孤军的张恨水,在抗战期间对通俗小说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理论思考。张恨水是自觉愿附新文学之骥尾的,但他明确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常以“诤友”的姿态来面对新文学。抗战初期,他批评新文学“浮躁与浅薄”,〔9〕“洋场才子们”没有真本事, “来到内地,也许三个月发表一篇短文”。〔10〕后来,张恨水经过下乡调查,写了一篇《赶场的文章》。他发现“那书摊子上,或背竹架挂着卖的,百分之八十,还是那些木刻小唱本。此外是《三百千》,《六六杂志》,《玉匣记》(一种查星宿的迷信书),《四书》,《增广贤文》,如是而已。至多带上一两部《三国演义》或《水浒传》、《征东》、《征西》等章回小说,那已经是伟大的书摊子了。如此供应着,可以知道乡下人在弄什么文艺。”张恨水进一步指出:
大都会的儿女,不但没有看见过赶场的书籍,我相信连书名都很陌生。在这种情形下,坐在象牙塔里的文人,大喊到民间去,那简直是作梦。我们要知道,乡下文艺和都市文艺,已脱节在五十年以上。都市文人越前进,把这些人越摔在后面。任何‘普罗’文艺,那都是高调,而且决对是作者自抬身价,未曾和这些人着想,也未曾梦到自己的作品,有可以赶场的一日。〔11〕
无独有偶,解放区的赵树理也发表过与张恨水惊人近似的言论。两大通俗小说家虽然一“上”一“洋”,却在相同的时期共同注意到了“文坛”与“文摊”的对立,并将立场明显倾向于“文摊”。
一方面倾向于文摊,另一方面则倾心于抗战,张恨水孜孜追求着可读性与进步性的统一。他在《偶像》一书的自序中言道:
抗战时代,作文最好与抗战有关,这一个原则,自是不容摇撼,然而抗战文艺,要怎样写出来?似乎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结论。
我有一点偏见,以为任何文艺品,直率的表现着教训意味,那收效一定很少。甚至人家认为是一种宣传品,根本就不向下看。我们常常在某种协会,看到存堆的刊物,原封不动的在那里长霉,写文字者的心血,固然是付之流水,而印刷与纸张的浪费,却也未免可惜。至于效力,那是更谈不到了。
文艺品与布告有别,与教科书也有别,我们除非在抗战时期,根本不要文艺,若是要的话,我们就得避免了直率的教训读者之手腕。若以为这样做了,就无法使之与抗战有关,那就不是文艺本身问题,而是作者的技巧问题了。〔12〕
张恨水强调“技巧”,反对“教训”,这明显是针对新文学阵营所大量“客串”的那些“短平快”的通俗小说而言。至于表现抗战,张恨水对此有着比较辩证的认识:
自然,我们并不否认报纸上文字,是要配合时间的,这样谈法,好象有意逃避现实。但是这个实,是客观的存在,我们如何去表现,其法倒不一格。〔13〕
《水浒新传》便是张恨水既表现抗战,又重视趣味的一个实例。在日伪控制下的上海报纸,不能明显流露抗日气息,张恨水便停笔不写。但得知上海小报请人冒名续写后,他担心“在敌人控制下的文字,不能强调梁山人物民族思想……甚至写得宋江等都投降了金人,也有可能。》〔14〕于是他又自己一气续完。此书既“充分的描写异族欺凌、和中国男儿抗战的意思”,“能够略解上海人的苦闷”,又是“现成的故事,也不怕敌伪向报馆挑眼。”〔15〕可见张恨水之煞费苦心。《水浒新传》出版后,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曾赋得七律《乙酉八月听读张恨水著水浒新传感赋》,诗曰:
谁缔宣和海上盟,燕云得失涕纵横。
花门久已留胡马,柳塞翻教拔汉旌。
妖乱豫么同有罪,战和飞桧两无成。
梦华一录难重读,莫遣遗民说汴京。〔16〕
毛泽东也曾对新闻界说:《水浒新传》这本小说写得好,梁山泊英雄抗金,我们八路军抗日。〔17〕张恨水通过《水浒新传》所表达的主张,成为通俗历史小说创作的一盏导航灯。
1944年5月16日,张恨水五十寿辰, 以文协为代表的全体文化界联合发起祝寿,重庆各报刊数十篇专文盛赞张恨水。潘梓年在《精进不已》中反复强调张恨水“有一个明确的立场——坚主抗战,坚主团结,坚主民主”。潘梓年借题发挥道:
是的,对于一个作家,也如对于一个从事革命事业的人一样,明确的进步立场始终是一个基本条件。立场不进步,他就看不清现实,甚至看不见现实,写出来的东西,也就不会受到进步人士的爱好,对于社会,更是有害无益。立场不明确,他就不能自有主宰,屹立不摇,他就不能在自己的作品中,显现出自己特有的风格,也就不能在作家之中,找得一个地位。〔18〕
这番话代表了新文学阵营对通俗小说的总态度:一方面高度重视,另一方面强调重视的首要前提是立场必须“进步”,否则“不能在作家之中,找得一个地位”。
称张恨水为“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19〕的老舍,称张恨水“对世道人心有很大的启示”〔20〕的罗承烈,以及其他文章的作者,不约而同地也主要从“人格”落笔,称颂了张恨水“最重气节,最富正义感”(老舍),“人格上的修养,实在值得敬佩和效法!”(罗承烈)“未尝做官,亦不耍钱”。〔21〕可以说,张恨水后来能够在正统文学史著作中占有一席之地,起决定作用的是他的“立场”。
面对如此厚爱,张恨水又欣喜又惶恐。他避寿家中,不敢露面,然后写了《总答谢》一文,道歉致谢,兼明心志。文中关于章回小说部分,可视为抗战时期张恨水的通俗小说理论大纲:
我觉得章回小说,不尽是可遗弃的东西,不然,红楼水浒,何以成为世界名著呢?自然,章回小说,有其缺点存在,但这个缺点,不是无可挽救的(挽救的当然不是我);而新派小说,虽一切前进,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所能接受。正如雅颂之诗,高则高矣,美则美矣,而匹夫匹妇对之莫明其妙。我们没有理由遗弃这一班人,也无法把西洋文法组织的文字,硬灌入这一班人的脑袋,窃不自量,我愿为这班人工作。有人说,中国旧章回小说,浩如烟海,尽够这班人享受的了,何劳你再去多事?但这有两个问题:那浩如烟海的东西,他不是现代的反映,那班人需要一点写现代事物的小说,他们从何觅取呢?大家若都鄙弃章回小说而不为,让这班人永远去看侠客口中吐白光,才子中状元,佳人后花园私订终身的故事,拿笔杆的人,似乎要负一点责任。我非大言不惭,能负这个责任,可是不妨抛砖引玉(砖抛其多,而玉始终未出,这是不才得享微名的缘故),让我来试一试。而旧章回小说,可以改良的办法,也不妨试一试。〔22〕
张恨水的通俗小说理论,第一强调“服务对象”,他愿为“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工作;第二强调“现代”,为他的服务对象提供“现代事物”。故而他要在“新派小说”和“旧章回小说”之间,踏出一条改良的新路,这一主张恰与新文学阵营的“民族形式”宗旨合掌对接。
张恨水的改良取渐进之法,“所有章回小说的老套,我是一向取逐渐淘汰手法,那意思也是试试看。在近十年来,除了文法上的组织,我简直不用旧章回小说的套子了。严格的说,也许这成了姜子牙骑的‘四不象’。”渐进之法并非新文学所提倡,所以“四不象”的通俗小说只能是一个过渡。
在具体的改良手法上,张恨水说:“我于小说的取材,是多方面的,意思就是多试一试。其间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者多。那是由于故事的构造,和文字组织便利的缘故。”这表现了张恨水“恋旧”的一面;他又说:“关于改良方面,我自始就增加一部分风景的描写与心理的描写。有时,也特地写些小动作。实不相瞒,这是得自西洋小说。”这表现了张恨水“求新”的一面。
张恨水关于通俗小说的理论思考,既有与新文学阵营不谋而合之处,也有他自己的独见之处,后者的一部分得到了吸收与肯定。王元化称赞张恨水的写作态度和艺术才能都是礼拜六派的新小说家可望不可及的。〔23〕宇文宙用评价新文学小说的标准称赞张恨水的《八十一梦》达到了“反映现实的本质的目的”。〔24〕这都对张恨水所代表的通俗小说作家起着提携和鞭策的作用。曾有文章说,若将张恨水的作品“依年代次序读下去我们可以对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变动,获得具体的了解”,〔25〕后来张恨水便是以同样的口吻去评价李涵秋的《广陵潮》的。
抗战时期,传统意义上的狭义通俗小说主要在沦陷区,而国统区只有张恨水一支孤军。与战前的繁荣、调整、中兴三个阶段相比,此期的通俗小说不可阻挡地走向了成熟。成熟的重要表征之一,是雅化。
张恨水的“雅化”,从他走上创作道路之初就开始了。他的整个创作道路,就是一个曲折的“雅化”进程。在他最早发表的小说《小说迷魂游地府记》中,他对新旧两派文学都进行了批评,借施耐庵之口,宣布要“和似是而非的小说商宣战”,借吴敬梓之口讽刺白话新诗。他提出了自己明确的文学主张——“花样无非翻旧套,文章也要顺潮流”。此后的张恨水的确是按照这个主张对章回小说进行改良的,即一方面在思想内容上顺应时代潮流,另一方面在艺术技巧上花样翻新。他先以古典名著作为雅化方向,精心结撰回目和诗词,后来发现时人对此不感兴趣,便转而学习新文学技巧,更注重细节描写、性格刻划和景物烘托。在思想观念上也逐渐淡化封建士大夫立场,接受了许多个性解放意识和平民精神。这使他成为二三十年代通俗小说的“超一流”作家,同时也成为新文学“擒贼先擒王”的重点打击对象。直到抗战之前,尽管他写出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名作,但他始终觉得尚未找到雅化的终极归宿。他时而在揭露社会的喝采声中获得一种成就感、优越感,时而又回到以小说为“小道”的自卑感、无聊感中。《金粉世家》自序中云:
初尝作此想,以为吾作小说,何如使人愿看吾书。继而更进一步思之,何如使人读吾之小说而有益。至今思之,此又何也?读者诸公,于其工作完毕,茶余酒后,或甚感无聊,或偶然兴至,略取一读,借消磨其片刻之时光。而吾书所言,或又不至于陷读者于不义,是亦足矣。主义非吾所敢谈也,文章亦非吾所敢谈也。吾作小说,令人读之而不否认其为小说,便已毕其使命矣。今有人责吾浅陋,吾即乐认为浅陋。今有人责吾无聊,吾即乐认为无聊。盖小说为通俗文字,把笔为此,即不脱浅陋与无聊。华国文章,深山名著,此别有人在,非吾所敢知也。
事实上,张恨水的顺应潮流也好,花样翻新也好,主要出于使人“愿看吾书”的促销目的。尽管他有着个人的痛苦和对社会的愤慨,但他的创作欲并非是要“引起疗救的注意”〔26〕,他更多的是把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27〕。所以无论他写作“国难小说”,还是改造武侠小说,一方面在通俗小说界显得太赶时髦,雅气得让人追不上,而另一方面在新文学阵营看来,却仍觉换汤不换药,不可救药。他的那些苦心实验的“技巧”、“革新”,都成了费力不讨好。
是抗战,使张恨水通俗小说的雅化飞跃到一个新阶段。
首先,在创作宗旨上,他从把写作仅仅当成谋生的职业,变成了当作奋斗的事业。他理直气壮地宣称要为“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工作,他满怀使命感地写道:
我们这部分中年文艺人,度着中国一个遥远的过渡时代,不客气的说,我们所学,未达到我们的企望。我们无疑的,肩着两份重担,一份是承接先人的遗产,固有文化,一份是接受西洋文明。而这两份重担,必须使它交流,以产出合乎我祖国翻身中的文艺新产品。〔28〕
在与新文学阵营的关系上,张恨水由对立和怨恨转变为合作和追随。他接受现实主义理论,接受新文学的主要创作态度和创作方法,接受新文学对自己的批评和鞭策。这些都反映在他八年抗战的创作中。
张恨水抗战时期的中长篇小说共有20部左右,从题材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抗战小说,包括《桃花港》、《潜山血》、《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游击队》、《巷战之夜》、《敌国的疯兵》、《大江东去》、《虎贲万岁》等。第二类是讽刺暴露小说,包括《疯狂》、《八十一梦》、《蜀道难》、《魍魉世界》、《偶像》、《傲霜花》等。第三类是历史和言情等其他小说,包括《水浒新传》、《秦淮世家》、《赵玉玲本记》、《丹凤街》、《石头城外》几部。这恰与该时期新文学小说的分类格局相同。而且在时间上也彼此呼应——抗战初期以抗战小说为主,后期则以讽刺暴露为主。这说明张恨水在文学观念上已经由“慢半拍”转为“同步和声”,与新文学共奏大雅了。
张恨水的抗战小说不同于他以前的“国难小说”,言情已经退居到可有可无的地位,如《大江东去》这样的“抗战与言情兼有者”〔29〕乃是谴责女子对抗战军人的负心,趣味中心并不在言情;而《巷战之夜》等根本无情可言。代替趣味成为作品中心的,是观念。张恨水大力追求“写真实”,放弃编织故事的特长。他说:
不肯以茅屋草窗下的幻想去下笔,必定有事实的根据,等于目睹差不多,我才取用为题材。因为不如此,书生写战事,会弄成过分的笑话。〔30〕
另一个观念是民众思想,即“人民战争”思想。他的多数抗战小说都以民众自发组织的游击队为描写和歌颂对象,而在描写正规军的《大江东去》和《虎贲万岁》中,也努力突出民众,以致引起当局注意,多数作品遭到“腰斩”。
与新文学的抗战小说一样,张恨水此类作品由于仓促求成,艺术上便禁不起时间的考验。平铺直叙,急于说教,既有拘泥于生活真实而放弃艺术真实的倾向,又有制造巧合图解观念的毛病。如《敌国的疯兵》写日寇中队长饭岛,率兵将李大娘的养女莲子轮奸致死,结果发现莲子竟是饭岛早年在北京与李大娘作邻居时,寄养在李家的自己的亲生女儿!于是饭岛真的发了疯。这种因果报应的俗套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感染力。
相比之下,他的讽刺暴露小说取得了成功,这本来便是张恨水的特长,也是通俗小说的特长。与民国初年的黑幕化小说和张恨水早期的新闻化小说不同,这一时期的讽刺暴露小说贯穿着统一的叙事立场,即从人民大众根本利益出发的正义感和深切的民族忧患意识。这是此前的通俗小说根本达不到的境界。张恨水写《春明外史》的时代:“老实说,写稿子完全为的是图利”,“没什么利可图的话,就鼓不起我写作的兴趣。”〔31〕而《八十一梦》和《魍魉世界》两书,揭露贪官污吏巧取豪夺,武力走私,全民皆商,发国难财者花天酒地,威风凛凛,知识分子穷得四处讨饭,卖掉一套善本《资治通鉴》,所得不值一包烟钱,下层百姓饥寒交迫,怨声载道,几乎写出了一部国难史,令人不由联想到安史之乱后杜甫那些“感时花溅泪”的“诗史”。二人均是在40岁至50岁之间,身经山河剧变,自己流离失所,目睹人民灾难,在入蜀前后,达到了新的创作高峰。张恨水的这些讽刺暴露小说,艺术上并不完美,缺点很多,当然比不了杜甫的“三吏”、“三别”。但其间那种“穷年忧黎元”的人民性,深深感动了广大读者,掩盖了其艺术上的不足,做出了新文学想做而做得没那么精彩的事,因此大获主流文坛的欢心。
不过,不能因为张恨水的这一部分小说在主流文学史里得到了肯定,就认为它们在艺术上雅化到与新文学的优秀作品不分轩轾的程度。许多论著过分称赞《八十一梦》对讽刺小说体式的创新,其实创新并不等于好。《八十一梦》的总体结构是散乱乏序的,每一个梦也并非都“自然而紧凑”,完全可以构思和创作得更完美、更精炼。其他小说也一样,给人以丑闻罗列、人像展览式的印象,这种手法是《春明外史》、《新斩鬼传》时代的路子,从《啼笑因缘》以后,张恨水已经有所超越,开始追求典型化的路子。而40年代张恨水的小说只在人们脑中留下了篇名,却没有留下人名。这说明艺术上的雅化与观念上的雅化不一定是携手并进的,有时也许反要倒退。事实上,是轰动效应构成了这些小说的文学史价值。读者们告诉作者:“写得对,骂得好;再写得深刻些,再骂得痛快些!”〔32〕周恩来鼓励说:
同反动派作斗争,可以从正面斗,也可以从侧面斗。我觉得用小说体裁揭露黑暗势力,就是一个好办法,也不会弄到“开天窗”。恨水先生写的《八十一梦》,不是就起了一定作用吗?〔33〕
政治家要求斗争的“作用”,群众要求“骂得痛快”,这都是从“通于世俗”着眼的,没有人关心其“结构”与“技巧”。张治中代表政府来劝张恨水罢手停写时,也说“写得好,骂得对”。这些小说仍然是通俗小说,比新文学同类作品中艾芜的小说大概要好一点,比沙汀的就要差一点了,比张天翼也许正好,只是份量要厚重得多了。
张恨水的第三类小说,与前两类基本相似。历史小说《水浒新传》写的是梁山英雄招安后抗击金兵、为国捐躯的悲剧,走的是借古喻今的路子。“要借古人的骸骨来,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34〕。其思想主题与同期郭沫若、阳翰笙等人的历史剧是一致的,时代性、政治性十分突出。毛泽东曾对访问延安的中外记者说:“《水浒新传》这本小说写得好,梁山泊英雄抗金,我们八路军抗日。”〔35〕《秦淮世家》、《丹凤街》等“半言情小说”,主题比较模糊,又想隐寓抗日,又想赞颂民众之“有血气,重信义”,“籍以示士大夫阶级”,〔36〕又含有对故都的怀恋,因此故事情节不够紧凑,影响不大。
总起来看,张恨水抗战时期小说的雅化核心在于创作宗旨和思想主题。他终于由消遣文学走到了听将令文学,终于“带师学艺”,被新文学招安到帐下。这使他终于有了“到家”的感觉。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感觉使他在艺术技巧的雅化上有所放松。抗战时期小说的普遍问题是结构感差,像《八十一梦》的结构也只能说有独到之处,并不值得立为典范。其次是叙事语言不如战前流畅精美,叙述干预增多,有控制“释义播散”倾向,这是向清末民初小说风格的倒退。艺术技巧上更加雅化的地方表现在心理刻划意识似比战前更为自觉,这使《魍魉世界》、《傲霜花》等还比较耐读。但他写了那么多的贪官污吏、商贩屠沽,却没能留下几个生动的人物形象。《八十一梦》等几部“斩鬼”之作,时过境迁以后,只能看作是他的“投名状”。提起张恨水,人们更多想到的还是他写于战前的“现代青年”系列。是新文学已经不再鼓励那些“雕虫小技”的探索,还是张恨水自己觉得“小雅”已经不必再努力,只要在思想上“精进不已”便是“大雅”,抑或是时代正要求新旧文学都向一种“四不象”的新形式靠拢?此中的得失很值得玩味。走向新文学的张恨水在现代通俗小说史上留下了一道长长的问号般的身影。
注释:
〔1〕荆有麟《鲁迅回忆》,转引自王得后《两地书研究》P357,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
〔2〕张恨水《我的小说过程》,《张恨水研究资料》P274,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
〔3〕《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 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
〔4〕参见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P598。
〔5〕《西滢闲话·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上海书店 1982年复印版。
〔6〕《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7〕见袁进《张恨水评传》P79,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8〕朱自清《新诗杂话·爱国诗》。
〔9〕水《文人谦和了》,重庆《新民报》1942年9月21日,转引自袁进《张恨水评传》P261。
〔10〕水《洋场才子何在》,重庆《新民报》1940年7月14日, 同上书P262。
〔11〕载重庆《新民报》1944年4月11日,同上书P259。
〔12〕《张恨水研究资料》P253—254,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3〕水《〈上下古今谈〉开场白》,重庆《新民报》1941年12月1日,同上书P250—251。
〔14〕《水浒新传》新序,同上书P252—253。
〔15〕同上,P251—252。
〔16〕《陈寅恪诗集》P42,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7〕《张恨水研究资料》P212。
〔18〕1944年5月16日重庆《新民报》,《张恨水研究资料》P109。
〔19〕《一点点认识》,同上书P110。
〔20〕《我所认识的恨老》,同上书P111。
〔21〕司马讦《何恨?》,同上书P114。
〔22〕同上书P279—280。
〔23〕佐思《“礼拜六派”新旧小说家的比较》,同上书 P309—310。
〔24〕《梦与现实》,载1942年9月21日重庆《新华日报》, 同上书P311。
〔25〕沙《恨水的创作表现》,1944年5月16日重庆《新民报晚刊》副刊,同上书P317—318。
〔26〕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收《南腔北调集》。
〔27〕《文学研究会发起宣言》。
〔28〕水《郭沫若、洪深都五十了》,重庆《新民报》1943年1月5日。
〔29〕《大江东去》自序。
〔30〕《巷战之夜》自序。
〔31〕《写作生涯回忆》,《张恨水研究资料》
〔32〕《八十一梦》前记。
〔33〕张友鸾《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张恨水研究资料》。
〔34〕郭沫若《孤竹君之二子·幕前序话》。
〔35〕《张恨水研究资料》P212。
〔36〕《丹凤街》自序。
标签:张恨水论文; 文学论文; 小说论文; 金粉世家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春明外史论文; 长篇小说论文; 水浒新传论文; 大江东去论文; 虎贲万岁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