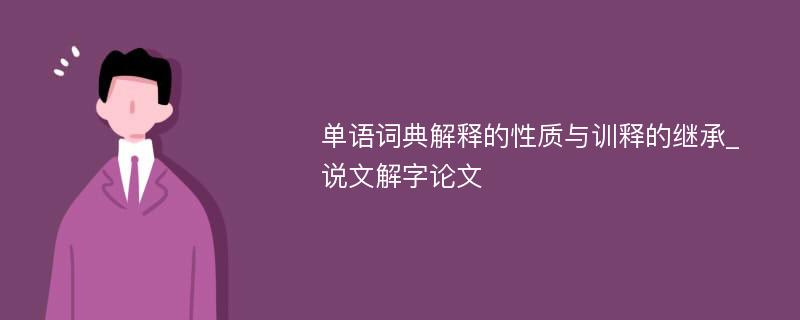
单语词典释义的性质与训诂释义方式的继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释义论文,语词论文,性质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单语词典释义的性质和难度
依照解释语与目标语的异同,我们可以把词典分成双语词典(解释语与目标语属不同语种)、历时语言词典(解释语与目标语属同一语种不同时代的语言,例如古汉语词典)、方言词典(解释语为规范语言,目标语为方言)和单语词典(解释语与目标语均为同一语种的规范语言)四种。古语词典和方言词典就释义而言都带有双语词典的特性,它们在以下两点上与双语词典是相同的:第一,这两种词典的解释语对使用者来说,都是已经掌握的语言,是已知;目标语则是沟通的对象,是未知;所以,解释语承担的任务,是通过对译的方式,把作为目标语的古语和方言,转换为现代规范语言。词典中大多数的释义,可以采用简单的对译,即意义的迁移来解决。例如,古汉语“书”有一个义项可以解释作现代汉语的“信”(如“家书抵万金”),释义作到这里,任务就完成了,而不需要再进一步解释为“按照习惯的格式把要说的话写下来给指定的对象看的东西”。(注:《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7月版,1403页。)第二,这两种词典的解释语与目标语的词汇系统和词义系统都在不同程度上是相异的,所以,在那些两种词汇系统和两种词义系统相互差异的地方,一般无法简单地对译,也就是说,有些词很难找到相应的对译词。这些地方,也就是释义的难点。只有这些地方,才需要采用别的方法来释义。例如“野”,在古汉语里有一个义项是与“朝”相对的,“朝”即“朝廷”,这种事物已经消失,“野”自然很难在现代汉语里找到一个可以与这个义项对译的词。只能用词组或句子来解释。
对于单语词典来说,它的释义与上面所说的情况有本质的不同。
首先,从释义的目的看,如果说双语词典的释义目的是进行双语的沟通以消除懂得解释语的人理解目标语的语言障碍,那么,作为解释语与目标语为同一种语言的单语词典,释义的目的就要复杂得多了。它除了要对疑难词义进行解释,帮助使用者理解和使用这些词外,还兼有将目标语的词汇加以搜集、贮存的任务。贮存不是单纯的收藏,同时还具有间接释义的作用。比如,“半”的本义是“二分之一”,其实,“半”比“二分之一”好懂。单独看起来这个释义没有多大意义;可是,“半”也有不均分的“中间”的意思,所谓“半夜”、“半路”、“半途而废”,都不必是正中间。这就使得“二分之一”的释义具有了区分义项的不可或缺的价值。再如“一”,本义是数目字,可以说无人不晓,但它的这个义项是解释其他数目字的基础,其他数目字虽然也不难懂,但是,汉语里的数字,有一部分除了表示精确数字以外,还具有其他意义,必须把这些意义与精确数字区别开,以防理解错误。同理,“二”有不同、别样的意思(言不二价);“三”、“九”都还可以是表多数的虚数(三令五申、一言九鼎),“九”还兼有表示季候(数九)的意思;“七”兼有专门数祭奠日期的意思(头七),“十”有“齐全”的意思(十全十美)。这就使数字精确释义的义项不可或缺,而最容易懂的“一”作为“最小正整数”的释义,不但不可缺少,解释用语还特别需要斟酌。单语词典的很多释义,具有区别义项、梳理词义系统的作用,必须贮存起来。这些人人都懂得、既不难又无疑的义项释义的难度,在某种意义上,要大于双语词典;弄得不好,原来人人都懂、都能把握的词义,一解释反而让人不懂了。
其次,从释义的方式看,单语词典的解释语与目标语是同一种语言,它们的词汇系统和词义系统完全是一样的。在同一个词汇系统和词义系统里,离开了语言环境,不会有两个词在意义上是全同的;因此,准确的对译和转换,除了个别风格色彩相同的同名异实的事物名称(如“电脑—计算机”、“出租车—计程车”等)外,只能是词语自身来对应自身,即A对A,因而是无意义的。选择同义词来对译,由于同义词之间必然具有的差异,因此必定是不够准确的。比如:当我们用“遮盖”去解释“覆盖”时,其实是忽略了“遮盖”不计遮挡的方向和是否周严而“覆盖”指自上而下的遮挡并且要遮挡周严这一差异的。又比如,当我们用“生日”去解释“生辰”时,其实也是忽略了它们的差异:各种语言所说的“生日”都只指出生的那一天,而中国所说的“生辰”,一般是含出生的天和时间的。所以,单语词典的释义方式,要受到较大的局限。
有人认为,编写双语词典,必须懂得两种语言,而编写单语词典,只需要懂得一种语言,所以双语词典的难度更大。这只说对了一个方面。从释义的性质和目的来说,单语词典释义的技术要求,实际上高于双语词典。
基于以上原因,单语词典的释义规则,与双语词典不可能完全一样,当我们对某些单语词典的释义成果和古今中外的释义理论加以分析时,可以概括出许多十分有益的规律和定则;但是,也可以觉察出,有些规则对双语词典适用,对单语词典不一定适用;而且,不同语种的单语词典,也会有一些仅属于自身的特殊规则,这是由目标语的特性决定的。为此,我们在借鉴国外释义理论的同时,也应该吸取一些中国古代训诂学的释义规则和技术,使汉语单语词典的释义更切近汉语的实际。
二 古代训诂的文意训释
古代训诂材料大约以三种形式保存下来:随文释义的注释书、将训释材料编纂到一起的纂集书,以及对个别词语的疑难意义加以探求或前人错释的词语意义加以纠正的考证材料。
随文释义是对存在于语言环境中的言语意义加以解释的工作。言语是语义存在的实际载体,语境中的词义特点是:单一性、具体性、经验性。这种训释有两种形式是不能搬到词典中去的:
第一种是显现言语具体性和经验性的文意注释。例如:
(1)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 (《诗经·召南·行露》)戴侗说:“穿,啮透。”
(2)乱今厚葬饰棺,故抇也。 (《荀子·正论》)注:“抇,穿也,谓发塚。”
(3)其犹穿窬之盗也与!(《论语·阳货》)注:“穿, 穿壁也。”
以上三处注释都是言语意义的解释,训诂学叫做文意训释。第一例释“穿”为“啮透”,第二例释“穿”为“发塚”,第三例释“穿”为“穿壁”。三个“穿”属同一义项,都是动词,当“穿通”讲,排除了多义,以单一的意义形式存在。由于语境的补足,语义内容显现了一定程度的具体性:在第一例中,显现了“穿”的方式“啮”(用牙咬),第二、三例中,显现了被穿通的物体“墓”或“壁”。三种解释的背后,本来还有其他未加显现的经验性内涵——也就是个性化的内涵,诸如穿透的目的、方式、时间、地点、情景等等,语境含量越大,语义的经验性内涵越丰富,但是在文意注释里,并不都把这些内涵显示出来,而是只拣与文意有关的显示在注释中。上述两例的训释显现的,只是狭义语境所规定的少部分内涵。也有经验性的内涵显现得更多一些,也就是个性化更强一些的。例如:
(4)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诗经·周南·桃夭》)《郑笺》:“宜者,谓男女年时俱当。”
(5)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 (《诗经·齐风·还》)毛传:“茂,美也。”陈奂《毛诗传疏》:“美者,谓习于田猎也。”
第一例显现了“男女年龄相宜,婚配时间相宜”的具体内涵,但还保持了“当”这个训释语,与“宜”在这里的义项相匹配。第二例中“茂”训“美”,“美”并不说明“茂”的任何义项,显现的只是诗作者内心对“子”的赞美,陈奂的解释把这种对人才的赞美更加具体化了,说明这里的“美好”特指“打猎熟练的人才”。
上述词的训释一旦脱离了语境,就不能使用了,因为,很少有两种文意是完全相同的。依赖语境的文意训释是个性化的,也就常常是唯一的,不能将他们普遍使用,自然也就不适合直接搬到辞书里去。文意注释转化为词义(语义)注释的关键是要把依附于具体环境的经验性内容——也就是在概括词义之外的个性化内容抽象出去。例如,把“穿”的动作方式、动作对象抽象出去,它的概括意义是“打通”。把“宜”针对对象抽象出去,它的概括意义是“相当”、“合适”。要从“茂,美也”这个注释中得到“茂”的概括意义,是要经过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辞书是不应选择这种训诂材料直接做释义材料的。
随文释义中,还有一种训释方式是不适用于单语辞书的,那就是单训的形式。单训就是以单词来解释另一个单词。例如:
(6)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郑注:“易,简也。”
(7)是子之易也。(《公羊传·襄公六年》)注:“易犹省也。”
(8)土不可易。(《左传·昭十八年》)注:“易,轻也。”
(9)易者使倾。(《易经·系辞下》传)陆注:“易,平也。”
(10)虽获田亩而不易之。(《孟子·尽心上》)注:“易。治也。”
(11)农不易垅。(《文选·射雉赋》)注:“易,修也。”
这种训释,训诂学里叫做“代语”,也就是说,在这个语言环境里,用训释词把被训释词代换下来,句义没有变化。这种训释的目的是用来确定句中词语的义项,或以常用而熟悉的词语把疑难词语置换下来。在有语言环境时,语言环境补足了训释未尽的一面,使“代语”变得形式简便,作用明显。如果用双音词来作一个对应:例(6)(7)的“易”是“省简”,例(8)是“轻易”,例(9)是“平易”,例(10)(11)是“修治”。但是,一旦离开语言环境,这种形式的局限是很明显的:首先,用甲训乙时,究竟采用的是甲的哪个义项,没有相关的标志可以显示,又没有语境可以补足,特别是当同一个义项用不同的词语来做训释词时(如例(6)和例(7),例(10)和例(11)),更难归纳到一起。其次,前面已经说到,在同一个词汇系统里,完全相同意义的两个词项是没有的,因为在两个词语之间,缺少了相互之间的区别特征,以甲训乙只能是不完全训释。
三 古代训诂的标准词义训释方式——义界
以上两种随文释义的方式属于言语意义的解释,不适合脱离语言环境的语言意义解释,也就是不适合字典辞书的释义。传统字书和现代辞书里都有一些词条释义照录那些随文释义的材料,实际上是分不清言语意义的解释和语言意义的解释造成的。但是,言语意义的解释与语言意义的解释又不是没有关系的。言语是语言的实际存在,是语义实际的载体,而脱离语言环境的贮存意义却是虚拟的,是言语意义的进一步概括,它只是在一般意义上反映词义。
字典辞书从实际的言语中概括出语言意义时,就把词义从使用状态转变为储存状态。这时的词是作为全民语言的建筑材料而存在的,在它的意义中,保存了使用该语言的人们对这个词所标识的事物全部的共同认识和感情色彩,包括了全民族统一的对于用这个词命名的事物的各种经验,这时的词义,发生了三方面的变化:
首先,它没有了语言环境的限制,解除了句义带来的规定性,因而只能是多义的。这就存在一个为它划分义项的问题。
第二,它失去了语言环境为之提供的具体内涵,不再有说话者个人希望展示的具体的情感和形象的体验,因而必然丢失了那些经验性的内涵,具有了概括性。
第三,随着经验性的个性化内涵的消失,它失去了具体的所指,产生了词的广义性。
这时的词义训释标准的方式是义界。我们把训诂的义界归纳为“主训词+义值差”,(注:详见王宁《训诂学原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年第二版,97页。)例如下面的古代字书训释:(注:以下9 例取自《说文解字》。)
(12)饯,送(主训词)去(义值差)也。
(13)缺,器(义值差)破(主训词)也。
(14)磬,器(义值差)中空(主训词)也。
(15)京,人所为(义值差1)绝高(义值差2)丘(主训词)也。
(16)婴,颈(义值差)饰(主训词)也。
(17)簪,首(义值差)笄(主训词)也。(笄,簪也。)
(18)观,谛(义值差)视(主训词)也。
(19)顾,还(义值差)视(主训词)也。
(20)瞻,临(义值差)视(主训词)也。
中国古代训诂家所做的义界大都简短、准确。义值差一般是一个,很少超过三个。我们从《说文解字》中选出3016个训释, (注:这3016个训释是参照现行汉字中的常用字表和常用单音词表大致选出的。 因为小篆的字与现行汉字的记词职能并不完全一致,所以这里不是穷尽性的选择。)含义界1615个,其中:
1个义值差的1405个 88%
2个义值差的 161个 10%
3个以上义值差的 49个
2%这说明,训诂家集数千年的训释实践,在描述词义、表述意义内涵方面,已经找到了切合汉语实际、反映语义规律的方法,需要对他们的方法加以总结,以充实和完善现代辞书学的释义理论。比较起来,现代汉语的单语词典虽然一般也是采用义界的方式来释义,但在释义方法上理性的成分还很不足。且看以下一组单音节动词的释义:(注:以下“甲—己”例A项取自《现代汉语词典》,B项取自《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语文出版社1998年版),C项取自《应用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0 年版)。
甲 A剔,从缝隙里(义值差1)往外(义值差2)挑(主训词)。
B剔,(从缝隙或孔洞里)(义值差1)往外(义值差2 )挑(主训词)。
乙 A挑,用细长的东西(义值差)拨(主训词)。
B挑,用带尖的或细长的东西(义值差1)先向下再向上用力(义值差2)○(注:原训释此项不出现。)(主训词)。
丙 A拔,把固定或隐藏在其他物体里的东西(义值差1)往外(义值差2)拉(主训词)。
B拔,○(义值差)抽出,拽出(主训词)。
丁 A拨,用手脚或棍棒等(义值差1)横向用力(义值差2), 使东西移动或分开(义值差3)○(主训词)。
B拨,用手脚或棍棒等(义值差1)横向用力(义值差2),使东西移动或分开(义值差3)○(主训词)。
戊 A提,垂手(义值差1)拿着(主训词)(有提梁、绳套之类的东西)(义值差2)。
B提,垂着手(义值差)拿(主训词)(有提梁、 绳套之类的东西)(义值差)。
己 A挖,用工具或手(义值差1)从物体的表面(义值差2 )向里用力(义值差3),取(主训词)出其一部分或其中包藏的东西(义值差4)。
C挖,1.从地面(义值差1)向下(义值差2)刨或掘(主训词), 使形成坑或沟(义值差3):~坑,~沟,~隧道。2.向着物体里面(义值差1)用力(义值差2),取(主训词)出其中包藏的东西(义值差3):~人参,~河泥作肥料。
观察以上义界可以看出,现代汉语辞书所作的义界,义值差的数量明显增多,义值差的内容也向描写过细发展。这一方面是因为现代词语的意义系统比古代复杂,同一义场中的词语量有所增加,选择一个义值差不足以与其他词语全部对立的缘故。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义界,由于没有吸取传统训释的合理经验,原则掌握不力,语言结构的优化程度不足,产生了义值差冗余的现象,反而影响了释义的准确性和适宜性。
四 义界的语言结构及其优化的原则
义界的基本语言结构是:主训词(Z)+义值差(C)。这个公式的意义是在一定的范围内,通过比较,确定被训词的特征,使被训词的训释成为惟一属于它的意义描写。主训词的作用是选定与被训释词比较的其他词语,或选定与它比较的词语所包含的范围。义值差的作用是确定被训词与训释词语不同的特征。
具体说,义界的主训词,有两种选择法:
(一)采用被训词的上位词。它的作用,是把被训词放在一个包含它在内的义场里,以便确立与之相区别的词语的有限范围;也就是说,把它放在同类义场里与同类的其他词比较,上述《说文解字》(15)(16)(18)(19)(20)各例属此,如例(15)“京”采用“丘”作主训词,《说文解字》“丘”训“土之高也”,是“京”的上位词。(注:《说文解字》在“丘”的训释后特别加注说它是“非人所为也”,根据这个提示,“丘”似乎是“京”的并列概念。实际上,“丘”与“京”的关系符合训诂“对文则异,散文则通”的原则,在一般情况下,“丘”指土的丘陵,有别于石山;所以它有资格作“京”的主训词。)它确定了包括“京”在内的类义场。在这类义场里,“京”不但因为是“人所为”而区别于自然形成的土丘,而且因为它的高度超过其他土丘而区别于其他人为的土丘。我们可以用如下公式表示这第一类义界:
Y=ZL-(C1+C2)表述为:“京”的义界(Y)是在“丘”所确定的类义场(ZL)中, 以“人所为”(C1)和“绝高”(C2)为独特特征而区别于这个义场中的其他词的。
同样,第(16)例“婴”的义界(Y)表述为:“婴”的义界(Y)是在“饰(饰物)”所确定的义场(ZL)里,以专门放在颈部(C )为特征而区别于其他饰物的。
(二)采用被训词的同义词。它的作用是在选择一个与它意义最接近的词,然后把最能表示二者区别的特征词选为义值差,也就是突出二者最明显的差别。上述(12)(13)(14)(17)各例属此。 如例(12)选择“送”作主训词,是“饯”的同义词, 但“送”可以有各种原因,“饯”则必须是以“送人离去”为目的,“去”则成为“送”与“饯”比较后择定的特征词,即义值差。我们可以用如下公式表示这第二类义界:
Y=ZA-C第(12)例可以表述为:“饯”与“送”(ZA)同类义近,而以“送别(去)”(C)为目的。同样,第(17 )例可以表述为:“簪”与“笄”(ZA)是同类的饰物, 而“簪”的特点必须是插在“头(首)”(C)部。
在明确了义界的基本语言结构之后,我们可以来讨论辞书在使用义界这种释义方式时如何是最优化的。一个优化的义界主要是选择好主训词和义值差。这种选择必须遵循的原则是:
第一,主训词与被训词临近的原则。采用上位词时,要尽量选用临位词——即,最靠近被训词的类词,如(18)“观”(19)“顾”(20)“瞻”三例,同时选择临位词“视”做主训词;采用同义词时,要尽量选用差异最小的同义词,如(12)(17)两例,(12)“饯”选择差别最小的同义词“送”,(17)“簪”选择差别最小的同义词“笄”(不选择临位词“饰”,是因为汉代“首饰”已有饰物统称的意义)。义值差的择定,是为了显示它与已确定义场中其他词语的区别。这种区别特征,要根据主训词所画定的范围来考虑。所以,主训词选择得越与被训词临近,义值差就越易简单、明确。
第二,义值差与主训词义场中其他词语全部对立的原则,也就是独特性的原则,如果与义场中每个词去一一对立,必然增加义值差的数目;只有采用总体对立的原则,义值差才可以既能反映意义特征,数目又减到最少。例如,“婴”与其他饰物的总体差异是它戴在颈部的部位特征。
第三,整个义界最大限度概括的原则。也就是将言语意义中经验性的具体内涵全部抽象出来的原则。这里用上面所举的现代辞书所举的“己”组A、C两项加以比较:C项明显抄袭A项,为了与A项保持差异, 故意把B项拆成两个义项。第一项选择“刨或掘”为主训词, 把“向下”作为义值的特征,第二项选择“取”做主训词,把“向里”和“取出包藏的东西”作为义值差与第一项对立。其实,挖坑、挖沟、挖隧道,都要取出里面的东西,如果挖窑洞,就得向里用力,而挖人参、挖河泥也是向下用力的。两项没有差异,他们之间的差异在第一项以挖成者为追求目的,第二项以挖出物为追求目的。这种差异属于言语意义的经验内涵,应当把它全部抽象出去。分成两个义项,是因为对言语意义抽象不足致误,属于画蛇添足。A是作得比较好的,但进一步分析, 也有抽象不足的毛病:挖的动作特征在于向里用力和向外取出,用什么工具和从什么地方开始,都属于具体化的内容,不应放入概括词义内。且看段玉裁对相当于现代汉语“挖”的“抉”字所做的义界:“抉者,有所入以出之”,可以说,概括到家了。
五 训诂学、辞书学与词汇语义学
人们往往用辞书的释义来作为语义分析的例证。其实,辞书的释义与词义结构的分析是在两个目的、两种原则下进行的。西方的词汇语义学对词义结构进行分析,是希望找到词在词汇系统中的位置,因而要对义位的内部结构加以切分,用义素的组合式来表述它的诸多特征。释义的目的不是结构分析,而是充当传意的沟通者,所以既要采用义素分析的方法,又不需要进行完备的义位结构分析。义界先选定一个接受主体已知的范围,并以被释词与其中一切词对立的原则确定其区别性特征,即可达到沟通的目的,所以,古代训诂释义大多采用两分法,从不采用烦琐的细胞式分解。一个好的义界,除了遵循上述三项原则外,还必须遵循用已知——也就是常用易懂的词语——来解释生僻词的原则。
义界的优劣还必须用是否体现词汇和语义的系统性来衡量。例如,上述例子在训释动词“提”时,把“垂手”当成它的义值差之一,而在用“提”训释“拔”时,“垂手”这个义值差却取消了。做释义的人也许会以为,“提”做被训词时是“提着”,“提”训释“拔”时是“提起”。其实,“提着”和“提起”就概括义而言,完全是一个义项。这就需要检验释义者对“提”的词义的把握是否准确。仔细分析,“提”的特征不在于是否垂手,而在着力的方向必须向上,以抵抗下方物件向下的力。
释义属于应用领域的操作,不但需要理论的自觉和完善,还需要熟练的操作技术。释义又是对词汇语义学的一种验证,将给汉语词汇语义学提出新的课题。这些,都需要继承训诂学的丰富经验。训诂学也必须借鉴西方词汇语义学适合汉语的部分,运用自身丰富的材料,走出经验,作出理论的总结,提高自身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从这里可以看出,训诂学、辞书学和词汇语义学的相互吸收和相互沟通,既是基础理论对应用的指导,又是应用科学对基础理论的检验;这是本世纪应当努力追寻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