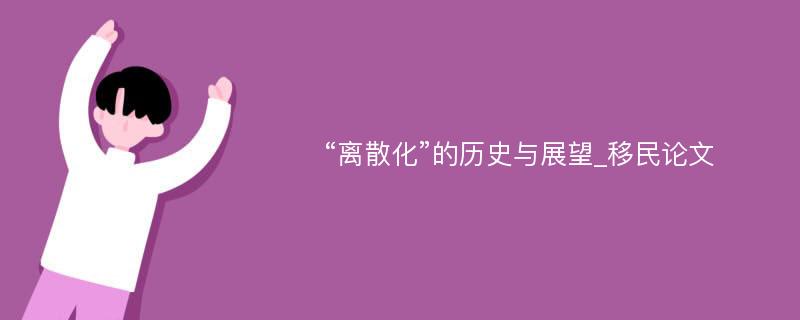
“离散”三议:历史与前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离散”一词在现当代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中的用法,源于《圣经·新约》关于犹太人于纪元前586年被巴比伦人赶出朱迪亚(Judae)和纪元前135 年被罗马人驱离耶路撒冷的记述,它强调丧失家园后四海为家,在迁徙过程中创造新生感知和另类文化身份的社会与心路历程。就此意义来说,“离散”与“移民”是两个十分不同的概念,因为后者涉及的迁徙过程往往以落地生根为目的;而前者则把注意力集中于离散过程本身,视漂泊为基本生存条件,同时刻意凸显离散主体与母国和移居国之间的心理和政治距离。“离散”一词有多种含义,可用来描写“离散”的实际经历,也可用来说明“离散”的文化特征,还可用来指离散中的群体本身,或是探究该群体在其原住国或其文化渊源之外生活时的内心感受。尽管“离散”的概念近来已经成为西方创作与批评话语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但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具体和行之有效的表现手法或分析范畴。实际上,“离散”在这些话语中的重要作用主要是通过一些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理论视角的普及得到体现的。这些理论视角包括“放逐”(exile),“游牧主义”(nomadism),“迁徙”(migration),“介于两者之间”(in-betweenness),“去领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关于“移民”(immigrant)的种种比喻,以及“跨国状态”(transnationality)等。当代西方文化研究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后现代批评。出自该语境的“离散”视角与概念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这种方法论中的反人本主义(antihumanist)美学和意识形态倾向。本文的目的是从历史的角度,就“离散”概念在现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中的地位、作用和演变进行梳理、综述和评价。
二、“离散”与现代主义理念和艺术实践的渊源
“放逐”与“游牧主义”是欧美现代主义文学的两个核心概念,也是使“离散”形象化和具体化的两个重要修辞手段。这两个概念的思想基础就是所谓的“错置”(displacement)感。这种感知体现在许多现代主义作家的生活经历和审美诉求。而现代主义作家对资本主义社会与文化持强烈否定态度,是受到了19世纪欧洲一些哲学思潮的影响。比如,丹麦神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认为,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挽回的商业化、集群化和非人化倾向,人丧失了起码的内在精神支柱和道德判断力,成为该社会通过出版印刷业建构起来的的“虚幻公众”(phantom public)的一部分以及听凭外力摆布和支配的被动群落。对克尔凯郭尔来说,现代社会的人为了保存自我的完整,就必须与堕落的世界保持距离并回避一切形式的社会参与,从而通过自我放逐的方式将被焦虑和负罪感困扰的人造就成一个能体现存在真实性的“孤独个体”。① 在尼采的哲学体系中,人是悲哀的,并且与社会处于完全分离的状态,而人的自由则只能来源于其对资本主义肌体的自觉和彻底的否定。尼采一方面肯定生活的悲剧性本质,另一方面又认为忍受悲痛是面对生活的唯一出路。他认为,对孤独的恐惧使人难以克服与被动群落为伍的本能,而自由的关键则是忍耐分离,拒绝沦为受现代文化与社会习俗规范的芸芸众生。就此意义来说,“孤独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崇高的冲动”。② 这种尼采式的“英雄”气概可以概括为:尽管自我在资本主义的挤压之下已荡然无存,但它仍可通过一种近乎自虐的方式,将孤独升华为一种美学原则,从而以倒错的方式重新肯定生活。克尔凯郭尔与尼采哲学思想中这些游移在社会—政治放逐与美学—心理放逐之间的批评意识,在许多有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家的艺术实践中都能见到踪影,如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双面人》(1846)中描写的通过恐惧和自我精神分裂症与社会保持距离的小职员,卡夫卡在《变形记》(1915)中塑造的一夜之间变成昆虫却还担心上班会迟到的公司雇员,以及海明威在《太阳还要升起》(1926)中用阳痿对现代人贫瘠、龌龊的内心世界的嘲讽。
批评家们有时将“放逐”区别于“移居”(expatriation)。前者指作家迫于外界压力而不得不背井离乡;后者指作家选择一时或永久性地脱离母国或放弃原国籍。乔伊斯本人以及他在《青年艺术家的肖像》(1916)一书中塑造的主人公史蒂芬·迪达勒斯,就是自愿切断自我与家庭义务、宗教信仰、阶级属性以及地域从属感等传统纽带之间关系的现代主义式人物。而乔伊斯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克服他认为阻碍艺术家成长的种种社会因素,并通过自我放逐营造出一种能表现其作品现代性的心理和美学距离。海明威、菲茨杰拉德、斯泰因和多斯·帕索斯等被称为“迷惘的一代”的美国作家,则出于他们面对非理性的战争的无能为力,自愿流亡到巴黎,透过充满矛盾和暧昧的时空来书写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与工业社会的疏离感。斯坦纳(George Steiner)据此将现代主义文学看成是一种“领土之外的”(extra-territorial)艺术。③ 严格地说,上述作家的经历用“移居”来形容似乎更为贴切。相比之下,康拉德和纳博科夫的社会与艺术生涯更能体现放逐的某些内涵。比如,康拉德在法国和英国的创作活动,以及他常年在海上漂泊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是他双亲因反对俄国沙皇暴政而被逐出波兰及他本人在放逐中出生并失去双亲的某种存在表征。而有上流社会背景的纳博科夫从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流亡到处于现代主义运动中心的伦敦、柏林、巴黎,随后又来到新批评理念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高等学府任教和写作。尽管其晚期创作的美学风格已经开始具有某些“元小说”(metafiction)的特征,但他作品中那些迷宫式的难题、双重性和关于性欲的大量描写,都可追溯到现代主义流亡传统通过象征主义手法对丧失语言和社会秩序所作的美学回应。④ 尽管“放逐”与“移居”之间存在着某些差异,但它们所传达的断裂与失落感却不约而同地呼应了现代主义对危机四伏的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以及对人类生存状况与再现手段的深切关注。
1923年,以犹太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法兰克福成立“社会研究所”(后称“法兰克福学派”),这是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关系十分密切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放逐”概念的来龙去脉。该所在霍克海默于1931年主持工作之前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此后,又转向社会哲学。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实施反犹政策,该研究所于是先迁到日内瓦,后移往巴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成员又陆续来到美国。在某种意义上,该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阿多诺就“放逐”问题所作的一些论述可以说集中概括了都市现代主义“错置”感的政治含蕴。阿多诺在《最低境界的灵魂:对被损毁了的生活的思考》(1951)一书中认为,放逐对个人的损毁能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剥夺了作家的语言能力,背弃了培育知识的文化与地域,并使新世界变得深不可测。他还认为,离散中的知识分子应培养一种能超越哀伤和正视现实的批判意识。也就是说,离散的个体只有在与其母国保持距离的情况才能重新获得关于生活的灵感。就此意义来说,与过去发生决裂固然使人失去一些实质性的东西,但这种决裂在所难免。阿多诺于是宣称:“住所一词,就其本意来说,现在已经失去了一切可能性。我们借以成长的传统住所已变得越来越难以容忍:因为它的每一丝舒适感都是通过对知识的背叛得来的;而它的每一点安全感也是对家族利益俯首听命的产物。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⑤ 阿多诺将距离与隔阂作为产生批判性真知灼见的前提,这是对“错置”感的一种不折不扣的现代主义回应。既然住所已经消失,那么就只能在写作中寻找归宿。阿多诺的这种思路与现代主义者试图通过艺术的“自主性”重新实现自我的说法是一脉相承的。
还值得一提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就放逐所作的思考。其中较有影响的是他在《技术复制年代中的艺术作品》(1936)一文中的观察,即19世纪后半叶不断发展的大众传媒复制技术(尤其是该技术在电影中的运用)使艺术作品的“灵光”(aura)——即艺术的独特性及其具体历史环境——丧失殆尽。这种情况使艺术作品赖以存在的传统发生衰落,并使人本主体陷入了空前的危机。本雅明认为,更新人本主体的潜在希望存在于下面两种倾向的互动之中:一是当代的“大众”运动方式;二是技术复制结构本身。在此,“大众”指的是“共众,”即电影的观众;“技术复制结构”强调的则是其为使电影便于观赏而具有的某种信息“发散”特征。这两者之间互动的实质则是同时被“摆置”和被“错置”的矛盾状态:前者暗示出观看的欲望;后者则构成了对这种欲望的阻碍。此互动过程于是和某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状态发生了联系,从而为探索“缝隙”地带提供了可能。⑥ 本雅明在这篇文章中的分析深受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关于现代性(modernity)往往通过影像化和抹杀距离及差异来征服客体这一论点的影响。而他关于如何在技术复制年代更新人本主体的思考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克尔凯郭尔对科技社会的批判,以及他为此所建构的游牧意象。尽管本雅明对放逐的论述比较抽象,但他的观点却影响了一些重要的离散评论家的理论视角。比如,周蕾(Rey Chow)在《写作离散:论当代文化研究中的介入策略》(1993)一书中就拓展了本雅明的上述分析,认为“错置”应当成为当代跨文化批评实践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因为与“错置”感密切相关的“离散意识”并不是某种历史的巧合。相反,它是西方人文知识分子为了有效地与东方主义和第三世界本土主义(nativism)同时划清界限所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现实。⑦
三、“离散”在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中的应用
如果说现代主义文学中的“放逐”想像是通过挖掘自我潜能和探索非理性领域来实现的,那么,这种想像在部分继承现代主义理念的后现代主义者手中就必须寻找新的出路才能得以延续。因为后现代主义对那种坚信内在真实性的康德式的自我并不感兴趣,对与人本主义纠缠不清、自恃清高的现代主义主体性更是充满了不屑与敌意。反之,他们极力强调人与知识、权力结构之间的纠结与交织,以及人与外部世界的共谋关系。然而,声称回归历史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者们——如福柯(Michel Foucault)、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等——并没有将外部世界对人施加的种种限制作为争取自由的一个物质性起点,而是千方百计地以回避这些限制的方式来保护他们认为具有内在颠覆性的所谓“差异”。“差异”是后结构主义通过部分挪用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关于符号的某些论述而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后结构主义者认为,索绪尔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1)他指出了符号中意指与能指之间的武断关系,差异性是意义生成的源泉,而不必依赖任何客观的指涉功能。2)他据此强调说,传统语言学不仅将言语(speech)凌驾于书写(writing)之上,而且还强行使语言的历时性(diachrony)隶属于其共时性(synchrony)。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将语言符号系统中的这种层级化关系称为“逻各斯中心论”(logocentrism)。而解构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补充式分化”(supplemental differentiation)的程序,在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不停顿地揭示并颠覆体现这种关系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德里达将这种“补充式分化”的解构运作过程称为“延异”。
后结构主义者认为,传统语言结构的压抑性、统合性和排他性,与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施加的种种限制和压抑如出一辙。因此,他们的一个中心任务就是要突破结构主义通过“文本”(text)所重新设置的形式主义指涉界限,使意义摆脱文本而走向“文本性”(textuality)。后结构主义的“文本性”中不存在内在与外在的区别,也不存在能妨碍或阻止“延异”运作的终点或底线。在此基础上,德里达提出了两个对离散研究至关重要的概念。一是“越界”说。他认为:“没有任何意义是一成不变的;所有边界的内侧和外侧都不是天造地设的结果”。其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文本的互涉性根本就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极限”。⑧ 边界是差异的标志,而边界的消失则是差异性得到释放的必然结果。随之而来的,便是后结构主义者对所有局限性的普遍质疑,因为客观指涉已经被文本化了的“痕迹”(trace)所取代。德里达的“越界”概念在象征意义上与“离散”概念不谋而合,因为前者显示出一种失去中心,能自由穿越变动中的不同形构,并永久性地迁徙、游牧和流动的状况,所以被大量采用到文学批评与文学再现中。例如,非洲裔美国批评家贝克尔(Houston Baker,Jr.)便借助德里达的某些概念提出了一种可以称为“布鲁斯摇摆乐”的批评方法(blues criticism)。该批评方法有两个重要的意象,即铁路调车场的换道室和铁路交叉口的标记。这些意象一方面体现了德里达的越界说,另一方面又使人想起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成千上万被剥夺土地的非洲裔美国分成制佃农(share-croppers)从南方乘火车北上求生的情景。在贝克尔看来,这种处于运动状态、不断被错置又不断实现自我建构的过程最能体现德里达的延异理念。⑨ 二是“散播”(dissemination)概念。这是德里达解构程序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即在所有指涉都不复存在的情况下,意义永远不能得到实现的那种状态。处于“散播”状态的语言不断地打破平衡,并以差异的形式无拘无束地永久性流散。一些深受解构主义影响的后殖民批评家喜欢在“散播”的字面上做文章,将dissemination写成dissemiNation,以此来显示“越界”的必要性, 以受他们对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或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批判。
霍米·巴巴(Homi Bhabha)是一位较多论及离散问题的后殖民批评家。他在《文化的处所》(1994)一书中将离散、难民、迁徙与第三世界等范畴看成是受到西方二元对立思维方式错置、贬低和延后的他方(alterity)。在他看来,后殖民批评家借以展开解构运作的文化的处所是一个既能跨越国界又能任意实现表意转换的混杂化的逾越性(transgressive)场域。他认为,在此文化场域中进行文化批判兼有勉强生存和“补充式分化”的特征:它一方面使人感到忧心忡忡,另一方面又总带有一些令人欢愉或顿悟的瞬间时刻。在这种动态的、充满机缘性(contingent)和阈限性(liminal)的补充式空间中,时间是非序性的(discursive)或是延后性的,从而为后殖民批评再现文化差异和建构主体创造了必不可少的居中性(in-betweenness)和分离性(disjunction)。而这种状态也正是巴巴想像中的庶民阶级(the subaltern)能在“补充式分化”的中介下实现去殖民化的理想境界。总起来说,巴巴批评语库中的“离散”、“难民”、“迁徙”与“第三世界”等词汇并不具有物质的含义;恰恰相反,它们不过是解构主义理论中所谓“重复式主体际时间性”(iterative intersubjective temporality)的某种语言效应而已。因为正如巴巴本人所言,他调动这些词汇的目的不是要用社会学的方式介入政治与历史的权力结构,而是想通过对符号的重新铭写(reinscription)来质询现代性的两个基本前提假设——即关于权力和责任的语言——从而达到改写社会时间性的目的。⑩
另一个颇具影响的后结构主义视角是德勒兹(Gilles Deleuze)与夸塔里(Felix Guattari)对现代主义游牧主义概念所作的伸展。他们在《反俄狄浦斯》(1972/1983)及另外一些著作中,借助心理分析方法提出了关于“去领土化”的观点,目的是为了摆脱僵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并使反本质化的主体能不受羁绊地自由运作。(11) 德勒兹与夸塔里采用了若干隐喻手法描述上述程序。其中较著名的就是他们用植物学中“地下茎”(rhizome)概念所作的比喻。也就是:钻入地下,根须并茂,四处潜行,然后爆发式的分散和传播。德勒兹与夸塔里认为:“地下茎的发育即没有开始,也没有尾声。它总是处于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状态,一个中强音节。树是依附性的,地下茎则是一种联盟”。(12) 作为一个富于政治寓意的意象,地下茎与西方人本主义传统中以树为想像蓝本的系谱学(genealogy)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为这种比喻能与国家—社群—家庭的既定空间范畴发生种种非本质化的联系。与此同时,地下茎借以运作的场域则是代表着方言土语(patois)且发育不良的贫瘠、渺无人烟的沙漠。而活跃在这种被西方文明边缘化的地段中的游牧者则是欧洲的吉卜赛人和第三世界的“移民”(immigrant)。在德勒兹与夸塔里的语汇中,吉卜赛人和第三世界“移民”都是遭受错置的象征物,以及自愿置身于现代性之外的“他者”。德勒兹与夸塔里将这种“去领土化”的过程叫作“成为弱方”(becoming the minor)。
法国人类文化史学家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从社会符号学的角度间接地确认了德勒兹与夸塔里关于“移民”比喻的重要性。他认为,移民是错置的“第一受害者”,巨大历史和文化变迁的“清醒见证人”,以及试图走出错置困境的“实验者与创新者”。在此基础上,德塞都认为应当提出一个“我们全体都是移民”的口号,(13) 以凸显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危机的严重后果。比起德勒兹与夸塔里的移民概念,德塞都的有关思考似乎涉及到了错置经历的一些物质层面。但他的这种建构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用来批判现代性的文化类比,因此并不能有效地质询西方社会学中关于“移民”的传统定义,以及被“移民、奋斗、适应、同化、落地生根”这一线性分析范式所掩盖的种种社会与历史矛盾。就此,亚裔美国批评家林玉玲(Shirley Lim)借用萨义德(Edward Said)就“认同”(filiation)和“加入”(affliation)两个概念所作的论述,对“移民”和“离散”之间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说明。(14) 林认为,移民一词的传统定义忽视阶级、种族和性别对移民过程的影响,从而间接地确认了欧美文化价值的权威性和政治现实。萨义德的“认同”概念指的是人类具有某种根植于地域感的繁衍后代的本能。但由于人类与其自身劳动成果(包括他们生育的子孙后代)之间存在着异化关系,“认同”于是充满了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并最终不能实现其物质性。“加入”指的是能自觉意识到上述困境,从而将自我的社会化当成一种与既定家园、宗教和民族—国家保持某种批判距离的做法。林通过萨义德的上述视角,从社会和文化政治的层面再度肯定了“放逐”和“离散”的政治必要性,同时也指出了传统“移民”定义的意识形态局限。(15)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萨义德本人关于“放逐”概念的思考。因为这些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代美国少数族裔作家和批评家对“离散”一词的理解和运用。萨义德的“放逐”理念深受其启蒙导师德国籍犹太学者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的影响,而后者则以精通中古文学和文艺复兴时期德国浪漫主义传统著称。奥尔巴赫于20世纪30年代为躲避纳粹主义的腥风血雨先流亡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战后又辗转来到美国。然而,正是这种艰苦卓绝的放逐岁月和远离家乡的无限怅惘,才使他写出了像《模仿论》(1946)那样的鸿篇巨著。萨义德认为,奥尔巴赫的离散经历具有独特的启示意味,那就是,只有脱离习惯性的社会氛围、文化期许和意识形态规约,作家才能将放逐对自我造成的种种负面影响转换为一种激越的批判意识。(16) 萨义德的这种观点明显地反映了欧美现代主义错置话语在他身上留下的深刻印记。与此同时,这种观点也为他对民族主义的批判进行了铺垫。他认为:“民族主义声称它与某个地方、某个群体和某份遗产具有从属关系,并由此印证了社群能通过语言、文化与习俗创造出家园的假设。民族主义因此避开了放逐,并极力使自身免受其害。”他进一步观察说:“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都起源于某种陌生化状况……而功成名就、志得意满的民族主义却总是以回顾与前瞻的方式为它有选择地将历史串联在一起寻找借口。于是,民族主义便有了开国元勋、带有准宗教色彩的读本、归属性的修辞、历史与地理标记,以及由官方认可的敌人与英雄。”(17) 萨义德在这段文字中对放逐与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论述深刻且发人深省。但它将后者描述成既有同一性又有明确终极目的的做法却忽视了民族主义的不同内部结构及其与霸权千差万别的关系。实际上,某些形态的民族主义根本无法依照既定语言学的修辞范式,按部就班地演化成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萨义德对民族主义不同历史和政治内涵的简约化处理,与美国文化批评界近来对法侬(Frantz Fanon)的“第三类空间”和拉康的(Jacques Lacan)“第三类处所”的提法的过分拥戴,是不无关系的。
四、“离散”的社会性与物质模态
针对“离散”概念在文化批评中的文本化和美学化倾向,非洲裔美国批评家胡克丝指出,这种非历史化的游牧主义实际上是西方社会与政治权力的一种产物。因为“离散”一词本身并不能用来概括美国历史上大规模贩卖黑奴、逼迫印第安人长途迁徙、迫使中国移民颠沛流离、将日裔美国人强制性地重置,以及对大批无家可归的城市游民不闻不问的本质。(18) 美国印第安人批评家克鲁帕特也认为,现有离散模式善于表现文化的多元性和不确定性,但难以准确描述美国少数族裔的实际错置经历与社会及政治霸权之间的关系。(19) 亚裔美国文化批评家圣胡安从另一个角度指出,后现代主义的去中心化运作将混杂性和居中性的感知神秘化,从而使属民阶级从后殖民领土到商业大都会的过渡变得毫无痛苦。(20) 出生于牙买加的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霍尔的《文化身份与离散》(1994)一文,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上述批评家就应当重视离散的历史与文化特殊性所发出的呼吁。在这篇论及黑人在19世纪中后期的环加勒比海大迁徙的文章中,霍尔认为新的文化身份只能产生于文化认同与文化差异的互动过程中。前者指的是寻找共同历史经历和共享文化符码,以便为离散群体提供某种能使他们动荡不安的现状变得相对稳定的参照架构。而这些连续性的因素正是反抗殖民压迫的精神与道德源泉。后者则暗示,离散文化身份不仅是一种历史“现状”,更是一种“呼之欲出的境界”。因为该身份是其在历史变迁、文化形构与权力更迭过程中不断与外界适应又不断被改造的结果。霍尔确信,只有通过文化的断裂和差异性,人们才能深切体会到殖民化的恶果。而试图用某种理想中的家园来界定离散身份的作法则反映了一种过时的、霸权式的“属性”观。换言之,“离散”的含义只能通过承认并接受多样化和混杂化才能得到充分体现。(21)
近年来,“离散”的概念在两个新兴的社会科学领域中得到了高度重视:一是迁徙研究(migration studies),一是跨国研究(transnational studies)。前者主要关心的是在全球范围内政治与经济边界松动对民族—国家内人口变迁和社会形构所产生的冲击和影响,以及民族—国家如何采取对策来应对这些冲击和影响。迁徙研究往往将来自不发达国家的移民、难民和外劳看成是企业式盘剥与种族歧视的受害者。跨国研究的主要兴趣是将全球化作为资本主义企业不断变换其经营策略的表现形式来分析,同时也关注个人、政治及族裔身份重组后所带来的局部影响。著名文化人类学家王爱华(Aihwa Ong)认为,跨国研究注重描述影响到跨越国界行为的一些新的文化逻辑及想像, 以及民族—国家对这些现象的具体回应方式。(22) 王特别强调跨国状态(transnationality)与跨国性(transnationalism)之间的区别。后者主要指全球化状态下的经济、政治及文化过程,以及这些过程的内部机制。而前者则主要指资本主义制度下那种能任意穿越时空且互相联系的文化状态。另一位文化人类学家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进一步指出,这种崭新的全球化经济应当被看成是一个复杂、交叠和分离性的秩序。此种秩序充满了经济、文化和政治的不平衡,并由此产生出种族、科技、金融、传媒以及意识形态等力场(scapes)之间的失衡与断裂。而全球化正是通过这些在想像中能取代民族—国家疆界的力场之间因摩擦互动而出现的缝隙得以蔓延。就此意义来说,经济全球化也必然是一种不均等与不平衡的过程。阿帕杜莱认为,构成这些分离性力场的个人和群体——一旦他们能意识到自身利益——就有可能在微观的意义上影响全球化的性质或进程。(23) 与阿帕杜莱这种意义比较空泛的离散主体性形成对照的是王爱华的“灵活公民身份”的说法。王用手持多本护照的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t)式企业家的实例想说明,全球化所造成的政治与经济不安定感,催生了一种能巧妙周旋于处于各种矛盾倾向之间的灵活的跨国主体,并由此构成了对全球化的讽刺性批判。
尽管王爱华与阿帕杜莱令人信服地使我们了解到全球化的复杂性、多样性和不平衡性,但他们建构的跨国/离散主体,与现代主义者所想像的孤独游牧人和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者精心策划的自我放逐一样,都是一些基本上不受阶级与经济地位限制的投射,因此并不能使离散概念从根本上摆脱那种去语境化的文本嬉游性。日裔美国作家凯伦·山下(Karen Tei Yamashita)的两部小说——《巴西商船》(1992)和《K圈循环》(2001)——似乎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些富于启发性的实例。前者以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艾弥尔,或论教育》(1762)一书为喻,记录了20世纪初日本人大量移民巴西过程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往事。该书将这些日本人的迁徙写成一种多层次的错置经历:他们的巴西之行不仅是对日本现代化进程的拒斥,以及对美国通过《君子协定》(1908)禁止日本人继续移民美国西岸的回应,而且也是出于他们渴望在巴西重新塑造新生文化身份的需要。这些移民在此过程中受到的深刻教育,就是只有不固守已经脱离原来社会环境且变得日益僵化的日本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才能在离散中求得生存。《K圈循环》实际上是《巴西商船》的续篇,讲的是在巴西出生和成长起来的一代只会讲葡萄牙语的日裔巴西人,于半个世纪后陆续回到经济发达但劳力奇缺的祖地日本,以做苦工来赡养国内的亲属。由于他们的不同文化背景、生活习惯和经济地位,这些日裔巴西人在日本受到了难以想像的歧视、限制和虐待,使他们在精神和肉体上饱受折磨与伤害。但他们既不能马上离开使他们身陷囹圄的祖地,又不愿立即回到仍处于新殖民主义羁绊之下、毫无生气的祖国。他们这种深深打上种族与阶级烙印的存在阈限性凸显出“离散”作为一个分析范畴的批判力度。(24) 山下还有一部成书于1996年、以洛杉矶为背景的寓意小说《柑橘回归线》。该书以讽刺的笔法描写了遍布于这座天使之城的无家可归的贫困大军,其中包括一位主动放弃心脏内科医生职位,自愿流落街头,每天站在立交桥上象征性地指挥城市交响乐的日裔美国人。这位医生出生于二战时期关押日裔美国人的重置营(relocation center);而他加入被剥夺基本生活权力的穷人行列的举动,正是作者通过日裔美国人在战时被自己祖国抛弃的惨痛经历,来展示“离散”在美国当代社会生活中的讽刺与揭示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山下的文学描写令人信服地印证了非洲裔美国社会学家布劳纳(Robert Blauner)关于美国存在着的内部错置和内部殖民状况(internal colonialism)的论点。
五、结语
综上所述,“离散”概念在当代美国文学中的应用主要借助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视角中的语言学与心理分析模式,强调不受民族—国家约束的越界行为和能与各种宏大叙事分庭抗礼的文化混杂化运作。它所提倡的微观政治使妇女、有色人种、移民和具有不同性取向的社会与政治话语受益良多。就此意义来说,“离散”概念对考察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和后果的确有着重要的揭示作用,对丰富人们的批评语汇并拓展他们的分析视野也有着独特的贡献。但作为一种批判视角,离散立场往往很难彻底摆脱上述反人本主义思潮中固有的美学化特征,以及它们忽视阶级属性和社会后果的非历史化倾向。斯皮瓦克在谈到目前美国学术界盛行的离散话语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少数族裔在思考其全球性时必须弄清楚这种全球性的受益者究竟是谁和最符合谁的利益。因为离散这个被想当然地看成一种象征着自由和解放的立场定位恰恰标志着它的自我否定。换言之,回避社会化与财产再分配问题的离散经历不过是一种随着当代跨国资本起舞的自由化的文化多元论而已。(25)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离散主体往往是在脱离其原住国和远离殖民统治的情况下进行他们反本质化的文本式抗争,它们的感受和文化政治因此不见得一定就能与其宣示的社会语境发生必然的联系。萨义德认为:“对一种理论突破如果不加分析、接二连三和不分场合地使用,这种理论就会成为一个陷阱。因为即使再高明的见解,它一旦成为时尚,就会在流传过程中被简约、被收编和被体制化”。(26) 依循萨义德的思路,我们可以说,“离散”概念对理解当代文学和文化表述的全球性、混杂性、和不平衡性至关重要,因而成为文化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然而,离散视角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的新奇(如本文所述,它的渊源其实相当古老),而在于它的历史化运用。离散的批判潜能不应当成为我们低估或忽视现实生活中矛盾冲突的借口。就此意义来说,这种理论视角也不见得一定总是高瞻远瞩的批评立场,因此似乎没有必要无条件地去效法或复制。
注释:
① Soren Kierkegaard,Two Ages:The Age of Revolution and the Present Ag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846/1978,pp.91—94.
② Friedrich Nietzsche,Beyond Good and Evil:Prelude to the Philosophy of the Future,trans.R.J.Hollingdale.Hammondsworth,England:Penguin Books,1973,p.195.
③ Malcolm Bradbury and James McFarlane,“Preface,”in Modernism:A Guide to European Literature,1890—1930,eds.Malcolm Bradbury and James McFarlane.New York:Penguin,1976,p.13.
④ “Metafiction”一词出自Linda Hutcheon的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1988)一书,用来指后现代小说通过有意识地写作关于小说的小说来回归历史的美学特征(5—7)。
⑤ Theodore Adorno,Minima Moralia:Reflections on a Damaged Life,trans.E.F.Jephcott.London:NLB,1974,38—39.该书名部分挪用了亚里士多德的Magna Moralia(即《灵魂论》)一书的标题。
⑥ Samuel Weber,“Mass Mediauras:or Art,Aura,and Media in the Work of Walter Benjamin,”in Walter Benjamin:Theoretical Question,ed.David S.Ferri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29—34.
⑦ Rey Chow,Writing Diaspora:Tactic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Bloomington: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1993,p.7,p.15.
⑧ Vincent B.Leitch,Deconstructive Criticism:An Advanced Introduc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pp.118—119.
⑨ Houston Baker,Jr.,Blues,Ideology,and Afro-American Literature:A Vernacular Theor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pp.4—8.
⑩ Homi Bhabha,Location of Culture.New York:Routledge,1994,pp.185—189.
(11)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Anti-Oedip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trans.Robert Hurley,el.at.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72/1983,II.
(12)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A Thousand Platea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trans.Brian Massumi.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0/1987,p.25.
(13) Winifred Woodhull,“Exile,”Yale French Studies 82 (1993):11.
(14)(16)(26) Edward W.Said,The World,the Text,and the Critic.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pp.16—24,pp.6—9,p.239.
(15) Shirley Geok-lin Lim,“Immigration and Diaspora.”An Interethnic Companion to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ed.King-Kok Cheung.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p.294—297.
(17) Edward W.Said,“Reflections on Exile.”Out There:Marginalization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s.ed.Russell Ferguson,et.al,Cambridge:Mass.:The MIT Press,1990,p.359.
(18) bell hooks,Black Looks:Race and Representation.Boston:South End Press,1992,p.173.
(19) Arnold Krupat,Ethnocriticism:Ethnography,History,Literatur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pp.122—123.
(20) E.San Juan,Jr.,From Exile to Diaspora:Versions of the Filipino Exper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Boulder:Westview Press,1998,pp.191—193.
(21) Stuart Hall,“Culture,Identity,and Diaspora,”in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pp.394—396.
(22) Aihwa Ong,Flexible Citizenship:The Cultural Logic of Transnationality.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9,pp.1—12.
(23) Argun Appadurai,Modernity at Large: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pp.33—43.
(24) 见Jinqi Ling,“Forging a North-South Perspective:Nikkei Migration in Karen Tei Yamashita's Novels.”Amerasia Journal 32.3(2006):1—22.
(25) Gayatri C.Spivak,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396—402.
标签:移民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移民欧洲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文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读书论文; 萨义德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