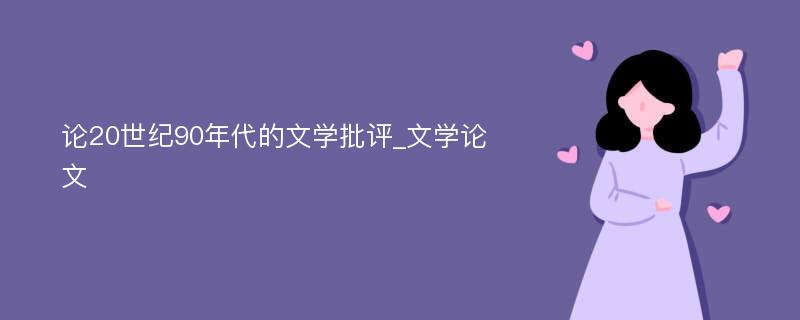
论90年代文学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看待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学批评,如何评价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这些问题在90年代末,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重视,或者说,上述这些问题,是被一种既定的价值迷雾所遮蔽着的。人们只听到一片批评90年代的声音,而很少从文学批评自身的增长角度,认真审视文学批评在90年代这10年间的变化。只有在新世纪来临之时,当人们听厌了那种毫无内容的高调批判之声,想回过头来,仔细寻思,90年代文学批评是否真是像一些人所说的那么不堪时,或许人们才会意识到,90年代文学批评是值得认真回顾的,其鲜明的个性和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刚刚过去的那个“新时期”。
一
那么,90年代的文学批评到底有些什么样的进展,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在我看来,最大的特点,就是分裂。人们再也不可能像梳理“新时期”文学批评那样,找到一种带有主潮特征的文学批评潮流了。90年代的文学批评已经脱离了那种主潮式的生长方式,而分裂出多种多样的话题,多种多样的表现形态和多种多样的价值取向。这里所谓的多样性,是就文学批评具有多样发展的精神空间而言的。从“新时期”过来的人们,对文学批评最熟悉的回忆,就是文学批评的批判性。不管在什么意义上界定这种“批判性”,事实上,对文学批评而言,批判性只是文学批评的重要表现之一。文学批评的发展空间有着远比所谓“批判性”更为辽阔的思想空间,我们甚至可以说,文学批评的主要价值还在于不断为我们的艺术想象和审美感受提供具有前瞻性的精神动力。这种前瞻性的思想是通过批评家不断与当代艺术的对话,从中敏锐地感受到,并形诸文字的思想。从文学史的进程来看,历史上那些优秀的批评家,都具有一种超凡的艺术感受力,这种感受力,直接体现为批评家在对同时代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敏感,能够不为既定的价值观念所淤,排除陈见,提炼出那些不为时人所看重,或不为时人所注意的新的思想萌芽及审美胚胎。这里所谓的新,不是人云亦云的抽象东西(就像没有一个批评家会反对创新、创造等等概念一样,但什么是新,却是很少有人作出明确界定,这样所谓的新,就是一种毫无疑义的抽象概念),就其一般特征而言,就是前代人所忽略或未曾经历的经验和历史过程。假如从这样的视角来看待90年代的文学批评的多样性,人们会注意到,9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的确有着许多值得注意和重视的地方。
第一,90年代的文学批评尽管呈现出非主潮式的思想增长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90年代的文学批评是一盘散沙,没有自己的建树,没有自己的思想特征。没有主潮这种文学现象,事实上恰恰意味着90年代的文学批评是遵循着思想自身的生长方式在发展。对于习惯于在一种传统的宏大思想体系下生活的人们,可能总以为人的思想只能按照一种总体或整体的思想系列来安排自己的思想,换句话说,他们在思考问题时,首先要确定现在的时代思想是什么,然后再来确定自己该思考些什么。这些人总在寻找一些所谓的思想热点和具有广泛社会效应的重大论题。但事实上,真正的思想领域的问题,精神领域的问题,包括文学创作、文学批评问题,并不总是以一种总体或整体的面目体现出来的,我甚至认为,对文学批评、文学创作而言,其增长的最常见的方式,是潜在的、沉默的、累积的和个体的,也就是说,是一种带有个性气质的个体思想活动。而那种振臂一呼,应者如云,由几个所谓的思想人物圈定一二个问题,然后大家围绕这一二个问题进行探讨的思想生长方式,大概只有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思想年代才存在。对于现代社会,特别是对于90年代的思想生长氛围而言,这样的思想增长方式,可能已经成为一种过往烟云般的历史记忆了,即便有人神往这种思想着魔的神圣岁月,即便有人发出“青春无悔”、今不如昔的深深叹息,我想今天的人们实在已经无意于也不愿意沉浸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之中了。思想首先是属于思想者自己的东西,文学批评的思考自然也是首先属于批评家自己。批评家关注什么问题,他选择哪些问题作为他思考的对象,是由批评家个人的艺术趣味和个人经历所规定的,而不是由什么抽象的总体性思想来安排的。这些道理,可以说人人皆知,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但是在对待具体的文学批评问题,特别是涉及到具体的批评家的批评行为时,不少人似乎将这一切都置之脑后,变得非常地健忘。他们总在抱怨90年代的文学批评缺乏所谓的深度和力度,也就是那种可以让大多数人依赖的总体性思想,但他们似乎没有想过诸多批评家的艺术趣味和探讨的问题,怎么可以以一种思想面目、一种表现形态呈现出来。相对于群体的轰鸣之声,作为个体的批评家的声音当然是细微的,而且所探讨的问题有时看来也完全属于个人的兴致所至,没有什么直接的社会效应。但这里却包含着每一个批评家对自己生活的真实体验,以及由这种体验而生发的审美思考。有些人士总在担忧,批评家们只顾自己的思想兴趣,会不会陷于无聊,会不会缺乏一种社会责任感,会不会对社会大众的生活状况缺乏起码的道德热情?我想,这种担忧其实是完全多余的。如果一个批评家的文学思考是与他自己的个人生活相对立,或者说,批评家的个人思考是一回事,文学批评的社会情怀又是一回事,在这样的状况下,一个批评家哪怕真的服从了所谓的社会责任的要求,暂时抑制自己的内心要求,这样产生的文学思考不仅不会真正有生命力,而且也说服不了普通读者。事实上,即便是文学史上最讲究性情、最看重个人艺术趣味的批评家,只要他是认真思考艺术问题的,就不会丧失一种关注社会的热情。因此,在上帝死了之后,人各行其事,尽管没有一个明确的总体方向可依靠,但对于每一个人而言,需要依据自己的判断来作出精神选择。这种选择,从表现形态看,当然没有整齐划一的思想和一统时代的思想来得有力和具备美学效果(诸如深刻、有力度等等美感),但多路向分散的个体思想行为,即便造成批评个体之间缺乏一种共同对话的现实基础,对文学批评而言,也不是什么坏事,甚至可以说是一件幸事,因为它避免了思想一统。而且,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进程稍有记忆的人,恐怕都会记得,对中国文学批评限制最多的,不是什么批评家的个体思想探索太多而导致的思想混乱,而实在是思想一统的年代太多太持久,以致许多人习惯以一种群体或“我们”的思想方式来思考问题,体现批评家个人情感活动和艺术趣味的批评反倒是凤毛麟角了。从这一意义上讲,没有主潮的90年代文学批评比新时期的文学批评有更多的进展,“新时期”尽管是一个伟大的思想时期,但“我们”的方式和口吻,依然缠绕在文学批评的字里行间。90年代是一个脱胎换骨的时代,“我们”在批评中越来越无力,甚至连那些真诚的批评家都感到“90年代的文学批评缺乏80年代中后期那种文化论争的气势和社会影响”,换句话说,不是批评家没有意识到当代文学批评的这种“软弱”,也不是没有人想到需要展开一场有规模有影响的批评讨论,但世道变化,中心已经崩溃,权威不再有力,连“新时期”过来的批评家都感到言说的困难,更不要说还有什么人有能力在90年代组织起一群人以一种方式来讨论同一个问题了。
第二,90年代文学批评的分裂,体现在批评话语和批评问题的选择上,呈现出地域分布的特色。所谓批评话语、批评问题的地域性分布,是指90年代文学批评所讨论的问题,在一个相对集中的区域内,有共同性。这里的区域,主要是指地域。90年代,批评界一度流行这样的说法,就是“后北京”、“新南京”和“旧上海”,即谈论后现代的北京批评家,提出新状态的南京批评家以及强调国学和文化根基的上海批评家。这种概括未必准确,但都涉及到文学批评与地域的关系。用地域来命名批评,这在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中是不多见的,但在中国以往的文学批评史上,倒是并不罕见。如,中国古代的批评家就一直在讲南北文化不同论,南北文学不同论。到了20世纪上半叶,还有“京派”、“海派”的说法(“京派”、“海派”其实主要还是指戏剧、文学创作),而到了90年代旧话重提,人们不知不觉中感到地域在文学批评中成为一个较为突出的文化现象。地域对90年代文学批评的影响,已不仅仅是一种风格学上的表现,而是体现为一种思想的形式方式和传播方式。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领域里的重要话题,一般都是集中由北京发起的,然后波及全国。而到了90年代,上海、南京及其他地方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批评话题,原有的整体性批评格局,被诸多带有地方色彩的批评群体所取代。这种状况体现了90年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对文学批评的辐射,已不像以往那样,集中由一个地域发出,而其他地方只是被动接受这种辐射。从90年代的文学批评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北京、上海、南京之外,像东北的《文艺争鸣》,广西的《南方文坛》,都逐渐形成了新的批评群体、新的批评话题和新的批评影响区域。因为地域的限度,一方面全知全能、无所不在的整体性批评影响方式在90年代已被阻断。90年代的文学批评,并不因为北京的批评家或北京的重要文学研究刊物较集中地讨论“现代性”、“后现代”或是“全球化”等问题,而影响到上海、南京或其他地方的批评家、批评刊物都得跟着集中讨论这些问题。事实上,上海、南京或其他地区的批评家、批评刊物很少,有的甚至根本就不涉及所谓的“现代性”、“后现代”等问题的讨论。这当然不是说“现代性”、“后现代”问题不重要,但也并不能说北京之外的批评家、批评刊物因为较少涉及这些问题就没有自己的思考和特色了,实际上,在不同的问题领域,不同地区的批评家、批评刊物都有着自己的关注焦点。如,广西的《南方文坛》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重要话语及关键词的历史梳理,就独树一帜。南京《钟山》所开辟的“博士视野”栏目,容纳了许多新锐的批评话题。吉林的《文艺争鸣》所开设的“20世纪中国文艺纵横”栏目,对90年代中国文学状况给予了关注。湖南的《芙蓉》,是国内文学期刊给90年代中出现的新作家新作品关怀最多的杂志之一。另一方面,因地域文化的影响关系,基于不同地域文化经验背景的文学批评,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如,上海批评家对于都市生活对文学创作及人们审美方式的影响机制的探讨,相对来说,要比其他地方来得早,而且,在评价态度上也更显得宽容。在上海的批评家的文本中,很少看到有什么人指责那些肯定商业写作不失为文学写作之一种的人为“金钱崇拜”,也没有举起义旗、集体讨伐。像1999年《文学报》所展开的对90年代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写作的讨论中,批评家们还是强调对大众文学需要有一个了解和研究的过程。河北石家庄的《文论报》,在90年代后期对新诗的讨论,别开生面,一部分诗人坚持“知识分子的写作立场”,而南方的不少诗人主张“民间写作立场”,这些来自诗歌实践,而不是偏于理论构想的诗歌批评讨论,开启了新世纪现代诗学的先声。这些批评探讨,尽管都是限定在一个有限的地域范围内,但探讨的问题无不具有普遍意义。面对这么多繁杂的批评探讨,我想哪怕是那些对90年代文学批评极度不满的人,大概也会不得不叹息,的确,仅靠一个人的力量,是绝对没有能力将这么多的批评文献纳入到自己的阅读视野之中的。因此,在90年代这个迅速廓大的批评版图面前,承认批评家个人视野的限度,特别是影响的限度,是适时的。再强大的批评家,在90年代也无法将他的思想观点辐射到所有的批评空间,而地域作为一种自然屏障,是最难以穿越的思想障碍之一。
第三,90年代文学批评的分裂,还表现在性别方面。女权主义或是女性主义批评异军突起,成为9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中最具活力的思想领域。女权主义或是女性主义批评,在9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中的突起,有两个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其一,是性别意识;其二,是有强大的文学创作作批评的后盾。所谓性别意识,是指90年代的女性批评非常自觉地强调女性意识在批评表述中的重要性。性别差异,不仅成为一种批评的价值尺度,同时也成为女性批评形态现实存在的合法性依据。那种整体色彩浓烈,充满思辨话语的逻各斯话语系统,首先成为女性批评的抨击对象,在女性批评面前,文学批评似乎要重新学习说话的方式,那种感觉型的,具有随笔形式的表达方式,在原来一些批评家眼中,可能被理解为思想的零乱或思辨的不彻底,而在女性批评视野中,恰恰是颠覆男性中心主义的最有效方式之一。谁规定批评思想的表达,一定要选取整体思辨的方式来呈现?在那些所谓强大而雄辩的表述方式下,恰恰掩饰着男性雄性的话语独断。这种批评话语的内部裂变,无形中撑开了批评的思想空间。类似于北京批评家戴锦华、崔卫平这样独特的女性批评话语,不仅具有语体学上的价值,而且也教会了不少男性批评家懂得了“她们”的说话方式。无论如何,性别意识使得90年代的文学批评多了一重参照的思想坐标。当然,女性批评在90年代的强大,不只是一种批评理论,而在于她有最为新锐的文学创作经验作为铺垫。几乎不用多想,就可以在90年代的文学长廊中列举出诸如陈染、虹影、林白、迟子建和更年轻的卫慧、棉棉等名单。像最具有90年代特色的批评话语,诸如“私人化写作”、“躯体写作”等等概念,几乎都来自于这些女作家作品引发的争论。面对这些文学存在,哪怕是再自信的批评家,如果你不想回避现实,就不能认真对待这一切。对这些90年代的女性文学所陈述的经验,文学评论面临的已不是如何解释她们的问题了,而是如何修正以往被视为金科玉律无法更改的既定价值体系的问题了。开放,在这时成为一种迫切,小说应该怎么写、批评应该怎么做,在女性创作和女性批评面前,似乎都变成了一个有待重新确证的东西,90年代的文学批评因此而又获得了一次检讨自己的机会。
二
90年代文学批评的变化,具有脱胎换骨的性质。这里所说的脱胎换骨,是指文学批评对当代文学的影响方式、文学批评的构成形态及文学批评思考的形成等方面,在90年代出现了新的变动。这种变化,较为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批评对当代文学的介入,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深入和广泛,这突出表现在文学创作和文学传播方式之间的密切联系上。在以往,文学刊物、出版机构与作家创作之间,无非是一个完成作品,一个将作品编辑发表。也就是说,创作和发表是被分割在两个不同的空间中进行的。而进入90年代后,文学杂志、出版机构开始以自己的尺度和要求,影响着作家作品。在人们记忆中,“策划”这一概念,毫无疑问是从90年代开始的。最初的实验,可能就是《钟山》杂志对一批冠名为“新状态”作家作品的包装。而最成功的策划案例,大概就是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废都》的出版发行。随之一批前缀词为“新”什么什么的作家作品源源不断地出现在9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对这种现象,不少批评家认为是一种名大于实,先有概念,后有作品的倒置归类活动,也就是说,是与以往先有作家作品,后有文学命名、归类的做法相悖逆的批评活动。这样的倒置归类的批评活动带有预设性,而这种做法到底行不行得通,在理论上,可以进行讨论,但就这种做法在90年代中国文学实践中的实际影响来看,的确开辟出一种不同过去,或者说,不同于“新时期”的文学传播方式和文学经验的组织方式。 不管这种做法对文学的影响如何,90年代一批新的作家作品,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进入文坛的。普通读者是通过这种方式知道有这样一些作家作品存在。并且,在对90年代文学批评作概括时,无论如何,也是难以删除这些所谓的“新”什么什么的批评归类现象的。这种文学杂志、出版机构在整个文学活动中的强大作用,意味着文学杂志、出版机构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传送作品的编辑部门,它的职能开始转向主导文学潮流,带有文学组织者的性质。可以说,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文学杂志、出版机构的这种组织功能越来越强。每一个文学刊物、出版机构的运作方式的改变,都会产生一批不同风格类型的作家作品的出现。譬如,90年代末,《北京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各自采用评选优秀作家作品的方式,重新包装一批作家作品,以评奖的方式将一种美学尺度肯定和传播出去。而事实上,这些作家作品早就存在了,评奖或是其他方式的传播,只是使一种分散的作品类型集中在一起,在一个时间段落和空间单位内,集中向社会辐射,由此产生远比单个作家作品影响更大的辐射范围。再譬如,99年包括珠海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等先后推出一批“70年代出生”的作家作品,原来不怎么明显的文坛“代沟”问题,随这些出版物的出版,一瞬间倒是成为一个社会关注的焦点了。只不过这次的代沟与新时期所出现的代沟有所不同,新时期的代沟,揭示的是成长中的“知青作家”与一批50年代形成社会影响的作家之间的价值观上的隔阂。而世纪末在中国文坛出现的这种代沟,显示出同样处于成长期的年轻作家与“知青作家”之间的价值隔阂。不论这些新时期过来的有着“知青”背景的作家、批评家如何激烈抨击所谓的“另类”作家作品,总之,一个新的文学世纪是在这种指责声中,以无法逆转之势诞生了。在写作与出版、编辑这样关系密切的文学生存空间里,原来意义上的那种作家写作和作品构成方式会不会改变,的确面临着最现实的考验。有不少人批评这种写作与编辑、出版同步进行的方式是带有商业写作的色彩,但90年代哪一个作家能够摆脱这种方式对自己写作的影响呢?一个不争的事实是,90年代中国作家的写作效率大幅度地提高,可能是20世纪以来最为突出的现象,稍有一点知名度的作家都推出了自己的“文集”、“文库”,而这种快速生产的背后,你能说没有商业写作的影响痕迹吗?对这样一种文学存在方式,当然,当然,人们可以说三道四、评头品足,发表各自的不同意见。但就这种存在本身而言,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讲,的确是一种新的现象,至少是新时期文学批评中所没有的。
其次,90年代文学批评表达形式的最大改变,就是由多人参与的对话体批评的流行,而且,对话成为90年代文学批评表达批评家文学思考的最主要形式。可以说,90年代那些较为重要的问题,那些有着较为广泛社会影响的批评话题,都是通过对话的形式表现和传播开来的。诸如,后现代问题、女性批评问题、传媒与大众文化问题、市民社会和都市文学问题、新生代作家作品、晚生代作家作品及70年代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等等,都可以看到不同群类的批评家,以一种沙龙谈话的方式,最简洁、也最快速地将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对这种表达方式,一些学者和批评家至今依然持反对态度,视其为90年代学风浮夸的一种表现。但假如对90年代的文学批评材料作一番搜寻的话,人们不难发现即便是今天被学术界视为治学态度最严谨的学者、批评家,诸如王元化、钱谷融等,大都参与过对话,并留下不少对话的文字。我甚至认为,排除了这些对话的文体材料,90年代文学批评许多最有思想深度、最具前瞻性的思考,将会被排斥在外。因此,对话体介入90年代文学批评并构成9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的一大特色,这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思想形态的变化。确实,形式不仅仅是形式,一种表达形式总有着特定的表达内容的需要。90年代对话体的流行,这其中所引发的思考,其实远远不止是批评本身的问题。为什么90年代文学批评中会广泛流行这样的思想表述方式,批评文体的选择有没有一定的规则,什么样的文字才可以归入文学批评的行列,其价值标准如何,等等,所有这些,大概都指向一个本源性的问题,什么是文学批评。一旦触及这样的文学思考,还能说不是一种脱胎换骨的思想转变吗?
第三,文学批评的概念在90年代已经不再关注于纯粹的文学文本,也就是说,文学作品的概念在90年代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譬如,流行歌曲的歌词,是不是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理解。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一些吟唱的歌词是被视为文学作品的,但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中,几乎很少见到这样的批评眼光。或许在一些批评家眼里,文学批评主要应该关注的是文学作品中涉及所谓的社会重大问题。而那些流行歌曲只是低吟浅唱、不入流的东西。至于流行歌曲的歌词,更是不能启齿的东西。事实上,这种文学观念的价值参照,还是以时代政治作为主要的坐标。所谓重要,所谓思考的严肃性,其指向无非是那些政府部门的决策、某个政治人物的脾性喜好,等等。这些因素对中国的文学现实,的确有重要影响,但对于普通读者的审美活动而言,政治未必是永恒的价值坐标。如果真要从普通中国人近20年的感情世界的变化着眼,流行歌曲对当代中国人情感的影响之大,恐怕不在那些政府部门的决策影响之下。从审美的角度来反思文学批评,有关“文学”概念的扩大,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了。在90年代,流行歌曲作为一种文学文本进入到批评家的分析视野之中。像批评家张新颖对崔健的摇滚歌谣的分析,像作家王朔在《我看大众文化港台文化及其他》一文中对电视剧的分析,都显示着世纪末的人们对“文学”一词的理解,有别于刚刚过去的那个“新时期”。另外,像世纪末广为流行的网络文学,不只是一种文学存在,而且昭示着新世纪“文学”概念潜在的变化。网络文学,不只是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传播方式,它对未来文学的影响,可能是全方位的。文学写作由传统的文字书写,转变为一种可视写作,作家面对的是显示屏,而不是纸张,操纵键盘和手握笔杆的书写,对作家写作心态的影响是直接的,具体地说,同一个作家,假如他面对的是同一个故事素材,但他依据的写作手段不同(或是笔杆或是电脑),会形成不同风格类型的作品,甚至思考问题的方式也会变化。任何一个习惯于笔杆写作的作家,在改换成电脑写作时,大概都会有一个风格转变问题存在。有些作家甚至会觉得电脑写作时原有写作的那种语感没有了,有的只是一种没有韵味的故事叙述。作品的平面化,也就是作品缺乏回味,是网络文学的通病。但网络文学会不会永远就这么下去,或者说,随着网络的发展,加入这一行列的作者队伍的扩展,文学写作会不会形成一种新的格式,就像人们对电影艺术与对文字作品会有不同的要求一样,网络文学在未来的批评家眼中,会不会又是一种新的“文学”呢?这些问题,在90年代的文学批评中尽管不多,但却都作为问题出现了,而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所从来没有经验过的,当然,也是新时期文学批评中所缺少的。
三
上述所列举的批评现象,最后都可以归结为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这就是90年代文学批评是不是有着自己的内在规定性?90年代有那么多的批评家在从事自己的研究,有那么多的批评文章散布在全国的各种报刊传媒之中,是不是所有这些文本都可以视为90年代的文学批评?换句话说,90年AI写作的、发表的批评文章是不是都具备90年代的思想个性呢?在我看来,90年代文学批评虽然包括所有90年代出版、发表的批评文字,但应该突出和强化的,还是那些涉及与90年代中国文学、文学批评生存状况,特别是90年代文学和文学批评发展所面临的问题的批评思考,否则,90年代与80年代、70年代的文学批评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那种认为90年代的文学批评所思考的问题,新时期的批评家早就提出来了,或者认为90年代的文学批评根本没有自己的个性可言的看法,体现着一种既定的价值观念对超越原有教规的新经验的隔膜和偏见。我想需要向这些恪守既定价值规范的批评家们提出这样两个问题:一,90年代文学批评有没有提出以往文学批评所从未遇到过的问题?二,90年代这10年间,有没有新的批评家成长起来,这些新的批评家的审美经验仅仅是平庸地复现了前几代批评家的审美经验,还是有着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独立思考?事实上,这两个问题也不是什么高难度的理论问题,但正视这些问题需要勇气。我常常在想,大概在新时期文学批评起步时,那些年轻的批评家也会遇到这种相似的诘难,总有人不满意现状,但一种不满是因为超越现有的问题思考所引发的,而另一种却是因为自己在现有文学秩序中的失落而产生的不满。在评价90年代文学批评时,这种历史的逻辑又呈现出来。或许这并不是历史的悲哀所在,而恰恰意味着新的思想萌动的开端。
2000年4月于华东师大
注:此文为即出的《90年代批评文选》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