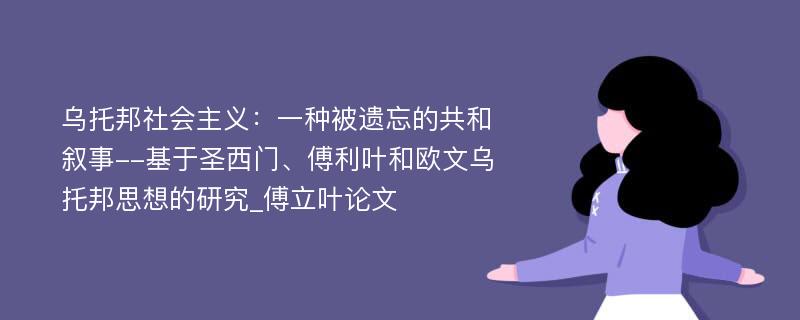
空想社会主义:一种被遗忘的共和主义叙事——基于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乌托邦思想之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傅立叶论文,乌托邦论文,空想社会主义论文,共和论文,西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638(2012)05-0001-06
一、引言
近年来,在西方语境下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出现了“复兴”,特别是在以约翰·邓恩(John Dunn)、J.G.A.波考克(J.G.A.Pocock)以及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为学术核心的“剑桥学派(the Cambridge School)”的推动下,一些传统的共和主义理论资源被挖掘出来。但总起来说,这是一项“未竟的事业(Unfinished Business)”,很多蕴含着共和主义叙事的思想资源依然沉寂于历史的尘封之中。比如说乌托邦思想,尤其是以圣西门(Comte de Saint-Simon)、傅立叶(Charles Fourier)和欧文(Robert Owen)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Utopian Socialism),而空想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共和主义叙事依然被人们遗忘于共和主义知识谱系之外。
尽管从词源学上来说我们要将乌托邦(utopia)一词追溯至托马斯·莫尔(Thomas Moore),[1](P533)但是实际上柏拉图(Plato)很早就在其《理想国》中提供了丰富的乌托邦给养。不仅如此,他们两人都致力于建构一种共和主义乌托邦(Republican Utopia),从而在乌托邦与共和主义之间建立一种逻辑勾连,某种程度上这种勾连一直延续于乌托邦思想之中,形成了一种连续性思维。
可以说,历史的脚步跨过柏拉图和莫尔,共和主义在革命的烈火中煅烧之后有所沉寂,但是共和主义这面旗帜并没有倒下,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举起了它并试图把它插上他们乌托邦共和国(Utopian Republic)的上空,共和主义在他们对自由资本主义的乌托邦的总体性批判(Holistic criticism)中得以彰显。一般的,他们的作为共和主义叙事的乌托邦常常被定性为一种“社团乌托邦”,因为“他们对理想社会的政治设计集中在市民社会的经济平等上,而漠视国家政权的意义,故所构建的乌托邦都具有强烈的结社性质”。[2](P214)假如我们将他们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事业比喻成一个棒球团队的话,那么他们将分别占据一、二、三垒的战略位置。
二、圣西门:乌托邦语境下共和主义叙事的第一垒
圣西门是引起争论的人物,这种争论性也凸显了他的乌托邦思想所具有的震动性。美国历史学家F·曼纽尔(Frank Edward Manuel)曾这样评价人们对圣西门的争论:“今天阅读圣西门的著作在某些方面仿佛阅读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著作一样。现代政治思想的口号的编纂者从他的华丽词藻中汲取了太多的东西,以至于同时不听一听它们下面解释的泛音,就不可能在心里懂得它们真正的内容。”[3](P1)而实际上这就是共和主义的泛音。
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说:“圣西门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4](P725)所以“在谈到圣西门时,特别应该提起同法国革命和无产阶级下层群众的这种联系,尽管圣西门的思想表面上看起来是与当时的无产阶级的愿望和目的完全格格不入的。”[5](P239)这种联系也说明法国所奉行的卢梭的共和主义潜在地影响了圣西门的乌托邦思想,虽然他明确表示反对手段的激进性和暴力性,但他承载了共和主义的基本理论内核。
相比于莫尔的生活年代,圣西门的时代是“进步的”和“文明的”,但在这些浮华的表象下面却埋藏着罪恶的渊薮。圣西门充分施展了乌托邦思想的批判精神,努力去打破“恶”的黑暗,迎接“善”的光明,为建立共和奔走他方。圣西门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压迫性、掠夺性和利己性,他说:“现有的政治体系的三个主要弊端即专横武断、腐败无能和玩弄权术。”[6](P247)“现在的社会完全是个是非颠倒的世界。”[6](P239)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国家把穷人应对富人宽宏大量作为一条基本原则,结果不得温饱的人每天还要省出一部分生活资料来为阔佬们锦上添花。”[6](P239)圣西门认为这主要归因于资本主义的利己主义特征。[7](P201)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实业制度”的乌托邦思想。在圣西门“实业制度”的乌托邦中,最高权力机构是最高行政委员会和最高科学委员会,而且建立了实现未来社会目的的财产所有制,“使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带来使大多数无产者拥有财产的结果,以使无产者能出色地管理财产。”[8](P239)并且保证每个人的劳动权,“一切人都应当劳动,都要把自己看成属于某个工场的工人。”[6](P24)同时为了保证“实业制度”的高效运作,必须实行有计划的调控,充分体现这种制度的协作性,而在分配方面则实行“使每个社会成员按其贡献的大小,各自得到最大的富裕和福利”[6](P223)的分配标准。此外,圣西门还注重道德和教育的建设,在他看来,“伟大的道德原则就是改善人数最多最穷苦阶级的目的。”[9](P178)要实行完全不同于旧教育的新教育方案和内容。最后,圣西门认识到“实业制度”的运转需要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他指出:“全人类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和一些共同的利益,所以每个人在社会关系方面只应把自己看成是劳动者社会的一员。”[6](P168)
强调公共利益就突出展现了圣西门抓住了共和主义的真谛,他“始终不渝地把人们的利益置于首要的地位。”[5](P243)但是他的乌托邦思想中又留有被恩格斯所称为的“资产阶级倾向”的东西,[4](P721)所以说:“尽管圣西门坚持对现存政治秩序作总体性的乌托邦批判,但是另一个方面,他在构建其乌托邦时又试图在现存政治体制的卵翼下寻求乌托邦实现的可能。”[2](P217)圣西门如同柏拉图和莫尔一样建构了一个公共领域,不过在那里私人利益也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因而他的乌托邦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定具有明显的模糊性,“圣西门并不原则性地反对所有财产,而只是针对社会的公有财产部分,认为应得到良好的管理。”[2](P217)进而可以看出圣西门的公共领域不是纯粹的,它更具务实性;相比于柏拉图和莫尔的草率,他显得有些懦弱。正由于圣西门为他的乌托邦留了一条通往现实的暗道,而通往现实却又往往无法实现,圣西门一定程度上使他的乌托邦思想陷入二难困境(Dilemma)之中:一方面他模糊性地界定了公私领域,就为私域蚕食公域提供了可能性,所以他的乌托邦思想有去乌托邦化的冲动;另一方面,圣西门又“把乌托邦的可能性寄托在由实业家组成的社团身上”,[2](P218)而相比于有机整合的社会而言,这些社团只能是小有规模的私人领域,此时这些社团所具有的不是批判性而是腐朽性,所以实际上圣西门把他的乌托邦的可能性寄托在一种不可能性上,这又加强了他的乌托邦思想的乌托邦化。
共和主义矢志不渝地在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圣西门在乌托邦思想中隐性地流露出这种念头,如他主张人人都有劳动权,但是劳动的内容和性质又定位了劳动者的身份和地位,实际上他的乌托邦是由实业贵族来治理的,赫茨勒(Joyce Oramel Hertzler)评价道:“正如他想象不出一个人人皆主人的工业作坊一样,他也无法想象出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要做好工作和管理好社会,就必须由专家当政。圣西门毫不动摇地相信世代处于领导阶层的祖先的后世子孙的领导能力。他正如后来的卡莱尔一样,盲目相信伟大人物的价值。”[10](P190)圣西门自己就承认说:“这种宣传的唯一目的,则是唤起君主利用人民赋予他们的权力来实现势在必行的政治改革。”[6](P303-304)
与柏拉图奉行“美德即知识”不同,圣西门则主张“美德即劳动”,他认为:“劳动是一切美德的源泉,最有益的劳动应当最受尊重。”[8](P71)圣西门如同其他共和主义者一样给予美德以无上的地位,但他更偏重于美德的肇因,即劳动。如此一来,他就用美德为他的实业家统治寻找到了合法性的法理依据,逻辑思路与柏拉图如出一辙,只不过他没有柏拉图那么思辨、抽象、曲折和复杂。
如果说柏拉图和莫尔的乌托邦还未把时间因素纳入考虑层面而只留于空间的话,那么圣西门则摆脱了这种思维定势,“他的世界观的特点是具有现实性,而不是具有静观性。”[5](P240)而且体现了典型的历史乐观主义,他说:“直到目前,人们都盲目地传说黄金时代是属于过去的事,其实它还在将来。”[7](P169)圣西门还赢得了恩格斯的高度评价:“我们在圣西门那里发现了天才的远大的眼光,由于他有这种眼光,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乎所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思想都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他的思想中。”[4](PP726-727)
三、傅立叶:乌托邦语境下共和主义叙事的第二垒
傅立叶与圣西门几乎同时而且几乎同在一地方但用不同的论说体系和话语结构宣扬着共和主义的核心价值。恩格斯说:“傅立叶不仅是批评家,他的永远开朗的性格还使他成为一个讽刺家,而且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讽刺家之一。”[4](P727)傅立叶试图用他那讽刺性批判之笔为共和主义开辟出一条道路。
法国革命不仅影响了圣西门,而且也影响了傅立叶,所以傅立叶的乌托邦思想中烙有卢梭的影子,同时社会现实也逼迫着傅立叶去思考,“傅立叶是在正确地认识了过去和现在之后才按照自己的看法想象未来的。”[11](P658)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构成了他的乌托邦思想的最有价值的一部分。[12](P250)可以说,“在傅立叶的著作中,几乎每一页都放射出对备受称颂的文明所造成的灾祸所作的讽刺和批判的火花。”[13](P289)傅立叶指出:“文明制度的机构在一切方面都只是一种巧妙地掠夺穷人而发财致富的艺术。”[14](P114)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所依靠的雇佣工人和奴隶阶级陷于绝望的境地。他们远比那在自然状态下享受可能得到的幸福的蒙昧人,实在要可怜得多。”[14](P283)因而他痛斥资本主义社会“是颠倒世界,是社会地狱”,[15](P103)咒骂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是恢复了的奴隶制度”。[16](P117)对此,他呼吁人们“必须怀疑文明制度,怀疑它的必要性、它的完善性以及它的持久性。”[16](P4)在这一点他的根本性认识还是相当具有革命性的,他说:“我的目的不在于改善文明制度,而在于消灭这个制度。”[14](P102)但是他和圣西门一样都不喜欢暴风骤雨式的革命,而是更偏爱和风细雨般的改革。在这种批判之上,傅立叶主张建立一个“和谐制度”的理想社会。傅立叶的乌托邦围绕“和谐”展开,“协作精神是它的特点”,[15](P89)因而它比圣西门的乌托邦还乌托邦化。
傅立叶的乌托邦思想中处处闪耀着共和主义的光芒。如同自然科学家那样,傅立叶在人类社会中发现了“情欲的引力规律”,他说:“情欲引力无须采取强制的手段,而且除了以快乐作为诱饵以外,并不需要任何支持,单靠情欲引力,就可以建立地球上的普遍的统一,并且在我们即将进入整个七万年存在社会协调制度的期间,消灭战争、革命、贫困和不义。”[16](P67)正如赫茨勒所说:“傅立叶相信,听任人类情欲自由发展,便可成功地为全人类解决最大的幸福问题。”[10](P194)傅立叶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他把一切情欲①都看作善,而这也反映了傅立叶头脑中的共和主义思维:公共利益高于一切,可以包含和内化其他一切非公共利益,个人利益自不待言。因而傅立叶所谓任由情欲自由发展,其最终是以公共利益为指归的。
在傅立叶的和谐社会中基本组织是“法朗吉”,②而“法郎吉”本身就是组织化的公共领域,在这一公共领域中,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实现了高度的统一,严格地说,私人利益被公共利益同化掉了。虽然傅立叶给私人利益提供了生存的机会,因为“傅立叶的‘法郎吉’不仅不反对私人财产权,相反他试图刺激个人的私有观念,把股份作为分配的依据之一。”[2](P223)但是私人利益在奉行“统一主义”或“和谐主义”的公共领域内是无法走很远的。实际上在公共领域中允许私人利益的存在就是允许不和谐因素或否定性因素的存在,它们会消蚀公共领域,而为了公域的存在必然会否定否定性因素的存在,共和主义所被人诟病之处在傅立叶的乌托邦思想中也不可避免。
平等这一共和主义宣扬的价值在傅立叶的乌托邦思想中得到了更具体的表达。如他主张社会地位的平等,而这种平等在傅立叶那里是由劳动来界定的,他认为人人都参加劳动,而且劳动不受分工制度的束缚,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自由地选择和交换工种;[9](P200)地域和阶级的平等,在傅立叶的和谐社会中将消灭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工业生产者不像现在那样集中在穷人麋集的城市中,而将遍布全球乡村和法郎吉中”,[16](P259)而且人们亦工亦农;[9](P201)分配平等,在傅立叶看来平等并不等于平均,他说在协作制度下“任何平均主义都是政治毒药”,[16](P215)所以他认为“按比例分配”能体现分配的平等;性别平等,在傅立叶的乌托邦中,妇女获得了彻底解放,她们竟同男子一样参加集体劳动,从事科研和艺术活动;[9](P202)教育平等,傅立叶主张普及高等教育。此外,他主张公职人员由群众选举产生,这体现了民主的底色,表达了政治平等的诉求。尽管共和主义的这些价值在傅立叶的乌托邦思想中得到了体现,但是在他准备将它们付诸政治实践层面时,他又对它们频频加以否定。
傅立叶与圣西门一样“有一种现实主义的气质”,[10](P198)他对资本主义作了总体性的批判,并将共和主义的某些价值渗透进他的乌托邦思想之中。傅立叶的共和国有着发达的市民社会,但是政治领域却出现了真空,也就是说他凸显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离,不过他走得太远了,以至于走到了反社会的边沿,[10](P198)因而共和主义因子的存在也无法淡化他那浓重的乌托邦色彩。
四、欧文:乌托邦语境下共和主义叙事的第三垒
在作为共和主义叙事的空想社会主义阐发事业中中欧文是一位骁勇的弄潮儿,恩格斯称他是具有像孩子一样单纯的高尚的品格,同时又是一个少有的天生的领导者。[17](P214)尽管“欧文的乌托邦思想集中于乌托邦的可能性问题上”,[2](P225)但是在探讨这种可能性的背后,共和主义价值铸造了他理论的几乎每个闪光点。
相比于圣西门和傅立叶,欧文的寿命最长,因而他看到了他们二人无法看到的一些东西,他长久的阅历使他看问题更犀利和深刻,“他比傅立叶和圣西门鲜明而彻底”。[9](P228)如同圣西门和傅立叶一样,欧文的乌托邦思想也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基础上的,不过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具有英国产业革命时代的特征,他直指机器大生产,说:“机械方面的新发明结果造成了一场大灾祸。”[18](P223)在生产过程中,“雇主把雇工只看成获利的工具”,[19](P139)而采用机器生产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经济危机,“农业和许多工厂生产部门的体力劳动的市场价格已经降到最低程度,而科学发明所造成的生产力却迅速地继续上升。结果,为市场而生产的行业很快就要发生危机。”[18](P223)同时欧文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罪恶,他指出:“私有财产是贫困的唯一根源。”[18](P13)它“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人们所犯的无数罪行和所遭受的无数灾祸的根源。”[18](P11)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评价他已经“猜到了文明世界的根本缺陷的存在”。[20](P107)当然批判只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而欧文是想去改造世界,他那“和谐公社”的乌托邦思想就是改造世界的方案。不过在这个方案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则是欧文所伸张的共和主义价值。
欧文突出强调了公共领域的重要性,他说:“所有一切生存的首要目的就是求得幸福。但幸福不能由个人单枪匹马地去获得;希望获得独享幸福是徒劳的;大家必须共享幸福,否则少数人是永远不能享有幸福的。因此,人只能有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目的,那就是使他的同类性格安宁,精神愉快,如同原始社会组织或每个人的本性所允许的那样。一旦所有的人都真诚地致力于使周围的人的幸福都达到这种制度,他们便进入了真正的生活,然后他们将最大限度地一心促进他们个人自己的幸福,而这种幸福与人类的幸福却永远是一致的。那时,人与人之间仅存的竞争乃是谁能最有成效地为他的同胞创造更多的幸福了。”[21](P54)在欧文看来公共领域关系到私人的生活质量,只有当私人进入公共领域并谋求公共利益时,他的私人利益自然就会伴随公共利益的实现的而实现,在这里欧文忽视了私人利益的多样性,他把这些多元的私人利益看作是单一的,他试图用公共领域限制私人领域的自我实现的内在冲动,这是典型的共和主义的逻辑维度。正是在强调公共领域重要性的前提下,欧文将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其乌托邦的经济基础,在他的乌托邦里“纯粹个人日常用品以外的一切东西都变成公有财产。”[18](P13)乍看起来,这就是共和主义的一般主张,但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在欧文那里财产公有不再仅仅是一项措施和政策,而是被赋予了基础性地位,这是他对共和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欧文的乌托邦还富有民主精神,[9](P234)在那里公社最高权力属于全体社员大会,公社的一切重大问题由社员大会讨论决定,社员“对一切事情有发表自己意见的充分自由。”[18](P231)并且呼吁平等的心声不绝于耳,如他试图缝补阶级之间以及地域的裂痕,因而他主张将要建设的公社是“工农结合的新村”,[19](P353)“新村将带有大城市的一切便利,然而却没有大城市的无数祸害和不便。新村还将保持乡村的一切优点,但又没有目前偏僻地区所具有的种种不利条件。”[19](P262-263)此外,欧文还将自由原则引入婚姻领域,在他的乌托邦里男女两性享有同等的权利,实现了完全平等。
尽管欧文设计了一个乌托邦,但是他并不把它当乌托邦来看待,他是要付诸实施的,并且他把这一切的可能性都维系于教育,他之所以认为教育可以扭转乾坤是因为他相信人性本善,赫茨勒说欧文“是具有卢梭传统的先知,他宣讲人性本善的福音。”[10](P214)在这里涉及欧文的环境论,他认为“人的性格主要是由出生以后的社会环境决定的,为了使人的善良性格和品质得到培养和发展,就要铲除恶的环境,创造善的环境,从而把社会成员都变成善良、聪明、有用的人。”[9](P218)实际上欧文只不过把共和主义的美德观表达得更隐晦一些而已,在他那里人的善即私德,环境的善即公德;环境的善影响人的善,也就是共和主义所认为的私德会伴随着公德的养成而养成,所以欧文对美德的认识会“导致绝对否定个人责任的宿命论观点”。[10](P210)
在欧文的乌托邦思想中,我们还发现了共和主义的整体思维。在欧文看来,人类向理想社会的过渡,乃是通过公社数量的增加,由几十个,几百个以至几千个公社结成公社联盟,直到联盟遍及欧洲,随后再普及到世界其他各洲,最后把全世界联合成为一个只被共同利益联系起来的伟大共和国。[18](P150)因而这种整体思维体现在欧文对他的乌托邦的动态认识上。对于“一”的追求是欧文的乌托邦的最终归宿,而这种整体思维也强化了他的思想的乌托邦性。严格地说,追求“一”是他的乌托邦的乌托邦。不过在某种程度上,欧文又“把他的乌托邦仅仅局限于社团范畴,无法上升到对国家政权的否定,实际上消解了政治现实与乌托邦的对立,而背离了乌托邦的空间意义。”[2](P228)一定意义上说,整体思维的存在是导致欧文的乌托邦思想成为一个矛盾体的众多因素之一。
其实,相比较于圣西门和傅立叶的共和主义叙事,欧文的现实性是最为强烈和明显的,恩格斯就说欧文的乌托邦“始终都保持着这种面向实际的性质。”[4](P730)然而“欧文的逻辑前提、思考和结论的具体性,并不意味着理论思维的无力,也不是降低到事务主义的实用主义的一种表现。”[5](P260)欧文企图用共和主义的一些价值去碰撞现实,并用它们去重塑现实,但是由于这些价值因子过强的现实性反而极易遭到现实既有社会秩序的排斥与扼杀,因而这些现实性无法找到现实生长点,终归摆脱不了被乌托邦化的命运。
五、结语
可以说,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在阐发空想社会主义的过程打出了一、二、三垒绝佳的战略配合,创造了乌托邦语境下共和主义叙事的一个新的理论高潮,因而共和主义的价值因子在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三个斗士那里得到了同一的认同,他们都主张建立一个谋求公共利益的公共领域,追求平等、民主和自由,注重美德,而且具有整体思维的深远眼光,“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4](P721)但是“他们却仍然在以陈旧的理智主义的方式做着他们那乌托邦的美梦。他们那处于社会边缘的情境,是通过一些扩展人们的社会视角和经济视角的发现表达出来的,然而,就他们所使用的方法而言,他们仍然保留了作为启蒙运动的特征而存在的那种不确定的见解。”[22](PP228-229)虽然他们都从现实性出发去积极寻求乌托邦的可实现性,不过“他们没有认识到尊重历史的深远意义”,[10](P217)从而历史给予他们一个反现实的归宿,当然在他们的乌托邦思想中共和主义价值因子在理论上获得了一次理论高潮的重要历史段点。综合权衡,我们完全有理由要求在共和主义政治光谱上将他们三个人的名字重新书写上,而从共和主义的视角来重新诠释空想社会主义也必将为我们提供新的认知维度。
收稿日期:2012-07-12
注释:
①傅立叶认为情欲共有12种之多,包括感官情欲和精神情欲,后者又分为以个人利益思虑为基础的依恋情欲和以公共利益思虑为基础的谢利叶情欲。
②“法朗吉”是希腊语,原意指严整的步兵队伍。它有固定的人数和土地面积,超过一定比例,就无法按照情欲来分配劳动。“法朗吉”设立一个权威评判会,人员由选举产生,对组织内的公共事务发表意见,它不具有任何强制性,因为“法朗吉”里的一切都是由情欲来自行调节和引导。如果说圣西门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委员会,那么“法朗吉”更像一个股份公司,它以农业和工业经营为主,下设若干谢利叶小组,进行劳动分工。由于傅立叶强调人的多样性情欲,所以人们可以不断的更换小组,以保持对劳动的兴趣。“法朗吉”的劳动收入,按照劳动、股金和才能进行公平分配。对此可参见陈周旺:《正义之善——论乌托邦的政治意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