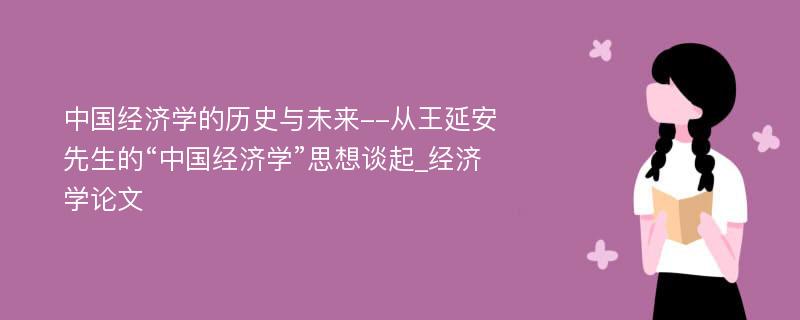
中国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从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学”主张所想到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未来论文,王亚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乍一看,这个题目很大,绝非一篇短文所可言。不过,如果暂且搁置眼下有关中国经济学的纷繁观点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内容而不论,仅仅尝试从中国经济学(假设这一概念成立的话)过去曾走过的道路中去探究它的未来发展前景,那么似乎又为本文讨论这一题目,留下了某些置喙的余地。
一
中国经济学或中国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并不是新近才出现的时髦名词。它可以追溯到数十年以前。关于这个概念的解释,早期比较具有典范意义的,恐怕要算是王亚南先生于1946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原论》一书。书中从“批论”当作舶来品输入的政治经济学角度,认为中国是经济落后的半封建国家,从而使国人的政治经济学修养程度受到限制,故没有产生以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为探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的环境。因此,我国有志于“中国社会经济之科学研究”的人,不应一味照搬模仿舶来政治经济学的那一套教义和内容,而“应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所谓“中国人的资格”,广而言之,是藉此期待由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达到三个目的,即确定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并用于指导我国的社会活动实践;了解近代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法则及其必然趋势,包括这一演变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冲突现象;扫除有碍于中国社会经济改造的一切观念上的“尘雾”,运用和“锻炼”政治经济学使之成为中国反对落后封建意识、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文化武器”;具体言之,是试图“创建一种专为中国人攻读的政治经济学”,它区别于舶来政治经济学之处,为“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阅读,特别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经济理论教程”;或者说,它的内容“比较更切实用”,意在“创立一种特别具有改造中国社会经济,解除中国思想束缚的性质与内容的政治经济学”。(注: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附论一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96—325页。)
以上解释,大致给中国经济学这个概念,从理论上划定了一个范围。其侧重点是要求在理论体系、论断结论、案例材料、性质内容等方面,努力形成一种全然不同于现行舶来的政治经济学、而特别适用于中国自身情况的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读本”。看来,王亚南先生自己撰写这部《中国经济原论》,也在实践着这一努力。此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以研究“中国原有的经济形态”为其宗旨,分别从导论、即论述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形成发展及其研究上的两种基本对立见解开始,随之相继考察了中国社会的商品与商品价值形态、货币形态、资本形态、利息与利润形态、工资形态、地租形态、经济恐慌形态,最后在结论中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生产关系下的诸经济倾向进行了总考察;此外,书中还以附论的形式,补充考察了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中国经济学界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国商业资本论、中国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间的流通问题、中国官僚资本之理论的分析等论题。显然,这是一部道地的中国式政治经济学读本,所以有人揣测说,“大概这部名著就是他自己所设想‘中国经济学’的初步尝试”。(注: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43页。)由此可见,早在50多年前,我国学者中就已明确提出了创立中国经济学的命题,而且关于这个命题的解释,在不少方面,与今天讨论中国经济学中的许多观点,也是相通的。
以王亚南先生的论断作为标志,如果进一步思索,似乎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有待说明和澄清。诸如中国经济学创立的历史前提条件是什么,它能否从先行经济思想资料(无论是中国传统的还是外国舶来的)中吸取其滋养,它在世界经济科学中应当具有怎样的地位和影响,等等。弄清楚这些问题,哪怕只是有所体会,或许对判断中国经济学的未来前景,也是不无助益的。
二
最初提出创立中国经济学,按照王亚南先生的观点,可以理解为包含着两个历史前提。一个是中国尚处于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换句话说,这种落后的经济形态,“始终踯躅在由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形态中”;另一个是从前一个引伸出来的,即中国落后的经济地位和环境,必然引起经济思想上的落后。前者意味着舶来经济学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必然与中国现实经济的特质格格不入,甚至成为理解这一经济特质的障碍。后者则意味着中国学者受到政治经济学修养程度上的制约,除了模仿或人云亦云之外,无力或无法鉴别那些不大熟悉的甚至完全隔膜的外国经济现实的理论。二者归结到一点,就是舶来经济学不可能解决,或者说,不可能适用于中国特有的社会经济问题。于是,创立中国经济学的主张便应运而生了。这样说来,中国经济学与舶来经济学之间,似乎形成了一种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其实,在提出中国经济学概念的背后,还隐含着一个不言自明的历史前提,即舶来经济学的输入。也就是说,当以欧美资本主义经济为其基础的政治经济学传入中国后,在这种舶来品的持续渗透和影响下,才引起了对于中国经济学问题的关注,从而显示出中国经济学与舶来经济学之间的密切联系。事实证明,从舶来经济学的输入到中国经济学问题的提出,其间经历了一个不短的过程。
如果把经济学理解为一种独立的科学理论体系,并把它与那些缺乏这种独立理论体系的零散经济思想区别开来,那么,有理由作出这样的判断:中国的经济思想有着自身的渊源和久远的历史,曾以其光辉成就自立于世界经济思想之林;而中国的经济学却是近代以来受舶来经济学影响的产物。考察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演变历史,其中一条重要线索,便是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曾经贯穿着中国传统的古旧经济思想与从西方引进的新鲜经济思想之间的较量和斗争。其总的趋势,大致表现为传统经济思想在舶来经济思想的冲击下,从最初以其支配思想的身份进行顽强抵抗,到逐渐发生动摇,直至被舶来经济思想所取代而退出其统治地位。这里所说的舶来经济思想,其内容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伴随着它在中国传播的不断展开,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即从最初的一般经济常识逐步深入到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领域。这场较量和斗争,后来以舶来经济思想战胜传统经济思想而告终。当然,传统经济思想的失势,并不意味着消失,它以成百上千年的历史积淀为其底蕴,仍会在冥冥之中显示其传统的力量,但无论如何,经过舶来经济思想的冲击,国人在思考和讨论经济问题尤其是经济理论问题时,已经从思维方式、逻辑体系、理论原则、研究方法乃至名词术语上,逐渐完成了由其传统古旧形式向新型科学形式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舶来经济思想的传播,实际上是为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中国经济学的创立,解除了束缚,扫清了障碍。
舶来经济思想的引进,一般说来,起始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那是中国清朝政府在外国列强的炮舰威逼下,被迫放弃闭关锁国政策,打开国门,对外开放。起初,人们通过旅欧中国人和来华传教士的猎奇式观感介绍或新闻性零星报道,接触到一些肤浅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常识。到19世纪80年代左右,开始有中国留学生运用所学习的西方经济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也有在华外籍人士为了办西学开课的需要,由人代笔翻译引进了一些西方经济学著作等等。不过,这一时期延续到19世纪末,仍基本上停留在支离琐碎地应用西方经济理论,或用传统经济概念和术语来生搬硬套地解释和转述这一理论的阶段。直至20世纪初,以严复翻译亚当·斯密的名著《原富》于1902年正式出版为标志,西方经济学的引进,才突破以往局限于一般经济知识的窠臼,形成西方各种经济学科的系统理论,以翻译或国人自撰的形式,被大量介绍到国内的局面。与此同时,大致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还间断夹杂着关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点滴介绍,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由少到多,由弱渐强。到“五四”运动时期,西方经济学的传播,已占据主导地位,其作用之一,便是以“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式的科学研究方法”,摧毁了旧的封建意识;(注: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第10页。)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介绍和传播,经过近20年的曲折积累,同样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此以后,政治经济学领域内的理论斗争也就变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经济学之间的斗争”。(注: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7月版,第473页。)
通过以上粗浅的考察,不难看出,中国经济学命题的提出,实在离不开舶来经济学的引进这一历史前提。这段历史,若从1840年算起,有整整一个世纪。在这100年间, 几乎经历了一个经济思想领域内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先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被舶来经济思想所否定,然后在舶来经济思想所铺垫的基础上,又以扬弃的方式,提出建立中国经济学的问题。如果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列入舶来经济学的范畴,那么还可以对这个否定之否定过程,采取另一种表达方式。即先是中国带有浓厚封建意识的传统经济思想的统治地位,被舶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所否定,然后舶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学为了维护自己已经夺得的支配地位,又对同样舶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一新生事物进行抵制和攻击,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却成为创立中国经济学的指导依据。至此,是否可以这样说,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学主张,强调的是单纯依靠舶来经济学不能解决中国经济问题,这无疑是正确的;可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又正是舶来经济学的渗入,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才为中国经济学主张的提出,创造了条件。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妨再举出我国“经济学”译名之由来的例子,以资佐证。
在中国的传统语汇里,从未有过“经济学”一词,它是借用古代汉语中“经济”这个称谓“经世济民”或“经邦济国”之类的缩略语,加以改造而成的新创词汇。在这里,姑且不论有人认为“经济学”译名原来是中国人首先使用,然后才被日本人所借用这个说法;(注:参看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第9页注①。 )也不论时人有关近代以后的“经济”一词,因“单纯讲追求财物的合理性而失去了本来面目”这种慨叹;(注:日本山崎益吉语,转引自叶坦:《“中国经济学”寻根》,《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而仅以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来进行考察。早期国门洞开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人们尚不知economy或economics一类的西文词汇为何物,也没有对应的译名。大约从1867年起,实际是到1880年才以正式出版物的形式确定下来,即最初选择了“富国策”的译名或其衍变名称如“富国养民策”、“保富述要”等。到19世纪末叶,这一译名开始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挑战。内部的挑战主要指国人在原有译名之外,又先后自创了“理财学”’、“资生学”’、“生计学”等新的译名,惟各持一辞,未能定于一尊。外部的挑战则主要指日本“经济学”译名的传入,如梁启超早在1896年的《变法通议·论译书》中,就提到泰西的富国学之书,“日本名为经济学”。不过,这一译名因在形式上与中国传统的经世济民观念相抵梧,故曾遭遇国内人士不同程度的抵制。从20世纪初叶起,由于留学日本热潮推动国人一度以日文读物包括经济学著作作为寻求新学的主要来源,遂使“经济学”译名从各种已有译名中脱颖而出,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直至20年代以后,最终成为我国约定俗成的统一译名。
王亚南先生在他的书中,也提到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译名的来源问题,如谓这个译名是沿用日本的,而严复则原译为计学等。但他藉此要强调的是,经济科学原先完全或主要由日本转输到中国,后来即便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形的演变,和中国文化水准相应提高,已渐能自行直接输入,仍不曾脱离:“述而不作”的阶段。(注:参看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第296—297页。)其言下之意是,直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都只有舶来经济学,而没有中国经济学。这确系事实。我们的考察无非是要说明,从近代历史上看,没有舶来经济学,就没有中国经济学。如果连基本的经济学概念都没有,又何来中国经济学。所以说,不能把舶来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二者截然对立起来。
三
中国经济学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继承关系,对此,王亚南先生的书中没有作直接的回答。但从他讥讽那些国粹主义者认为孔子的《论语》中有经济学原理,因而孔子是大经济学家,以及鄙视某位经济学博士称王莽的经济措施是近代统制经济的渊源这些言辞来看,(注: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第297页。 )似乎在批评他们用“一切古已有之”的幻想来附会和攀比舶来经济学的同时,也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采取了不屑一顾的态度。若真是如此,则无异于切断了拟议中的中国经济学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间的联系。
我们在前面曾经指出,舶来经济学的传输,尤其是在它的初期,遭到了国内传统经济思想的顽强抵抗。所谓国粹主义者的言论,恐怕也可以归属于这种抵抗的表现形式之一。可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从资本主义经济环境中所孕育产生的舶来经济学,以其新锐之势,终究取代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经济条件下所形成并凝固起来的传统教条在经济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失去其统治地位后,是否还具有其影响力。这大概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去看。
一方面,中国自古以来几千年的经济思想,由于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一直保持着独立发展的态势,尤以清朝的天朝自大思想而达到其顶瑞。长此以往,在经济思想领域,自然也就习惯于一种封闭条件下的思维模式。这样,面对倚仗船坚炮利优势涌入中国的包括各种西方经济学说在内的外来思潮,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也就在情理之中。而且,即使后来这一传统经济思想在与西方舶来经济思想的较量中败下阵来,那种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封闭或半封闭思维模式,仍不可能轻易退出人们的思想习惯,而在暗中作祟,阻碍他们用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之长,来创中国经济思想发展之新。如果说,在20世纪上半叶,尽管各种西方经济学说充斥于国内,却很少看到能运用其中的合理要素结合中国实际来进行经济理论创新的代表作,那么,究其原因,这既有当时客观条件的局限,以及王亚南先生所说的对于舶来经济学盲目崇拜的劣根性,也不可否认传统思维模式的干扰和掣肘。此外,传统经济思想中还包含着其他一些消极因素,其残留影响的持续与顽固,显然同创立中国经济学的宗旨,是相悖的。
另一方面,历史是割不断的,传统经济思想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不论如何进行评价,却是客观的存在。它通过代代相传,深深渗入人们的意识之中,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中华民族特色的一个组合部分。因此,就像忽视发展和创新,历史传统便会趋于保守落后和停滞不前一样,否定传统的继承,发展和创新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尤其是在中国这样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经过长期积累所沉淀下来的那些经济思想传统,是不可能挥之即去的。虽然在舶来经济学浪潮的冲刷下,近代以来的中国经济思想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似乎历史传统已经消失得全无踪迹。但稍加思索,就不难发现传统经济思想中的一些基本要素,仍以各种形式被保留下来,而且这些传统要素的历史积淀愈深,它们的持久影响力也就愈大。(注:参看谈敏主编《新中国经济思想史丛书》的总序,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8—10页。)这些经济思想上的深刻民族烙记,不是根据此一时或彼一时的主观价值判断来任意加以选择的,而是既定的历史前提。同此理,中国经济学的创立,也不可能摆脱或回避这一历史前提,毋宁说,它只能在历史给定的前提下来发展自己。只不过这个历史前提所包含的那些思想传统,决非一成不变,它们会在借鉴吸收各种外来经济学知识和立足本国经济实践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扬弃。
事实上,当创立中国经济学的主张提出应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或者应使政治经济学能应用于“我们的现实经济”和有利于理解“中国经济之特质”时,这里所突出的区别于外国情形的中国实际,理应包含在传统上不同于外国的那些中国经济思想因素。换言之,中国经济学的创立,旨在使政治经济学密切联系中国实际,这一旨意,除了要借鉴和吸取舶来经济学中的合理内容外,也离不开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批判继承和创造发展。否则,撇开了中国自己的这些先行思想(主要指基本理念,而非具体表述方式),中国经济学恐怕也很难称其为“中国”经济学了。
四
谈到中国经济学与舶来经济学之间的关系,还引出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即这种关系究竟是单向的还是互动的。具体言之,舶来经济学对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向现代中国经济学的转变所给予的影响,看来是比较容易确定的;而中国经济学在王亚南先生的那个时代,既然尚处于倡议创立的初期,似乎也根本谈不上对舶来经济学会有什么影响。可是,再往上追溯,若考察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对于舶来的西方经济学的形成曾否有过什么影响,分歧便产生了。很明显,王亚南先生断然否认有过这种影响。他在批驳日本学者泷本诚一说明欧洲重农学派思想的根源完全出自我国古代的“四书”“五经”这一观点时,不仅断言“这段传奇的说明,完全不合事实”,而且分析魁奈所撰写的《中国的专制制度》论著,是仿效中国古代学者的“托古改制”作法,假借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来阐发其理想的政治制度,以讽喻规劝法国国王,其中的农业经济思想与中国的农业“根本没有相同之点”。他的分析,注重于指出重农学派所说的农业,是“大农形态”或“资本主义化的农业形态”,在此基础上所建立的经济理论,是“近代资本主义之最初的系统的发言人”,因而“与中国古代重农思想无涉”。(注: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第297—298页。)这里实际上隐含着这样一个意思,即重农学派学说是近代资本主义农业的最初理论体现,而中国传统重农思想则是古代落后的封建农业经济的观念表现。故后者不可能对前者产生任何影响。由此推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也不可能对西方经济学的形成产生任何影响。
对此,分歧意见并不在于泷本诚一的考据本身是否合理,更何况此君的结论疏于论证,自然难于为人们所凭信;也不在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与西方经济学二者各自依赖的经济基础是否存在着落后与进步的本质差别,因为这是客观事实;而在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因其出自相对落后的封建经济环境,是否也限制了它根本不可能对由比较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孕育的西方经济学产生任何影响。
从理论上看,经济思想一旦产生,便具有了某种相对独立性,不必完全受制于它所由以产生的经济基础的约束。也就是说,古代经济思想完全有可能跨越时间和地域的限制,给予后来的经济思想以某种影响。至于王亚南先生坚持重农学派思想“与中国古代重农思想无涉”的论断,这可能同他引用马克思的理论分析有关。不过,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中,还可以在一部著作里同时看到这样的观点:一方面,与资本主义经济科学有关的原则和定理,“也能在例如古代希腊社会的著作家那里见到,这只是因为一定的现象,如商品生产、贸易、货币、生息资本等等,是两个社会共有的。由于希腊人有时也涉猎于这一领域,所以他们也和在其他一切领域一样,表现出同样的天才和创见。所以他们的见解就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注: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7—268 页。);另一方面,“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注: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6页。)这两段论述其实并不矛盾, 而是相辅相成地表达了历史上出现的任何经济思想,既是特定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物,不可能成为通用的模式,也不妨碍其中那些合理的思想要素,作为人类共同的精神遗产,可供借鉴和继承。这样就为考察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对外影响作用,从理论上铺平了道路。
从事实上看,中国古代以其大一统的悠久历史和长期居于世界前列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曾经在经济思想领域积累起极其丰富并具有鲜明特色的内容,其中同样蕴含着不逊于古希腊人的“天才和创见”,足资珍视。惟因后来的落伍,遂使这些宝贵遗产逐渐被湮没了。直至本世纪初,才由梁启超提出“拟著一《中国生计学史》,采集前哲所论,以与泰西学说相比较”,以示中国经济思想之“壮观”。(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年),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梁启超的这一愿望,并未实现。而在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屈辱状况下,即使有人提及甚至试图整理中国经济思想的历史遗产,竟系藉此让中国人“自知不足”, (注: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 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16页。)或者证明它与今天的欧美经济科学比较,“本无一顾之价值”。 (注:赵兰坪:《近代欧洲经济学说》, 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自序”。)其自信心之沦丧,于此可见一斑。此后虽然出现过几本运用现代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断代历史的专书,终不成气候。难怪有的西方学者妄言,东方国家的古老文化中,没有任何东西“足以同中世纪西方的经院学者们在经济分析方面所做出的良好开端相媲美”。(注:欧·泰勒:《东方经济思想及其应用和方法》,《美国经济评论》1956年5月,转引自赵靖主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导论”第3页。 )真是落后的境遇必然引起落后的思想。以这种扭曲的心态,根本不可能去想象中国经济思想会对西方经济学有过什么影响,假使有人这样做,那也必被指为非份之想,将遭到嗤笑。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中国经济思想从古至今的历史逐步得到比较系统的发掘、整理和总结,过去阴霾笼罩的局面也为之一变。现在,国内许多专题论著运用大量史实资料,展示了祖先遗留下来的关于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并通过中国与西方两个完全独立的经济思想体系之间的对比分析,来证明中国人民在数千年的历史时期中,也创造了不少同西方经济学说相类似的观点。(注:参看胡寄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不仅如此,近数十年来,甚至西方学者中亦不乏有人从中国和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去探索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尤其是儒家经济思想)所具有的持续生命力之奥秘。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当国家走上富强之路,人们抛弃妄自菲薄,恢复了自尊时,才有可能比较客观地去审视中国经济思想的固有成就。这也是事实。
经过新旧对比,再回到原来的话题,来讨论中国经济思想曾否对西方经济学的形成产生过某种影响这一问题,似可以一种比较平和的心境来对待了。这里的切入点,是如何认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与重农学派学说的关系问题。事实上,西方学者早已注意到17、18世纪风靡欧洲特别是法国的崇尚中国热潮,铸就了像魁奈这样被时人称作“欧洲的孔子”的奇特代表人物,并对他创立重农学派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诸如1906—1907年在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祥地,维吉尔·皮诺发表了《十八世纪的重农学派与中国》一文;1909年法国经济学家季德和利斯特合著的《经济学说史》一书,更是无偏见地公开承认重农学派曾从中国古代文化中吸收了若干有益思想。在20、30年代,法文方面有《中国与法国重农主义体系》(1922年)、《中国、重农学派与法国革命》(1929年)、《中国对重农主义学说的产生和发展之影响》(1938年)等著述,并有中国留法学生李肇义以《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主要流派及其对形成重农学派学说的影响》一文,于1936年在第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德文方面有利奇温的《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一书(1923年),其中论证了魁奈学说的渊源,不是古代希腊人,而是古代中国人;英文方面有赫德森的《欧洲与中国》(1931年)和埃儒迪的《重农学派的公正管理学说》(1938年)两部著作,前者确信重农学派曾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并告诫西方经济学家不应在这一考察中存在着思想偏见,后者则指出重农学派的一些基本政治概念来源于对中国制度的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马弗利克的论著,他先是发表了《中国对于重农学派的影响》(1938年)、《中国人与重农学派》(1940年)、《中国对于魁奈和杜尔哥的影响》(1942年)等论文,然后综合而成其名作《中国:欧洲的模范》(1946年),以丰富的史料来证实中国给予重农学派的影响之强烈。此作曾引起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其《经济分析史》中注意到有关中国人对重农学派产生过影响的推测;而同样享有盛誉的马克·布劳格的《经济理论的回溯》一书,也提及马弗利克的著作关于斯密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新奇见解来自于魁奈这一证明是吸引人的研究。惟西方学者的研究,精于重农学派背景及著述之类史料的搜集和考证,而对中国古代思想和制度的分析,则有隔靴搔庠之嫌。
在中国和日本学术界方面,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早期大多是转述西方学者的有关论著而作不同程度的发挥。其中有的中国学者在当时自卑感盛行的氛围里,还一面转述,一面声明这不是“国粹主义”、“夜郎自大”、“狭义的民族主义”,或“非敢谓中国经济思想果胜欧西”云云,生怕引起别人的误会。其实,深入考察重农学派所处的历史背景、他们追逐中国典章制度的主客观基础、由此引起其经济理论体系的变革和特色、尤其是魁奈自撰《中国的专制制度》所透露的寓意,可以发现,重农学派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间的关系,决非简单的“托古改制”一语可以了断。相反,此学派在经济学说史上的各种独特贡献,如自然秩序、《经济表》、自由放任、重农主义、纯产品、土地单一税及其他观点等等,几乎都或多或少地留下了中国思想的痕迹。其中有的是完全根据中国思想的启发而创为新说,有的是以接受中国观念为主而辅之以若干西方论据,也有的是用中国的例证去加强和充实重农学派原有的论点,或是基于西方的某些传统而补充中国的类似资料为佐证,还有的纯粹是从中国古代传统中借助亡灵来给他们帮助。无论如何,把重农学派基本观点作整体考察,凡属在西方思想源流里被视作具有原创意义的那些特殊内容,均比较容易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找到其先行近似样品。所以说,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不仅以它自身的光辉成就,而且应当作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直接思想起源之一,被载入世界经济思想的史册。(注:参看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这个结论,过去或许被认为是不可思议,而在今天,连不少海外学者都在认真加以思索并试图予以加强和扩展。如出生于爱尔兰的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家L·扬格,曾在1996 年发表《市场之道:司马迁与看不见的手》(The Tao of Market:Sima Qian and the Invisible Hand)一文。其中论证司马迁早在亚当·斯密之前就在其《史记·货殖列传》提出了市场机制概念和“看不见的手”的等价隐喻即“低流之水”;认为司马迁在价格机制的阐述上远比斯密详尽和充分;推测斯密《国富论》的中心思想,可能是在他造访巴黎期间,通过杜尔阁及其正在接待的两位中国学者,了解了司马迁的思想从而受到启发,或者说,可能直接从杜尔阁和两位中国人那里“盗用了”司马迁的贡献;谈到中国思想通过重农学派已植根于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之中是早已被证明之事;司马迁与中国的重农主义结盟,其思想启发了作为斯密盟友的法国重农主义学派;等等。(注:见《太平洋经济评论》(Pacific Economic Review )1996年第一卷第2期, 转引自蒲勇健:《司马迁:先于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家》,《经济学消息报》1998年3月6日第4版。 )据说此文曾在香港经济学界引起轰动,认为它可能导致整个现代经济思想史甚至现代西方文明的历史都应重写。又如香港《远东经济评论》的总编迈克尔·瓦蒂基奥蒂斯曾于1999年6月10日撰文指出, “虽然在进入工业时代的时候中国可能是落后于欧洲了,但是中国对现代欧洲经济思想的贡献是巨大的”。其依据是欧洲在启蒙时代认为中国比较开明,故“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思想是在中国人理论的帮助下,由18世纪中叶的耶稣会传教士得出的”。文中引用当代英国哲学家约翰·詹姆斯·克拉克的说法,认为由亚当·斯密创立的现代自由市场经济原理,系受到魁奈的“自由放任”思想、即政府政策不应干涉经济自然法则运行的思想启发,而这些思想的来源又是老子的《道德经》,是魁奈把这个道教经文中的“无为而治”概念翻译成“laissez-faire”(自由放任), “这一思想对斯密影响很大”。(注:参看《参考消息》1999年6月18 日载文《英国哲学家克拉克认为西方自由市场原理源于〈道德经〉》。)这些文章的论述,虽然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者耳熟能详的内容,而且未能超出拙著《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的范围,但它们却反映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曾对法国重农学派、从而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这一结论,正被更多的学者所接受。
附带指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对于西方的影响,恐怕还不仅限于上述结论。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我国早期于1911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陈焕章, 在其由大学刊行的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序言中, 曾自称是一名采矿者,努力从孔子著作这座蕴藏着富矿资源的大山中去采掘一种特殊的矿石,“把它奉献作为世界的产品”,供人类使用,以求“为人类的知识增添了某些内容”。 (注:Chen Huan- chang,
The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 New York,Colunlbia University,1911,"Author's Preface".p.7.)的确,这一研究成果就像是一座桥梁,沟通了中国古代主流经济思想与西方世界的联系。如熊彼特在他的《经济分析史》中,就是通过陈焕章的这部著作,试图从古代中国,去寻找世界上从事经济分析努力的最早痕迹。更值得注意的是,新近的研究表明,在30年代美国为对付经济大萧条而推行“新政”期间,时任农业部长的亨利·A ·华莱士(后任副总统)曾提出“农业调整法”,其指导思想,据他自己说,是为了“把中国古代农业政治家的实践——‘常平仓’(ever normal granary )引入美国农业立法中”,而“常平仓”的名称,便是从陈焕章的书中得来的。“农业调整法”曾为解决当时的农产品过剩问题起到了缓和作用,并构成美国农业制度的一个基础。如此重要的农业经济政策,其创议者华莱士本人一再声明这是他多年来关注中国古代农业问题并对陈书中提出的“常平仓”法悉心研究的结果,而他周边的知情者也在不同场合证实了这一说法。(注:见李超民:《华莱士与常平仓:美国经济制度中的中国思想》(未刊稿)。)于此可见,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的“天才和创见”,不止对于早期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及其继承者,有着不同凡响的吸引力;而且对于后来西方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同样有其不可忽略的启迪作用。
话题扯得远了些,但其宗旨是始终一致的。过去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人在漫长的年代创造和积累起来的经济思想成就,曾在世界经济思想的宝库中独树一帜。尽管17世纪以后,中国经济思想从整体来说,落后于西方,但这并不能阻挡它经过新的时代洗礼,重现其智慧与辉煌。这应当也是创立中国经济学的宗旨。
五
在讨论了以上问题后,现在,似乎可以对中国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说上几句话了。
第一,中国经济学的基础,应当深深扎根于中国现实经济的土壤之中。在这方面,王亚南先生的创议,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的中国经济学主张,在当时弥漫着盲目照搬套用舶来经济学观念的环境中,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致力于使政治经济学能够适用于理解和指导中国自己的经济实践活动,并以此来观察和解释世界经济问题,确实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其真意倒不仅在于出几部适合中国人阅读的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读本,而在于让大家明白要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最终只有靠中国人自己。经济学作为致用之学,如果脱离了实际,也就失去了它的生命力。同样,中国经济学的生命源泉,亦来自中国的实际。或许,这就是中国经济学创立的初衷,同时也决定了它的未来发展方向。
第二,中国经济学之区别于舶来经济学,是由于中国有着独特的经济环境、人文背景、理念习俗、历史路径等,由此产生的经济课题,不可能简单地诉诸由舶来经济学来越俎代疱,但这一切,都不应成为拒绝或排斥舶来经济学的理由。各种类型的舶来经济学,虽然出自不同国度、时期或经济利益集团的要求,其中毕竟包含着理论探索与科学研究方法方面的智慧结晶,作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可供中国经济学建设加以借鉴参考和采择吸收。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也正是向西方学习运动的一个集中体现。过去,西方列强凭借武力迫使中国开放门户,从而在丧权辱国的条件下造成国人被动地接受舶来经济学的局面,这是一个在长期封闭环境里养成的盲目排外心理与受舶来品影响而滋长的崇洋媚外观念二者相互冲突和同时并存的痛苦过程。今天,我们是在改革开 放政策的指导下,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主动地汲取国外经济学说的一切合理因素以为我所用。将来,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仍要坚持走对外开放之路,自我封存是没有出路的。
第三,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应珍视我们祖先所留下的经济思想遗产。这并不是说,要让早先那种“一切古已有之”的愚昧思想死灰复燃,而是不得不承认,经济思想从而经济学有其民族传统或民族特色,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尽管自1776年《国富论》发表以来,经济学被认为开始独立成为一门科学,再经过西方学者历代不断的更新和改进,已经成为目前世界上最有权威的范式;尽管中国经济思想在过去二、三百年间明显落后于西方,并日益转向从舶来经济学中去吸取滋养,但事实证明,经济学的民族个性终究难以被抹煞。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和历史久长的发展中国家,面对各种复杂的经济问题,既不可能期待有现成的舶来经济学模式为你度身定制,也不可能完全置本国经济思想的传统于不顾。传统经济思想中的一些基本观念,通过长期的潜移默化过程,往往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思想深处,于有形或无形之中成为人们处理经济事务的行为规范。当然,传统的东西良莠不齐,传统也可以被改变。但传统不会消失,也不会被割断。中国经济学的一个任务,应当是从传统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取古今中外的一切文明成果来发展自己。
第四,中国经济学应在世界经济学中占有一席之地。世界是丰富多采的,世界上的经济学也是丰富多采的。以中国人的智慧和目前正在从事的伟大实践,完全有理由为世界经济学的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从将来看,我们的优势,正在于我们的特色。因为着力于研究具有鲜明本国特点的经济实践,才最有可能提出理论上的创新,并进而对世界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否则,脱开自己的特色,一直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充其量,也只能算作一个合格的转述者,这显然不是中国经济学界的奋斗目标。在历史上,我们的先人曾经创造出许多值得称道的经济思想成就,昂首走在世界古代经济思想的前列。后来的固步自封,导致了落后。但这并不能阻挡中国人民在历经坎坷和曲折之后,重新振作起来,以令世人瞩目的巨大创造力和经济成就,再现中国经济学的未来辉煌。
标签: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政治经济学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王亚南论文; 奥地利经济学派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西方经济学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形态理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