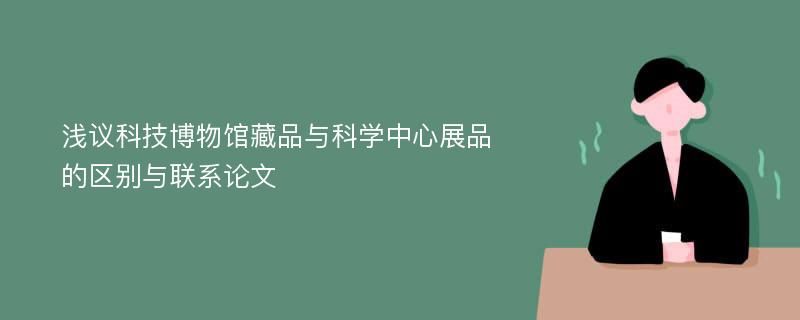
浅议科技博物馆藏品与科学中心展品的区别与联系
龙金晶①
【摘要】 科技藏品与互动展品的关系,是研究博物馆与科技馆教育功能关联性的基础。本文从科技藏品与互动展品的不同来源与特性入手,分析了科技藏品与由科技藏品转化而来的“互动展品”之间的关系,以及转化的原因和途径,并从教育学和认知的角度分析归纳了科技藏品与互动展品的本质差异。在此基础上,说明依托科技藏品的博物馆教育与依托互动展品的科学中心教育的不同思路和策略。
【关键词】 科技博物馆;科学中心;藏品;互动展品;科学教育
科技博物馆和科学中心都是依托科技类展品开展科学教育的社会教育机构。两者由于各自展品属性与特征的不同,使得两者在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上存在着较大差异。科技博物馆以承载科技发展历史文化的藏品作为科学教育的主要资源和载体,而科学中心则以体验感悟科学原理的互动展品作为科学教育的主要资源和载体;科技博物馆创立之初偏重收藏、研究,后来又加强了教育功能,而科学中心兴起伊始就将互动体验和教育作为根本要务。
从“腾笼换鸟”到“绿色蝶变”,面对曾经伤痕累累的长江,从上游、中游到下游,跨省市协同发展的实践在探索中前行。这一切,正是源于“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共识的深入人心和行动自觉。
一、科技藏品与互动展品的来源与特性
(一)科技藏品的来源与特性
博物馆的科技藏品来源广泛,既有前人遗留的文物,又有来自考古发掘的文物,还有通过其他渠道搜集的自然标本、科技成果和工农业产品等。藏品是一定物质形式的信息载体,是反映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实物见证。随着人类社会与科技的发展,科技博物馆的藏品种类也随之丰富。总体而言,科技博物馆的藏品主要有三类:动植物、矿物、化石等自然标本;机械设备、工业产品实物或模型等工业技术产物;以科学仪器、科学实验、技术发明和科学考察对象为原型的科学展品[1]。
藏品真正的价值在于它蕴含的信息,即人类文化遗存的信息和自然遗存的信息。人类文化遗存信息,是指过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遗存物所包含的信息。自然遗存信息,指自然界中除去人类文化遗存信息之外的一切客观环境的遗存信息。藏品正是由于包含这些信息,才具有了人类和人类环境见证物的地位。从这个角度看,藏品是储存信息的载体。它们不仅承载着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信息,而且记录着发现、发明、应用过程及其背景的信息以及这一过程中所体现的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和科技与社会的关系等信息[1]。
MOSFET有利于提高电源效率,减小开关电源体积,因而得到了广泛应用。论文选择型号为IRF3710的MOSFET作为本系统的功率器件。
同时,博物馆的藏品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特点,它是原始实物资料,与其他物品不同,不能进行再生产,也不能用其他物品代替。即使能够按照藏品的原状制作出来,或者能够找到同样的物品进行替代,也已失去了原物固有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博物馆藏品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科技藏品的以上特点,使它成为博物馆收藏、研究的对象和展示、传播、教育的资源。
(二)互动展品的来源与特性
科学中心的互动展品与博物馆的藏品有很大的区别,它不是反映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实物见证,而通常是人造的物品。虽然互动展品也包含着大量信息,但这些信息不是人类文化遗存的信息和自然遗存的信息,而是为了某种教育目的人为附着于展品之上的信息。
科学中心在建立之初即定位为面向观众的“感受”(体验),而不是面向“实物”[2]1。面向感受(体验)的实践场所就要有被实践的对象,但是科学中心的有限空间无法放置并提供所有的人类实践对象,诸如飞机、火车、生产车间等人类实践对象也不便进行展示。因此,探索馆创始人弗兰克·奥本海默就想办法把可实践对象中的科学原理提取出来,在保留可实践性的同时,制作出一种新的物品。这类物品既包含科学原理,又有一定的艺术性和趣味性,还可以实践,这就是科学中心里的互动展品。奥本海默曾提及:“探索馆的不少展品是由实验室标准设备或教学演示设备改造而成的,一些身边的事物和自然现象也成为展品的来源”[3]。
由此可见,科学中心的展品是从实验室仪器、自然现象、科学原理、生活用品、工业生产等领域转化而来[4],它主要包括智力因素和艺术因素。智力因素是指科学的概念、原理等,艺术因素是指趣味性和娱乐性、参与性等。与科学中心的互动展品相比,工业设备、实验室仪器等只具备智力因素,缺少了艺术因素。这是由于工业设备是为了解决生产中的问题,实验室仪器是为了科学研究,而科学中心的展品则是为了解决认知和娱乐。制作和使用目的不同,造成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工业设备、科学仪器等需要改进具备艺术因素后方才适合作为互动展品,而自然现象、科学原理等则需要进行再创造和实物转化,才可称其为互动展品。科学中心的展品,是要为观众创造出一个可以实践、体验科学的环境。互动展品的以上特点形成了科学中心最基本的属性。
二、科技藏品与互动展品的关系
(一)部分科技藏品是科学中心互动展品的原型
通过梳理以上科学中心互动展品的来源,我们发现,科学博物馆中陈列的科学家们曾经使用过的科学仪器有些便是科学中心互动展品的原型,例如光岛演示台、真空体验、法拉第笼、怒发冲冠等互动展品。经典展项“光岛”来源于牛顿的光的分解与合成实验,“真空体验”源于著名的马德堡半球实验,“法拉第笼”来源于法拉第的电磁屏蔽实验,“怒发冲冠”则源于静电实验。在部分科学博物馆里至今还可见当年科学家所使用过的这些科学实验仪器,目前它们作为宝贵的历史遗留物被保存下来,成为科学发展历史的见证。
同样,在科学中心也可以陈列一些藏品,当观众精心体验反映某一科学原理的展品时,看一看过去科学家是怎样运用这一原理的藏品也会得到很多启发。科技藏品中所富含的历史信息会给观众带来神秘感和神圣感,还会帮助观众还原真实历史,创设真实情境来辅助观众的体验和思考。虽然一些科学中心不收藏和展示藏品也可以存在,但为了丰富体验内容,也为了使展览的故事线更加完整,目前越来越多的科学中心在展览、教育项目和其它活动中都使用了科技藏品。他们已经发现在科技藏品和互动展品两者之间可以架起一座“双重性”的桥梁[2]143。科技藏品和互动展品的不同,形成了博物馆和科学中心的差别,藏品和展品的共同点又使它们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由此可见,科学中心的互动展品很多是以科学仪器、科学实验、技术发明为原型,它们所承载的科学信息都是以某种形态、成分、反应、运动状态等形式存在于展品的体验过程中。
(二)科学中心互动展品是科技藏品教育功能的深度转化
科学中心几乎没有藏品,取而代之的是人工制作的展品。展品使得原本只能在生产劳动、科学实验、社会生活时进行的实践活动,可以在科学中心中进行了。展品中包含的信息,是制作展品时人为加入的,大多数都是人类经过实践考验的知识,虽然这些信息对一般公众来说是未知的,但是只要观众认真与展品互动都会体验到这些知识的存在。此外,科学中心的展品可以批量生产,一般不具有收藏价值,也无须长期保存,这样的展品观众可以随意操作,不怕损坏。
随着科技博物馆教育理念的进步,其教育功能日益突显,依托科技藏品进行公众教育的手段和方式也逐渐丰富。配套藏品说明、进行讲解和诠释、营造特殊的展览环境和氛围帮助公众加深对藏品的理解。情境学习、场馆学习等教育学理论被引入博物馆教育研究,指导博物馆教育的发展。20世纪以来,在美国科学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建构主义、启发式学习、探究式学习理论成为科技教育研究的热点,也被科技博物馆所关注,并以此为依据寻求突破。
习主席在2014年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开幕式上强调:“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强大的科技创新力量。”在我国发展新的历史起点上,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吹响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
藏品是建立博物馆的必要条件,是博物馆存在的物质前提。因此,任何一个博物馆都必须拥有藏品,依托藏品开展研究工作,并把研究成果传递给公众,这是博物馆的教育目标。藏品的数量和质量,以及研究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博物馆社会地位的主要标志。
随后,以奥本海默为代表的科学中心研究者们想到,不仅要让科技藏品“动起来”,还得让参观者能亲自主导与藏品的互动,实现参观者的自主学习和探究。然而,科技藏品的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使得这一想法和做法无法实现。于是有人想到制作科技藏品的仿制品提供给观众触摸体验。在此过程中,奥本海默想到要更近一步,不仅要让观众了解科技藏品本身所附着的材质、加工工艺、图式纹样等知识信息,还要让观众学习理解藏品蕴含的科学原理和现实应用、学会像科学家那样去思考问题。于是,他将科技藏品中蕴含的原理信息抽取出来进行转化,制作成观众能够动手体验的展品,模拟科学家进行科学实验的过程,引导观众通过展品互动完成观察、假设、实验、解释、验证等科学探究的过程和方法。为此,奥本海默要求:凡是探索馆制作的展品和开发的展览,必须不惜成本,营造出一种“与科学家真实的工作环境一模一样的氛围”,并强调:“每个展览都要围绕学习者来进行设计,以帮助学习者自主地进行发现与探索”[6]。
这种学习方式不仅让博物馆参观活动的趣味性大大提升,而且促进了参观者的认知发展,实现了科学知识、过程与方法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三维学习目标,提升了博物馆教育的效果,得到了广泛认可。20世纪60年代,科学中心快速发展,在短短几十年内风靡全世界,成为科技博物馆领域的一种重要形态。
由此可见,科学中心的部分互动展品虽然脱胎于科技藏品,但是它在转化的过程中提取了科学家进行科学探索的过程,揭示了科学原理知识、科学探究过程等多层次的展品信息。经过转化,互动展品不再单纯是一件科学家使用过的科学仪器,而是承载了科学家使用该藏品进行科学探究活动整个过程的信息。
(三)科技藏品与互动展品的融合发展
由此可见,科学中心是把人类已知的科学的原理、方法、思想融入人工制作的展品之中,观众与展品打交道时,通过观察与展品的互动,通过思考与相互讨论,直接从展品中获得知识。这种学习不再是从一个大脑向另一个大脑传递知识,而是自己从实践中学习。
200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对博物馆定义进行修订,具体表述为:“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常设机构,为教育、研究和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和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9]。“教育”被列为博物馆的首要目的。
法国发现宫创建人让·佩兰与美国探索馆的创建人弗兰克·奥本海默都曾将用于科学研究的实验仪器转化为教学设备为中小学生上课,并由此发明了最初的科学中心展品,再进而把科学中心展品的原型从科学实验仪器逐步扩大至生产工具(机械)、自然和生活中的科学现象[2]1。
三、基于科技藏品与互动展品开展科学教育的差异
博物馆与科学中心,都是社会教育机构,都是为教育公众而举办的。但是,由于博物馆和科学中心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发展的过程不同,观众获得的知识不同,特别是科技藏品与互动展品的本质属性不同,因此它们的教育方式也不完全相同。
(一)基于科技藏品的科学教育
德意志博物馆首先想到让科技藏品“动起来”。他们将之前陈列展示的工业设备揭下盖板,露出内部结构,通电运转进行演示,引导观众观察并深入了解藏品的科学原理。“动起来”的科技藏品不仅为博物馆带来了大量观众,而且促进了参观者对藏品的认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仙草性味涩、甘、寒,自古以来用作清暑解渴、凉血之良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仙草具有抗氧化、抗损伤、抗缺氧、降血压、降血糖、降血脂、抗菌等多种功效。
然而,藏品中包含的大量未知信息,不是一般观众可以自己解读的,必须由专业人员研究验证之后,传递给观众。因此,通常情况下,博物馆的藏品只能静态陈列在有保护装置的展示柜里,通过专业人员的研究解读将信息传递给观众,博物馆通常也是通过静态陈列展览的方式来实现对公众的教育。
类似地, ⊇1)1).由命题2.3知,是X的一个犹豫模糊反群滤子.综上所述,是X的一个犹豫模糊闭反群滤子.
静态陈列的藏品需要研究员、教育人员和设计人员赋予它们诠释和支持,才能与观众进行沟通。“诠释”是指可帮助说明展览内容的行动和元素,解释和传达这组藏品及它们所代表的知识和信息,表现真实物品承载的意义,通过诠释让其对观众变得有意义[7]。因此博物馆是通过研究人员为中介让广大观众与藏品进行交流与沟通[2]140,而观众获得的知识往往是从研究人员阐释中获得的间接经验。
(二)基于互动展品的科学教育
博物馆兴起于14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最初以私人收藏为主,以保存、研究为目的,仅供少数人观赏。18世纪末法国卢浮宫首先向公众开放,此后博物馆成为社会服务机构,教育职能得到发展。20世纪以后,博物馆的教育职能不断扩大,其教育属性越来越得到社会认可。1974年6月,国际博物馆协会于哥本哈根召开会议,明确了博物馆的定义:“博物馆是一个不追求营利的,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永久性机构,为研究、教育和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和人类环境的见证物”[5]。教育被列为博物馆的三大目的之一。
观众操作体验展品的过程,其实就是再现当年科学家们对于科学现象的观察、分析、总结和归纳的过程。这个参与过程可以使观众体验和关注其中的科学现象,并将科学家们以科研为目的的科学探究实践,转化为观众以学习为目的的科学探究实践。经此过程,实现了观众对于展品蕴含的科学信息的认知,使观众获得“直接经验”[8]。
科技藏品和互动展品虽然有很大区别,但仍然有许多共同的地方。首先,科技藏品和互动展品都是物质的、有形的;其次,它们都包含有信息,这些信息都是人类认知和学习所需要的,而博物馆和科学中心都是利用物品中附着的信息来开展科学教育。有了共同点,博物馆和科学中心就可以相互融合,找到共同发展的道路。事实上,科学中心的部分展品本身也是从科技藏品仿制而来,如伽利略测重力加速度仪等。
在各种3D打印技术中,熔融沉积造型技术(FDM:Fused Deposition Modeling)虽然精度和工件强度相对较低,但设备及材料成本低,对环境的要求低,得到了迅速的推广,目前市场上多数产品均采用此技术[3]。教学模型不同于实际工件,对精度和强度要求较低,因此,选用成本相对较低的FDM技术进行教学模型打印。
通常情况下,大多数人的科学知识都是通过图书、杂志、电视以及学校里开设的物理、化学、生物等科学课程来获得,是一种间接经验的学习,它不同于科学家们通过科学实践和实验获得的直接经验。没有直接体验,对基本的科学现象和科学原理就很难理解。科学中心建立的初衷就是要给观众创造一个获得直接体验的机会,“互动展品”就是观众操作体验的对象。只有通过与展品的互动,从多个方面接触科学,观众才能在实践中获得直接经验。科学中心的主要教育目的是让观众通过参与、实践了解科学的本质,主要的教育形式是体验,体验获得的是直接经验[1]。
红河特大桥元阳侧主塔位于二叠系下统茅口阶(P1m)细晶白云质灰岩分布区,综合地形坡度40~50°之间,覆盖层厚度小于2m,下伏基岩为细晶白云质灰岩,钻探揭露岩体以中风化为主,局部分布有强风化、强溶蚀夹层,浅表部局部溶蚀发育外,深部岩芯上基本未见溶蚀现象,岩溶弱发育,深部中风化岩体呈块状,较为完整,强度高,岩层陡倾坡内,工程地质条件较好。
按照光学成像原理,物点和像点及光心三点一线,此直线上任何一点对应同一像点,因此,当A、A′、O共线,B、B′、O共线,C、C′、O共线,D、D′、O共线,且有长度lA′B′=lAB,lC′D′=lCD,A′B′//OX,C′D′//OX时,目标AB等效于A′B′,目标CD等效于C′D′。
由此可见,由于科技藏品和互动展品之间的差别,观众从博物馆与科学中心获得的知识类型是不同的。观众在博物馆获得的是间接经验,而在科学中心获得的是直接经验。
(三)科技博物馆藏品向科学中心展品转化的依据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展览的形式和手段也越来越丰富,为博物馆和科学中心提供了互相学习借鉴的可能。例如:科技博物馆也可以根据对藏品研究的结果制作一些特殊的展品。它们可分为藏品的仿真展品和模拟藏品性质和特点的展品。前者是以一定程度形式相似的模型再现藏品,表现其外在的特征信息;后者是表现藏品内在的特征信息。把这样的展品放在博物馆,博物馆就不仅具有研究和陈列的功能,观众也可以进行互动和体验,可以更好地辅助观众学习,加深对藏品的理解和认识。
3.4.1 各地年降水量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和80年代末出现异常偏多,天峻年降水量在2005年也发生了异常偏多,年降水量出现异常偏少的年份和地区较少,仅出现在刚察(1990年)、天峻(1978年)和海晏(2000年)。
博物馆的教育效果逐渐成为衡量博物馆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科技博物馆陈列式的静态藏品在调动公众学习兴趣方面和提升参观效果方面收效欠佳,多数公众在走马观花式的参观模式之下,并未对参观内容留下深刻印象。因此,科学中心的展品“可动”通常被认为是相比于博物馆藏品的一个重要优势。
不少科学中心为了到达“动起来”的目的,通过增加按钮、多媒体触摸屏等方式来实现,但实际的展示教育效果并不好。正如国际著名科技博物馆专家詹姆斯·布雷德伯恩所指出的:这些科学中心都制作了大量的“动手型”展品,以推演出一些具体的科学现象或演示一定的众所周知的原理……很多科学中心的设计者都意识到他们有必要把展品设计得更有趣,于是刻意增加一些不必要的互动,用大众通俗文化的色彩包装常规的展品,或为使用新技术而使用新技术……这种方法背离了科学中心的基本宗旨,科学中心成了裹着糖衣的学校,其目的是诱使参观者进入乏味的学习[10]。
那么究竟怎样的“互动”才是有意义的,才不是“为了互动而互动”呢?答案就在于真正的互动表现在“基于实物的体验”和“基于实践的探究”获得直接经验,本质特征就是:“引导观众像科学家进行科学实验一样观察体验展品”,“动”的过程应该是模拟科学家做实验的过程,这不是简单地按按钮就可以实现的。“《美国探索馆展品集》中的绝大多数展品均可以设计出这种如同科学实验一样的教育活动”[11],涵盖了科学家观察现象、提出问题、进行假设和解释,操作展品进行实验论证的全部过程。
由此可见,通过科学中心展品所谓的“有效互动”,就是要“引导观众像进行科学实验一样观察体验展品”,而科学实验的过程就是科学探究的过程。让·佩兰与弗兰克·奥本海默都曾将科学实验仪器转化为科学中心的互动展品,正是因为这些科学试验仪器承载了科学家做科学实验活动的信息。
不论是自然标本、仪器和设备等实物展品,还是以实验装置、机械工具、自然或生活中科学现象为原型而研发的展品,它们所承载的科学信息都是以某种“现象”(形态、成分、反应、运动状态等)存在于展品之中,而不是文字、语言、图表等形式。当初,科学家们正是通过对于这些“现象”的观察体验(包括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和分析,获得了认知,并归纳为我们今天在教科书中所看到的原理和知识。在教育学上,科学家的这些认知被称为“直接经验”(指通过亲身实践获得的知识)。而科学家们的研究、考察、实验的过程就是科学探究实践的过程。在科学中心中,通过展品、环境、辅助展示装置的设计和展品辅导等方式,使观众体验和关注其中的“现象”;并可将科学家们以科研为目的的科学探究实践,转化为观众以学习为目的的科学探究实践[1]。这就是科学中心互动展品的本质特征。
但是,科学家当初的科研对象或工具(实验仪器、自然标本、发明物等,即藏品),其科学现象不一定很明显,不易被发现,有的还掺杂着干扰观察与认知的其它现象,有的还须掌握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因此,这些科研对象或工具有时不适于观众直接观察、体验、认知。所以,需要重新设计,将这些原型转化为互动型展品。通过设计、转化,排除其它因素的干扰,将最有利于观察、体验、认知的科学现象分解、强化、显性化出来。
以“旋转的金蛋”为例,可将展品的互动过程分解为“操作展品的现象是什么?”“假设现象产生的原因”“操作展品进行实验”“对假设的结果进行验证”等过程,分别对应于科学家做实验过程中的观察现象、提出假设、实验验证、做出解释等几个探究程序。观众们的认知便是在操作体验展品的过程中完成的。因此,“互动展品”模拟了科学家探究科学原理的经典实验情境,兼顾了显著性和直观性两个因素,这样的实践情境激发了科学家的思考和认知,也同样能够激发受众思考。“动脑”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是一种有效互动。
四、结语
本文从科技藏品与互动展品的来源入手,分析了科技博物馆科技藏品和科学中心互动展品的特性。科技藏品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互动展品则具有智力因素和艺术因素两方面特征。通过梳理科技藏品和互动展品的来源发现,科学博物馆中陈列的科学家们曾经使用过的科学仪器、生产工具等藏品有些便是科学中心互动展品的原型。作者在分析科学藏品作为原型以及原型转化物“互动展品”之间的关系基础上,总结出两者的本质差异,以及原型转化的原因和途径。
笔者认为:科学中心互动展品的“有效互动”表现在“基于实物的体验”和“基于实践的探究”来获得直接经验,其本质特征是“引导观众像科学家进行科学实验一样观察体验展品”,“动”的过程应该是模拟科学家做实验的过程。因此,科技藏品在转化为互动展品的过程中,要遵循“分解-体验-认知”[12]的规律,能够将展品的互动过程分解为科学探究的观察现象、提出假设、实验验证、做出解释等几个探究程序。只有如此,科学中心才能使受众在体验展品过程中获得直接经验,激发思考,最终达到认知效果。这也是科学中心与科技博物馆最本质的区别。
在当前国际化背景下,社会对英语能力的要求逐步提高,而当前的高中英语教育仍存在诸多问题,将应试作为主要目的,导致学生综合语用能力低下,其中输入(阅读)教学有很大突破空间。在“互联网+”时代,应重视多媒体与教学结合,扩大学生阅读量,拓宽阅读范围,增强学习兴趣,提高综合能力,在基础课程、校本课程、指导课程、远程交互课程、课外阅读补充方面,为教学创造资源共享的环境。教师应分析学情,根据学生需求及教学环境,合理运用多媒体,改进教学理念与模式,采用新型教学策略,提高学生的英语阅读能力和综合语用能力。
参考文献
[1]朱幼文.教育学、传播学视角下的展览研究与设计——兼论科技博物馆展览设计创新的方向与思路[J].博物院, 2017(6):70-80.
[2]维克多·丹尼洛夫.科学与技术中心[M].中国科技馆, 编译, 北京:学苑出版社, 1989: 1, 140, 143.
[3]“科技馆创新展览设计思路及发展对策研究”课题组.科技馆创新展览设计思路及发展对策研究报告[M]//科技馆研究报告集(2006-2015), 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 2017:603-629.
[4]王恒.蕴含先进科学教育理念的科技馆展品宝典——写在《探索馆展品集》中文版出版之际[J].自然科学博物馆研究, 2017(3): 87-92.
[5]王宏均.中国博物馆学基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26.
[6]罗伯特·赛姆帕.试验样板法——浅论探索馆展项之设计[M]//科技馆研究文选.王建国, 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8:373.
[7]博伊兰.经营博物馆[M].黄静雅, 韦清琦, 译, 北京:译林出版社, 2010:139-140.
[8]袁媛.提升科技馆展品科学传播效果的方式[J].自然科学博物馆研究, 2018(4):52-59.
[9]宋向光.国际博协“博物馆”定义调整的解读[N].中国文物报, 2009-03-20(06).
[10]詹姆斯·布雷德伯恩.寻找我们的道路:适应21世纪的博物馆学战略[M]//伯纳德·希尔, 埃姆林·科斯特.当代科学中心.徐善衍, 欧建成, 石顺科, 等译,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20-55.
[11]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科技馆专业委员会.科技场馆基于展品教育活动项目调研报告[M]//科技馆研究报告集(2006-2015), 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 2017:720-748.
[12]陈闯.“分解-体验-认知”——探究式展品辅导开发思路[J].自然科学博物馆研究, 2016(4):46-52.
① 龙金晶:中国科技馆资源管理部副主任,副研究员;研究方向:科普场馆科学教育,流动科普设施发展;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5号;邮编:100012;Email:longjinjing888@sina.com。
引用格式: 龙金晶.浅议科技博物馆藏品与科学中心展品的区别与联系[J].自然科学博物馆研究,2019(4):20-26.[Long Jinjing.Differences and Connections between Collections of Science Museums and Exhibits in Science Centers[J].Journal of Natural Science Museum Research,2019(4):20-26.].DOI:10.19628/j.cnki.jnsmr.2019.04.003
(编辑:王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