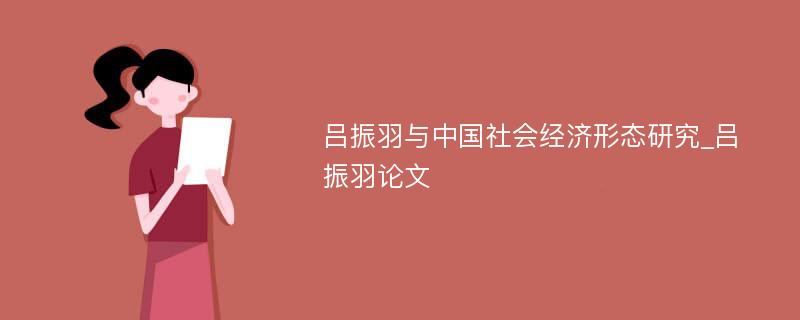
吕振羽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经济论文,中国论文,形态论文,吕振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00)04—0001—10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有了近80年的历史。20世纪初,国内一些出版物上有人开始片断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但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注意。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9年以后,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不仅在介绍唯物史观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而且开始用唯物史观来观察中国历史。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国内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由此在我国理论界和史学界又引发了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郭沫若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被公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代表性的奠基之作,它一问世就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为契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史坛的一支新军迅速崛起。从20年代到30年代,可以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童年期。在这个历史阶段,有一批先驱者筚路蓝缕,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长作出了重大贡献,吕振羽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在纪念吕振羽同志百年诞辰的时候,我们重温他的著作,缅怀他的业绩,对于了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史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仅就吕振羽同志有关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谈一点学习的心得。
一、《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的学术贡献
吕振羽同志是以参加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在史学界崭露头角的。他依据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提出了自己关于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认识:殷代以前为原始社会,殷代为奴隶社会,西周至鸦片战争为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之后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的这个分期意见,后来为相当多的历史学者所赞同。
吕振羽关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研究的第一个重要贡献,是肯定中国在有成文历史之前经历了母系和父系氏族社会。在他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出版之前,中国史前时代是谈不到有真正科学的研究的。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中国古代史》)在“上古史”篇中以“传疑时代”命名太古三代。书中虽然也从西方社会学引进了“渔猎社会”、“游牧社会”、“耕稼社会”等概念,但并没有能够阐明社会关系的本质特征;而且把夏商周三代与太古时代同列为“传疑时代”,也显然混淆了传说时代与文明时代的界限。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认为,“对于东周以前的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古代的书只有一部《诗经》可算得是中国最古的史料。”顾颉刚在《古史辨》第1册自序中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 为考辨伪书伪史开创了新的局面。但他和胡适一样,把史料和历史混为一谈,结果得出了“照我们现在的观察,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注:顾颉刚:《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古史辨》第1册,北京朴社1926年出版。 )的错误结论。当顾颉刚热衷于辨伪研究时,他已经知道罗振玉、王国维在甲骨文考释方面所做的工作。他甚至也“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我的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面致力罢了。”(注: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自序。 )但是他认为自己“考古学的素养也缺乏”,宁愿只做考辨伪书伪史的工作,而从未想过把历史文献的考辨和考古实物的研究结合起来,探索古代历史的真实面貌。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的贡献,恰恰在于他避免了疑古派的片面性和把史前社会排除在历史研究视野之外的错误,指出“古籍神话中保留着的神话传说式的记载,不仅能正确的暗示着一个时代的历史意义,并且还相当丰富。”(注: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北平人文书店1934年出版,第82页。)他把文献记载的神话传说与新出土的考古文物结合起来,把历史学和民族学的理论方法结合起来,从而整理出一个体现了唯物史观的中国原始社会史的体系来。
以胡适、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对于廓清长期以来由于完全相信不可靠的历史记载而存在于古史研究中的迷雾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由于他们使用形式主义的思想方法,把疑古推向极端,这也就削弱了他们古史观的科学性。因而疑古派所谓东周以前“无史”的观点,并没有能够在学术界取得多数人的赞同。且不说柳诒徵、刘掞藜、胡堇人这些泥古信古派,就连近代实证史学的一代宗师王国维也不同意疑古派辨伪的绝对化。他在《古史新证》中既批评了“信古之过”,也批评了“疑古之过”。王国维指出:“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措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注:王国维:《古史新证》第一、二章,《古史辨》第 1册。)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王国维认为“二重证据法”是研究古史最可靠的方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注:王国维:《古史新证》第一、二章,《古史辨》第 1册。)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长期以来一直被治古史的学者奉为圭臬。因此可以说,《古史辨》问世之后,虽然轰动一时,但以胡适、顾颉刚为代表的完全否定神话传说对史前期历史研究重要意义的极端疑古思想,从来就没有在史学界取得支配地位。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的出版,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对极端疑古派的一种回应。
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自序中曾明确表示:“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振玉)、王(国维)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从处理史料的方法来说,显然也受到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影响。他在自序中说:“我在这一部分的研究所根据的材料,第一为各种古籍中的神话传说式的记载,第二为仰韶各期的出土物。可说是以后者为正料,而以前者为副料的。”和王国维所不同的是,他并没有停留在“二重证据”的互证上,而是以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为指导,分析了尧舜禹时代的家庭婚姻形态和社会结构,得出了神话传说所反映的史前时代是原始社会的结论。
无庸讳言,《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无论在处理历史文献或考古实物方面,都存在着一些粗糙和不足之处,书中的具体观点也未必都为学者们所认同。但吕振羽在中国史前社会研究方面所开辟的这条道路,方向无疑是正确的。正如民族学家岑家梧先生1958年在《中国原始社会史稿》书中所说的,吕振羽的这部早年著作“至今还不失为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的一本体系完整的关于中国原始社会史的著作。”(注:岑家梧:《中国原始社会史稿》,民族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9页。)
二、从奴隶制到封建制:殷周时代社会性质的辨识
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奴隶社会阶段,是社会史论战中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吕振羽在论战中所发表的《中国经济之史的发展阶段》和《殷代奴隶制度研究》等论著,支持郭沫若肯定中国经历过奴隶社会阶段。但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对殷商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估计过低,认为殷商还处在氏族社会末期,吕振羽不同意这种估计。他指出:“殷代不仅有很繁盛的畜牧,而且有很盛的农业;不仅在生产事业的范畴里及其他事务上都使用奴隶,而且有专靠奴隶为生的自由民阶级的存在;在上层建筑的政治形态上,已经完全看不见民主主义的形迹,充分在表现阶级支配的机能。”(注:吕振羽:《中国经济之史的发展阶段》,《文史》创刊号,1934年。)殷墟出土的生产工具基本上是石器或骨器,只有少量祭器、食器、装饰品和兵器使用青铜器。郭沫若据此认为殷代是“金石并用时代”。吕振羽对此有另一种解释,他认为殷墟出土的石刀、石斧、骨簇等大批窖藏,当属已经废弃使用之物;青铜祭器、食器、兵器数量不多,可能是大部分在周族攻入殷都后,被囊括西去。但从殷墟遗址中冶炼场之规模及其冶炼技术之高度看,殷代应该已进入青铜器时代。
郭沫若关于殷代是原始公社末期的意见,后来有了改变。1945年,他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说:“中国的青铜器时代起源于什么时候,现在还不知道。但我们所知道的是殷末和西周前半已经达到了青铜冶铸的最高峰。”(注:郭沫若:《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又说:“殷代确已使用大规模的奴隶耕种,是毫无问题的。”(注:郭沫若:《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到了1952年,他在《奴隶制时代》一书中,更明确宣告殷代是“奴隶制时代”,“殷代已经是铜器时代,并不是所谓金石并用时代,也是毫无疑问的事”。郭沫若观点的前后变化,表现了一个追求真理的学者勇于自我批判的可贵精神。而他对殷代奴隶制社会性质的肯定,则证明吕振羽先前的认识确有其过人之处。
吕振羽对甲骨文没有专门研究,但他参照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和郭沫若对卜辞的考释,却能够对殷代的社会结构和土地关系得出独到的认识。他认为甲骨文的“邑”是一种村落公社,其“土地是属于国家所有的一种所有形态”。“国家对这种公社所派的代理人,大抵为公社原有之酋长,这种酋长因此便转化为具有阶级性质的贵族。”(注:吕振羽:《殷代经济前论》,《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3卷第4期,1936年。)《易经》说“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正可证明这种村落公社的存在。吕振羽还根据《左传》定公四年所说周武王分封鲁公“殷民六族”和分封康叔“殷民七族”的记载,认为村落公社的内部仍然存在着氏族组织。“初期的种族国家,在其下面的氏族性的村落公社的组织,反而是一个普通存在的形态而为其特征之一。在殷代,无论其本族(子族)或被征服之族(多生)都带着这种组织的特色。”(注:吕振羽:《殷代经济前论》。吕振羽后来曾经声明,他早年用“种族奴隶制”一词不科学,应改为“初期奴隶制”,见《史学研究论文集》,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出版。)吕振羽所分析的上述殷商社会经济形态的特点——土地国有,保存氏族组织的村落公社,以及由公社酋长转化的具有阶级性质的贵族等,在经过了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看来,仍然显示出其观点的鲜活性。建国以来关于商代社会性质的讨论,尽管在实证研究方面比吕振羽20世纪30年代所做的工作是大大深入了,但诸如土地国有、氏族组织、村落公社等被多数学者所认同的历史特点,应该说早在20世纪30年代吕振羽就已经提出来了。
关于西周的社会性质,吕振羽的理解也和郭沫若有很大不同。他认为西周虽然还有使用奴隶的现象,但在生产领域里,奴隶经济已退出支配地位,而让渡给了农奴经济。(注:吕振羽:《中国经济之史的发展阶段》,《文史》创刊号,1934年。)在社会史论战之前,有的学者也曾提到西周的封建制度,但他们都是根据西周初年的封建诸侯而立论的。分封制严格说来是一种上层建筑,对于它的内涵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郭沫若就认为那其实是一种部落殖民制度,与封建制的社会经济形态无关。吕振羽则是最早从分析生产方式入手,论证西周是封建社会的学者。他认为周族在古公亶父时还过着氏族村落公社的生活,文王自身还没有完全脱离劳动。到武王伐殷以后,“便从其前时期的村落公社和殷代奴隶制所遗留下来的历史条件的基础出发,而转化为封建制度=农奴制度的采邑经济。”(注:吕振羽:《西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第1期,1935年。)在吕振羽看来,西周分封制的所谓“受民受疆土”,意味着受封者并不仅占有自然的土地,而是连同土地上的人民。等级分封形成了等级从属的“土地所有的属性”。“在西周的彝器铬文中,和‘锡田’同时又‘锡夫’、‘锡白丁’、‘锡庶人’的记录,正是这个历史事实的说明。”(注:吕振羽:《西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第1期,1935年。)郭沫若认为“庶人”可以被赠赐,当是奴隶身份的见证。吕振羽则指出,农奴是封建主“不完全占有的劳动者”,他们可以被赠赐或买卖并不足为奇。
吕振羽认为,井田制的记载虽然有后代儒家理想设计的成分,但它在周代确实存在,是一种封建的庄园组织。“农奴以部分的劳动时间在自己的‘私田’上劳动,一部分则在领主的‘公田’上劳动。”(注:吕振羽:《西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第1期, 1935年。)《诗经》一些篇章的内容表明,“农夫”或“庶人”有自己的经济和生产工具,这正是农奴与奴隶不同的重大特点。农奴不仅以赋役的形式为领主提供剩余劳动,还须向领主贡纳牲畜与其他物品,并供采薪和围猎劳役。
吕振羽从土地所有制形态、直接生产者的身份地位和剥削方式等方面阐述西周的社会性质,这比起仅从分封制而立论的西周封建论者来,显然前进了一大步。吕振羽还指出,周族封建制度的形成,类似于日耳曼人封建化的过程。这个观点后来也得到了一些西周封建论者的赞同。可以说,西周封建论的理论框架,吕振羽基本上都提出来了。当然,在他之后,主张西周封建论的一些学者,如翦伯赞、范文澜、徐中舒、杨向奎等,在充实和发展西周封建论的学说方面也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吕振羽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提出中国封建生产方式经历了从领主制到地主制的转变。他认为,战国时期雇役佃农制兴起,“给予负荷奇重的农奴们以一种有力的吸引,而作为他所逃亡的一个归宿地”,“从而又把领主们的农奴制生产引向地主经济的雇役佃农制生产,结果使原来的领主也不断地转化为地主”。商鞅是“秦国地主阶级政治上的第一个代理人”。商鞅变法所实行的徕民政策和奖励耕战政策,是满足新兴地主阶级农业劳动力和发展地主经济的政策。(注:吕振羽:《秦代经济研究》,《文史》第1卷第3期,1935年。)。吕振羽的上述观点,大体上也为当时和后来的西周封建论者所接受。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的深入,吕振羽对自己的学术见解也多少有所调整。他仍然坚持西周封建论的基本观点,但却强调要从社会形态发展的过渡性和不平衡性来认识西周的社会性质。例如他说:“由于周人自己原来的家长奴隶制和殷朝奴隶制度的影响,以及迁入的‘殷遗民’所带去的奴隶制度的作用,在西周又有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并存。”(注:吕振羽:《论西周社会形势发展的过渡性和不平衡性——关于中国社会完成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问题的探讨》,《新建设》1959年第9期。)吕振羽还考察了西周王畿、齐鲁、秦国、越国四个不同区域,认为它们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是平衡的,自己过去只把“视野拘限在西周的圈圈内”,“过多地注视封建性方面的东西,而忽视了奴隶制和原始公社制方面的东西。”(注:吕振羽:《论西周社会形势发展的过渡性和不平衡性——关于中国社会完成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问题的探讨》,《新建设》1959年第9期。)
关于商周时代的社会性质问题,虽然在史学家中间至今未能取得共识,但吕振羽作为商代奴隶社会论和西周封建社会论的首倡者,其理论贡献是不可抹煞的。近几年来,有的人因为古史分期问题长期聚讼纷纭,就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没有科学价值,讨论这种问题是浪费时间。这些人如果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一种偏见,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科学意义毫无认识。马克思说:“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3页。)历史现象错综复杂,我们只有把复杂的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这样才能准确认识一个时代的基本特征,也才有可能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怎么能够说应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来研究历史没有科学价值呢?
三、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解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社会史论战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史来考察,“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包含着如下一些内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亚细亚生产方式”最初的涵义是什么?马、恩在使用这个概念时,是否赋予了一定地理条件的限制?他们后来是否放弃了这个概念?苏联和其他国家一些学者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解是否正确?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学者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如何理解的?等等。吕振羽对这些问题都认真进行了考察并作出回答。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经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 83页。)众所周知,马克思所说的古代生产方式,也就是希腊罗马的奴隶制。亚细亚生产方式既然出现在古代生产方式之前,是否就意味着它是国家产生之前的原始社会呢?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中,认为马克思在读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之后,大概改变了他对古代生产方式和亚细亚生产方式关系的观点。普列汉诺夫认为,由于地理环境不同,东方和西方在氏族组织解体之后,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东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希腊罗马的古代生产方式是“两个并存的经济发展的类型”。“像中国或古代埃及的经济发展的逻辑并没有引导到古代生产方式的出现”。“古代社会代替了氏族社会组织;同样,东方社会制度产生以前的社会组织也是氏族社会组织。这两种经济制度的类型,每一种都是生产力在氏族组织内部增长的结果,生产力的这种增长最后必然要使氏族组织解体。如果这两种类型彼此有着很大的区别,那么它们的主要特征是在地理环境的影响之下形成的”。(注: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中译本,第40页。)
1928年苏联中国问题研究所出版了马扎亚尔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一书,依据普列汉诺夫的上述观点,认为中国自氏族制度瓦解后,直到西方列强入侵之前,都是处在亚细亚生产方式阶段。1931年初,曾经来中国考察农业问题的约尔克发表了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专文。他不同意有所谓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存在,认为东方各国的前资本主义关系是奴隶制和农奴制的混合物,地租采取赋税的形式是这种生产方式的特点。同年2月, 苏联东方学会和东方研究所在列宁格勒共同召开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会。戈德斯在会上作长篇报告,批判马扎亚尔学派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不仅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在历史的根本问题上的方法论,也抹煞了现代东方的封建主义残余问题,这样的理论在政治上是有害的”。戈德斯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只是马克思在读到摩尔根《古代社会》之前的一个“假设”,因为“当时历史科学本身正经历着连马克思在对历史过程的个别环节的理解上也不得不留下空白那样的发展阶段”。但自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说明了原始共产制的崩溃和私有制的产生之后,这种假设就失去了它的作用。因此,马克思在他最后的几部著作中已经不再提到亚细亚生产方式。(注:参看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出版,戈杰斯(即戈德斯):《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讨论总结》,见郝镇华编:《外国学者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1934年,科瓦列夫发表了《关于奴隶社会的几个问题》。他引用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序言》和《〈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中所说的两段话:
在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阶级压迫的主要形式是奴隶制,即与其说是群众被剥夺了土地,不如说他们的人身被占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8-259页。)
家奴制是另外一回事,例如在东方:在这里它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构成生产的基础,作为家庭的组成部分,不知不觉地转入家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76页。)以此作为理论根据,科瓦列夫得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东方“奴隶制变种”的见解。
受科瓦列夫的影响,但又得出和他不同观点的,是雷哈德的“过渡形态”说。1935年,雷哈德出版《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史论》,书中说:“我们不反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物质,就是奴隶所有者社会的变种或其不完全性,但同时也不赞成把这种生产方式看作一种社会构成。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可说就是原始公社和古代奴隶制度间的过渡形态。”(注:转引自吕振羽:《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理论与现实》第2卷第1期,1940年。)
在日本,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解,大致有四派:森谷克已等人主张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前阶级社会;羽仁五郎、伊豆公夫等主张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奴隶制和农奴制的混合体;平野义太郎、相川春喜等主张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先于奴隶制的第一个阶级社会;早川二郎等主张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种“贡纳制”,并非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
我们在上面之所以要略为介绍一下苏联学者和日本学者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见解,这是因为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一些理论问题上都不免受苏联理论界的影响,而且有些影响还间接来自日本的学者,吕振羽于此也不例外。他在《“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一文中,承认自己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解,受到戈德斯的影响。在《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一书中,他认为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希腊罗马而外之其他国家的奴隶制度阶级的社会”,实际上也是受到了科瓦列夫东方“奴隶制变种”论的启发。(注:吕振羽把亚细亚生产方式说成是一种“种族国家的奴隶制”,后来他觉得“种族奴隶制”的提法欠妥,修正为“初期奴隶制”,见所著《史学研究论文集》,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出版。)
吕振羽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解读,虽然受到苏联学者的影响,但平心而论,他并非是人云亦云,而是经过自己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独立钻研,并结合对中国历史实际的深入思考得出的结论。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所提示的内涵是:“(一)土地国有;(二)全国分成许多各自孤立的公社;(三)农耕上的人工灌溉的重要性,但治水和其他公共事业的承担者则是国家;(四)公社受着国家政权的统治——它们须向国家纳税——政权表现为中央集权的专配的形态。”(注:吕振羽:《“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理论与现实》第2卷第2期,1940年。)他还指出,恩格斯和列宁则都明确说奴隶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初的阶级社会。依此,马、恩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不是在国家出现前,而是属于国家的历史时代的范畴。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吕振羽说:“所谓‘亚细亚的’社会的内容,一面具有奴隶主和奴隶之社会的阶级构成和它们间特定的生产关系,这在本质上与古希腊罗马是相同的;另一方面又具备着土地国有、中央集权、公社形态、国家治水事业等特殊形态,这是古希腊罗马所不具备或不在其全部过程中都具备的诸特征。在这种种特征中,最基础的东西,却是奴隶制度的生产关系、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阶级的对立;其他则是建基于地理条件的差异性和其发展的不完全性等等而形成起来的。”(注:吕振羽:《“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理论与现实》第2卷第2期,1940年。)吕振羽还指出,在古代东方各国发生军事征服的情况下,“统治阶级的奴隶主和下层自由民诸阶层或等级,大都是出身于征服者的种族而从其内部分化出来的;被统治阶级的奴隶与所谓‘半奴隶和农民’,主要是被征服的‘异族的人民与战争俘虏构成的;奴隶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全国的土地在名义上均属于国家所有,通过村社的分配,自由民都有使用的权利,但实际上仍是有些人占有较多土地,有些人丧失土地。农村公社的形式,是一般地存在着的。不过在这里,所谓农村公社有两种形式:一是统治阶级自己管辖的公社,有着奴隶主、一般自由民和奴隶的阶级构成的内容;一是被征服‘异族’的公社,允许其保持原来的组织与‘内部自治’,只须向国家‘支付租税’——这也就是所谓‘半奴隶的农民’——和充作奴隶的人口等。”(注:吕振羽:《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理论与现实》第2卷第1期,1940年。)
吕振羽在阐述自己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认识时,对苏联和日本学者的见解都有所评论,其中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他对日本学者早川二郎“贡纳制”的批评。何干之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一书中,曾肯定了早川的“贡纳制”说,认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特点,都可以由此得到说明。何干之这本书对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作了系统的介绍和评论,在读者中有较大的影响。可能正因为这个缘故,吕振羽觉得需要对“贡纳制”说作更多的剖析。早川二郎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乃是一种贡纳制,它是“氏族制时代到奴隶所有者社会经济构成的过渡期,不待说,它并非什么独立的社会经济构成。在生产方式上说,这里只能看到公社制度与初期家内奴隶制度的混合”。(注:早川二郎:《古代社会史》,耕耘出版社1946年版。)吕振羽指出,所谓“过渡期”,不是原始公社制生产方式占优势,便应是奴隶制生产方式占优势,绝不能是两种生产方式的“均衡”,或既非前者又非后者。早川认为过渡期意味着氏族制的“最后阶段”,但他的“贡纳制”又已经产生了国家,这是理论上的一个矛盾。贡纳制是从国家尚未出现的原始公社末期到奴隶制和封建制时代都存在过的形态。马克思说:“征服者一方面容许被征服者继续原来的生产方式,一方面以获得贡物为满足。”(注:吕振羽引自《马克思全集》日译本第10卷。)无论是征服者或被征服者,贡纳制都不改变它们原有的生产方式,这在中国封建时代中央王朝和一些藩属的贡纳关系中也可得到证明。应该说,吕振羽对贡纳制的上述分析是很有说服力的。
20世纪30年代以后,前苏联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在很长时期内曾被视为禁区。但在中国,这个问题却始终吸引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巨大兴趣和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许多亚非拉国家在取得独立之后,面临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重新成为许多国家进步学者热心探讨的课题。但无论在中国或在国际上,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历史的和现实的解读迄今并没有一致的认识。可以预计,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今后还会继续下去。而以往一些学者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成果,对于后来者的继续探讨无疑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中,当然也包括吕振羽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
四、对所谓“中国社会之特有的停滞性”的批判
马克思在阐述亚洲一些国家和社会形态时,曾经提到过这里社会经济发展滞后的历史特点。例如他说过:“从遥远的古代直到十九世纪最初十年,无论印度的政治变化多么大,可是它的社会状况都始终没有改变。”(注: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卷,第65页。)他还多次谈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亚洲国家,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古老传统极其牢固,使得所有制形态很难发生变革。当马克思对亚洲社会形态作出这样一种判断时,他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是一些西方的商人、旅行家和传教士有关东方各国的文字记载。这些西方的商人、旅行家和传教士对东方各国的描述,固然有不少是他们耳闻目睹的材料,但它们不免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有些材料甚至是来自错误的传闻。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他们所能接触到的材料,敏锐地指出了亚洲各国传统社会的一些历史特点。他们的有关论述对于我们研究亚洲各国的历史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但是谁如果认为可以不顾亚洲各国的历史实际,而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个别论述当作一种先验的模式来剪裁亚洲各国的历史,这显然是不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的。
日本学者秋泽修二本来自诩是唯物史观的信徒,但在中日战争爆发后,他却堕落成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宣传员。他在《东洋哲学史》和《中国社会构成》两书中,歪曲马克思关于亚洲社会形态的一些论断,竭力宣扬中国历史发展的“停滞性”,认为“中国社会经济的近代化的过程,不是发生于中国社会自体内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生的发展”,而是由于“外力之侵入中国”所决定的;进而无耻地宣称“日本皇军的武力”将“给予中国社会之特有的停滞性以最后的克服”,使中国“与……日本结合。”(注:参看吕振羽:《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理论与现实》第2卷第2期,1940年。)
吕振羽指出秋泽修二的谬论不仅歪曲了马克思论东方社会形态的论断,而且完全违背了中国的历史实际。他用大量的事实说明,中国封建社会所经历的时间虽然比西方一些国家长久,但在世界各国的封建社会史上,中国封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却远比其他各国先进。只是由于地理环境、人口增长以及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各落后民族统治集团的残暴压制与掠夺等诸多原因,阻碍了生产力的进步,从而使中国的封建社会后来走上了迟滞发展的道路。明清之际,东南沿海沿江地区开始了资本主义萌芽(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的手工业工场),但却被人关之初的清朝统治者扼杀了。在康熙中叶后重新出现的这种资本主义萌芽,到了鸦片战争之后,又被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所打断。历史表明,“中国封建社会在较迟缓的发展进程中,并没有‘静止’、‘退化’、‘复归’或‘循环’,而是螺旋式地或波浪式地前进。”(注:吕振羽:《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理论与现实》第 2卷第1 期,1940年。)秋泽修二宣称,“中国社会的停滞性是社会矛盾的循环,社会过程(社会运动)之反覆的形式,是中国社会的根本性格”(注:参看吕振羽上引文摘录秋泽修二的谬论。),并引申出“日本皇军的武力”是克服中国社会“特殊的停滞性”和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动力的结论,这完全暴露了他充当日本军国主义宣传员的丑恶嘴脸。
秋泽修二认为建立在农村公社基础上的“父家长制”和“专制主义及中央集权的官僚制”,是“中国社会之特有的停滞性”的根源。本来,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农村公社、父家长制和专制主义及中央集权的官僚制,这是包括吕振羽在内的多数中国史学家都承认的事实;它们对中国历史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和消极作用,也是可以研究的问题。如果秋泽修二只是在理论和学术层面上来讨论这些问题,这并无可非议。但秋泽却是别有用心地把这些问题的讨论,借以论证中国社会“特殊停滞性”的先天“社会性格”,因而吕振羽也就不能不在这些问题上展开对他们的批判。
吕振羽指出,中国历史上诚然存在着专制主义的集权国家,然而“在理论上,在历史的现实性上,思想和政治形态虽能给予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反作用’,但政治却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又要受着社会生产方式的规定”。在秋泽修二那里恰恰相反,政治被“看成为规定中国社会发展形式的决定因素”。秋泽说,由于水利事业“只有由中央政府的干涉才能进行,因而在这里,可说由于政府施行水利事业这一机能,而成为产生集权国家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机能”。但事实上,大规模的水利事业须由国家施行,“只能予中央集权专制统治以增强作用,却不能作为其成立的重要因素。”(注:吕振羽:《“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理论与现实》第2卷第2期,1940年。)
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着父家长制的残余,但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历史现象。秋泽认为中国父家长制的表现是“子对父、家族成员对父的奴隶关系”。实际上,在中国封建社会,“子”和其他“家族成员”依照其家族社会地位的不同,他们在家族中的地位也是不同的。“有的是不劳而食者,有的是家族劳动的辅助者,有的则和‘父’同为家族劳动的主要担当者,却并不是‘奴隶的关系’”。“土豪劣绅之充任中国封建统治的基层势力,并非什么‘父家长制的集权专制的统治’,只是表现着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的属性”。秋泽的观点是“把社会构成的阶级对立关系,消解于所谓‘父家长制’的关系下面”。秋泽把庙宇和祠堂的祠产,都说成是农村公社的残余,把“ X世同居”视为“原始家族共产体”,这也是对历史的曲解。农村公社和家族共产体的残余,根本不可能对历史和发展起“根本的制约”作用。俄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着“米尔”(农村公社),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一个时期甚至还存在着父家长制的经济形态,但这并不妨碍“俄国从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一千余年间,就跨过了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的历史诸阶段,而进入了社会主义的时代。”(注:吕振羽:《“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理论与现实》第2卷第2期,1940年。)
****
吕振羽同志是一位有深厚理论素养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是一位随时服从党的需要把人民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革命者。他在20世纪30年代所撰写的一些史学论著,都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特色。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投身于民族解放战争的神圣事业。1941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后,他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从重庆前往苏北新四军军部。侯外庐在他的回忆录中,曾经谈到吕振羽临行前向他辞别的情景,其庄严气概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注:侯外庐:《韧的追求》第111页,三联书店1985年出版。)新中国成立后,吕振羽同志在党政部门和高等学校担任领导职务,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历史研究的爱好和关注。不幸的是,从1963年1月起,他就蒙受不白之冤,被幽禁审查,随后又被捕入狱。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才得到平反。他被隔离审查期间,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还写下了多篇历史评论文章,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理论信仰的执着追求。在纪念这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诞生一百周年时,面对他留下的珍贵的史学遗产,我们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感叹:命运对他是太不公平了!要是他一生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历史研究工作,或是没有含冤遭受缧绁之灾,他将给我们增添多少理论和学术成果?可以告慰吕振羽同志的是:我们的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已经纠正了过去的“左”倾错误,新时期的中国历史学正以前所未有的生机蓬勃的发展。随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流传下来的学术薪火,将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学子发奋图强,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扬光大而努力工作。
[收稿日期]2000—09—12
标签:吕振羽论文; 史前时代论文; 形态理论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东方主义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论文;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论文; 古史辨论文; 生产方式论文; 亚细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