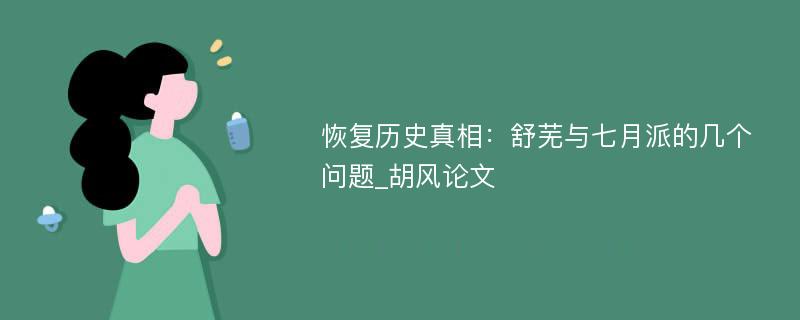
还原历史的真相:关于舒芜和七月派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真相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舒芜因参与胡风理论的建构和导致最高当局最终处理“胡风集团”而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焦点”人物,在诸多文学史著述中,舒芜或者被当做七月派的异己分子简单地清理出场,或者把他与胡风捆绑在一起,只关注他的“陪绑者”角色,而忽视了他作为七月派重要成员的文学史身份。本文探究他与胡风交往的内在思想依据、在七月派中的实际地位、对七月派理论建设的贡献,还历史一个本来面貌。
一、文化思想的亲缘
在战乱岁月中,舒芜通过路翎结识胡风“走进”七月派,虽说是人生的机缘,但也隐含着胡风经营七月派的思想进路。1941年5月胡风因皖南事变退居香港,9月《七月》停刊,此期间他申办了一个大型杂志《七月》香港版,他向七月派同人提出组织“编辑联络站”的设想,要求每站“按期寄稿,并积极在青年朋友里面发现新的作者”。胡风把路翎、陈守梅(阿垅)、何剑熏和张元松筹划为重庆的一个站点,告诉路翎很需要杂感、批评之类的短文章,希望动员能写的青年朋友试试[1] (p183—188)。恰在此前,路翎在工作中结识了舒芜。胡风回重庆后,路翎约舒芜去见他。而舒芜“不愿搞文艺”,对胡风也不感兴趣,但在路翎的坚持下,舒芜还是带着自己的几篇文章去见了胡风[2] (p122)。见胡风之前,舒芜虽与路翎、何剑熏、陈守梅等七月派成员有密切交往,但与七月派没有实质性关联。当路翎执意把舒芜引到胡风的身边后,就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胡风通过几篇哲学论文敏锐地发现了舒芜的才华,给舒芜的首封信就期望他写一本小册子来代替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并以“广义上的启蒙运动”相点拨,这决定了舒芜后来的思想和写作方向[2] (p124)。胡风帮助发表舒芜的哲学文章,对舒芜的写作、生活(包括情感)、工作殷殷关切,过往甚密。在胡风和路翎的指导和启发下,舒芜完成了《论主观》、《论中庸》等哲学论文。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胡风在《希望》创刊号上“强力推出”了舒芜这位新来的“同道伙友”。在这一期上,舒芜的文章除了长达15000字的《论主观》外,还有文化论文、书评和11篇杂文,合计占了刊物的2/7版面,以后各期中依然占很大比重,舒芜事实上成为《希望》的主笔。尤为重要的是舒芜文章在内容上对胡风理论的有力支持和发表后产生的巨大影响,使舒芜迅速成为七月派中仅次于胡风的理论批评家。
七月派成员都是满怀革命理想和激情的文学青年,他们以作品为中介与胡风结缘,并在胡风的文学精神和人格魅力感召下凝聚起来。有着相同或相似的人生目的和文学追求,把胡风奉为“精神导师”,自觉实践着他的文学思想。而舒芜是一个例外,他开始是立志于哲学而非文艺,与胡风志趣不合。但二人结识后迅速遇合,原因应是思想的亲缘。胡风是左翼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但一直被视为左翼的“反对派”和“异端”,其主因是他忠贞不渝地坚持五四启蒙文化传统。胡风对五四和鲁迅的虔诚和执著,触发了有着类似情怀的舒芜。在胡风引导下,舒芜成为七月派的“同道”。
舒芜从小受到五四启蒙文化精神的影响,进中学前,新文学就是他的“精神摇篮”,鲁迅和周作人的影响最大。虽然他从小就对哲学感兴趣,新文学并没有给他多少艺术的熏陶,但新文学作品中的人道主义、个性解放、民主意识、批判精神在他的思想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舒芜的传统文化素养和家学渊源也为他承接五四新文化提供了条件,比如他对墨子的学说非常感兴趣,从中感悟出现代人学观念。他自幼学习桐城派诸家论著,方以智、方东树等都给了他文化精神的熏染。在学习、研读梁启超、胡适及其父亲方孝岳等人的著作时,他同样获得了启蒙的思想理路。舒芜由此形成了“反儒学、尤反理学、尊五四、尤尊鲁迅”的思想基础。舒芜在流亡途中也阅读过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产生了浓厚兴趣,但无法遮掩内心深处的五四情结[3] (p555—623)。因此,他的文章都是“从‘五四’出发,向前看,想通过马克思主义,追求彻底的个性解放;向后看,想继续‘狂人’的事业,在历史的满纸‘仁义道德’下面,不断挖掘‘吃人’两个大字”[4]。
七月派是一群战乱年代的流浪者用文学构筑的文化家园。在胡风影响下,五四文化精神和鲁迅文学传统成就了七月派的独特精神品格和潜在文化结构。七月派同人融合思想启蒙、民族救亡和人民解放等时代文化要求,形成了一个相互共守的整体。正是基于一种文化精神的共感,舒芜实现了与七月派的融合,而这种融合又为我们提供了整体把握七月派文学特征的契机和通道。
二、流派发展的建构
七月派是时代催生的文学群体,它在抗日战争号角中诞生,在战乱岁月里壮大,在解放战争凯歌中解体。它的组织形态和生存空间主要是文学刊物,1937年创刊的《七月》和1945年创刊的《希望》成为七月派前、后期的标志。
1937年9月胡风在上海创办《七月》,在抗战初期影响很大。自觉承担起民族救亡使命的作家们自发地向《七月》靠拢,《七月》作家群迅速崛起。胡风在《七月》代致词中指出:“在神圣的火线后面,文艺作家不应只是空洞地狂叫,也不应作淡漠的细描。他得用坚实的爱憎真切地反映出蠢动着的生活形象。在这反映里提高民众底情绪和认识,趋向民族解放的总的路线。”[5] (p8)本着这种精神,胡风“在编辑上有一定的态度,基本撰稿人在大体上倾向一致”,结果《七月》被认定“有同人杂志的姿态”[6]。虽然胡风没有着意经营一个流派,但他在编辑刊物时“充分体现自己的文艺思想和精神力量”,“源源地发现在实际斗争里成长的新的同道和伙友”,结果不自觉地孕育出一个群体的生命——《七月》作家群。当初人们将其界定为一个流派,是从作品中共有风貌中所作的感性概括。后来七月派成员回顾说,他们“只是一种松散的思想上的结合,决没有什么组织纲领之类,……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个流派,也没有存心结成一个流派”[7]。他们“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世界观、美学观、创作方法上相互吸引,互相影响,互相促进,渐渐形成艺术志趣大体相近的一个作者群,客观上形成了一个流派”[8] (p124)。
《七月》作者众多,涵盖范围广,流动变化大。据粗略统计,从创刊到终刊,前后陆续加入的作者共有180多人,分别来自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其中有百余位只发表过一两篇作品,整体呈现出来来往往、开放流动的格局。但在人员变化中还是有一批“基本撰稿人”,如艾青、曹白、萧军、丘东平、阿垅、端木蕻良、田间、萧红、彭柏山、欧阳凡海、聂绀弩、辛人、吴奚如、贾植芳、邹荻帆、天蓝、孙钿(以发表篇目多少排序)。他们大都是被胡风敏锐发现和着力栽培的对象,构成了七月派的核心队伍和中坚力量。概而言之,《七月》作家群外围扩大势力、内部缔结核心的态势,意味着前期七月派是一种“缔结中心的发散性辐射型结构”。这种动态结构说明七月派还处于不稳定、不成熟的自发状态。
从《七月》的版面内容看,主体是报告文学(特写、速写、通讯、报告)和诗歌。这与宣传抗战的办刊宗旨有关,报告和诗歌更有利于“向献给祖国的神圣的战场敬礼”和“启发蕴藏在民众里面的伟大力量”。后来胡风决定“扩大篇幅,容纳较长的创作”,小说得到加强。与集中鲜明地体现着胡风文学精神的诗歌、小说相比,理论批评显得比较薄弱,主要是译介外国各家文艺理论和探讨“民族革命战争与文艺”的问题,很少有深入系统阐述胡风自己的文艺思想、统摄《七月》作家群的理论文章。
随着《七月》及七月派的发展,胡风理论日趋明晰,流派意识日益浓厚。可以从1939年7月《七月》在重庆复刊后的内容上乃至停刊后的文章中感受到这种思想动向。胡风在复刊致辞中说《七月》“不过是整个文艺战线上的堡垒之一”,表示“对于作为友军的许多文艺堡垒的尊敬”和“对于各派作家底创作方法的重视”[5] (p70),含蓄地流露出一种流派意识。1941年,胡风决意不再“把《七月》做成文豪们的交际沙龙”,开始结合文学创作鲜明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并强调理论批评对文学创作的主导作用,发挥理论的战斗力以保持作家群体的凝聚力。1942年底胡风表示在文艺上“理论批评是落后于创作的”[5] (p298),1943年元旦呼唤理论批评“对于创作实践的领导”[5] (p311)。胡风在《七月》后期直言不讳地指斥郑伯奇、艾思奇、穆木天、徐迟等人的理论倾向,坚决反对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但在阵营和气势上显得势单力薄。有一些《七月》核心成员认同了时代和历史的选择,将现实主义首先视为一种政治需要,走向了胡风反对的那一边。面对救亡运动兴起后的文坛现实,胡风深感弘扬五四传统和鲁迅精神的必要,加强杂文、文化评论等“突击性文体”的重要,《七月》复刊后开始刊发锋芒毕露的杂文,当然还不是一个固定栏目。
正当胡风迫切感到必须以理论批评领导创作实践、试图给自己的队伍注入新鲜血液和新生力量,需要“投枪”、“匕首”式杂文的时候,舒芜的出现让胡风倍加欣喜。他对舒芜书传言教,悉心指导,不久就在精心准备的《希望》创刊号上隆重推出了这位“新人”。舒芜的加盟是胡风理论自觉的必然要求,也是七月派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1945年1月胡风在《希望》创刊号上“集束”推出《置身在为民主斗争里面》及阿垅《箭头指向》、舒芜《论主观》三篇理论文章,实际上成了七月派的理论“纲领和宣言”。以后各期,胡风总是把2至3篇理论文章“联袂”编发,每期都有舒芜的文章。理论的强化表明七月派的发展从不自觉走向自觉,《希望》的创刊“标志了‘七月’内部机制的成熟,也标志了‘七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9] (p237)。
胡风对舒芜相当器重和欣赏,有着从舒芜那里寻求理论支持以弥补自己底蕴不足的意图,舒芜《论主观》、《论中庸》等文也显示了为胡风理论寻找哲学基点的努力。胡风又把舒芜作为自己的理论盟友,展开与对手的论争。他把《论主观》当成是“抛手榴弹”[2] (p134),准备给予对手狠狠一击。正是有了舒芜,胡风在《希望》创刊号的编后记中说:“和两三年前相比,战斗的思想加强了。”胡风总评说:“青年哲学家舒芜的出现,在后方读者社会中造成了一个惊奇。他的每一篇论文都深深刺入了现代中国的思想状况的要害,因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10] (p383)舒芜突显了胡风现实主义理论的主体性特征,引发了长时间大规模的论争,不仅显示了胡风文艺思想的有效存在,而且使胡风在日后的文艺论争中不断修正和补充自己的现实主义理论,促进了胡风文艺思想的发展和成熟。
《希望》的作者与《七月》相比,数量大大减少,新加入的作家只有20余人。胡风自己也说“没有提拔新人的大志”,《希望》的作家都是共同作战的诚心的“共感者和同道者”[11] (p115)。这说明《希望》已形成了一个积极响应胡风精神的同人圈,舒芜、阿垅、路翎、贾植芳、鲁藜,冀汸、化铁、绿原、朱健、何剑熏、公木、邹荻帆、胡征、吕荧、孙钿、方然、耿庸等人既是《希望》的主创人员,也是《呼吸》、《泥土》、《蚂蚁小集》、《荒鸡小集》等其他七月派刊物的中坚力量,七月派已具备一支稳定的创作队伍,胡风的现实主义理论在他们那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阐释和体现。作家的气息相通和群体意识浓厚,自然导致对其他流派或异己主张的拒斥,集中自守的特征也就明显起来。牛汉曾表示:“如果说流派,《希望》更明显,审美观点,流派思想,更集中,更典型。”“《希望》有自己的理论,作者阵营、范围较小……团结得很紧。”[12] 七月派此时已从“发散性的辐射型结构”转向了“内敛性的向心型结构”。
在版面内容上,《希望》的版面可以大致三分:理论批评(舒芜、阿垅、方然等)、诗歌创作(绿原、翼汸、牛汉、鲁藜、邹荻帆等)、小说创作(路翎、贾植芳等)。版面的“三分格局”象征着七月派的“三维建构”。其中舒芜是理论批评这一极的重要代表,他的文章显示出的战斗力和影响力,体现了七月派内部结构由流动开放转向集中自守,他的哲学文化论文不仅强化了胡风文艺思想的哲学底蕴和理论修养,也给七月派造成很大的声势,所引发的长时间论争不自觉地把七月派推向独立发展的高峰。
三、理论批评的互动
胡风主导下的七月派,作家和理论家有着共同的理论追求,创作与理论批评有着内在的精神联系。七月派前期,艾青、吕荧、阿垅等人与胡风在理论思想上相互感应、启发,对七月派作家影响很大。舒芜是后期七月派理论批评的旗手,但他的理论没有直接作用于七月派作家。诚如牛汉所说:“阿垅、舒芜的理论与‘七月派’的形成不能划等号,不是一个简单的因果关系。理论不是直接地发生影响,而是曲折地对作家的创作发生作用。”[8] (p124)舒芜的理论彰显了七月派创作的艺术特征,七月派创作的文化底蕴又在舒芜的理论中得到显现,彼此之间的互动是潜在而又复杂的。
舒芜虽然不以文学批评见长,但表现出呼应七月派作家创作实践的努力。他的《什么是人生战斗——理解路翎的关键》是研究路翎小说的重要论文,首先指出了路翎小说的意义,又从叙事角度指出路翎的小说特色,接下来分析路翎创作的特征。尽管舒芜没有结合具体文本,但切合路翎的创作精神。舒芜理论文章在指向具体的现实问题、应合时代精神同时,融注了个体的生命体验,为七月派创作营造了理论氛围,《论主观》从文学创作的意义上声称“我们的一切斗争是都为了解放和发扬人类的主观”,而“主观”是一种“有生命存在”和“个体本身的力量的发挥”的“能动力”,把文学的本体确认为人的自我生命存在及其活动,把创作过程理解为作家自觉建构自我生命的过程。七月派作家在创作中融注和传达强烈的生命体验,而舒芜把文学的本质与人的生命存在密切关联,都承接了胡风的文学思想。在深层的文化意识里,舒芜和七月派作家表现出同构性与同源性。
在胡风文艺思想烛照下,舒芜和七月派理论家表现出高度的共识精神。胡风从作家的主体性和创作实践出发,建构了以“主观战斗精神”为内核的现实主义理论。舒芜等人的理论批评,也体现着“主体性追求”的特征。胡风认为“把握真理要通过能动的主观作用”,“只有从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开始,在文艺创造里面才有可能得到创造力底充沛的思想力底坚强”[11] (p18—19)。舒芜则为此寻找哲学的依据:“人类的斗争历史,始终是以发扬主观作用为武器,并以实现主观作用为目的的。”[13] (p38)胡风在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基础上把“主观战斗精神”和现实生活紧密联系起来,避免它陷入唯心主义泥沼,但还是被人穿上了唯心主义的外衣。为此,舒芜从主观与客观的辩证关系中说明不能把“主观战斗精神”与唯心论相混淆:“主观作用,是以客观因素为质料而有机地构成的。被克服了的客观因素的具体的质量,也构成了主观作用的具体的差异,所以发扬了自己的具体主观作用,自然就可以显示出自己的战斗地位来。”[13] (p45)
反对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是贯穿七月派理论批评始终的主题。胡风坚决抵制和反对脱离生活的主观主义和奴从于现实的客观主义。舒芜和吕荧、路翎、阿垅等人一样,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理论批评。舒芜的《论主观》和《论中庸》都强调作家发扬主观战斗精神。在反对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的过程中,舒芜和七月派同人也出现过一些分歧。胡风、路翎、吕荧都有不同的意见,然而不管存在怎样的分歧,七月派理论家的思想律动都围绕着同一根主观精神的红线。
舒芜理论批评的缘起与胡风和七月派同人的思想互动直接关联。在《向生活凝视》中,舒芜承接胡风的反对“题材决定论”,主张“到处有生活”的理论观点,指出若没有日常生活,一切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就都无从产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平凡卑微的男女,他们的平凡卑微的一生,倘能照以燃烧着的爱与憎的强烈的光明,往往便可以显示出正是一部英雄的悲壮的传记”,“真理离不开生活,而生活又无处不在”。舒芜纵横捭阖的论述和发挥,使胡风的理论更具气势和风度。有时,舒芜直接运用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去理解鲁迅、周作人、梁实秋、易卜生、罗曼·罗兰等作家作品。这些文章看似关注的是社会文化思想,实际上是从作家主体的角度论述文学创作实践的基本要求。比如在《思想斗争和思想的途径》中,他写道:“《狂人日记》,不是普通的一篇小说,是新思想与现实的人生要求,在中国的第一次结合,有机的结合。”鲁迅的杂文“是从现实人生要求中随处发掘出一切新思想”,“在自己的生命燃烧中,把新思想和人生要求化学地结合起来”的产物。显然,舒芜的阐述也就是胡风对现实主义作家创作过程的论述。舒芜从接受的角度,对胡风的文艺思想作了具体的运用和分析,虽然有别于七月派作家从创作的角度对胡风文艺思想的贯彻和运用,但这种别致的理论建设为胡风的现实主义提供了更宽泛的实践空间和有效性。
七月派后期的理论批评主要由舒芜、方然、阿垅和路翎等人承担。在《希望》、《泥土》、《呼吸》、《蚂蚁小集》等刊物上的理论批评大都由他们四人“协同演出”。他们都标举胡风的现实主义理论,但批判的路向和重点有所不同。阿垅和路翎的文学批评主要结合具体的创作实践展开,而舒芜和方然是另外一对批评组合,趋向于对抽象的理论问题和思想倾向进行演绎分析,文章大多围绕胡风理论中的关键词进行阐发和揄扬。如舒芜的《论因果》、《论存在》、《论主观》、《论中庸》、《什么是人生战斗》、《论温情》、《向生活凝视》、《论生活二元论》等,方然的《释“战斗要求”》、《释“过程”》、《“主观”与真实》、《论唯心论底方向》等。他俩的文章既是对七月派诗歌、小说创作特色的概括和创作理念的阐释,又赋予了胡风的文艺思想某种哲学意蕴,扩大了“主观战斗精神”的影响力和与左翼文坛的“灰色倾向”作斗争的战斗力。
四、余论
1949年7月1日,七月派成员出版了最后一期《蚂蚁小集》(解放号),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作家胜利会师,正式启动了当代文学的一体化进程。七月派及其理论体系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在第一次文代会上,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受到了周扬的重点批评,舒芜和七月派成员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面对现实处境,他们都在沉思:“胡风和我们过去常给《希望》杂志写稿的这批人,在进步文艺界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位和处境。”[2] (p218)胡风说:“解放后,我虽然竭力避免写评论,编刊物,但‘七月派’依然犯忌,而成为禁区。”[11] (p415)1950年,阿垅的“艺术政治一元论”受到严厉批判;1952年,吕荧的美学观点和路翎的小说横遭指责。建国初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蔚为时代主潮,胡风和七月派自然成为重点对象。由于胡风接受批判和自我改造的态度一直存在“问题”,于是舒芜的检讨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经发表,就成了批判胡风的“导火索”。而当舒芜交出胡风的信件后,对胡风的批判随之迅速全面展开,不断扩大升级。1955年,胡风及七月派同人以“反革命集团”罪被捕入狱。“那以后,‘七月派’再也不被提起,消失了。所谓‘七月派’的诗人和作家,绝大多数都失踪了。”[11] (p415)因此严格说来,到1955年,七月派在文学史上才真正终结。
毋庸赘言,舒芜的文章在七月派的消解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确实关联着七月派成员后来的悲剧命运。如果说舒芜背叛了七月派,则恰好说明他曾经是胡风的理论信徒,与七月派成员有着密切联系。正因为舒芜曾经与七月派成员同歌共唱、并肩作战,是重要的理论家和关键人物,所以他的“反戈”才是最有力的一击,导致了七月派历史终结的悲剧。当然,这一事件已经超越了文学的界域,我们认为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道德问题,当有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客观的态度来加以研究,但这显然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姑且先存而不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