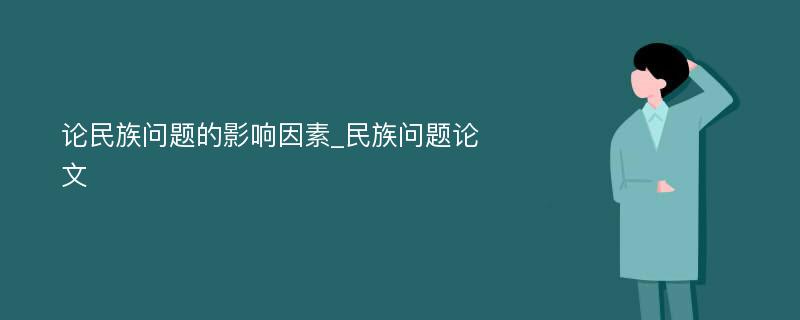
论民族问题的诸影响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因素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39(2001)02-0042-04
当今世界,民族问题仍是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许多国际争端、国家和地区局势动荡均与民族问题有关;在我国国内的不安定因素中,民族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一环。因此,民族问题研究仍然具有理论和现实的意义。在分析当今社会影响民族问题发展的诸因素的基础上,科学地探讨国内和国际民族问题的发展趋向,这对于我们采取正确策略,保持和平、稳定的国内外环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对于民族问题概念的具体内涵,学术界历来有不同的看法,突出反映在形形色色的民族问题定义中。这些定义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二是民族问题发生、存在的范围。由于对这两点理解的不同,导致了对民族问题定义的侧重不同的论述,诸如民族问题仅仅是阶级问题还是更加广泛,民族问题存在于民族之间还是也存在于民族内部等。[1]笔者认为,对民族问题应该在一种交往(contact)、互动(interaction)、关系(relationship)的动态场景中来分析和认识。在我国民族问题之所以凸显出来,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民族多样性和文化差异,另一方面是因为民族间社会发展存在差距。这样,我国的民族问题不仅是民族关系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民族问题应该在社会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得以解决。一个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在它自身是一个社会问题,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面就是民族问题。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目标就是在这种多民族场景中提出来的。因此,我们应该全面地分析和认识民族问题的概念。
民族文化差异是民族问题产生的自然根源;民族交往是民族问题产生的另一前提,或者说是民族问题得以发生的场景。按照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民族的不同表现于民族四个基本特征的不同;而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语言和共同心理素质的不同又最终体现为民族文化差异。差异是产生矛盾、造成问题的前提。但彼此孤立、不相往来的民族不会产生矛盾。只有在民族交往、互动中,民族间的差异才在对比中显露出来。
对民族群体利益的关注是民族问题产生的直接动因。人类社会的起点是从事物质生产的实践活动。人首先是为满足生理需要而从事劳动,在劳动中结成群体、集团、组织,从而构建了人类社会及其文明。民族群体在一定意义上又是一个利益群体,群体利益的关注也是对个体利益的维护。民族交往首先是经济交往,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2](P77)在频繁的民族交往中,不仅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暴露无遗,而且对各自民族的群体利益——首先是经济利益——的关注和维护也随之出现。对群体利益的维护自然产生了对异族的排斥和对本族的认同,于是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推广至政治、军事、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民族的差异性被人为地加以重视,并且作为排斥异族的手段。民族之间的相互排斥、对本民族利益的维护就自然导致了民族问题的产生。民族问题表现于各种领域,既可以是经济问题,也可以表现为政治问题、文化歧视问题等,但对民族群体利益的关注是促成这些问题发生的直接动因。
阶级不平等在民族关系上的延伸是阶级社会民族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阶级不平等是生产力发展、私有制存在的必然结果。各民族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是有差异的,先进民族的剥削阶级就其阶级本性而言必然要把阶级剥削和压迫延伸到落后民族之中,并且这种剥削和压迫往往要披上民族利益的外衣。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人对人的剥削—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2](P131)
因此,本文在参考对民族问题的各种探讨的基础上提出:民族问题是在民族交往联系中,基于民族文化差异,民族群体利益的关注,或者阶级不平等的延伸等原因造成的民族间复杂的社会矛盾问题。
二
我国的民族理论研究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静态的和动态的民族研究。前者是关于“民族”的基本理论探讨,后者是关于“民族发展”、“民族问题”、“民族关系”的探讨,金炳镐教授对此做了丰富的论述。[1]“民族发展”、“民族问题”、“民族关系”是相互联系的概念,必须从互动(interaction)、关系(relationship)的角度加以研究。我国传统的民族研究往往忽视这一方面,而致力于割裂各民族的联系,追溯和构建每个民族单独的历史。这种研究模式可以描述为单线的、保守的、消极的。因为现实的民族存在于互动的关系场景之中,并非割裂的、自足的。改革开放20年以来,民族理论研究日趋发展繁荣,研究重点转向“民族发展”,[3]这意味着传统民族研究模式已经发生变化,一种适应时代要求并紧密联系现实的,多线的、开放的、积极的民族理论研究模式呼之欲出。
从互动、关系的角度研究民族和民族问题,可以借鉴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有关理论和方法。美国学者高登(Milton M.Gordon)在1964年提出了衡量民族关系的7个变量(variable),即:文化、社会交往或社会结构的相互进入(实质性的渗入)、通婚、意识(ethnic identity)、偏见(prejudice)、歧视(discrimination)、权力分配。高登主张,这7个方面的变量是测度、分析民族关系的主要方面,各地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具体研究,探讨个体如何影响群体,群体关系的改善又如何影响到每个个体态度的变化,以及7个变量是如何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对象而次序变化的。[4]马戎教授在借鉴西方民族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从6个方面分析了影响民族关系的因素:(1)民族集团之间历史上的关系对现今关系的影响(历史因素);(2)社会制度的异同(社会因素);(3)经济活动类型的异同(经济因素);(4)文化、宗教、语言、习俗方面的差异(文化因素);(5)个别事件(偶发因素);(6)政府政策(政策因素)。[5]
影响民族问题产生和发展的因素可以用“变量(variable)”的概念加以描述。本文认为,可以从7个方面分析影响民族问题诸因素/变量。这些因素/变量与前述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前提等密切相联;在不同民族中其表现程度是有差别的;在同一民族的不同历史时期其表现程度也是有差别的。
1.民族文化传统的差异程度。广义的文化概念是指“人类在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6](P372)文化学研究中把文化划分为四个层次,即: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7]其中物质文化是基础,观念文化是最上层并贯穿于其它三个层面。物质文化作为文化体系的基层和直接与生产劳动相联系的部分,在各民族中是最容易互相交流和趋同的。文化系统的其它三个层面在不同文化中存在较大差异,如风俗习惯、社会组织,尤其是观念文化中上升到哲学领域的部分。典型的例子是不同宗教信仰体系使不同民族间文化传统的差异十分明显。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以民族文化中哲学、意识形态部分的差异程度来衡量民族文化传统的差异程度。差异程度越大的民族在交往中产生障碍、造成摩擦的可能性也越大。
2.民族交往程度。民族交往程度指民族间交往领域的广泛程度和交往的频繁程度。前文已经论及民族交往是民族问题产生的前提之一和必要场景。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物质交往——首先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交往,乃是任何一种交往的基础。”[2](P881)民族交往也始自物质领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民族交往的领域和交往的频繁程度不断扩展。民族交往程度的增加,一方面打破了民族间的孤立状态,促进了民族间联系和相互依赖;另一方面使民族文化传统的差异性显露出来,使对民族群体利益的关注成为必要,从而增加了民族问题爆发的机会。此外,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2](P78)战争对野蛮民族来说是对群体利益维护的一种极端手段,但在文明社会也被用作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一种手段,殖民主义时代就是充分利用这种手段的结果。很明显,战争作为民族交往的一种形式,是直接造成民族问题的原因,并在民族关系上造成持续的消极影响。
3.民族社会性质和阶级状况。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私有制和阶级产生以后,这一点成为影响民族问题的最重要因素。迄今为止,世界上存在着两种性质的民族:一种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存在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民族,一种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族。前一种性质的民族,无论是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其民族内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从其阶级本性来讲必然要把阶级剥削延伸至本民族以外,对弱小民族进行经济上的剥削、政治上的统治、文化上的歧视。历史上和现实中大量的民族问题都是这样产生的。而后一种性质的民族,在民族内部已经消除了阶级剥削和压迫,各劳动人民之间团结、友爱、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已经成为主流。社会主义民族的性质决定了民族问题主要不是由民族阶级状况所造成,而是由其它一些因素所造成的。
4.政府的政策导向。政府总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政府在民族问题上实施的政策,从根本上来讲是摆脱不了其所代表的阶级的历史局限性的。但由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国家政体不同,具体政党或统治者思想观念和政治理念的不同等原因,使不同的政府采取了不同的民族政策,对民族问题产生了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在存在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社会里,彻底解决民族问题是不可能的,但在一定限度内解决民族问题是可能的,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民族和平(就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可能实现的限度内来说)只有在彻底民主主义的国家里才能实现”。[8](P242)列宁举了瑞士作为例证。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虽然消灭了阶级压迫和剥削,但政府政策的失误也会带来严重的民族问题。如前苏联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对内推行大俄罗斯主义,最终导致了国家的解体。可见政府的导向对民族问题的发生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以前的民族理论研究中往往忽视政府政策对民族问题、民族关系的影响,而在社会学、政治学中,这已是传统的研究领域。按照辛普森(Simpson)和英格尔(Yinger)的分类方法,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共有6种可以采取的政策,在程度上逐渐递进:同化政策(assimilation),多元社会政策(pluralist society),立法保护少数民族的政策(Legalprotection),和平或强制的人口迁移政策(population transfers),持续镇压的政策(subjugation),以及种族灭绝政策(extermination)。[9]按照沃思(Wirth,Louis)的分类方法,为了回应主体民族的态度和行为,少数民族可能采取的途径则有以下几种:[10]多元论(pluralistic)、同化论(assimilant)、分离论(secessionist)和好战论(militant)。主体民族的这6种政策及少数民族的这些反应并非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能同时并存或依次出现的。例如,一个逐渐显露的少数民族群体可能开始时是寻求宽容(多元论的途径),然后经过同化论阶段,最后,作为同化愿望受到挫败或拒绝主体民族价值观的结果,发展到分离主义或好战论。国内学者宁骚教授也就政府民族政策的类型等作了有益的探讨。[11]
5.民族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异程度。不同民族由于种种原因而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存在差异。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民族社会的总体发展水平,决定了民族力量对比的强弱,从而决定了民族间交往的不平等。发展程度高的民族打破落后民族的壁垒发生民族关系,这种交往一般是发达民族对落后民族的掠夺、剥削和压迫。全球性民族殖民地的出现,全球范围内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划分,正是由此产生的。此外在多民族国家内部,大民族对弱小民族的统治往往也是基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异上的。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异仍是造成民族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的问题就是这样产生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各民族的社会历史状况与其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应,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美国学者杜磊(Dru C.Gladney)认为,中国的民族识别既是一种共同性的划分,同时也是一种历时性的划分。因为中国的56个民族分布于依次演进的社会形态进化图式之中:汉族处在最前边,已经到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门槛,少数民族序列于后,从封建农奴制(藏族)到奴隶制(凉山彝族)再到原始社会末期(基诺族等)依次排列。[12]事实上,这种“生产力——社会形态”差异是新中国民族问题中迄今面临的最重要的方面。
6.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状况。很多不同的民族长期以来共同生活在相邻地区,以各种方式发生关系。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状况不是转瞬即逝,而是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友好往来,还是剥削压迫、战争、民族歧视,都会在民族心理、民族文化中留下深刻的印记。对现实中的民族来说,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状况无疑是影响如今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历史,深刻地影响着这些国家、民族对日本的态度。
7.民族分布地域与国家界限的吻合程度。民族与国家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现实中同一民族居住的地域并非都在同一国家之内,而同一国家之内往往居住着不同的民族。跨界民族问题是当今世界上普遍存在的问题。因此,民族分布地域与国家界限的吻合程度是影响民族问题的重要因素/变量之一。例如,中东库尔德人的分布地域分属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国,这直接造成了库尔德人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以上7个方面的指标主要是根据中国民族问题的特点而总结提出的,这些因素/变量的变化将是测度民族问题的发生、发展趋向的重要参考依据。此外,如果结合世界范围内的民族问题,我们还可以加上“体质特征的差异程度(种族特征)”等其它指标。
三
列宁曾经论述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民族问题上的两个历史趋势:“第一个趋势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第二个趋势是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被打破,资本、整个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10](P230)这实际上指出了民族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对立统一:民族交往的时空范围的扩展与民族问题发生的时空范围的扩展是成正比的。在人类日益向全球化发展的今天,民族问题也必将在历史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国际冲突、地区危机、国内政局动荡的一幕幕时兴剧中,民族问题的影子随处可见。
如果用本文的观点来分析当今世界的热点问题,我们或许可以发现各种因素是如何次序变化出不同的配方,上演出不同的故事的。例如,在库尔德人问题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民族分布地域与国家界限的不吻合性,但库尔德人在不同国家的不同遭遇又反映出政府政策导向的重要影响。因此,在不同事件中,往往是一种因素起主导作用,同时又是多种因素在综合起作用。
在我国,多民族互动的历史和场景决定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社会主义中国要把实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作为自己的社会目标,就要在现实中具体分析各种因素在具体民族问题中的变化情况,适时制定和调整政府的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