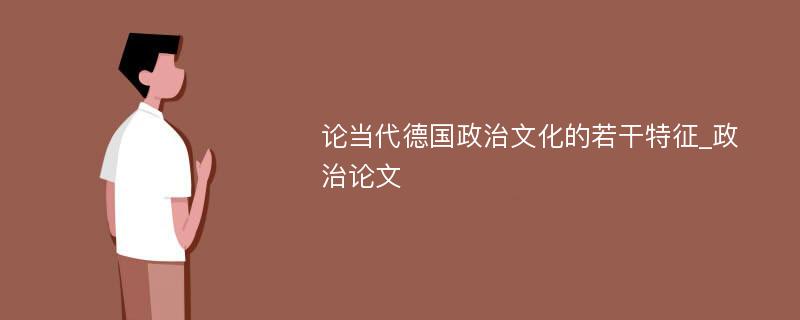
论德国当代政治文化若干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当代论文,政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16./731.77;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06)01—0021—05
一、德意志民族曲折的历史及政治文化史
1945年以前的100年间,德国的战争与革命几乎不断,整个国家及其政治文化云翻雨覆、大起大落,其领土和疆界也相继发生了多次重大改变;而自1945年以来的60年间,虽然截止到1989年11月的冷战期间热战的阴影始终存在,但是和平与发展成为其主流。只有比较深入全面地了解当代德国以及欧洲的政治文化及其特点,才能比较全面和深入地了解、理解和研究当代的德国及欧洲。
德国的政治文化特点与英国和法国等相比有着很大不同。首先,德国从近代以来至今的政治文化不像英国和法国等那样有比较强的连续性,而是因多次发生重大历史转折而发生很大变化。其次,德国在政治上的发展曾长期落后于英国和法国等,德国迟至1871年才实现国家统一,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成立魏玛共和国,但是于1933年又蜕变为纳粹专制国家,因此,对于1945年以前的德国而言,英国、法国乃至于美国是它的“西方”,主要自二次大战以后,联邦德国才开始融入西方世界(Westintegration),同时也开始了其政治现代化的进程。这个过程是德国历史上基本上没有过的(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民主制是一次失败的尝试),是一个新的历程。
英国有“日不落帝国”的自豪,法国有大革命的光荣传统,而德国基本谈不上有什么光荣历史传统自持,有的几乎只是惨痛的历史教训,其政治文化的突出特点之一是权威主义①,曾盲目相信和崇拜军国主义色彩浓厚的专制性国家,这恰恰是将德意志民族屡屡带入了战争的深渊。1949年9—10 月先后成立的两个德国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重要任务就是建立和巩固民主政治的基础,不使法西斯专制和战争危险卷土重来。德国的政治文化在战后开始了一个全新而又复杂曲折的历程。在纳粹统治时期,从国内政治制度角度看是实行专制独裁,从其对外政策看是实行极端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战后西德的国内政治制度是实行议会民主制,对外则主要是以克服极端民族主义、实行欧洲一体化为突出特征。
[美]阿尔蒙德和维巴在《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中区分了“参与型”、“臣属型”(又译“依附型”)和“地域型”这三种政治文化类型,并认为德国的特点主要是臣属型的,其具体表现是:1、 民众对政治生活不够主动和热心;2、习惯于服从;3、法治思想较为根深蒂固。这种总结固然有一定道理,但也有其历史局限性,因该书是以50年代调研资料为依据的,当时西德正处于战后政治文化重建阶段,此后情况又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政治文化也获得进一步发展。1990年德国重新统一之后,其政治文化又显示出新的特点。
政治文化的研究者把政治文化区分为主流文化和亚文化。对战后德国来说,反对战争、主张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及实行欧洲一体化、融入欧洲大家庭是德国政治文化的主流,而诸如极左翼、极右翼势力等问题则是其政治亚文化。
德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使战后德国政治文化显示出与欧洲其他国家及自身历史上的政治文化都很不相同的一些特点,突出的有:第一,极右翼势力始终存在,但遭到社会主流力量的反对;第二,极左翼势力和思潮虽始终存在,但趋于不断衰落;第三,反对战争、主张和平的呼声始终很高;第四,出于自身利益和与过去历史一刀两断,努力克服狭隘民族主义,坚决走欧洲一体化的道路,并努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两个德国政治文化的差异及其互动
战后德国的分裂状况既是冷战的产物,同时两个德国也分别处于冷战的最前沿。在这个时期德国的土地上,既存在着剑拔弩张、明争暗斗的局面,也出现了反对战争、热望和平的强大呼声。1990年德国的重新统一及冷战的结束,为欧洲一体化事业开辟了崭新的前景。
在希特勒军队于1945年5月彻底战败之后,有约250万纳粹国防军官兵被关进战俘营,还有几十万“纳粹积极分子和强烈同情纳粹的人”被拘禁,约1200万德国人从东普鲁士以及东欧等地被驱逐到奥德—尼斯河以西,纳粹政府文官系统也彻底瓦解。无论是工人还是中产阶级都一样陷于贫困当中。但德国并没有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那样发生政治革命或社会动乱,没有出现游行示威或者要求惩处纳粹领导人的呼声。生活在一片废墟当中的6千多万德国人基本上处于一种沮丧、 无奈和麻木的状态中,被称为“男人失去了希望、女人失去了自尊”的国家。德国重新回到历史的“零点”(Stunde Null),一切都必须从零开始。
德国在二战后被美、英、法、苏四大国分别占领,在德国建立什么样的政体当时不可能由德国人民自己决定,而是分别由东部占领区的苏联和西部占领区的美、英、法,尤其是美国所决定。此外,人们普遍担心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内乱和极右翼势力因此得势的历史在战后德国有朝一日重演,因此纷纷采取各种措施未雨绸缪,努力避免。
二战结束时,德国作为战争的主要发动者受到十分严厉的国际制裁,不仅国土被四大战胜国分区占领、10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被割让、不享有充分的国家主权,而且德意志民族被一分为二,形成了两个政治实体、两个德国。德意志民族背负着沉重的战争罪责,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事实上沦为二等国家和二等民族。1949年9 月联邦德国诞生时只享有部分国家主权,国际社会,尤其是其邻国对德国抱有严重的戒心。为了消除国际社会的疑虑,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3条因此明确规定:“(1)在联邦参议院同意下联邦可以通过法律将部分主权让予国际机构”。与此同时,在德国《基本法》中没有写入“德意志民族”或者“民族国家”等字眼。这主要是因为以希特勒为代表的德国法西斯主义曾经大肆煽动民族沙文主义,利用了德国人民的民族情绪,大肆滥用了这些字眼,联邦德国各界因而普遍认为二战的主要原因就是德意志民族主义即大日耳曼民族主义的恶性膨胀,从而普遍羞于再谈论“民族”和“民族国家”,更几乎闭口不谈爱国主义等,即把民族、民族主义甚至爱国主义都给“妖魔化”了,视之为洪水猛兽。而极右翼势力则继续滥用这些字眼,煽动排外情绪。
阿登纳等对于德国所负的历史责任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认为无论是俾斯麦、威廉二世的第二帝国还是希特勒的第三帝国,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和军事侵略性质,必须完全摈弃这一传统,代之以新的国际主义立场和形象。他十分警惕以往的民族自大狂卷土重来,认定大德意志帝国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德意志的未来在于与其他西欧国家在统一的联盟内共同协作。他反复强调“欧洲是我的指路明星”,要成为一个“欧洲色彩比德国色彩更浓的人”,并带领西德与法国和解,加入舒曼计划、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委员会、北约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等,使曾经“受人憎恨的德国佬和纳粹分子的国度重新取得在道义上受尊敬的地位”。② 但他企图通过重新武装联邦德国以及与西方结盟的实力政策迫使苏联政府允许德国重新统一的做法,在客观上却多少助长了联邦德国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极右翼势力,与他关于防止联邦德国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多少有些自相矛盾。由于德国缺少其他西欧国家的民主政治传统,因此不少人曾经担心联邦共和国会得到与魏玛共和国相同的下场。
民主德国于1949年10月成立时同样不享有完全的主权。在经历了纳粹专制统治之后,民主德国党和政府同样反对专制独裁。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及当时复杂而特殊的冷战背景,加之西方国家,尤其是联邦德国力图瓦解民主德国、争取让德国在联邦德国的基础上重新统一,使得民主德国对外和对内更多地采用强硬和高压的手段,采取了一些错误的政策,在社会上引起不少不满情绪。许多公民逃往西德。从1949年10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到1961年8月“柏林墙”建立这一期间,东德约有269万人流入西德,占东德人口的1/8,其中有150万人是从西柏林逃出的,多数是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有74%是45岁以下,50%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其中不乏一些知名人士。东德当局虽然在边界设置了检查站和管制站,但未能遏制出走的势头,而西方则把东德公民大批出走视为颠覆东德的“廉价原子弹”而予以鼓励。东德因此于1961年8月建起“柏林墙”以阻止公民外逃。从历史角度看,“柏林墙”的修建是东西方冷战的必然产物,沿边境线曾经密布铁丝网和地雷区,标志着当时德意志民族的完全分裂,对于德意志人民、尤其对当时的西德人在心理上和感情上造成了沉重的打击,认为德国重新统一的希望似乎遥遥无期。但与此同时,“柏林墙”也使东德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
西德与东德的政治经济体制及政治文化有很大差异,两者之间有着复杂的关联和影响。东德认为西德是“资本主义”、力图“复活军国主义”,西德则认为东德是“极权专制”、“暴政”、“不民主”等等。双方都把对方与希特勒政权相联系或相比较。客观地说,尽管阿登纳政府在努力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加入北约、起用若干前纳粹官员等方面的政策有不妥之处,但根本谈不上想重整军备、走纳粹扩张侵略的老路,也并不是想通过武力统一德国。当时东德政府对西德的抨击既有认识上的偏激,也有出于政治上即冷战的需要。也就是说,无论西德还是东德,当时都充满冷战思维,无法摆脱各自的成见和偏见,因此必然采取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尖锐对立态度。
西德把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当作其恩人和主要庇护者,完全依附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东德则把苏联当作其恩人和主要庇护者,完全依附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在两个德国因此必然形成完全不同的政治文化。东德的主流意识形态认为自己的道路及制度是完全正确的,而西德所走的道路和所选择的制度是完全错误的、“反动的”;而西德则正相反,认为自己的道路及制度是完全正确的,东德的道路则是完全错误的。但与此同时,无论在东德还是西德都存在亚文化群体,即东德有一部分人认为西德的道路更可取、向往西德的社会和生活,而西德也有一小部分人认为东德的道路更为正确,这主要是左翼乃至极左翼力量。极左翼和极右翼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否定民主制。历史的发展堪称物极必反,即法西斯德国的极右政策和前民主德国的极左做法都被联邦德国的主流力量所否定和反对。
两个德国在1990年实现重新统一固然有国际大环境发生变化的外部因素,但其内部因素起着更重要和更直接的作用。首先,虽然德国被分裂达45年之久,但两个德国的人民在语言、文化、生活习惯、民族认同意识等方面的共同之处仍始终存在,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东德政府否认存在一个统一的德意志民族,这是无视起码的事实;其次,两个德国在经济实力方面存在明显的差距,尽管东德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一些成就,在当时苏联东欧集团中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和西德相比差距十分明显,对于许多东德人,尤其是年轻人来说,认为同样是德意志人,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而西德的经济和生活水平要高得多,社会生活的活力和吸引力也大得多,感到无法理解和接受,因而迫切希望向西德看齐,希望通过统一迅速提高生活水平以及能够自由旅行、自由迁徙等;第三,自70年代以来,西德历届政府实行“以接近促转变”的东方政策,以各种方式显示自己的优越之处并在经济方面对东德慷慨解囊、大力支援,加强与之在经济、文化和人员等各方面的联系,为重新统一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第四,前东德政府思想保守、僵化,不思改革、进取和开放,对民众的改革要求置若罔闻,坚持一些极左的错误做法,造成社会不满、人心思变,最终被自己的人民所抛弃。
三、德国统一后政治文化的发展
统一后的德国,不少东德人最初对统一抱有极大的希望,但很快却失望了,民主社会主义党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失望情绪的得益者,对于许多人来说,只有民社党才能“为东部争取更多的权益”。萨克森州民社党领导成员克里斯蒂尼·奥斯托夫斯基主张,民社党应转变成一个“东部德国人的政党”,就像巴伐利亚的基社盟一样。民社党通过在三个地区的获胜于1994年重返联邦议院。而在东部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社民党在民社党的非正式支持下组成了一个政府。4年后, 在另一个东部州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出现了第一个正式的社民党—民社党联合政府。1998年,在社民党同绿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同时,民社党在联邦议会选举中获得了5 %的选票,这主要归功于其东部实力的增强。
另外,统一后的德国因为东西经济实力过分悬殊使德国东西部的人民都纷纷不满,而特别是东部的青少年由于大量失业,对前途没有信心,很容易将其艰难处境和仇恨情绪归咎发泄到外来难民及外国移民头上,认为是他们不仅消耗德国的经济实力,而且“夺去”了德国人的生存机会。当这些不满情绪受到新纳粹主义的挑拨,这些没有方向感的年轻人很快便学会通过蔑视其他种族来找回心理上的自尊和骄傲感。
德国的重新统一也使少数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上升。据1994年发表的一份青年调查报告显示,有45%的青年人觉得自己作为德国人比其他民族优越。原东部地区的政治体制全面瓦解,给社会造成某种混乱和失控,同时给东部地区人民普遍带来失落感和信仰危机,原有的政治观念和价值标准崩溃,失业人数迅速上升,这些都促使社会风气向右转。在德国统一之前,前东德基本上没有极右翼势力存在,更没有极右翼组织。在重新统一之后,位于德国西部的极右翼组织利用东部的混乱局面,迅速发展和网罗成员,使极右翼势力一度甚嚣尘上,超过了德国西部的势力。
在德国,极左翼势力有反美情结,极右翼势力同样有,并且与反犹主义密切相关。左翼反美除了反对军备竞赛之外,主要是因为反对剥削和社会分配不公。极右翼反美的原因与此相类似,也是反对美国及犹太人的“拜金主义”。
柏林墙倒塌15年后,2004年一项民意调查发现,仍有21%的德国人希望回到柏林墙时代:西部有24%、东部有12%的被调查者怀念过去的“好日子”。同时,还有20%的西部人和57%的东部人认为“大转折”之后他们的境遇得到改善。但在是否满意统一后政治制度的问题上,西部人只有41%、东部人只有27%表示满意。德国《明星》杂志2004年9月发表的民意调查结果表明,1/5的德国人希望重建柏林墙,德国西部居民中对其倒塌表示不满的人数远远多于东部居民,分别占24%和12%。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不满东部地区的发展耗费了大量资金(约占西部各州生产总值的4%);二是与先前的西德时期相比,生活状况恶化,工资减少, 失业率居高不下。2004年德国东部地区失业率仍为18%,西部地区为8%左右。不过, 57%的东部地区居民则对德国统一表示满意,宣称生活水平与前东德时期相比,得到了改善。
基于德国法西斯在二战期间犯下的滔天罪行,德国有不少人赞成把投身欧洲联合当作德意志民族得到救赎的基础。在学术界,也普遍把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视为“落后的”和“过时的”东西,认为目前世界已经到了“后民族国家时代”。例如,联邦德国著名政治学家策姆皮尔教授(E.Czempiel )认为“民族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了”③。哈贝马斯等则用“宪法爱国主义”取代民族主义。联邦制以及民族认同意识淡化是联邦德国政治文化的突出特点。在1972年联邦德国的一项民意调查中,有71%的人回答他们了解“国家”指的是什么,但回答不知怎样理解或定义“民族”一词的人却高达34%。这与当时德意志民族被一分为二、两个德国并存直接有关。在关于“民族自豪感”的调查统计中,德国人对本民族感到自豪的比例在欧盟国家中最低,在1986年时仅为71%,1993年更降为63%,2005年仅为64%(西部地区),均远低于欧盟其他国家;东部地区1993年为61%,2005年上升为66%。而对本民族不感到自豪的比例则最高,在1986年为27%,1993年达到37%,2005年为33%(西部地区);东部地区1993年为39%,2005年降为31%。德国战后占主导地位的民族观主要是“文化民族”观,而极右翼势力所持的民族观主要是“国家民族”观,与法西斯主义传统一脉相承,要求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民族即种族、种族“纯洁”是历史的首要因素。而“文化民族”观则以文化方面融合为主,同时允许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外来文化。
综观当代德国政治文化整体状况,可以看出其主流政治文化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1.当代德国已经从以往缺少政治民主传统逐步过渡到在整个德国完全确立西方的政治民主制度,并且已经站稳脚跟,魏玛共和国民主制度遭到失败的历史已经不可能重演。
2.德国的政治文化已经从昔日以臣属型为主、民众对政治参与冷淡,过渡到民众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摈弃了以往单纯信赖和服从政府的权威主义、国家主义传统。
3.从根本上摈弃了极端民族主义传统,以积极的姿态投入到欧洲一体化事业中并积极融入欧洲,同时积极参与国际范围的和平与发展事务。不过,由于社会和思想方面等多方面原因,其极右翼和极左翼思潮及势力作为政治亚文化仍将长期存在,但是几乎不可能重新成为社会的主流。
注释:
① 参阅王明芳:《权威主义政治文化与德国国家性格的改变》,《欧洲研究》,2005年第6期。
② 转引自[美]哈特里奇:《第四帝国》,新化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页。
③ 转引自[美]克雷格;《德国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6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