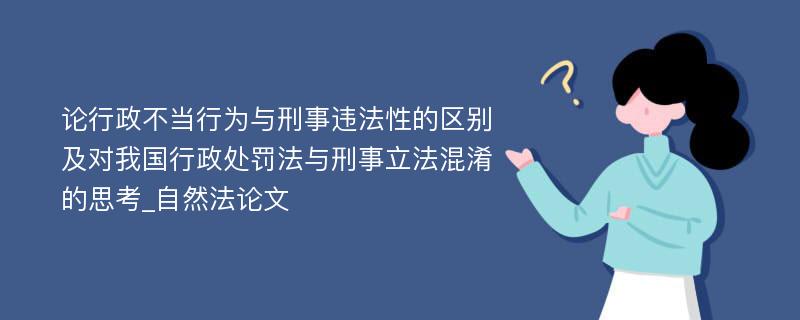
论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分野及对我国行政处罚法与刑事立法界限混淆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行政处罚法论文,分野论文,界限论文,行政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2008)10-0026-08
一、引言
在中国刑法的框架内探讨犯罪成立与否,不得不持久地面对罪量要素问题。刑法条文在某些犯罪构成中不仅对犯罪行为的类型进行规定,即某种具有社会危害性行为的性质特点,也对罪量做出一定要求,即要求这种社会危害性需要达到一定程度,始构成该条文规定的犯罪。分则条文对罪量的要求,在语言表述上体现为“情节严重”,“情节恶劣”“数额较大”或者“后果严重”等规定。这些规定,与刑法第13条关于犯罪的法定定义中的“但书”,即“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相对应,清晰地反映出我国犯罪论中的量化思维脉络。
这种对不法的量化思维不仅存在于刑事不法之中,而且也延续到行政不法领域。作为刑法犯罪构成之中罪量要求的结果,大量未达到罪量要求的行为,被置于行政法领域作为行政违法行为加以处置。这部分行为也体现出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因而需要被遏制。这种遏制必须以公法的手段进行,因而用行政处罚的办法解决轻微不法的问题,在我国就成为符合逻辑的立法选择。
二、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分野
(一)我国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关系
行政违法行为与行政刑法的性质在我国法学界一直未得到澄清。过去学者所作的大多数努力都是在现行的实在法框架下进行的[1],而我国现行的实在法在行政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之间的界限本就是十分模糊①,因而大多不具有理论上的批判意义。这些归类与定性的尝试在进行实在法上的分析的同时,又使用着西方法律理论的语言(这种语言以行政违法与犯罪行为之间的清晰界限为前提),往往在逻辑上存在问题,总是给人有似是而非之感。因而本文无意于对行政违法行为或者行政刑法进行实在法上的定性,为方便下文论述,仅根据实在法上的规定,将科以行政处罚的行政违法行为称之为行政不法行为,将刑法上被科以刑罚的犯罪行为称之为刑事不法行为。
如上所述,中国刑法中的量化思维与犯罪构成既定性又定量的立法模式,导致对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不法行为的遏制无法穷尽,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剩余部分,大量的行政不法构成要件被创造出来,以实现国家公权力对具有社会危害性行为的无缝隙的遏制。
对比我国刑法典与行政处罚法性质的法律,可以发现在刑事不法行为构成,即犯罪构成与行政不法行为构成类型之间存在大量重叠。例如对某种利益的侵害,可能同时是刑事不法行为和行政不法行为。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中的大量犯罪构成,都存在与之相对的行政违法行为构成,规定于相应的单行法的法律责任或罚则部分之中。例如刑法第140条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与《产品质量法》第50条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政违法行为的行为构成差别仅在于刑法第140条含有“销售金额5万元”的罪量规定。同样刑法第198条关于保险诈骗罪的规定与《保险法》第138条关于保险欺诈的行政违法行为的规定,在行为构成要件的描述上几乎完全吻合,二者之间的差别仅在于,刑法第198条中附加了“数额较大”这一罪量要素的规定。刑法第330条关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规定与《传染病防治法》第73条,刑法第331条关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规定与《传染病防治法》第74条也分别以极为相似的规定描述了相同的行为构成要件,差别之处仅在于刑法第330条要求引起甲类传染病威胁和情节严重,而第331条仅要求情节严重。
相似的例子在我国刑法中不胜枚举,此处不作赘述。这类行政不法的行为构成,实际上是作为补充刑法上犯罪行为构成而存在的。如果我们越过表面上的部门法的界限来观察,可以感触到立法者从社会防卫角度出发的不法行为遏制一体化思维,正如单行法中大量的“……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法条所显示的那样,立法者希望通过行政处罚法与刑法的平行立法创造公权力制裁的无缝隙对接。
这种在不法类型②上发生重合的犯罪行为与行政违法行为构成要件,我们在此姑且称之为“双重性构成要件”。这类构成要件在不法类型上既具有行政违法的性质,又具有刑事违法的性质。大量双重性构成要件的存在,与刑法第13条但书相对应,表明我国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之间区别,是纯粹的量的区别。而且这种量的区别主要是就行为客观方面的社会危害性程度而言,对行为人主观方面的考量极为有限。“数额较大”“后果严重”等罪量要素的表达用语,毫无疑问是就行为的客观方面提出量的要求。“情节严重”的罪量要求,学者认为既包括主观情节,也包括客观情节[2],然而大量的对“情节严重”进行细化要求的司法解释都是针对客观情节而言[3]。所以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刑法中的罪量确定主要是根据客观的不法含量来进行操作的。相应地,我国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之间的区别,基本上也就成为客观的不法含量的区别。
(二)德国法关于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区分的理论与实践
在德国法中,在行政不法(Verwaltungsunrecht)与刑事不法(kriminelles Unrecht)的分野问题上,学者展开了一场长达百年的争论。行政刑法理论(Verwaltungsstrafrechtstheorie)的创立者Goldschmidt发现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之间存在不同的目标设置,刑事法追求的目标是“欲求允许”(Wollenduerfen),即保障意志载体(Willenstraeger)的意志自由,而行政法追求的是福利(Wohlfahrt)③。刑事不法是一个意志载体对全体社会的意志的反抗,这种反抗必然侵犯另一个意志载体的权力范围,因而是法益侵害(Rechtsgueterbeeintraeehtigung)④。而行政不法是拒绝支持旨在创造国家或者公共福利的行政行为,是对福利的反抗,是违反国家行政的意志实现(Willensbetaetigung)的行为⑤。它仅仅是一种行政不顺从(Verwaltungsungehorsam),不是对某种实质的因素的侵犯。行政不法不是法益侵犯。从结果上来看,刑事不法造成的是实际的损失(damnum emergens),而行政不法造成的不是实际的损失,即已经存在的权益的损失,而是既得利益的损失(lucrum cessans),即通过行政行为所欲达到的更大的福利的不可实现⑥。
在Goldschmidt行政刑法理论的基础上,Erik Wolf将上述两种不法领域的差别进行了法哲学意义上的深化。从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思想出发,他认为在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之间存在着“超验的价值差别”(transzendentale Wertverschiedenheit),即刑事不法领域的价值是公正(Gerechtigkeit),而行政不法领域的价值则是福利(Wohlfahrt)⑦。刑事不法行为造成的损害是一种个人损失或者文化损失(Individual-oder Kulturschaden),而违反行政法的行为造成的仅仅是一种国家或者说社会的损失,这种损失不具有实质的内容,仅是一种特殊的拟制的损失⑧。
这种由学者热情倡导的行政刑法的理念,在20世纪上半期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动荡的德国,没有产生立法上的作用。直至在德国《1949年经济刑法》之中,这个被冷冻了近半个世纪的闪耀着自由主义的个人本位色彩的学说才被Eberhard Schmidt重新发现,获得了它在立法上的新生。该法尝试在行政刑法与刑事刑法之间进行泾渭分明的划分,以限制此前行政法对经济领域的过度干涉,改变行政刑法与司法刑法严重重合的现象[4]。
德国《1949年经济刑法》(Wirtschaftsstrafgesetz von 1949)将一些违反经济法规的行为明确规定为犯罪行为(第1-5条),另一些行为规定为违反秩序行为(Ordnungswidrigkeiten)⑨(第23,24条),而对第7条至第26条的行为,仅就构成要件无法区分其为行政违法还是犯罪行为,第6条作出规定,根据构成要件的具体实现情况,决定该行为的性质。即如果客观上行为损害到国家整个经济制度的,并且这种行为反映了行为人主观上对国家经济制度保护的漠视,即应当视为犯罪行为,否则仅构成行政违法行为。行政不法行为由行政机关处置,而犯罪行为则由司法机关定罪处罚,以抑制两种权力的交织。在该法的基础上,德国《1952年违反秩序法》(Ordnungswidrigkeitengesetz von 1952)的立法历年延续了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质的区别说⑩,创设了一套适用于各个行政领域的处理行政违法行为的实体与程序规则。
《1949年经济刑法》梳理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的出发点是值得赞赏的,然而这种立法例在实践中被证明是失败的。该法第7条至第26条的混合构成要件(Mischtatbestand)模式,即将行政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用一种构成要件进行规定,然后在根据第6条进行区分,在程序法上操作起来不易,反而造成行政资源与司法资源的浪费[5]。而且从法律明确性原则(Bestimmtheitsprinzip)的角度上来看,这种立法模式也不无问题(11)。因此1968年违反秩序法抛弃了这种立法例,不在实质法的意义上规定如何进行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区分,仅规定了一部分行政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其余的由具体部门法作出规定,某种行为到底是行政违法行为,还是犯罪行为。该法认识到行政违法与刑事不法行为在实际生活中的联系,因而试图创造程序法上的连接,以更有效地处理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行为(12)。
现行德国《违反秩序法》规定行政违法行为,如虚报姓名(第111条),违反立法机关场所管理(第112条),非法集会(第113条),制作不被允许的噪音(第117条),饲养危险的动物(第121条)等几乎全是单纯违反行政管理的行为,不涉及法益的侵害,即使个别法条禁止的行为触及到刑法保护的法益,也仅仅是抽象的危险犯的形式(13),不是直接的法益侵害行为。如果我们继续检索其余大量的散在单行法中的行政违法行为,例如《1977年税收法》(Abgabenordnungsgesetz)第377-383条,《道路交通法》(Strassenverkehrsgesetz)第23-24a条,《1954年经济刑法》(Wirtschaftsstrafgesetz von 1954)第3-5条规定的行政违法行为,上述发现也可以进一步得到支持。值得注意的是《1977年税收法》,该法在第370条将故意的偷税行为规定为偷税罪(Steuerhinterziehung),在第378条则规定,以重过失的罪过形式实施第370条规定的行为,则为行政违法行为,即轻率的逃税行为(leichterferitge Steuerverkuerzung)(14)。可见即使在此涉及到相同的法益,但是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之间仍然有着明确的界限,或者法益的侵犯方式不同,一种是实害犯,一种是危险犯;或者是行为主观方面不同,一种是故意的行为,一种是过失。这些差别反映出不同的不法或者罪责含量。
Goldschmidt所主张的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之间的质的差别说在19世纪50、60年代逐渐受到了挑战。量的差别说认为,Goldschmidt的人本主义的出发点,即把个人视为独立的个体,把个人作为意志载体受到的侵犯视为法益侵害,而行政违抗则认为是未损害到具有实质意义的因素的行为,已经不再适合现代社会国家(moderne Sozialstaat)的时代需要(15)。在社会国家时代,个人对行政行为的依赖性增大,对集体利益的损害同样也会触及到个人利益(16)。因而以法益侵害作为标准,在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之间进行泾渭分明的划分,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国家的语境。二者之间不存在质的差别,只存在量的差别,即社会危害性的大小,或者不法程度的高低之间的差别。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相比较,仅仅是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而已,是程度较大的不法(17)。
目前德国学界的主流观点(18)与联邦宪法法庭(19)承认质量区别混合说(20)。根据该观点,行政违法行为与刑法的核心区域的犯罪行为之间的区别是质的区别。例如谋杀,绑架之类的传统犯罪,只可能是由刑法规制的刑事不法行为,而不可能是行政违法行为。而处于刑法边缘区域的犯罪行为与行政不法之间,仅存在着不法程度的区别,即量的区别(21)。在刑法中存在着核心区域,其目的与任务是保护对于共同体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的价值(22)。侵犯这些核心价值的行为是刑事不法,其中反映出社会伦理的无价值判断(sozialethisches Unwerturteil)(23),反映出强烈的社会伦理的谴责。这个核心区域不是立法者可以任意划定的(24),而是由立法者所处的社会群体的价值形成所决定的。
因而如果立法者将本应属于这个核心区域的行为规定为行政违法行为,而不是犯罪行为,就是立法上的错误。属于这个核心区域的行为,即使其实施方式仅体现出较小的不法内容,例如数额较小的财产犯罪行为,也不得被规定为行政违法行为(25)。因为在这些行为构成要件中,即使被情节轻微的实施行为实现,也体现出对其所保护的价值的侵害。刑法法规范所传达的,是该价值应受到绝对保护的信息。构成要件所保护的价值的属性,而不是这种价值在具体构成要件实现中被侵害的范围,决定了它的归属性,即究竟属于行政不法还是刑事不法。
而在刑法的边缘区域,主要是一些违反经济、卫生、环保等行政制度的损害集体法益的犯罪方面,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之间存在的只是量的区别。在此立法者可以决定,对一种行为是运用刑法的手段,还是行政法的手段加以遏制(26)。例如上述德国《税收法》中第370条将故意的偷税行为规定为偷税罪,在第378条则将此种过失的行为规定为行政违法行为。虽然这两种行为构成涉及到相同的法益,但是在不同的行为主观方面反映了罪责与不法含量的不同。
从德国关于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区别的学说与法律实践中可以看到,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作为德国法上一对对应存在的概念,不断吸引着学者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立法者在立法活动中也有意识地对二者进行区别。质的区别说因袭自然法个人本位主义的价值观,在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之间进行泾渭分明的区分,有利于维护刑法的纯洁性,限制行政权力的扩张,重视保护公民的权利。然而如它的批评者所言,随着行政行为在现代社会中作用的不断增强,这种对于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观点已经过时了。而量的区别说未认识到刑法基本价值保护的使命,难免导致行政法与刑事法的融合,使刑法丧失独特性。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质量区别混合说的主流观点是值得赞赏的。这种观点既强调刑法在个人生命、自由与财产等自然法上的价值保护方面的独特性,也认识到西方现代刑法的社会背景发生转变,对行政利益与个人法益保护之间的区别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调和。
三、我国刑法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界限混淆的法理学解释
仅仅从客观的不法含量上进行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的区分,在犯罪构成中设置罪量要求,反映出我国刑法价值思维的缺失。价值判断的过程,从本质上就是倾向于类型化思维,而排斥量化思维的。对以法益被侵害的程度而不是以法益的类型作为标准,决定犯罪构成要件,进行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区分的立法思路,我们似乎可以做出此种解读。这种缺少价值导向的立法选择,也有着实用主义哲学的背景,使刑法的适用集中于社会危害性较大的犯罪行为上。如果大量的法益,不是根据其本身固有(von der Natur der Sache)的类型,而是根据其被侵害的程度,被决定到底须由刑法保护,还是由行政法保护,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刑法的存在是为了保护这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法益或者价值(elementare Werte)么?或者这个提问也可以这样进行:如果一些法益或者说价值,既可以由刑法保护,也可以由行政法保护,那么人们也不禁要问,这些价值还具有重要意义么?我国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在如此广泛的领域存在着重合,必然造成行政法对刑法所保护的价值的冲淡。刑法规范中体现的价值,因为受到来自行政法规范的挑战,而被相对化了。
我国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之间界限模糊,刑法的价值淡化,源于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自然法观念的缺失。从自然法产生的历史上来看,根据韦伯(Max Weber)的观点,中国缺少自然法产生的基础,即古代的宗教法律与世俗法律之间的紧张对峙,以及近代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对立(27)。我国在漫长的封建文化价值观中,独立的个人(在自然法意义上天赋权利的享有者,以及Goldschmidt所谓的作为意思载体的个体)是不存在的,个体总是作为家族与国家的组成部分而存在。而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然法理论强调对人与生俱来的生命权,自由权与财产权的绝对保护,防止公权力对个人权利的干预。这种自然法思想含有将个人与国家社会作为一对对应存在物来观察的倾向,试图确立防止政府违反自然法的有效措施(28)。于是试图探讨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之间的区别,防止以对待行政不法的方式,即运用简化的行政程序处理涉及个人权利侵犯的刑事不法,就成为符合自然法逻辑的理论追求。实际上,在Goldschmidt之前,Feuerbach就在自然法的意义上发现了刑事犯罪(Verbrechen)与违警罪(Polizeiuebertretungen)之间的区别,认为前者是违反个人体的权利(Verletzung subjektiver Rechte),这种自然权利是先于客观的实在法而存在的,而后者只是对法律规定的违反(Gesetzesverletzung)(29)。而Erik Wolf更为激进,认为“侵害”(Verletzen)这个概念原本就是取自自然法的语言世界(30)。
四、区分的必要性:行政权对司法权的牵制与刑法行政犯罪规定的闲置
我国法律制度中犯罪行为与行政不法行为构成类型之间的大量重叠,即大量“双重性构成要件”的存在,必然带来司法与行政权力的在处理具体案件时的冲突问题。对同一构成要件类型的行为,原则上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都拥有追诉权与处罚权。一般来说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力的时候较先获得对不法行为的调查权与处罚权,在此过程中当发现行为的不法含量达到刑法要求的程度时,才将案件移送至司法机关进行刑事追诉(《行政处罚法》第38条第4款)。因而对于“双重性构成要件”的犯罪行为而言——除非行为的情节非常严重,直接提示行为应被刑事追诉——刑事追诉与刑事处罚往往发生在行政机关介入之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行政机关的查处与移送决定,形成行政权对司法权的掣肘。
行政调查权与处罚权前置于公安机关的侦查权与检察机关的追诉权并与之竞争,会带来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在程序上造成行政处罚资源与刑事诉讼资源的重合浪费。即行政机关启动行政调查与处罚程序后,发现案件情节严重达到刑事追诉的标准,将案件移送至公安机关,其收集的证据不得直接采用,公安机关须重新侦查收集证据,带来资源的浪费(31)。第二,对于行政相对人或刑事被告人来说,因为对一件行为面临两次国家公权力的追问与处罚,可能违反“一事不再理”与“一事不再理”的原则[6]。
在我国的行政执法与刑事诉讼实践中,这一问题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行政机关对达到刑事追述标准应该移送的案件不移送而只给予行政处罚,所谓“以罚代刑”现象(32),已经引起学者与司法工作人员的重视。大量违反经济、卫生、环保等行政法规的经济犯罪与行政犯罪行为被行政机关查处结案,无法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使得行政犯罪的法规无法得到充分的适用而被闲置。
针对实践中的以罚代刑问题,国务院2001年7月颁布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同年9月制定了《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2004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与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同出台了《关于加强行政机关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工作联系的意见》,200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监察部和保知办等六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在行政执法中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同年3月,公安部分别与海关总署、国家版权局、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发布部门规章。这些法律文件尝试建立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刑事案件的工作衔接制度,提出了公安机关、监察机关、行政执法部门和人民检察院建立联席会议、信息共享等机制,加强执法协作,以及保障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权的方面的措施。然而这些措施,以及至今学者提出的建议,都只是集中在程序法的层面,并未触及实体法上深层次的问题:即实体法上行政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规定的重叠,大量双重性构成要件的存在。这是导致我国在处理行政处罚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纠结不清的根本原因。只有在实体法上理顺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之间的关系,降低行政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之间交叉的可能性,才能最终解决行政执法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冲突,减少“以罚代刑”等形式的行政权对司法权的侵蚀。
五、明晰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界限的方法探讨
如上文所述,无论是在法理的层面上考虑,还是从实践上更有效地遏制行政法罪的角度出发,我们都应该从实体法上理顺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之间的关系,减少双重性构成要件的数量,减少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之间不法类型的交叉。
(一)根据不法性质进行区分的尝试
首先,在涉及个人生命、财产法益的刑法核心区域,确立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之间存在性质上的区别的意识,尽量减少设置涉及直接侵害个人生命,财产法益的行政不法行为构成。例如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我国采取行政保护与刑事保护双轨制,对于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根据其侵害程度大小,分别予以行政或者刑罚的处罚。刑法第213条至217条规定的犯罪构成,与《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承担行政责任的行为构成之间,存在着大量的类型上的重合。知识产权作为一种财产法上的私权,对这种权利的侵害反映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冲突。以行政处罚的方式平息个人之间的私权利的冲突,似乎与行政行为促进大多数人的福利的宗旨不相符合。另一方面行政罚与刑罚并行存在于这个领域,互相竞争,也冲淡了在制裁这种权利侵害行为中表现出来的负面的社会评价。因为行政机关作为制裁的主体,反映的仅仅是行政机关对一个行为的不赞成与纠正的意愿,而非刑事法庭在适用刑法过程中代表国家与社会所表达的谴责。
在这些领域保护的是对于社会共同体的存在至关重要的价值,这些价值保护应是刑法的排他性的任务。如果对这些价值的侵害,哪怕是程度较轻的侵害,交由行政法规进行处罚,也会损害犯罪构成要件作为不法类型的呼吁功能(Appelfunktion des Tatbestandes)(33),即呼吁法规范对象慎为犯罪构成要件行为的功能,从而降低刑法的威慑作用,损害法规范对象对这些价值的尊重。
然而如果减少行政不法行为的构成,对不法行为仅以刑罚的方式遏制,在原有犯罪构成的框架下,仍然坚持对达到刑法上罪量要求的行为才予以定罪处罚,那么未达到该罪量要求的行为就得不到制裁。如果依照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模式,在犯罪构成中放弃罪量要素,将所有的侵犯法益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都视为犯罪,而无论法益侵害或社会危害性的程度,势必使现行法框架下的本应以行政罚处理的行为都面临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可能性,带来巨大的刑事追诉的压力。考虑到我国现行的程序法框架和司法资源配置情况,在现阶段采取只定性不定量的犯罪构成要件模式不够现实。因而废除大量行政不法构成要件之后,在保留现有定性加定量的犯罪构成要件模式前提下,可以考虑调低罪量要求,降低刑事追诉的起刑点,使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不法行为也能够被纳入刑罚遏制的范围之内。而对在这个起刑点以下的,具有更低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则不予公权力的制裁。这部分不法行为,由于往往涉及对他人私权利的侵犯,完全可以由承当民事责任的方式得到一定的遏制[7]。
(二)根据不法的量进行区分的尝试
而在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之间仅存在量的区别的刑法边缘区域,如何避免双重性构成要件的规定,就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简单归类问题。进入现代行政国家之后,行政法规在社会中的作用日益增强,违反行政规定的行为不再只是具有形式上的违法性,而是可能直接损害现代国家的功能与社会秩序(如国家的经济利益,公共卫生安全,道路交通安全),最终也会影响到对个人利益的保护。因而现代刑法在构成要件中与大量的行政法规相连接,创造了众多的行政犯罪构成要件,于是违反行政规定的行为也可能成为刑事不法行为,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范围的重合似乎在所难免。刑法上也因而发展出集体法益的概念,产生了法益抽象化现象(Abstraktionsprozess der Rechtsgueter)(34)。Erik Wolf对法益抽象化现象提出批判,认为法益逐渐与基本的生活利益脱节而被抽象化,已经无法在不同法益价值位阶之间进行区分,导致轻罪与重罪之间的区别逐渐消失,最终导致法益概念的形式化。在这个意义上,Erik Wolf指出,法益的抽象化过程也是对法益的否定过程(35)。
在刑法与行政法交界的边缘区域,法益概念由于被不断地抽象化而失去了批判功能,因而利用法益侵犯标准进行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的区分,已经失去实际的意义。这里无法再仅仅根据法益侵害的类型,或者传统上已经确立的刑法保护的价值,来决定不法行为的属性。这就向立法者在立法技术上提出更高的要求。在此亟需拓宽关于罪量的过于狭窄的思路,即将罪量仅仅理解为关于客观上的行为后果或者行为外在表现的数学上的值(36)。
实际上,对罪量的考察是一个多维的全面性的考察过程,衡量罪量大小的因素可以是多方面的。德国刑法学者kruempelmann尝试对犯罪进系统化的量化分析,认为衡量罪量大小应从行为无价值,结果无价值,以及罪责三方面进行(37)。我国刑法学者也主张对“情节”进行综合性的理解,要求司法者应该从法益的性质,行为的方法,行为的对象,行为的结果、行为人的故意,过失内容,动机与目的等方面对“情节”进行综合性的解释[8]。但是,这种对罪量要素的探讨,不应该只停留在司法层面,作为司法机关对定罪情节的进行解释时的要求。对如此范围广泛的罪量因素,完全交由司法机关进行判断衡量,似乎已经超出了司法裁量权的范围。司法解释中列明的一些情节严重的行为,本就是典型的类型化行为,完全可以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加以固定。实际上,如果在立法层面能够对罪量在构成要件中进行较为细化的描述,可以改变我国刑法中“情节严重”的规定比比皆是这一立法粗疏的现象(38),使法定构成要件更加精致,也有利于行政不法构成要件与刑事不法构成要件之间的区分,避免大量双重性构成要件的产生。
因而立法者应该努力探讨实害犯(Verletzungsdelikt)与危险犯,在实害犯内部探讨不同的法益侵害方式,以及行为故意或者过失等,特定的行为目的等行为主观方面的差别所反映的不法与罪责的程度差别,作为我们在罪量方面考察的量化标准,并以此作为划分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立法上的依据。例如,可以考虑尽量将实害行为和存在具体的法益侵害危险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行为,而对那些仅仅违反行政规定,还没有给法益带来即将实现的具体危害的抽象的危险行为作为行政不法予以规定。例如,德国《1977年税收法》中规定危害税收的行为,即以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形式出具相关不实证明材料,或者获取报酬使用相关证明材料,以及不正确的簿记,有可能造成少缴纳税款的,以及不尽相应的通告义务或者不实通告,或者违反保证账户真实义务的,或者故意或过失不履行配合税务部门税收稽查的,须承担行政责任(第379条)。而实际发生的故意的偷税行为,在第370条中被规定为犯罪行为。
如我国《传染病防治法》第73条的行为构成包含“导致或者可能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的情节要求,第74条的行为构成包含“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以及其他严重后果”的要求,已经涉及对他人生命健康权这种基本价值的侵犯,不应再作为行政不法来规定,以减少行政法与刑事法在构成要件类型上的重合。因而在上述两条规定中,应该删去上述情节要求,仅对违反行政管理规定的行为作为行政不法予以行政罚,而对已经引起传染病传播的行为,与存在确实的导致传染病传播危险的行为,规定为结果犯或具体的危险犯形式的犯罪行为。相比之下,刑法第141条生产、销售假药罪与第142条销售劣药罪分别与《药品管理法》第75条、76条相比,分别在犯罪构成中增加了“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与“对人体造成严重危害的”规定,当属为数不多的行政立法与刑事不法之间界限明晰的立法例。即将违反行政规定,尚不足以造成具体法益侵害危险的行为规定,以抽象危险犯的形式规定为行政不法,而对存在具体的法益侵害危险的行为或者造成实际侵害的行为,作为犯罪行为加以规定。
问题是对于实害犯来说,如果只将实害犯规定为犯罪行为,而我国刑法又在罪量要素方面对具体侵害的情节或者数额做出要求,那么对于未达到这些要求的行为又无法再追究行政责任,会导致对这部分行为的放纵,结果成为对于实害犯的遏制反而不如对危险犯严格。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另外,这部分行为往往涉及侵害抽象的法益,没有具体的权利人对于权利侵害主张权利,因此也不存在对这些行为的民事制裁。因而对于实际侵犯法益的行为,不能够简单地废除行政处罚的行为构成要件,而只能是容忍它们与犯罪构成要件的并存。对于这部分行为,行政执法权与司法权之间的竞争关系无法划分不法类型的立法层面上上得到解决。但是可以考虑通过降低犯罪数额或者情节要求的方式,使更多的行政不法行为进入刑事诉讼的程序,以限制行政权与司法权相交叉的范围,进而限制行政权对司法权的干涉。
六、结语
我国传统法律中自然法权利观的缺失,刑法的价值淡化,造成行政处罚法与刑事立法界限模糊,催生了大量双重性构成要件。对于当下处于法治国建设时期的中国,探讨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的分野问题,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从刑事政策上来说,区分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也必然伴随着逐步降低刑法中罪量要求的过程。这两个过程都有利于促进刑法的价值生成,使刑法在一些基本的价值保护中寻回其独特性。在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实现构成要件类型上的分离,罪量要求在构成要件中被细化并被逐步降低以后,刑法的构成要件作为不法类型的呼吁功能才能够得到增强,刑法上的价值才能够受到更大程度的尊重。
收稿日期:2008-08-12
注释:
①在如下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我国的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之间本就不存在性质上的区别。
②即Unrechtstypus,这一概念为德国刑法学界广泛使用,指不法行为的类型,也就是Tatbestand。因为德国刑法中的犯罪构成要件是类型化的思维,而不是如我国那样是类型化加量化的思维,罪量要素很少出现在德国刑法犯罪构成要件中。但是在我国刑法与行政处罚法的框架内使用不法类型这个概念,就是撇开罪量要素,指构成要件的“类型”而言。因此在我国刑法中,不法类型不等于构成要件。但是如果在德国刑法中使用“构成要件的类型”这样的语词,就会有同义反复之嫌。
③See James Goldschmidt.Dss Verwaltungsstrafrecht:Eine Untersuchung der Grenzegebiete zwischen Strafrecht und Verwaltungsstrafrecht auf rechtsgeschichtlicher und rechtsvergleichender Grundlage,Berlin [M],1902,S.529ff.
④同注释③Goldschmidt,Das Verwaltungsstrafrecht,S.540,
⑤同注释③Goldschmidt,Das Verwaltungsstrafrecht,S.544.
⑥同注释③Goldschmidt,Das Verwaltungsstrafrecht,S.545.
⑦See Erik,Wolf.Die Stellung der Verwaltungsdelikte im Strafrechtssystem,in Festgabe fuer Reihard von Frank Bd.2 [M],Tuebingen,1930,S.521ff.
⑧同注释⑦Erik Wolf,Die Stellung der Verwaltungsdelikte im Strafrechtssystem,S.565.
⑨这些行为由行政机关追诉与惩罚,相当于我国的行政违法行为。为了方便进行比较法意义上的讨论,以下即将德国法中的Ordnungswidriskeit称之为行政违法行为。
⑩See Erich Goehler.Ordungswidrigkeitengesetz 12.Aufl.,Muenehen,1998,Vor § 1 Rn.4.
(11)BT-Drueksache V/1269,S.27f.
(12)See Heinz Mattes.Untersuchung zur Lehre von den Ordnungswidrigkeiten,Bd.11 [M],Berlin,1982,S.336.
(13)Roxin指出,众多道路交通法中的秩序违反行为都是抽象的危险犯,认为这些犯罪也涉及到个人生命健康法益的侵犯。见Roxin,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4.Aufl.,Muenchen,2006§2Rn.131.
(14)相同的观点参见王世洲.罪与非罪之间的理论与实践——关于德国违反秩序法的几点考察[J].比较法研究,2002(2):185.
(15)同注释(12)Heinz Mattes,Untersuchung zur Lehre von den Ordnungswidrigkeiten,Band 11,S.124.
(16)See Justus Kruempelmann.Die Bagatelldelikte:Untersuchung zum Verbrechen als Steigerungsbegriff [M],Berlin,1966,S.167f.
(17)同注释(16)Justus Kruempelmann,Die Bagatelldelikte,S.171.
(18)Roxin,同注释(13)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2 Rn.133; Goehler,同上,vor § 1 Rn.6; Jakobs,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2Aufl.,3/9; Jescheck/Weigend,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5.Aufl.,§ 7 V3 b,进一步的引注见Roxin,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4.Aufl.,§ 2 Rn 133,Fn.194.
(19)BVerfGE 51,60,74:NJW 1979,1981,1982.
(20)Roxin,同注释(13)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2 Rn.133; Goehler,同上,vor § 1 Rn.6; Jakobs,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2.Aufl.,3/9; Jescheck/Weigend,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5.Aufl.§7 V3 b,进一步的引注见Roxin,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4.Aufl.,§ 2 Rn 133,Fn.194; BVerfGE 51,60,74:NJW 1979,1981,1982.
(21)Roxin,AT4,§ 2 Rn.132; Jakobs,AT2,3/10.
(22)BVerfGE 27,18,29:NJW 1969,1619,1621.
(23)BVerfGE 27,18,28:NJW 1969,1619,1621.
(24)同注释⑩Goehler,Vor § 1,Rn.8
(25)同注释⑩Goehler,Vor § 1,Rn.6.
(26)同注释⑩Goehler,Vor § 1,Rn.6.
(27)转引自陈兴良的论述:陈兴良.刑法的价值构造[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1.
(28)博登海默认为,这是洛克自然法学的标志。参见陈兴良的论述:陈兴良.刑法的价值构造[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3.
(29)同注释③Goldschmidt,Das Verwaltungsstrafrecht,S.232f.
(30)同注释⑦Erik Wolf,Die Stellung der Verwaltungsdelikte im Strafrechtssystem,S,533.
(31)关于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中的证据材料转化问题参见:杜娟.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机制的层次化思考,刘远,王大海.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机制论要[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218-219.
(32)例如关于2001-2003年工商行政管理系统与质检系统移送案件的统计数据可见李仁和:《形成打击经济犯罪的合力——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相衔接机制座谈会述要》,载《人民检察》2003年第12期。国家商标执法数据显示,2005年全年共查处商标侵权假冒案件39107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商标侵权假冒案件仅为236件。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网站:http://sbj.saic.gov.cn/pub/show.asp?id=82&bm=zfal 国家版权执法的统计数据也显示了较低的案件移送率:2005年全国各级版权行政管理部门共受理案件9644件,其中处罚7840起,调解1174起,移送司法机关366起。2004年全国各级版权行政管理机关共受理案件9691件,其中处罚7986起,调解1363起,移送司法机关101起。见国家版权局网站:http://www.ncac.gov.cn/Galaxy Portal/inner/bqj/include/list-columnbqtj.jsp?BoardID=304&boardid=11501010111610&bqgbid=11501010111610
(33)关于Appelfunktion可见Roxin的简短论述:Roxin,同注释(13)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4.Aufl.,§14,Rn.66f.u.§19,Rn.3.在相同的意义上kruempelmann引证了刑法的指示作用(Weisungsfunktion des Strafrechts),参见kruempelmann,同注释(16)Die Bagatelldelikte,S.135以及脚注30。
(34)同注释⑦Erik Wolf,Die Stellung der Verwaltungsdelikte,S.537f.
(35)同注释⑦Erik Wolf,Die Stellung der Verwaltungsdelikte,S.538.
(36)如上所述,我国司法实践中一直是基于这种局限的理解来确定罪量要素的,司法解释偏爱于追求数学上的精确性,习惯于给出一个具体的数额作为确定罪与非罪的界限。
(37)Kruempelmann,同注释(16)Die Bagatelldelikte,Drittes Kapitel,S.62ff.
(38)陈兴良.刑法哲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499,563.反对的观点参见: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27.
标签:自然法论文; 法律论文; 犯罪构成要件论文; 刑法理论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刑事犯罪论文; 行政立法论文; 构成要件要素论文; 社会法论文; 行政违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