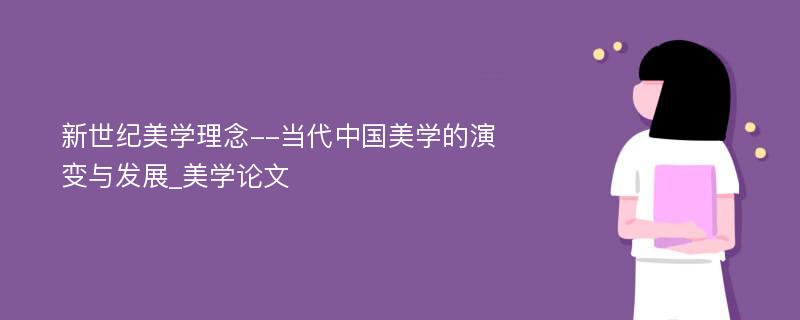
中国当代美学的演化与发展——新世纪美学的一个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新世纪论文,中国当代论文,思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世界是在人、自然、社会的三维互动中实现的,其中人与自然的维度作为第一进向,涉及的是我—它关系,人与社会的维度作为第二进向,涉及的是我—他关系。它们又都可以一并称之为现实维度,是人类求生存的维度,然而,由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必然导致自我的诞生,也必然使得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完全失去感应、交流与协调的可能。而这就相应地必然导致对于感应、交流与协调的内在需要。这一需要的集中体现,就是“爱”。但是,真正的爱只能是一种区别于现实关怀的终极关怀,也只能是一种对于一切外在必然的超越,而这就必然融入作为第三进向的人与意义的维度之中。因为作为第三进向的人与意义的维度正是一种区别于现实关怀的终极关怀,也只能是一种对于一切外在必然的超越。人与意义的维度涉及的是我—你关系。它可以称之为超越维度,是求生存的意义的维度,意味着最为根本的意义关联、最终目的与终极关怀,意味着安身立命之处的皈依,是一种在作为第一进向的人与自然维度与作为第二进向的人与社会维度建构之前就已经建构的一种本真世界。它也称为信仰的维度。因为只有在信仰之中,人类才会不仅坚信存在最为根本的意义关联、最终目的与终极关怀,而且坚信可以将最为根本的意义关联、最终目的与终极关怀诉诸实现。就是这样,人与意义的维度使得最为根本的意义关联、最终目的与终极关怀成为可能,也使得作为最为根本的意义关联、最终目的与终极关怀的集中体现的爱成为可能。至于审美,毫无疑问,作为人类最为根本的意义关联、最终目的与终极关怀的体验,它必将是爱的见证,也必将是人与意义的维度、信仰的维度的见证。显而易见,中国并没有走上这条道路。在人、自然、社会的三维互动中,对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的全力看护,使得中国作为第一进向的人与自然维度与作为第二进向的人与社会维度出现根本扭曲。在人与自然维度,认识关系被等同于评价关系,以致忽视自然与人之间各自的规定性,片面强调两者的相互联系,并且把自然和人各自的性质放在同质同构的前提下来讨论。在人与社会维度,政治、经济以及道德情感等非自然关系被等同于自然关系,君臣、官民等非血缘关系被等同于血缘关系,总之是用以血缘为纽带的伦理关系来取代以利益为纽带的契约关系。显然,这样一来本位应运诞生的“自我”根本就无从产生。
进而言之,由于对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的全力看护,加以进入“轴心时代”之后血缘关系并没有被彻底斩断,因此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出现的感应、交流与协调的巨大困惑就不会通过“上帝”而只会通过自身去加以解决。这样,从“原善”而不是原罪的角度来规定人,就合乎逻辑地成为中国的必然选择。而作为现实关怀的“德”也就取代了作为终极关怀的爱。我们知道,人与意义的维度只是一种可能,是否出现与如何出现,却要以不同的条件为转移。在中国,由于作为现实关怀的“德”对于作为终极关怀的爱的取代,人与意义的维度的出现,事实上就只是以“出现”来扼杀它的“出现”,只是一种逃避、遮蔽、遗忘、假冒、僭代。所以鲁迅说:中国有迷信、狂信,但是没有坚信。很少“信而从”,而是“怕而利用”。鲁迅还说:中国只有“官魂”与“匪魂”,但是没有灵魂。这正是对中国人与意义的维度的“逃避、遮蔽、遗忘、假冒、僭代”的洞察。至于审美,则正是中国人与意义的维度的“逃避、遮蔽、遗忘、假冒、僭代”的见证。
当然,中国美学也并非对于上述缺憾就毫无察觉。从明中叶开始,中国美学的无视向生命索取意义的人与意义维度以及为此而采取的“骗”、“瞒”、“躲”等对策,逐渐为人们所觉察,其中,被汤因比称之为“最后的纯粹”的王阳明堪称序曲,他的“龙场悟道”意味着真正的思想不可能是别的什么,而只能是“愚夫愚妇亦与圣人同”的“人人现在”,这就是所谓“切问而近思”,即最切之间、最近之思。正是他,迈出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率先在心之体的角度统一了宋明理学的天人鸿沟,为人心洗去恶名,提倡“无善无恶”,不过在心之用的角度却仍旧认为“有善有恶”,因此天人还是割裂的;王畿迈出了第二步,统一了心之用,这就是他提出的心、意、知、物“四无”说;罗汝芳进而把心落实为生命本身,“盖人之出世,本由造物之生机,故人为之生,自有天然之乐趣”(罗汝芳:《语录》),从而迈出了第三步;至此为止,他们都是在将“天理”这一“自然“原则加以自然化,而且真诚地认为良知的自然流行肯定会转化为积极的道德成果,然而却导致了“天理”的灰飞烟灭,导致尊天理灭人欲最终转向灭天理尊人欲。李贽正是因此而应运而生。有感于人们始终为传统所缚的缺撼,李贽疾呼要”天堂有佛,即赴天堂;地狱有佛,即赴地狱”,甚至反复强调”凡为学者皆为穷究生死根由,探讨自家性命下落”(注:李贽:《李贽文集》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页。)。而李贽所迈出的决定性的一步则在于,干脆把它落实到“人必有私”的“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之中,这是第四步,也是中国美学走出自身根本缺憾的第一步。他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颠倒千万世之是非”,提倡庄子的“任其性情之情”,各从所好、各骋所长、各遂其生、各获其愿,认为“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从而把儒家美学抛在身后;同时认为“非于情性之外复有所谓自然而然”,因此没有必要以“虚静恬淡寂寞无为”来统一“性命之情”,从而把道家美学也抛在身后。应该说,这正是对于生命的权利以及自主人格的高扬。在他的身后,是“弟自不敢齿于世,而世肯与之齿乎”并呼唤“必须有大担当者出来整顿一番”的袁宏道,是“人生坠地,便为情使”(《选古今南北剧序》)的徐渭,是“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牡丹亭记题词》)的汤显祖,是“性无可求,总求之于情耳”(《读外余言》卷一)的袁枚,等等。从此,“我生天地始生,我死天地亦死。我未生以前,不见有天地,虽谓之至此始生可也。我既死之后,亦不见有天地,虽谓之至此亦死可也。”(廖燕:《三才说》)伦理道德、天之自然开始走向人之自然,伦理人格、自然人格、宗教人格也开始走向个体人格,胎死于中国文化、中国美学母腹千年之久的自我,开始再次苏醒。而曹雪芹的为美学补“情性”,则是其中的高峰。“开辟鸿蒙,谁为情种”,曹雪芹深知中国美学的缺憾所在,洞察到第三进向的人与自我(灵魂)的维度的阙如,并且发现大荒无稽的世界(儒道佛世界)中,只剩下一块生为“情种”的石头没有使用,被“弃在青梗峰下”,于是毅然启用此石,为无情之天补“情”,亦即以“情性”来重新设定人性(脂砚斋说:《红楼梦》是“让天下人共来哭这个‘情’字”),弥补作为第三进向的人与自我(灵魂)的维度的阙如。这无疑意味着理解中国美学的一种崭新的方式(因此《红楼梦》不是警世之作,而是煽情之作)。“因空见色,由色传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红楼梦》实在是一部从生命本体、精神方式入手来考察民族的精神困境的大书。它作为中华民族的美学圣经与灵魂寓言,将过去的“生命如何能够成圣”转换为现在的“生命如何能够成人”,同时将过去的理在情先、理在情中转换为现在的情在理先。先于仁义道德、先于良知之心的生命被凸显而出,“情”则成为这个生命的本体存在。这“情”当然不以“亲亲”为根据,也不以“交相利”的功利之情为根据,而是以“性本”为根据。由此,曹雪芹希望为中国人找到一个新的人性根据,并以之来重构历史。我们看到,在“德性”、“天性”、“自性”、“佛性”之后,发乎自然的“情”,就这样被曹雪芹放在“温柔之乡”呵护起来(类似《麦田守望者》中的小男孩霍尔顿的守望童心,大观园中的贾宝玉则是守望“情性”),坚决拒绝进入社会、政治、学校、家庭、成人社会,不容任何的外在污染,“质本洁来还洁去”,则成为《红楼梦》的灵魂展示的必要前提。鲁迅先生发现:“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注:《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31页。)堪称目光犀利。
显然,《红楼梦》的出现,深刻地触及了中国人的美学困惑与心灵困惑,同时也为解决中国人的美学困惑与心灵困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答案。但是由于自我始终没有出场,因此这无所凭借的“情”最终也就没有能够走向“爱”,也就必然走向失败。历史期待着“自我”的隆重出场,期待着从以“情”补天到以“爱”补天,期待着从引进“科学”以弥补作为第一进向的人与自然的维度的不足和引进“民主”以弥补作为第二进向的人与社会的维度的不足到引进“信仰”从而弥补作为第三进向的人与自我(灵魂)的维度的阙如。而这,正是从王国维、鲁迅开始的新一代美学家们的历史使命!
中国美学的20世纪,是王国维与鲁迅的世纪。而王国维、鲁迅对于个体生命的关注,则是中国美学的创世纪。不过,在他们之间,“个体生命”所导致的结果又有其不同。我们已经知道,在王国维,个体生命的发现使得他成为开一代新风的中国现代的美学之父,同时,个体生命的发现也使得他成为打开魔盒并放出魔鬼的中国现代的美学潘多拉。然而,个体一旦诞生,生命的虚无同时应运而生。由此而来的痛苦,令王国维忧心如焚、痛不欲生。个体生命确实“可信”,但是却实在并不“可爱”;人生确实就是痛苦,但是难道痛苦就是人生?王国维绝对无法接受,于是不惜以审美作为“蕴藉”与“解脱”的暂憩之所,结果为痛苦而生,也为痛苦而死,整个地让出了生命的尊严。在鲁迅,则有所不同。纠缠王国维一生的美学困惑在鲁迅那里并不存在。相比王国维的承受痛苦、被动接受和意志的无可奈何,鲁迅却是承担痛苦、主动迎接和意志的主动选择。因此,痛苦在鲁迅那里已经不是痛苦,而是绝望。有什么比“走完了那坟地之后”却仍旧不知所往和活着但却并不存在更为悲哀的呢?生命与虚无成为对等的概念,担当生命因此也就成为担当虚无。所以,生命的觉悟就总是对于痛苦的觉悟而不再是别的什么。而“绝望”恰恰就是对于“痛苦”的觉悟。既然个体唯余“痛苦”、个体就是“痛苦”,那么直面痛苦,与“痛苦”共始终,则是必须的命运。换言之,虚无的全部根源在于自由意志,个体的全部根源也在于自由意志。因此,可以通过放弃自由意志以致贬损自我的尊严,也可以通过高扬自由意志以提升自我的尊严。既然个体生命只能与虚无相伴而来,那么担当生命也就是担当虚无,而化解痛苦的最好方式,就是承认它根本无法化解。显然,这正是鲁迅的选择。由此,鲁迅把一种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荒谬的审美体验,破天荒地带给了中国有史以来生存其中而且非常熟悉的美学世界。心灵黑暗的在场者,成为新世纪美学的象征。而鲁迅的来自铁屋子的声音,也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在场者的声音。
然而,在王国维之后,鲁迅的探索却仍旧没有成功。尽管在鲁迅真正的人性深度借助灵魂维度的开掘而得以开掘。然而,成也绝望,败也绝望,鲁迅最终仍并未能将绝望进行到底,鲁迅只意识到灵魂的维度,却没有意识到信仰的高度。他没有能够为自身的生存、为直面个体生命的痛苦、直面绝望找到一个更高的理由,没有能够走向信仰,最终也就没有能够走得更远。同样,鲁迅确实来到了客西马尼园的入口处,但也仅仅是来到了客西马尼园的入口处。他没有能够在绝望中找到真正的灵魂皈依,也没有能够在虚无中坚信意义、在绝望中固守希望。他的来自心灵黑暗的在场者的声音,只是为绝望而绝望的声音。就是这样,鲁迅与信仰之维、爱之维失之交臂,也与“信仰启蒙”这样一个20世纪的思想的制高点失之交臂。
遗憾的是,此后的无论社会美学、认识美学还是实践美学都从根本上偏离了王国维、鲁迅所开创的美学道路,面对王国维、鲁迅所开创的弥足珍贵的生命话语,他们之中能够在其中“呼吸领会”的美学家竟然至今也未能出现,因此始终既未能“照着讲”,也未能“接着讲”,王国维、鲁迅所创始的生命美学思潮犹如“于今绝也”的《广陵散》,被遗忘得无影无踪。而王国维、鲁迅所创始的生命美学思潮的根本缺憾,也因此而始终没有进入王国维、鲁迅之后的20世纪美学的视野。
显然,对于美学的追求事实上就是对于内在自由的追求。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不仅包括外在自由即自由的必然性,也包括内在自由即自由的超越性。科学与民主的实现(理性自决、意志自律),必须经由内心的自觉体认,必须得到充足的内在”支援意识”的支持。否则,一切自由都会因为失却了终极关怀和无所信仰,因为在价值世界中陷入了虚无的境地并为”匿名的权威”所摆布,而反而最不自由。康德之所以要从基督教的“信仰”中去提升出“自由”,着眼所在正在这里。进而言之,对于内在自由的追求,显然与对于信仰之维、爱之维的追求密切相关。爱唤醒了我们身上最温柔、最宽容、最善良、最纯洁、最灿烂、最坚强的部分,即使我们对于整个世界已经绝望,但是只要与爱同在,我们就有了继续活下去、存在下去的勇气,反之也是一样,正如英国诗人济慈的诗句所说:“世界是造就灵魂的峡谷”。一个好的世界,不是一个舒适的安乐窝,而是一个铸造爱心美魂的场所。实在无法设想,世上没有痛苦,竟会有爱;没有绝望,竟会有信仰。面对生命就是面对地狱,体验生命就是体验黑暗。正是由于生命的虚妄,才会有对于生命的挚爱。爱是人类在意识到自身有限性之后才会拥有的能力。洞悉了人是如何的可悲,如何的可怜,洞悉了自身的缺陷和悲剧意味,爱,才会油然而生。它着眼于一个绝对高于自身的存在,在没有出路中寻找出路。它不是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而是看清人性本身的有限,坚信通过自己有限的力量无法获救,从而为精神的沉沦呼告,为困窘的灵魂找寻出路,并且向人之外去寻找拯救。也正是因此,置身审美活动之中,我们会永远像没有受过伤害一样,敏捷地感受着生命中的阳光与温暖,欣喜、宁静地赞美着大地与生活,永远在消融苦难中用爱心去包裹苦难,在化解苦难中去体验做人的尊严与幸福。这,或许可以称之为:赞美地栖居(它幸运地被拣选出来作为信仰与爱所发生的处所)。因此审美活动不可能是什么“创造”、“反映”,而只能是“显现”,也只能被信仰之维、爱之维照亮。而且,信仰之维、爱之维已经先行存在于审美活动之外,审美活动仅仅是受命而吟,仅仅是一位传言的使者赫尔墨斯,是信仰之维、爱之维莅临于审美活动而不是相反,否则,审美活动就无异于西壬女妖的诱惑人的歌声。也因此,就审美活动而言,对于人类灵魂中的任何一点点美的东西、善良的东西、光明的东西,都要加以“赞美”(区别于时下美学的“歌颂”);对于人类灵魂中的所有恶的东西、黑暗的东西,也都要给予悲悯(区别于时下美学的“批判”)。而且,从更深的层面来看,悲悯也仍旧就是赞美!试想,一旦我们这样去爱、去审美,去在“罪恶”世界中把那些微弱的善、零碎的美积聚起来,去在承受痛苦、担当患难中唤醒人的尊严、喜悦,去在悲悯人类的荒谬存在中用爱心包裹世界,世界的灿烂、澄明又怎么不会降临?精神本身的得到拯救又怎么不会成为可能?
最后的结论显而易见,回首20世纪,惟有王国维、鲁迅所开创的生命美学思潮给人以深刻的启迪,进入新的世纪,惟有从王国维、鲁迅所开创的生命美学思潮“接着讲”,才是我们亟待面对的课题。而信仰之维、爱之维,则是我们能够超越王国维、鲁迅并且比他们走得更远的所在。
以上,就是我所关注的新世纪美学的一个思路,是否妥当,谨请方家与同行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