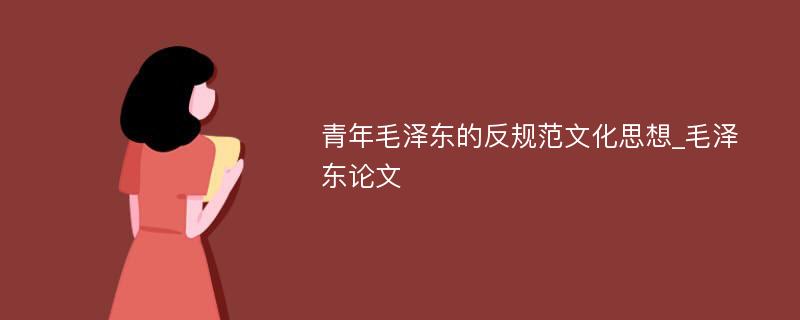
青年毛泽东的反规范文化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青年论文,文化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01)03-0016-03
所谓规范文化是指一个时代或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文化。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中国虽已有些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着统治地位。在这种社会基础上形成的传统文化,以“礼”为基本特征,以“三纲”、“五常”为行为规范。这种规范文化是封建性的,它束缚人的个性发展。毛泽东从小就有反对这种规范文化的倾向。
毛泽东八岁起就开始读私塾,但他喜欢阅读的不是四书五经,而是《岳飞传》、《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通俗小说。通过阅读和讲述,有一天,毛泽东“突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他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1](P109)毛泽东从那时候起就开始意识到传统社会中有权有势的人都是不参加劳动的。1910年,长沙发生饥民暴动,在这次事件中,许多贫民在与官府的冲突中丧生。毛泽东闻讯感到非常气愤。25年后他回忆至此,还非常激动地说:“大多数同学都同情造反的,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出发……我却始终忘不掉这件事。我觉得造反的人都是像我们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对于他们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1](P110-111)他的心与造反者息息相通。因此,他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1](P110)此外,在家中少年毛泽东还抵制父亲的家长专制,拒绝父母为他娶妻。在私塾,他曾以逃学方式抗议塾师对学生的体罚。
通过这些事件,毛泽东产生了对束缚个性发展的封建性规范文化的强烈反抗意识。待到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一师”)求学以后,随着知识的日积月累,思维能力的增强,他对封建性的政治文化、学校教育、伦理道德不但反感日甚,而且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作了相当广泛、深刻的批判。
一、青年毛泽东反规范政治文化思想
1910年秋,毛泽东进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此时,他借阅了两册《新民丛报》。在该报第4号《新民说》“论国家思想”第三段末,毛泽东批写道:“正式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2](P5)在这里,他明确指出,中国古代各朝代均是“盗窃得国”,而不是“人民推戴”产生和使人“心悦诚服”的。这种大胆抨击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思想是他全面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最初尝试。经过“一师”的学习与五四之后的一系列社会政治活动,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四千年来之政治皆空架子,大规模、大办法,结果外强中干,上实下虚,上冠冕堂皇,下无聊腐败。民国成立以来,名士伟人,大闹其宪法、国会、总统制、内阁制,结果只有愈闹愈糟。”[2](P488)毛泽东全面否定了直到“五四”的中国传统政治制度。
传统政治制度阻碍中国社会文化的进步和繁荣,使中国“愈闹愈糟”,传统政治观念也是如此。毛泽东认为,按照传统观念,政治、法律乃是“一个特殊阶级的事”,是穿了长褂子一类人的专门职业。[2](P519)但是,到了近代,这种观念已不合时宜。在湖南自治运动中,毛泽东向自命为规范文化代表的上层统治者反问道:“意英法美的劳动者,口口声声‘要取现政府而代之’,这些劳动者都是学过政治法律的吗?”[2](P519)特别是“大战而后,政治易位,法律改观。从前的政治法律,现在一点也不中用。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他们对于政治,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对于法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2](P519)在这里,毛泽东用欧美各国人民在战后造反的事实批驳传统的政治观念,讴歌了以工人、农民为主人的新政治。
二、青年毛泽东反规范教育文化思想
学校是传递知识与文化的渠道,也是统治阶级传播规范文化思想的基地。青年毛泽东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在“一师”的五年半,他一直坚持紧张的学习和锻炼。对学校的各种活动,他也积极参加。1915年11月至1917年10月,他担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友会”文牍,1917年11月至1918年5月改任“总务”。他对组织运动会、举办“夜学”也花费了很大精力。这些活动,体现毛泽东对学校教育的某种认同感。但另一方面,他对当时学校教育还流露过强烈的不满情绪,并进行过多方面的批判。
1.学校的规章制度束缚学生的个性自由
“一师”在当时还算一所比较开明的学校,但是,其校章中关于学生应遵守的秩序就有35条。而毛泽东认为“人类最可宝贵,最堪自乐的一点”就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最重要的是‘我’是‘个性’”。[2](P519)繁琐的规章压制人的言行自由,使人们的才能不能自由发展。1915年11月9日,毛泽东致函黎锦熙,表示他“性不好束缚”,但学校却使他感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摧落,以衰以逝,心中实在太悲伤……如此等学校,直下下之幽谷也。”[2](P369)因此,他决定“必欲弃去,就良图,立远志”。[2](P30-31)1918年从“一师”毕业以后,他为筹备赴法勤工俭学、计划工读“新村”和组织自修学社作了多方面的努力,但地并不想进正规学校。1920年6月7日,他甚至说“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进学校。自由研究,只要有规律有办法,未必全不可能。”[2](P47)
2.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不合理
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对当时学校的课程设置深表不满地说:“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顽固之身,犹莫能举,况未成年者乎?况弱者乎?观其意,教者若特设此繁重之课以困学生,蹂躏其身而残贼其生,有不受者则罚之”。[2](P67)课程负担重,质疑问难和自由思考的时间就少,他觉得自己“近年来所有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苟合谭论而专求之书,其陋莫甚。”[2](P13)因此,他一向主张精简课程,让学生多有时间进行自由研究。同时,对教学内容要及时更新。他说:“我们的国文先生那么顽固。满嘴里‘诗云’‘子曰’,清底都是一字不通。他们不知道现今已到了20世纪,还迫着我们行‘古礼’守‘古法’。一大堆古典式死尸式的旧文章,迫着向我们脑子里灌。”[2](P374)他主张教学要与实际生活密切结合,《讲堂录》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2](P587)这就是强调要从实践中学习。他在“一师”时主办“夜学”,离校后提倡半工半读和赴法勤工俭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矫正学校教育与实际生活脱节的偏向。在《夜学日志》中,他说:“更有进者,则现时学校之大弊,在与社会打成两橛,犹鸿沟之分东西。”[2](P97)在发起成立上海工读互助团时,他又说:“现在中国的学制,是求学的时代不能谋生活,学问就变成了形式的、机械的了;谋生活的时代不能求学,学问就是不永续的、不进步的了。”[2](P676)
3.师生关系不正常
由于教师习惯于压服而不是启发学生的思想,使学生们与教师无法进行平等的思想交流。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毛泽东代表学生们申诉:“我们好苦,教我们的先生们,待我们做寇仇,欺我们做奴隶,闭锁我们做囚犯。”当时学生们“眼睛花”、“脑筋昏”、“精血亏”、“贫血症”、“神经衰弱症”等症状的形成和“呆板”、“不活泼”特点的产生,“都是先生(们)迫着我们不许动不许声的原故。”[2](P374)他要求废除“压服”式的教学方式,增进师生之间的思想交流。
三、青年毛泽东反规范伦理文化思想
毛泽东在1917年下学期至1918年上学期,在研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时,写下了一万一千多字的“批注”,他对一切违背个性发展的伦理道德规范作了尖锐的批判。他说:“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在,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2](P151)“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它是中国封建规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规范将人们束缚在固定的尊卑等级秩序中,使人的个性无法得到自由发展。“教会”是西方伦理规范的代表。毛泽东将对“教会”的否定与对“资本家”和“君主”、“国家”的否定联结在一起,表明他对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基础与上层建筑(包括伦理道德)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五四运动之后,毛泽东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分析更具体、批判更深入了。在1919年7月14日所发表的《什么是民国所宜》中,毛泽东针对康有为反对拆毁明伦堂所讲的“强要拆毁,非民国所宜”,反问道:“难道一定要留着那‘君为臣纲’、‘君君臣臣’的事,才算是‘民国所宜’吗?”[2](P327)
在《健学会之成立及其进行》一文中,毛泽东批判了“道统”、“孔子”。他说:“中国什么‘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乎做两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2](P368)毛泽东在这里特别强调,孔子是中国传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规范文化的代表,批判他就是对占统治地位的传统规范文化的反叛。对于婚姻问题上的伦理规范,毛泽东则利用评论“赵五贞女士自杀”的机会,接连写10篇文章揭露中国传统婚姻的罪恶,批判了“男尊女卑”、“男女授受不亲”以及“贞节观念”等等。综上所述,毛泽东早在青少年时期就对规范文化的各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分析、批判,形成了较系统、全面的反规范文化思想。毛泽东从现实斗争的需要出发,继承传统俗文化的反抗精神,吸取西方文化的积极因素,形成了既富个性特征又反映时代要求的文化思想。五四运动期间,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对传统规范文化作了总结性的批判,他说:“原来的中华民族,从几千年来,都是干着奴隶的生活,只有一个非奴隶的是‘皇帝’。(或曰皇帝也是‘天’的奴隶)。皇帝当家的时候,是不准我们练习能力的。政治、学术、社会,等等,都是不准我们有思想,有组织,有练习的。”[2](P393)“于今却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2](P393)他要求彻底批判封建文化,热切呼唤中国人民从“思想”到“政治”,从婚姻到“教育”都从封建专制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盼望着新型的大众文化的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