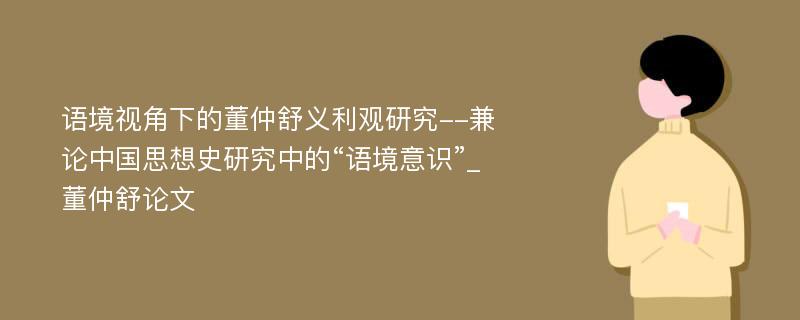
从语境看董仲舒义利观的一段学案——兼论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语境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董仲舒论文,义利论文,中国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代董仲舒有一句众所周知的话:“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句话一般理解为要求人们只讲道德礼法,安贫乐道,不讲谋取经济利益。宋儒程颢对此有很高的评价:“董仲舒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诸子。”(《遗书》卷二五)其后成为儒家义利思想的一个重要命题。朱熹、吕祖谦称其“可以为(儒者)法矣”。(《近思录·为学大要》)后世的批评者们也从这个角度理解。如叶适说:“‘正义不谋利,明道不计功’,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习学记言·汉书》)颜元也有批评:“问董子正谊明道二句,似即谋道不谋食之旨,先生不取。何也?曰:……全不谋利计功,是空寂,是腐儒。”(《颜习斋先生言行录·教集门第十四》)但是,从原典考据上看,上述褒扬与批评都是误解,因为董仲舒这句话并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陈述,而是他的自我表白以及对君王的规劝,出自他在险恶环境中的自我保护。本文拟从语境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考证,以澄清长期以来的误解,并就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语境意识”作一探讨。
我们先来看“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原文出处。《汉书·董仲舒传》和《春秋繁露》对此分别都有记载,内容相近,但文字上还是有些差别。为了体现其整体语境,特将其完整摘录:
王问仲舒曰:“粤王勾践与大夫泄庸、种、蠡谋伐吴,遂灭之。孔子称殷有三仁,寡人亦以为粤有三仁。桓公决疑于管仲,寡人决疑于君。”仲舒对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对。闻昔者鲁君问柳下惠:‘吾欲伐齐,何如?’柳下惠曰:‘不可。’归而有忧色,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为至于我哉!’徒见问耳,且犹羞之,况设诈以伐吴乎?由此言之,粤本无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苟为诈而已,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也。五伯比于他诸侯为贤,其比三王,犹武夫(指一种石头——引注)之与美玉也。”王曰:“善。”(《汉书·董仲舒传第二十六》)
命令相曰:“大夫蠡、大夫种、大夫庸、大夫睪、大夫车成,越王与此五大夫谋伐吴,遂灭之,雪会稽之耻,卒为霸主,范蠡去之,种死之。寡人以此二大夫者为皆贤。孔子曰:‘殷有三仁。’今以越王之贤,与蠡种之能,此三人者,寡人亦以为越有三仁,其于君何如?桓公决疑于管仲,寡人决疑于君。”仲舒伏地再拜,对曰:“仲舒智褊而学浅,不足以决之,虽然,王有问于臣,臣不敢不悉以对,礼也。臣仲舒闻:昔者,鲁君问于柳下惠曰:‘我欲攻齐,何如?’柳下惠对曰:‘不可。’退而有忧色,曰:‘吾闻之也:谋伐国者,不问于仁人也,此何为至于我?’但见问而尚羞之,而况乃与为诈以伐吴乎!其不宜明矣。以此观之,越本无一仁,而安得三仁!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致无为而习俗大化,可谓仁圣矣,三王是也;春秋之义,贵信而贱诈,诈人而胜之,虽有功,君子弗为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童子言羞称五伯,为其诈以成功,苟为而已也,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五伯者比于他诸侯为贤者,比于仁贤,何贤之有?譬犹武夫之比于美玉也。臣仲舒伏地再拜以闻。”(《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第三十二》)
后世校注者大都以为《春秋繁露》里的记载是从《汉书》中抄来的。不难发现,上面两句话在文字表述上有一些差别:《汉书》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春秋繁露》为“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张岱年先生认为:“此二记载不同,必有一误。……疑《春秋繁露》所载,乃董子原语,而《汉书》所记,乃经班固修润者。”(张岱年,第392-393页)但笔者认为:《汉书》和《春秋繁露》的记载都没有错,因为这两段话虽然都是董仲舒所言,但说话对象却不是同一个人。《汉书》里记载的话,是董仲舒对汉“江都王”说的;《春秋繁露》里的话,却是他后来对汉“胶西王”说的。前者是在武帝元年至二年间(公元前140年左右),后者是在元狩三年(公元前122年)。①时间上前后相差18年,且估计《春秋繁露》是在董仲舒退出政界以后写的,所以《春秋繁露》上的这段话,其记载的时间可能还要晚一些。
之所以说两者的记载都没有错,还因为这两句话中,问者问的虽然都是同一个问题,但董仲舒的回答却有微妙的差别,这个差别体现出了当时语境的不同。
《汉书》上的记载是董仲舒与汉武帝之兄、江都王刘非的对话。董仲舒时任刘非的丞相。据《汉书》记载:“吴、楚反时,非年十五,有材气,上书自请击吴。景帝赐非将军印,击吴。吴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吴国,以军功赐天子旗。……非好气力,治宫馆,招四方豪杰,骄奢甚。”(《汉书·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也就是说,刘非属于那种能力不错、自视甚高、有着强烈的建功立业愿望的人。此时的董仲舒正是年富力强,刚上完“天人对策”,大受皇帝及群臣们的欣赏,而刘非身居财源富庶之“吴地”(今江浙一带),自己的身体气力都处于鼎盛时期,正想大干一番,因此对董仲舒也抱着“贤臣辅助明君”的期望。所以,刘非就向董仲舒提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表面上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即越国那三个辅助勾践的大夫是否称得上仁者,实际上刘非是想借助古人来问董仲舒:你能否帮助我,像范蠡帮助勾践、管仲帮助齐桓公那样,成就我的一番事业呢?
刘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危险,董仲舒很难回答,唯恐在这个问题上犯忌。在封建社会里,皇兄的位置是最接近皇帝宝座的,所以皇帝最提防的就是他的兄弟。尤其是在西汉经历了吴楚等王之乱后,汉武帝刘彻派董仲舒到刘非身边,目的并不是要帮助刘非成就一番“霸业”,而是希望董仲舒运用他的知识与智慧,让刘非明白一些做臣子的道理,压一下他的骄奢之气,顺便也是对董仲舒的考察。董仲舒对此心里自然非常清楚,所以,他到刘非身边后,一直“以礼谊匡正,王敬重焉”(《汉书·董仲舒传第二十六》)。董仲舒对刘非这个问题不可能给予肯定的回答,因为刘非这样问的时候有个前提:他自比齐桓公,说如同齐桓公信赖管仲那样,我也信赖你的回答。董仲舒如果回答说:“那三个人确实是仁者”,就等于是站在了“管仲”的地位,等于承认自己作为“仁者”(董仲舒当然不能说自己不是仁者或者说不想做仁者)也要帮助刘非建立霸业。这种话如果传出去,有谋反的嫌疑,弄不好是要杀头的。但是,董仲舒也不能直接否定刘非的问题。因为刘非建功心切,对董仲舒期望值很高,可能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危险性。所以如果直接戳穿刘非的用心,作出否定的回答,比如坦言:“我不是管仲,你也做不了齐桓公”,那也会惹怒刘非,招致杀身之祸。
董仲舒不愧是大儒,他很巧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首先他就自谦“愚”,回答不了这样的大问题(“臣愚不足以奉大对”),然后就用柳下惠的例子说明仁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个回答,表面上是否定了五伯为“仁者”,实际上是表白自己不过问建功立业、政治权术一类的事。因为董仲舒对仁是这样看的:“何谓仁?仁者,憯怛爱人,谨翕不争,好恶敦伦,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嫉妒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诐之事,无辟违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气和,其欲节,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无争也,如此者,谓之仁。”(《春秋繁露·必仁且智第三十》)意思是说,仁者的心中有爱,不会用手段,不伤害人也不嫉妒人,与世无争,心气平和。
但是我们要注意,董仲舒的这些说法已经有点偏离了孔子儒学的轨道。因为孔孟虽然强调仁义为先,却并不否定儒者从政。而且只要从政能给国家和百姓带来好处,儒家也并不排斥用一些违反“礼”(即不仁)的手段。典型的例子就是:孔子曾批评管仲违反“礼”:“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但由于管仲辅助齐桓公治国有方,百姓受其好处,所以孔子仍然称赞他:“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众所周知,孔子很少许人为“仁”,由此可见孔子对管仲评价之高。因此刘非说越国有“三仁”并非全无儒学根据。而且孔子心目中的仁者是爱憎分明的:“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相比之下,前引董仲舒对仁之“平易和理而无争”的理解,其实已经有点儒学中“乡愿”的意思。另外,董仲舒以柳下惠作为“仁者”之例也是不妥当的,原因是孔子对柳下惠的评价并不高,并不曾许他为仁,只是说他言行中规中矩,还算可以(“柳下惠……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论语·微子》])
作为大儒的董仲舒当然不会不知道自己的说法已经偏离了孔子,那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这就是因为他要借此声明自己不过问“霸业”的事,他说仁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实际上是告诉刘非:我们这些人只会讲仁义,只会做学问,不会用计策手段,不过问那些攻克杀伐的事情。所以你要富国强兵,还是找其他人去吧。可见,这里的“利”并非指经济利益,而是特指刘非的“霸业”。当然,这也是说给那些潜在的政敌们听的。因此,这句话是在当时环境下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措施。对此,我们要注意其中的细节:董仲舒在这里说“正其谊(义)不谋利”,是提醒刘非注意“反思自我”。因为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对“义”之作用有个独特的看法:义是用来“正我”的,具体地说就是“反理以正身,据礼以劝福”(《春秋繁露·仁义法第二十九》)。董仲舒在这里要刘非“据礼反思”的是“君臣关系”:因为儒家“五伦”其中一条就是“君臣有义”,董仲舒在这里讲“义”,一方面是暗示自己是出于“君臣关系”才回答刘非这个不太妥当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间接地提醒刘非,不要忘了你自己对汉武帝也有个“君臣关系”。而且这里用“谊”代替“义”也堪称巧妙,因为虽然古语“谊”“义”相通,但儒家以义利、仁义对举的时候都只用“义”,董仲舒这里用“谊”来通“义”,是强调“适宜”的意思,也就是暗示刘非应考虑这个问题本身是不是妥当。估计刘非正是因为懂得了董仲舒的用意,想到了这点,才不再进行探讨,而只是简单地说:“善”。
《汉书》此处寥寥数语,既写出了董仲舒的沉着与智慧,也写出了刘非的心机志向与从善如流。由此也可见班固史书“一字褒贬”之厉害。
事隔18年之后,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记载的“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一段,虽然问题相同,所回答的内容也差不多,但其语境大不相同。不同在哪里?就是胶西王刘端这个人与江都王刘非大不相同。据《汉书》记载:胶西王此人也是汉武帝之兄,但性情恣纵,为所欲为,有着病态的阴险心理,喜欢残害官吏,引起朝中王公大臣的公愤,一致请求汉武帝诛灭了他;只是汉武帝于心不忍,所以此人就更加肆无忌惮。此人尤其喜欢残害自己手下享受二千石俸禄的大官,设计陷害,杀了不少官吏。“相二千石至者,奉汉法以治,端辄求其罪告之,亡罪者诈药杀之。所以设诈究变,强足以距(拒)谏,知足以饰非。相二千石从王治,则汉绳以法。故胶西小国,而所杀伤二千石甚众。”(《汉书·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再到后来,由于胶西王倒行逆施所引起的公愤实在太大,汉武帝不得不同意众人的请求,“削其国,去太半”。胶西王由此干脆破罐子破摔,租税不收,财物不管,封了宫门,自己化装成一介平民,到处乱窜:“端心愠,遂为无訾省。府库坏漏,尽腐财物,以巨万计,终不得收徙。令吏毋得收租赋。端皆去卫,封其宫门,从一门出入。数变名姓,为布衣,之它国。”(同上)一个好端端的封地被他弄得不成样子,所以到后来,都没有人敢去他那儿任职了。
此时的董仲舒由于学问渊博又为人廉直,遭朝中高官公孙弘嫉恨,被差遣到胶西王处任相(参见《汉书·董仲舒传第二十六》),实际上是想借刀杀人。好在胶西王在这件事情上头脑还算清醒:“胶西王闻仲舒大儒,善待之。”(同上)《史记》上也说:“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史记·儒林列传第六十一》)再加上董仲舒担心在那儿招致不测,不久便称病去职,公孙弘的阴谋才没有得逞。
这里我们首先就遇到一个问题:胶西王怎么会问了一个跟江都王当年同样的问题呢?笔者认为这里有疏漏,理由在于:其一,胶西王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因为一般地说来,相隔18年的两个人对董仲舒提出同样的问题,本身的可能性就不大。另外,像胶西王这样一个声名狼藉、心理变态、为人卑劣的人,也不大会向董仲舒提这样的问题。理由很简单:他没有跟江都王同样的意向。他如果真的有建立霸业的志向,就会像江都王那样励精图治,广招四方豪杰,而不会把自己的封地搞得乱七八糟,也不会残害官吏。其二,因此,《春秋繁露》可能本身传抄有误:可能漏了前面一段。因为这篇对话的开头“命令相曰”实在有点莫明其妙。《春秋繁露》的第一个校注者、清代的卢文弨注云:“‘命令’疑是‘令问’。”(苏兴,第266页)但“令问”也是莫明其妙。因为“令”并不能指胶西王。所以,这里谁发问、问谁、为什么问,都不清楚。这样的开头不符合董仲舒《春秋繁露》全书一贯严谨的风格。纵观《春秋繁露》全书各篇,都是文字结构严谨,表述清楚,其中的对话篇也不少,但都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对话的人物交代得很清楚。只有这篇,不但篇幅特别短,而且整个事情也没有交代清楚,与其它篇章很不相应。所以笔者认为可能有些内容漏掉了。由于董仲舒的著作一直没有受到重视,文篇散佚,直到清代才有人去抄写整理(参见同上,“点校说明”),此篇开头可能漏掉了这样一段:胶西王问起董仲舒以前跟江都王的事情,董仲舒就对他重复了一遍以前自己对江都王的回答。
由于语境不同、对象不同,所以董仲舒对这段话作了一些微妙的调整:《汉书》里的回答重点是自我表白,同时也是希望江都王做一个“贤臣”;但《春秋繁露》里的回答“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致无为而习俗大化,可谓仁圣矣,三王是也”,已经没有自我表白的成份,仅仅是借对江都王的对话表达对胶西王的希望,并且不是希望他做贤臣,而是希望他做一个“明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董仲舒可以自称为“仁人”、“仁者”,但他无论如何不敢自称为“仁圣”。按照孔子的说法,作为“圣”,就要“博施而济众”,这是做人的最高境界,连尧和舜都未必能达到:“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董仲舒如何敢自称!所以这段话不可能是董仲舒的自我表白。而且,“仁者”与“仁圣”这两种人,不仅身份境界不同,要做的事情也不同:“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但“仁圣”却要“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致无为而习俗大化”。
我们要注意:两段话里的“正其道”与“正其谊(义)”、“修其理不急其功”与“明其道不计其功”,虽然只差一两个字,意义却相差很大。“正”在这里是动词,是“纠正”,也就是后面那个“修”的意思,“正义”是儒者(仁人者)应当做的事情。孔子说:从政的第一件事就是:“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孔子的“名”就是尊卑之“礼”,“正名”就是把已经被弄乱了的等级秩序重新弄回去,也就是董仲舒这里的“正其谊(义)”的意思。所以,董仲舒“仁人者正其谊(义)不谋其利”这个说法,是合乎臣子的身份的。但是“正其道不谋其利”就不一样了:儒家从来没有要求儒者去“正道”,因为“道”是至高无上的,儒者可以了解它(闻道、明道)、学习它(学道)、宣扬它(弘道)、实行它(行道、遵道),但是不能去纠正它。因为“正其道”(这里的“道”是指国家的发展道路)要根据“天理”来进行,一般的儒者没有这个能力,也不具备这样做的条件。只有“仁圣”可以这样做。诚如《春秋繁露》所言:“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虽有巧手,弗修规矩,不能正方圆;虽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虽有知心,不览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则先王之遗道,亦天下之规矩六律已!故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也;所闻天下无二道,故圣人异治同理也,古今通达,故先贤传其法于后世也。”(《春秋繁露·楚庄王第一》)意思就是说只有仁圣才可以以正道而得天下。“修其理……致无为而习俗大化”也是一样,跟“正其道”的意思基本一致,也是指圣人才可以做的事:“圣人所欲说,在于说仁义而理之,知其分科条别,贯所附,明其义之所审,勿使嫌疑,是乃圣人所贵而已矣。”(《春秋繁露·重政第十三》)所以这里的“正其道不谋其利”中的“利”既非刘非的那个“霸业”,也非经济利益,而是特指胶西王的个人修为,意在劝他安心治理国家,不要乱来,如此“可谓仁圣”。他又劝胶西王: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太着急,不要急于求成,顺其自然,时间长了自然会成功:“修其理不急其功,致无为而习俗大化,可谓仁圣矣。”
这些话董仲舒对江都王都没有说过;他之所以要把以前的话改过来,对胶西王这样说,就是希望胶西王能改正自己的错误做法,希望他能成为一个老百姓和儒者心中的“仁圣”,至少把自己的领地治理好。而且,董仲舒这样说也不会有以前对江都王说话时的顾忌:这些话不能对江都王说,但可以对胶西王说,因为胶西王的名声实在太臭,所以即使董仲舒说的这些话传出去,朝廷也决不会认为董仲舒是鼓动胶西王“谋逆”,而只会认为是在规劝他。另外,董仲舒之所以把对胶西王的这些话记在《春秋繁露》里,而没有记他与江都王的对话,大概也是希望这些话能对后来的君王们有点启发教育作用。
只是董仲舒怎么也不会想到,后世会把他的这些话当作不管经济利益、“安贫乐道”的思想来理解。其实,对于这种理解,除了仔细考证之外,凭逻辑推理也能看出里面的破绽:当时董仲舒身为丞相,主管全领地的经济,怎么可能说出不讲经济利益这样的“腐儒之语”呢?张岱年先生在引用这些话时,曾经很正确地指出,从董仲舒的思想整体来看,他并不是主张“取义弃利”,而是主张“公利”、“兼利”、“爱利天下”的:“董子之意,乃重公利而轻私利。人当以‘为天下兴利’为务,而不当谋个人或少数人之私利。”(张岱年,第393页)但由于他没有回归到董仲舒当时的语境,所以仍然没有能够弄清楚“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和“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的原意以及它们之间的不同,而只能归咎于“史官修润”。
由董仲舒的这段学案,可以引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语境意识”问题。
“语境原则”(context principle)就是认为“语境”决定言语的“意义”,它是弗雷格提出的,属于现代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在弗雷格那里,语境原则还仅限于理论体系或者文本本身;到后来,随着日常语言学派语言“用法论”的兴起,“语境原则”扩大到语言的使用环境和对象,即把语言和其使用的环境与对象看成一个整体,语言的意义就在这个整体的使用环境中。罗素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就主张,所谓懂得一个词的意义,就是会在恰当的条件下使用它,以及在听到这个词时作出恰当的反应。(参见徐友渔,第82页)这就是说语言的用法不同决定了其意义的不同。他后来又认为语句可以分为陈述句和祈使句,它们的意义是不同的。在陈述句中,词的意义相当于一个事物或环境的一个特征,词的出现引起关于该事物或环境的思想;而在祈使句中,人们听到它,话语引起人们的身体行动,就算懂得了它的意义。(罗素,第85-86页)后来,维特根斯坦明确提出了语言意义的用法论:“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维特根斯坦,第31页)塞尔认为,语言的使用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传统记述式话语。说话者与所陈述的对象(人、物或事态)构成一个语境,即把话语看作是对所陈述的对象的“反映”。另一类是完成行为式话语。话语与其所要交流和说服的对象(个人或人群共同体)构成一个语境。话语不是用来描述对象,而是用来完成某种行为,分为“以言行事”和“以言取效”。这两个语境中的话语的功用及其意义是不一样的。(参见徐友渔,第2章;塞尔,附录“什么是言语行为?”)
语言哲学的上述语境思想,对我们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一直忽略了这个问题。张岱年先生曾指出,中国传统哲学是重人生而不重知识,由此形成的区别于西方哲学的一个特点就是“合知行”:“中国哲人研究宇宙人生的大问题,常从生活实践出发,以反省自己的身心实践为入手处;最后又归于实践,将理论在实践上加以验证。”“要之,中国哲学乃以生活实践为基础,为归宿。行是知之始,亦是知之终。研究的目的在行,研究的方法亦在行。”(张岱年,第5、6页)这个说法实际上讲的就是中西方哲学的语境不同的问题。传统西方哲学的语境是塞尔所说的第一类“传统记述式话语”语境。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西方哲学就有了一个“只为自己而存在”的“自由”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中,其语言观是指称论的,即认为判定语言有效性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它是否能摆脱主观性去描述客观对象;用分析哲学家艾耶尔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是否并且在何种程度上有可能不依赖事物与我们的关系而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描述事物。”(艾耶尔,第7页)而中国的思想家们,尤其是儒家学者们,往往处于塞尔所说的第二类“完成行为式话语”语境。他们基本上没有西方传统学术那种“为知识而知识”的观念,他们都是很自觉地使自己的思想切合社会需要,服务于社会和大众。因此他们重体悟而不重论证,重效用而不重逻辑。其思想大多不是从一个起点建构的逻辑严密的体系,而是在生活实践中,在与他人的对话的互动中逐步形成的(在这一点上可能道家老子是个例外);其语言不是用来描述经验对象,也不是进行逻辑演绎,而是根据其交谈对象“随处点化”,用来完成“以言取效”,即对受话人发生一些作用。许多时候,中国思想家的语言看起来好象是“陈述句”,是对一个事物的反映述说,实际上它是罗素说的“祈使句”,即希望能影响受话方。典型的例子就是孔子关于鬼神和生死问题的思想观点。
众所周知,孔子“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对鬼神、生死的问题等都避而不谈。为什么会这样?研究者们往往从知识论的语境出发,认为孔子从经验论立场出发,对搞不清楚的事物不妄发言论。但实际上孔子这样做,很可能是从效用的角度考虑,只是他不愿意明说。《说苑·辨物》载:“子贡问孔子:‘死人有知无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也;欲言无知,恐不孝子孙弃不葬也。赐欲知死人有知将无知也,死徐自知之,犹未晚也。’”意思是说,我如果说死人有知,怕孝子们重死不重生;如果说死人无知,又怕不孝子们连父母死了都不葬。此话可作为孔子语言“效用论”的一个例证。再比如,孔子在《论语》中说“仁”,往往针对不同的说话对象的特点:子路勇猛,孔子就说“仁”是迟缓,不能听到了就去做;冉求迟缓,孔子就说“仁”是听到了要马上去做;司马牛急躁,孔子就说“仁”是语言迟缓;樊迟好稼,孔子就说“仁”是付出努力然后有收获,等等。②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学生,而不是为了形成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没有去考虑这些论述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结果导致直至今日,人们仍然对孔子关于“仁”是否有过具有普遍性的定义莫衷一是。至于本文所述的董仲舒为了在险恶的环境中生存下去,不惜违反传统儒家经典,而对“仁”、“义”、“利”等重新定义,更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其实董仲舒未必就是他自诩的那种只讲仁义的“纯儒”,《董子年表》记载他曾劝汉武帝杀骨肉大臣,此举使后人洪迈惊其为“与(董)平生学术大为乖剌”。苏兴注云:“仲舒此书,因时之论……仲舒学术尚仁,而有时主刑,所以为大儒也。洪论失之。”
但是,由于中国儒家的经学传统,后来的思想家们阐述自己思想的时候,往往要引证前人的话语作为根据,如此一来,就不得不把前人的话语从他们的语境中抽出来,放到自己的话语体系和对象当中,这就置换了语境。董仲舒的那句话首先就是被程颢如此引用,才出现了后人的误解。这种情况在近代“西学东渐”以后变得尤为严重。为了证明中国思想家们的思想也与西方哲学一样有严密的逻辑性,为了证明中国也有西方式的哲学,中国思想家们的言论被从原先的语境中分割出来,硬塞进西方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社会历史观”几大块中,被人为地纳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等对立之中。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思想家们特有的语境,从而其语言的意义也被扭曲,甚至完全走到了反面。
本文对董仲舒“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研究,虽然只是个案,但也可以说明上述问题。
注释:
①见《董子年表》,载《春秋繁露义证》(苏兴)。另见“百度百科”关于董仲舒的词条,称其“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任江都易王刘非国相;元朔四年(前125年),任胶西王刘端国相”,但笔者对照《董子年表》,认为此言恐有误,故不采。
②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论语·颜渊》)(樊迟)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雍也》)
标签:董仲舒论文; 儒家论文; 春秋繁露论文; 义利观论文; 汉朝论文; 管仲论文; 国学论文; 汉书论文; 孔子论文; 西汉论文; 西王论文; 江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