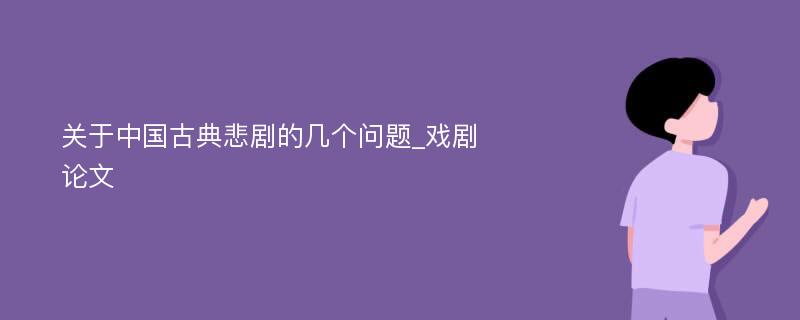
关于中国古典悲剧的几点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点论文,中国古典论文,悲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悲喜交错”是中外戏剧史上共有的现象,也是中国传统戏曲固有的表现方法,“团圆之趣”并非中国悲剧的民族特征的体现;判定一个剧作是悲剧、喜剧还是悲喜剧,主要应从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来着眼,而不是根据思想内容。
关键词:悲剧 悲喜剧 悲喜交错
一、关于“悲喜交错”和“团圆之趣”
中国古典悲剧除一部分是一悲到底外,大多数采用“悲喜交错”的结构方法。如有一类是在悲苦灾难之中,夹杂喜剧性的、甚至闹剧式的小插曲,以乐衬悲。再一类是悲喜交错,层层递进,使故事情节曲折变化,跌宕起伏,波澜叠起。还有一类是悲与喜、苦与乐大起大落,形成强烈的对比。
有的研究者据此认为这种“悲喜交错”的结构方法,是区别于西方悲剧的民族特色。事实果真是如此吗?我们翻开西方戏剧发展史,可以看到西方悲剧的表现形式和理论观念并非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变化的。例如希腊悲剧与希腊喜剧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较严格的界线,而悲剧诗人不写喜剧,喜剧诗人也不写悲剧。但是,正如罗念生先生说的:“‘悲剧’这个词应用到古希腊戏剧上,可能引人误解,因为古希腊悲剧着意在严肃,而不着意在悲。”(《论古希腊戏剧》)它所描写的内容不全都是流血和死亡。像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亚》第三部《报仇神》不再出现凶手,而是以和解告终。他的《普罗米修斯》第一部写普罗米修斯被囚禁在高加索山峭壁上,受雷鸣电火和打入地狱的折磨,第二部中宙斯主动同他和解,第三部与《报仇神》一样,表现雅典人民高举火炬游行,场面宏伟壮观。按照今天戏剧类型的观念,与其说是悲剧,不如当成正剧,似乎更确切些。
至于悲喜相混,在希腊悲剧中也不是绝对没有。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为加强戏剧效果,在悲惨事件发生之前,利用第三合唱歌,先制造一点轻快欢乐的小气氛,紧接着在第四场中,把悲剧推向高潮。希腊悲剧到了欧里庇得斯手里,又有新的突破,他的不少剧本,把悲剧性和喜剧性结合起来,《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即是写姐弟悲欢离合、圆满收场的故事,这种新型悲剧实际上已属于悲喜剧范畴。
古典主义戏剧家把悲与喜完全对立起来,自古罗马的贺拉斯,经过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传到十七世纪的法国达到顶端,制订出悲与喜绝对不能混合的清规戒律。尽管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古典主义理论和创作,但仍有不少作家冲破古典主义的教条,创作出新的戏剧类型——悲喜剧。莎士比亚更将喜剧性因素大胆引入悲剧之中,同时代的西班牙著名剧作家维加在他的悲剧《塞维利亚之星》里,也是悲喜相间的。
彻底、完全打碎悲喜不相容的枷锁则是启蒙主义的平民戏剧,狄德罗、莱辛、博马舍等大力倡导介乎英雄悲剧和轻快喜剧之间的第三种戏剧,称之为“严肃喜剧”或“家庭悲剧”的正剧。受启蒙运动影响而掀起的浪漫主义思潮像狂涛一般淹没了古典主义。在德国,歌德和席勒等,崇尚自然,注重戏剧性,他们的悲剧有不少是悲喜交错,以喜衬悲的。法国的雨果,他的悲剧吸收了奇情剧的特点,如《欧那尼》,悲与喜的转换变幻莫测,忽而转危为安,忽而出生入死,大喜大悲,充满激情。此后,从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不论是批判现实主义,还是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甚至荒诞派的戏剧作品,他们的悲剧作品莫不插入喜剧性因素。意大利的皮蓝德娄两部悲剧《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和《亨利第四》中,作者大胆地运用了即兴喜剧、假面剧、戏中串戏等手段,与传统的悲剧形式相结合,嬉笑怒骂,诡奇独特,犀利有力地揭穿了资本主义社会凶残虚伪、卑鄙阴险的本质特征。而俄国的契诃夫,他的戏剧像小说一样,善于将悲与喜共存在同一的时空里,交织成一个整体的两个侧面。别林斯基以现实为依据,认为“整个人类生活就是英雄、恶汉、平常人物、渺小家伙和愚人彼此间的冲突和相互作用而构成的。”所以,“悲剧包含戏剧诗的全部实质,包括着它的一切因素,因而喜剧的因素也有充分根据容纳在内。”(《戏剧诗》)
还必须指出,“悲喜交错”并非悲剧一家独有,而是我国传统戏曲共有的表现方法。众所周知,元杂剧篇幅短,从现有的作品来看,悲剧中一悲到底的倒比悲喜交错的悲剧多一点,而喜剧中悲喜交错的,要比一喜到底的要多。南戏与传奇的篇幅长,适宜表现曲折复杂情节、文武冷热相剂的场面,通过新奇变幻的故事,“极摹人情世态之岐,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剧作家们按生活中悲喜混合的原貌呈现人生,“悲欢沓见,离合环生。”(袁于令《焚香记序》)使观众看后,收到“快者掀髯,愤者扼腕,悲者掩泣,羡者色飞。”(臧懋循《元曲选序二》)的效果,所以,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几乎都是悲喜交错的,何况还有名符其实的悲喜交错的悲喜剧,它们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
古典悲剧不仅在结构布局上注意苦乐相间,而且在结尾处理上常常带有一个“光明尾巴”,或出现“亮色”,即是在主人公遭受苦难或毁灭之后,用浪漫主义的手法,给人以希望和安慰,表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其中有的采用鬼神或其他正面人物复仇斗争,皇帝清官为民伸冤雪恨,使恶人得到应有的惩罚,有的则通过幻想、象征方式,让男女主人公化蝶、成仙。当然,也有少数悲剧,主人公最后遁入空门,或处于哀怨悲苦的氛围之中。有的学者将“光明尾巴”称之为“团圆之趣”,还引用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的一段话,说明这正是中国悲剧的民族特征的体现。
“团圆之趣”的说法,出于李渔《闲情偶寄·格局第六》。他认为剧作家在处理最后结局时,不仅要“自然而然,水到渠成”,而且应在“山穷水尽之处,偏宜突起波澜,或先惊后喜,或始疑而终信,或喜极信极而反致惊疑,务使一折之中,七情俱备,始为到底不懈之笔。”也就是说要有“团圆之趣”。李渔这里是指一般戏曲创作的结构技巧,要求剧本的结尾,虽是大团圆套子,但仍应曲折有致,生动有趣,不要一览无余,索然乏味。李渔所言,并非专指悲剧。
再看王国维的一段话:“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困者终于亨。”是不是如某些评论家所云,它阐明了我国悲剧形式的特征,王国维没有明说。但从他所举的《南桃花扇》、《红楼复梦》等例子,可知是指一般古典小说、戏曲的“大团圆”俗套。在王国维看来,中国的戏曲中最缺乏的是悲剧,《宋元戏曲考》云:“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但“元则有悲剧”,例如《汉宫秋》、《梧桐雨》、《西蜀梦》、《火烧介子推》、《张千替杀妻》等,“初无所谓先离后合,始困终亨之事也。”特别是《窦娥冤》、《赵氏孤儿》“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王氏的悲剧观是本于叔本华“厌世解脱”的悲观主义理论,有其局限与缺陷,但他把始悲终欢、始困终享的“大团圆”排斥在悲剧之外,仍是正确的。
二、悲剧、喜剧与悲喜剧辨析
由于悲喜交错是中国古典戏曲的传统表现手法,我们在辨析哪一种剧目是属于悲剧时,要细心谨慎,以免混淆不清,把悲喜剧和喜剧也归入于悲剧的行列。
首先,需要分清剧本总的风格情调、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下面,试举三个不同类型样式的爱情剧作一简要的分析比较:先看《西厢记》,作者笔下的张生是个喜剧人物,他迂酸而又志诚,他对莺莺的爱情如痴如醉,风魔般执着地追求,但一遇困难又束手无策,不是病倒就是要上吊,红娘讥讽他是“傻角”,是“银样蜡枪头”。莺莺在开场时虽然充满了郁闷和哀愁,但随着剧情的进展,逐渐显露出她的喜剧性格:她端庄而娇慵,凝重而会“做假”,以致与张生、红娘演出了一系列生动风趣的喜剧性冲突来。红娘勇敢、机智,善于调侃,犀利而泼辣。《拷红》一折,她的反守为攻的一番大道理,说得老夫人哑口无言,使崔张的爱情获得胜利。尽管穿插有“长亭送别”、“草桥惊梦”凄凉幽怨的悲剧性场景,但无法掩盖住全剧明快、诙谐、轻松、幽默的格调。再看汤显祖的《牡丹亭》,杜丽娘比崔莺莺有更多的悲剧色彩,春天唤醒了朦胧中的爱情,她渴望自由和解放,现实中没有,便到梦中去追求;寻梦而不得,觉醒后更加痛苦,就抑郁而死。但她对人生和理想的追求,一往而情深,便战胜了死神,死而复生。这种生生死死的光怪陆离的奇遇,既有着凄艳欲绝的悲剧色彩,又富于欢愉乐观的喜剧风味。因而它应该归属于悲喜剧。至于孟称舜的《娇红记》,全剧自始至终笼罩在悲剧的氛围之中,其间虽有喜剧性欢乐场面,甚至是闹剧性的插曲,但它不是为了淡化悲剧气氛,而是起着烘托、对比和强化的作用,迂回曲折地将矛盾推向高潮。王娇娘曾坚贞不屈地对抗买卖婚姻,寻求“死共穴,生同舍”的同心子。但美好的愿望在严酷的封建礼教高压下幻灭了,最后只能自怨自艾,归咎于命穷,与申纯双双殉情,以求解脱。
其次,要着眼于剧本的戏剧冲突和总体结构。例如:李玉的《清忠谱》和无名氏的《鸣凤记》,两剧同是以忠奸斗争为题材,表面上似乎都符合“喜→悲→喜→悲→大悲→小喜”的公式。但如果进一步考察,就可以看出其结构上的差异了。《清忠谱》描写周顺昌冤狱事件,主线表现周顺昌与魏忠贤阉党的斗争,副线是以颜佩韦等为代表的苏州市民群众掀起援救周顺昌的暴动。全剧二十五折,至第十七折,周顺昌被暗害囊首;第十八折中,颜佩韦五义士就义被戮;第二十折,周顺昌和五义士的英魂相遇;最后五折,写魏忠贤倒台,群众奋起摧毁魏奸生祠,建造五义士墓,周氏一门受到圣旨旌表。全剧一气呵成,始终围绕周顺昌与魏堂之间展开矛盾冲突,塑造出周顺昌嫉恶如仇、威武不屈的悲剧形象。《鸣凤记》则不然。全剧四十一出,叙述嘉靖八谏臣对严嵩的斗争,尽管这条线索贯串始终,但由于缺乏中心人物,结构散乱,分成前后两截。前十六出谱写杨继盛、夏言在与奸相严嵩的斗争中壮烈牺牲,是典型的悲剧人物;后二十五出则转演邹应龙等继续与严嵩父子展开斗争,最后严氏父子覆灭身亡,邹应龙等谏臣虽也遭受挫折与磨难,但已不是悲剧性人物,而是胜利的英雄。因此,《鸣凤记》很难说是一部悲剧。
有一类作品,从单独一折或某个插曲来看是悲剧,但从整体看只是一部悲喜剧或是喜剧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王玉峰的《焚香记》里的《阳告》,写敫桂英死前在海神庙对王魁负心的控诉,尽管悲情激愤,然终究是大戏中的一段,不能称为独立完整的悲剧。再如周朝俊的《红梅记》,剧中有两个故事,一是写裴舜卿与名门小姐卢昭容的悲欢离合,两人因折红梅而相识,故以命剧名。这是贯串全剧的大故事。一是写裴生与贾似道侍妾李慧娘的生死恋,是全剧中的小插曲,用以揭露贾似道的荒淫凶残,衬托裴舜卿正义刚直的品格。李慧娘小故事套在大故事里,不能使《红梅记》变成悲剧。但由于它可以独立成篇,若将它从全剧中分离出来,重新结构,也能成为完整的悲剧作品。
最后,要从结局来考察。悲剧之所以成为悲剧,应是剧中主要人物(不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受到邪恶势力的阻挠、迫害,或是本身的失误,造成失败,甚至毁灭,即由顺境转为逆境,从而激起人们对他(她)的同情、怜悯、悲痛或悲壮、崇高、敬仰的感情。如果主人公已从苦难中和不幸中被彻底解救出来,即由逆境转为顺境,那么,应该说它只是一部悲喜剧或喜剧。有人会质问:照你这么说,岂非要将一大批带有“团圆”结局的优秀悲剧排斥在外了?我们对于“团圆”结尾应该分清两种不同的性质:一种是非现实的、虚幻的,不是真正的团圆;另一种是现实的、活生生的真正团圆。像《窦娥冤》、《清忠谱》、《娇红记》、《长生殿》等所谓的“团圆”结局属于前一种,不论是鬼魂复仇也好,表忠也好,升仙也好,化成鸳鸯也好,都是幻觉中的想像,借以寄托理想,安慰心灵,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不是生活逻辑的必然发展。《赵氏孤儿》、《清忠谱》等剧最后写孤儿刺杀了奸佞,群众焚毁了生祠,并不能改变主人公们的悲剧命运。最后的胜利,只是表明正义与邪恶斗争、较量的结果,是作者扬善惩恶思想的要求。后一种可以《白兔记》为例。穷汉刘知远入赘李家庄,与李三娘结为夫妻,受到三娘兄嫂的欺凌。刘知远被迫出走投军,三娘在家挨打受骂,推磨挑水,饥寒交迫,吃尽苦楚。李三娘身上概括了封建社会千千万万劳动妇女的凄惨和不幸。可是,李三娘最后否极泰来,终于与丈夫、儿子团圆相聚,把悲剧化为悲喜剧。
上述的三个问题,常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是有机的统一体。一位优秀作家创作剧本时,必然从结构布局到人物形象、戏剧冲突、风格手法等方面,有一个系统的构思。任意改动一点,往往牵一发而动全局,带来损害,决非能像金圣叹那样,随随便便将《西厢记》拦腰一斩,就可以把喜剧改成悲剧。反之亦然。
三、关于“寓哭于笑”
我国古典戏曲中有一类剧本,采用喜剧手法表现悲剧性的故事内容。这种“寓哭于笑”的作品,有人称之为悲剧,理由是:“我们判断一个戏是不是悲剧,主要的不是看手法,而是看内容。”并认为徐渭《四声猿》中的《雌木兰》、《女状元》等即是这样的悲剧。
众所周知,悲剧给人带来眼泪,用纯洁的泪水洗涤去忧伤和痛苦,净化心灵,化悲痛为力量;喜剧则给人带来欢笑,用辛辣的笑声烧毁黑暗、丑恶,除掉病垢,促进身心健康、精神愉快。但是笑与泪有时并非完全对立的,可以相互转化,也可以兼容并蓄。一个例子:石君宝的《秋胡戏妻》,写罗梅英嫁给穷儒秋胡,新婚三日,丈夫即被勾去当军。十年中,她含辛茹苦,勤奋劳动,侍奉年老多病的婆婆。丈夫得官归来,以为她是别人家女子,在桑园内对她调戏引诱。作者用悲喜剧的形式塑造了这位勇敢泼辣、富于斗争性的光辉女性。当她得知自己的丈夫竟是这个流氓,尽管他带来了霞帔金冠,也坚决要讨休书。可是由于婆婆以寻死要挟,梅英只得妥协屈从。最后,这欢乐的大团圆饱含着辛酸和血泪。另一个例子:关汉卿的喜剧《诈妮子调风月》。聪明美丽的婢女燕燕,幻想摆脱奴隶的命运,取得美好的生活归宿,答应小千户的求爱,以身相许。不料小千户看上一家贵族小姐莺莺,把燕燕抛弃了。燕燕不甘心受骗,奋起反抗,大闹婚礼喜堂,揭露小千户对她的欺骗,迫使小千户让燕燕当个二夫人。全剧格调明快风趣,但深蕴着奴隶的屈辱和痛苦。燕燕“和丈夫一处对舞”、“花生满路”的结局,可说是“含泪的笑”,或是“寓哭于笑”了。
以上两位女主人公都是被歌颂的正面人物。有一类讽刺喜剧,被嘲讽的对象并非奸恶小人,而是有缺点的好人。如康海和王九思两种同名《中山狼》的剧本,写东郭先生救了处于危难之中的中山狼;中山狼不仅不感谢东郭先生,反而要吃掉他。作者以幽默诙谐的笔调,辛辣地讽刺批判了是非不分的温情主义,用喜剧手法写出了东郭先生迂腐愚昧的悲剧性格。东郭这种可笑又可怜的形象,既是喜剧性的又是悲剧性的,也可以说是“含泪的笑”,或是“寓哭于笑”。而这两部作品无疑又都是纯粹的喜剧。
悲剧与悲喜剧、喜剧的区别,往往不是因为在题材内容上有多大差别,而是在于审美形式、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的不同。元人尚仲贤的《柳毅传书》原是悲喜剧,到了李渔手中,把原剧中悲剧性因素削弱或剔除,挖掘人物的喜剧性格,创造幽默诙谐、滑稽热闹的情节、场景和气氛,成为一部妙趣横生、令人捧腹不已的上乘喜剧《蜃中楼》。
一部作品处理成悲剧还是喜剧,或是悲喜剧,还取决于作者对生活的认识和态度。同样的一个故事,在不同的作者手中,会变成不同样式、不同思想的剧本,这在戏曲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宋元戏曲中揭露黑暗、歌颂正义、宣扬复仇精神的《窦娥冤》、《赵氏孤儿》、《王魁负桂英》等悲剧,到了明人手里,一个个增饰翻演成宣传伦理教化的大团圆式的悲喜剧,令人大煞风景。如《焚香记》是替士子婚变负心的翻案戏,写王魁中举后,既没有重婚,也没有写休书,套用《荆钗记》关目,由奸商金垒和鸨母串通改家书为休书,致使桂英误会,在海神庙自缢身死。桂英鬼魂在冥间告状,海神遣使拘捕王魁魂魄对质,审明原因,让桂英复活,与王魁重圆。此类戏在民间不能为观众所接受,于是在清代出现了像《赛琵琶》、《秦香莲》等谴责婚变负心的剧本;后来,川剧《情探》仍恢复“王魁负桂英”的路子。这并不是说把悲剧改成悲喜剧的都不好。汤显祖也有一本改悲剧为悲喜剧的戏《紫钗记》,其创作目的与上述诸剧相反。剧本据唐人小说《霍小玉传》改编,删掉原作中因李益负心而致霍小玉死去的情节,以突出书生对爱情的坚贞不渝,强调对权相豪富的批判和斗争,体现了作者针砭黑暗政治的进步思想。
现在再回过来谈谈徐渭的《四声猿》。徐渭生活的时代,正处在严嵩专政擅权、朝纲崩圮的黑暗岁月。他面对污浊的社会现实,一肚子不合时宜的愤懑无由发泄,便借自己独创的杂剧形式表达出来。他取“峡猿啼夜,声寒神泣”(钟人杰《四声猿引》)之意,四个短剧总题名《四声猿》。作者狂歌长啸,寓哭于笑,用喜剧手法来抨击黑白混淆、是非颠倒的世俗社会。《狂鼓吏渔阳三弄》写祢衡击鼓骂曹,骂的实是严嵩。他采用壮怀激烈的悲剧样式,却以荒诞喜剧手法,让祢衡在阴曹地府重演骂曹的故事。剧中极尽揶揄嘲弄之能事,痛快淋漓,浩气冲天,直令“奸雄胆裂”(澄道人语),好让世人为之一快。他对在封建礼教重压下的妇女深表同情,便在《雌木兰》和《女状元》中正面展现巾帼女豪的英姿,大声赞颂女子卓异的才华,批判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玉禅师》中,更是辛辣地讽刺了官府、佛门尔虞我诈的丑态和禁欲主义的虚伪性。徐渭为人蔑视礼教,狂放不羁,其《四声猿》艺术风格,正好与他的思想品格相一致。袁宏道在《徐文长传》中说得好:“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坟。”他即是这样把杂剧当作抒写胸臆不平的长诗来写,嬉笑怒骂,长短不拘;恣肆纵横,一无遮拦。因为只有这样的喜剧形式,才能完全收到如此的艺术效果。
我们常说文如其人,对悲剧、喜剧、悲喜剧的选择运用上,反映了作家的个性特征。同是表现狂放不羁的愤世之情,沈自征与徐渭可说是同中有异。晚于徐渭的沈自征,落拓半生,明末国变,卒于抗清军中。他的三种杂剧合称《渔阳三弄》,明示系骂世之作。三剧都以失意文人为题材。《霸亭秋》写宋杜默落第归乡,路过乌江亭项羽庙,拜神像朗读其试卷而放声大哭,项羽泥神亦随之长嘘流泪。《鞭歌妓》写唐张建封落魄江湖,遇礼部尚书裴宽偕二家妓还朝,张建封豪气勃勃,笑傲今古。裴尚书便将一船金帛与二歌妓相赠。歌妓轻侮张建封贫穷位卑,建封乃以剑相胁,用鞭斥责。《簪花鬟》写明杨慎贬谪云南,醉后身穿妓衫,头作双丫鬟,携妓游春,簪花嬉笑。作者或抨击科举制度,或藐视功名富贵,或颂扬落拓不羁,借古人自喻,或哭或骂或笑,表达忧愤不平之情、狂放傲岸之态,以示对社会的不满。三剧哭中有笑,笑里藏哭:《霸亭秋》最后,杜默转哭为笑;《簪花鬟》末尾,杨慎却又转笑为哭。所以,祁彪佳《远山堂剧品》评论《簪》剧道:“人谓于寂寥中能豪爽,不知于歌笑中见哭泣耳。曲白指东扯西,点点是英雄之泪”。同是“寓哭于笑”,《四声猿》重在骂、讽,《渔阳三弄》重在愤、恨,因而艺术风格、审美形式也就随之各异。
经过易朝换代后的清初,杂剧作家不满异族统治,仿效《四声猿》形式,或作《续四声猿》(张韬),或以读《骚》命名,如尤侗《读离骚》、嵇永仁《续离骚》,以诉抑郁愤懑的牢骚。如果这时还有点国家兴亡感的话,到了清代中叶,这类短剧主要是感伤个人身世、哀叹怀才不遇的遭际。如桂馥《后四声猿》,通过白居易遣放樊素、陆放翁沈园题壁、苏东坡谒府帅受冷遇、李贺诗遭忌被毁的故事,抒写文人失意的痛苦和烦恼,与徐渭《四声猿》相比,早已失去血泪并作的悲愤和指天骂地的豪气,只剩下哀怨和伤感。作家的思想、个性、审美趣味、时代环境的差异,对于戏曲类型样式的选择和运用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判定“寓哭于笑”是悲剧、喜剧,还是悲喜剧,主要从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来着眼,而不是根据思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