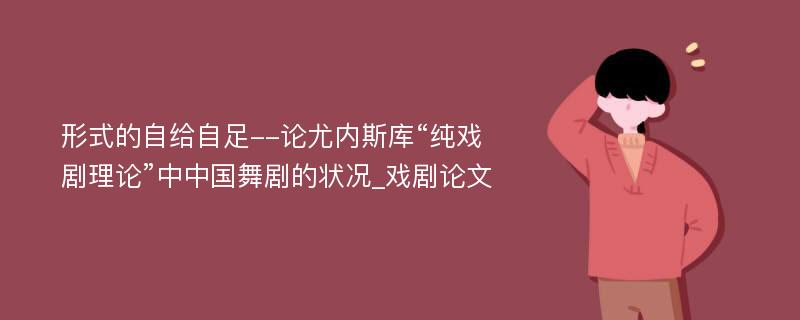
形式的自足——有感于尤涅斯库“纯戏剧论”论中国舞剧状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舞剧论文,中国论文,戏剧论文,形式论文,状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尤涅斯库为了强调戏剧作为艺术的独立性,即“戏剧就是戏剧”,举了一个例子:同 样表达一个思想概念,语言是“人必死于孤独”,而莎士比亚的戏剧则展示理查二世监 禁其中的空空四壁。他通过舞台形式表达的特殊性直指戏剧独立的品质。
尤涅斯库强调“戏剧就是戏剧”,其实就是强调戏剧表达形式本体的重要性,其本体 有了独立自足不同于他者的品格质地才称得上是一门特立的艺术。戏剧如此,舞剧亦是 如此。作为小作品的舞蹈,由于题材形式的单一简短而使舞蹈本体,即肢体动作语言, 能够相对地自成一个完满的艺术个体。而作为大型作品的舞剧,由于文学文本的加入, 使肢体语言必然失落于具象的故事空间,将部分抽象的能力转向文学文本的图解,从而 大大削弱了动作语言在舞剧中的自主性。这个现象在中国舞剧创作中是显而易见的。
20世纪50年代初,《宝莲灯》为新中国舞蹈史翻开舞剧创作的第一页,它是以戏曲《 目连救母》为原型母本发展创作的。从舞蹈本体来看,舞剧《宝莲灯》是其戏曲剧目基 础上的身段扩大化,也就是说,用舞蹈化的身段代替以往的唱念做打来讲述这个古老的 故事。它在探索试图在戏曲身段的程式化语言中寻找并建立中国古典舞,所以还未真正 涉及舞蹈语言与剧作文本关系的处理,这是当时舞蹈发展的必然阶段。这个情形在后来 的原创舞剧《小刀会》中依然延续,剧作文本的新创没有改变它与动作语言之间的疏离 关系。与前两个舞剧不同,《鱼美人》的创作则走向“西学”道路,大到舞剧结构,小 到双人舞的处理,大都套用西方芭蕾舞剧的模式。除了演员没有上脚尖以外,舞蹈语言 程式也是芭蕾化的。无论学“中”还是学“西”,此时舞剧创作的眼光始终没有离开对 舞蹈语言的探索,而对舞蹈语言与剧作文本的关系则缺乏关注。此外,由于当时政治对 文艺干涉甚多,使得舞剧创作对题材尤为关注,造成了剧作文本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剧 作文本成为舞蹈创作中舞蹈语言围绕的核心,势必导致在舞剧中舞蹈与文学形成分立的 二元关系。同时。对题材的突现,也成为后来“文革”八大样板戏中两个芭蕾舞剧《红 色娘子军》和《白毛女》立足的重要因素。应当说,用现在的眼光来评价《红色娘子军 》和《白毛女》的成功之处,依然是其在舞蹈语言的探索上有着突出的表现。脚下足尖 的西方“语汇”和腰身把势的中国“方言”,使这两个舞剧成为舞蹈史上高扬在那个年 代的屹立不倒的旗帜。
直到20世纪80年代,舞蹈语言的探索仍方兴未艾。舞剧《丝路花雨》以敦煌壁画中的 舞姿形象为基础,提炼出以“S”形为主的造型和动律规则,为中国舞蹈开辟了一个新 的视域。一直到今天,21世纪在纪元年代上的跨越,也未给中国舞剧中舞蹈语言的探索 画上一个中止的符号。民间舞、古典舞、芭蕾舞、现代舞等等不同舞蹈种类在舞台上杂 糅交和,为舞蹈语言的探索提供了各种可能性。然而,除却表面的繁荣,这些舞蹈本体 语言的探索对于舞剧独立品格的建立并未提供新鲜的经验。如前所说的舞蹈与文学分立 的二元关系依然存在,一如既往的舞蹈语言探索从根本上来说,性质属于小作品的舞蹈 创新,文学文本只是提供了一个舞台框架和叙事对象。舞蹈语言和文学文本实际上是在 二元的空间里自说自话,靠图解功能来维系整体的表象。所以,几十年来的舞剧发展就 是变换各种“方言”来讲故事,造就了中国舞蹈史上的丰产期。
但是,在中国舞剧的这种发展状况下,并不是没有站在“范式转换”的角度上思考问 题的人。作为《小刀会》编导之一的舒巧,在其后来的舞剧创作中提出“舞蹈结构作为 表达的语言”的观点,从整体上把握舞蹈语言和剧作文本的关系,让舞剧的这两个要素 从“自为”状态转换为“互为”状态。她以舞剧《岳飞》的编排经验说明了这一点:“ 第四场在全剧中分场任务是:(一)剧情推进需要交待南宋小朝廷与金媾和;(二)人物方 面要突出岳飞力阻议和;(三)色彩铺排对比前半部的战斗场面,需要女性慢板舞蹈。三 大任务苦坏了编导。媾和:双方捧出‘和约’来,女子舞用来祝贺媾和。力阻议和:皇 帝正欲递交‘和约’时岳飞赶到扑地长跪……依此排来,三易其稿终不成。无论是表演 舞蹈反复加工、还是场面调度再三整理,岳飞独舞加大幅度。都无济于事。忽然大家醒 悟是不是从结构上想想办法,改换一下视角。第四稿整场戏改用宫廷宴会,餐几铺排满 台,开门见山便是皇帝与金使同桌共饮,宫女上菜献舞,众官醉生梦死。如此‘和约’ 用不着拿出来了,也不用担心观众看不清‘和约’二字。女子舞几乎未作修改,只更动 了在本场结构中的位置,卖国求荣、偏安的调子就塑出来了。在此气氛中岳飞进场,仅 只一站,举目环视这一切,此时此景一个爱国将领的心境观众已可想而知。三大任务以 编舞所力不能及的结构来完成了。”(注:舒巧:《舞蹈结构作为表达的语言》,转引 自北京舞蹈学院:《舞蹈编导教学参考资料》第160页。)舒巧从单纯动作组织语言的层 面跃升到剧作结构组织语言,抛却了舞蹈语言对个别场景情节微观讲解式的说明交待, 使其脱离哑语境地。但还应当看到,她用结构象征功能替代肢体指示功能的“范式转换 ”仅体现在个别场景和情节的处理上,没有贯穿整个舞剧,因而还是一个不彻底的“革 命者”。
如果说舒巧是先觉者的话,那么编导赵明就是自觉者,他在谈论舞剧《梁祝》的构思 时,体现出对舞蹈语言和叙事文本关系的思考深度。他指出:“舞蹈很适合铺染场面仪 式的东西,如果用舞蹈的思维来解构《梁祝》的话,一上来就是婚礼的场景,紧接着就 是丧礼的场景。”他这样安排是因为梁祝故事的精神就在于生不能合,死后才能到阴间 圆满的悲剧性。舞蹈语言抽象的形式手段正好在婚礼和丧礼的呼应中深化悲剧意味,同 时这也丝毫不改原著的精神内涵。如果说,对原来故事的叙述发生了改变,那就是舞蹈 和文学对时空叙述方式的不同,这种不同也正是舞剧立足艺术的本质所在。赵明不同于 舒巧之处就在于,他意识到了舞蹈语言的特性,并将其作为舞剧创作的根本指导,用舞 蹈解构作品而不是文学给出框架,同时又尊重剧作文本中的事件和精神,这就契合了尤 涅斯库有关戏剧的艺术独立性的内在精神。当初,尤涅斯库提出“纯戏剧论”是针对戏 剧工具论而发的,他指出:如果戏剧注定只能成为哲学、神学政治、意识形态和儿童教 育的工具,它本身的职责何在?“一部心理剧比不上心理学,读心理学专著要比看心理 剧更好。一部哲理剧也比不上哲学。与其去看舞台上图解这种或那种政治,我情愿去读 每天的日报,去听我们党派候选人的讲演。”(注:尤涅斯库:《戏剧经验谈》,转引 自《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21页。)实际上,回顾中 国舞剧的发展,舞蹈又何尝不是故事的工具呢?
当然,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舞蹈自身发展的历史决定了舞剧的创作必然在此 时经历舞蹈语言和剧作文本的分立状态。元代以前的古代乐舞是以女乐为主的伎乐舞蹈 ,它强调一种娱人的声色享乐,技艺很强却有失格调。元代以后,中国的艺术舞蹈就融 入到戏曲的身段当中,失去了独立的身份。在20世纪初,有了西方芭蕾舞和现代舞的传 入才有了中国舞蹈的觉醒。而中国舞蹈体系化的建立则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了,所 以中国舞剧的发展和舞蹈发展是同步的,它的创作过程也就是舞蹈语言的探索过程,无 怪乎一路走来无法见到尤涅斯库“纯戏剧论”意义上的“纯舞剧”。作为舞剧特立的形 式,就应当打破舞蹈语言和叙事文本分立的二元关系,从舞蹈的艺术特性当中寻找叙事 的独有形式,而不是让舞蹈沦为叙事的工具。这一点,尤涅斯库已说得足够清楚,中国 舞剧的发展道路也走得足够明了。
对事物的评判总是此一时彼一时,高低是非总随人随时而变。然而无论怎样,尤涅斯 库“纯戏剧论”中的眼光和道理对于中国当代舞剧创作还是有前瞻意义的。无论后现代 怎样通过打破界规来树立当下的艺术标准,中国舞剧的创作还是需要建立一种意义纯粹 的形式来实现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