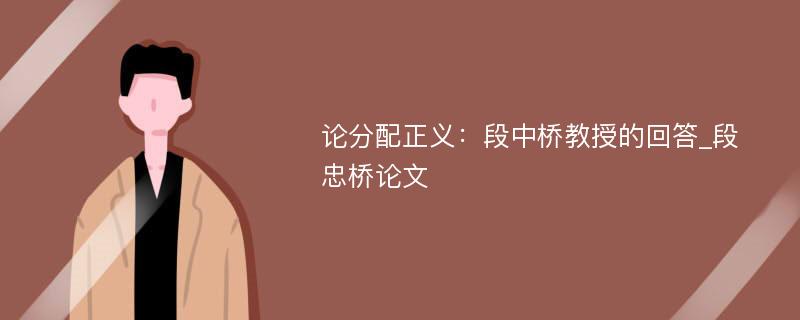
三论分配正义——答段忠桥教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正义论文,分配论文,教授论文,段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在《哲学研究》2011年第3期发表《分配正义:从弱势群体的观点看》一文,表达了关于分配正义问题的一些观点,特别是提出了分配正义的原则。段忠桥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发表了《关于分配正义的三个问题——与姚大志教授商榷》,就分配正义问题提出了一些与我不同的观点并对我的一些观点提出了批评。针对该文,我又写了《再论分配正义——答段忠桥教授》(以下简称《再论分配正义》),在分配正义、平等和应得三个问题上表达了我的观点,此文发表在《哲学研究》2012年第5期。然后,段忠桥教授又写了《也谈分配正义、平等和应得——答姚大志教授》,就我的《再论分配正义》一文提出了批评。应《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的邀请,我现在对这篇文章做出回应,以推动相关问题的讨论和深入研究。
尽管我自己更关注关于分配正义的一些实质问题而非琐碎的争议,鉴于段忠桥教授抱怨“他(指姚大志)在文中没有直接回应我的不同意见”①,我下面首先对他的批评做出回应,然后再讨论我们之间存在分歧的实质性分配正义问题。
一、对批评的回应
在这样一篇篇幅极为有限的文章中,我不可能回答段忠桥教授的所有批评。而且,这样的回应具有一种内在的缺点:为了说清楚我回应的是什么,我需要先讲清楚段忠桥教授批评的是什么,而这种批评所针对的又是我的上一篇文章“再论分配正义”。要把所有相关的背景都交代明白,这些琐碎的文字会使读者产生极其糟糕的阅读体验。因此,下面只对一些我认为重要的问题做出回应。
1.关于外在的(客观的)分配正义观念。在《再论分配正义》中,我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我认为不存在某种外在的(或客观的)分配正义观念,以致我们一旦发现了这种分配正义观念,只要按照它的要求去做就行了。我也不认为分配正义观念需要建立在某种外在的(或客观的)权威上面,无论它是神法还是自然法”[1]。而我之所以表达这样的观点,是因为我推测段忠桥教授的相关观点就建立在这种外在的(或客观的)分配正义观念上面。对此,段忠桥教授提出了如下批评:第一,我的推测是“不成立的”,他并不持有这种外在的分配正义观念②;第二,我不能证明“不存在一种外在的(客观的)正义观念”,他特别表明对此的举证责任在我这一方③;第三,我为了证明不存在这种外在的(客观的)正义观念,举了平等主义、功利主义和至善主义三个例子,而段忠桥教授认为,“这些例子恰恰证明不了他想要证明的东西。这是因为,如果不同的人可以设计出不同的制度,而不同的制度设计可以基于不同的正义观念,那就意味着,人们持有的正义观念是先于他们的制度设计的。那他们的先于制度设计的正义观念源于哪里?能源于‘现实的困境’吗?显然不能!如果不能,那他们持有的正义观念就只能源于姚大志教授认为并不存在的外在的(客观的)正义观念”④。
对上述批评的回答如下:
首先,我承认我的推测可能是错误的,因为在段忠桥教授的两篇文章中,他或者对我的观点进行批评,或者引用西方政治哲学家的观点,而几乎没有表达自己在分配正义问题上持有什么观点。我确实不知道他的观点是什么,因此我的推测可能会出错。
其次,段忠桥教授要求我来证明“不存在一种外在的(客观的)正义观念”,并声明举证责任在我这里。一个人如何能够证明他认为不存在的东西?比如说,我认为没有鬼,但是我确实无法证明没有鬼。能提供证明的是主张有鬼(或存在外在的正义观念)的人。换言之,举证责任在持有肯定观点的一方。即使举证责任不在我这里(因为我无法证明我认为不存在的东西),我在“再论分配正义”中还是举了一些例子(平等主义者、功利主义者和至善主义者)来说明我为什么认为不存在外在的(客观的)正义观念。
最后,段忠桥教授认为我举的例子证明的不是不存在外在的(客观的)正义观念,而是恰好相反,即存在外在的(客观的)正义观念,因为平等主义者、功利主义者和至善主义者用于制度设计的正义观念“只能源于姚大志教授认为并不存在的外在的(客观的)正义观念”。我不明白这里的逻辑是什么?平等主义者、功利主义者和至善主义者分别持有不同的、甚至冲突的平等主义正义观、功利主义正义观和至善主义观,就正义问题来说,这些正义观对他们而言是终极性的,即在这些正义观之外不存在更为基本的(外在的或客观的)正义观念。反过来,如果存在外在的(客观的)的正义观念,那么也只会存在一种(真的),而这种(真的)正义观念不可能包容冲突着的平等主义、功利主义和至善主义。
关于外在的(客观的)正义观念问题的实质在于:我自己在正义问题上持有一种建构主义的观点,即我们思考一个正义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然后按照我们的正义理想来设计相关的制度。在这种对正义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思考中,没有为外在的(客观的)正义观念留有任何位置。
2.关于“平等的分配”。我在“再论分配正义”的第二节讨论了平等的观念,其中特别是分配正义中的平等问题。对此段忠桥教授认为,“姚大志教授对‘平等的分配’的界定、对需要分配正义来分配的对象的限定和他对平等的分配为什么是不公平的论证,都是不能成立的”⑤。比如说,“与分配正义问题相关的‘平等的分配’指的是‘把人当作平等者来对待’。姚大志教授这里论证的‘平等的分配’无疑也是与分配正义问题相关的,但他却把‘平等的分配’理解为‘所有相关者都得到了平等的一份’,这样的界定显然不能成立”⑥。看来,我们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在于对“平等的分配”具有不同的理解。
我对“平等的分配”的理解是清楚的。假设一个简单的例子,有两个人,他们面对两种分配方案:第一种分配为A得到10,B也得到10;第二种分配为A得到15,B得到12。其中的数字代表他们各自在分配中得到的数额。我认为这是清楚的,即第一种分配是“平等的分配”,而第二种分配是“不平等的分配”。我也认为这是没有争议的。至于第二种不平等的分配,它可能是正义的,也可能不是正义的。那么一种不平等的分配在什么情况下能够是正义的?我认为,如果第二种分配得到了其中所得更少者(B)的同意,那么它就是正义的。
段忠桥教授对“平等的分配”的理解却是不清楚的。按照他的说法,“与分配正义问题相关的‘平等的分配’指的是‘把人当作平等者来对待’”。但是,在分配问题上什么是“把人当作平等者来对待”?这是不清楚的。让我们假设这样一种分配,A一个月工作了20天并因此得到了2000元,B一个月工作了10天并因此得到了1000元,其他情况都相同。我们会认为,他们都被“当作平等者来对待”了,但是这种分配确实是一种“不平等的分配”。显然,“把人当作平等者来对待”与“平等的分配”是无关的,起码它无法界定什么是“平等的分配”。这是因为“把人当作平等者来对待”是一种程序性的标准,它无法解决分配正义这样的实质性问题。
在关于分配正义的探讨中,平等是最关键的问题,我们还需要说更多的东西。为此,我们将在第二节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3.关于应得。我在《再论分配正义》的第三节讨论了应得的问题,比较详细地表达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段忠桥教授对此提出了如下一些批评:第一,对于我推断他赞同麦金太尔等人把“应得”当作分配正义原则的观点,他认为“这是明显的误解”,“是毫无根据的”⑦;第二,他批评说,“姚大志教授却把这三人的论述说成是‘麦金泰尔等人确实把应得当作分配正义的原则’,这有根据吗?‘麦金泰尔等人’中的‘等人’指的是谁,是科恩、米勒吗?如果是,那有什么理由说他们二人‘确实把应得当作分配正义的原则’?”⑧第三,他批评说,“他(指姚大志)在这里却只字不提麦金泰尔等人理解的‘应得’是什么,而是大谈他理解的应得是什么,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他理解的‘应得’是麦金泰尔等人理解的‘应得’吗?据我所知,显然不是!如果不是,那他说的‘应得不能作为分配正义的原则’,其含义就只能是‘他理解的应得’不能作为分配正义的原则”⑨。
首先是关于我的“误解”。由于段忠桥教授在讨论应得的时候没有阐明自己的观点是什么,而是引证了麦金太尔等人(包括柯亨和米勒)关于应得的观点,所以我推断他是赞同麦金太尔等人的观点的。否则,他引证他们的应得观点又是为了什么呢?引证一种自己不赞同的观点来反对另外一种观点有什么意义呢?我承认我可能误解了段忠桥教授的观点,除非他在应得问题上明确阐明他的观点是什么。
其次是“麦金太尔等人”的问题。到底是谁“确实把应得当作分配正义的原则”?我的回答是“麦金太尔等人”。“等人”是谁?是持有与麦金太尔相同观点的人,而且,在当代政治哲学中,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很多,其中包括米勒和柯亨。段忠桥教授另外也追问“根据”。关于麦金太尔,我在《现代之后》和《何谓正义》中都有专门的章节来讨论麦金太尔的应得观念,而且我也认为它们提供了足够的根据。关于米勒,他在《社会正义原则》中用两章的篇幅专门讨论了应得的问题,并且明确表明应得是分配正义的一个原则,尽管他也把平等和需要当作分配正义的原则。关于柯亨,从段忠桥教授所引证的那段话及其注释中可以看出,他确实把应得当作分配正义的原则,尽管他对此“并不完全满意”。那么柯亨为什么对应得作为分配正义的原则“并不完全满意”?因为他在其他的地方曾明确表达过另外一种观点,即“优势平等”作为分配正义的原则。至于“应得”与“优势平等”是相容的还是不相容的,这需要专门的考察。
最后是我与麦金太尔等人所理解的“应得”是否是一致的。我在“再论分配正义”中对应得给予了这样的界定:“所谓‘应得’(desert),就是人们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东西”[1]。我认为,麦金太尔以及其他持有相同观点的人(其中包括米勒和柯亨)对此的理解是一致的,而且我也认为他们能够同意我的说法。段忠桥教授对此表示不同的意见:“据我所知,显然不是!”公平地说,他的意见也有某些道理。但是,他的意见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道理,即应得还有其他的含义。除了我上面所表达的说法之外,应得还有另外两种含义。一种是应得意味着“道德应得”,另外一种意味着“地位的应得”。如果是前者,那么正如罗尔斯所认为的那样,“道德应得”与分配正义无关,它应该被排除于分配正义的考虑之外。如果是后者,即像古希腊社会那样人们是基于家庭出身应得其报酬,从而贵族应该比平民应得更多的东西,那么显然这种实行于等级制社会的应得不适合于当代社会。
以上是对段忠桥教授提出问题的几点回应,下面让我们讨论实质性的分配正义问题。
二、平等与优先性
关于实质性的分配正义问题,在我关于分配正义的两篇文章中,以及段忠桥教授对这两篇文章的回应中,核心问题是平等的观念。导致我们分歧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对平等的理解,而我们对平等的理解是不同的。比如说,关于什么是“平等的分配”,我的理解是“所有相关者都得到了平等的一份”,而段忠桥教授的理解是“把人当作平等者来对待”。同样,很多人都认同“平等主义”,并且把自己视为平等主义者,但是他们对平等的理解却是大相径庭的。这种情况表明我们需要对平等观念本身进行分析,以澄清其含义。
平等主义的核心是这样一种原则(帕菲特把它称为平等原则):“如果一些人的处境比其他人更差,这本身就是坏的。”[2]314比如说,在一个社会里,一半人的生活状况为10,另一半人为20,这种情况就是坏的。这种平等原则意味着,在一个共同体(或社会)里,一些人生活得更好,另外一些人生活得更差,如果这些生活更差者不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过错,而其他情况相同,那么这种状况本身就是坏的。这种平等原则也意味着,平等是一个比较性的观念,一些人的处境更差是相对于另外一些人而言的,而这些人的处境比他们更好。这种平等原则还意味着,平等具有内在的价值,即平等是好的,不平等是坏的,从而它具有重要的道德意义。如果一个人认同平等主义,那么他就应该对这种平等原则具有坚定的承诺。反过来,如果一个人不认同平等原则,那么他就不能说是一个平等主义者。
这种平等主义及其平等原则会面临一些困难。请看下面的情况(我们用数字代表人们的福利,而福利在这里代表人们的生活状况):
(1)a.所有人的福利都为10;b.所有人的福利都为20。
这里有两种处境,a和b,而且这两种处境中人们的福利都是平等的,尽管后者的福利比前者高出一倍。处境b比处境a更好吗?从直觉看,我们会认为处境b比处境a更好。但是对于平等主义者,处境a是一种平等的状态,处境b也是一种平等的状态,因此两者是一样的。基于平等原则,平等主义者不能说处境b比处境a更好。平等主义者要说处境b比处境a更好,他们除了信奉平等原则之外,还需要信奉功利原则:“如果人们的处境更好,这本身就更好”[2]314。也就是说,这需要平等主义者持有这样的观点,即平等不是我们信奉的唯一价值,还有其他的价值也值得我们信奉。事实上,大多数平等主义者都持有这样的多元主义观点。一般来说,多元主义的平等主义者通常会把平等原则放在第一位,而把其他价值(如功利原则)放在后面。只有在承诺了其他价值(如功利原则)之后,在面临情况(1)时,平等主义才可以有理由说处境b比处境a更好。但是,遇到稍微复杂一点的情况,平等主义还是无能为力:
(2)a.有人的福利都为10;b.一半人的福利为18,另一半人的福利为12。
在(2)中,处境a是一种平等的状况,处境b是一种不平等的状况,但是其中所有人的福利都提高了,尽管一半人的福利比另外一半人更少。现在我们假设,一个社会从处境a变为处境b,那么这种变化是变得更好还是更坏了?从只信奉平等原则的严格平等主义者来看,处境变得更坏了,因为它从平等的变为不平等的。从功利主义者的观点看,处境变得更好了,因为后者的总功利或平均功利都提高了。但是对于多元主义的平等主义者,则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从他信奉的平等原则看,处境变得更坏了,因为它从平等的变为不平等的。从他认同的功利原则看,处境变得更好了。在这里,平等原则与功利原则是冲突的,而当两者冲突的时候,平等主义者就不知如何做出决定了。问题不仅如此,平等主义还会遇到更有力的反驳:
(3)a.一半人的福利为20,另一半人的福利为10;b.一半人的福利为10,另一半人的福利也为10。
在处境a中,一半人的福利比另外一半人更少,而且这不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过错,其他情况都相同。对于这种不平等的处境,平等主义者是无法容忍的。我们假设,由于某种原因,一半人的福利为10,而且是无法提高的。平等主义要想实现自己的平等理想,就需要把另外一半人的福利从20降低为10,从而拉平两者的福利。这样就从处境a变成了处境b。基于平等原则,这种福利的拉平是合理的。但是,几乎所有人都会认为,这种拉平是不合理的,因为它没有使任何人得到好处。如果这种拉平是不合理的,那么平等主义(起码是这种基于平等原则的平等主义)就是不合理的。这就是对平等主义的“拉平论反驳”。而且,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这种“拉平论反驳”是非常有力的。
与这种基于平等原则的平等主义不同,还存在另外一种版本的平等主义。这种平等主义关注的焦点不是人们之间的不平等,而是那些生活处境不好的人们,那些连最基本需要都没有满足的人们,那些存在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们。这种版本的平等主义最早是由内格尔(Thomas Nagel)表达的,后来被帕菲特(Derek Parfit)加以详细阐述,并把它称为“优先论”(priority view or prioritarianism)。按照帕菲特的解释,优先论的原则是:“人们生活得越差,使这些人受益就更为重要”[2]329。为了说明优先论与以平等原则为基础的平等主义的不同,请看下面的情况。
(4)a.一半人的福利为20,另一半人的福利为10;b.一半人的福利为10,另一半人的福利也为10;c.一半人的福利为20,另一半人的福利为15。
在分配正义问题上,平等主义(平等原则)考虑的是消除两部分人之间存在的福利差距,这或者通过提高处境更差者的福利,或者通过拉平处境更好者的福利,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如果通过拉平来实现平等,即由处境a变为处境b,那么这种实现平等的方式没有使任何人得到好处,同时又损害了一些人的福利。因此,拉平论就对平等主义构成了有力的反驳。与其相反,优先论赋予处境更差者的福利以更大的分量,它关注的是改善他们的处境,提高他们的福利水平。如果处境更差者的福利水平得到了提高,即由处境a变为处境c,那么这种变化使一半人得到了好处,同时也没有损害另外一半人的福利。而且我们也应该看到,与处境a相比,处境c减少了两者之间的不平等,使分配变得更平等一些。也就是说,虽然优先论的重心是改善处境更差者的处境,但是它也带有平等主义的后果。
为了更明确区分开平等主义与优先论,让我们对它们进行更深入的分析。首先,从本性上看,平等主义是关系性的,它关注的是“弱势群体成员与其他群体成员相比的福利之相对差距”,而优先论则不是关系性的,它关注的是“弱势群体成员的福利之较低的绝对水平”。[3]其次,在平等观念上,平等主义主张平等具有一种内在的价值,一些人比另一些人具有更少的福利,这本身就是坏的。优先论则认为平等只具有一种工具主义的价值[4]135,因为它把改善弱势群体的处境放在优先的地位,而平等不过是提高弱势群体成员之福利的一种后果。最后,在面对反平等主义的反驳时,平等主义无法避免拉平论的反驳,而优先论则能够避免这种反驳。
在分配正义问题上,平等主义的任务是消除不平等,而由于“不平等是复杂的、个人性的、并且在本质上是比较性的”[5]307,所以它需要关注的东西太多,以致无法聚焦于某一点。相反,优先论的首要任务不是消除不平等,而是改善处境更差者的处境,这样它就有了明确的焦点,有了可以着手解决的确切问题,从而能够参照它们来设计制度,以实现正义的理想。
而且,我们还必须追问一个问题:平等观念真正的道德关切是什么?如果我们深入思考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会发现,平等观念真正打动人的地方是它关心那些生活困苦的人们。假设存在一个百万富翁的社会,它要比我们现在的社会富裕100倍,其中一半人的收入为400万,另一半人的收入为800万,我们会在意这个社会的不平等吗?恐怕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在意。而在我们存在于其中的社会里,即使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中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很多人变得富裕了,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生活困难,处境艰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平等观念表达了我们的道德关切:应该改善弱势群体成员的处境。
一方面,我们真正的道德关切在于那些弱势群体成员的艰难处境,另一方面,平等主义面对着拉平论的有力反驳,因此我认为,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看,优先论是一种比平等主义更合理的平等观念。
注释:
①段忠桥:《也谈分配正义、平等和应得——答姚大志教授》,见本刊,第34页。
②段忠桥:《也谈分配正义、平等和应得——答姚大志教授》,见本刊,第35页。
③段忠桥:《也谈分配正义、平等和应得——答姚大志教授》,见本刊,第35页。
④段忠桥:《也谈分配正义、平等和应得——答姚大志教授》,见本刊,第36页。
⑤段忠桥:《也谈分配正义、平等和应得——答姚大志教授》,见本刊,第40页。
⑥段忠桥:《也谈分配正义、平等和应得——答姚大志教授》,见本刊,第40页。
⑦段忠桥:《也谈分配正义、平等和应得——答姚大志教授》,见本刊,第41、42页。
⑧段忠桥:《也谈分配正义、平等和应得——答姚大志教授》,见本刊,第42页。
⑨段忠桥:《也谈分配正义、平等和应得——答姚大志教授》,见本刊,第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