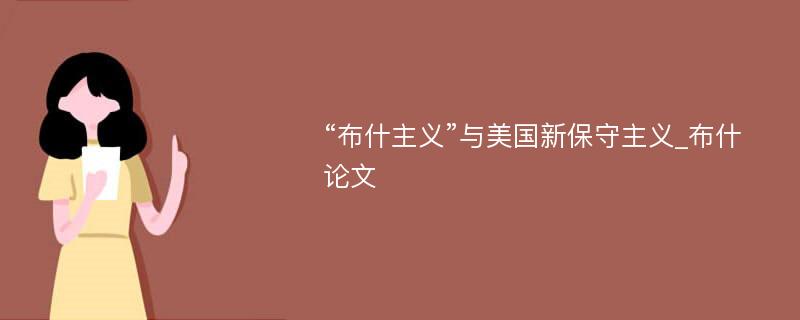
“布什主义”与美国新保守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布什论文,保守主义论文,美国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美国在伊拉克遇到的麻烦日益增大和美国国内对布什政府伊拉克政策的怀疑日益加深,广受争议的“布什主义”似乎走到了尽头。本文旨在判定“布什主义”在美国意识形态中的位置,揭示它与新保守主义的关联,说明它与“美国例外论”、自由主义、里根主义和威尔逊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而探讨“布什主义”与新保守主义两者共同兴衰的历程及原因。
一 “布什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契合
如果给“布什主义”下一个简要定义的话,就是布什所主张的先发制人、单边主义,追求美国仁慈的霸权,运用美国的军事力量在世界上推进民主的外交政策。2002年6月布什在西点军校的讲话和2002年9月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大多被认为是“布什主义”形成的标志。
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除了重复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些传统目标之外,如在全世界促进自由民主政府和自由贸易制度,还提出了一个标志着美国外交政策转向的引人注目的观点:不能通过使用遏制和威慑工具对付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武装起来的非国家恐怖主义者。报告说,“鉴于流氓国家和恐怖主义者的目标,美国不能仅仅依靠我们以前依赖的反应姿态。”“美国长期以来保留了先发制人行动的选择,以对抗对我们国家安全的充分威胁。威胁越大,不行动的威胁性就越大——采取预期的行动来保护我们自己的案例就越令人信服,即使关于敌人进攻的时间和地点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为了抢先和防止我们敌人的敌对行动,美国应当,如果必要的话,先发制人。”在必要的情况下,美国将需要诉诸“志愿者的联合”(the Coalition of the Willing)。① 由此,这个文件提出了美国将采用先发制人、预防性战争和单边主义的方法,对付威胁其安全的国家和非国家因素。
美国外交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认为,先发制人和单边主义都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新特征。第一个根据先发制人的主张而采取的行动发生在1818年,当时美国人认为,西班牙对佛罗里达的不稳定统治使这片领土成为抢掠者和敌视美国的印第安人袭击美国的基地。为此,美国军队对佛罗里达采取了先发制人的入侵。同时,美国大战略家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说服了门罗总统写信给西班牙政府,要求其或者在佛罗里达部署足够的军队来有效地维持治安,或者把这片土地割让给美国。亚当斯的战略最后确保了美国对佛罗里达的控制。在亚当斯1820年当选为总统之后,他开始把这一战略应用到整个美国西部边界。先发制人的主张以后被美国应用于为兼并可能会受到敌对国家控制的领土辩护,例如波尔克总统以此来为他1845年兼并得克萨斯辩护,并为后来美国兼并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科罗拉多和内华达进行辩护。② 此外,艾森豪威尔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曾围绕着先发制人的战略进行过讨论,肯尼迪政府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也曾考虑过对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不过他们最终都没有采纳这一方法。③ 在美国外交传统中同样有影响的是亚当斯的第二个主张——单边主义。单边主义的观点认为,美国不能依赖于其他国家保护美国安全的良好意愿,因此美国必须准备自行其是。华盛顿在其著名的告别演说中谈到1778年的美法联盟时表达了这一观点。④
“布什主义”的基础是新保守主义的观念,关于这一点几乎没有人怀疑,无论布什本人是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新保守主义者。虽然自称为新保守主义的人持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新保守主义思想可以成为范围广泛的国内外政策选择的基础,但是无论新保守主义有多么复杂的根源,它现在已经不可避免地同“布什主义”中的下述主张联系在一起:先发制人、政权变更、单边主义和仁慈的霸权。⑤
与布什主义相关的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思想的成型可以追溯到冷战结束之后。那时,新保守主义者开始提出各种旨在保持美国在世界上的军事干预和对自由世界的领导的思想。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和罗伯特·卡根(Robert Kargan)1996年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走向新里根主义外交政策》(Toward a Neo-Reaganite Foreign Policy)。他们拒绝接受美国权力的衰弱是不可避免的假设,也不愿意接受美国国内的一些政治和思想派别提出的美国应在冷战后收缩其外交的要求。他们鼓吹,美国的道德和美国的国家利益几乎总是和谐一致的,“适当的美国外交政策是在未来尽可能长久地维持美国的霸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需要一个新里根主义的外交政策,即军事上的优势和道德上的自信”,并追求里根在80年代勇敢追求的“仁慈的全球霸权”和行使这一霸权。他们认为美国在打败了苏联这个“邪恶帝国”后,就享有了战略和意识形态上的支配地位。在九一一事件之前,他们把中国看作是冷战后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要对手。为此,他们主张,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应是遏制、影响和最终寻求改变北京的政权。⑥
1997年,这两位作者着手成立了一个设在华盛顿的新保守主义思想库“美国新世纪计划”(The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旨在推广他们在文章中赞同的观点。“美国新世纪计划”提出了一个“原则声明”(The Statement of Principles),声称其任务是“提出美国应当充当全球领导者的理由和征集对美国全球领导的支持”,强调所谓的“里根政府成功的基本因素”是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时刻准备应付“当前和未来的威胁”。声明说,里根强大的军事力量和道德清白对于确保下个世纪美国的安全和伟大是必需的。在“美国新世纪计划”的章程上签字的有25人,其中有7人后来成为小布什政府的重要成员,他们是迪克·切尼(Dick Cheney)、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I.刘易斯·利比(I.Lewis Libby)、扎尔迈·哈利勒扎德(Zalmay Khalilzad)、彼得·罗德曼(Peter Rodman)和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Elliott Abrams)。从1997年起的五年之后,他们将在实现“美国新世纪计划”中起关键作用。⑦
“美国新世纪计划”第一次肯定了《1992年国防计划指南》(The Defense Planning Guidance)草案中包含的思想。这是一个定期更新的五角大楼秘密政策文件,它概括美国军事战略,提供制定国防预算的框架。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草拟新的《国防安全指南》的任务被交给了当时负责拟订政策的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及其主要助手刘易斯·利比,他们是在老布什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的少数新保守派中的两人。他们在指南中主张用先发制人的手段阻止潜在的对手挑战美国的霸权,防止流氓国家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这个文件在草拟阶段就被透露给媒体,随即引起了轩然大波,迫使当时的国防部长切尼同意在定稿时降低原有观点的调门。该文件最后于1993年以《1993年地区防卫战略》(The Reg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1993)为题发表。⑧
另一个表达同样观点的报告是1996年的《彻底突破:保卫国土的新战略》(A Clean Break:A New Strategy for Securing the Realm),它是一份为即将上任的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准备的一份备忘录,它制定了一个可以迅速改变地区平衡使之有利于以色列的以色列中东战略,旨在使以色列摆脱“土地换和平”计划。它所建议的战略的第一个步骤是推翻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并用一个亲西方的政府来取代他。该文件是戴维·沃尔姆瑟(David Wurmser)起草的。他在2003年后期成为副总统切尼的中东顾问。这两个文件后来都受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围绕“美国新世纪计划”而出现的鹰派联盟的拥护。
1998年,“美国新世纪计划”⑨ 发表了两封关于伊拉克问题的公开信,一封是在1月给克林顿总统的公开信,另一封是在几个月后给国会领袖的公开信。两封信都论证说,对伊拉克的遏制政策既无效也不可能持久,“唯一的保护美国及其盟国不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的方法是采取将导致推翻萨达姆及其政权”的政策。这两封关于伊拉克的公开信成为一个新保守派领导要求改变美国外交政策的强大游说攻势的一部分,两名有权势的新保守派人物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和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这一攻势的结果是国会在当年10月通过了《伊拉克解放法》(The Iraq Liberation Act),它使伊拉克的“政权变更”成为美国的官方政策。⑩
2001年9月,在基地组织袭击美国仅9天之后,“美国新世纪计划”发表了一封给布什总统的公开信,倡议在他的“反恐战争”中采取一些步骤,敦促推翻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捕获或杀死”本·拉登。这封信被发表在《华盛顿时报》和《旗帜周刊》上。其建议也受到美国政治领袖的广泛支持。实际上,“美国新世纪计划”成员的头脑中还有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与实际的恐怖主义袭击没有关系的目标,就是要在伊拉克进行政权变更,“即使没有证据把伊拉克和(九一一)袭击直接联系在一起”。他们在给布什总统的信中还建议对伊朗和叙利亚采取“适当报复措施”,如果它们拒绝遵从美国切断对黎巴嫩真主党援助的要求,并建议华盛顿应当停止对巴勒斯坦临时机构的援助,除非它立即停止反以色列占领的持续行动;他们还呼吁大量增加国防开支来进行反恐战争。在这封信的签名者中,引人注目的是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詹姆斯·伍尔西(James Woolsey)。支持这一计划的是40名有影响的政策精英和公众人物。他们大多属于新保守派,但也包括一名基督教右翼领袖、右翼民族主义者,以及一些民主党人士,后者支持以色列,并主张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和对外干预。(11)
2002年4月3日,“美国新世纪计划”又发表了一封在很大程度上关于巴以冲突的信。该组织的负责人威廉·克里斯托尔征集了34名权势人物的签名,包括五角大楼“国防政策委员会”的成员。这封信敦促布什断绝同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的联系,再次号召“推翻萨达姆的政权”,对以色列着手进行的清除威胁以色列市民生命的恐怖主义网络的行动给予全力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布什总统与新保守主义观点的一致并不是随着布什的上台而开始的。事实上,在2000年大选前,新保守主义者们并没有看好布什。那时,“美国新世纪计划”发表了《重建美国的防卫》(Rebuilding America’s Defenses)的文章,编辑了题为《当前的危险》(Present Danger)的著作,旨在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拟订一个外交政策纲领。然而,布什当时并没有接受新保守主义对美国全球作用的看法,他在1999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一种独特的美国国际主义”代表了处理国际事务的平衡方法,强调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诸种手段的结合。(12) 布什还提到:“军事力量不是实力的最终措施。”他也很少谈到威尔逊主义的外交政策目标,而且他针对克林顿总统的人道主义干预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我认为我们的军队不应当被用于国家建设,而应当被用于战斗和赢得战争,”(13) 并强调,美国应当是“谦卑的”全球力量。这些都与新保守主义的核心信条“仁慈的霸权”、“政权变更”和单纯依赖军事力量不一致。为此,当布什赢得初选后,新保守主义者非常失望。威廉·克里斯托尔甚至表示,“我们对布什是一个注重外交政策的总统不抱大的希望。”(14) 同样,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政策主张在布什竞选期间和当选后的最初几个月中没有在其政策上留下任何印记。但是,这些新保守主义者并没有放弃寻找接近布什政府通道的机会,仍然期待着他们的观点最终能够被白宫采纳。
九一一为新保守派把其思想变为实际政策提供了一个契机。他们比政府中的任何其他人都为九一一后的美国对外战略做了充分的准备,正如一个同情新保守主义者的观察家所说,九一一“使这个国家围绕着他们(新保守主义者)关于世界的看法团结起来。”连新保守主义者都认为,九一一后布什总统及其顾问主动地接受了新保守主义观点。虽然鲍威尔和其他现实主义者在危机处理中占了上风,但是九一一改变了权力平衡,使鹰派取得了明显优势。
随着反恐战争在阿富汗展开,布什把其世界战略的目标扩大到超出了摧毁塔利班的任务。在2002年6月1日西点军校的毕业典礼上,他提到后冷战世界的新特征是恐怖主义的存在。此时,“对自由的最严重的威胁在于激进主义和技术处在危险的十字路口。”在这个世界上,“甚至连最弱小的国家和小集团也可以获得灾难性的权力来打击大国。”虽然冷战时期的威慑和遏制战略在某些情况下仍然适用,但“新的威胁要求新的思想”。他迂回地提到了先发制人的政策,强调“反恐战争将不会在防卫的基础上获胜”,并重申“这个国家将行动起来。”(15)
2002年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主张恰恰是布什在其竞选演说和辩论中所反对的,但与新保守主义者在之前的10年中所倡导的观点完全一致。先发制人的政策在这个报告中被正式确定为布什政府的政策。一位新保守主义者把《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描述为包含了“新保守主义精髓的文件”。新保守主义者马克斯·布特(Max Boot)认为,九一一事件使布什意识到美国不再承受得起“谦卑”的外交政策,意识到美国需要追求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采取促进民主的积极行动,并采用先发制人的方法来打击恐怖主义。因此,《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一个典型的新保守主义文件。(16)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具有的革命性是它把先发制人的传统观念扩大到等同于预防性战争。根据约翰·刘易斯·加迪斯的解释,先发制人是指粉碎迫在眉睫的进攻而采取的军事行动;预防性战争则是指对一个可能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制造战争危险的国家发动战争。而布什政府却把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它实际上是用先发制人这个概念来为在伊拉克的预防性战争辩护。这意味着在一个恐怖主义被核武器武装起来的时代,先发制人和预防性战争之间的区别已经不复存在。(17)
九一一袭击发生一年后,随着2002年9月布什的第一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问世,《国防计划指南》的关键概念成为美国的官方政策,包括政府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努力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流氓国家”上,这一点在布什2002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也曾被重复过,当时他宣布伊拉克、伊朗和北朝鲜是“邪恶轴心国”。这样,当小布什总统寻找一个应对新威胁的新方法时,新保守主义思想为他提供了一个现成的选择。
二 “新保守主义”成为布什外交政策的途径
布什总统本人并不是一名新保守主义者,那么新保守主义的主张是通过什么途径而成为政府政策?
一个答案可以是,布什班子中的重要成员是新保守主义者。但这并不是事实。虽然布什政府中的一些主要人物积极支持发动伊拉克战争,例如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副总统迪克·切尼,但是他们也都不是新保守主义者,(18) 或许可以把他们称为“侵略性的民族主义者”,或按照斯蒂芬·哈尔珀(Stefan Halper)和乔纳森·克拉克(Jonathan Clarke)两位作者的看法,是“美国民族主义者”。这些美国民族主义者与新保守主义者之间有着长期的密切联系,他们的关系可以追溯到福特政府时期。他们由衷地接受与新保守主义者相一致的思想——美国例外论和单边主义。(19) 根据对布什政府内部情况消息灵通人士詹姆斯·洛伯(James Lobe)和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的看法,在布什政府内部和外部存在着一个鹰派的联盟,它由三部分人组成:新保守主义者、侵略性的民族主义者和基督教右翼。这个鹰派联盟在九一一之后立即帮助建立了美国外交政策路线,而这个路线是以新保守主义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倡议的外交政策为蓝本的。作为“美国民族主义者”的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的支持对于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在外交政策领域里的推进起了关键作用。他们两人都在1996年“美国新世纪计划”的“原则声明”上签了字,拉姆斯菲尔德还在1998年1月“美国新世纪计划”给克林顿的公开信上签字,要求推翻萨达姆;而切尼则像新保守主义者一样厌恶国际组织,认为它们侵犯了美国的主权。正是在他们的支持下,新保守主义的计划才得以实施。
在切尼的建议下,拉姆斯菲尔德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同样,是切尼敦促提名新保守主义者沃尔福威茨而不是国务卿鲍威尔推荐的候选人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担任国防部副部长。虽然新保守主义者提供了实质性的政策计划,但他们极大地依赖于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来操纵决策过程。作为国家安全顾问的康多莉扎·赖斯未能确保传统的跨机构决策过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做出的决定常常被五角大楼所绕过或忽略。结果,国务院常常发现它自己被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领导的“阴谋小集团”(cabal)边缘化了,后者得到了一些主要的新保守主义者如负责政策的助理国防部长道格拉斯·菲斯(Douglas Feith)、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和副总统的办公室主任刘易斯·利比的支持和咨询。(20)
小布什就职后的第一个月,作为外交政策的新手,他最终将听取谁的意见?是其父亲老布什所欣赏的鲍威尔和赖斯所领导的现实主义者,还是鹰派拉姆斯菲尔德、切尼及其主要的新保守主义顾问?政府内部的深刻分裂很快变得十分明显。2001年3月当韩国总统金大中访问美国时,布什公开表示不赞同鲍威尔支持金大中的朝鲜半岛“阳光政策”,也不赞同克林顿1994年提出的处理朝核问题的政策框架。不过,此时小布什总统的对华政策也被新保守主义者批评为绥靖政策,克里斯托尔和卡根在《旗帜周刊》发表文章,谴责撞机事件是一个“民族耻辱”,认为鲍威尔领导下的缓和危机的外交努力是投降之举,将带来严重后果。
九一一事件还被政府内的鹰派建议用来作为改变中东政策的跳板。在恐怖袭击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内,根据一个解密的笔记,拉姆斯菲尔德对其一名助手建议,九一一事件应当被用来为推翻萨达姆辩护。然而,在入侵伊拉克问题上呼声最高的人是沃尔福威茨。当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并占领了伊拉克之后,威廉·克里斯托尔在2003年5月的《旗帜周刊》中写到:“解放伊拉克对于中东的未来是第一个伟大的战斗”。新保守主义者们欢欣鼓舞,他们感到自己的计划不仅成为官方政策,而且“美国新世纪”正在成为现实,他们看到,“现在美国是强大的,它像强大的国家一样行动。”(21) 到2003年5月,当伊拉克的叛乱开始加剧时,新保守主义达到了其权力的顶峰,而鲍威尔和布什政府内的现实主义者则被边缘化了,赖斯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三 新保守主义的起源和基本观念
新保守主义很大程度上源自于犹太知识分子组成的群体。这些人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和40年代进入了纽约城市学院。他们之中的最重要的人物包括: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西蒙·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菲利普·塞尔兹尼克(Phillip Selznick)、内森·盖尔泽(Nathan Galzer)、丹尼尔·布罗德卡斯汀(Daniel Broadcasting)等。所有这些人都出生于工人阶级,是外来移民,而且他们之所以进入纽约城市大学,是因为像哥伦比亚和哈佛大学这样的精英学府在很大程度上对他们关闭了大门。他们在校学习期间,都追随左派政治,崇拜托洛茨基。但是,这个群体中几乎所有的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都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成为了反共主义者,但他们完全不同于美国传统右派的反共主义者。传统右派反对共产主义是因为共产主义是无神论的,与一个敌对国家——苏联联系在一起,而且反对自由市场制度。反共产主义的左派同情共产主义的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不过到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他们开始认识到现实的共产主义(即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与他们理想中的完全不同,已经变成了一个从良好意愿出发的可怕怪物。福山把这种反共主义称为“自由主义的反共主义”。理解这一自由主义的反共主义的起源是理解新保守主义的关键。例如第一代著名的新保守主义者欧文·克里斯托尔最初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和托洛茨基主义者。在60年代新左派运动之后进行的反思中,他完成了转变并开始与企业界和保守主义阵营建立了联系。克里斯托尔在许多这类新保守主义者中很有代表性,因此,人们一般认为,美国新保守主义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
这些纽约知识分子的政治活动在40年代和50年代初是围绕着《党派政治评论》(Partisan Review)和《评论》(Commentary)展开的。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担任后者的主编。冷战日益加剧和麦卡锡主义盛行背景下的辩论,导致更多左派的背叛和新保守主义阵营的壮大。《评论》杂志也在向右转,成为新保守主义的主要思想阵地。
新保守主义思想的第二个潮流是围绕着《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杂志成长起来的,这是由欧文·克里斯托尔和丹尼尔·贝尔于1965年创办的杂志,目的是同新左派进行论战。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新左派在民权运动中和越南战争期间兴起。这些新左派人士同情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也想要仿效欧洲的福利国家,消除社会不平等,此时也是美国政府开展“向贫困开战”和追求“伟大社会”的时期。但《公共利益》的作者不断抨击“伟大社会”,认为追求社会公正的努力可能导致比原先更糟糕的结果,因为它扰乱了有机的社会关系,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公共利益》的抨击为以后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社会政策右转奠定了基础。以后,欧文·克里斯托尔又建立了一个关注外交政策的杂志《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于是从《公共利益》开始的对国内政策的批评,扩大到了外交政策方面。(22)
新保守主义者马克斯·布特认为上述描述对解释欧文·克里斯托尔等人的思想形成是适用的,后者曾把新保守主义者定义为“受到现实打击”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曾赞成福利政策、种族平等及许多其他自由主义的信条,但是他们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向右转,因为当时美国的犯罪率在增加,苏联在冷战中不断扩张,而民主党的左翼在这两个方面都不愿采取强硬立场。(23) 但布特认为,大多数新保守主义者,如前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特(Keane Kirkpatrick),是鹰派的民主党人,他们在民主党20世纪70年代继续左转时发生了思想转变。
布特还指出,另一些新保守主义者,如理查德·珀尔,起初是围绕着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Henry “Scoop” Jackson)聚集在一起的,后者领导了反尼克松—福特的对苏缓和政策的运动。70年代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导致新保守主义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当以尼克松—基辛格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者主导美国的外交政策,推动同苏联的缓和时,围绕着杰克逊参议员形成了一个民主多数联盟(Coalition for Democratic Majority),这个联盟直接挑战已经影响了大部分民主党人的孤立主义。其成员认为,美国的自身利益与人类的利益并非是不和谐一致的。他们声称,如果积极利用美国的权力,世界可以变得更美好。为此,他们主张理想主义的和国际主义的外交政策。
这些新保守主义者被劳伦斯·F.卡普兰(Lawrence F.Kaplan)和威廉·克里斯托尔称为独特的“美国国际主义者”。他们拒绝接受越南战争的教训,拒绝承认美国权力和责任的有限性,要求坚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杜鲁门总统开创的独特的美国国际主义的外交政策传统,或称之为自由主义的反共主义,把美国看作是“世界上争取善的最强大的力量之一”。他们认为苏联是美国面临的真正危险,而美国有能力应付它。在他们的眼中,从尼克松政府到卡特政府所坚持的国际战略是:由于美国人没有能力坚持对苏联的制度进行严重挑战,美国应尽力与苏联和平共处;参加与苏联的军备竞赛将导致破产或与苏联的大决战;挑战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观念,声明它是恶魔和非法的,是唐吉柯德式的愚蠢行为。“当美国国际主义者挑战这一共识时,当他们批评缓和核武器控制并号召发展军备和对苏联共产主义进行广泛的核战略进攻时,他们的建议大体上受到了忽略,被看作是天真的或鲁莽的”,只有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解体可以证明他们的建议是正确的。(24)
这一“独特的美国国际主义”传统也是新保守主义的组成部分,其观点在以后的15年间在政府中一直得不到回响,直到1980年上台的里根总统接受了它的观点。里根坚信冷战中的决定因素将“不是炸弹和火箭,而是对意志和思想的检验。”美国将帮助其他国家“培育民主的基础”。里根大力发展军备,并提出通过在全世界支持反共产主义的反叛来“击退”苏联。为了在民主国家中帮助实现“政治自由”,他批准建立了像全国民主基金会这样的半政府组织。他把苏联说成是一个“邪恶帝国”,认为只有通过改变美国对手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平衡”或与之“交往”,才能确保美国和世界更为安全。更重要的是,他开始公开和频繁地谈论美国的世界使命。(25) 这样,从里根起,新保守主义者可能依靠总统作为其事业的载体。
鉴于左翼反共主义运动的根源,新保守主义者大都反对20世纪70年代基辛格所代表的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正如国际关系理论所定义的,现实主义是从下述前提出发的:所有国家,无论其政治制度如何,都为权力而斗争。现实主义者总的来说不相信民主制是未来政府的普遍形式,也不相信构成自由民主制基础的人类价值一定优于那些构成非民主社会基础的人类价值,他们不断警告那些进行圣战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行动可能由于导致不稳定而造成严重危险。基辛格试图寻求同苏联的缓和,实际上这反映了他认为苏联是世界事务的一个永久组织部分的看法。(26)
此外,大多数较年轻的新保守主义运动的成员,包括一些新保守主义者的后代,如《旗帜周刊》的编辑威廉·克里斯托尔(他是新保守主义的奠基人欧文·克里斯托尔的儿子)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K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资深研究员罗伯特·卡根从来没有经历过从左派右转的过程。
一般来说,大多数新保守主义者选择了共和党阵营,虽然有些持新保守主义观点的人仍然把自己看作是民主党人,一些民主党中的“新自由主义者”在外交政策方面也带有相当多的新保守主义观点。(27)
一些媒体记者简单地把新保守主义者等同于追求以色列利益的犹太人,他们不仅指向克里斯托尔、卡根,而且特别集中在例如帕尔、沃尔福威茨、埃利奥特·科恩(Elliot Cohen)和其他明显带有犹太姓氏的人。他们把一些新保守主义者同以色列利库德集团之间的联系作为证据,指出新保守主义者对中东的强硬政策出自于他们想要创造一个对以色列安全的中东的动机。这种看法遭到了一些反驳,包括来自新保守主义者本身的反驳。反驳者的理由是,新保守主义者不仅同利库德集团,而且同英国的托利党和世界上的其他保守党都有联系,正如民主党类型的英国工党和以色列工党有联系一样。这一联系反应了意识形态,而不是种族上的相同。虽然许多新保守主义者是犹太人,但也有许多不是,如前里根和布什政府的教育部长比尔·贝内特(Bill Bennett),前中央情报局主任詹姆斯·伍尔西、社会科学家詹姆斯·Q.威森(James Q.Wison)、神学家迈克尔·诺瓦克(Michael Novak)和珍妮·柯克帕特里克都不是犹太教的信仰者。虽然他们都像犹太新保守主义者一样承担对以色列防卫的责任,但这不是建立在共同的宗教和种族上,而是建立在自由民主的价值上。反驳的意见还认为,无论美国人的信仰如何,以色列已经赢得了他们之中大多数人的支持,因为它是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而且它的敌人也声明自己是美国的敌人,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伊朗和叙利亚)。(28)
的确,如果新保守主义者的视角确实像一些人所说的,仅局限于中东地区,他们仅盯住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特别是如果他们还带有犹太人的姓氏,那么还可以说他们只是追求以色列利益的犹太人。但是,新保守主义者在20世纪80年代是在尼加拉瓜、波兰和南朝鲜实现民主化方面的主要支持者,90年代是干涉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最热情的斗士,其使命是解救当地的穆斯林而不是犹太人,如今新保守主义者想要在中国促进民主化,而且反对苏丹对基督徒的虐待。此外,新保守主义者最大的关注是如何追求美国的“仁慈的帝国霸权”。这些都表明新保守主义者的目光并非只是集中在中东和以色列,而是出自更广泛的对世界和美国作用的看法。
四 新保守主义包含的美国基本意识形态
虽然新保守主义并不是铁板一块,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是建立在一个一贯的思想核心的基础之上。福山指出,正是知识潮流的汇合导致了新保守主义的思想界限不分明。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越来越难以区分新保守主义和其他更为传统的美国保守主义,包括主张减少政府干预的自由意志论、宗教保守主义、社会保守主义和美国民族主义者。甚至分辨谁有资格作新保守主义者都变得十分困难了。福山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新保守主义的许多思想被主流保守主义者接受了,而且甚至被更广泛的美国公众接受了。另一个原因是,许多新保守主义者开始接受传统保守主义者在国内政策上的立场,例如市场资本主义。到20世纪90年代,他们与传统保守主义的趋同扩大到文化和宗教领域。(29)
新保守主义者之间在外交政策上也缺乏一致性,这在冷战结束以后变得更为明显。此时外交政策上的共同基础消失了,他们之间开始辩论什么是真正的美国国家利益。在1990年代,新保守主义者对促进民主和人权在多大程度上应当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美国应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世界事务方面并没有共识。在一些重大外交政策问题上,例如中美关系、北约东扩和是否对巴尔干地区进行干预等,他们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尽管如此,福山认为还是可以提炼出新保守主义所信奉的四个基本原则,这些原则能够解释新保守主义者所采取的政策立场,并把新保守主义者与其他关于外交政策的思想流派区分开来。这些原则也可以说是对新保守主义的界定:
1.新保守主义者一贯持有的观点是:政权的性质对于对外行为是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必然反映自由民主社会最基本的价值。
2.相信美国的权力曾经而且能够被运用于道德目的,美国需要继续参与国际事务。作为世界上的主导国家,美国在安全领域里负有特殊的责任。
3.反对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大规模干预,认为它会带来不良后果。
4.怀疑国际法和国际体制的合法性及其实现安全和公正的效率。新保守主义者是国际体制的强烈批评者,认为联合国不能有效地充当仲裁人或国际公正的强制执行者。(30)
现在世界上大多数人所理解的新保守主义实际上是新一代的新保守主义者威廉·克里斯托尔和罗伯特·卡根等人重新定义过的,他们所主张的外交政策也因此成为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的标志。克里斯托尔和卡根首先在《旗帜周刊》上为这种政策辩护,并在他们1996年为《外交事务》杂志撰写的文章《走向里根主义外交政策》和《当前的危险》(后来在2000年被扩大为一本书出版)中,首次系统地定义了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政策。他们在这些文章中同另一名著名的新保守主义者、里根政府的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进行辩论,后者提出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应回到“正常状态”,而他们则号召建立美国领导下的“仁慈的霸权”。他们主张的政策是,美国应抵制正在兴起的专制者和敌视的意识形态,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削弱它们的基础;追求美国的利益和自由民主的原则;并对那些正在同反人类的恶魔进行斗争的人提供援助。他们明确地为政权变更辩护,并把它当作其新里根政策的核心组成部分。他们断言,在长时期内只有通过民主化才能确保那些国家与美国利益的趋同。(31) 此外,克里斯托尔和卡根等人所代表的1990年代新保守主义另一个特点是,他们一般对经济学和国家发展缺乏兴趣,他们总的来说关心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他们提出了相对较少的关于全球化、竞争、发展和其他问题的有特色的观点。(32) 这种新保守主义被布特称之为“强硬的威尔逊主义”。
如果威尔逊主义意味着相信美国外交政策应当促进美国的理想和价值观念,而不是像权力政治的信奉者所认为的那样,仅促进狭窄定义的国家利益,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威尔逊主义”。但是,新保守主义者在另一方面又对威尔逊本人缺乏认同,认为他过于天真。新保守主义者之所以被看作“强硬的”威尔逊主义者,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信念建立在权力上,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是西奥多·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哈里·杜鲁门和罗纳德·里根这样一些运用权力来追求更高目标的美国总统。他们认为,美国应当使用武力来为理想和利益而战,不仅出于人道主义,而且也是为了通过促进自由民主而促进美国的安全。(33) 与自由主义的威尔逊主义者不同,他们不是为了民主和人权本身的缘故来促进民主。确切地说,促进民主对于新保守主义者来说意味着支持美国的安全和进一步提高美国的世界地位,促进民主与美国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34)
像大多数保守主义者一样,新保守主义者对联合国抱有很大的怀疑。克里斯托尔和卡根所提出的新里根主义外交政策虽然也被描述为是威尔逊主义的,但它是“威尔逊主义减去国际体制”。(35) 威尔逊本人寻求通过在国际联盟基础之上创立自由的国际法律秩序来建立民主与和平。罗斯福和杜鲁门建立联合国的努力使这一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传统继续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这一传统在无论老的还是新的保守主义的日程上都缺失了。他们强调用三个工具来代替国际体制以发挥美国的影响:压倒性的军事优势;重新对美国的同盟做出贡献;把导弹防御当作一个保护美国本土不受反击打击的手段。(36)
新保守主义者追求美国仁慈的霸权。根据这一政策,美国将运用其权力来创建一个仁慈、和平和民主的世界秩序。关于美国需要在冷战后建立霸权来保障全球秩序和安全的最早看法之一来自于查尔斯·克劳塞默(Charles Krauthammer),他在冷战结束后即提出,美国面临着一个“单极时刻”,而且“单极时刻”延长成为了一个时代。此时,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挑战美国的霸权,因为美国与其他所有国家之间存在着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权力差别。这造成了一个现代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国际结构。克劳塞默还辩驳说,美国不像其他大国那样寻求帝国,它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强制、维持和扩大和平来维持当前国际制度的稳定。(37)
关于新保守主义的核心思想,需要强调的是,它“深深地真正根植于美国的各种传统之中”。(38) 新保守主义同保守主义一样,信奉美国两个基本意识形态:美国例外论和古典自由主义。
新保守主义关于美国“仁慈的霸权”的概念来自于“美国例外论”。美国例外论是指:上帝选择了美利坚民族把它安置在北美这片新大陆上,并赋予了它特殊的使命:在这里建立一个自由和民主的样板;美国因此成为一座“山巅之城”,是世界各国的榜样。美利坚民族还由此肩负着上帝所委托的把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和民主制度推广到全世界的使命。美国政治学教授戴维·福赛斯(David Forthes)指出,美国例外论包含了下述观念:“美国人组成了一个异常优秀和伟大的民族;他们首先代表了对个人主义和自由的信奉:他们建立在个人自由主义的理念基础上的社会和国家,树立了值得向世界其他地方输出的榜样。”(39) 因为美国在道德和精神上是例外和特殊的,所以美国的霸权可以是与众不同,可以是仁慈的。
“仁慈的霸权”的说法最初来源于创建和拥有《时代》、《财富》和《生活》三大杂志、从而对美国舆论产生过极大影响力的亨利·卢斯(Henry Luce)。卢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曾在《时代》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把20世纪称为“美国世纪”。他通过美国例外论的视角来观察美国外交政策,相信上帝选择了美国来担负特殊的使命。在他看来,在20世纪,美国是范围不断扩大的事业领域的中心,是上帝的人类熟练仆人的训练场所,是虔信上帝的乐善好施者;美国所给予的多于所接受的,美国是自由和正义理想的源泉,“在只有美国知道什么对于其他民族是最好的前提下,美国将作为仁慈的霸权,或父亲般的权威来发挥作用。”(40) 他敦促美国出于责任和利用美国安排国际事务的自然权利来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历史上,“美国例外论”指导了美国的大陆扩张和海外扩张。美国从一个大陆国家转变为一个全球国家的同时也带来了例外论思想的变化。当美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时,美国的使命感同其取得世界霸权的驱动力开始结合到了一起,导致它的外交更加频繁地显示出圣战精神,这反映出美国人的一种信念:不仅美国的自由价值和民主制度具有普遍的意义,而且美国在20世纪的世界头号地位也使它具有了在世界各地保护自由和推行民主制度的责任和实力。
新保守主义者所赞赏的代表了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威尔逊主义正体现了美国例外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像他的前辈一样,怀有坚定的美国例外论信念。在他之前美国的政治家们,如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外交家之一、美国的第六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出于对美国安全的顾虑曾告诫美国人说:“不要到海外去寻找恶魔来消灭”,(41) 如果美国这样做,就将失去自己的灵魂,但威尔逊把这种说法颠倒了过来,他的观点是:如果美国不走出海外去消灭恶魔,就将失去自己的灵魂。威尔逊的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为美国介入世界事务建立了一个道德依据。他要求国会对德国宣战,从而使美国卷入了发生在欧洲的战争,这在以前对于美国是不可思议的。他在这样做时并没有论证说,由于德国危及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战争是必要的,而是说,美国必须参战,因为“必须建造一个对于民主社会来说安全的世界。”(42) 威尔逊把“拯救者民族”的使命理解为促进建立在民族自决、正义和和平之上的世界秩序。
新保守主义者对亚当斯告诫的回答是,为什么要让恶魔逍遥法外?为什么美国不应走出国外寻找恶魔来消灭?对于1823年来说是明智的选择,在今天已不再适用。那时美国是赢弱的、孤立于欧洲巨人世界的国家,而现在美国已成长为巨人。美国已经有能力摧毁世界上的许多恶魔,而且美国负有维持国际秩序、和平和安全的责任,在山巅之城中通过树立榜样来领导世界的政策,是怯懦的和令人丢脸的政策。(43)
至于新保守主义同古典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首先必须说明保守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嫡亲关系。在美国,“自由主义”这个词直到进步主义时代才被普遍用于政治领域,它在20世纪初代表的是进步主义。(44) 这是因为作为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欧洲意义上的保守主义传统在美国是不存在的。变化发生在罗斯福新政时期,新政的实质就是要使政府在经济方面的作用从“一只看不见的手”转变为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以刺激总需求,扩大就业,防止经济危机。新政因此是一次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改革,它把美国人的心目中的自由概念从摆脱政府干预的消极自由,扩大到包括依赖政府来获得某些社会和经济权利的积极自由。罗斯福总统1941年在国情咨文中提出的“四大自由”,既是对自由概念本身的扩大,也是扩大政府职能的要求。也正是在新政时期,古典自由主义开始被贴上保守主义的标签,虽然古典自由主义者最初并不接受这样的称呼。无论是新政的支持者还是新政的反对者都自称为自由主义者,但以新政为转折点,美国政治中开始形成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分野,他们分别为民主党和共和党所信奉。然而事实上,美国的保守主义维护的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而不是欧洲意义上的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相对立的保守主义。(45) 新保守主义者也像传统保守主义者一样,反感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和社会,不过他们是从不同的途径接近古典自由主义的。正如上文所讨论的,他们并不反对追求社会公正与平等的动机,而是认为这种努力可能导致更为不幸的后果,不仅如此,许多新保守主义者已经开始接受传统保守主义者的市场资本主义的观念。
美国例外论和古典自由主义是美国的两个最基本的意识形态。它们同美国外交政策的关系是,美国例外论要求美国人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推广到全世界,而它所要推广的就是以古典自由主义为标志的价值观念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民主政治制度。古典自由主义是美国立国的基础,它不仅体现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也指导着美国的国内政策;而美国例外论则是美国外交政策特征的重要决定因素,它用美国独特的方式使古典自由主义与美国的外交政策衔接在一起。
一般来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民主党的国内政策倾向于自由主义,共和党倾向于保守主义;而自威尔逊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把理想主义运用于美国的外交政策起,民主党的外交政策一般倾向于理想主义,共和党倾向于现实主义。但这并不是绝对的。实际上,自里根政府以来,越来越难以仅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来划分美国的外交政策。
威尔逊主义的理想主义外交政策最重要的特点是,运用美国的力量来建造一个能够保障民主国家安全的世界。众所周知,里根在内外政策上是一名保守主义者,确切地说,是新保守主义者,但是正如托尼·史密斯在其著作《美国的使命:美国与20世纪世界范围内争取民主的斗争》(America’s Mission: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wid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中所说,里根在其抵制苏联共产主义的圣战中是推行威尔逊主义的最好典范。连基辛格也赞同里根外交政策中体现的威尔逊使命。他承认,在外交中,“像伍德罗·威尔逊一样,里根懂得,美国人民在其整个历史上循着美国例外论的鼓声前进,他们将在历史理想,而不是地缘政治的分析中,找到最终的激励。……像威尔逊一样,里根更切实把握住了美国灵魂的作用,威尔逊的遗产为里根的为民主而战的全球圣战提供了意识形态方向”。(46)
由此可见,采纳了新保守主义的“布什主义”深深扎根于美国基本的意识形态之中。认为小布什总统外交政策的理论根基回复到了当代威尔逊主义,这种看法在美国不乏其人。九一一恐怖主义袭击之后,布什总统及其主要政府官员的政策声明都包含一个核心理念:总统及其政府是上帝指派来用他们的意识形态重新塑造世界的,这意味着布什将选择运用军事和经济力量来使世界摆脱“邪恶轴心”。布什赞同威尔逊的看法:只有一个民主的世界才是安全的世界,并想要运用美国的武力来建造这样一个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什的外交理念也被看作与威尔逊主义息息相通。
于是在这里看到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部分重合,这种情况的发生恰恰是因为新保守主义者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发生了变化。当把国家利益定义为,为了保护美国的安全,必须在全世界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和民主制度时,理想主义的(追求道德、理想的)外交政策同现实主义(追求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在重要的方面就重合起来,所剩下的差别更多的是追求目标手段上的差别,例如是通过多边主义、集体安全,还是通过单边主义,自行其是。
五 结论:“布什主义”与新保守主义共兴衰
当新保守主义对布什外交政策的影响在伊拉克战争前后达到顶峰时,其影响实际上就离衰落不远了。衰落的直接原因是在伊拉克的叛乱日益加剧。到2004年后期,已经变得很清楚的是,布什政府发动战争的理由是没有根据的,美国不仅没有发现萨达姆和基地组织(更不用说九一一)之间的任何联系,也没有发现萨达姆已经掌握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可靠证据。到美国中期选举前夕,伊拉克战争以来已经有2800名美国士兵,120名英国士兵和数以万计的伊拉克人丧生,但美国仍然控制不了伊拉克的局势。此外,美国所期望的稳定的民主制并没有出现,相反,每天都有许多什叶派和逊尼派穆斯林、库尔德人和基督徒死于宗教仇杀或暴乱。许多人认为,目前伊拉克已经陷入“内战”状态。伊拉克的未来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担忧。
随着伊拉克的局势迟迟不见好转,布什政府内部的鹰派受到了重创,甚至连新保守主义的刊物《旗帜周刊》也转而批评拉姆斯菲尔德未能提供足够的军队来确保伊拉克当地的秩序,并要求他辞职。在布什政府2004年连任获胜后不久,沃尔福威茨、菲斯和利比相继离任。
在布什的第二任期,更多的现实主义者进入了政府,包括负责政策的副国务卿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国务卿赖斯的顾问菲利普·泽利科(Philip Zelikow),以及担任国家情报部门主任这一新位置、取代中央情报局长为总统作日常情况简介的约翰·内格罗蓬特(John Negroponte)。新任国务卿赖斯强调她的主要关注是修补破损的联盟,尤其是同欧洲的联盟,即使这意味着在从伊朗到北朝鲜问题上需要进行妥协。在布什的第二任期,由于人事变动,政府中鹰派和新保守主义者的网络已经被极大削弱,他们控制外交决策过程的能力也大大降低了。事实上,布什第二个任期的外交政策已经开始避免通过预防性战争来进行政权变更。由于美国军队被在伊拉克的持续战争搞得筋疲力尽,布什政府对它心目中的其他两个邪恶轴心国伊朗和北朝鲜发出了信号:它不打算使用军队来实现政权变更。布什政府已经近乎承认,它为伊拉克战争付出了巨大的政治代价;预防性战争不能成为美国战略的核心。(47) 美国在伊拉克的困境使新保守主义名誉扫地,并使外交政策的现实主义者逐渐恢复了他们的权威。
尽管新保守主义者遭到这些打击,但由于切尼仍然是新保守主义纲领的保护人,无论是在政府内部还是在政府之外,新保守主义者在过去的两年中仍然是一个权力因素。(48) 虽然他们在五角大楼中的资深官员的数量减少了,而且现实主义者已在推动政府与美国视为敌人的国家采取交往政策,鹰派仍然可以保持着限制现实主义者活动余地的能力,并能有效地阻止政策方面的实质变化。
2006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出人意料的胜利再次引起关键的人事变动。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被迫辞职,其职位被现实主义者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所接任,这是新保守主义集团的重大损失,也使政府内部的力量平衡最终倒向了现实主义一边。此外,老布什政府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被国会任命为跨党派“伊拉克研究小组”(Iraq Study Group)组长,这个小组在2006年12月初发表了《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报告》,该报告等于公开承认了美国伊拉克战争的失败,它建议美国于2008年初从伊拉克撤军;在中东问题上与伊朗和叙利亚和解。而对于布什政府内尚存的鹰派来说,在失去了拉姆斯菲尔德和利比这样的左右手之后,副总统切尼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立。
2005年9月当新保守主义者聚集在一起欢庆《旗帜周刊》创刊10周年时,他们为10年前备受冷落的新保守主义如今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指导着政府的政策而喜形于色。但是,他们未曾料到,不久他们便会遭遇政治上的滑铁卢。“布什主义”的命运显然不如20多年前同样以新保守主义为基础的里根主义。关于后者,许多美国人至今仍然津津乐道于它以不战而胜摧垮了苏联共产主义这个冷战对手,而如今“布什主义”却似乎已经穷途末路。
“布什主义”及其新保守主义的理念所存在的问题使得它的破产成为不可避免的。“布什主义”本身的问题首先涉及伊拉克战争后国际上不断提出关于美国发动战争的合法性问题,提出的问题方式包括:即使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是否有权发动预防性战争?美国是否有权通过武力来推翻一个政权,“给那里的人民带来自由”?未经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入侵另一个国家是否合法?这些问题在国际上得到的回答大都是否定的。美国认为自己有权侵入其他国家,创造防止恐怖主义的政治条件,这就违反了现存的以尊重各国主权为前提的国际法体系。国际社会担心,美国的做法可能会造成一个蔑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先例,削弱国际社会在冷战后所期待的国际法和联合国的权威性,给未来的国际关系带来后患无穷的新问题。此外,如果美国有权采取预防性的军事行动,那么是否其他国家也有权这样做?对此美国是讳言的。
其次,布什政府把冷战后最危险的敌人看作是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流氓国家”和恐怖主义者,而且认为九一一恐怖袭击已经使预防性战争成为对敌人作战的一个必要手段,但是,布什政府至今并没有发现伊拉克发展和拥有这类武器的证据,这就很难为它在伊拉克进行的预防性战争辩护。
第三,布什政府把美国看作是“仁慈的霸权”,对美国是出于良好的动机在国际上采取行动深信不疑,认为自己入侵伊拉克是为了全球的公共利益,而不是狭隘的美国自身利益。但是它没有料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美国的“仁慈霸权”深恶痛绝,布什政府对国际组织和国际合作的轻蔑更加剧了国际上的反美情绪,甚至连其欧洲盟国都对其单边主义的做法深感不安。
最后一个重要问题是,美国认为自己应当而且有能力通过军事手段来实现一个国家的政权变更,并可以在此之后轻易地完成国家重建的复杂工作。但事实已经证明,由于复杂的宗教矛盾、民族特质及特殊的文化、传统和习俗,重建国家的工作的艰巨性要远远超出布什政府的想象。况且许多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已经证明,民主化的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密切的相关性,而且一个成功的民主化的动力必须来自一个国家的内部,来自于在经济发展中逐步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的要求,而不能从外部强加。因此促进民主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等待经济和政治条件的逐步成熟。
注释:
①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2) ,pp.4,5,19.
②John Lewis Gaddis,Surprise,Security,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 ,pp.17~18.
③Ibid.,pp.62~63.
④Ibid.,p.22.
⑤Francis Fukuyama,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Democracy,Power,and the Neoconservative Legacy( 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 and London,2006) ,pp.4,7.
⑥William Kristol and Robert Kargan," Toward a Neo-Reaganite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1996,Vol.75,pp.20,23.
⑦James Lobe and Michael Flyn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Neoconservatives" ,November 17,2006,Paper to a Conference on Midterm Election in Beijing on November 19,2006,p.8.
⑧Stefan Halper and Jonathan Clarke,America Alone,The Neo-Conservatives and the Global Order(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2004) ,p.33; James Lobe and Michael Flyn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Neoconservatives," pp.6~7.
⑨“美国新世纪”概念针对的是亨利·卢斯所提出的“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的观念。(见正文下文)“美国新世纪计划”意指要使21世纪成为一个新的美国的世纪。
⑩James Lobe and Michael Flyn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Neoconservatives," p.9.
(11)Ibid.,pp.1~2.
(12)Stefan Halper and Jonathan Clarke,American Alone,The Neo-Conservatives and the Global Order,pp.112~113.
(13)转引自Fukuyama,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Democracy,Power and the Neoconservative Legacy,p.46.
(14)Stefan Halper and Jonathan Clarke,America Alone,The Neo-Conservatives and the Global Order,p.112.
(15)Ibid.,p.140.
(16)Max Boot," Myths About Neoconservatism," in Irwin Stelzer,ed.,Neoconservatism( London:Atlantic Books,2004) ,p.45.
(17)John Lewis Gaddis," Grand Strategy in the Second Term," Foreign Affairs,Jan/Feb.2005,Vol.84,p.4.
(18)弗朗西斯·福山也持此看法,他认为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副总统切尼在进入布什政府之前都不是新保守主义者,而且他们的观点来源也不明了。见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Democracy,Power,and the Neoconservative Legacy,p.4.
(19)Stefan Halper and Jonathan Clarke,American Alone,The Neo-Conservatives and the Global Order,p.14.
(20)新保守主义者对“阴谋小集团”的称呼非常敏感,他们竭力否认这一点,参见Joshua Muravchik," The NeoConservative Cabal," Commentary,September 2003,pp.26~33; 关于这个小集团,还可见Jeffrey Steinberg," Neo-Conservative Cabal Under Mounting Attack," 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June 6,2003,http://www.larouchepub.com/other/2003/3022countercoup.html
(21)Stefan Halper and Johathan Clarke,American Alone,The Neo-Conservatives and the Global Order,p.31.
(22)关于新保守主义的起源可参见Murray Friedman,The Neoconservative Revolution,Jewish Intellectuals and the Shaping of Public Policy(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pp.117~136; Francis Fukuyama,America at Crossroads,The Neo-Conservatives and the Global Order,pp.15~20; Stefan Halper and Johathan Clarke,American Alone,The Neo-Conservatives and the Global Order,pp.40~73.
(23)Max Boot," Myths About Neoconservatism," Irwin Stelazer,Neoconservatism( London,Atlantic Books,2004) ,p.46.
(24)Lawrence F.Kaplan and William Kristol,The War over Iraq,Saddam' s Tyranny and America' s Mission ( San Francisco,California,Encounter Books,2003) ,p.67.
(25)Ibid.,p.68.
(26)Francis Fukuyama,America at Crossroads,The Neo-Conservatives and the Global Order,p.37.
(27)Max Boot," Myths About Neconservatism," in Irwin Stelazer,Neoconservatism,pp.46~47.
(28)Ibid.,pp.47~48.
(29)Francis Fukuyama,America at Crossroads,The Neo-Conservatives and the Global Order,p.39.
(30)Ibid.,pp.6,48~49.
(31)Robert Kagan and William Kristol,eds.,Present Danger,Crisis and Opportunity in American Foreign and Defense Policy( San Francisco,California:Encounter Books,2000),pp.9~24.
(32)Francis Fukuyama,America at Crossroads,The Neo-Conservatives and the Global Order,p.43.
(33)Max Boot," Myths About Neconservatism," Irwin Stelazer,Neoconservatism,p.49.
(34)Robert Kagan," A Matter of Record," Foreign Affairs,Jan/Feb.2005,Vol.84,pp.170~173.
(35)Williams Kristol and Robert Kagan,Present Dangers:Crisis and Opportunity in American Foreign and Defense Policy,p.29; Francis Fukuyama,America at Crossroads,p.41.Williams Kristol and Robber Kagan," Toward a Neo-Reaganite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1996,Vol.75,pp.18~32.
(36)Robert Kagan," America' s Crisis of Legitimacy," 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2004,Vol.83,pp.65~87; Robert W.Tucker and David C.Hendrickson," The Sources of American Legitimacy," Foreign Affairs,Nov/Dec,2004,Vol.83,pp.21~23; and Robert Kagan," A Matter of Record," Foreign Affairs,Jan/Feb.2005,Vol.84,pp.170~173.
(37)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Revisited," The National Interest,Winter 2002,pp.5~20.
(38)Francis Fukuyama,America at Crossroads,The Neo-Conservatives and the Global Order,p.13.
(39)戴维·福赛斯:《美国外交政策与人权:理论的分析》,载于周琪主编:《人权与外交》,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109页。
(40)Siobban McEvoy-Levy,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nd US Foreign Policy,Public Diplomacy 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London:Palgrave,2001) ,p.28.
(41)Walter A McDougall,Promised Land,Crusader State ( 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97) ,p.15.亚当斯的外交政策路线体现了美国的现实主义外交传统。
(42)Lloyd E.Ambrosius,Wilsonianism; Woodrow Wilson and His Legacy i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 New York:Palgravfe MacMillan,2002) ,pp.8~9.
(43)William Kristol and Rober Kagan," Toward a Neo-Reaganite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1996,Vol.75,p.31.
(44)钱满素:《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
(45)同上,第64、195页。
(46)Lloyd E.Ambrosius,Wilsonianism:Woodrow Wilson and His Legacy i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2) ,p.180.
(47)Francis Fukuyama,America at Crossroads,The Neo-Conservatives and the Global Order,pp.182~183.
(48)约翰·汉纳(John Hannah)曾经是副总统办公室与亲美逊尼派人士、现任伊拉克副总理艾哈默德·查拉比 (Ahmad Chalabi)之间的联络人,利比离任之后被提升为切尼的国家安全顾问,而戴维·沃姆瑟(David Wurmser)仍然是切尼的中东政策顾问。同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埃利奥特·阿布拉姆(Elliott Abrams)主持中东处,他在这个职位上处理了2006年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