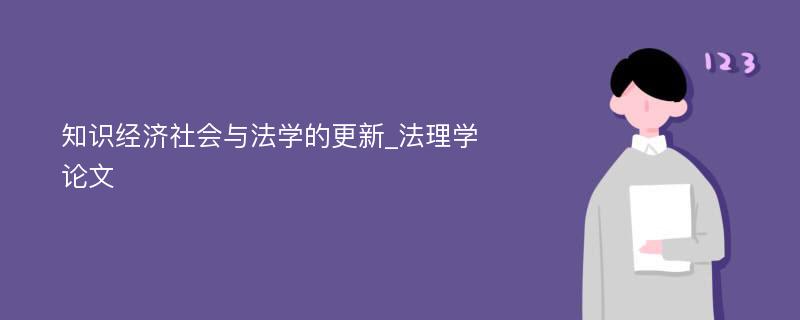
知识经济社会与法理学的更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理学论文,经济社会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对人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的整体法律现象进行研究的“法理学”,作为对本国各部门法学进行高度概括的“法理学”,因其知识结构和思维品质的特殊性,只能是工业革命的成果,而不可能是农业文明的产物。
16、17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和随之而来席卷欧洲的工业革命,催生了各种人文思想、启蒙学说和一浪接一浪的政治变革。凡是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在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时代变革中,在科学与人文的浓浓氛围中,诞生了法学的“法学”——法理学。自从科学意义上的现代法理学诞生后,整个法学和法律制度、人类法治秩序都被提升到了一个更为理性、更合乎人性、更具可预测性和效率性的阶段,成为工业社会法律发展必不可少的价值理念体系和理论支撑。法理学的诞生与工业社会分工程度提高,组织、制度资源的相对增加,人们自由选择的余地增大等,有密切关系;它是人类社会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全面发展的结果。
在知识社会即将取代工业社会而占据主导的21世纪,历时300 年的工业文明所催生的法理学,又将如何发展呢?
科学发展对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同一些学者指出:法的出现本身就是人们认识自然、社会及人类自身的科学的重大成果;法律观和法学理论受科学的制约,因而法的进步也受到科学的影响;科学知识丰富了法的内容和根据;法律方法论受科学的制约和影响;科学是法的重要的价值标准。
而在知识社会到来之际,科学对法的影响,包括对法理学及整个法学的影响,将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可以预见,知识社会人类社会、生产范式的变革,将引起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某些基本理论、基本内容、知识结构和研究方法等的重大变化。
一、由法律所确认的民主政治形式、立法与决策机制和公民民主权利等将发生重大变化;高科技将成为“制度创新”、法制改革的资源寻求之一。
知识社会高科技的发展,知识与信息的普及,网络和计算机革命,将逐步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社会范式的全球化、知识化、智能化和信息化,使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转变,物质型生产向非物质型生产转变,经济资本向知识资本转变,封闭性、地区性向开放性、全球性转变。这些转变将使法理学研究的工业社会的民主政治形式、决策机制、民主与法制关系,公民民主权利以及人权问题等发生变化。
(一)工业社会实现民主的基本形式将因高科技引导的知识社会到来受到严重挑战
普选制和代议制等民主形式,是伴随工业文明而发展起来的现代民主制度,由普选基础上产生的代议制(议会制和代表制等)被认为是工业社会里民众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最可行的形式。然而,资本主义议会的“金钱政治”特征,严重影响了议员代表民意行使权力的公正性和广泛代表性。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制也因体制不健全和社会各方面发展条件的制约,难以使选民真正行使对代表的监督罢免权,也难以使广大民众真实直接深入地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
而网络时代的到来,将使普选制和代议制等工业社会的民主政治形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意义逐渐淡化。民众不必完全通过工业社会的政治形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而可以通过网络,对他们关注的各种社会问题,从本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到全球性事务,进行“投票”、发表意见、参政议政。美国俄亥俄州的哥伦比亚市在20世纪90年代初便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电子市政厅”,使当地居民可以通过电子通讯系统参与地方政府政治会议的决策。人们只需在家中客厅按一下按钮,就能对有关决策进行表决。
这还只是知识社会初露端倪时较粗糙的简单的“网络政治”形式。但从这一端倪中可以想见,“网络”将为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自我代表与他人代表的结合,创造一种崭新的知识社会的民主形式开辟道路。
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进一步扩大直接民主的范围已势在必行,但究竟采用什么形式才能减少实施的社会成本?这确实是需要慎重考虑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扩大“制度创新”的资源寻求。而高科技的发展,网络的普及为这种资源寻求至少提供了一种启示。事实上,这已不是遥遥无期的事情,我们只要仔细分析“电子商务”从最初出现到现在遍及世界的过程,就可想象,“电子政务”、“电子立法”、“电子司法”等一系列由高科技引起的政治权力运作的新机制、新事务,在知识社会中都可能变为现实。而这不仅仅是民主实现的手段的某种改变,还将带来实质内容上的变革。对于人们感到失望的工业社会的普选制和议会制,无疑已受到了严重挑战。
(二)工业社会的立法与决策机制将发生变化。
第一,工业社会的立法与决策机制特点是权力的集中、划一,立法与决策信息反馈的缓慢和单一,“民众参与”在口头和实际上的严重脱节。这些都将由知识社会的到来发生变化。首先,知识社会的信息爆炸和知识爆炸,引起了政治权力系统的“决策爆炸”甚至“立法爆炸”(如现代一些国家的经济立法、社会立法大量涌现,虽说不像中国汉代时期法律“汗牛充栋”,但人们实际已很难掌握)。而任何高明的政治权力组织都只能处理一定数量的信息,解决部分社会问题,产生数量和质量都十分有限的决策和法律。知识社会的到来,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快速运转,使各种新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这必然将原来按部就班的政府体制推到“决策爆炸”和“立法爆炸”的临界点之外。为使政府抓最主要的问题,提高决策权和立法权的效率,转移部分立法权和决策权势属必然。
第二,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工业社会高度集中、整齐划一的立法与决策机制,是与大工业的社会化生产相适应的。尤其在一些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建立统一的工业布局,国家必须集中人力物力进行统一管理,才能有效发展经济。这就使得立法与决策的集权程度更高。而这种立法与决策机制在快速运转的知识社会中,往往会因地区行业的分散多样和纵向与横向信息周转的缓慢而变得效率极低,互相掣肘。生产的分权必然带来决策的分权,知识社会生产方式呈现出的非群体性、多样性、差异性、扩展性、分散性和个体性,必然要求立法权和决策权配置的改变,即这一权力“向上”与“向下”的转移。向上转移,是指主权国家的部分立法与决策权将转移到跨国层次上,如关于国际性、区域性金融危机的防范、违规金融行为的惩处,环保和生态平衡的立法、区域性战争的制止、网络的国际化管理、国际性犯罪等等的立法。向下转移,是指中央政治权力的部分立法和决策权将移至一国境内的地区、省、州或地区性、非地区性组织,使集权式立法与决策方式变为集权与分权并存,或向分权式转移。
(三)公民实际享有的权利自由将大大超出工业社会的范围。
知识社会公民实际享有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及公民的信息权、知情权、发表权等,在内容和实现途径上都将发生变化,其所享有权利的范围将大大超出工业社会的范围。网络时代,人们所享有的上述权利已远远超出工业时代的法律界定;国家强制系统对一些网络上明显违法或错误的言论,不得不采取讲道理,摆事实,以“平等”说服来争取大众的态度。我们只要仔细分析从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使馆被炸后,网络上关于如何看待北约轰炸,中美关系走向等问题的看法,就可看到知识社会的“自由”程度,已大大超出了国家政治权力的控制范围;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上也只能平等地发表意见。当然,这种权利自由事实上的扩展,也带来了法律的失控,并向国家法律提出了严峻挑战。
上述这些变化,必然影响到法理学所研究的民主与法制关系、人权理论等一些基本原理的发展。如民主是法制的源泉,在民主实现形式变化的情况下,法制如何确认这些民主形式呢?同时,民主实现形式的改变,对立法权、行政权等政治权力系统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这些,都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二、知识社会经济结构所引起的社会阶级、阶层变化,将直接影响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从而引起对“法律阶级意志性”等法学基本理论的新认识。
工业革命时期,马克思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财富生产方式出发,认为产业无产阶级与大工业流水线生产相联系,生产的社会化、群体化、规模化和规范化,使得他们最有组织性、纪律性、团结性和协调性;还由于他们在社会物质生产资料的占有上“一无所有”,因此他们具有“大公无私”的阶级品质。而这些农民阶级所没有的优点,使无产阶级成为工业社会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肩负着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建立在经济分析基础上对无产阶级阶级特性的分析,正是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出发点。无产阶级法律即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也是从这里出发的。
而知识社会中,物质形态的资本已不是主要的生产要素,知识——智能资本、人力资本正逐步取代经济资本;社会劳动的方式也从工业社会群体性有组织的大机器生产,变成了分散化、个体化、家庭化、流动式的非物质形态生产方式;知识产业正以一种“永恒的朝阳产业”姿态取代工业产业;白领阶层数量在一些国家已大大超过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蓝领(如美国在1955年就已出现了这一状况),知识阶层正逐步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或社会力量(对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很难说是从经济实证分析中得出的结论)。
知识社会的一个根本变化:不是谁与流水线大工业生产相联系谁最先进,而是谁掌握了这一时代最先进的知识和科技,谁最能开发“人”自身,实现人的价值,谁就是“社会中坚”,谁就在历史发展中掌握了优先权、主动权和决定权。知识不仅是“力量”,而且是“权力”;不仅是一种经济权力,也是一种政治权力。科学技术在知识社会中不仅是“第一生产力”,还是“第一精神力”、“第一意志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社会中的法律所体现的主观意志性,首先不是什么“阶级意志性”,而是“科学的意志”;知识社会已把工业社会中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从僵化的静态论证变成流变的动态解析,从既定单一模式变成立体、多面的不定格式。知识与科学素质不高的社会群体,即使与大工业生产相联系,但在知识社会中却往往因其素质低下而导致技术停滞,效益下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为数不少的生产资料占有上一无所有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往往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边缘群体”,是诸多社会问题发生和社会次生集团(如娼妓、乞丐、三无人员、犯罪团伙等)产生的供给基地。缺少知识含量,尽管是“民主”的法律,在本质上也很难说是“先进”的。
知识经济到来引起的社会阶级、阶层状况的变化,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提出了严峻挑战;也对目前法理学根据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提出的“法律的阶级性”问题提出了严峻挑战。WW丁以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