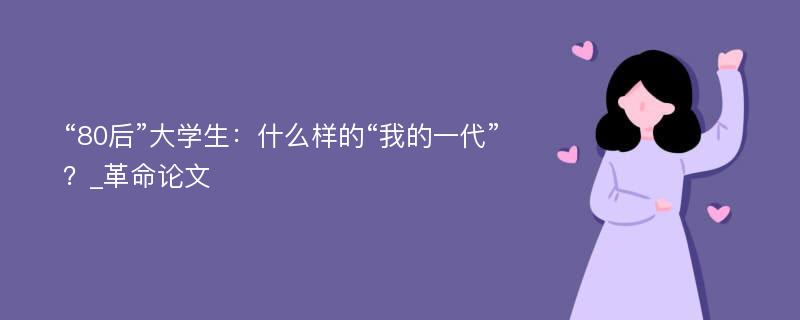
“八零后”大学生:怎样的“我一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学生论文,八零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八零后”已经成为一个社会议题,不仅种种“后”说大行其道,外国媒体也来赶热闹。去年英国广播公司在上海为“八零后”做了一个专题,片名是“Me Generation”(“我一代”),我接受了采访,为“八零后”说尽了好话,我的辩护多半是受了片名的刺激。事后平心而论,“我一代”的标题还是有意思的,既讲“有我”(me),但又非“唯我”(selfishness),作为一个“五零后”的人,我深知这是新一代的人格特征,而绝非我们的。
我在大学的工作,从十年前就已经全部地与八十年代出生的“八零后”大学生发生直接的关系了。我的工作让我的关切聚焦在“八零后”大学生,我谈论“八零后”,默会的对象就是“八零后”大学生。在后面的叙述中,除非特别说明,文中的“八零后”都可视为“八零后”大学生。在中国高等教育十年迅猛的平民化后,“八零后”一代差不多都是大学生了,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和中国的省会城市,这一等式大体就是事实了。
1、“八零后”说法:一个可以成立的世代范畴和社会分析范畴
“八零后”叫开后,繁衍出一系列其他的“后”,如前“八零后”的“七零后”,或者更老朽的“五零后”、“六零后”,或后“八零后”的“九零后”等。不管是老的“后”还是少的“后”,在我看来,统统都是“八零后”的徒子徒孙。因为所有这些新的“什么什么后”,都是按“八零后”的模本复制出来的,本身不具有社会建构和范畴原创的意义。可以说,“八零后”在共和国的编年史上分出了两个人群,前“八零后”的一群(五零、六零和七零)和“八零后”及以后的一群(目前还只有“九零后”)。所有纷繁的世代说,不能与“八零后”说法平起平坐,更不能动摇“八零后”的地位,因为“八零后”是作为一个社会世代分析范畴被创造出来的。上海学者金大陆认为“八零后”分析之所以成立,因为“八零后”世代与其父辈世代隔了一个“文化大革命”,成长为迥然不同的一代,并形成了社会分析意义的代沟。他论证,真正的代沟必定形成于历史的大变故,如大战、大灾、革命等。说“文革”后的一代,如同说二战后的一代,就不仅仅是世代的时间意义上的,更是世代的社会意义上的[1]。我同意金先生的观点,但要补充一点,“八零后”世代及“八零后”分析之所以成立,不仅因为他们与其父辈隔了一个时代(“文化大革命”),更因为他们成长于一个新的时代(改革开放时代);他们不同于其父辈,不仅是因为他们生活的世界已经没有了“文革”的政治,更是因为有了常态的政治和恢复了个人感性权利的社会生活。由此不仅可以明确地划分出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更可以明确地对比出一系列重大的不同来,如总体主义的和原子主义的,阶级斗争主导的政治运动与常态政治,定于一尊的意识形态与多元价值取向,大公无私与个人感性权利的肯定,封闭的与开放的,城乡分割的与城乡流动的,一切有待分配的与依赖个人竞争的等等。这是真正的社会变迁,从而才会成长起真正区别于前辈的“新一代”。
而这一回归常识回到平常人性的改革,是历史之摆从一极向另一极的全幅而迅疾的摆动,新的一代自然新,而且新得刺眼、新得让上一代人觉得陌生。无论从老传统(中华文化传统)还是新传统(中共革命传统)看,“八零后”有人格嬗变,更有传统失重,不论见仁见智,“八零后”作为一个区别的社会范畴是可以成立的,它具有特定的坐标功能,不仅可分析本身,也可同时关照前后的世代。在下面的讨论中,我将逐步展开“八零后”作为世代范畴和社会范畴的分析面向。
2、“八零后”大学生的政治:爱国但不爱政治
“八零后”一直是备受争议的一代,社会舆论对他们的评价也很少表扬,如“小皇帝一代”、“享乐的一代”、“消费主义的一代”,更激烈的如“叛逆的一代”、“迷茫的一代”、“垮掉的一代”、“政治冷漠的一代”等等,几乎一边倒的是批评。2008年,“八零后”时来运转,以上的帽子不仅一顶不剩,极具色彩的“鸟巢的一代”的称号被社会授予了“八零后”集体,让“八零后”扬眉吐气。“八零后”一代在大喜大悲之年的表现,够得上让父辈、师长和社会刮目相看,有学者为“八零后”的表现所兴奋,甚至嫌“后生可畏”不够劲,要用“后生可怕”的字眼了[2]。
对“八零后”或抑或扬,如此从一极端到另一极端,“八零后”自己怎样看?一个“八零后”网站说:“我们一边被人注目着,一边被人鄙视着;一边任人宠溺着,一边任人声讨着。”[1]这个态度真是酷得很,言下之意,或骂或捧,全是你们大人自己忙活的事,我们还是那个样,以前没有垮掉,现在也没有崇高。
最后的言下之意是我设计的,但绝不是虚构的,生活中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谁没有听过自己的或别人的“八零后”孩子这样揶揄我们?我们的担忧和惊喜,实际上反映的是我们这代人,更一般地说社会与国家的领导者对年青一代、特别是大学生的根本关切:他们是父辈事业的接班人还是掘墓人?我们是在这样的问题的拷问中走过来的,这样的问题轮到我们来评价“八零后”大学生了,我们对他们的大部分困惑和争议,我相信主要来自这个是否接班人的缠人问题。
我的看法是,今天的大学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接班人或掘墓人。这样一个对立项及其选择,在今天的中国政治、社会情势中多半已经失去了意义。此对立项本出自对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错误估计,出自乌托邦的政治理想主义,浪费了至少两代中国人的热情和精力。邓小平的改革,坚决抛弃阶级斗争路线,就是要走出这虚构的对立,发展出常态的政治,即发展经济、满足民生、肯定普通人感性权利的人本主义的政治。“八零后”大学生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态度是在这样的正常政治生态中发生、发展的,血缘上是去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的。接班的问题还在,但对整一代人来说,那主要是一个职业的、专业的、职位的、人生谋划的问题,不再是以“红色江山”永葆千秋万代为使命的政治意识和政治选择的问题,当然也没有相反的同样宏大的政治抱负和政治追求的问题,因为他们是改革开放路线的受益者,从而是现实政治体制的拥护者。政治接班人与否的问题完全超出了“八零后”的想象和眼界,这不是说他们没有了他们父辈的理想,而是这个时代就没有了这样的议题。看“八零后”青年学生,再用接班人的话语是无意义的,因为形势和大局已经使之成为假问题。在一代人的尺度上,根本政治意义上的接班人和掘墓人是无边的抽象和无益的空话,再拿这特定政治路线和实践中流行的“大问题”来说事,是为难今天的一代人,更是折磨我们自己。在这个意义上,根本的政治立场问题不是“八零后”一代人的问题,却多少是我们弄出来的。目睹中国的大学生在欧洲、在北美、在内地反藏独的无畏表现的人们,都会坚信他们是中国的薪火、中国的种。
“八零后”爱国,但多半不爱政治,对他们父辈熟悉的政治的态度是疏离的和冷漠的,对高调的政治宣传或意识形态不再敏感,更没有“革命”的热情和抱负,如果“革命”是持续不断地“斗私批修”,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话。他们的理想是去政治化的,或倾向于拉开距离的。绝大多数大学生接受现代的民主的政治文明及其价值,但激进主义没有市场,在政治参与上,更多冷淡和旁观。以上特点,不是单由个人人格可以解释,同样要从他们生活的世界和时代中寻找影响的力量。现代中国政治是高度集中的,邓小平时代全面改革,政治垄断没有改变,但政治不再如先前时代那样地决定一切,对社会生活个人生活有全面的渗透和控制,并使一切政治化。邓小平限制了政治的场域,不再搞折腾国家折腾干部折腾人民的“革命”,政治从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个人生活中大踏步地撤退,退回到政治本义的领域。是邓小平对生活世界的去政治化,才有“八零后”一代人的去政治化的常识心态,所以他们的政治意识不如他们父辈那般亢进。这不是政治意识的倒退,而是政治文明的进步。政治从日常生活中退潮,恢复了经济的价值、职业的价值、专业的价值、感性的价值、个人的价值和种种非政治经营的价值。青年人谋划人生,不再以政治前程为唯一的甚至不是主要的考量,在一个以发展为硬道理,把共同富裕视为国家最重要发展战略的时代,是再自然不过的。另一方面,政治依然是集中的,政治参与依然是精英主义的,个人的政治热情面对巨大的体制实体和体制能量,容易失去耐心,容易走向政治无力感,从而汇成政治冷淡氛围。以上的分析旨在支持一个看似悖谬的结论,走向政治开化的进步,带来的往往不是政治参与意识的高涨,而是普遍的政治冷淡主义。观察“八零后”大学生的政治意识和行为,必须基于上述的对政治生态的宏观认知。
3、“八零后”大学生:有“我”且不讳言“自我”的一代
“八零后”大学生是有“我”的一代,而且是不讳言“自我”更不忌惮追求自我利益的有“我”的一代,这与他们的父辈区别开来。这不是说他们的父辈不知道有“我”,不追求“自我”利益,只知道牺牲自我利人利他,对“八零后”的“我一代”(me generation)的描绘和批评,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误解甚至神话之上。毛泽东的意识形态革命,力图改变人性从而培育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新人,结局是不成功的。“文革”最高潮时,自留地的庄稼全比人民公社的庄稼长得好,证明改变人性的实践即使在最革命最讲理想的时代也是千难万难。“文革”一结束,人们对自我利益的追求马上爆发,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毛泽东的努力完全落空。这说明,从来没有完全无“我”的世代,区别在于“我”在制度上和意识形态中的不同命运。毛泽东的革命是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号召而集合起中国革命的力量的,这是有“我”的政治。群众路线更是有“我”的政治。但在走向毛泽东理解的社会主义的实践时,“我”失去了正当性,或确切说,小我失去了合法性,大我或者说集体和国家名义的利益压倒了小我、吞噬了小我。这样的实践的确造就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雷锋,以及为此精神感召的几代人,但由小我完全没有正当性产生的“无我”的人格和道德,多少是扭曲的,更多的是两面人格的,还必须靠不断的政治动员和道德说教,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和自我的不断地狠斗私字一闪念的灵魂深处的革命来维持。但即便如此,还是不能消灭“我”,至少不能消灭作为生命本能的“自我保全”。上面自留地的例子透露了最浅显也最顽强的人性真相。以革命的名义不断进行的政治运动,消灭了忠诚、消灭了友情,甚至毁灭了亲情,但终于没有完全消灭最后一点的自保,所以有苟活,有多数人自以为是革命而实际上是自保的苟活。在一个疯狂的时代,没有自我,就是灭亡。“文化大革命”让告密风行,这是不正常的社会行为,但并非完全反常的人性行为,恰恰是有“我”的人性的难以泯灭的表现。当撤去所有的制度的意识形态的高压后,有“我”的人性一定以更无忌惮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是今天“八零后”给社会和他们的父辈的形象。总体上,“八零后”一代确比他们先前的世代更自我,但并不必然更自私;如果说他们的父辈分不清自我和自私,常常在自我的(正当)追求上有道德负罪感;“八零后”则可能分不清自私与自我,常常将可能的自私当作自我权利来肯定。如果说父辈因为常常被迫“无我”而有“他人”,“八零后”则是因为不加约束的“自我”而没有“他人”。用父辈的“无我”,并不能克服“八零后”的太“自我”,因为从“无我”到“有我”,正是改革的中国带来的伟大历史进步之一,是今天的青年人比他们的父辈更有作为的根据。批评“八零后”的太“自我”,既不能用过去时代的“无我”观,更不能回到“大公无私”的“无我”,而是要走向如金大陆所倡议的“有我的利他观”,承认“他我”,承认普遍意义的自主的自由的和自律的主体。梁漱溟说中国文化的问题在于个人永不被承认。孔子传统的儒家文化只承认道德的个体和主体,而没有法权的个体和本体。计划经济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也是取消本体意义的个体的,因此没有“自我”的正面价值和积极意义。邓小平的共同富裕的政策,是承认每个人的感性权利的正当性,在哲学上实为肯定个体的实在性和正当性,是中国思想史上里程碑式的大进步。然而,从完全抹杀个体的总体主义中解放出来,带来的常常只是原子式的个人主义,表现在“八零后”一代身上,常常是有“自我”少“他人”的个人主义。批评“八零后”的自私,要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不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要从个人本位,走向个人与他人互为本位,而不是从个人本位退回到无我的集体本位。在“2006-2007上海大学生发展报告”中,笔者指出,“中国改革的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也在于怎样在肯定个人正当利益和个人自主价值选择的同时,确立和实践为全社会共信共识的若干核心价值”[3]。这不仅是对“八零后”有意义的任务,也是全社会价值和道德建设的重大任务。
4、“八零后”的叙事,才刚刚开始
“八零后”的说法开始流行时,我是不大在意的,特别对其中诟病的声响是从不以为然的。我十一年前开始上海大学生专题研究,并非自觉的“八零后”研究,但研究的对象就是被今天公认的“八零后”大学生群体是绝无疑义的,针对这一不断成为大学生的“八零后”人群的分析,形成一个连贯的观点和一致的态度,基本是肯定这一群体的。例如我的2000年的报告,这样描述他们生活的世界和他们的处境,“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全面影响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造成了一个对当代大学生来说大异于其父辈的生活世界。价值的多元竞争和市场经济制度是这一生活世界中全新的现实。他们固然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自由了解各种主义学说,选择职业生涯;但也同样面临更多选择和自主决策带来的困惑、压力、挑战和责任。如果说其父辈尚在因割断计划体制的脐带所带来的阵痛中,他们已经命定地要接受市场经济的制度。”[4]我的希望是学校和社会如实地了解大学生生活世界的根本改变,从而给予他们的成长和发展压力给予同情理解与支持,关切之情是在学生一边的。
我始终认为,与他们的父辈相比,“八零后”是正常的一代、吃饱肚子的一代、最有知识的一代,也是心理最正常的一代。因为他们是在中国经济高度发展中获益的一代,是在政治最和平最开明的社会环境中成长的一代,是获得资讯得到教育扩展眼界和旅游世界最多的一代。我在2005年主持的“上海学生民族精神教育研究”中,这样描绘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学生,“青少年生活在一个真正开放的世界里,他们的知识、情趣、志向不再限于本土和故乡。上学伊始的孩子就把出国看作读书的目的,无论稚气的小学生,少年初成的中学生,还是雄心万丈的高中生、大学生,半数以上的学子鼓荡着海外留学的志向,他们决意去了解和施展身手的世界是他们的父辈只能在梦想中浮现的世界……他们没有民族的与世界的两个断然分明的世界界限,在他们身上,不仅看出时尚文化的影响,更看出中国融入世界、世界走向中国的广度与深度”[5]。他们经历的这一切是他们的父辈梦想不到的,进而他们的人性不也更丰富、人格更正常?别人怎么想,我不知道。反正我觉得我的“八零后”崽子不仅比我幸福,也比我更健康更自然,无论是身体的、心理的还是精神的。
无论如何,“八零后”还是发展的一代。鸟巢的一代是“八零后”,胡斌也是“八零后”,昨天他们博得满堂喝彩,今天也许让你垂头丧气,明天怎样,让“八零后”自己告诉世界吧。想想美国战后的一代,从baby boom,战后一切的发明、机会(如大学)和物质好处都伴随他们的一代,到反战的一代、颓废的一代,再到掌管美国的一代(如克林顿、戈尔等),年青一代的可能性是无法预知的。把上代人的价值、理想和方式,生硬地加于下一代人,在今天这样一个迅速变革的时代免不了是自寻烦恼。2008年,南方一家报纸推选改革开放三十年风云人物,李宇春的候选引来了阵阵争议。要知道李在2005年就被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选为当年度“亚洲英雄”并选作为当期的封面人物,李宇春作为无论哪一路哪一级的风云人物,在外界来看会有什么问题呢?姚明、李宇春和春树等“八零后”都上过世界大牌媒体的封面,我感兴趣的是,他们是否也都被热捧他们的洋人们当作中国“八零后”的代表?无论如何,我坚持李宇春作为改革开放的标志人物是十足够格的,我对《解放日报》说,也许平民偶像的诞生过程非常肤浅,完全没有哲学,但是作为公众事件,它还是体现出了社会价值观的演进。“年轻人有做梦的权利。给他们机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实现人生,即使没有成功,但未必没有成长。我年轻时做的是解放全人类的梦,当代人有当代人的梦,未必伟大深刻,但本质一样,都是释放青春的活力和能量。做梦的过程就是不断校对自己人生的过程。万千人失败了,而李宇春成功了,那万千失败者仍然从她的成功得到希望,因为在她的身上,集中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的变化,表达了新一代的某种心声和寄托。这个时代,大众想选的不是高大全的完美人,而是其某种天分和才情足以把你‘雷’一下的普通人”[6]。
“八零后”的叙事,才刚刚开始……
标签:革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