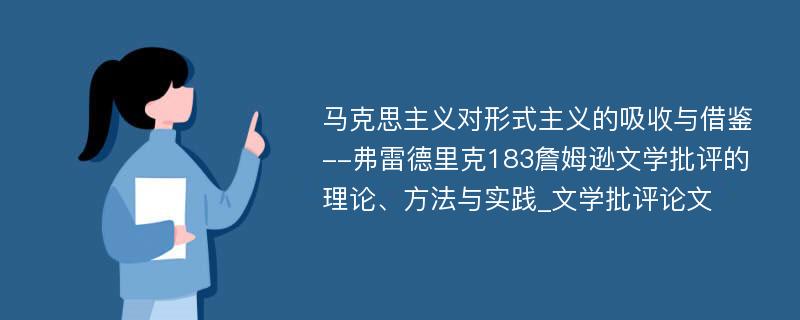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对形式主义的吸收和借鉴——弗雷德里克#183;詹姆逊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形式主义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里克论文,弗雷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对中国文论和美学影响巨大,自1985年的北大演讲以来,我国文学理论和美学研究等领域的诸多问题都与他密切相关。2012年12月詹姆逊再次来到中国,在北大做了题为“奇异性美学: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的演讲,使中国的詹姆逊热又一次达到高潮。三十年来,中国学界对詹姆逊的追踪式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对他的新著《辩证法之价》(Valences of the Dialectic,2009)和《重读〈资本论〉第一卷》(Representing Capital:A Commentary on Volume One,2011)的研究也已经展开,并有成果陆续发表。但是本文所关注的并不是他的最新著述,而是研究他的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因为文学研究是他的学术起点,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方法一直贯穿于他的学术研究的始终。更重要的是,他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极具特色,对我国当前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而中国学界对此却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海登·怀特认为詹姆逊“不仅仅是一个对立的,而且是一个真正辩证的批评家。他严肃地接受其他批评家的理论,而且不只是那些基本上与自己具有共同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相反,他对那些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的著作特别感兴趣。因为他知道,衡量一种理论,依据的不是其推翻对立思想的能力,而是其吸纳最强劲的批评者中有根据的和富有洞见的思想的能力”(怀特196)。肖恩·霍默(Sean Homer)也认为詹姆逊的贡献就在于他“反思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的可能性,以及与非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同情的对话的必要性”(Homer 5)。他把这些异质的理论流派和思潮都吸纳进来,并用马克思主义加以融会与综合。在所有的理论来源中,最重要的是形式主义(包括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法国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詹姆逊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点,吸收和借鉴形式主义,尤其是结构主义,从而使他的马克思主义表现出明显的结构主义特征,也使他成为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对话史上继巴赫金之后最为重要的理论家。在借鉴和吸收形式主义的基础上对二者进行辩证综合是他的方法论基础,对他的文学批评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辩证思维”与“元评论” 从理论渊源的角度来看,对詹姆逊思想的形成影响最大的就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德国理论和以萨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为代表的法国理论。詹姆逊从中学时代就精通德语和法语,而后来在德国的留学生涯为其接受德国和法国的理论思潮奠定了基础。人们通常认为这两种思潮就像俄国形式主义与苏联马克思主义之间那样是对立的,但是詹姆逊则认为以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法国理论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性中的一部分,它们的形成本身就与马克思主义不无关系(詹明信5)。更准确地说,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问题,就不可能有结构主义者的答案。甚至马克思本人就是一个形式主义者,他所做的就是对资本主义进行结构主义式的分析(杨建刚 王弦78)。事实也正是如此。尽管索绪尔对马克思似乎并无深入了解,俄国形式主义者也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论战的对象,但是法国结构主义者却不仅不能忽视马克思主义,而且本身就“大大得益于马克思主义”(Jameson “PHL” 102)。因此,当后来很多结构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避之而唯恐不及的时候,后结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却出版了他的《马克思的幽灵》,以此来表达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肯定和怀恋。因此,和巴赫金一样,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要取得发展,就再也不能将结构主义“拒之门外”,而是“应该把当代语言学的这项新发现结合到我们的哲学体系中去”(Jameson “PHL” vii)。正因为如此,詹姆逊同时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研究工作,并先后出版了研究著作《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和《语言的牢笼》,①试图通过“钻进去对结构主义进行深入透彻的研究,以便从另一头钻出来的时候,得出一种全然不同的、在理论上更加令人满意的哲学观点”(Jameson “PHL” vii)。 虽然詹姆逊明白“在不同的立场之间对话实在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詹明信5),但是他也深刻地意识到,“方法论问题之间的张力与冲突总会打开通向更大的哲学问题的大门”(詹明信11)。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进行对话就不再只是出于学术兴趣,而且成为他有意识的学术选择与探索。詹姆逊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之上,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的眼光,来审视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把其纳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并以“符码转换”(transcoding)的方式将其转化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一部分,以此来丰富、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萨特向詹姆逊打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大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使他真正成为一个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法国结构主义则使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了浓重的结构主义色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称詹姆逊的理论是“对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和新的法国理论的独一无二的综合”(Kellner 12)。 詹姆逊认为其他的批评方法大都是封闭的体系,而以辩证法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则是多元开放的,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与众不同、得天独厚的思维模式,原因不过在此,而非因为你自己一口咬定发现了真理。马克思主义的‘特权’就在于它总是介入并斡旋于不同的理论符码之间,其深入全面,远非这些符码本身所能及”(詹明信22)。所有的理论都是阐释,而在这些阐释模式中,“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比今天其他理论阐释模式更具有语义的优先权”(詹明信146-47)。作为一种“无法超越的地平线”,马克思主义“容纳这些显然敌对或互不兼容的批评操作,在自身内部为它们规定了部分令人可信的区域合法性,因此在消解它们同时又保存它们”(Jameson “PU” 10;詹明信148)。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层建筑”的阐释模式,所有的其他理论阐释模式,比如结构主义的“语言交流”、弗洛伊德主义的“欲望”或“利比多”,荣格或神话批评的“集体无意识”,各种伦理学或心理学的“人文主义”等等,都不具有绝对的优越性。而马克思主义却可以把所有这些理论都纳入其中,为我所用,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理论资源。詹姆逊所做的就是要建立这样一种囊括其他多种理论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 詹姆逊把这种思维模式称为“辩证思维”(dialectical thinking),或“思维的二次方”。综合詹姆逊关于辩证思维的多处论述,可以得出在辩证思维指导下文学批评的三个主要研究对象,即对研究对象的研究、对研究者立场的思考和对研究过程中的方法、概念和范畴的反思。其特点在于:一是“强调环境本身的逻辑,而不是强调个体意识的逻辑”,即把研究对象放入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来加以研究,或者说将研究对象“历史化”;二是“寻求不断地颠覆形形色色的业已在位的历史叙事,不断地将它们非神秘化,包括马克思主义历史叙事本身”;三是“坚持以矛盾的方法看问题”(詹明信35)。建立在辩证思维基础之上的批评方法就是“辩证批评”,或“元评论”(metacommentary)。②这种评论是一种“评论的评论”,它带给我们的不只是“批判的武器”,同时也是“武器的批判”,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一种“元评论”。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并非只有信仰共产主义才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许多事实上在做元评论工作的人没有意识到他们干的正是马克思主义”(詹明信20)。这样,“元评论”就成为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一种方法论,也成为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标志。 在此基础上,詹姆逊提出了他那句振聋发聩的口号——“永远历史化”(Always historicize)!这已经不只是一个口号,而是变成了一种方法论。任何批评都不可忽视历史的存在,都应该把研究对象纳入历史的语境之中,从历史的角度来加以审视,历史也就成为詹姆逊自始至终的研究视点。可以说,“从六十年代末期到现在,詹姆逊一直把文本的历史维度和历史的阅读置于特权地位,他把自己的批判实践带入了历史的屠宰房,也将批判话语从学术的象牙塔和语言的牢笼中移开,使其经历了学术领域里的荣衰和变动,而‘历史’这一术语正是这一过程的标记”(Kellner 5)。他正是以这种历史化的视角来审视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的。索绪尔语言学,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的致命缺陷就在于抛弃了历史,从而将自身囚禁于自己建立的“语言的牢笼”之中。因此,要超越形式主义就必须为其增加一种历史的维度,并把它与社会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詹姆逊认为,只有“通过揭示先在符码和先在模式的存在,通过重新强调分析者本人的地位,把文本和分析方法一起让历史来检验,[……]只有这样,或以相类似的东西为代价,共时分析和历史意识、结构和自我意识、语言和历史这些孪生的、显然无法比较的要求才能得到调和”(Jameson “PHL” 216)。③也只有这样,结构主义才能打破这个“语言的牢笼”,把文学和语言向历史开放,回归文学和语言的意义层面和意识形态功能。但他并没有抛弃结构主义的合理内核,而是在拒绝了结构主义的非历史化倾向的同时,极力肯定了索绪尔、格雷马斯和其他结构主义者的科学的中立立场和批评方法(Goldstein 151)。他把这些理论和方法通过“符码转换”的方式转变成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并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阐释学之中。 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任何历史研究的最终指向都是当下政治,关注历史只是关注政治的一种表征。正如詹姆逊所言:“一切事物都是社会的和历史的,事实上,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Jameson “PU” 20)。罗兰·巴特为了批判萨特的介入文学,把文本作为一种能指的游戏,并认为对文本的阅读所获得的是类似于性欲满足的身体快感和愉悦,这种“文本的愉悦”与政治毫无关系。但是詹姆逊则认为这种愉悦和快感本身与政治根本就无法分离,甚至干脆把那篇评述萨特与巴特之间论争的文章直接定名为《快感:一个政治问题》(Jameson “Pleasure” 61)。他的《政治无意识》的主旨就是要“论证对文学文本进行政治阐释的优越性”,并把政治视角“作为一切阅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域”(Jameson “PU” 17)。可以看出,在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中,政治和历史是紧密相连,互为表里的。只有具有政治指向的历史研究才是有价值的,同时也只有依据历史的政治批评才是深刻的。 但是文学的本质是审美的,审美则是形式的。文学艺术的政治(在文学中表现为意识形态)和历史内涵都蕴含于艺术形式之中,并通过审美形式的中介得以存在和呈现。因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中,政治(意识形态)、历史和形式是三位一体的。不同于苏联庸俗马克思主义对艺术形式的排斥,詹姆逊认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必须把形式作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批评家需要像关注文学内容一样关注文学形式。因为形式不只是艺术作品的‘装饰’,而且体现着强大的意识形态信息”(Roberts 4)。艺术形式与意识形态的内在关联使批评家需要首先把形式作为研究对象,更重要的是作为探索意识形态内容的先在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批评家只需停留在形式层面,形式研究的最终指向还是政治。正如其所言,“我历来主张从政治、社会和历史的角度阅读艺术作品,但我决不认为这是着手点。相反,人们应从审美开始,关注纯粹美学的、形式的问题,然后在这些分析的终点与政治相遇。[……]我更愿意穿越种种形式的、美学的问题而最后达致某种政治的判断”(詹明信7)。尽管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要求“永远历史化”,认为政治才是其“绝对视域”,但是和形式主义一样,认为文学艺术的首要研究对象还是形式。不同只是在于形式主义仅仅停留在形式层面,不敢向意义、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迈进一步,而马克思主义则把后者作为其形式研究的最终指向。詹姆逊认为,“把社会历史领域同审美—意识形态领域熔于一炉应该是更令人兴趣盎然的事情”,而他之所以对卢卡奇情有独钟,原因就在于卢卡奇“从形式入手探讨内容”的方法是文学研究的“理想的途径”(詹明信13)。 由此可见,以辩证思维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主义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创新是詹姆逊的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论。正因为对形式主义理论的吸收和借鉴,以及对艺术形式的普遍关注,詹姆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批评方法,也为他赢得了空前的声誉。2008年,挪威路德维希·霍尔堡纪念基金会将被誉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诺贝尔奖”的霍尔堡国际纪念奖授予詹姆逊,认为他创造的“社会形式诗学”“对理解社会形成和文化形式之间的关系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王逢振91)。詹姆逊自己也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或“历史”与“形式”来概括自己一生的学术研究(何卫华 朱国华2)。詹姆逊坦言,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之所以对形式问题如此感兴趣,原因在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大都致力于内容和意识形态分析,总是关注内容因素,即作品的思想是什么?反映了什么样的意识形态?等等。很少有人研究叙事的特点、作品所采用的叙述方式以及意识形态得以呈现的形式”(杨建刚 王弦78)。因此,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要取得新的进展就应该将“形式的意义”或“形式的意识形态”作为突破口。 二、形式的意识形态 詹姆逊发现,“在近来的文学批评中,关于‘形式的意识形态’的观点,即作品的形式而非内容有可能表达一定的意识形态倾向的观点,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Jameson “MP” 114)。伊格尔顿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批评划分为四种模式,即人类学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模式,在这四大模式中最具特色的当属意识形态批评模式,因为这种模式不是对文学作品的意识形态内容进行简单分析,而是把“形式的意识形态”作为研究对象。这种模式之所以能够获得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的普遍接受,原因在于它解决了文学理论研究中长期以来崇尚形式与崇尚内容两种观念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正如伊格尔顿所言:“如果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第三次浪潮最好称为意识形态批评,那是因为它的理论着力点是探索什么可以称为形式的意识形态,这样既避开了关于文学作品的单纯形式主义,又避开了庸俗社会学”(Eagleton and Milne 11)。可以说,“形式的意识形态”概念的提出,或者把形式的意识形态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对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对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长期以来持续不断的论争的回应,也是在他们之间进行对话的结果,而这一批评范式的真正成熟完全得益于詹姆逊的批评实践。 马尔赫恩认为“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中遇到的两大难题之一,另一个难题是“文本及其外部领域的关系”问题(21)。不只是形式主义者对形式问题情有独钟,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一直非常重视形式问题。卢卡奇认为:“艺术中意识形态的真正承担者是作品的形式,而不是可以抽象出来的内容”(伊格尔顿28)。阿多诺也认为,在艺术中,“形式是理解社会内容的钥匙”(394)。马尔库塞同样关注形式问题,认为“一件艺术作品的真诚或真实与否,并不取决于它的内容(即是否‘正确的’表现了社会环境),也不取决于它的纯粹形式,而是取决于它业已成为形式的内容”(196)。因此,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那里,本来由内容所承载的艺术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批判性在这里自然而然地转移到了审美形式上。 詹姆逊在对形式主义理论进行充分吸收的基础上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式理论推向深入。如其所言:“整个这一‘形式—内容’的问题既不是纯粹局部的、美学的问题,也不是局部的、技巧的哲学问题,而是在各种当代语境中不断反复出现的问题。[……]内容和形式的问题大大超越了它们纯粹的美学指涉,从长远看,会不断涉及社会的各个角落”(Jameson “MP” xvii-xix)。因此,解决形式与内容之间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成为建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关键所在,而整个形式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的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对立关系的反思为詹姆逊重新思考这一问题奠定了基础。詹姆逊认为一切事物都处于二元对立的矛盾之中,我们对世界和事物的解释也是借助于二元对立。比如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与上层建筑、主体与客体,结构主义的能指与所指等等。“要摆脱二元对立并不是要消除它们,而是常常意味着使它们增多”(Jameson “MP” xiii)。在文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二元对立就是形式与内容。“内容是形式的前提条件,形式也是内容的前提条件。要克服形式与内容的对立(即使它富有成效),必须使它复杂化,而不是消除其中的一个方面”(Jameson “MP” xiii)。在他对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对立进行复杂化而建立形式的意识形态批评模式的过程中,语言学家路易斯·叶尔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为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根据叶尔姆斯列夫的看法,一种形式可以拥有自己的内容,这种内容区别于事件、人物和场景等内容,在一个特定作者修改形式以再现一种现实的过程中,事件、人物等内容可能充满形式(怀特207)。也就是说,在一部文学或艺术作品中,形式中有内容,内容中有形式,事实上我们很难说清楚什么是形式,什么是内容。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体裁、文体、句法、修辞是形式,而人物、故事、情节就是内容。可以说,在现代主义作品中,形式就是内容;反过来说也成立,现代主义作品的内容就是形式本身。在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对立中片面强调任何一方而忽视另一方都会导致一种歪曲。形式与内容是互为条件的。因此,解决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对立的唯一办法不是仅仅抓住一方而抛弃另一方,而是将这种对立进一步复杂化,并且分析二者之间的交叉和互渗关系。在叶尔姆斯列夫的两组二元对立,即表达/内容和形式/材料的分析模式的启发下,詹姆逊提出了自己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模式。他将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对立复杂化为四项对立,即内容的形式、内容的内容、形式的形式、形式的内容(Jameson “MP” xiv)。 这四种组合已经穷尽了形式与内容之间可能构成的所有情况。詹姆逊认为,“从实践角度来看,其中的每一个组合或观点都反映了一种文学批评类型,它们各自在具有自己的有效性的同时也具有自己的内在局限性;从某些外在边界的角度来看,在从描述向处方(prescription)的滑动中,每一种组合都将为作家设置一个用以遵循的特殊的美学和程序”(Jameson “MP” xiv)。④内容的内容指的是一种尚不具有实际的文学形式的社会和历史现实,或者说内容还处于无法表达和尚未定型的阶段。内容的形式是作家用以将这种无形的、原生态的现实,也包括抽象的观念,表达出来的具体的文学语言和艺术形式。比如狄更斯以小说形式反映贵族阶级的生活。即使没有小说,这种生活也存在,但是它却只能是无形式的,而小说则使这种内容的内容具备了审美的形式,从而转化为艺术对象。一旦作家赋予了无形式的内容以形式,那么这种内容的形式就已经包含了我们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的任何东西。寓言就是对内容的形式的最集中体现。而形式的形式则是那种纯粹的无内容的纯形式,是康德所说的作为纯粹美的形式。詹姆逊认为,对内容的内容和形式的形式的过分强调代表了文学批评活动中的两种极端倾向。可以说,将文学艺术与社会现实和经济基础简单等同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和简单的实证主义属于前者,而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形式主义则是后者的代表。绝对地指向内容会走向自然主义,而绝对的形式主义则使艺术成为唯心主义和虚无缥缈的东西。那么,要超越这两种极端化倾向,就必须走向第四种情况,即关注形式的内容。现代主义表面上强调的是艺术形式的变革,但是它那变异的艺术形式下面隐藏的则是社会批判的意识形态内容。詹姆逊之所以对现代主义艺术情有独钟,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他对现代艺术的形式分析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揭示出这种形式中的内容。詹姆逊把第四项,即形式的内容(形式的意识形态)作为文学艺术批评中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对立的最佳解决方案。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形式主要体现为叙事性文本,而内容就是意识形态。这样,形式的内容,或形式的意识形态就转变为文本的意识形态。马歇雷和伊格尔顿的艺术生产理论讨论的就是意识形态如何进入文本,进而转变成文本深层的政治无意识的。形式的意识形态极其隐蔽,这就需要批评家对文本进行深度剖析,从而将这种意识形态或政治无意识挖掘出来,这也正是詹姆逊建立马克思主义文本阐释学的目的所在。 三、马克思主义的文本阐释学 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元评论,它的阐释学和诸如伦理的、心理分析的、神话批评的、符号学的、结构的和神学的等等阐释方法都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多元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可以容纳当今知识市场上所有的理论方法,并将其转化为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资源。正是这种开放性使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学成为“包含了明显敌对或不可通约的批判操作的所有批评都‘无法超越的视域’”(Jameson “PU” 10)。詹姆逊的“视域”(horizon)概念明显来自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它对各种理论方法的综合吸收、融会转化也正是伽达默尔所说的“视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但是他并不关注现代解释学所注重的那些问题,比如海德格尔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或先在结构(fore-structure)、伽达默尔的偏见(prejudice)和赫施(Hirsch)的假设(hypothesis)等等。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所关注的是艺术形式中的历史和意识形态内容,即“形式的内容”或“形式的意识形态”。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的文本阐释学就是要将文本“永远历史化”。这包括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把形式或文本历史化,即把特定文本放入历史语境中来加以理解。在历史的长河中,任何解释都是相对的,都会带上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偏见”,都体现着特定阐释者的“前理解”。但是如果就特定的历史语境而言,这种阐释则是“绝对有效的”。詹姆逊认为伽达默尔的阐释的历史相对主义和赫施的阐释的绝对有效性的对立忽视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意识形态限制,如果加入马克思主义的“绝对的历史主义”这一视域的话,这种对立就可以迎刃而解(Jameson “PU” 75)。另一方面则是历史的形式化或文本化。不同于马歇雷和伊格尔顿对文本概念的抽象化理解,詹姆逊极为关注叙事作品,他所说的文本就是叙事,而文本化就是叙事化。正如内容的内容不能成为艺术一样,历史本身在文本中也只能成为一种阿尔都塞所说的“缺场的原因”。因此,历史要成为艺术对象就必须将其加以文本化,把历史纳入文本和叙事之中,这样历史才能转化为审美对象,我们所能看到的也只是文本化或叙事化了的历史,因此新历史主义把历史本身看作一种叙事也不无道理。 但是不同于叙事学所说的讲故事意义上的叙事,詹姆逊把这种叙事作为一种“社会象征行为”,一种潜藏着丰富的历史、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象征性内涵的“寓言”。文本的审美化效果则使这种内涵处于一种无法察觉的状态,即文本中的“政治无意识”。用他的话说就是,“一切文学,不管多么虚弱,都必定渗透着我们称之为一种政治无意识的东西,一切文学都可以解作对群体命运的象征性沉思”(Jameson “PU” 70)。比如,詹姆逊认为“现代主义自身就是资本主义,尤其是资本主义中的日常生活的异化现实的一种意识形态的表现。[……]然而,现代主义同时又可以看作是对物化给它带来的一切的乌托邦补偿”(Jameson “PU” 236)。康拉德的现代主义作品就是高度物化和异化的资本主义现实政治的象征,其中每一个叙事文本都是一种意识形态象征行为,而每一个人物的故事都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在康拉德的《吉姆爷》中,“斯坦的故事就是资本主义扩张的英雄时代正在逝去的故事”(Jameson “PU” 237)。通过吉姆的故事,“康拉德假装讲述个人如何与自身勇气和恐惧斗争的故事,但他非常清楚真正的问题并不在这里,而在于吉姆不得不树立的社会样板,以及吉姆在意识形态神话中发现萨特式的自由而产生的非道德化效果,也正是这些意识形态神话使统治阶级发挥作用并断言它的统一性与合法性的”(Jameson “PU” 264)。由此可见,叙事作为一种社会象征行为,其文本深层刻写着时代的意识形态。没有意识形态内涵的文本是根本不存在的,问题仅仅在于这种意识形态的性质和强度不同而已。但是由于文本的意识形态不同于作家的意识形态,它可以独立存在,因此文本的叙事过程中所潜藏的这种意识形态甚至连作家本人也没有意识到。这也就有了作家背弃自己的阶级立场、作品超出作家预期效果的情况。 正是因为历史和意识形态是通过叙事的编码方式体现出来的,叙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并且文本的表层语言和结构与深层意蕴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所以对叙事文本进行阐释就是极有必要的。可以说叙事和阐释是一对孪生姐妹,有叙事就必须有阐释。只有通过文本和叙事,历史才能够接近我们;同时,也只有通过阐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这种历史和意识形态。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任务不是拒绝阐释,而是在历史的否定和压抑中解救阐释”(Dowling 99-100)。这种阐释不是简单地弄清楚“它的意思是什么?”,而是通过“主符码”或“主叙事”对复杂现实的不可避免的重写。可见,詹姆逊的这种阐释和形式主义者的“内在阐释”是不同的。在六十年代之前美国学术界居主导地位的阐释模式是新批评,而詹姆逊所提出的阐释模式则完全不同。有人把二者做了一个比较,认为“新批评的巨大成功就是将美国大学中对文学的‘政治的’解释锁闭起来,这种成功直接来源于他们所宣称的内在阐释。新批评的基本观点是,只有当所有外在于文本的信仰或教义都被悬置起来,文学作品的阅读唯独能够运用他们自己的标准和价值的时候,文学理解才成为可能。如果对这种内在解释看得过于重要的话,要发现形式主义者在哪里错了就是非常困难的。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政治的’文学批评方法认为新批评是错误的,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逃避主义的形式,用詹姆逊的话说就是,它否定和压抑了历史”(Dowling 104)。在詹姆逊看来,新批评等形式主义者试图摆脱政治和伦理的“内在的超越阐释”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主符码是意识形态,准确地说是“形式的意识形态”。 “形式的意识形态”批评要求像形式主义者那样关注艺术形式,但是它“绝不是从社会和历史问题向更狭隘的形式问题的退却”(Jameson “PU” 99),而是通过对艺术文本的审美形式的分析来揭示其中所蕴含的历史、社会和意识形态内涵。可以说,“詹姆逊对形式的强调已经成为他将以前明显非政治的东西予以政治化的主要工具”(Irr and Buchanan 5)。因此,在具体的阐释模式的建构中詹姆逊对形式主义,尤其是结构主义的阐释方法进行了批判性的吸收和借鉴。 通过对弗莱等人的批评理论的吸收和借鉴,詹姆逊提出了自己的“三个同心圆”阐释模式,并将其作为发掘文本深层政治无意识的有效方法。这个问题笔者已经有过分析,故在此不予赘述(杨建刚22)。除此之外,他还将结构主义叙事学和符号学方法,尤其是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运用于对文本深层的政治无意识的发现和挖掘之中。詹姆逊虽然也意识到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能否无限丰富地运用于文学与叙述性结构的分析也还是一个问题”(詹明信332),但是这种方法为我们的文化分析提供了“整个意义产生的可能性”,可以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一条进入文本的路径”。比如,格雷马斯用符号矩阵将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研究中所关注的两性关系进行分析,建立了“两性关系的社会模型”、“两性关系的经济模型”、“个体价值模型”,并由此构建起了一个人类的“性关系体系”(格雷马斯147-54)。詹姆逊认为如果我们把某一社会的婚姻规则作为起点,“这个语义四边形就能让我们得出这个社会常规的和可能发生的两性关系的全部内容”(詹姆逊286)。因此,正如把符号学方法作为“分析意识形态封闭的特殊工具”一样,詹姆逊把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也作为“一种探讨意识形态的方法”,并从中发现了“政治无意识”的运作方式。 如果说格雷马斯主要用这个符号矩阵来探究文学叙事中的深层结构模式,那么詹姆逊运用这一模式所发现的是这种深层结构模式中所包蕴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内涵。比如,詹姆逊用这种方法对《聊斋志异》中的《鸲鹆》进行分析,剖析了人、非人、反人和非反人这四项对立所生成的金钱影响下的权力和友谊的逻辑关系。在詹姆逊看来,《鸲鹆》不再只是一个用于娱乐的故事,而是关于文明进程的,“探讨的是究竟怎样才是文明化的人”,“探讨‘人’怎样可以变得‘人道’,‘人’又怎样成为‘反人’,以及‘非人’又怎样可以具有人性,等等。”在对《画马》的结构分析中,詹姆逊从中看到的也不只是故事是如何展开的,而是“一种新的再生产关系”,是对货币社会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即“货币怎样才能增长”或“货币再生产”进行艺术思考。康拉德的《吉姆爷》体现的是行动和价值的对立,“《吉姆爷》中的矩形是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意识形态,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诊断”(杰姆逊110-40)。由此可见,通过对格雷马斯符号矩阵的运用,詹姆逊已经把文学故事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寓言”。 除了对文学作品的分析之外,詹姆逊还把这一方阵运用到了对包括马克思·韦伯社会学理论、拉康的精神分析、乌托邦问题以及后现代主义建筑等文化问题的分析和阐释中去。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在詹姆逊这里已经具有了更广泛的用途和更深刻的文化价值,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用于文化分析的特殊工具,而且成为社会文化存在的一种基本的方式。格雷马斯的符号学分析中运用了大量类似于数学公式的图式,因此有人称符号学为人文社会科学里的数学,具有明显的科学主义倾向。格雷马斯主要运用这个符号矩阵对叙事性作品的叙事结构进行语义分析,进而试图揭示故事背后的文化原型和深层结构。詹姆逊对格雷马斯符号矩阵加以运用并推进一步,用其挖掘文学作品叙事结构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或政治无意识,体现出较强的人文主义色彩。无论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理论正确与否,詹姆逊将它作为一种意义生产机制来使用的做法却是新颖的,而且对于说明叙事如何发生作用以加强或消解在不同发展时期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具有启发意义。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形式主义,尤其是结构主义的方法已经渗透到了詹姆逊文学批评的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的方方面面。如果说结构主义也是一种阐释学的话,那么詹姆逊已经把它完全纳入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框架之中,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吸收和借鉴形式主义,进而对二者的方法和理念进行辩证综合,也成为詹姆逊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伊格尔顿的新著《怎样读诗》(How to Read a Poem,2007)和《怎样读文学》(How to Read Literature,2013)延续了詹姆逊的批评方法,在借鉴形式主义批评方法对文学文本进行细读的基础上,进行了“形式的意识形态”的批评实践。尽管詹姆逊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的对话也存在诸多问题,对二者的辩证综合也不尽完美,但是这种在不同理论之间进行综合创新的方法却是非常有效的,对我国的文学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目前,我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影响力之所以不断缩小,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对艺术形式的忽视使其对文学艺术缺乏真正的解释力。摆脱过去的宏大叙事,从粗线条的社会历史批评向文本自身的形式结构和审美价值回归,或者说把文学艺术的形式问题作为社会历史批评的起点和重要方面,应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走出当前的低谷状态的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者到底该怎样读文学?”也应该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者认真思考和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 ①按照詹姆逊的说法,《语言的牢笼》和《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本来就是同一部书稿的两部分,只是在出版的时候,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认为书稿太长,于是将两部分单独成册,分别于1971年和1972年先后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和《语言的牢笼》。事实上,在詹姆逊看来,对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一个整体,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部分而已。这两部著作的汉译本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合订为一本于1997年出版。参见杨建刚 王弦:“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教授访谈录”,《文艺理论研究》2(2012):77-81。 ②凯尔纳认为《元评论》(Metacommentary 1971)一文不但是从《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向《语言的牢笼》的过渡,而且也是通过保卫批判的解释学来反对当时甚为流行的桑塔格的“反对阐释”(anti-interpretation)。凯尔纳认为完全可以用“元评论”来概括詹姆逊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实践的特点。参见Kellner,Douglas,ed.Postmodernism,Jameson,Critique.Washington,D.C.:Maisonneuve Press,1989.11. ③在一年前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詹姆逊已经明确提出了类似的表述,这为《语言的牢笼》奠定了基本主题。他认为辩证思维的基本运动就是要“调和内部的与外部的、内在的与外在的、现存的与历史的,以便使我们能够在单一的确定形式或历史时刻中进行探索,同时在对它做出判断的过程中置身其外,超越形式主义和对文学的社会学的或历史的运用之间的那种无效的和静止的对立,而我们却往往被要求在这种对立之间做出选择”。参见Jameson,Fredric.Marxism and Form.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330-31。 ④詹姆逊认为,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对立构成的这四种可能组合各自代表了一种文学批评类型。他对这四重组合的分析是以从内容的内容、内容的形式、形式的形式到形式的内容的顺序进行的。他仅仅对前三种情况做了简要的分析和描述,而把第四种作为克服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对立所出现的极端化倾向和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方案。因此他说他的分析是一种由描述向处方的滑动。标签:文学批评论文; 结构主义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形式主义论文; 文学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二元对立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法国历史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