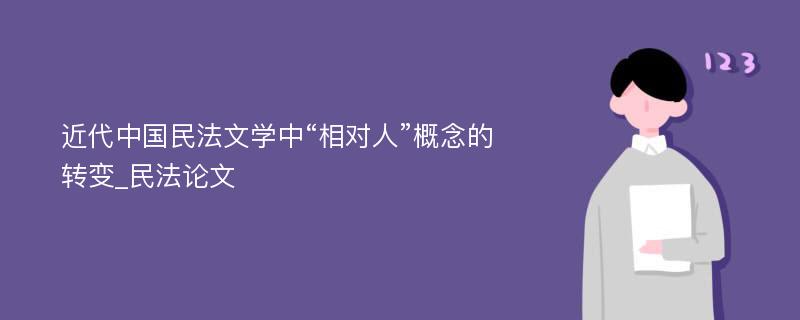
“亲属”概念在近代中国民法文献中之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法论文,亲属论文,文献论文,概念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12)06-0170-08
一、导论
从清末修律到民国时期民法亲属编经历了五次①的立法。除此之外,还有民国初年为了解决法律适用的混乱局面,大理院颁布了很多的解释例和判决例,这为民国初年的各级司法机关提供了判案的标准。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各级法院除了运用六法全书进行裁判外,也运用一些判决例和解释例来辅助司法实践处理亲属问题。
民国时期学界针对清末民国时期民法亲属编的立法历史多有论述,如谢振民之《中华民国立法史》、杨幼炯之《近代中国立法史》、杨鸿烈之《中国法律发达史》等,而对于民法亲属编之通则具体条文问题没有详述,如亲等、亲属范围、亲属种类等基本问题。民国时期,一些亲属法著作论述对民法亲属编,大多关注婚姻、继承、妾制、夫妻财产制、宗祧、家族制度、女性法律地位及权利义务、家制等。关于民法亲属编通则的相关论文不多。20世纪80年代以后,当代学者著作论述了中国近代民法典中亲属、亲属种类、亲属范围、亲等等基本问题。这些著作主要关注中国民法近代化中的《大清民律草案》《民国民律草案》《中华民国民法》等亲属立法过程,或对某一专门问题进行论述(如结婚、离婚、立嗣、宗祧等),或是对近代中国五次亲属立法中某一部法典进行解释和评价。当前一些论文是对清末民国时期之亲属法的立法原则,亲属法对传统亲属制度的改造、亲属法在中国法律近代化过程中的影响及意义等方面。
学界对清末民国时期中的五次亲属法通则条文的研究比较薄弱,故本文通过梳理中国近代五次亲属立法中通则条文,还原亲属、亲属种类、亲属范围、亲等等概念在在近代中国民法典文献中的嬗变,揭示“亲属”概念在清末民国时期历次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原貌。
二、近代中国民法文献中的“亲属”
(一)清末修律中的“亲属”
“亲属”一词,在清末民法学中没有自己的观点,大都是对日本法学的翻译和传播。“亲属”在日语中为“亲族”,在日本民法中亦不称“亲属”,而称为“亲族”,日本学者梅谦次郎在《民法要义·相续编》第一章总则中,对“亲族”进行了描述,“第725条,左列各项为亲族。一、六等亲内之血族。二、配偶者。三、三等亲内之姻亲”[1]。从其对法典中的“亲族”中亲属范围的解释看出,“亲族”包括血亲、配偶、姻亲,故“亲族”与中国古代的“亲族”不可等同,中国古代的“亲族”仅指男系同宗之亲。而中国古代法典中的“亲属”,如《大清律例》中有“亲属相为容隐”、“亲属相盗”、“亲属相奸”等诸多条文,以上这些条文中的“亲属”不仅包括同姓之宗亲,还包括异姓之外亲和妻亲。故日本民法中“亲族”与中国古代法典中的“亲属”词义是相同的,但不能简单地从字面理解“亲族”和“亲属”,要放在中国特有的法律文化背景中来理解。
《大清民律草案·亲属编》第1317条:“本律所称亲属者如下:一、四等亲内之宗亲;二、夫妻;三、三等亲内之外亲;四、二等亲内之妻亲。夫族为宗亲,母族及姑与女之夫族为外亲,妻族为外亲。”[2]可见从《大清民律草案》可以看出,“亲属”包括三种:宗亲、外亲、妻亲。故若用中国古代“亲族”的称呼,不能完全概括亲属的种类,只能指代宗亲一种。
《大清民律草案》起草者之一的邵羲先生②所著的《民律释义》对《大清民律草案》“亲属编”的命名作了解释,邵羲先生道:“惟各国之所谓亲族者,其意义则不如是狭窄也。盖其于同宗之血亲外,复包有异姓之配偶者及姻族在内。然则彼之所谓亲族者,于吾之所谓亲族者,其范围之广狭,有不可同日而语者。乃今欲编纂民律,自不得不以亲族二字之外,另求适当用语也。夷考中国旧时律例,凡指族亲姻亲之全体者,必曰亲属。”[3]由此观之,“亲族”在中国古代和西方各国的含义是完全不同的,词义有广狭之分,而西方各国的“亲族”包括宗亲、外亲、妻亲三种亲属,而我国古代“亲族”仅指宗亲一种,而我国古代的“亲属”则是指宗亲、妻亲、外亲三种亲属,故为避免歧义,中国近代民律草案取“亲属”来命名民律亲属编,从而适合中国固有的亲属制度,避免和西方各国发生混淆。
(二)民国时期民律草案及民法典中的“亲属”
《民国民律草案.亲属编》第1055条:“本律称亲属者如下:一、四等亲等内之宗亲;二、夫妻;三、三等亲内之外亲;四、二等亲内之妻亲。夫族曰宗亲,母族及女子之出嫁族为外亲,妻族为妻亲。”[4]此处所称的亲属亦包括四种亲属种类:宗亲、妻亲、外亲、夫妻。故只有“亲属”才能包括四种亲属种类,而“亲族”根据其在中国古代的指代,仅指宗亲一种。故《民国民律草案》也延续了《大清民律草案》的传统,以“亲属”来命名亲属制度。
在《中华民国民法典》亲属编中,第967条:“称直系亲属者,谓己身所从出,或从己身所出之血亲。称旁系血亲者,谓非直系血亲,而与己身出于同源之血亲。”第968条:“称姻亲者,谓血亲之配偶、配偶之血亲、及配偶之血亲之配偶。”[5]从以上两条看出,虽然亲属种类从历次民律草案中的宗亲、外亲、妻亲、夫妻变为血亲和姻亲,但是亲属的种类还是“亲族”所不能包含的,因此只有用“亲属”来命名更适合中国的现实。
(三)民国亲属法学著作中的“亲属”
近代四次民律草案中均以“亲属”为名称来命名亲属编,一直到《中华民国民法典》的颁布,一直沿用“亲属”二字。因此,近代很多民法学者对为什么采用“亲属”,而不用“亲族”?民法学者在“亲属”和“亲族”在中国古代所包括的亲属种类上,取得了共识,即“亲属”包括宗亲、妻亲、外亲的全体,而“亲族”仅指宗亲,仅为亲属的一类,故沿用中国古代律例中的“亲属”来命名。但诸多民法学者对“亲属”和“亲族”两词的词义理解上,对二者的区别给予了诸多解释,有诸多分歧,现将四种说法列出:
1.“亲属”与“亲族”词义没有区别,但所指亲属种类不同,沿用中国古代律例中的“亲属”来命名。
汪波对“亲属”和“亲族”给予了解释,认为:“亲属二字,日本的民法称为亲族。考诸我国典籍,亲属与亲族其义本可通用。盖‘亲’是取亲爱的意思……‘属’是从属的意思……‘族’是取群簇的意思。[6]”因此“亲属”二字是因亲爱而相互从属,而“亲族”因为亲爱而相互聚集,“亲族”和“亲属”在词义上没有太多的区别。
汪波对《中华民国民法典》采取“亲属编”的命名给予了如下的理由,“我国律例,以为‘族’字须用其专指同宗族之亲为宜,倘兼指姻亲,字义上似有未妥。所以后来定亲属法的名称,不依日本名以‘亲族’而以‘亲属’,即因‘亲属’二字,指族亲姻亲的全体,实较稳妥”[7],故在命名上,为避免歧义,而和日本的“亲族法”作出区别,用“亲属”。综上,此种观点承认在中国古代,“亲族”和“亲属”的意思是相近的,而日本的“亲族”和中国古代的“亲族”相去甚远,日本的“亲族”包括姻亲和宗亲,而中国古代的“亲族”仅包括同宗之亲,则日本民法中的“亲族”和中国古代的“亲属”(所包含的宗亲和姻亲),意思相同,故近代民法学用“亲属”来命名民法典亲属编。
2.“亲属”与“亲族”词义不同,所指亲属种类不同,虽日本民法中的“亲属”出自中国古代典籍,但词意已经发生变化,非中国古代的“亲族”,故用中国古代律例中的“亲属”来命名。
徐朝阳认为:“尝考日本《亲族法》以族通称于各种亲类,不专指同宗之血亲;即异姓之配偶者及姻族,均包括在内,皆谓之亲族。欧美亦然,日盖仿欧美也。中国有亲族无亲族律之称。《律例》中凡亲族二字,专指同宗族之亲而言;若包括族亲姻亲之全体,则用亲属二字。所谓亲族者,不过亲属中之一种而已。”[8]屠景山也持此说。③宗惟恭亦持此种解释。④李谟亦认为“亲属云者,乃血亲姻亲之总称也。我国向例,称同宗族之亲曰亲族。称族亲姻亲之全体曰亲属”[9],故亲属编“不仿日本之例曰亲族。而称亲属,盖取概括之意也。”[10]曹杰亦称“历次民法草案均定名亲属编,现行民法第四编因之,其所以不采日本民法‘亲族编’之命名者,盖以吾国旧律所用亲属二字,则包括亲族姻亲全体而言,至云亲族,则专指同宗之亲族而言”[11],加之“日本民法所采用亲族二字,亦由吾国经典,诠释而出,非其臆造”[12]。但日本民法典的“亲族”已非我国古代“亲族”的含义,故我国民法典为免除歧义,而用“亲属”。同时,曹杰认为“亲属”和“亲族”的命名之争没有必要,法典应以立法内容和立法精神为标准,而不必以名称作为区别。赵凤喈⑤也认同此种说法。此种观点对中国古代的“亲族”和“亲属”辨析,尤从古代律例中得出中国古代有亲属有亲属律,也有亲族而无亲族律,故历次民律草案及《中华民国民法典》均用“亲属”,是沿用中国古代旧律之用语。同时指出日本民法中“亲族”亦出自我国古代典籍之中,但日本“亲族”的本意已经不是中国古代“亲族”之义,所以不能混淆中国古代的“亲族”和日本近代民法中的“亲族”。
3.中国有“亲属”而无“亲族”,而“亲族”来自日本,日本“亲族”又来自于外文翻译,故沿用中国古代律例中的“亲属”来命名。
黄右昌认为“我国有亲属而无亲族,而亲族二字,来自日本,日本亲族法之称,翻译来自于英law of family,法L I dela famila on.Droit domestique,德Familienrecht。而诸国亲族法之文字则又发源于拉丁Familias”[13]。而日本“亲族”翻译自外文,包括同宗、异姓之配偶、姻族。而中国律例中的“亲族”仅指同宗之族,唐律中多有用“亲属”二字,而无“亲族”用法,如亲属相为容隐、亲属相盗、亲属相奸等律文。故中国古代律例中的“亲属”指宗亲、族亲、姻亲,而“亲族”仅指同宗之亲。胡长清亦坚持中国古代有“亲属”而无“亲族”之说法。⑥郁嶷亦持此种观点。⑦
综上,此种说法坚持中国古代有“亲属”,而无“亲族”。中国古代律例中只有“亲属”,例文中没有“亲族”之说。且日本民法中的“亲族”实出自外文翻译,取自外国法学的“亲族法”的称呼,而不是出自中国古代典籍。因此,日本民法中的“亲族”不是中国古代“亲族”之义,二者不是同源关系,故日本民法中“亲族”和中国古代律例中“亲族”没有直接联系。中国近代四次民律草案以及《中华民国民法典》采用“亲属”命名民法典亲属编,实为近代中国民法沿用自唐律、明律、清律以来的用语而已。
4.否定“亲属”,主张用“亲族”来命名。
陈宗蕃对以“亲属”命名提出三点反对意见,一是“亲”字的古义包括宗亲、外亲、妻亲三种。二是“亲属”二字开始于明律,而非古义也。三是因为“亲属”二字仅能表示卑幼对尊长的亲属关系,而不能反映尊长对卑幼的亲属关系。故“亲属”的称呼并不能完全反映亲属法的内容和立法精神,与名称和内容不符。陈宗蕃进一步指出,“至名称亲属,而不沿日民之例称亲族者,则以大清律例所用亲属之字义,较亲族为稍广,与本法之规定相符也”[14]。陈宗蕃对“亲属”和“亲族”两词的辨析和其他民法学者观点一致,即“亲族”在中国古代专指宗族,“亲属”指宗族、外族、妻族三种亲属种类。但陈宗蕃氏认为“亲属”和“亲族”二者的意义是相同的。但“亲属”二字并非古义,“属”字有“系属”的意思,“有家者各以属为之服”,有卑幼对尊长之意思,而不能包括尊长对卑幼之关系,故用“亲族”命名较为妥当。
综上所述,通过以上对近代诸多民法学者对“亲属”和“亲族”两词的争论,反映了“亲属”这一词在历次民律草案和近代民法学中的演进过程。近代民法学者对中国古代的“亲属”和“亲族”有了一致的认识,即中国古代“亲族”仅指宗亲之一种亲属种类,而“亲属”在古代律例中则包括宗亲、外亲、妻亲全部亲属的种类,故近代历次民律草案和民国民法典运用“亲属”的称谓,这样反映了亲属法的基本内容(即全部亲属种类,而不仅仅规定男系宗亲的亲属权利义务,而是宗亲、外亲、妻亲全体的权利义务),故近代历次民律草案均以中国古代律例中的“亲属”命名。
而学者对日本民法中“亲族”和中国近代历次民律草案中“亲属编”的关系存在很多的争议。首先,《大清民律草案》前三编是由日本法学博士志田钾太郎、松田义正起草,而亲属编由章宗元、朱献文起草。亲属编也遵循了修律的基本原则,“求最适于中国民情之法则。……是编凡亲属、婚姻、继承等事,除与立宪相背,酌量变通外,或本诸精义,或参诸道德,或取诸现行法制,务期整饬风纪,以维持数千年彝于不赦。……[15]”既然制定《大清民律草案》亲属编注重本国风俗,那么应充分考虑本国古代例文中亲属相关条文如何在近代得到更好的继承和转变,“亲属编”的命名就应该和中国古代的亲属例文联系起来,从而找到最佳的命名方式,而不是和日本民法中的“亲族”来混淆,仅需要对中国古代的“亲属”和“亲族”进行辨析,从而为近代民律草案中有关亲属条文的命名作参考,《大清民律草案》就采取中国古代律例中的“亲属”来命名。
其次,日本民法中的“亲族”命名,固然有其渊源,而民国时期学者没有对日本民法中的“亲族”一词进行深入的考据,仅仅从表面上认为中国古代典籍中演绎而来的,或是从外国亲族法翻译而来的,如此简单的考据,是不能对日本民法中的“亲族”一词的来源有很强的解释力。毕竟日本在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之前,所适用的法律是参照中国古代《唐律疏议》为蓝本来制定的,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向西方学习,大量移植西方法律,来改造本国的法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法律体系和法律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故“亲族”这一词在这次法律大转型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或是沿用了中华法系的含义,或是完全西化,抛弃“亲族”的本义,而采取了西方诸国亲族法的含义,抑或是折中,既保留了“亲族”的本意,又加入了西方诸国亲族法的含义。因此,只有在弄清日本民法中的“亲族”一词的含义演变的前提下,才可以谈日本民法中的“亲族”和中国近代历次民律草案及民国民法典中“亲属”的关系。纵使清末修律时期中国以日本民法典为样板,请日本法学博士志田钾太郎和松田义正来起草民律草案前三编,但是亲属编是由中国人起草的,且符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以维持中国千年礼教为宗旨,故历次民律草案及民国民法典命名“亲属编”充分考虑了中国古代律例对“亲属”的定义,最终命名“亲属编”。
三、近代中国民法文献中的亲属种类和亲属范围
(一)立法
清末修律时期,《大清民律草案》⑧亲属编第一章通则主要规定了亲属范围、亲属种类、亲等计算法、亲系、妻于夫之宗亲、外亲的关系、嗣子与嗣父母的关系、由婚姻与承嗣成立亲属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一共六个条文。其中,第1317条对亲属种类作了规定,亲属种类包括宗亲、妻亲、外亲三种,并对亲属种类逐个进行了定义。
北洋政府时期,1915年《民律亲属编草案》第1条规定了亲属种类,即以夫妻、宗亲、外亲、妻亲四类,没有对《大清民律草案》进行改变,还是沿用原来的分类。此条直接是对《大清民律草案》的照搬,亲属范围中对“外亲”的定义少了“姑之夫族为外亲”之规定。至1925年《民国民律草案》亲属编总则中,针对亲属范围、亲等、亲属种类予以了规定。总则一共有八条。⑨第1055条规定了亲属种类,延续了《钦定大清现行刑律》以来,经《大清民律草案》所坚持的夫妻、四亲等内之宗亲、三亲等内之外亲、二亲等内之妻亲的亲属种类和亲属范围。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年法制局《亲属法草案》⑩分通则、婚姻、父母与子女之关系、扶养、监护人、亲属会议七章,共82条。第1条规定了亲属范围,以四世以内的血亲,三世以内的姻亲、配偶为限,采用寺院计算法来计算世数,以此确定亲属范围在纵向上的限度。为维持男女平等之原则,亲属种类采用血亲和婚姻两项事实标准,分亲属为血亲、配偶、姻亲三类。1927年法制局《亲属法草案》规定凡有血统关系之亲属,统称为血亲。血亲没有作宗亲与外亲的区别。而姻亲是指血亲之配偶、配偶之血亲、配偶血亲之配偶。姻亲中不再分宗亲与妻亲。法制局之《亲属法草案》仅有血亲和姻亲分类。亲系分为直系亲和旁系亲。
1931年《中华民国民法典》亲属编总则共有五条,第967条给出了不同种类亲属的定义,即以直系亲和旁系亲为准,与《大清民律草案》《民国民律草案》大不相同。首先,直系亲和旁系亲不再以“妻”作为“所出者或所从出”,而仅是以“己身”为中心来确定直系亲和旁系亲的计算标准。
其次,直系亲的定义较《大清民律草案》《民国民律草案》范围有所变化。即“从己身所从出”没有变化,但“从己身出之血亲”,强调了“血亲”二字。《大清民律草案》《民国民律草案》没有规定“从己身出之血亲”的亲属种类,而《中华民国民法典》不仅强调了“从己身出”的“血亲”,也改变了历次民律草案中的亲属分类,“血亲”代替了宗亲和外亲,同西方民法之亲属制度接轨,这样更准确地定义了直系亲,即“从己身出”与其有直接血缘关系的子孙,不论男女,包括历次民律草案中的外亲(如出嫁的女儿)和宗亲(伯叔兄弟之子及其子孙、姑姊妹之子及其子孙)。
再次,旁系亲的定义也有很大的变化。改变《大清民律草案》《民国民律草案》之“与己身出于同祖若父者”的表述方式,而用“而与己身出于同源之血亲”的表述方式,即不再用历次民律草案中“同祖若父者”的说法,取而代之是“同源之血亲”。虽旁系亲的范围变化不大,但同样采取了“血亲”的说法,向西方亲属制度靠拢。
复次,亲系分类。亲系分为三类,一是直系亲与旁系亲。直系系是指上溯己之所从出,下溯己之所出之亲系。旁系亲是指“由己所从出之直系亲分衍之亲系也”。[16]二是尊亲系与卑系亲,尊亲系是指与父母同辈及父母辈以上亲属,卑亲属是指子女及与之同辈以下之亲属也。三是男系亲与女系亲。男系亲是指以男子为连系者之亲系。女系亲是以女子为连系者之亲系。
最后,血亲之分类。血亲分为天然之血亲和拟制之血亲。天然之血亲是出于血统关系,于出生时取得血亲之身份;或出于婚姻关系而生血亲之分类。“非婚生子女,如昔之所谓私生子、庶子等。苟为生父所认领或抚育,以及其生父与生母结婚者,亦取得天然血亲之身份。否则,仅对于其生母有血亲关系,而对于其生父,法律上否认为其血亲也。”[17]拟制之血亲,本无亲生之血亲之关系,通过拟制建立亲属关系。尤其养子女与养父母。另外,《中华民国民法典》第969条指明了三类姻亲:一是血亲之配偶;二是配偶之血亲,如夫之父母为夫之直系血亲;三是配偶之血亲之配偶。1931年《中华民国民法典》不再列举亲属范围,仅规定亲属种类,以罗马亲等计算法来确定亲属关系的远近。
(二)司法实践
司法实践中,清末修律时期民事实体方面起作用的是《钦定大清现行刑律》中宗亲、外亲、妻亲三种亲属种类,亲属范围以服制图为核心。至北洋政府时期,民事实体法方面起作用的是《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大理院解释例、判决例、民事习惯、条理等。而《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是对《钦定大清现行刑律》的沿袭,故亲属种类分为宗亲、外亲、妻亲三类亲属。亲属范围还以服制图为中心来确定,并加之“三父八母”。
《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中有两条直接规定了亲属范围。第一条是“期亲祖父母条”,揭示了“期亲”的亲属范围,“期亲”并不以期服亲为限,不仅仅指祖父母,而是曾祖父母、高祖父母都包括在内。同样律中所称的“孙”,包括曾孙、玄孙。第二条明确指出了“嫡母、继母、慈母、养母”(11)四种身份与亲生母亲相同。嫡母指妾所生的子女,对父之正妻称之嫡母。前妻所生子女,称夫后娶之妻为继母。从小过继给他人者,称抚养自己的母亲为养母。子女的亲生母亲亡故,父将子女交给妾来抚养,子女称妾为慈母。上述“四母”因与子女感情深厚,自幼抚养,视同其亲生母亲。故子女与“四母”的服制关系为斩衰三年。
在大理院民国九年统字第1289号判决例中亲属范围不是光停留在《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确定的服制图之内,亦不受《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之束缚,尤其是在告争远祖坟地这一类民事案件中,“子孙对于远祖,应认为尚有宗亲关系”[18],亲属范围有可能溯源至宋元时期,可见亲属范围远超已经超出《中国民国暂行新刑律》第82条第二项本宗四等亲之外。由此可以看出大理院解释例对亲属范围进行了扩充解释。另外,大理院判决例四年上字第292号(12)规定了庶母在现行民事实体法中不认为直系尊亲属,对亲属范围又进行限制解释。
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至1931年《中华民国民法典》亲属编把亲属种类分为血亲和姻亲。至此,中国传统旧律服制图之宗亲、妻亲、外亲三种亲属种类,经过近半个世纪修律,终于采用血亲和姻亲分类方法,并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此种分类。同时,不再限定亲属范围,仅规定亲属种类,以罗马亲等计算法来确定亲属关系的远近。最高法院解释例和判决例对民法典亲属编进行了补充和扩大解释。如1928年判决例规定妾对亲生子女是直系尊亲属,而对于家长其他子女的不同。(13)进一步在最高法院解释例二十年解字第48号(14)对妾的法律身份给予了规定,妾不能与正妻相提并论,故被承继人之妾,不能成为承继人的直系亲属。但妾与自己亲生的子女为直系血亲,“若其所生之子女亡故,自可为其第二顺序之遗产继承人”[19]。又规定后母在旧律称为继母,后母与前母之子不是直系血亲关系,前母之子亦不是后母的卑亲属。(15)而后母与前母之子是直系姻亲,因为后母非父亲己身所从出之血亲。(16)对于子女方面,养父母收养不同性别的子女,养子和养女不是血亲关系。(17)子女因为父亲为赘夫,从母姓,并不影响其与父之直系血亲尊亲属的关系,因为这些亲属是己身所从出之血亲。子女与父之旁系血亲仍有尊亲属关系。故子女不因从母姓而影响其与父之亲属的关系。(18)又有血亲之配偶之血亲不在《中华民国民法典》亲属编第969条姻亲的亲属范围内,如“甲之女嫁与丙为妾,甲与丙之父丁既无姻亲关系”[20]。
在亲属立法中,从《大清民律草案》开始,亲属种类分为宗亲、外亲、妻亲三种,亲属范围包括四亲等内之宗亲、夫妻、三亲等内之外亲、二亲等之妻亲之内。一直到《民律草案亲属编》《民国民律草案》亲属编、法制局《亲属法草案》一直都是坚持宗亲、外亲、妻亲三种亲属。亲属范围到《民国民律草案》没有变化,仍沿袭了《大清民律草案》原条文。故在历次亲属法草案中,亲属种类仍坚持自中国传统旧律以来的宗亲、外亲、妻亲的三种。到《中华民国民法典》亲属编最终将亲属种类分为血亲和姻亲,亲属范围不再列举,而是以罗马计算法来设定范围、司法实践中,清末修律时期还是以《钦定大清现行刑律》宗亲、妻亲、外亲的为核心亲属种类,亲属范围是以服制图为核心确定。北洋政府时期《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及大理院解释例、判决例亦是坚持宗亲、妻亲、外亲三类,亲属范围亦是以服制图为标准确定。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亲属种类为血亲和姻亲,亲属范围不再明确列举,而是按照罗马亲等计算法划分血亲与姻亲的亲属之远近。
四、近代中国民法文献中的亲等
(一)立法
清末修律时期,《大清民律草案》第1318条所采用是寺院计算法,直系亲从己身上下数,一世就为一亲,而旁系亲就与直系亲不同,而是采取从己身或妻出发,算到同源祖父,然后从所要指代的亲属,由此人数至同源祖父,这样如果世数相同,那么就采用此世数。如果双方世数不相同,那么以世数多的作为亲等数。本条第二项也对直系亲和旁系亲作了明确的规定,即从己身或妻所出者,或与己身或妻同源所出,即为直系亲。而旁系亲是与己身或妻出于同源之祖。且亲等计算仍然以服制图为准。
北洋政府时期,1915年《民律草案亲属编》(19)第2条的亲等亦采用寺院计算法,亲系分为直系亲和旁系亲,相比较《大清民律草案》直系亲的定义,少了“非直系亲”的字样,后半部分完全一致,分析旁系亲的定义与《大清民律草案》实质上无异。第6条:“彼此互相同一亲等之关系。”亲属彼此之间适用同一等的亲等关系。本条是对《大清民律草案》第1321条的照搬。
1925年《民国民律草案》第1056条的亲等制度亦采用寺院计算法,延续了《大清民律草案》第1318条之亲等计算法。即直系亲从己身上下数,以一世为等亲,直系亲的亲等为相同。而旁系亲的亲等数如果相同,那就以相同数为准,如果世数不相同,以多数者为准。同时,对直系亲和旁系亲给予了法律的定义。又在第1060条规定亲属彼此互有同一亲等之关系,本延续了《大清民律草案》第1321条的规定。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年法制局之《亲属法草案》亦仍采用寺院寺院计算法,延续了前三次亲属立法的规定。至1931年《中华民国民法典》第968条彻底改变了这种格局,首次采用罗马计算法,一改历次民律草案之寺院计算法。《大清民律草案》《民律亲属编草案》《民国民律草案》、法制局之《亲属法草案》与服制图相对应,凡五服之内的亲属,均可包括在寺院计算法中。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典》第13条,亲属范围也是采取寺院计算法为标准来计算,与我国旧律服制图所列亲属之范围相吻合,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典》仍采用寺院计算法。南京国民政府为统一民刑两大法中的亲属制度,故在1931年《中华民国民法典》采取了西方普遍采用的罗马亲等计算法,故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典》最终要被修订,来维持与《中华民国民法典》一致的亲等制度。后来在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典》将亲等制度定为罗马计算法,修改了1928年刑法典的亲等制度,保持了与《中华民国民法典》亲属编一致。
其次,古代服制计算法与亲等计算法。亲等者,是表示亲属关系之远近。凡扶养、继承之相关事宜,应以亲等之远近为标准来确定扶养顺序之后,继承顺序之先后。亲等的远近计算分为两种古代服制计算法和近代亲属计算法。古代服制计算法是阶级亲等制,是“以血亲关系之远近,地位之尊卑,情谊之厚薄,男女之标准,就各种亲属,列举的定其亲等之谓也”[21]。我国古代没有亲等这一说法,但中国古代服制图,表示亲属关系之远近。近代亲属计算法是世数亲等制,即罗马计算法和寺院计算法,以血统之远近,世数之多寡为标准,从而免除中国古代服制图列举各种亲属以定亲等之繁琐。故近代历次民律草案虽“采宗亲之旧制,欲改用世数亲等制。现民法之亲属组织,既从一般法例,以血亲姻亲为准,则关于亲等之制,自亦以采世数计算为妥”[22]。故近代中国历次民律草案采取世数亲等制,前四次亲属草案均采取寺院计算法,是因为寺院计算法所包括的亲属范围与服制图相吻合。今《中华民国民法典》为适合国际立法趋势之罗马计算法,“以期合乎情理,而顺应世界之潮流焉”[23]。
最后,本条可分为直系血亲之计算法和旁系血亲之计算法。直系血亲之计算法从己身上下数,以一世为一等亲。旁系血亲之计算法是从己身数至同源之直系血亲,再由同源之直系血亲数至所要计算亲等之血亲,以其总世数为亲等之数。同时,《中华民国民法典》第970条进而对姻亲之亲系和亲等的计算进行规定,即一是血亲之配偶,从其配偶之亲系及亲等。二是配偶之血亲,从其与配偶之亲系及亲等。三是配偶之血亲之配偶,从其与配偶之亲系及亲等。
(二)司法实践
而在司法实践中,清末修律时期,清廷亦采用服制图之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等计算法。北洋政府时期仍采用服制图计算法,只是大理院判决例中对具体亲属关系的亲等进行了细化。如四年字第650号规定了对于儿子出继后,即变更与本家的亲等关系,“自难仍计算本法之亲等”。又有四年上字第1271号判决例规定在亲等问题上,异姓子与血统之子在族谱上宜有所区别,即“现行律例有异姓不得乱宗之明文,故从前旧谱若将异姓之子与血统之子显为区别者,自不得轻改其例,以紊乱血统”[24]。故异姓子在族谱上就有所区别,在族谱中与养亲亲族的亲属范围、亲属种类、亲等等方面有所差别,要区别对待。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司法实践中适用与立法中一致的罗马亲等计算法。
综上所述,亲等在未颁布的四次亲属法草案中,《大清民律草案》采用的是寺院计算法,到民国四年(1915)的法律编查会的《民律草案亲属编》,进而至民国十四年(1925)修订法律馆的《民国民律草案》亲属编,第四次到民国十六年(1927)国民政府法制局的《亲属法草案》,四次亲属法草案均采用寺院计算法,这是为了适应我国传统服制图的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的五等亲属计算法,传统服制图中的亲属均包括在寺院计算法之内。这仅是未真正颁布的草案而已。而在司法实践中,修末修律时期,民事方面起作用的是《钦定大清现行刑律》,亲等贯彻是服制图的五等计算法。到民国初年北洋政府时期,采用的《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及大理院解释例、判决例、民事习惯及条理,依旧使用五服图计算方法。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随着1931年《中华民国民法典》颁布,亲属法彻底丢弃了中国传统的服制图计算法,而采用了罗马计算法,自此实现了亲等制度与西方民法典上的接轨。
五、结论
纵观清末修律至民国时期的五次亲属立法,前四次均属于亲属法草案,虽没有正式颁布,但立法者一直在中国传统固有法与西方继受法之间摇摆,对亲属范围、亲属种类、亲等等亲属基本问题权衡再三,四次亲属法草案的制定时而进步,时而后退,使得立法者在“进步”和“落后”之间徘徊,进也难,退也难,陷入两难尴尬境地。立法上四次草案一直向西方亲属制度趋近,但因中国传统固有法的生命力如此之顽强,使得四次亲属法草案都不能社会中实施,无果而终。最终在1931年《中华民国民法典》亲属编确立了近代亲属制度。
司法实践中,真正民事实体法是《钦定大清现行刑律》《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大理院解释例和判决例和《中华民国民法典》亲属编、最高法院解释例、判决例,使得司法实践与亲属立法呈现出较大的差距和断裂。晚清民国近五十年的司法运作中,近三十年一直沿用了中国传统固有法的服制图为中心的亲属制度,只有在《中华民国民法典》亲属编颁布后才采用近代亲属制度,传统亲属制度一直向近代亲属制度转变,其实质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继受法文化的较量和冲突,即家族主义与个人主义,义务本位与权利本位,传统身份等差与近代平权立法,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较量和冲突。
[收稿日期]2012-04-22
注释:
①晚清民国时期五次亲属立法:第一次是宣统三年八月(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亲属编,学界称为“民律第一次草案”;第二次是民国四年(1915年)的法律编查会的《民律亲属编草案》;第三次是民国十四年(1925年)北洋政府修订法律馆的《民国民律草案》亲属编,学界称之为“民律第二次草案”;第四次是南京国民政府法制局的《亲属法草案》;第五次是1931年《中华民国民法典》亲属编。
②在清末修律中没有“邵义”一人,而有“邵羲”名字,此人为中国近代著名民法学者,参与《大清民律草案》中的起草工作,著有《民律释义》(民国六年二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一书,并与1911年3月同其他几十位法学才俊成立《法政发杂》。
而王志华所勘校的《民律释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中把作者的名字看错了,把“羲”看错看成繁体的“義”了,所介绍的作者“邵义”的生平跟“邵羲”的生平一致,而查陈玉堂先生的《中国近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根本无“邵义”此人。又查1911年3月所发起成立的《法政杂志》创刊号的成员名单中没有“邵义”一名,而只有“邵羲”一名。又见程燎原先生的《中国近代法政杂志的兴盛与宏旨》一文对《法政杂志》的介绍中,所列出的发起人只有“邵羲”一人,并没有“邵义”一人,故此处的“邵义”其实应为“邵羲”。
③屠景山,《亲属法原论》,上海世界书局1932年版,第5页。
④宗惟恭,《民法亲属释义》,上海法学编译社1932年版,第1页。
⑤赵凤喈,《民法亲属编》,正中书局1945年版,第2页。
⑥胡长清,《中国民法亲属论》,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页。
⑦郁嶷,《亲属法要论》,朝阳大学出版部1934年版,第1-2页。
⑧杨立新点校,《大清民律草案民国民律草案》,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页。
⑨杨立新点校,《大清民律草案民国民律草案》,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4页。
⑩《亲属法草案说明书》,载屠景山,《亲属法原论》,世界书局1932年版,第27-28页。
(11)郑爱诹,《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集解》,世界书局1930年版,第240页。
(12)郭卫,《大理院解释例全文》,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2年版,第912页。
(13)十七年上字第267号判决例。陈顾远,《民法亲属实用》,上海大东书局1946年版,第4页。
(14)吴经熊,《中华民国六法判解理由汇编》第二部,会文堂书局1948年版,第911页。
(15)最高法院解释例二十一年六月七日院字第774号。陈顾远,《民法亲属实用》,大东书局1946年版,第4页。
(16)最高法院判决例二十八年上字第2400号。陈顾远,《民法亲属实用》,大东书局1946年版,第4页。
(17)最高法院解释例二十五年三月二日院字第1442号。陈顾远,《民法亲属实用》,大东书局1946年版,第4页。
(18)最高法院判决例二十七年沪上字第117号。陈顾远,《民法亲属实用》,大东书局1946年版,第4页。
(19)民国北京政府修订法律馆,《法律草案汇编》第一集民事,1926年。
标签:民法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旁系血亲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民法基本原则论文; 文化论文; 历史论文; 直系亲属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