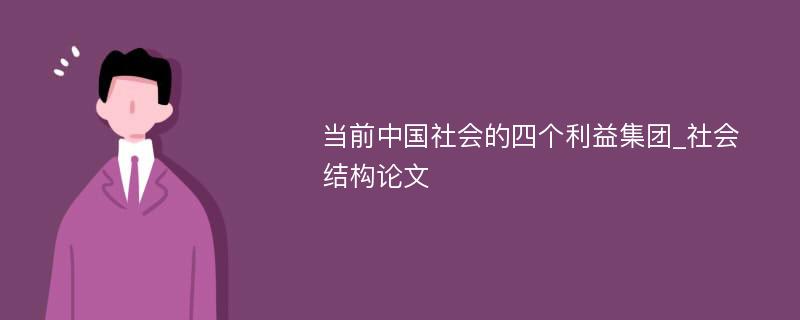
当前中国社会的四个利益群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社会论文,群体论文,利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试图从利益结构的角度,分析改革以来的中国社会群体利益关系的变化。为什么要从利益结构的角度进行分析呢?首先,改革本身就是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而利益结构的调整显然会使得一些集团或群体获得利益,同时会使得另一些集团损失利益。当然,“全赢”的局面——即社会每一个集团都获得利益,社会整体利益上升——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在目前要实现这种局面实在是太困难了。当前的住房体制、医疗体制、养老金体制、失业保障体制的改革,几乎每一项都难免会损伤一些人的利益。为使得改革顺利进行,我们就必须分析,这样的改革究竟对 于哪一部分人群有利,对于哪一部分人群不利。为使得我国的改革能够顺利推进,我们就应做到使改革措施尽量能够对于更多的人有益。这也就是边沁(Jeremy Ben-tham )提出的观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注: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78页。)
那么,二十年来的改革究竟使得哪些利益群体获得利益、哪些群体利益受到损失呢?为阐述这个问题,笔者先从社会群体利益分化的最一般观点谈起。
在中国大陆传统的社会结构分析中,社会学家大多使用阶级、阶层的说法。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人开始使用“利益群体”的说法。据考证,最先提出此种分析方法的是黑龙江的顾杰善先生。(注:参见顾杰善、刘纪兴等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利益群体分析》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11月第4页。)此后, 湖北的于真研究员和顾杰善先生等还承担了社会科学课题,专门对于“利益群体”进行研究。该课题组给社会利益群体下的定义是:“社会利益群体指在社会利益体系中,具有相同的利益地位,有着共同的利害与需求、共同的境遇与命运的群体。广义的社会利益群体泛指以各种不同的标准划分出来的有相同社会特质的人群,如以生产资料占有与否和是否受剥削为标准划分出的阶级,以某项社会差别的不同层次划分出的阶层,以具有某项特殊利益划分出的集团等等均可涵盖在内。”(注:顾杰善、刘纪兴等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利益群体分析》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11月第8页。)在此,笔者试对这一定义作一评价。笔者以为,对于利益群体下定义的关键是要解释清楚什么是“利益”,而上述定义的缺点就在于没有阐释清楚,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利益”。上述定义提出了“相同的利益地位”、“共同的利害与需求”、“共同的境遇与命运”,这样三个限定语。但是,三个限定语的涵义相近,并且,没有对于利益本身做出解释。反不如社会学在分析社会群体差异时所说的经济的、政治的(权力的)、声望的三个维度的解释更清晰。
笔者以为,所谓利益群体,核心问题说的是“在物质利益上地位相近的人所构成的群体”或者说“在经济利益上地位相近的人所构成的群体”。物质利益上地位相近的群体,在大陆,传统上称为“阶级”或“阶层”,为什么我们不直接使用“阶级”或“阶层”,而采用“利益群体”或“利益集团”的说法呢?这主要是受到“历史误区”和“大众心理”的影响。在1979年我国理论界拨乱反正以前,阶级、阶层曾经是非常流行的政治术语。当时,对于所有社会问题的分析,动辄就是“上纲、上线”为“阶级斗争”。而一旦称为阶级或阶级斗争,就可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所以,直到今天,说到“阶级”的概念,仍然会使人“谈虎色变”。历史的误区使得“阶级”一词在中国有了特殊的涵义,由于长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使得人民大众对于“阶级”一词普遍产生厌恶的心理和态度。所以,近年来,中国的理论界、学术界多采用“利益群体”或“利益集团”的说法,来反映在经济利益上、物质利益上有差异的群体。在笔者的论述中,“利益群体”和“利益集团”的涵义基本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是可以互换的词汇。
笔者使用利益群体范式而不使用“阶级、阶层”范式进行分析的另一个原因是,阶级阶层在涵义上是指利益分化已经完成、物质利益地位已经相对稳定的集团。然而,当今中国社会,利益结构变迁十分迅速,各个社会利益群体正在分化、解组(disorganization)、 “重新整和”(reintegration),因此, 使用地位相对稳定的阶级阶层概念就不太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经验研究中,笔者曾对于80—90年代的多种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社会群体出现了大范围的分化组合,很难发现稳定的阶级阶层。比如,1994年笔者研究城市国企职工,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无论在收入地位、福利待遇,还是在社会声望方面,它都是一个社会地位颇高的阶层。但是仅仅二、三年后,到了1996、1997年再做研究时,笔者发现国企职工的地位竟一落千丈。社会结构变迁速度之快颇使本人惊讶。这就迫使笔者不得不从利益结构变迁的角度来分析当今中国社会,而使用利益群体、利益集团的概念,有一种涵义在内,就是该集团内部的构成是随着利益的变化而随时调整的。所以,利益集团或利益群体的说法比较能反映出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现状。
本文根据改革以来人们利益获得和利益受损的状况,将中国人分为四个利益群体或利益集团,即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注:对于社会底层群体,笔者最初曾称之为“利益绝对受损群体”,下文有解释。)。四个利益群体观点的原型,最初是由笔者与孙立平教授、沈原博士在有关社会结构课题的讨论中共同提出的。(注:参见: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社会结构转型课题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第6—7页。 )四个利益群体或集团的说法突破了传统社会群体分析的界限。传统上,我们常常讲“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是我国的基本社会群体,后来又加上了个体户、民营企业家等。改革开放至今,从社会利益结构角度来看,原来的社会分层结构全都变了,如果今天还延用传统的群体结构的框架去分析,肯定会有很大问题,因为现在几乎每个群体内部都大大地分化了。比如农民这个群体,里面既有西南、西北贫困地区极端贫穷的农民,也有一些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的农民,有一些知名度很高的“农民企业家”。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近来分化得也很厉害,一部分名牌演员、歌星、记者、主持人成为“大腕儿级”人物,住高级别墅、开高档轿车,而有些乡间教师却因地方上发不出工资而生活拮据。所以,虽然都叫知识分子,但是,他们的利益需求肯定是不一致的。所以笔者试着从改革以来利益结构变迁的角度,把社会群体分成这样四个利益群体。
一、特殊获益者群体
这个群体在改革20年中获益最大,比如民营企业家、各种老板、经理、工程的承包人、市场上的各种经纪人、证券大户、歌星、影星、球星等明星,以及与外资、外企结合的外企管理、技术层等等。
改革初期的那些“个体户”、“万元户”现在已经从这个集团中退出去了,现在这个集团里主要是大企业主、外资企业的雇员,都是些获益很大的人,收入水平相当高。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这个集团的心态还算稳定,但是现在这个集团感到了制度环境对他们的威胁,其离散倾向很重。这是很奇怪的现象。这个集团在这场体制变迁中获益最大,本应是改革中“动力”最强的人,但是他们现在对改革存有很大疑虑,不少人手里都有外国护照,或者老婆、孩子干脆就移居国外,一旦有什么问题,他们马上就出去。当然这也与产权明晰有关,产权不明晰时,一些人可能还感到有自己的利益和动力在里面,一旦明晰了,倘若他们的利益得不到保证,他们的离散倾向就更加严重。
这个利益集团也包括国企的老总们。表面看,国企老总的收入相对是低的,为此老总们的抱怨很多,当然,老总们实际的经济利益并不少,但是,问题是很多经济利益不是通过正当工资收入获得的,所以,老总们一方面获得了实际经济利益,但是,另一方面,也对于收入待遇不满。褚时健的例子比较典型,他本人对于“玉溪卷烟厂”的成功贡献是很大的,然而最后却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广而言之,很多老总们、高层管理集团对改革的贡献很大,但是他们自己却感觉没有得到法律认可的回报。所以这个集团一方面是获得了很大利益,另一方面也对现状不满。
特殊获益者集团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有很大的变化。八十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时社会上开始出现一部分“万元户”、“个体户”,这是最初的特殊获益者。当时的问题是,这个群体的素质不高,引来人们所谓“不三不四的挣大钱”的种种非议。九十年代以后,特殊获益者的结构发生很大变化,越来越多的高素质者进入这个集团,这应该是一种社会正向的变化。1992年以后出现的文人下海,儒商现象,近来出现的所谓“知本家”现象都反映了此种正向的变化。
对于九十年代以后发展起的高素质的特殊获益者集团,用社会学的术语可以称之为“经济精英集团”。在任何市场经济的社会中,“经济精英集团”都是非常宝贵的社会力量。高素质的“经济精英集团”是保证一个国家经济起飞和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力量。所以,我们应该对于“经济精英集团”的形成给予肯定的评价。中国目前决不是“经济精英集团”太大,而是太小,和国际上的经济精英集团还无法比较和抗衡。试想,中国如果多出几个“李嘉诚”、多几个跨国企业,那对于中国经济的腾飞显然是至关重要的。当然,“经济精英集团”由于和社会其他群体的经济差异较大,这里面有一个如何协调他们与社会其他群体的利益关系问题。
总的来说,中国的“经济精英集团”形成的时间还甚短,与世界的高水平的“经济精英集团”相比,其本身的无论是管理技术素质、知识水平素质还是道德素质都还有很大差距。因此,中国的“经济精英集团”如果要真的对于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前提是必须提高自身的素质。
对于目前的特殊获益者群体,也可以称之为社会上层群体,它是相对于社会中间层和下层而言的。迄今为止,就我们在文献、信息和现实生活中见到过的人类社会而言,还没有发现过哪一种社会没有上、中、下的分层。所以,社会分为上、中、下层是正常的现象,不过,不同社会筛选分层的标准并不一样,有的注重于经济分层,有的注重于政治分层,有的注重于权力分层、也有的注重于声望分层。当然,无论是哪一种标准,都是要将高素质者筛选上去、将低素质者筛选下来。因此,我们特别强调,经济精英集团应由高素质群体构成,而要形成高素质群体的经济精英集团,就必须有正常的流动机制。所谓正常的流动机制就是使高素质者能够进入上层的机制和低素质者能够被淘汰出精英集团的机制。
二、普通获益者群体
笔者过去的研究证明,中国的普通获益者群体人数非常巨大,它包括各个阶层的人,其中既有知识分子、干部,也有一般的经营管理者、办事员、店员、工人、农民等。笔者在1996年曾主持过一次全国规模的入户问卷调查, 该问卷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让被调查者比较从1986 年到1996年的生活水平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结果,无论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很高比例的人均回答,“好了一点”和“好了许多”,而回答“生活变差了”的人比例甚低,具体数据参见下表(表1):
表1 中国城乡居民对于1986-1996 生活水平评价的百分比分布(1996年)
地区
样本数好了许多
好了一点
几乎一样
差了一点
城市3,087 52.7
30.9
10.6
3.8
农村3,003 49.2
39.58.5
1.6
城乡加 51.0
35.19.6
2.7
地区 差了很多合计
城市
2.0 100.00
农村
1.1 100.00
城乡加 1.6 100.00
从上表可以看到,高达83.6%的城市居民和88.7%的农村居民均认为他们的生活“好了一点和好了许多”,相反,认为生活变差了的城市和农村居民分别仅占5.8%和2.7%。1986至1996年是中国的体制改革迅速推进的十年,是体制变革从农村推向城市的十年,根据笔者的理论,是市场改革从边缘群体向核心群体推进的十年,(注:李强:“脑体倒挂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6期。)是商品市场改革急剧发展的十年。因此,中国居民对于这十年给予正向评价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我们可以断言,从物质利益的获得和受损的角度看,在中国有一个相当大的群体——由众多职业和阶层构成的群体——他们通过改革是获得了利益的。这是中国改革的非常重要的社会基础。在当前社会矛盾丛生、体制变迁困难重重的局面下,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还能稳步推进,多数中国人之所以还能对于改革给予认同,关键就在于有这个重要的社会基础。所以,笔者的观点是认为,普通获益者群体仍然是当今中国最大的社会集团。特别是当我们将中国的改革与前苏联、东欧的改革作对比时,就会更突出感受到普通获益者群体的重要意义。
1994年,研究人员对于东欧国家居民所做的类似调查,得出的数据和结论却与中国的情形完全相反。在对于东欧国家居民的调查中,回答生活水平“上升”的比例非常小,大部分人回答生活水平“下降”。东欧的数据是由两位著名的社会学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基分校的撒列尼(Ivan Szelenyi)教授和特雷曼(Donald J.Treiman )教授所主持的课题“1989年后东欧社会分层研究”完成的。该问卷中的此问题是:“与1988年时相比较,您现在的生活变好了还是变差了?”下面表2 就是回答者的百分比分布。
表2 东欧国家居民对于变革以后生活水平评价的百分比分布
(1994年)
国家 样本数好了许多
好了一点 几乎一样 差了一点
保加利亚 4,802 2.81
13.92 16.07 31.97
捷 克5,698 8.91
25.59 24.08 28.42
匈牙利4,380 2.09
13.58 18.11 36.28
波 兰3,54
6.97
20.42 17.66 26.77
俄 国4,747 4.88
12.39 18.08 23.80
斯洛伐克 4,940 3.55
14.27 19.81 36.20
加 权
4.94
16.85 19.21 30.63
国家差了很多合计
保加利亚 35.24100.00
捷 克13.00100.00
匈牙利29.94100.00
波 兰28.18100.00
俄 国40.85100.00
斯洛伐克 26.17100.00
加 权28.37100.00
资料来源:由UCLA的Donald J.Treiman和Ivan Szelenyi 教授提供。
从表2可以看到,相当多的东欧居民都表示, 他们的生活比变革前的1988年更差了。其中,俄国、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情况要更差一些,认为生活变差了的居民比例分别达到64.65%、66.22%和67.21%。 表中所有国家的加权平均值是,认为生活变差了的居民比例为59%;相反,所有国家里,只有21.79%的人回答说生活变好了。所以, 在东欧国家,利益受损群体的比例比中国的要大得多,而普通获益者群体的比例比中国的要小得多。由此指标我们也可以判断,比起包括俄国在内的东欧国家来,中国的改革要成功得多。
下面,我们试对普通获益者集团中的典型群体作一分析。那么,谁是典型的普通获益者群体呢?笔者以为,相比较而言,知识分子是比较突出的普通获益者群体。为什么这样说呢?笔者以为,与笔者所提出的劳动者参与市场两阶段理论(注:李强:“脑体倒挂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6期。)相一致,改革以来,我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变迁也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在市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即从1979年的改革开始,我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有了很大提高。作为中国改革起点的政治口号之一,就是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论断。这个口号的意义主要并不在于阶层划分的学术涵义,而是在于调整了社会改革的动力机制。在这一口号的影响下,知识分子从改革以前的“臭老九”、受批判、被改造群体,一跃而成为受尊敬的先进生产力代表。所以,这个口号使得知识分子在改革的一开始,就成为支持改革的最主要的社会群体。我们可以说,知识分子是市场发展第一阶段政治地位上升最快的群体,从政治地位很低的群体上升为政治地位较高的群体。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发展进入到第二个阶段,知识分子又成为市场改革的经济上的获益者。在这一阶段,与其他群体相比较,知识分子又成为经济利益相对上升较快的群体。所以,知识分子在市场转型的两个阶段都是获益者。在第一阶段,知识分子获得了政治利益,在第二个阶段,知识分子获得了经济利益。因此,我们可以判断,知识分子是中国市场改革中最为典型的获益群体。由此可以断言,知识分子会成为我国市场改革的最主要的支持者。
那么,知识分子成为改革最主要的支持者的意义何在呢?社会学在群体分析中,一般将社会群体分为两个最主要的集团,一个是“精英集团”(elite),另一个是普通大众集团。那么, 两个集团哪一个对于改革更重要呢?应该说,在任何时候都是精英集团对于社会的变革、发展起到最重要的作用。精英集团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其能量极大。普通大众集团之所以会发挥作用,最主要的前提条件就是组织起来。而大众集团之所以能够组织起来,也主要是因为有了精英的发动与管理。
普通获益者群体内部的情况也有很大差异。特别是,1995、96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经济增长的变缓,普通获益者集团的利益开始受损。收入增长开始停滞,很大一部分人开始从此集团分离出去。本人1994年的调查还能证明,绝大部分国企职工还是属于这个集团的,但是1995、96年以后的调查却证明,很大一批国企职工开始从这个普通获益者集团中分离出去,进入了下面的一个集团:“利益相对受损集团”。其原因主要是国有企业运行出现危机、经营的不景气愈来愈严重,突出的表现就是出现了大批失业下岗职工。
随着失业下岗问题的严重,普通获益者集团中一个很大的群体落入下面第三个集团,其表现之一是在流行语言中,“职工层”、“工薪层”成了低收入层的代名词。此种变化也是影响今天市场销售、造成市场不景气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80年代中期以前,社会的最主要消费群体是城镇的职工阶层。职工阶层是当时票证制度的主要获益者,他们手持票证到市场上积极购买各种消费品。而今天,这个集团由于经济地位的衰落已经不能积极地到市场上购买东西了,这是值得忧虑的。应该说,普通获益者集团是有消费能力的,但目前的状况是,他们就是不去消费,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对前途的忧虑。1995、96年以后,由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相对而言,他们的收入明显下降,又加上医疗、住房、养老、教育收费等项制度的改革或面临改革,他们发现,自己的收入基本上是三位、四位数字,而将来的每项改革都需要五到六位数的支出(注:笔者友人孙立平语。),所以他们不再敢消费了。笔者曾将职工层称为中国社会的“类中产集团”,就是说它处在类似于中间阶级的位置上,这个集团的生活水平如果得不到保障的话,整个经济就很难搞上去。
三、利益相对受损群体
通过对于第二个集团“普通获益者群体”的分析,已经可以看到,第三个集团的人数比例不很高。根据笔者前述的劳动者参与市场两阶段理论,相比较而言,市场转型的第一个阶段,一部分脑力劳动者曾出现经济利益受损的现象(即所谓“脑体倒挂”现象),到了市场转型的第二个阶段,经济利益相对受损的现象则主要发生在体力劳动者中间。目前,最为突出的利益相对受损集团就是失业、下岗职工群体。下面试对这个群体的状况作一分析,此处所使用的数据来自笔者与中国人民大学姚裕群教授于1998年组织的全国调查。该调查抽取了黑龙江、河南、山东、江苏、浙江、江西、广东、湖北、湖南、四川、北京、天津、重庆、内蒙、新疆、宁夏等16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并选择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城市,共完成1043份有效问卷。
首先我们看看,我国城镇中,失业下岗人员究竟有多少?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98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1%, 登记失业人数为571万。由于该数据既没有包括下岗人员也不包括待业人员,所以, 在失业分析上有很大欠缺。一般认为,我国的实际失业人数和失业率要高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笔者在与姚裕群教授的调研中,将失业下岗人员分为三类:登记失业人员、下岗人员(指虽已停止工作,但与工作单位还保持关系者)和待业人员(尚未找到工作的新就业求职者),这三类失业下岗人员的人数和比例如下(表3)。
表3 城市失业下岗人员比例
失业分类数 有效百分比(%)
登记失业人员30031.6
下岗人员 54557.4
待业人员 10511.0
不适合与未回答
93
missing
合计1043
100.0
从表3可以看到,登记失业人员仅为全部失业人员(包括下岗、 待业人员在内)的31.6%,这样,可以与上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相结合,由此推算出,全国包括下岗、待业人员在内的失业率应为9.81%,人数约为1807万人。从历史比较的角度看,目前的失业人数和比例还是相当高的。
关于城市失业下岗人员的构成,本次调研显示,从地域上看,失业下岗人员比较集中的是东北、西北和西南的一些老的工业基地。从行业上看,失业下岗人员多集中在工业制造和采矿业等行业,在本次调查中,占了45.8%。从单位经济类型看,失业下岗人员多集中在国有、集体企业,根据本调查,90.9%的失业下岗人员是来自国有、集体企业。而且,这个集团的利益受损是比较长期性的,据我们的调查,失业下岗后,处于长期失业状态的人员比重较大。(参见表4)
表4 您失业下岗已有多长时间了?
失业的月数 人数 有效百分比(%)
6个月以下 304 34.0
7-12
141 15.8
13-24 205 23.0
25-36 103 11.5
37个月及以上
140 15.7
不适合或未回答 150 missing
合计1043100.0
由表4可以看到,失业下岗7个月及以上的长期失业者达66%,而且
竟然还有15.7%的人失业37个月及以上。
很多失业下岗人员的生活也是比较困苦的,下面我们试比较一下他
们失业前和失业后的收入情况。
表5 失业下岗人员,失业前与失业后的个人月收入对比
失业前 失业后
有效样本959 673
missing 84 370
平均收入(元)419.71 235.07
标准差(元) 365.14 173.15
最低收入(元)30.00
20.00
最高收入(元)6000.00 1230.00
表5反映出,与失业前的收入相比,失业后这些人的月收入锐减,
当然,失业者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很大,最高的1200元以上,最低的月收
入仅有20元。当我们询问那些既得不到救济,又陷入贫困的人是如何维
持生活时,我们得到了如下的回答(表6):
表6 您靠什么维持生活? (多项选择,并按重要性排序)
多项选择
依靠下列方式次数 百分比(%) 按重要性排序,加权得分
靠过去的存款积蓄252 29.4 666
亲戚朋友接济254 29.6 635
打零工 195 22.8 486
借钱156 18.2 296
合计857 100.0
由表6可以看到,生活困难的失业下岗人员, 维持生活的两项最主要手段是:“靠过去的存款积蓄”和“亲戚朋友接济”。由此可见,对于这些人来说,存款是他们的保命钱。在此情景下,无论银行怎样降低存款利率,这些人也不会将存款转入消费市场。
总之,以上的数据证明,我国失业下岗职工人数多、失业时间长,失业后生活水平骤降、维持生计困难,这确实是典型的利益相对受损群体。下岗人员的利益相对受损还表现在社会地位、社会身份的变化上。市场改革以前,国有企业职工是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都比较高的群体,国企工人曾经是人人羡慕的职业。市场改革以后,随着国有企业的不景气,国企职工的地位已经有所下降,现在又遇到了失业的现实,更使人有一落千丈之感。
前面的第一个集团和第二个集团都从改革中获得了利益,而这里的第三个集团则相反,他们在改革的现阶段利益受到了损害,所以,他们当然会对改革不满或持否定态度。其实,从绝对的客观标准看,我国城镇中的失业、下岗人员并不是生活条件最差的人,如果与中国农村地区的贫困群体相比、如果与中国西南、西北地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生活相比,城镇中的失业下岗人员的生活状况还是要好一些的。但是,要注意,失业下岗人员从不和这些贫困地区的农民相比,他们总是和城市中没有下岗的人相比较、总是和生活比较好的人相比较,同时,他们也和没下岗以前的生活相比较。这样一种心态,在理论上称作“相对剥夺感”或“相对丧失感”,英文是relative deprivation。
在此笔者试用相对剥夺或相对丧失理论范式对于失业下岗职工作一个分析。最早提出相对剥夺范式的是美国社会学家斯托夫(S.Stouffer),他认为,相对剥夺感是社会不满和社会动荡的重要源泉。 相对剥夺感是一种很矛盾的心理状态,此种心态的产生是由于,人们将自己的命运与那些既和自己的地位相近,又不完全等同于自己的人或群体作反向的比较。此种心态变得强烈是由于,人们所对比的群体变成了自己的潜在对手。(注:斯托夫(S.Stouffer):The American Soldie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5.)社会学家默顿(R.Merton )则用“参照群体”(reference group)的理论来解释相对剥夺感,即关键是人们将哪一个群体视为自己的参照群体、同哪一个群体比较。从绝对的生活条件看,中国改革二十年来,人们的绝对生活水准有了很大上升,如果与二十年前的粮油票证制度相比、与每月每人只有半斤油、一斤蛋的供应相比,今天,即使是失业下岗人员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上升。但是,今天的失业下岗人员并不是用那个时期的工人生活作参照,前面已经说过,他们也不是以农民作为参照群体。那么,谁是失业下岗人员的参照群体呢?他们往往是以未下岗的人员作为参照,他们往往是以国有企业管理者的生活作为参照。而使得许多失业下岗工人感到最为不满是,一些国有企业管理者挥霍企业的钱财,贪污腐败,一些国企经营者打着改制的旗号,转移企业资产,将原本运转较好的企业关闭,辞退大批工人,抽出资金,以参股、合资的名义、甚至以他们自己的名义另建新厂,甚至将企业据为己有。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腐败的国企管理者就成为下岗工人的参照群体,并由此引发失业下岗工人强烈的不满和相对剥夺感。近来,类似的事端在一些地方激化了失业下岗职工的矛盾,甚至引发了社会冲突。此种情况尤其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那么,以失业下岗人员为主体的“利益相对受损集团”是否会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安定,是否会引发较大的社会动荡呢?笔者以为,目前的失业下岗问题虽然严重,但还不至于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安定。这里面有两种情况不要忽视。
一是隐性就业的现象。据笔者观察,我国城镇失业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实际上处于就业状态,或曰“隐性就业”,即:名为失业、实为就业。根据笔者在劳动局组织的一些“再就业服务中心”的调查,前来找工作的失业人员中,有1/3的人承认,目前正在从事有收入的工作。至于那些没有到“再就业中心”来找工作的失业人员,隐性就业的比例可能还要更高些。迄今为止,大陆人头脑里所想象的“就业”,是指将自己的档案转入一个单位并享有该单位的一切“劳保福利”,如果只是干活挣钱,即使是每周干48小时那也不算就业。在笔者的调查中,下岗工人就是这样回答的。
二是“生活机会”现象。中国地盘大,各地区千差万别,例如,东北、西北、中部地区失业问题比较严重,东南则缓和很多。我国总共有670多个城市,城市之间失业问题也很不相同。据笔者观察, 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大城市,象北京、上海、广州以及各省省会等,这些城市是国有企业职工最为集中的地方,也是失业人数最多的地方。然而,大城市因人口聚集的效应,经济机会和就业机会也比较多。这些地方的下岗职工和失业市民主要是“放不下架子”的问题,他们不愿意从事那些所谓“伺候人”的工作。另一种是中小城市,这里的经济机会不多,职工下岗后很难在本城市找到工作。不过,这些城市的国企下岗人员不是很集中。再者,中小城市的城乡分界不明显,不少职工下岗后在家里养猪、种菜等等,自谋生路,据笔者的观察,这里的生活机会也还是有的。
再者,失业下岗人员,在家庭内部也得到一定的补偿。这不仅因为,大陆家庭内部成员联系密切,而且也在于,自五十年代起,中国已将阶级体系打碎,此后,一家之内阶级混杂的现象是常有的,家庭成员中有下岗的,也有变成“款爷”的。家里面一个成员富有之后常要接济其他成员,国企职工下岗后,兄弟姐妹、父母子女之间常有互助。80年代是父母给孩子钱,现在倒过来了,是孩子给父母钱。
笔者以为,我国失业问题的真正危机,在于年轻一代失业的增长。本人的研究已经证明,目前的失业还主要是中年以上人的失业。在未来的一段时期里,有一种可能性,即失业的主体将从年纪大的一代人转为年轻的一代人,未来的毕业生将面临着毕业即是失业的危机。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那会是对于社会安定的最大威胁。解决的办法也只有靠保持和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率。
四、社会底层群体
社会底层群体的说法听起来不那么悦耳,但是,这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一个社会事实。且不说中国边远山区的特困人口,就是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中国最富裕的超大城市里,我们每天都目睹着乞丐群体、制假贩假群体甚至犯罪团伙等等。在做四大群体分类时,笔者起初称之为“利益绝对受损群体”,主要是与“利益相对受损群体”相区别,后来考虑到改革以来很难说有哪一个群体一点没有获得利益,所以,想来想去还是称之为“社会底层群体”比较符合实际,类似于英文的underclass一词。
实际上,从逻辑上讲,利益的获得与受损是一个过程,而底层、中层和上层是利益分化的一种结果。在此意义上,也可以将第一个群体称为上层,第二个群体称为中层,第三个群体称为中下层,这样,第四个群体就可以称为底层群体了。笔者以为,对于目前的各个社会群体之所以难以命名,恰恰反映出中国的社会群体分化还远没有形成。
笔者以为,社会底层群体可以有经济底层、政治底层的区分。1949年以后,中国在经济方面实际上打碎了阶级体系,从1949年—1979年,中国并没有经济意义上的底层社会。那时大家生活水平都不高,但在城市里也没有明显的“贫民窟”之类的现象,反倒是现在的城市里出现了“富人区”、“穷人区”。但是,改革以前,中国社会上确实存在着政治底层群体,比如“地、富、反、坏、右”就是当时社会的政治底层。笔者以往所阐述的经济分层与政治分层原理,就可以解释当时社会的政治分层状况。 (注:李强:“经济分层与政治分层”《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4期。)
从经济上说,所谓“底层群体”是指经济收入低于贫困线以下的社会群体。传统上,我国经济收入低于贫困线的群体主要是在农村地区。1984年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研室最先提出了我国农村居民的贫困线。按此规定,集中连片贫困乡的标准是:人均年收入120元以下; 人均口粮,南方水稻产区400斤以下,北方杂粮产区300斤以下。1985年以后,我国农村人口的贫困标准大体定在两条线上,即,人均年纯收入150元以下为赤贫户,200元以下为贫困户。按照这个标准测量,1986年5月,我国农村人均年纯收入200元以下的贫困者有1亿零200万人,占当时农村总人口的12.2%;而人均150元以下的赤贫者有3643万人, 占农村人口的4.36%。据世界银行估计,按1990年当年价格计算,1990年中国农村的贫困线为年人均275元,农村低于贫困线的人口有9700万人,占农村人口的11.5%。根据中国官方数据,1992—1993年,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约8000万人,占农村人口的8.8%。根据1999年的统计, 到1998年底, 中国农村的贫困线依地区之不同而设定在年人均纯收入600元至750元之间,贫困人口4200万人,占农村人口的4.83%。 根据2000年初的统计,农村贫困人口为3400万,占农村人口的3.91%。如果用这个比例与1978年比,据中国官方统计,1978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为2.5亿人,占农村人口比例为31.1%,那么,20余年来中国贫困人口的比例确实是大大下降了。然而,这是不是说20年前中国有一个庞大的“底层社会”,而今天已经大大缩小了呢?并不能这样说。20年前,中国社会处于普遍贫穷的状况,社会上存在着比例相当庞大的低收入层。但是,在经济上,群体之间的相对差距不是很大,所以,很难说谁是底层,谁是上层。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占统治地位的是绝对平均主义的观念。例如,物质生活水平很低的所谓“贫下中农”,在精神上、政治上却被置于较高的位置上。当时是政治分层社会,政治地位是人们的首要地位,经济地位倒居于次要的位置。根据社会学原理,首要地位是判定人们社会地位的主要依据。因此,在当时并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所谓“底层社会群体”。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从政治分层社会进入经济分层社会,今天倒比较容易看到经济上的底层群体。
由此看来,底层社会是由如下的几个群体构成的:第一,西南、西北集中联片贫困地区,那里的贫困人口还有约3400万(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99年底,中国绝对贫困人口为1200万)。第二,下岗工人中的生活极端贫困者。第三,贫困农民和一大批流入城市、居无定所、无正当职业的农民工。
底层群体的构成比较复杂,其内部的差异性也很大。虽然,很大一部分贫苦村民都是老老实实的农民,但是,确有一部分底层社会群体明显地具有社会仇恨性质。例如,最近报载的中国河南平顶山地区的郑营村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绑架勒索活动的村民,广西出现专门拐买儿童的家族,武汉江岸西站的竹叶山段铁路上活跃着“偷盗游击队”,不少地方出现了专门抢劫过往乘客的团伙(笔者的学生在协助笔者做社会调查时就遇到过光天化日之下拦截长途汽车进行抢劫的团伙)等等。底层社会明显带有反社会倾向、社会暴力倾向,这对改革威胁很大,成为改革的不稳定因素,例如严重的暴力犯罪现象层出不穷,对社会损害很大,社会治安不好,少数犯罪团伙将社会搞得人心惶惶。一些抢劫团伙甚至打出劫富济贫的口号,这是比较可怕的。
当然,底层的犯罪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原因,下面表7 显示了对于在押的城市农民工罪犯的调查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犯罪的经济原因。
表7 被调查的犯罪民工解释他们处于经济困境的原因
原因 百分比
无工作35.0
开销太大 10.0
赌博输光
2.5
工资被克扣25.0
其 他27.5
合 计
100.0
资料来源:俞得鹏:《浙江省城市外来民工犯罪问题研究》宁波大学法律系1998年10月第51页。
从上表可以看到,高达60%的流动人口犯罪者,他们在经济上陷于困境的原因是没工作或工资被老板克扣。可见这部分人的犯罪,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没有经济上的来源和保障。
迄今为止,社会保障制度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底层社会的状况。全国总工会近年对失业工人的调查发现,只有1.7 %的失业工人领到了民政部的救济,25.4%的人拿到了单位的救济,余下的人就哪儿的救济也没有了。更何况,笔者1998年的调查发现,一些拿到了社会保障金的人不是生活最困难的人,许多生活最困难的人并没有拿到社会保障金。而且,目前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只是针对城市居民而言。而底层社会不光是城市居民,还有很大部分是从农村到城市来的流动人口、民工群体,这部分人对社会的威胁比较大。所以,从长治久安的角度看,我们最终还是要建立起能够覆盖全社会的保障体制。
标签:社会结构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精英阶层论文; 失业证明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群体心理学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精英集团论文; 精英教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