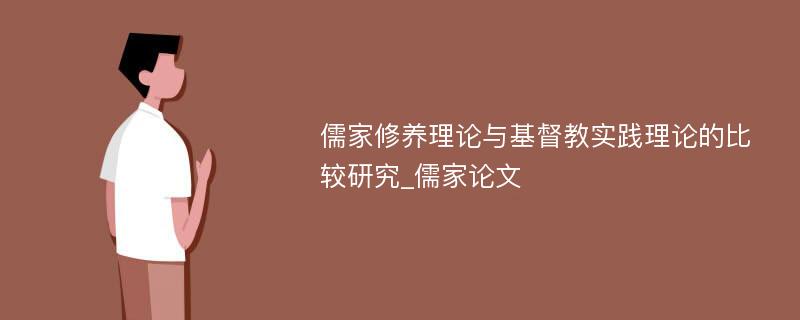
儒家修养论与基督教修行论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基督教论文,修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 B[,5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627(2001)04-0015-12
在当代西方思想界,将精神修养或道德修养视为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融合的重要基础的观点是一个较为流行的见解。这种情况不仅与精神修养或道德修养在双方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有关,而且与道德修养在当代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有关。就此而言,比较研究儒学的修养学说和基督教的修行学说,对于理解儒学和基督教的道德修养学说的同异和实质、反思传统文化的精华并进行现代化的诠释,将是有所裨益的。
一
在中西方传统的伦理学说中,儒学的修养论与基督教神学的修行学是可以相互媲美的,二者都是一种完整的理论类型。如果以现代眼光来看儒家的修养论,可以发现它是一种集形而上学、认识论、心理学、道德修养学说、人生学的特点于一身的理论类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儒家的心性论是形而上的修养论,而儒家的修养论是实践的心性论。同样,从现代的眼光来看,基督教的修行学也是集德性论、心理学、宗教活动学说、形而上学多种学科的特点于一身的。仅仅在道德修养活动的意义是无法全面而忠实地理解和把握儒家的修养论与基督教的修行学的。在《尼各马可伦理学(Ethika Nikomakheia)注释》里,托马斯·阿奎那把伦理哲学分为修行学(以最高目的对各种行为的制约性为研究对象)、经济学(以个体所固有的德性为研究对象)和政治学(以个体的公民行为为研究对象)三部分。在这里,修行学的理论意义显然不是道德修养活动学说甚至宗教活动学说所能概括得了的。
修行的词义起码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1)学习、教学、教导的意义;(2)教训、培养、训练的意义;(3)学说、理论、艺术的意义;(4)组织、纪律、制度的意义;(5)习惯、原则、方式的意义。修行如此宽泛的词义,与其担负体现人生的总体性的努力活动的概括性范畴的地位是相称的。事实上,修行在基督教中就是一种包括各层次的总体性人生活动的个体宗教活动。就儒家的“修养”范畴而言,虽然不一定包含像修行如此之多的词义,但缺少以上五方面的任何一个要素,也无法把握它的完整内容。修养首要的前提是学习,没有学习就无所谓修养问题。作为士大夫,儒者是知识的承载者和传播者,是社会知识的良心。没有教与学的相长,既谈不上修养,更谈不上儒者士大夫的身份;修养作为人类活动的一般含义就是培养、训练、磨练,因为修养是人生的一种自我超越过程,是生命在刻苦挣扎中的一种成长或自我放大过程;修养论是儒学的重要学说,是实践形态的心性论;修养与“家—宗族—国—天下”的社会结构或曰以人伦关系为核心的宗法家族制度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个体修养以之为依据;修养的结果自然表现为体现人之所以为人的行为方式、习惯或品性,高超的修养还表现为心灵或言行的境界。无论是修行还是修养,都不仅仅局限于道德修养的意义,然而,道德修养作为渗透于人生的各个方面的实现人格的基本活动方式,则在修行、修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因为,道德修养的基本内容,就是完成人之所以为人、实现人所当然的活动,这正是修行、修养的实质,是儒家的修养学说和基督教的修行学说最根本的契合点。舍此无法正确地理解和把握儒家的修养学说和基督教的修行学说。
儒家认为,通过道德修养,人才能作为主体由“格致正诚、修齐治平”的途径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或真正的人。基督教认为,通过道德修养,人可以摆脱现世的束缚或局限,享有与无限的真善美相联系的高尚生活。儒家的社会化的人,并非世俗的人。儒家并不停留于认可生理学意义上的人。在儒家,衣食往行色欲也是人的属性,但只是一种生理本能,并非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而修养之所以必需,就在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因此,儒家的修养本质上仍然是一种高尚的人生活动。基督教的修行则明显地将自身与尘世生活区别开来。修行不在于培养社会化的人,而是个体享有与神相联系的超凡脱俗的人生方式。这是一种高尚而纯洁的人生。对于基督教而言,与绝对本质相悖的现世人生是与生俱来的罪,修行就在于以严格的戒律摒除尘世利欲之罪。正因如此,修行往往是思辨性的,远离尘世现实利益。修养则与社会现实利益息息相关,因修养主体是现实利益关系的承担者。利益关系是主体和主体之间的内在联系。修养的目的是高尚的人格,而完美的人格以德性为起码的要素。为此,修养活动必然内含道德活动于自身,并以道德价值为人生修养活动的指南针。儒家重视道德修养活动在于道德活动在人生总体活动中的核心地位。同理,基督教也非常重视道德活动,视之为接近上帝的最基本的方式和途径。譬如说,如果上帝是绝对的爱,那么,爱具体的个人、邻人,则是靠近这种绝对的爱的途径。无论是儒家的修养还是基督教的修行,其实质都在于人格的一种自我超越,或曰人性的一种自我提升。对于人类而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这种自我超越或自我提升都是一种永远不会完结的过程。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价值依据。
二
无论是修行还是修养,作为道德活动,最基本的意义都是心灵回到自身,即反省、反思、自省、内求。儒家要求经常性的反省。曾参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孔子要求在反省过程中以善去恶,克服缺点发扬优点。《论语·里仁》有言:“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公冶长》有言:“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孔子的“内自省”的教导在后儒中一直延续下来。在孟子那里,反省已被提高到不怨天不尤人并勇于直面自己的境界。《孟子·离娄上》有言:“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公孙丑上》有言:“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在反省过程中,心灵回到自身,检查主体的动机、意识和行为过程的善恶、是非、正邪、荣辱,由基本的伦理尺度衡量其应当与不当。这是道德修养最基本的活动方式。
自我反省,是人格在心理意识上建立的标志,因为在自我反省中意识主体已经把自己作为客体或放在客体的地位上来对待,完成了人格的初步自我超越。托马斯·阿奎那要求人回到自己:“‘首先跑到你的房中,在那儿,开始转向于用心智做一些事。’追求越多表明自制越多,这是智慧的特权。在外部的工作中,一个人依赖许多他人的援助,但通过个人独处的沉思默想,他工作起来更为老练。因此,《圣经》经文要求一个人回到自身,要求他首先‘跑到’他的房中,并且在他能够受到感染之前避免外界的干扰。所以说,‘当我走进我的房屋时我将依赖她。’这就是依赖智慧。全部心思都集中于智慧的存在并且不迷失;因而经文补充道,‘在那儿返回自身’,换言之,使思想完全集中,房屋是安静之地,而且思考的人是一心一意又充满热望,那么接下来要做的事是开始;‘在那儿转向心智’。”(注:托马斯·阿奎那《基督教箴言隽语录》,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周丽萍、薛汉喜编译。)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人是自己的主人,在于人有自由判断的能力,即舍此就彼或舍彼就此的选择能力。人为了选择,必须判断;为了自由地判断,必须能判断自己的判断,即反省自身。人只有回到自身,才可能对自身的缺点或错误做忏悔。忏悔是一种出于罪感而对缺点、错误、罪过所进行的反省。对于宗教忏悔的作用,W·詹姆士说道:“对于一个忏悔者来说,假的东西过去了,开始了,(一个人)清除了他的腐朽的东西,假如(一个人)尚未能实际摆脱它,(他)至少也不再用伪善的德行表现来掩盖它了。”(注:转引自玛丽·乔·梅多、理查德·德·卡霍著《宗教心理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92页,陈麟书等译,吴福临、陈麟书校。)忏悔的实质是人格自己真正面对自己,意识到自身的缺点、错误、罪过对自身人格而言是必须清除的虚假的朽臭。反省、忏悔的反面就是虚伪。虚伪从外的方面说,就是巧言令色、口心不一、两张面皮,以不违反社会规范的外表来掩盖不道德的实质;从内的方面说,就是自我欺骗,不能真正面对自身存在的不属于自己生命的缺点、错误、罪过,认可虚假。对自己不能实事求是,必然产生对反省或忏悔的歪曲。由于虚荣心,人可能对自己的缺点、错误、罪过有过分的罪感而导致过分焦虑,不能保持跟随真理的平常心;反之,由于不敢面对虚假的自我,对自己的某些缺点、错误、罪过不予确认,甚至对犯错的事实加以否认,处于讳疾忌医心态,是自我人格尚未充分建立的表现。忏悔作为改正错误的手段,是一种“忠诚疗法”,不是过于频繁、过度自我折磨的苦修,不是回避自身虚假的空洞而草率的活动。忏悔的实质在于个体作为有限存在返回无限的真实即上帝。人作为有限存在必然有缺点、错误、罪过,问题是能不能直面虚假,归依或皈依绝对真理。这是出于自由意志的选择。
同理,儒学的反省非常讲究诚意。《大学》有言:“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由此可以看出,反省关键在诚意:一者,不自欺欺人,过则勿惮改。孔子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子贡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二者,返诚归真,出于应当选择天道。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诚是天之道,天是绝对真理;思诚、诚之是人之道,即择善固守、选择归依绝对真理。朱熹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之道也。’此言天理至实而无妄,指理而言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之道也。’此言人当有真实无妄之知行,乃能实此理之无妄,指人事而言也。”(《朱子语类》卷64)在返回自然或本性的意义上,《孟子·告子上》提出:“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可见,儒家的反省和天主教的忏悔的本质都在于抛弃虚假而追求真实的生命。对此,罗光教授指出:“天主教的伦理思想和儒家伦理思想相同的一点,是于两家伦理都注意内心。”(注:罗光著《士林哲学(实践篇)》,台北,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143页。)罗光教授清楚意识到儒学和基督教在注重心性修养方面人类意识在自我反思中追求真实的共同本质。
反省和忏悔的精神实质都是有限的真实或善向无限的真实或善的一种依归,所以反省和忏悔的目的都在于追求生命、强化个体的生命力。偏离此点,反省和忏悔活动只能导致焦虑和自我折磨,导致生命力的弱化,从而失却其真实意义。意识不到此点,不仅无法理解忏悔的罪感基础,也无法理解反省的耻感基础。在反省和忏悔的过程中,情欲的冲动往往被视为一种无法控制的强大生命力,对情欲的压制也因而往往与对生命力的压制混淆起来,从而导致对其精神实质的误解。为此,对知、情、欲问题的探讨是双方共同的重要课题,下面将继续讨论。在此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儒家的修养论还是基督教的修行论,虽然每个个体都没有等同于绝对的无限真理或善,但也不能说绝对的无限真理或善在反省或忏悔的个体之外,因为绝对的无限真理或善的原理是反省和忏悔活动的内在结构或支柱。如果一切是相对的,反省和忏悔就成为无目的、无意义的活动。
三
修行、修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使心灵的理性、感情、欲望达到水乳交融的和谐统一。儒学和基督教都以理性为人之本性,但对于理性与感情、欲望的关系,各自本身就有不同的理解。在儒学内部,有人倾向于讨论理性与感情、欲望的统一关系,因为任何理性都必然伴随着特定的感情、欲望,要求情欲与理性相适应,防止情欲异化为与理性分离的因素。这种倾向在儒家居于主导地位。有人则倾向于讨论理性与情欲的对立关系,对天理和人欲的对立关系在学理上细加分辨。这种倾向以程朱理学、王阳明哲学为代表。后者虽然在政治上影响较大,但其地位在儒家学理中并不突出,甚至理论上的偏激之处受到毫不留情的抨击。在基督教内部,将理性和情欲视为二元对立的思想是一种基本的路线,绝大部分思想家将感情、欲望视为与理性相对立的肉体生活的特性,将感情、欲望视为魔鬼占据人类躯体的一种邪恶属性,但也有人倾向于将情欲做评价上中性的理解,比如托马斯·阿奎那。因为,对于基督教,肉体生活与心灵生活不是分割的,肉体生活的有限性有可能成为心灵生活的累赘,也有可能服从理性,归依上帝。
在理性与感情、欲望的关系问题上,修行、修养显然有不同的形而上基础。就儒家修养论而言,理性与情欲之间不是二元对待,而是一元心性内的体用关系。《中庸》提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这对心性与情欲的中和、体用关系是明白的阐发。由于理性和情欲二元对立的观点并不是儒学主导性观点,不能简单地把儒学中的天理人欲之辩与基督教的理性和情欲二元对立观点等同起来。在宋明理学中,并非所有的学者都赞成天理和人欲对立的提法。陆九渊认为:“天理人欲之言,亦自不是至论。若天是理,人是欲,则是天人不同矣。”(《象山语录》上)至于王安石、王夫之、戴震等数十位思想家,更是明确地将天理和人欲的关系视为体用关系。使理性控制感情和欲望,让情欲的发动与理性相适应,是儒家道德修养论的重要内容。(注:请参见拙文《传统儒家道德义务思想研究》一文第四部分论述,《孔子研究》1997年第2期。)在程朱理学,符合天道的感情和欲望也是天理,不符合天道的情欲才是人欲。比如,朱熹认为:“天理本多,人欲便也是天理里面做出来。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朱子语类》卷13),所以他以饮食为天理,食而求美味为人欲。然而,将食而求美味视为违反天道,很难为大部分儒家学者认可,无怪乎程朱理学为戴震所激烈抨击。儒家讲究寡欲、节情,视之为修养之要,是在情欲于理性的控制下顺道发动,从而与理性达到和谐统一的意义上讲的。以食而求美味为不合天道,寡欲、节情就有灭欲、灭情之嫌。既然心性和情欲的关系是体用关系,情欲作为心性的中规中矩的表现就是自然而应然的,而与心性对立则是例外而异化的。
就基督教的修行学而论,理性与激情(感情、欲望)是一种二元对待,因理性属于对无限上帝的分有,而情欲属于有限的肉体生活。因此,情欲与理性的对立是易然而经常的,情欲对理性的服从是艰难而非必然的。修行的本意就是严格的自我制约和刻苦的自我训练。虽然基督教以理性与情欲的二元区分作为自身的理论基石,但不等于理论上它就一定认为理性和激情是不可调和的。在理性驾御激情、肉体生活服从心灵生活的意义上,理性与激情的相容在基督教是一种自然的理论延伸。托马斯·阿奎那属于认为理性与激情可调和的少数大家。他引证亚里士多德以下的话,“一个节制者欲求他所应该欲求的东西,以应该的方式,在应该的时间。”(注:亚里士多德著《尼各马可伦理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4页,苗力田译。)并提出:“德性的完善并不是完全取消激情,而是控制激情。”(注:Saint THomas Aqui-nas,THe Summa Theologia,I-I,95,2.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Volume19,Encyclopaedia Britannica,Inc.1980,23th printing,P508.Translated by Fathers of the English Dominican Province,Reviced by Daniel J.Sullivan.)那么,理性对激情的控制是怎么样的一种控制呢?他说:“据说灵魂控制肉体是按照暴君似的规则;但理性支配激情的生活是按照公民的规则,因为感觉欲望有它自己的一些内容并且因此能够抵抗理性的支配。因为根据它的性质,它受到控制,不仅是由于由普遍理性指导的特殊理性而且还由于想象和感觉。当我们想象某些被理性禁止的令人愉快的事物时,或者某些被理性控制的令人不愉快的事物时,我们经历一种抵抗。这并不拒绝服从。”(注:《基督教箴言隽语录》第198页。)在这里,“理性支配激情的生活是按照公民的规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由此可知,与儒学一样,基督教也可能强调理性、感情、欲望的和谐统一。这是两家修养学说在知、情、欲问题上的精髓。作为对立教派的天才哲学家,弗兰西斯教团的邓斯·司各托、威廉·奥康则认为意志的本性是自由,意志既不受制于欲望也不听令于理智,理智、意志和欲望作为人的灵魂的部分相互配合,任何一个部分不能统摄或代替另一部分。至于一生历尽迫害和苦难的彼得·阿伯拉尔更是明确指出诸如性欲、食欲之类的人的自然欲望本身并不是邪恶:“既然肉体的自然满足很明显不是罪恶,那么这种满足必然伴随着的快乐感情同样也不能称之为罪恶。”(注:转引自赵敦华著《基督教哲学1500年》第261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至于邓斯·司各托、威廉·奥康的意志主义亦可参见同书的第480-485页、第519-520页。)根据基督教的学说,善在于由较低的层次上升到较高的目的,恶则在于由较高的目的下降到较低的层次,那么,感情和欲望本身就无所谓内在的善恶与否,只有情欲处于由较低的层次上升到较高的层次或由较高的层次下降到较低的层次的情况时,才会产生高尚或卑劣的问题。如果感情和欲望处于理性的控制或命令之下,就是道德的。(注:参见THe Summa Theologia,I-I,24,1的论述,第727页。)故基督教并不必然以感情和欲望本身为恶,而只以背离绝对真实的上帝、投奔虚假为恶。感情和欲望的正确导向性是德性的开始。
四
修行、修养表现在现实生活中,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学习,二是过社会生活。
儒家强烈的士大夫责任感总是使之自觉地担当起社会学识和社会良心的职责。因此,对于儒家而言,学习是修养最基本的途径之一。一事不知,儒者之耻。孔子重好学,要求立志向学。《大学》的“八条目”,首先就是“格物”、“致知”。子夏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作为修养的方式,儒家强调学习的目的是切切实实地有得于己。因此,为学为己是儒家的重要原理。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对此荀子的解释是:“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荀子·劝学篇》)程颐进一步解释道:“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知于人也。”(《论语集注》)学贵为己,为己贵自得,因此之故,《孟子·离娄下》有言:“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其大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陈献章对读书与自得的关系有很深刻的体会。他说:“夫学贵自得也。自得之,然后博之以载籍。”(《陈白沙年谱卷一》)所谓自得,就是自得于心,即实实在在有得于己,充实和培养自己人生途中接人待物、守分尽责的高尚道德人格。陈献章说:“学者苟不但求之书而求诸吾心,察于动静有无之机,致养其在我者,而勿以闻见乱之,去耳目支离之用,全虚圆不测之神,一开卷尽得之矣。非得之书也,得自我者也。盖以我而观书,随处得益;以书博我,则释卷而茫然。”(《道学传序》)这种自得于心就是体验、体认、体察、体觉、体会、体味、体证、体悟道本体的工夫,或总称为体验的工夫。通过知行合一的体验把握本体,使心明意清、神与道会,才真正是自得于心。读书证之于心,以求以心契道、自得于心,这是心学一派的法门。
儒学的所谓修养,不是脱离现实社会的活动。儒家强调在日常生活的现实活动中进行修养。《大学》云:“如切如磋,道学也;如琢如磨,自修也。”可见,修养就是要在事上磨炼,犹如治玉一般的切磋琢磨,方可成功。对此,朱熹说:“善在那里,自家却去行他。行之久,则与自家为一;为一,则得之在我。未能行,善自善,我自我。”(《朱子语类》卷13)陆九渊也认为践履是道德修养的根本或根基:“要常践道。践道则精明,一不践道,便不精明,便失枝落节。”(《象山语录》上)王守仁更是一贯强调要在事上磨炼、随地用功:“区区格致诚正之说,是就学者本心日用事为间体究,践履实地用功,是多少次第、多少积累在,正与空虚顿悟之说相反。”(《传习录》中)所以他主张“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主张“知行合一”,认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同上)可以说,离开社会生活或社会活动,儒家的修养就一无所是。
基督教哲学家本身就是社会知识的承载者和传播者。秉承亚里士多德以来为求知而求知的传统,许多经院哲学家以异乎常人的力量不懈地体认和追求真理,颇多百科全书式的渊博学者。作为修行方式,求知是为了获得接近上帝的能力。出于社会义务是上帝所要求的,基督教的修行学不反对履行尘世职责,因为履行尘世职责能增加上帝的荣耀。但是,基督教修行学与儒家修养论不同的是,儒家的修养虽然也指向超越性目的,但就其重心而言,是属于尘世的活动,而基督教修行虽然不反对履行尘世职责,但就其重心而言,是一种出世的宗教活动,重来生于今世。修行虽然也可以在尘世中进行,但与修道院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即与特定的宗教机构或组织相联系。对于儒学的修养论而言,修养作为一种灵魂的净化,它是有社会化的内容的,换言之,灵魂的净化与社会化过程是同一件事情。而修行作为一种灵魂的净化,虽然也包含着社会化的内容,但社会化只是灵魂净化的手段,即通向上帝的途径或阶梯。这一点不同,从儒家与基督教对不朽的理解之区别也可以略窥一斑。根据《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的记载,儒家的“三不朽”是:“立德、立言、立功”,其价值主要是属于尘世生活的,尽管本身具有超越性。基督教的“不朽”则是指灵魂不朽,其实质在于获得上帝的恩宠,进入天国。对此奥古斯丁说:“天主舍弃人时,灵魂就要死亡,如同灵魂离开肉身后,肉身就要死亡一样;若灵魂为天主所弃,它亦与肉身分离,那末就是人的死亡;因为天主已不是灵魂的生命,灵魂不是肉身的生命了。整个人的死亡,是圣经上说的第二次死亡。”(注:奥古斯丁著《天主之城》,台北,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442页。吴宗文译。)奥古斯丁指出,圣人接受第一次死亡,即肉体的死亡,而避免第二次死亡,即灵魂为上帝所遗弃的那种死亡,以达到不朽。灵魂不朽的根据,在于灵魂是来自上帝的赋予,灵魂不朽的可能,在于灵魂不背离上帝。在此我们看到儒学与基督教的重要区别:基督教将神圣或理想的实现寄托于宗教机构或宗教活动,以神圣或理想去对抗尘世,从而修行是一种培养超越尘世价值的活动;而儒学将神圣或理想的实现寄托于社会活动特别是政治活动,以神圣或理想去美化尘世,甚至以神化个体君主作为达到理想的方式。
因入世与出世立场之区别,儒家修养论与基督教修行学对人的主体性有不同理解。儒家相信在现世通过修养人人皆可以为尧舜,由“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与天地参。天道生生,修养活动就在于人的自强不息,故儒家强调“刚”,要求培养顶天立地的浩然之气。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陆九渊也要求人“自得,自成,自道,不倚师友载籍”,“自立自重,不可随人脚跟,学人言语。”(《象山语录》下)同是由修养而发挥生命力,在儒学为高度独立的主体性,在基督教则为对上帝的依归。基督教是一种启示宗教,启示是基督教的基石。在基督教,人对上帝的认识依赖于上帝的启示,人绝对不可能依靠自己认识上帝。修行不仅依靠个体自身的努力,而且更主要的是依赖上帝的恩宠。如果不是来自上帝的超越性力量的帮助,人无法依靠自己完成修行。而儒学则认为人人生而有与天为一的人性,每个人通过自己的修养都可以与天为一。在自尊和谦卑的关系上,儒学强调人格的自尊和精神的自立,但又敬畏天命。基督教强调意志自由的尊严或不可侵犯性,但更强调个体人格在上帝位格面前的谦卑。托马斯·阿奎那说:“像大地一样按照谦卑的原则,听众应该是身份或地位卑下的:‘哪儿有谦卑,哪儿也就有智慧’。”(注:《基督教箴言隽语录》第144页。)既然基督教的谦卑是在上帝位格面前人格的谦卑,那么在上帝面前人格一律是平等的。因此,对个体人格的侵犯是在上帝面前的一种狂妄和无知,个体之间关系维系的前提条件是人格的不可侵犯。由基督教的谦卑得出的必然结论是人格平等,而不是对强权或政治势力的服从。同理,由儒学的畏天命,得出的结论必然是为儒家学者广为服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由此看来,假如不是歪曲的话,强调主体性的儒学和强调谦卑的基督教都同样没有倾向于个体人格的依赖性或奴性,相反,依其内在逻辑得出的政治结论必然是:在上帝或道德面前人人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格神圣不可侵犯。对主体性不同的理解却在理论上得出相同的个体独立和平等结论,这实在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
五
修行、修养作为人生的整体过程,自然会表现为不同的阶段。无论在基督教还是在儒家,修养都是一个从低级境界向高级境界发展的过程。孔子在自述其人生时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在此,孔子指出了自己人生修养过程的六个阶段。孟子则论述了修养、境界的不同层段:“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孟子·尽心下》)在整个过程中,“善”、“信”、“美”、“大”皆处于渐进的现实可感的道德修养阶段,而由“大”到“圣”或“神”则为一非人为的飞跃。在基督教中,修行也同样体现为不断地向更高境界发展的阶段。比如,圣维克多的雨果和理查德师徒二人,前者把人皈依上帝的过程分为阅读、沉思、祈祷、执行、洞察五个阶段,认为在穷尽世俗的知识之后,可以达到神秘的最高境界;而后者则把人和上帝的关系分为感觉、想象、推理、沉思、洞察、狂迷六个阶段,在最后的狂迷阶段达到对上帝的忘我的爱。一般说来,修行的发展有三个阶段的境界。第一个阶段是顺从戒律。在此阶段,修行是由于修行者相信被告知修行是出于他的利益。修行者在修行中体现到对自己的真正好处,证明被告知的宗教教育或理论是正确的。第二个阶段是修持,即一种习惯性的遵守。在此阶段,修持者已经体验到修行对自己的好处,相信修行在自己身上起到一种积极的作用,而且正在改变自己的整个生活。因此,修持者心甘情愿,高高兴兴地进行修持。第三个阶段是崇拜,即一种内在型的宗教修行。在此阶段,修行者不再关心修行对自己的好处,超越了出于对自己的好处而进行修行的境界。修行者用爱心崇拜那个独一无二的上帝,因为上帝在其心中,并使这一切成为可能。儒家修养与基督教修行虽然就发展阶段而言具有不同的方式,但都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那就是都从道德修养出发,逐步达到“天人合一”或“神人合一”的境界。每一个个体的人生境界都可以通过道德修养而进展,这在古代哲学和伦理学是一个重要的结论,它意味着人的价值有了自身的根据,即人自己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人生富有价值,完全不需要依赖于任何其他人或外部世界的赋予。
修养、修行的最高境界就是与天、上帝、绝对、无限、存有融而为一的神秘境界。在基督教的灵修体验中,我们可以看到与上帝交合或融而为一的境界有以下诸方面的表现:第一,它是一种个体与整体、有限与无限相统一的或相融合的心灵感受,在此,心灵有一种回归本体的满足感和愉悦感,充满了由极为痛苦转化而来的狂喜;第二,它是超越相对的变动世界进入绝对的静态心域的心理体验,在此,心灵超越了感觉和理性所能认识和把握的有限世界的变动事物,只默观或静观感觉和理性不可认识、无从把握、无可通晓的本体。心灵所体验的对象是不可言喻的,所以体验上帝在基督教被称为“说不可说之神秘”,而这在道家哲学中也被称为“无”;第三,它是心灵摆脱有限世界或感觉、理性的束缚而进入无限世界的一种自由。在此,心灵由于解放而有一种由模糊、昏暗而在刹那间进入心灵通体明亮的体验。在从基督教的教父学学者那里可以看到对这种境界的典型描述:“在我看来,人最值得向往的境界就是:关闭感官对外的种种接触,逃离肉身和这个世界,重返他自己之内,除非绝对必要,中止与任何人类的接触,只与天主交谈。生活在一切具体可见的事物之外,常在内心戴着神圣的肖像,常常清纯,总不被世上迅速流逝的各种杂物触及;成了真正的、日益加深的了无尘埃的明镜,照耀神圣者和神圣的事物,并在自己的光内接受两者的光,以自己微弱的萤光,赢取它们无限璀璨的光芒;在希望中收集已有的,未来的生活的果实。生活在与天使的交往中,虽然仍羁留在世上,然而遨游于世外,让圣神带入更高远的境界。”(注:转引自王晓朝著《神秘与理性的交融》,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17页。关于基督教修行最高境界亦可参见王晓朝教授的描述。)
儒家的天人合一,与基督教的与上帝交合有着相似的体悟。儒家的修养存在于世俗义务的履行过程之中,是在世俗利益中经受考验的一种超脱,当然,儒家也要求不受外界干扰的必要个人独处的空间,虽然不借助一系列的宗教仪式,儒家仍然能在个人独处的安静空间里进入超越感觉和理性的心理活动,进行难以言说的对无限或绝对的体验。陈献章就是通过静坐方法学求道的例子:“于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约,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间种种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衔勒也。体认物理,稽诸圣训,各有头绪来历,如水之有源委也。”(《白沙子全集·复赵提学佥宪一》)在此,静坐的目的在于保持心境的虚静统一,以便直接与道相契。在心境平和、不为物化的情况下,最易于达到对世界和人生生命的最深邃本质的一种整体洞见。当然,儒家的虚空不是佛家的寂灭无闻,而是随事顺应而不滞于物,是一种有无相成、动静相生的静。所以,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的儒家修养论不像基督教最高境界的体验是一种痛苦之上的极乐,而是一种轻松的、超逸的精神自由。孔子的“吾与点也”,孟子的“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就是这种最高境界的心理体验。这种对道体的把握是一种“抽象的具体”的把握,即只能是动态的,不可能有相对固定的形式。虽然可用语言形式留记,但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概括无遗,因为以有限的语言表达无限的道体总是一种无法摆脱的矛盾。王阳明说:“道之全体,圣人亦难以语人,须是学者自修自悟。”(《传习录》上)天人合一境界,儒家称之为物我两忘的浑然天地气象。孟子说:“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上》)《中庸》有言:“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陈献章说:“终日乾乾,只是收拾此而已。此理干涉至大,无内外,无终始,无一处不到,无一息不运。会此则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霸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来今,四方上下,都一齐穿纽,一齐收拾,随时随处,无不是这个充塞。”(《白沙子全集·与林君博七》)在此,人类的心灵把自身融化于外在客体之中,使主体和客体的对立、差别消融,超越主客体的对立,超越人和外在世界的隔绝、阻滞、障碍,人和世界同为一体,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成为这个世界的内在构成,在自我反思中把自身同化于外在对象(客体)的本质、规律。
修行、修养的最高境界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一致的,如果有区别,也仅仅是理论把握方式的区别。在此意义上,也许可说儒学的修养论境界是一种道德型的天人合一境界,而基督教的修行学境界是一种宗教型的天人合一境界。就前者而言,归于天或融于唯一,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就后者而言,归依上帝或神人如一,则是任何一个无助的人都可以得到的救助。李振英教授提出天人合一的三种境界:自然境界、道德境界、宗教境界。自然界是物我一致的体验,如民胞物与,天下一家。相对于认知关系、意志关系、审美关系而言,大自然是真、善、美之存有。在美感中透过感觉内容直觉本质。道德境界起点是人,终点是至善。天命是至善的天命,至善是天命的至善。处于此境界的人们在宁静幸福的道德精神中体验更有深度的天人合一。在宗教境界中,无限者与人的关系不仅仅是因果关系、立法者与守法者的关系,而且是父子关系、人格与位格(另一位)的关系。事天是一种继续不断的工夫。人心与天心相接时,便在无限的爱中融合。心灵要时常回到沉默,便是要与上帝交谈,从无限的爱吸取不尽的活力,然后去扩大存在的圈子,为别人服务,从而不会遭遇到自我贫乏及空虚的危险。(注:参见李震著《人与上帝》,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卷,第4章第4节。)在笔者看来,三种境界的划分只是理论性质的划分,三者彼此之间并无高下之分,彼此之间总是相互渗透的,在理论性质上被划分为自然境界的天人合一境界可以包含道德境界和宗教境界,在理论性质上被划分为道德境界的天人合一境界也可以包含自然境界和宗教境界。虽然可在理论性质的意义上将儒家修养的境界理解为道德境界,但应当意识到儒家修养的境界本身不仅包含物我一体的体验,而且包含超越的意义。与基督教修行境界的宗教意义的不同在于,儒家的超越境界从性质上来说不是外在超越性,而是内在超越性。在基督教的天人合一境界中,有限投入无限具有超自然性质,上帝的位格性和意志性历来受到强调。作为超越者,上帝虽包含作为被超越的自然,但同时也是高于自然或自然之上的存有。相反,在儒家的天人合一境界中,天不是自然的超越者,天是自然的,道是自然的,人、心、德性也是自然的,天、道、自然、人性、良心、仁这些范畴一以贯之,都是彼此贯通而非相互隔绝的。《中庸》有言:“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由此看来,儒家的道德型的修养境界也是天地境界,事天配天,与天地参,具有深刻的超越内涵,其立意与基督教的宗教境界一样悠深而高远。
(本论文系辅仁大学中西文化研究中心补助课题)
标签:儒家论文; 基督教论文; 自我修养论文; 人生的意义论文; 人格结构理论论文; 修养论文; 读书论文; 文化论文; 大学论文; 国学论文; 道德修养论文; 朱子语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