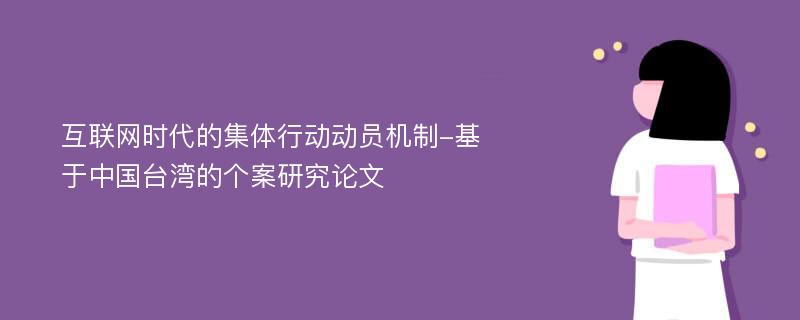
互联网时代的集体行动动员机制
——基于中国台湾的个案研究
蔡一村
(广州大学 台湾研究院,广东广州510006)
摘 要: 互联网时代,信息通信技术(ICTs)深刻影响了集体行动的动员过程,但其作用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挖掘。本文认为,互联网时代的集体行动并不必然遵循传统的动员逻辑,去中心化的、个性化的路径同样可以实现动员。通过对“3·18反服贸运动”的个案分析,本文发现,互联网时代的集体行动通过以下三个机制实现动员:通过重复暴露机制,相似主题的运动号召得以不断出现在潜在参与者的社交网络中,积累了巨大的动员效果;通过压力遵从机制,运动参与者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观点,不仅实现了自我激励,还对其他群体成员施加了参与行动的社会压力;通过居间联络机制,ICTs把原本相互隔绝的政治支持网络联系到了一起,动员信息广泛传播于秉持不同诉求和意识形态的群体之间。
关键词: 互联网;集体行动;连结性行动;动员机制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ICTs)的进步与普及,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当代政治,尤其是抗争政治的样貌,是集体行动相关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从21世纪初利用短信进行协调的抗议活动,到通过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实现动员的“阿拉伯之春”“占领华尔街”等社会运动,新技术背景下的一系列抗争造成了重大的社会和政治影响。与传统社运相比,新形态的集体行动往往呈现出扁平化、去组织化和去中心化特征。有学者将这样一种绕过传统政治组织、通过ICTs直接面对群众进行动员的政治参与行为,称为“快闪政治”(flash-mob politics)[1]。
本文选择发生在2014年的“3·18反服贸运动”作为研究对象。这场运动作为华人本土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发展历程中的一次重要事件,不仅对两岸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是台湾社会内部诸多脉络的“事件化”[2]展现,是一个值得深入分析的典型案例。
5.农田水利施工机械。按照2011年中央1号文件的部署,今后一个时期,中小河流治理、病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农村饮水安全、抗旱水源工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等工程将是“十二五”期间国家水利投资的重点,这类项目普遍强度不大,且大部分项目规模相对较小,所以中小型机械特别是一些衍生机种将在水利机械市场占有更大的份额。在挖掘机、推土机或装载机上研发多种附属装置,以适应小河、灌溉渠道的疏浚清淤、坡面修整等施工需要,将大有市场潜力。同时,为支持和配合节水型、环境友好型农业,应研究开发各种节水灌溉机械,渠道的开挖、修坡和混凝土连续衬砌机械以及节水型喷灌机等设备。
先后成立于2004年和2006年的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为众多抗争提供了虚拟舆论场与联络平台,而2005年之后才逐渐普及的“第三代移动通讯技术”(3G)和智能手机则为抗争的动员提供了技术保障。从“野草莓学运”“白衫军运动”到“3·18反服贸运动”,台湾“快闪政治”的动员模式与演化脉络渐次显现:通过ICTs,互不相识的人们被串联起来,共同参与行动;在行动之前,他们既不受传统实体组织约束,也没有象征性的、统一的集体身份认同。那么,这些异质的、碎片化的群体是如何被动员起来的?ICTs在这一过程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实证材料的情境化分析,挖掘ICTs在“快闪政治”动员过程中产生作用的机制。研究发现,ICTs使集体行动的动员逻辑发生了演变,通过“重复暴露”“压力遵从”“居间联络”这三个机制的共同作用,集体行动在没有正式组织参与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实现并长期维持。
二、文献综述:集体行动逻辑中的ICTs
ICTs如何影响集体行动动员,这一问题在社会运动领域的研究中已得到大量关注。目前大多数文献依循着经典解释框架,主要包含两种研究取向:一种取向将新技术视为一种新兴资源,集中探讨了新技术为动员提供的有利条件;另一种取向则聚焦于现象背后的社会机制,试图说明新技术是如何促进动员的。
第一种取向以描述性研究为主,罗列出互联网利于动员的种种特征。研究指出,新技术在降低信息传播成本的同时提高了统治集团的镇压成本,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集体行动动员过程中的物理障碍和地理区隔。[3]在一些案例中,ICT精英借助技术力量就足以与政府对抗,而少数“运动企业家”依托互联网也有能力发动大规模的社会抗争。[4]例如,有学者指出,Facebook、PTT、Yahoo!、Live这类数字化平台的多人互动特征不仅使台湾的社运精英能够迅速传播运动信息,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关注度,还大大提高了运动的组织以及管理效率,保证了社运精英能够更加持久地开展抗争活动。[5]
这一类研究将新技术视为社运精英动员“工具箱”中的新武器,善加利用就能够提供正向的动员效果。然而,新技术并非被某个社会群体或世代所垄断,ICTs既可以为试图发起抗争的社运精英提供支援,也可以被需要遣散抗争的政治精英所利用。[6]也就是说,这类带有技术决定论色彩的成果缺乏中层理论(mid-range theory)的支持,我们不能理所当然地默认新技术就必然有利于动员,而要在具体情境中分析其作用机制。
为弥补前者的缺憾,第二种取向重点关注线上与线下的交互行为,试图挖掘新技术的影响机制。甘瑞特主张从以下三个维度来讨论ICTs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动员结构(mobilizing structures)、机会结构(opportunity structures)和构框(framing)工具。[7]具体而言,在宏观结构层面,ICTs有效地扩大了运动者的政治机会及其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范围,允许参与者通过网络交流来获得认同感和成就感,争取话语权并建构其道义优势。[8]在中观组织与关系网络层面,ICTs既能够通过微博、业主论坛、QQ群等数字化媒介,提供某种具有集体行动能力和利益诉求的自组织,[9]也能够在已有人际关系网络基础上发起动员,促进群体成员参与到集体行动当中。[10]在微观个体层面,ICTs为参与者集体认同的形成提供了互动平台与认知基础。与主流媒体不同,新技术所承载的庞大信息流没有筛选机制,这使社运精英得以更有创造力地激发受众的情感与道德感知,进而凝聚起异质化的庞大人群参与抗争。[11]
这一类研究所遵循的经典理论脉络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上,即新技术的引入没有改变集体行动的核心动因。其逻辑的出发点落脚于某种先于集体行动动员存在的必要条件,既可能是有能力执行“选择性激励”机制的正式组织,也可能是足以建构出集体身份认同的人际关系网络。[12]
这根源于学界对奥尔森“搭便车困境”(free-rider problem)的回应。麦卡锡和左尔德从社会运动的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问题入手,探讨运动组织乃至社会运动“产业”规模是如何影响集体行动动员的。[13]其中,基于组织强制力的“选择性激励”(selective incentive)机制通过整合和分配各种资源,保证了组织成员的团结。[14]除此之外,事先存在的人际关系网络同样能够有效影响集体行动的动员。[15]格兰诺维特将关系网络分为弱联系与强联系。[16]在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由诸多启蒙报刊杂志的读者所构成的弱联系关系网络,是欧洲社会革命运动得以产生的基础;而在二战后的台湾地区,工人之间的兄弟义气凝聚了一个个强联系关系网络,各自内部的道德压力形塑了劳工运动“支离破碎的团结”。[17]
提出分类方案的总体要求。5.2.1“立档单位应对归档文件进行科学分类,同一全宗应保持分类方案的一致性与稳定性”;
显而易见,这些成果在特定的情境下具有足够的解释力。在当代中国大陆,国家治理的制度安排建构了社会中的政治过程,进而诱发了基于无组织利益之上的集体行动。[18]而ICTs的出现,则通过其具备的多人互动性为社会中的潜在运动者提供了低成本的互动空间。运动者在其中形成组织、编织关系,补充了现实中正式组织的缺位,提高了人们建构集体认同的可能,进而提升了动员能力。
当今社会,科技的发展使得复制的艺术很难得到大众的认同,因此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对其再造才是更好的出路。再造不是直接抛弃过去的所有,而是将自身发展,甚至到极致。艺术作品在每个阶段都会有那个阶段的文化特征,而现代青花瓷艺术特征正是无数个陶艺家汇聚的总和,在众多的个性中存在着共性,是当今社会的物质文化产物。但是在创作的同时又不能完全摆脱传统、与过去断层,因此在进行现代青花创作时必要的需要吸取传统青花文化的精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深作品的文化内涵才能使现代青花艺术瓷加深印象深入人心。
海量相关信息在虚拟空间中的富集,提高了大规模动员的可能性。在相关研究中,重复接触到相似动员信息的英国选民更有可能外出投票。[34]而如果某个争议性话题的细节在不断重复中被逐渐完善,那么这一话题的动员效应强度和持续时间将不断提高。[35]
如果我们回顾台湾的社会运动发展就会发现,传统的议题型社会运动往往由深耕于相应领域(例如劳工、环保、LGBT、人权等等)的运动组织发起动员,运动的诉求和参与群体相对单一,结盟行为一般也仅发生在特定议题内部。[50]在工人运动领域,台湾几个主要团体之间甚至充满对抗。但我们却注意到,在这场运动中,多元的运动者之间尽管理念、诉求、运动方式有着明显差异,却仍在没有组织或者政党介入的情况下维持了长时间的共存。
为确保校企合作实验平台项目的落地,应广泛听取校、企双方专家的意见和建议,详细落实校企合作的各个衔接点,设定实践项目的目标、内容和实施方案,双方的权利和责任具体化,保证合作模式能够稳定持久,并随着合作的日益成熟继续推进扩展。
三、分析路径与研究方法
(一)ICTs带来的演化:作为分析路径的连结性行动逻辑
通过对“以人为本”运动(Put People First)和“愤怒的人群”运动(Los Indignado)的研究,本内特提出,ICTs对集体行动的意义远不止于降低了行动的成本,还演化出了一种新的动员逻辑——“连结性行动逻辑”。[21]其核心在于,新技术提供了新的动员方案,组织与运动积极分子的作用被削弱了,自发的参与者们通过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观点来实现自我激励,进而实现集体行动。
这一洞见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切入点,也留下了发挥的空间。诚然,ICTs的普及触发了诸多新形态的集体行动,但线上的号召并不必然意味着街头的抗争,一个脸书用户不会天然地支持或者反对另一个脸书用户的观点和倡议。换句话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不会因为进入虚拟空间而消弭,观点的分享不仅不必然带来信任和认同,反而可能造成更大的割裂。同时,即使能够通过分享观点而建立起某种弱联系关系网络,其议题导向的、碎片化的特征也不利于维持大规模的集体行动。[22]还有研究指出,基于社交媒体的动员可能并不必然比面对面动员更有效。[23]
基于此,本文提出ICTs影响集体行动动员的居间联络[52]机制:连结性行动所在的虚拟生态圈,将可能成为搭建社会关系的平台,促使原本相互隔绝的政治支持网络交织到一起,共同参与行动。
为了打开这一“黑箱”,黄荣贵等以江门“反核”群体性事件为案例,发现社交媒体的使用提高了人们参与抗争的可能性。但其作用机制在于,个人化的观点分享模糊了线上表达与线下抗争的界线,在传播了潜在抗争人数这一重要信息的同时,还提高了人们对抗争成功可能性的预期。[24]卜玉梅则指出,对于时间成本低且政治风险弱的浅层行动(如签名、意见书等)而言,在线动员往往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对于时间成本高或政治风险大的深层行动(如上访、对谈、“散步”等)来说,在参与热情高涨的运动初期,在线动员仍有较为理想的效果,而在外在控制力提升而行动力弱化的运动维持阶段,则需要转换为传统的现实组织与关系网络,才能保证动员的效果。[25]
历史研究资料表明“如果病人可以从他们的病房的窗户看到室外园林中的树木比他们直接看到砖墙和需要的药品多,他们的康复速度将会得到提高”。这些研究资料显示了医院建筑设计应该高度重视患者所处的医护环境。由于医护人员和患者之间容易在行为和情绪上相互影响,舒适宜人的医疗环境可有效减轻医护人员紧张的精神状态,提高其工作效率和积极性。而这种良性刺激亦会缓解病人的心理压力,为患者的治疗与康复创造有利条件,促进医生和患者之间的良性循环与互动。
现有研究为如何打开连结性行动逻辑的“黑箱”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思想基础。我们注意到,在政治机会较为紧缩的结构之下,社交媒体的使用者为了避免过早招来政府的注意,有意无意地将观点的分享限定在特定的框架当中。但在需要进行深层行动之时,仍需要回归传统动员模式。那么,在政治机会相对开放、中层组织发达的社会当中,连结性行动逻辑是如何运行的?当运动精英的作用不再显著的时候,动员是如何实现的?
为了进一步揭示“观点分享”与“运动爆发”之间的逻辑链条,本文试图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运用连结性行动的相关概念和理论,以“3·18反服贸运动”作为案例,重现其动员过程,挖掘ICTs的影响机制,以期全面深入地理解互联网时代集体行动的运行逻辑,对现有理论有所补益。
太虚年轻时用过一个笔名“悲华”,充分体现了太虚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与对现实中华文明不断衰落的担忧,他一生致力于佛教改革就是为了以佛法救世,同时作为中国人有着造福中国僧俗两界的责任感,也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这一宏愿。所以说,太虚的佛学所本是中国佛教,他更多地关注的也是中国佛教与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搜集
本文采用个案研究方法,进入到事件内部,追踪集体行动动员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因果机制。本文所说的机制,指的是能够规律性地产生某个特定结果的一系列主体和行为的组合。通过发现和验证总是导致某个社会现象的基于行动和主体的社会机制,才能解释这个被观察到的社会现象。[26]本文将采用“因果-过程观测”(causal-process observations,CPOs)这一定性研究技术,探寻案例中的因果机制。因果过程观测项(CPO)是在从原因到结果的过程中,能够表明某个机制存在的经验证据,这一经验证据说明了联结各要素之间的因果链条的存在。[27]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收集手段与研究方法紧密相关,以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为主要手段,并与新闻报道、视听材料、“立法院”公报等政府档案、回忆录、先行研究等二手资料互相印证,尽量保证经验数据的完整与准确。本文作者曾于2010年前往台北大学交换。该校众多学生积极参与了后来的“3·18反服贸运动”,社会学系主任甚至在运动期间停课,鼓励学生参与运动。作者与许多运动参与者互为脸书好友,并能够进入部分聊天室、脸书群组等小型网络空间。运动者冲入“立法院”时,作者通过脸书观察到了众多与运动相关的动态、图片和视频,还曾进入网络聊天室观察网友反应,跟踪事件发展。主要访谈工作开始于2015年11-12月在台湾进行的田野调查,至2016年7月暂告一段落。受访者总计53人,其中半结构式访谈41人,日常访谈12人。
为了获得尽量真实的数据,作者在访谈中向不同受访者求证同一场景、同一时段的事件,通过对照他们的回答,尽可能逼近事件真相。在大多数情况下,被访者的叙述与基本事实之间能够相互呼应。
四、过程与图景:“3·18反服贸运动”的动员机制
“3·18反服贸运动”爆发于2014年3月18日晚间,数百抗议者在台湾当局“立法院”群贤楼外集会,抗议《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以下简称“服贸”)的“粗暴闯关”。21时左右,数十名抗议者冲入“立法院”议场。事件在社交媒体上迅速发酵,两小时内就有近三百人涌入议场,场外的抗议者则增加至数千人。直到4月10日下午退场,学运分子占领“立法院”达24天。占领期间,为回应3月23日发生的“行政院”事件,抗议者发动了近十万人参与的“330凯道大游行”。
那么,这场运动是如何动员起来的?本文将从运动的两个关键事件——“立法院”占领与“行政院”事件出发,重现运动的动员过程。
3月18日晚对“立法院”议场的占领是第一个关键事件。17日下午国民党“立委”张庆忠通关“服贸”的操作,是占领事件的导火索,推动黄国昌、林飞帆等运动积极分子策划了次日对“立法院”的冲击。占领成功后,“黑色岛国青年阵线”(简称“黑岛青”)在脸书粉丝专页发布声明,阐述了他们对“服贸”的看法和运动的诉求,并号召关注者前来支援。[28]警方在错失短暂的清场窗口之后,仅能维持对议场的包围,无法驱散示威者。占领状态一直延续到4月10日运动者主动走出议场方告结束。
3月23日晚至24日凌晨的“行政院”流血事件是第二个关键事件。占领事件后,警方封锁了议场,内外人员难以大规模流动。此时,议场内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并逐渐垄断了与当局的沟通管道。很快,部分场外的运动者以“行政院”为新目标,试图复制占领行动,扩大运动的烈度和影响力,引导运动的走向。然而,“立法院”议场易守难攻,而“行政院”内地势开阔,即使占领了也无法据守。同时,台当局不愿重蹈覆辙,时任“行政院”院长江宜桦在冲击开始后半小时即下令警方换装清场。从23日23点50分一直到24日7点,警方出动近两千警力,三台镇暴水车,将聚集于“行政院”的抗议者驱离。[29]
在时域测量过程中,采用一定的时域窗口进行采样,通常采用阿伦方差来表征时域的频率稳定度。阿伦方差的定义式为:
两次事件的关键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这是两次充满了偶然和意外的行动。偶然性因素和能动的行为者共同造成了许多“意料之外的结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深刻影响了运动的发展。[30]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两次事件都提供了可以激发“观点分享”的引爆点。不论是占领行动背后蕴含的对“公民想象”的实践,还是清场事件中“人民受难”的画面,都引发了大量的讨论和转发,[31]人们在社交媒体网络中发表观点、宣泄情绪、号召行动。而ICTs所提供的多人互动性,使不同个体的观点和情绪交织在一起,最终实现了动员。
本文将运动的动员过程分述如下,并挖掘其背后的动员机制。
(一)重复暴露:信息潮的积累式动员
“立法院”被占领后,运动积极分子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更新事态发展,而普通参与者则通过个人社交账号发布文字或影像信息、在“立法院”周边打卡,或者在各积极分子的发文下评论、交流、争吵。[32]由于脸书、PTT的呈现机制,与运动相关的信息在很短的时间内汇聚成了一股信息潮。其意义不仅在于吸引了台湾社会的关注,更重要的是填满了社交媒体网络的时间线,使几乎所有台湾社交媒体用户都不可避免地沉浸于大量相关信息之中。
已有研究[33]与第一手经验资料都能够证实,脸书是运动参与者最重要的信息来源,仅有少数年纪较长的学者和官员是通过传统媒体,如电视、报纸等渠道获得信息的。
在这种情况下,当计算yj和yk两个点yi与之间的M时,yj和yk可以合并为一个点来考虑。BHSNE通过使用Barnes-Hut算法[18]来决定哪些点可以合并,ST-SNE也沿用这一做法。进行近似后计算式(16)后半部分的时间复杂度降为O(N log N)。ST-SNE算法实现具体描述如下:
在进入议场后,进去的学生们开始发脸书,或者通过社交软件把情况告诉外界:“我们进来了。”……陈(为廷)、林(飞帆)有丰富的社会运动经验,就号召大家发脸书,动员更多的学生,或者同情这一运动的人过来,用人数来保护“占领”这一果实,以免警察清场。但关于这个,也有人说其实他们没有动员,是很多学生看到脸书以后,自发过来保护占领议场的学生。——被访者P5访谈记录,访谈时间2015年11月26日。
在这个碎片化学习的时代发展潮流中,不论是个性化教学,还是培养学生终身的学习习惯,微课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教学利器。在农村语文教学过程中,由于教学资源的匮乏和教学环境的限制,很多学生学习语文知识只能凭借着教师引导进行想象,不能通过事物或者视频来进行更好的学习。微课作为互联网教学的一种产物,如何在农村语文教学过程中发挥出最大的优势,从而帮助学生提高语文综合素质能力,将要依靠教师的有效设计和合理引导才能实现。
基于此,本文提出ICTs影响集体行动动员的重复暴露机制:如果相似主题的信息重复出现社交网络中,其动员效果将不断积累。
然而,一个好的个案研究,必然需要在对社会总体有所把握的情况下实现。[54]就本文而言,仍然存在以下两点局限。这些局限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可能的方向。
大家都互相传最新的消息,还有po上自己的看法,那段时间社交媒体上基本都是3·18的信息。——被访者S5、S6访谈记录,访谈时间2015年11月20日。
在另一方面,运动积极分子的动员作用被高估了。以主要发起团体“黑岛青”为例,其抗议“服贸”的行动从2013年6月就已开始,但未掀起波澜。[38]即使在策划占领行动时,所能动员的力量也不过近百人,占领之后的发展远超他们的预料。尽管运动中出现了松散的“九人联席会议”试图统筹全局,但仍有多元的运动者各自为战,并形成了诸多孤岛式的展演舞台,[39]甚至在权力中心所在的议场内都出现了“二楼奴工区”这样一批拒绝调遣的抗争者。[40]
3·18晚上的守护民主晚会,其实也就300多人参加,当时有纠集第一线的人要冲进去,不超过100人。从晚上9点冲进去,到了凌晨就有很多民众陆陆续续过来支援……原本的重心在济南路,本来没有想要什么包围“立法院”的,是后来人多了以后,一个地方站不下了,自然就慢慢往两侧移动,最后就变成是包围了。——被访者P11访谈记录,访谈时间2015年12月8日。
至此,我们可以认为,重复暴露机制更有力地推动了运动的发展。这一机制的关键在于大量信息的分享,以脸书而言就是发布动态、文章,以及对他人动态、文章的评论、转发和点赞;以PTT而言就是发帖、回帖、“推”(支持)和“嘘”(反对)。但是,面对杂乱的信息潮,一旦足够多的人选择视而不见,那么分享的链条就断裂了,动员效果也就无从积累。因此可以合理地假设,还有别的机制在产生作用,使得这一分享链条能够不断外延。
(二)压力遵从:临时规范对行为者的约束
回顾动员过程,在虚拟生态圈这样一个松散的弱联系关系网络之中,却观察到了本应存在于强联系关系网络中的道德压力。[41]本文认为,这种压力源自临时出现的社会规范,而这正是保证运动动员能量不断积累的关键因素之一。
议场内占领者与警方对峙的画面、“行政院”事件中特警殴打染血抗议者的视频和照片,在社交网络中被大量转发和评论,不仅将事件暴露在了众多旁观者眼中,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强权镇压”这样一个吸睛主题。围绕于此,痛斥当局、心灰意冷、“陆资入侵”、“国共勾结”……散乱的个人化观点分享胶连着种种难辨真伪的传言,与“解严”后台湾社会“推翻威权、守护民主”的“主框架”[42]产生共鸣,最终演化出了“反抗强权”这一非正式、临时的社会规范。临时规范所带来的道德压力,驱使着人们改变了使用互联网的方式,以获取资讯和娱乐为目的的个体性介入将受到谴责,以互动为目的的集体性介入也被限定在了框架之内。[43]
在一开始,我只是希望学生们能够坚持得久一点,……当时还没有对“政府”产生反感。……到了“行政院”流血事件之后,我完全无法接受这样的事情。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公务员,我一向是很信任“政府”的,而流血事件之后,我对“政府”的印象出现了幻灭,当时在脸书上看到那些影像和文字,我有一种“人间地狱”般的感受。——被访者S21访谈记录,访谈时间2015年12月3日。
[1]林泽民、苏彦斌:《台湾快闪政治——新媒体、政党与社会运动》,《台湾民主季刊》(台北)2015年第2期,第123-160页。
社会规范感知是个体为了迎合社会或者参照群组的习惯而进行的行为意向选择,这一现象也被称为从众心理。[44]这一现象在线上行为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有学者指出,个体向其他在线用户寻求接纳的意愿,正是促进线上政治参与的关键驱动力之一。[45]从众心理的社会影响分为两类,规范性影响与信息性影响,二者呈负相关关系。前者指的是个体对社会规范的感知与服从程度,后者指的是个体对信息的接受程度。当大量不确定的信息在短时间内传播时,个体将倾向于服从社会规范。[46]
基于此,本文提出ICTs影响集体行动动员的压力遵从机制:在社交网络中,短时间内大量观点的分享,将创造出一个只容许相似内容的舆论环境,并对网络内的其他成员构成社会压力,迫使他们遵照主流行为模式行事。
那么,传统解释路径中的策略性构框(strategic framing)理论[47]是否对压力遵从机制构成了挑战?通过对一系列关键事件的追踪可以发现,这场运动并不完全依赖于某个动员框架进行动员,其参与者存在不可忽视的多元属性。其中,“国族主义”、左派反自由贸易、反黑箱、世代正义等诸多论述轴线,[48]共同构成了这场运动初始的框架样貌。以“反中”框架为例,这一框架是在运动的不断互动中逐渐聚焦而成的,是为了运动的团结而寻找到的“最大公约数”,[49]是动员的结果而非原因。
民众本来就对马英九的执政不满,而“服贸”本身也有许多说不清或者没有说清的模糊空间,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宣泄点,并不是所有参加的人都是“反中”或者“反服贸”的。——被访者S4访谈记录,访谈时间2015年11月20日。
能源转型将通过数字化进程发展出新的生命力。未来会有怎样的商业模式占据能源市场的主导地位?只有效率、勇气和创造力都具备的企业,才能在其中占得先机。客户也会在未来取得更大的收益。
(运动)确实有不同的理念,比如一直在说3·18就是“反中”,……当然“反中”这个因素肯定有,这个因素比较好叫人嘛,说出来比较慷慨激昂,讲别的人家不一定听得懂。但其实如果认真追究的话,其实“反中”只是一个因素而已,甚至都未必是最大的因素。……当时中山南路那里就是“独派”的地方,……如果照片在那个地方拍,当然就全部都是“台独”的标语和大旗了。——被访者S19访谈记录,访谈时间2015年12月1日。
也就是说,对于运动中确实存在的框架整合现象,与其说是以运动积极分子为核心的策略性行为,不如说是大势裹挟之下的水到渠成。因此,压力遵从机制能够更准确地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但是,台湾不同社运派系和领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隔阂,互相之间甚至存在竞争关系。那么,这两个机制是如何同时影响不同群体成员的呢?
(三)居间联络:虚拟生态圈的积累式扩张
然而,上述逻辑不能很好地解释前文所描述的经验现象。随着新技术的普及,社会结构也在发生变迁,正式的组织开始失去成员,组织关系逐渐被大规模的、流动性的社交网络所取代。[19]通过ICTs所建构的线上平台,人们政治参与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政党等传统政治组织的角色被弱化,人们对个人愿望、生活方式和不满的表达同样起到了动员的作用。[20]现实变迁之下,有必要寻找一种可相匹配的解释路径。
我听说当时第一批冲进“立法院”的人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同志”或者“同志团体”。……现场很有序,不过“公民1985”有参与,……最爱把事情搞得非常温馨的样子。……当时在议场外面有一个区域,自称“贱民解放区”,他们当时也是第一批冲进去的。这些的成员主要是工运的人。他们比较激进,觉得太平和了不是搞运动。——被访者S21访谈记录,访谈时间2015年12月3日。
像“贱民解放区”那帮人,就是光谱的另一头了,跟“台独”这些比的话,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民族情结,他们反对所有跟自由贸易有关的事情,也同时反对国民党和民进党,说两个党都是右翼政党,只顾资产阶级利益。在二者之间也还有许多光谱,互相之间还会贴标签。——被访者S17访谈记录,访谈时间2015年12月1日。
可以发现,尽管经济萎靡、“反中”情绪、世代特征等因素确实使跨领域的运动者更有可能参与到这场运动中,但是,这些因素同时作用于整个台湾社会,为什么是这些群体而不是另一些群体被动员起来了呢?
追溯发生在台湾的一系列经验案例可以发现,基于ICTs的观点分享自2008年就已成为动员的重要前提。在参与运动之前,许多参与者往往互不相识,在运动中以脸书好友、共建Line或WhatsApp群组等方式发生联络。这使虚拟生态圈在一次次运动中不断积累更新,本属不同社会网络的社交媒体使用者们无意中成为桥接各自社会群体的纽带。这一更新的过程发生于虚拟空间之中,但却与现实中同学、同乡等关系网络相重叠,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社会网络“结构洞”(structural hole)[51],不仅为“反服贸运动”中多元运动者的跨领域动员提供了可能,也为运动后更进一步的广泛政治参与打下了基础。
(台湾)社运团体之间是有串联的,互相都熟悉,但没有所谓的领导人,都是靠着私人关系在维持,有时就是因为双方私人关系闹僵了,那团体间可能也就不往来了。但关系维持着的话,即使离开了团体,还是会有联系,线不会断。——被访者S15访谈记录,访谈时间2015年12月1日。
私人交情在(诸多)运动的发起时有很大的影响。很多运动的发起者或者团体的召集人是同学、朋友,那么在某个运动开始的时候,最先想到的不一定是议题导向,而是我跟谁比较熟。而运动本身也变成一个扩展自身人脉的平台,我来参加你的运动,相当于留个人情,以后你也要来参加我的。——被访者S25访谈记录,访谈时间2015年12月7日。
也就是说,ICTs的普及演化出了新的动员逻辑,但这一逻辑的运行过程尚未得到揭示,“观点分享”与“运动爆发”之间的“黑箱”仍未被打开。
如果说压力遵从机制展现了ICTs影响下社会行为者行为动机的演变,那么居间联络机制则反映了新技术对动员结构的改造。这一改造的关键,在于ICTs所具有的特性,即信息的传播不以特定的人或组织为中心,只要接触到相关的信息潮,就成为了受动员的对象。这为我们理解新技术背景下,关系网络对动员过程的作用机制提供了新的启发。ICTs已不仅仅是使用者手中的工具,而是形成了一个用户准入的虚拟活动空间。随着人们在其中互相接触、建立关系,虚拟生态圈不断扩张,使重复暴露和压力遵从机制得以影响到更加多元的社会群体。
(四)小结
通过对经验资料的分析,本文提出,在“3·18反服贸运动”的动员过程中,ICTs通过三个机制促进了动员:通过重复暴露机制,海量的信息流在社交网络中积累了足够的动员能量,为运动的爆发打下了基础;通过压力遵从机制,临时的社会规范约束了社交网络成员的行为,保证了信息传递的畅通,并迫使群体成员参与到运动中;通过居间联络机制,虚拟生态圈不断扩张,容纳了众多原本互相隔离的传统动员网络,确保了个人化的观点能够被分享到足够多的群体之中。任何单一的机制都不足以完成动员,只有在三个机制共同运行的情况下,运动才得以实现。
五、基本结论、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关于互联网时代集体行动的动员,现有文献为后来者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但其所默认的基本假设——即正式组织与统一的集体身份认同是实现动员的必要条件——却忽视了集体行动自身的演化。随着ICTs技术的不断普及与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个体通过个人化的手段使行动和内容通过社交网络被广泛传播,ICTs不再仅仅是某种资源或者前提条件,而是提供了一种克服“搭便车困境”的新路径,为运动提供了无需组织和集体认同的动员方案。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全新的、具有自身独特的逻辑和动因的行动模式,有必要进行单独分析。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对“3·18反服贸运动”的深描,提出了连结性行动的三个动员机制:重复暴露、压力遵从与居间联络。重复暴露机制指的是,如果相似主题的信息重复出现于社交网络中,其动员效果将不断积累;压力遵从机制指的是,在社交网络中爆炸式地分享观点,将创造出一个只容许相似内容的舆论环境,并对该网络内的其他成员构成社会压力,迫使他们遵照主流行为模式行事;居间联络机制指的是,连结性行动所在的虚拟生态圈,将可能成为搭建社会关系的平台,促使原本相互隔绝的政治支持网络交织到一起,共同参与行动。这三个机制在台湾的政治社会结构中纠缠、互动,形成了一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现象运行过程的“机制的结晶”[53],为更全面地理解互联网时代的集体行动提供了知识积累。
不料刚出蜜月,我这个过了明面儿的“三等女”还没开始施行“新政”,他这个潜伏太深的“大丈夫主义”者就开始攻城掠池了:他可以跟哥们儿胡吃海喝到半夜十二点才大摇大摆地回家,我跟同事聚会超过十点他就一个接一个的电话“凶铃”催我;他可以偷懒耍滑地不刷碗、不拖地、不扫除,而我一旦连着两天因为工作忙带了外卖回家,他老人家脸就拉成了长白山;他可以跟男女朋友、客户相识遍天下,而我单独见个男采访对象他就跟缉毒犬般围着我转上三圈……
需要说明的是,重复暴露机制与经典理论解释的差异在于,信息潮的传播并不依托于组织或者人际关系网络,而动员能量的积累也非源于运动积极分子的动员行为。由于本次运动的参与者中,青年学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因此我们往往会先入为主地认为,动员的信息主要通过同学、校友、脸书好友等人际关系网络实现传播。但正如赵鼎新指出的,我们不能把在一个地方大喊大叫的信息传递方式看做社会网络的结果,特殊的空间布局为运动的动员创造了不同于组织和关系网络的生态环境。[36]萧远进一步提出,ICTs形成了超越实体空间的“虚拟生态圈”,承载了主要的信息传播功能。[37]
第一,仅关注了个案中的特定事件片段。本文主要关注这场运动中表现出的种种连结性行动的特征和运行逻辑,试图揭示“观点分享”到“运动爆发”之间的动力机制,填补现有文献的不足。但在这场复杂的运动中,运动积极分子与集体认同的影响同样存在,只是它们并非运动爆发的必要条件,而是产生于运动动态发展过程之中。那么,这对连结性行动逻辑的运行产生了什么影响?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有利于深化对这一个案的理解,进而增进对互联网时代集体行动的把握。
第二,“机制的结晶”仍待打磨。基于案例,本文提出一个“结晶”了三个机制的解释方案,试图以此来说明互联网时代集体行动的动员模式。但在构成这三个机制的因果链条当中,还存在着行动者在关键节点上的策略选择、事件发生的时机和顺序、制度与意识形态惯性带来的路径依赖等诸多影响因素。这些因素本身并非因果机制,而是需要更低层次的因果机制来支撑。[55]也就是说,本文虽然为“观点分享”与“运动爆发”之间的“黑箱”打开了一条缝隙,但仍只是一次较为粗糙的尝试。在将来的研究中,有必要降低分析层次,补充缺失的因果链条,进一步充盈这一“黑箱”。
随着社会的变迁,愈加普及的ICTs重塑了抗争政治的样貌,并在台湾地区已经造成了深远的政治和社会效应;而在大陆,特定场景下的特定议题同样有可能依循连结性行动逻辑,在短时间内迅速发酵并实现动员。因此,连结性行动背后的动力机制和运行逻辑有必要得到更系统的深入研究。而本文的发现,有利于深化对互联网时代集体行动发展的复杂过程的理解。
注释:
很多人都被逼着表态、站队和改变立场。……(像我这样反对“反服贸”的人)会被严词批评,因为他们会认为自己是在反对黑箱,所以是守护民主,是在反对大陆的经济渗透,所以是爱台湾。那我跟他们唱反调,在他们眼中,就算没有讲明,等于是不捍卫民主、又不捍卫台湾吧。……台大政治系老师反对“反服贸”的比较多,但出来讲话的很少。吃力不讨好,当时“服贸”就像万恶不赦的东西,敢出来挺“服贸”,或敢出来质疑“反服贸”,就会被打成罪人。——被访者S20访谈记录,访谈时间2015年12月2日。
[2]有关“事件化”的相关论述,参见渠敬东:《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研究》,《社会》2019年第1期,第1-36页。
[3]参见林鹤玲、郑陆霖:《台湾社会运动网路经验:一个探索性的分析》,《台湾社会学刊》(台北)2001年第25期,第111-156页;邓力:《新媒体环境下的集体行动动员机制:组织与个体双层面的分析》,《传播学研究》2016年第9期,第60-74页。
[4]参见 Jennifer Earl and Katrina Kimport.Digitally Enabled Social Change :Activism in the Internet Age ,Boston:MIT Press,2011;吴小坤:《潜行的力量:ICT精英如何嵌入并影响社会运动》,《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1期,第41-59页。
[5]参见信强、金九汎:《新媒体在“太阳花学运”中的动员与支持作用》,《台湾研究集刊》2014年第6期,第16-24页;刘伟伟、吴怡翔:《台湾青年与“太阳花学运”——基于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的视角》,《台湾研究集刊》2016年第2期,第10-18页。
[6]Gary King,Jennifer Pan and Margaret E.Roberts.“How Censorship in China Allow Government Criticism but Silences Collective Expressi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3,107(2):326-343.
[7]R.Kelly Garrett.“Protest in an Information Society:A Review of Literature on Social Movements and New ICTs”,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06,9(2):202-224.
如果说对等理论类似于“信”和“达”,是翻译的初衷,那么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则是实现这一初衷所要跨越的障碍和考虑的方面。前者是翻译的理据,后者也是翻译的理据;前者是理想层面的,后者则是实践层面的。该文仅限于论述西方语言人名的汉译,探究其翻译实践中的理据。
[8]参见童志峰:《互联网、社会媒体与中国民间环境运动的发展(2003—2012)》,《社会学评论》2013年第4期,第52-62页;陈云松:《互联网使用是否扩大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基于CGSS2006的工具变量分析》,《社会》2013年第5期,第118-143页;熊美娟:《政治信任、政治效能与政治参与——以澳门为例》,《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10-15页。
[9]参见黄荣贵、桂勇:《互联网与业主集体抗争:一项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研究》,《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5期,第29-56页;丁未:《新媒体赋权:理论建构与个案分析——以中国稀有血型群体网络自组织为例》,《开放时代》2011年第1期,第124-145页;曾繁旭、黄广生、刘黎明:《运动企业家的虚拟组织:互联网与当代中国社会抗争的新模式》,《开放时代》2013年第3期,第169-187页;陈先红、张凌:《草根组织的虚拟动员结构:“中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联盟”新浪微博个案研究》,《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4期,第142-156页。
[10]参见黄杰:《互联网使用、抗争表演与消费者维权行动的新图景——基于“斗牛行动”的个案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5年第4期,第98-133页;肖唐镖:《人际网络如何影响社会抗争动员——基于混合方法的研究》,《理论探索》2017年第2期,第35-41页。
根腐病在甜樱桃树上多发现于5-15年生初盛果期树上。发病部位多从根颈开始,逐渐蔓延到粗大侧根。韧皮组织被破坏,出现溃烂,最后腐烂。树势因此衰弱,花量增多,但坐果率低,果实发育不良,变小,致使整树死亡。
[11]参见 Alan Scott and John Street.“From Media Politics to E-protest:The Uses of Popular Culture and New Media in Parties and Social Movements”,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00,3(2):215-240;卞清、高波:《从“围观”到“行动”:情感驱策、微博互动与理性回复》,《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6期,第10-17页。
[12][21]W.Lance Bennett and Alexandra Segerberg.“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Society ,2012,15(5):739-768.
[13]John D.McCarthy and Mayer N.Zald.“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A Partial Theor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7,82(6):1212-1241.
[14]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6-59页。
[15]Doug McAdam,John D.McCarthy and Mayer N.Zald.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16]Mark Granovetter.“The Strength of Weak Ti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78(6):1360-1380.
[17]参见 Sidney Tarrow.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 ,Collective Action and Politic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何明修:《支离破碎的团结——战后台湾炼油厂与糖厂的劳工》,新北:左岸文化出版,2016年。
[18]周雪光:《无组织的利益与集体行动》,《社会发展研究》2015年第1期,第182-208页。
[19]Manuel Castells.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2nd ed.),Oxford:Blackwell,2000.
[20]兰斯·本内特、亚力山卓·赛格伯格:《连结性行动的逻辑:数字媒体和个人化的抗争性政治》,史安斌、杨云康译,《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2013年第26期,第211-245页。
[22]Mario Diani.“Social Movement Networks Virtual and Real”,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00,3(3):386-401.
[23]陶振超:《传播个人性与动员:社交媒体比亲身接触、大众媒体更有效?》,《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2017年第41期,第41-80页。
[24]Ronggui Huang and Xiaoyi Sun.“Dynamic Preference Revelation and Expression of Personal Frames:How Weibo is Used in an Anti-nuclear Protest in China”,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6,9(4):385-402.
[25]卜玉梅:《从在线到离线:基于互联网的集体行动的形成及其影响因素——以反建X餐厨垃圾站运动为例》,《社会》2015年第5期,第168-195页
[26]彼得·赫斯特洛姆著:《解析社会:分析社会学原理》,陈云松、范晓光、朱彦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6页。
[27]加里·格尔茨、詹姆斯·马奥尼著:《两种传承:社会科学中的定性与定量研究》,刘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03-104页。
[28]“黑色岛国青年阵线”:《318青年占领“立法院”反对“黑箱服贸”行动宣言》,http://goo.gl/xGLMvX,最后查询时间:2016年6月1日。
[29]《“立法院”公报》(台北)第103卷第20期,2014年。
[30]陈超、蔡一村:《以“互动”为中心的社会运动演化分析——对中国台湾的个案观察》,《公共管理学报》2016年第4期,第113-126页。
[31]参见叶浩:《太阳花照亮民主转型的未竟之处:“318运动”的政治哲学侧写》,《思想》(台北)2014年第27期,第161-182页;陈嘉铭:《一个自由的篇章:行动的网路和行动的语法》,《思想》(台北)2014年第27期,第183-198页。
[32]被访者S20访谈记录,访谈时间:2015年12月2日。
[33]陈婉琪:《“太阳花学运”静坐参与者的基本人口图像》,引自《那时我在公民声音318-410》,One More Story公民的声音团队主编,台北:无限出版,2014年,第233-244页。
[34]Edward Fieldhouse,David Cutts,Paul Widdop and Peter John.“Do Impersonal Mobilisation Methods Work?Evidence from A Nationwide Get-Out-the-Vote Experiment in England”,Electoral Studies ,2013,32:113-123.
[35]参见 Dona-Gene Mitchell.“Here Today,Gone Tomorrow?Assessing How Timing and Repetition of Scandal Information Affects Candidate Evaluations”,Political Psychology ,2014,35(5):679-701;Sophie Lecheler,Mario Keer,Andreas R.T.Schuck and Regula Hanggli.“The Effects of Repetitive News Framing on Political Opinions over Time”,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2015,82(3):339-358.
[36]参见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2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49页;Dingxin Zhao.“Ecologies of Social Movements:Student Mobilization during the 1989 Prodemocracy Movement in Beijing”,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8,103(6):1493-1529.
[37]萧远:《网际网络如何影响社会运动中的动员结构与组织形态?——以台北“野草莓学运”为个案研究》,《台湾民主季刊》(台北)2011年第3期,第45-85页。
[38]被访者S3访谈记录,访谈时间:2015年11月20日;被访者P11访谈记录,访谈时间:2015年12月8日。
[39]蔡一村、陈超:《角色与惯习——“3·18反服贸运动”中的多元运动者》,《台湾研究集刊》2017年第3期,第6-16页。
[40]晏山农、罗慧雯、梁秋虹、江昺仑:《这不是“太阳花学运”:318运动全记录》,台北:允晨文化,2015年,第274-279页。
[41]关于强、弱联系特征的论述,参见 Mark Granovetter.“The Strength of Weak Ti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78(6):1360-1380.
[42]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2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13页。
[43]关于个体性介入与集体性介入的论述,参见孟天广、季程远:《重访数字民主:互联网介入与网络政治参与——基于列举试验的发现》,《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第43-54页。
[44]李峰、沈慧章、张聪:《我国危机事件下从众意向模型——基于Fishbein合理行为模型的修正研究》,《管理学报》2012年第3期,第451-458页。
[45]Darren G.Lilleker and Karolina Koc-Michalska.“What Drive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Motivations and Mobilization in a Digital Age”,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017,34(1):21-43.
[46]杨庆国、陈敬良、甘露:《社会危机事件网络微博集群行为意向研究》,《公共管理学报》2016年第1期,第65-80页。
[47]David A.Snow and Robert D.Benford.“Ideology,Frame Resonance,and Participant Mobilization”,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1988,1:197-217.
[48]曾柏文:《“太阳花运动”:论述轴线的空间性》,《思想》(台北)2014年第27期,第129-148页。
[49]被访者A2访谈记录,访谈时间:2015年11月19日;被访者S5访谈记录,访谈时间:2015年11月20日;被访者P5访谈记录,访谈时间:2015年11月26日。
[50]顾忠华:《社会运动的“机构化”:兼论非营利组织在公民社会中的角色》,引自张茂桂、郑永年主编:《两岸社会运动分析》,台北:自然主义,2003年,第1-28页。
[51]关于“结构洞”概念的论述,参见 Ronald S.Burt.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52]居间联络机制最早由麦克亚当等人提出,受这一洞见启发,结合本文研究对象和目标,借用这一名称。但需要说明的是,在其著作中,“机制”的定义与本文不同。具体参见道格·麦克亚当、西德尼·塔罗、查尔斯·蒂利著:《斗争的动力》,李义中、屈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30-33页。
[53]“机制的结晶”一词源于郦菁对《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一书方法论取向的精彩总结,原文为:“‘宏观结构观照下的机制研究’……不仅要考察单个机制,更要推究一组机制如何起作用,相互间的关系又如何,在特定结构中如何表现,结晶为何种总体模式。”参见郦菁:《历史比较视野中的国家建构——找回结构、多元性并兼评〈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开放时代》2016年第5期,第27-36页;Dingxin Zhao.The Confucian -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
[54]渠敬东:《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研究》,《社会》2019年第1期,第1-36页。
[55]张长东:《社会科学中的因果机制:微观基础和过程追踪》,《公共管理评论》2018年第1期,第10-21页。
Mobilization Mechanisms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Internet Age—Based on the Case Study in Taiwan
Cai Yicun
Abstract: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ICTs)in the Internet Age have mad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mobilization process of collective action,but their operation mechanism still needs to be further tapped.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collective action in this Age does not necessarily follow the traditional logic of mobilization.In fact,it can be realized by means of decentralization and personalization.Based on the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case study on the“3.18 Anti-CSSTA Movement”we have found that the collective action is mobilized by three mechanisms.The first one is the repeated revealed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the campaign call in the similar topic can constantly appear in the social network of the potential participants and thus accumulates a huge mobilization effect.The second is the pressure compliance mechanism,which means that the participants who share their point of views through the social media can not only get self-motivated but also put social pressure of participating in action on other group members.The last one is the intermediate contact mechanism by which ICTs integrate the isolated political networks and disseminate the mobilization information among the people with different demands and ideologies.
Key Words: Internet,collective action,connective action,mobilization mechanisms
中图分类号: D67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1590(2019)03-001-012
基金项目: 2019年度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新时期台湾青年网络政治动员的现状、机制与对策研究”(2019GZGJ246);广州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启动项目“组织还是网络:‘3·18反服贸运动’中的动员结构”(69-18ZX10240)
作者简介: 蔡一村,男,广州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师。
(责任编辑:唐 桦)
标签:互联网论文; 集体行动论文; 连结性行动论文; 动员机制论文; 广州大学台湾研究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