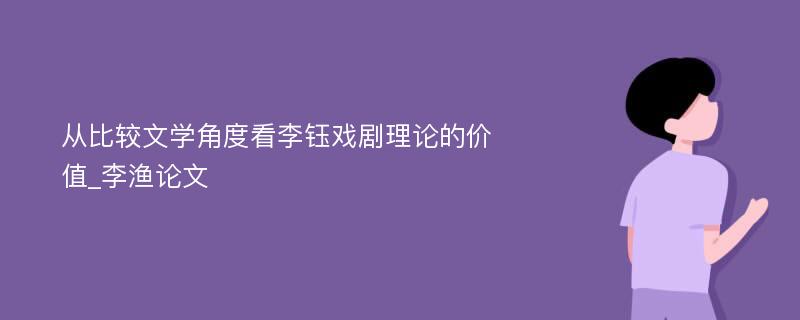
从比较文学角度看李渔戏剧理论的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李渔论文,比较文学论文,角度看论文,戏剧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渔(1610—1680)在清代文化史上有多方面贡献,他兼诗人、小说家、戏剧家、戏剧理论家于一身。李渔不少诗写得很好,袁枚说“其诗有足采者”。拟话本小说有《十二楼》、《无声戏》(又名《连城璧》)两个集子,共三十篇,其中《妻妾抱琵琶梅香守节》有《李尔王》之趣,《谭楚玉戏里传情,刘藐姑曲终死节》构思巧妙,结构紧凑,但总体水平逊于宋话本及明拟话本。李渔的十个喜剧虽然瑕瑜互见,但从总体上说,达到清代喜剧的最高水平,《风筝误》等几个剧本,从中国喜剧史的大范围上说也是一流作品。李渔对自己的著作的评价比较老实:“我亦多撰著,瑕瑜互相濛。”(《予改〈琵琶〉、 〈明珠〉、〈南西厢〉诸旧剧,变陈为新,兼正其失。同人观之,多蒙见许。因呈以诗,所云为知者道也。》)〔1〕李渔对自己的喜剧有一个总的评价,认为不输元曲。他说:
年少填词填到老,好看词多,耐看词偏少。只为笔端尘未扫,于今始觉江花绕〔2〕。这种情文差觉好,可惜元人,个个都亡了, 若使至今还寿考,过予定不题凡鸟。(《慎鸾交·第一出“造端”·蝶恋花》)〔3〕李渔著作的国际性,不在诗与喜剧,更不在小说,而在喜剧理论。他的《闲情偶寄》(1671年首次雕版印行)是他最自豪、最得意的著作,是中国古代空前绝后的戏剧理论经典作品。与法国布瓦洛的《诗的艺术》(1674)分别代表着同一时期东西方戏剧理论的最高成就。
李渔的戏剧理论有六大价值是前无古人的独创,是有国际性的。
第一,他提倡笑的艺术。李渔是中国戏曲史上不多见的只写喜剧的人,他以毕生精力从理论和创作上探求喜剧艺术的特点,抓出一“笑”字。他说:
传奇原为消愁设,费尽杖头歌一阙;何事将钱买哭声?反令变喜为悲咽。惟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举世尽成弥勒佛,度人秃笔始堪投。(《风筝误·第三十出“释疑”·尾声》)〔4〕这是他的喜剧宣言。他有一首诗是这个宣言的注脚:
学仙学吕祖,学佛学弥勒。吕祖游戏仙,弥勒欢喜佛。神仙贵洒落,胡为尚拘执。佛度苦恼人,岂可自忧郁。我非佛非仙,饶有二公癖。尝以欢喜心,幻为游戏笔。著书三十年,于世无损益。但愿世间人,齐登极乐园。纵使难久长,亦且娱朝夕。一刻离苦恼,吾责亦云塞。还期同心人,种萱勿种檗。(《偶兴》)〔5〕喜剧的特征是“笑”,没有笑就不是喜剧,这是一般的道理。但李渔的喜剧理论又很有自己的艺术见解,他认为传奇的目的就是“消愁”,“笑”与“哭声”是对立的,所以喜剧不能写“愁”,不能变喜为悲咽。他的“笑”的理论的真谛就在“举世尽成弥勒佛,度人秃笔始堪投”这两句诗。从小范围说,一出喜剧要让所有观众都看得高高兴兴。从大范围说,要让笑声充满人间。李渔着眼于大,他认为喜剧家应是快乐天使,把欢笑的花雨洒遍环宇。
对李渔的评价,历来毁誉参半。他一生没做过官,伸手向达官贵人公卿大夫要钱要物要姬妾的事是有的、自轻自贱也常有,但也不能说他是御用文人。他晚年凄凉,所谓“十日有三闻叹息,一生多半在车船”。他穷到卖剑、卖琴、卖砚、卖画。他的诗中常见的字是“饥”和“贫”。“欲将饥字呼儿煮,厨下无薪难举烟”,“砚田食力倍常民,何事终朝只患贫”。他六十二岁时,最宠爱的乔姬病逝,年仅十八岁。次年,另一位宠爱的王姬病逝,年仅十九岁。他一连失去他家庭戏班这两个旦、生名角,心痛欲摧。他那三十首悼亡诗情真意切,在中国源远流长的悼亡诗中是占一席之地的。“士与红颜多薄命,生偕逝者尽如斯”,文人若有他这样的遭遇,是容易颓唐的。但李渔不颓唐,更不颓废,他用喜剧传播笑声,给人间欢喜,这是善良、可贵的心地,是不能因他向达官贵人“折腰”而抹杀的。
李渔的喜剧没有善恶对立面,不像关汉卿的《救风尘》,也不像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莫里哀的《伪君子》。在李渔十个喜剧(这公认是他的作品)中,只有《意中缘》有一个坏人是空和尚,算是代表恶势力。其他九个剧本,都没有坏人。净丑是有的,代表“恶”的势力的角色是没有的。
那么,李渔“笑”的理论就没有倾向性了么?不是。他说:
矧不肖砚田糊口,原非发愤而著书;笔蕊生心,匪托微言以讽世。不过借三寸枯管,为圣天子粉饰太平;揭一片婆心,效老道人木铎里巷。(曲部誓词)〔6〕这是他的“誓词”。在《闲情偶寄》中,他又把倾向性放在编剧的首位,这就是“结构第一·戒讽刺”。喜剧要“劝善惩恶”,要有“忠厚之心”,不能“填词泄愤”,这三句话是“戒讽刺”的主旨。李渔也反对“道学气”,提倡寓教于乐:“非但风流跌宕之曲,花前月下之情,当以板腐为戒,即谈忠孝节义与说悲哀怨之情,亦当抑圣为狂,寓哭于笑。”(词采第二·重机趣)〔7〕。他反对喜剧写色情, 主张“谑而不虐”(科诨第五·戒淫亵)〔8〕。
李渔的喜剧思想跳不出儒家正统的框框,他甚至不主张“发愤著书”,“微言讽世”,把司马迁和“诗可以怨”都忘了。但他有时也说过一些有血性的话:
我无尚论才,性则同姜桂,不平时一鸣,代吐九原气。鸡无非时声,犬遇盗者吠。我亦同鸡犬,吠鸣皆有为。知我或罪我,悉听时人喙。(《读史志愤》)〔9〕李渔生逢康熙盛世,他说:“方今海甸澄清,太平有象,正文人点缀之秋也。”〔10〕他要歌颂,是顺历史潮流而动。范文澜说:“清朝武力强盛,在明帝国基础上,开拓了广大的疆域,在征服汉族前后,也征服了其他许多民族。……我们有大好河山的祖国和兄弟众多的民族大家庭,在这一点上,清朝统治集团客观上是起了积极作用的。”〔11〕周谷城说:“清代的政绩,以康、雍、乾三朝为最可观。……若单只著重巩固统治的一点看,也便可以看出许多革新的成绩来。……诸多政绩之中,尤以提倡文化为值得注意。”〔12〕李渔“为圣天子粉饰太平”,是应该批判还是肯定呢?李渔身为汉人,却没有狭隘的民族观念,他既歌颂文天祥“忠纯而义全”,又赞美元世祖五次不忍杀文天祥的“委曲优容”,说“从来创业之主,必有大过于人者在”〔13〕。这是李渔过人见识,符合中国民族大家庭的统一观念。
综合上述,李渔的“笑”的喜剧理论在中国古代确乎是“一家言”,是有价值的。在欧洲同一时期,法国的戏剧理论泰斗布瓦洛和李渔的观点完全一致。布瓦洛给路易十四歌功颂德,也是顺应历史潮流。他说:“喜剧性在本质上与哀叹不能相容,/ 它的诗里绝不能写悲剧性的苦痛;”这正是李渔的主张。他说:“喜剧也就学会了善戏谑而不为虐/ 它不挖苦,不恶毒,工指教,又工劝勉;”这也是李渔的主张。他说喜剧应“不伤人”,李渔也反对用笔“杀人”。布瓦洛也反对道学,提倡寓教于乐:“然而我也并不像老道学那么古板,/ 要从一切雅言里阉割掉恋爱美谈。”〔14〕布瓦洛在西方诗学史上的地位可高了,我们自己倒是把李渔“笑”的理论评价过低乃至一棍子打死。〔15〕
第二,他提倡对白的艺术。中国戏曲理论从来重曲轻白,李渔深知这极不利于戏曲去获得观众,便大胆、坚定地提出曲白并重的崭新理论:
故知宾白一道,当与曲文等视。有最得意之曲文,即当有最得意之宾白。(宾白第四)〔16〕明王骥德《曲律·论宾白第三十四》说“诸戏曲之工者,白未必佳,其难不下于曲”,已有二者宜兼重之意,到了李渔就明白打出旗帜来。为了扭转戏曲界轻视宾白的倾向,李渔甚至主张对白比词曲更为重要:
词曲一道,止能传声,不能传情。欲观者悉其颠末,洞其幽微,单靠宾白一着。(词别繁减)〔17〕这是前人未说过的话。深知词曲之于戏曲具有生命价值的李渔,为了强调对白传递戏文信息的作用,甚至说了过头话。李渔是一代大喜剧家,岂有不知曲文传声又传情之理?李渔的过头话包含接受美学的合理因素,因为传奇与文章不同,文章是做给读书人看的,传奇的服务对象是老百姓,老百姓的确听不懂戏文的曲词,确实只能当音乐来欣赏,他们要了解剧情人物,确实“单靠宾白一着”。
李渔十种曲对白之多,远远超过了元曲及明代著名的传奇,所以他不无自负地说:“传奇中宾白之繁,实自予始。”〔18〕他的代表作《风筝误》是“宾白之繁”的典型,全剧最精彩的“惊丑”、“诧美”两出戏最精彩的笔墨就是对白。《奈何天》“虑婚”、“惊丑”、“误相”也有趣味横生的对白。《比目鱼》第十出“改生”本身就是一出闹剧,对白之多可以作“话剧”看。他的《琵琶记·寻夫》改本与高明的原著比较,最显著的特色是加了三倍对白。〔19〕
李渔从声音与意义两方面肯定对白,有台词“意则期多,字唯求少”的八字原则〔20〕。戏剧语言与小说语言不同,戏剧语言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要比小说语言精练;戏剧语言又与诗歌语言不同,观众不能中止看与听来玩味与思索,故不能像诗那样脱节,又要“贵显浅”。李渔要求对白要短,要明白,又要含蓄,又要传递最大的信息,这是“潜台词”的理论,是戏剧语言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李渔从戏剧的特征来论述“潜台词”,给后人以莫大启发。顾仲彝先生就用李渔这八字原则写出一篇很好的文章来〔21〕。随着戏曲的历史发展,中国戏曲界日益从观众接受心理的角度认识到对白的重要性,所谓“千斤话,四两唱”,就是戏曲演员积几代人的舞台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三百多年前的李渔,正是从观众接受美学的角度对宾白的重要性从理论上予以阐述。
第三,提倡动作的艺术。戏剧是动作的艺术,在西方,亚里斯多德首先下了这个定义。他说:“有人说,这些作品所以称为drama, 就因为借人物的动作来摹仿。 ”〔22〕希腊文drama (即戏剧)一词原出dran,含“动作”之意,所谓“动作”,指演员的表演,更准确说,“动作——是表演的灵魂”。〔23〕但他并没有对“动作”作任何论述〔24〕。贺拉斯在《诗艺》中也极少论“动作”,只指出自然主义的动作不应在舞台上出现,如不必让美狄亚当着观众表现屠杀自己的孩子,因为这样表演会使观众产生厌恶〔25〕。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有三处谈到“动作”,其一是:“倘若戏剧动作里出现的那感人的冲激,/不能使我们心灵充满甘美的‘恐惧’,/或在我们灵魂里不能激起‘怜悯’的快感,/则你尽管摆场面、耍手法,都是枉然。”其二是:“不便演给人看的宜用叙述来说清,/当然,眼睛看到了真象会格外分明;/然而,却有些事物,那讲分寸的艺术/只应该供之于耳而不能陈之于目。”其三是:“人性本陆离光怪,表现为各种容颜,/它在每个灵魂里都有不同的特点;/一个轻微的动作就泄漏个中消息。”〔26〕在西方现代戏剧理论家中,美国的贝克(奥尼尔和洪深的老师)对“动作”给予最大的重视,贝克把动作界定为戏剧的本质特征,认为动作先于性格、对白而在原始戏剧中就已成为主要因素:“历史无可置辩地表明,戏剧从一开始,无论在什么地方,就极其依靠动作。”“通过多少个世纪的实践,认识到动作确实是戏剧的中心,这对于多数没有先入为主的理论的剧作者说来,已经成为一种本能了。”〔27〕
在李渔之前,很少有人论及戏剧动作。中国戏曲“以歌舞演故事”(王国维给戏曲下的定义),“四功五法”中的“做”、“打”及手眼身法步就是“动作”,这是程式化的,与西方所说的“动作”不同。但在戏曲中,特别在喜剧中,非程式化的“科诨”是很多的,这里头就包括“动作”。明王骥德在《曲律·论插科第三十五》中有论述;而第一个指出“科诨”重要性的人是李渔,他把“科诨”提高到一出喜剧能否赢得观众的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说:
插科打诨,填词之末技也。然欲雅俗同欢,智愚共赏,则当全在此处留神。文字佳,情节佳,而科诨不佳,非特俗人怕看,即雅人韵士,亦有瞌睡之时。作传奇者,全要善驱睡魔,睡魔一至,则后乎此者虽有《钧天》之乐,《霓裳羽衣》之舞,皆付之不见不闻,如对泥人作揖,土佛谈经矣。……若是则科诨非科诨,乃看戏之人参汤也。养精益神,使人不倦,全在于此,可作小道观乎?(科诨第五)〔28〕在这段话中,要注意“则当全在此处留神”一语,这是说,喜剧若无“科诨”,则失去艺术魅力,失去观众。因此“科诨”绝非“小道”。李渔提出了在喜剧中非程式化的“科诨”的重要性,这对于程式化的中国戏曲来说,确实是一个崭新的而且富于启迪的问题。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李渔对“科诨”提出四条原则:“戒淫亵”、“忌俗恶”、“重关系”、“贵自然”。“戒淫亵”、“忌俗恶”是“破”,不说自明,别说古代,放到现代世界喜剧中也有绝不能忽视的价值。“重关系”、“贵自然”是“立”,有破有立,立与破同等重要。所谓“重关系”,是说“科诨”要贴切脚色身份:“科诨”二字,不止为花面而设,通场脚色皆不可少。生旦有生旦之科诨,外末有外末之科诨,净丑之科诨则其分内事也。然为净丑之科诨易,为生旦外末之科诨难。雅中带俗,又于俗中见雅;活处寓板,即于板处证活。”〔29〕还要有思想性:“于嘻笑诙谐之处,包含绝大文章;使忠孝节义之心,得此愈显。”〔30〕所谓“贵自然”,是说“科诨”要符合喜剧情境的真实性,不能勉强,生硬造作:“科诨虽不可少,然非有意为之。如必欲于某折之中,插入某科诨一段,或预设其科诨一段,插入某折之中,则是觅妓追欢,寻人卖笑,其为笑也不真,其为乐也亦甚苦矣。妙在水到渠成,天机自露,‘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斯为科诨之妙境耳。”〔31〕
在李渔之前,没有人把“科诨”提到如此重要地位,没有人提出这四条原则,所以说李渔是中国戏曲史上第一个建立“动作”理论的人。诚然,“科诨”只是“动作”的一个方面,但是“科诨”对戏剧尤其是对喜剧而言,则是“动作”的极为主要的组成部分。在西方,“科诨”就是“闹剧”,闹剧(farce)一词原是从拉丁字farcio 派生而来,farcio的意思是“我填满”,因此,“闹剧”就是指“填满低级幽默与过火戏谑”的那类戏剧。任何形式的戏剧都可以有“闹剧”成份,悲剧也不例外。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几乎出出都有“科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穿裙子的丑角”的奶妈,《哈姆莱脱》中的掘墓人,《李尔王》中的弄人,《麦克白》中醉醺醺的看门人,都是举世闻名的“科诨”角色。莎氏的喜剧《仲夏夜之梦》,给波顿安上一个驴头;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让福斯塔夫藏在脏衣篓子里挣扎;在《第十二夜》中,有个总是扎着十字架吊袜的马伏里奥;《驯悍记》则是一出闹剧,它依赖滑稽可笑的情景吸引观众。必须指出,自古迄今,许许多多的世界喜剧名著之所以使人感到欢乐愉快,总是和角色的精彩的“科诨”分不开。哥尔多尼《一仆二主》最能博得满场笑声的是特鲁法尔金诺同时为两个主人“端盆子”那场戏。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姻》最能博得满场笑声的是伯爵晚上去赴花园约会被捉弄那场戏。莫里哀笔下两个最有名的人物答丢失和阿巴公一上台亮相就是以“科诨”出之。中国的戏曲也是这样,去掉红娘的科诨,红娘的喜剧生命便大为减色。去掉春香的科诨,也就没有“闹塾”这出著名的折子戏。在“闹塾”这出戏中,杜丽娘也有“科诨”,又多么符合她的身份。以上所举中外名剧“科诨”的例子,可见剧作家的思想倾向,角色的性格特征,人物的相互关系,其举手投足,嘻笑诙谐不流于淫亵俗恶,都能说明李渔对“科诨”的立论很有科学性与普遍价值。
第四,提倡结构的艺术。元明两代戏曲理论是极不重视戏剧结构的,一个原因是受传统所囿,戏曲家把注意力都放到音律上。还有一个原因是元曲绝大多数是四折一楔子,结构已经定型。明传奇兴起,成为戏剧主流,戏剧结构由简变繁,与元曲大不相同。由于中国戏曲的演进,结构问题就必然被戏剧发展的本身提了出来。晚明王骥德作《曲律》已意识到结构的重要性,到了清代李渔就提出“结构第一”的全新观念。
李渔是把“结构”视为戏曲最重要成分的中国戏剧理论家。他说“填词首重音律,而予独先结构”,因为“结构”是一剧情节的布局,犹如人之一身,建宅之成局。“音律”只能在布局中方能见出它的功能。“有奇事,方有奇文,未有命题不佳,而能出其锦心,扬为绣口者也。”结构就是“事”,也就是情节的安排;结构也是“命题”,如何安排剧情离不开全剧的主题思想。至于“词采”与“音律”的关系,应是“词采”第二,“音律”第三。“词采似属可缓,而亦置音律之前者,以有才技之分也。文词稍胜者即号才人,音律极精者终为艺士。”〔32〕
李渔的结构理论是一个崭新的体系,没有大无畏的反传统的理论勇气和真知灼见的戏剧实践经验绝难提出。他的结构理论包括“结构”、“词采”、“音律”三者的先后主从关系。“结构第一”的新声,旷古未闻。日本著名汉学家青木正儿说:“论结构者,笠翁外,未之见也。”〔33〕王骥德也谈过结构,但王没有说“结构第一”。至于“词采”与“音律”孰主孰次,是李渔对明代戏曲史上临川派与吴江派争论的评定。沈汤之争只局限于“词采”与“音律”,都不谈“结构”,李渔居高临下,提出了“结构第一”。对于“音律”与“词采”的关系,也不像王骥德那么中庸,而是旗帜鲜明地提出“词采”高于“音律”。李渔的观点符合中国戏曲发展的趋势。
李渔的结构理论又是比较的理论,厚今薄古的理论。他把元曲与传奇作了比较,得出传奇的结构胜于元曲的论断。他说:
吾观今日之传奇,事事皆逊元人,独于埋伏照映处胜彼一筹,非今人太工,以元人所长全不在此也。(密针线)。
然传奇一事也,其中义理分为三项:曲也,白也,穿插联络之关目也。元人所长居其一,曲是也,白与关目皆其所短。(密针线)〔34〕李渔的结构理论具有中国民族戏曲理论的特色,他所主张的“一事”绝非亚理斯多德及“三一律”的“一事”,而是指一剧戏剧冲突的根本起因,用他的话说是“根源”。近似西方戏剧理论的一个“引发事件”(inciting incident),也就是一件发动主要戏剧行动的事件, 直接导往全剧中心的“主要戏剧问题”(major dramatic question)。 如“重婚牛府”、“白马解围”。这不仅从他的立论可以说明,从他对《风筝误》的自评(“放风筝,放出一本簇新的奇传”),对《玉搔头》的自评(“方才那两桩事情,合来总是一事”),对朱素臣的《秦楼月》的评点均可说明。李渔的“一事”论丰富了世界戏剧的结构论,是理论上的一个首创。
李渔绝非戏剧单一线索论者,而是戏剧双重线索论者。他把自己四篇小说改编为戏曲,都增加了情节线索。他把《柳毅传书》与《张生煮海》改编为《蜃中楼》,也是两条线索。他的十部喜剧全是“节外生枝、线上打结”的多线索结构。
总之李渔提倡的不是元曲的结构,而是提倡传奇的结构,明清传奇正是突破了元曲的单一结构而显得丰富多姿。如果借用西方戏剧的术语,李渔不是鼓吹古希腊与古典主义的戏剧结构,而是鼓吹莎士比亚式的多样结构。亚理斯多德不可能看见莎氏的剧本,十七世纪法国的古典主义理论家如布瓦洛对莎氏又视而不见。美国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阿伯拉姆说得好:“一个亚里斯多德没有预见到的成功的发展是一种靠双重情节获得的结构一致。这种双重情节在伊丽莎白时代较为常见。在这种结构形式中,一个次要的情节也就是一个次要的、本身也是完整有趣的故事,被引进到戏剧中;如果处理得巧妙,它有助于扩大我们对主要情节的视野,增加而不是分散全局效果。”阿伯拉姆没有提出具体的办法,李渔提出“立主脑”。而“主脑”、“一事”、“一线到底”是同一概念。
关于李渔的“一事”与亚氏及三一律的“一事”的比较,是国内中西戏剧理论比较一个误区,另文再谈。
在西方,第一个提出结构第一的人是亚理斯多德。他说戏剧有六大成分:情节、性格、言词、思想、形象、歌曲。在这六大成分中,最主要者是“情节”,即“事件的安排”,亦即结构:
六个成分中,最重要的是情节,即事件的安排。
各成分已界定清楚,现在讨论事件应如何安排,因为这是悲剧艺术中的第一事。而且是最重要的事。〔35〕在中国,李渔第一个提出结构第一,在西方亚氏第一个提出结构第一,李渔与亚氏,都是“第一个”。亚氏生于公元前384年, 李渔生于公元后1610年,从世界戏剧史的范畴说,亚氏是西方戏剧结构论的开创者,李渔是中国戏剧结构论的开创者。古希腊戏剧是世界数一数二古老的戏剧,这是亚氏理论得天独厚的历史条件。中国和希腊虽都是文明古国,但我们是诗文大国,叙事文学相对地说发展较迟,戏曲发展更晚。诗文与小说戏剧比较,结构问题并非首要。李渔的结构理论产生于清初,也是受中国文学史的条件所限定的。亚氏的结构论是对古希腊悲剧的总结,亚氏生时,古希腊悲剧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一两百年,而古希腊悲剧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亚氏的结构论是共时性的结构论,仅就希腊悲剧这一个范畴论结构。李渔的结构论,是对中国戏曲由元杂剧到明清传奇的总结,李渔生时,元曲已成过去,传奇方兴未艾,所以李渔的结构论有比较的条件,是历时性的结构论。亚氏提出结构第一,没有阻力,气贯长虹,李渔提出结构第一,富于论战性,要有反潮流的勇气。
第五,提倡“体验”的艺术。李渔强调假戏真演,演员必须“体验”角色的思想情感,才能表演得好,才能打动观众。他说:
戏文当戏文做,随你搬演得好,究竟生自生,而旦自旦,两下的精神联络不来。所以苦者不见其苦,乐者不见其乐。他当戏文做,人也当戏文看也。若把戏文当了实事做,那做旦的精神,注定在做生的身上;做生的命脉,系定在做旦的手里,竟使两个身子合为一人,痛痒无不相关。所以苦者真觉其苦,乐者真觉其乐。他当实事做,人也当实事看。〔36〕李渔的“体验”理论,既指表演,也指创作。剧作家为角色“立言”先得为角色“立心”,写台词要考虑角色能否“上口”,观众是否“入耳”。李渔要求剧作家得先把自己变成角色、观众,才能写出好的本子,收到好的演出效果。他一再强调“设身处地”是剧作家创作思维的出发点:
言者,心之声也,欲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若非梦往神游,何谓设身处地?无论立心端正者,我当设身处地,代生端正之想;即遇立心邪辟者,我亦当舍经从权,暂为邪辟之思。务使心曲隐微,随口唾出,说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弗使浮泛,若《水浒传》之叙事,吴道子之写生,斯称此道中之绝技。果能若此,即欲不传,其可得乎?(语求肖似)。
从来宾白只要纸上分明,不顾口中顺逆,常有观刻本极其透彻,奏之场上便觉糊涂者,……因作者只顾挥毫,并无设身处地,既以口代优人,复以耳当听者,……笠翁手则握笔,口却登场,全以身代梨园,复以神魂四绕,考其关目,试其声音,好则直书,否则搁笔,此其所以观听咸宜也。(词别繁减)。〔37〕
第六,打通小说戏剧。李渔是小说家兼戏剧家,一个作家又写戏剧又写小说,自然会思考二者的关系。李渔又是一个理论家,自然会从理论上去思考。他思考的所得,有以下几点:
其一,他认为“稗官为传奇蓝本”〔38〕,这说明李渔深知中国小说是中国戏曲素材的来源;中国古代戏曲绝大多数源于稗官,又说明李渔深知中国戏曲的编剧法亦得益于小说。所谓“蓝本”,不仅指素材,还指手法。中国散文叙事文学从《论语》到《史记》,从古典短篇小说到古典长篇小说,几乎全用直叙法,最能讲好故事,写活人物;好懂易记,最可以满足最广大读者的阅读习惯;又最擅以对白、动作、肖像描写去塑造人物,本身就有戏剧因素。
其二,他认为小说是“无声戏”,这说明李渔深知小说戏剧的异同。戏剧是代言体,中国戏曲以歌舞演故事,是“有声”的,当然与小说不同。李渔说:“《西厢》系词曲,与小说又不类。”(《三国演义》序)〔39〕。但二者也有相同之处,都是叙事文学。所以他把自己的小说集命名为“无声戏”,在《十二楼》第七篇《拂云楼》第四回末尾又说“看演这出‘无声戏’”〔40〕。
其三,他认为小说戏剧都是“传奇”的。他欣赏韩愈的《毛颖传》,说“昌黎《毛颖传》,绝世单行”〔41〕。他欣赏冯梦龙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评定为“四大奇书”,而认为《三国演义》的史实最富于戏剧性,最宜于写小说(鲁迅看法与之相近),而作者“以文章之奇而传其事之奇”,行文又忠于史实,故在四部小说中是奇中之奇。〔42〕戏剧也是“传奇”的。他说:“古人呼剧本为‘传奇’者,因其事甚奇特,未经人见而传之,是以得名,可见非奇不传。”〔43〕
其四,他认为小说戏剧都是“寓言”,都要重视虚构与想像。他说:“小说寓言也,言既曰寓,则非实事可知也。”〔44〕又说:“传奇无实,大半皆寓言耳。”〔45〕李渔举楚襄王和巫山神女阳台一梦的恋爱故事一直流传至今说明“幻境之妙,十倍于真,故千古传之”〔46〕。
其五,他认为“戏文小说”的语言都“贵浅不贵深”,他说:“能于浅处见才,方是文章高手。”他举施耐庵的《水浒传》及王实甫的《西厢记》作证明〔47〕。他特别欣赏《水浒传》,誉之为“叙事”的“绝技”〔48〕。又说《水浒传》的语言是古今文字中最好的:“吾于古今文字中,取其最长最大,而寻不出纤毫渗漏者,惟《水浒传》一书。”〔49〕
戏剧与小说确实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在西方,第一个从理论上致力于“打通”二者的人是亚里斯多德,他指出荷马史诗的戏剧成分,并说荷马既是伟大的史诗诗人,又是第一个伟大的戏剧家〔50〕。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小说家兼戏剧家的塞万提斯〔51〕又从创作实践上“打通”二者。《堂·吉诃德》中有小说理论,也有戏剧理论。他向戏剧艺术汲取塑造性格的经验,把古希腊喜剧的滑稽与悲剧的严肃糅合在一起,并借鉴民间喜剧,塑造出堂·吉诃德这位既是喜剧又是悲剧人物,既是可笑的傻子又是最聪明的哲人的复杂典型。
到了十八世纪,小说家兼戏剧家的菲尔丁独创性地提出“散文喜剧史诗”的新小说理论,从理论上“打通”了戏剧小说。菲尔丁是欧洲第一位自觉地把二者结合起来写的作家,他的《汤姆·琼斯》可以说是用编剧法写成的长篇小说。小说的悬念比比皆是,但都紧紧围绕汤姆出生的秘密及汤姆与苏菲亚一对情人的命运生灭,并不分散如断珠。他把最大的悬念搁置到最后一卷才解开,与之同时,写了奥尔华绥的发现及他对两个外甥态度的突转,构思巧妙,笔法经济,有很高的戏剧性。小说有二十七处巧合,或用作伏笔,或为补叙作准备,或推动冲突的发展,写法又有简繁之分,并不雷同。小说有十一次误会,其中一些与重要悬念有关,有的误会对推动情节发展起了关键的作用。菲尔丁称自己的小说为“喜剧”,擅长用喜剧性冲淡悲剧性,眼看悲剧即将酿成,他却笔锋一转,使主人公化险为夷。有些情节全用对话体写成,如17卷12章,语言个性化,富于动作性,三人感情充分交流,只要用戏剧形式编排一下,不必改动一字,就是一篇上乘的戏剧小品。
到了十九世纪,小说家兼戏剧家的雨果继续“打通”小说戏剧。他说:“在司各特的散文体裁的小说之后,仍然可以创造出另一类型的小说。在我们看来,这一类型的小说更加令人赞叹,更加完美无缺。这种小说既是戏剧,又是史诗。”又说:“当对过去的描绘流为科学的细节的时候,当对生活的描绘流为细致的分析的时候,那末,戏剧就流为小说了。小说不是别的,而是有时由于思想,有时由于心灵而超出的舞台比例的戏剧。”这是他用编剧法写《巴黎圣母院》的总结,《巴黎圣母院》是完全可以作为戏剧来看的,诸如悬念设置的手法、发现与突转的手法、巧合手法、用场景叙事、穿针引线手法、用独白与短句重复表现心理、静动结合的节奏、在戏剧冲突中表现悲剧性等等,都是戏剧手法。如同李渔一样,雨果也现身说法地指点读者注意他的编剧法的应用。例如第六卷出现“荷兰塔”与“绞台”两个平行的场景:在“荷兰塔”外,三个妇女认出了女修士即十六年前失踪的妓女;在“绞台”上,吉卜赛女郎爱斯梅哈尔达送水给钟楼怪人加西莫多喝。雨果从三个妇女的对白中引入女修士的故事,用巧合手法使十六年前的旧相识重逢,十次强调那只粉红色小鞋(道具)的作用,另一只在哪儿?又设下悬念。雨果设计了一个戏剧性细节,把两个平行的场景联系起来。从“荷兰塔”的窗口可以望见方场,当女郎步上方场的绞台送水时,女修士在窗口便望见她了。十几年前,女修士的女婴就是被吉卜赛人偷走的,女修士这时并不知女郎是亲生女儿,便高声诅咒她(这是“戏剧性细节”),注意,雨果写到这里,就现身说法了,他指出“女修士的诅咒”是这“平行发展的两幕剧的关联”。
到了二十世纪,德国的布莱希特又从理论与创作双方面提倡叙事的戏剧,要“填平”小说戏剧“不可逾越的鸿沟”〔52〕。他说:“现代戏剧是史诗(叙事)戏剧。”〔53〕,“中国和印度早在二千年前已经历了这个先进的形式。”〔54〕
以上说明,李渔“打通”戏剧小说的见解在西方是不乏知音的。既有理论上的呼应,又有创作实践上的呼应,还有理论与实践双管齐下的呼应。所不同者,西方的戏剧的编剧法要比中国戏曲丰富,所以西方作家喜欢把编剧法引入小说,从而“打通”小说戏剧。中国的戏曲手法源于小说,杨绛先生认为中国戏曲是“小说式的戏剧”〔55〕。中国小说的结构比较单纯,李渔“打通”戏剧小说,除了汲取小说叙事的优点,还要丰富自己的编剧法,变小说的简单结构为复杂结构,他把自己的小说改编为戏剧就是这样做的。还有,李渔没有说小说等于戏剧,他只是说二者异中有同,而雨果则干脆说除了容量大小不同外,小说等于戏剧。雨果忽视了戏剧与小说“有声”与“无声”的根本区别,这方面,东方人李渔高明于西方人雨果。
从李渔戏剧理论的六大贡献可见李渔戏剧理论的先锋性与现代价值。所谓“先锋性”,是一反传统,说了前人未曾说的见解,这些见解既有科学性,又不失中国戏曲的特性。所谓“现代价值”,是李渔的戏剧理论于中国当代戏曲具有启示性,可以作中国当代戏曲改革的参考。可见李渔戏剧理论在当时的超前意识,是中国古代文化一笔宝贵遗产。
以西方戏剧理论为镜,则可见中西戏剧理论异中有同。戏剧理论是戏剧创作的总结与升华,由此也说明中西戏剧异中有同。中西戏剧虽然是不同文化圈的两个不同的戏剧体系,但也有不少相同或相通之处。西方十八世纪的伏尔泰、二十世纪的布莱希特、当代美国的阿瑟·密勒,都致力于“打通”中西戏剧。而中国从“五四”时期开始,就有人致力于“打通”莎士比亚与中国戏曲。1986年首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在上海和北京隆重举行,上海演区十四台戏中有四台是戏曲。这是在高层次上中国戏曲与莎士比亚戏剧的沟通和对话。八十年代以来,莎士比亚成为“打通”中西戏剧的主要切入点。而四百年前,李渔就提倡写莎士比亚式的戏曲,他戏剧理论著作《闲情偶寄》就是联系中西方戏剧,特别是中西方喜剧的一座理论上的桥。
注释:
〔1〕《李渔全集》第二卷“笠翁一家言诗词集”14页, 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江花绕”一句李渔得于梦中。他有诗云:“梦中曾得句, 江管复生花。醒来何处觅,散作晓天霞。”自注云:“梦中得句,醒辄忘之,止记‘江管复生花’五字,因见晚霞。补成一绝。”见《李渔全集》二卷258页。
〔3〕《李渔全集》第二卷“笠翁一家言诗词集”14页。
〔4〕《李渔全集》第四卷“笠翁传奇十种”203页。
〔5〕《李渔全集》第二卷“笠翁一家言诗词集”25—26页。
〔6〕《李渔全集》第一卷“笠翁一家言文集”130页。
〔7〕《李渔全集》第三卷“闲情偶寄”20页。
〔8〕《李渔全集》第三卷“闲情偶寄”56页。
〔9〕《李渔全集》第二卷“笠翁一家言诗词集”19页。
〔10〕《李渔全集》第三卷“闲情偶寄”1页。
〔1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23—24页,人民出版社1949年第1版。
〔12〕周谷城:《中国通史》下册28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
〔13〕《李渔全集》第一卷“笠翁一家言文集”495—497页。
〔14〕以上引文均见《诗的艺术》第三、四章,任典译,王道乾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15〕例如敏泽先生说:“宣扬封建伦理观念,为统治者点缀升平,这就是李渔在创作上的根本见解和纲领,从这一方面说,李渔的见解完全是封建糟粕。”(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下825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16〕《李渔全集》第三卷“闲情偶寄”44—45页。
〔17〕《李渔全集》第三卷“闲情偶寄”49页。
〔18〕《李渔全集》第三卷“闲情偶寄”48页。
〔19〕《李渔全集》第三卷“闲情偶寄”76—82页。
〔20〕《李渔全集》第三卷“闲情偶寄”51页。
〔21〕顾仲彝:《编剧理论技巧》403—408 页, 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版。
〔22〕《诗学》第9页,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23〕[英]克雷:《论剧场艺术》2页,李醒译, 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版。
〔24〕“动作”与“行动”非同义词,罗念生先生译得很准确。
〔25〕《诗艺》146—147页,杨周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26〕上述引文均见《诗的艺术》第三章,任典译,王道乾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27〕贝克:《戏剧技巧》第二章, 余上沅译, 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版。
〔28〕《李渔全集》第三卷“闲情偶寄”55页。
〔29〕《李渔全集》第三卷“闲情偶寄”57页。
〔30〕《李渔全集》第三卷“闲情偶寄”57页。
〔31〕《李渔全集》第三卷“闲情偶寄”58页。
〔32〕以上引文均见《李渔全集》第三卷“闲情偶寄”4—5页。
〔33〕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王古鲁译,转引自《李渔全集》19卷345页。
〔34〕以上两段引文均见《李渔全集》第三卷“闲情偶寄”11—12页。
〔35〕以上两段引文均见亚里斯多德《诗学》第六章,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36〕李渔:《谭楚玉戏里传情,刘藐姑曲终死节》,见《觉世名言十二楼等两种》24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37〕以上两段引文均见《李渔全集》第三卷“闲情偶寄”47—48页。
〔38〕《李渔全集》第九卷《合锦回文传》第二卷卷末评语。
〔39〕《李渔全集》第十八卷“杂著”538页。
〔40〕《觉世名言十二楼等两种》15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年版。
〔41〕《李渔全集》第十八卷“评鉴传奇两种”149页。
〔42〕《李渔全集》第十八卷“杂著”538—540页。
〔43〕《李渔全集》第三卷“闲情偶寄”9页。
〔44〕《肉蒲团》八回后评语, 转引自《李渔全集》第二十卷321页。
〔45〕《李渔全集》第三卷“闲情偶寄”15页。
〔46〕《李渔全集》第三卷“闲情偶寄”109页。
〔47〕《李渔全集》第三卷“闲情偶寄”24页。
〔48〕《李渔全集》第三卷“闲情偶寄”47—48页。
〔49〕《李渔全集》第三卷“闲情偶寄”55页。
〔50〕《诗学》13页、88页,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51〕塞万提斯写过二、三十出戏,多已散佚。
〔52〕〔53〕〔54〕均见《布莱希特论戏剧》68—69页,106页, 129页,丁扬忠等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
〔55〕杨绛:《李渔论戏剧结构》,《春泥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