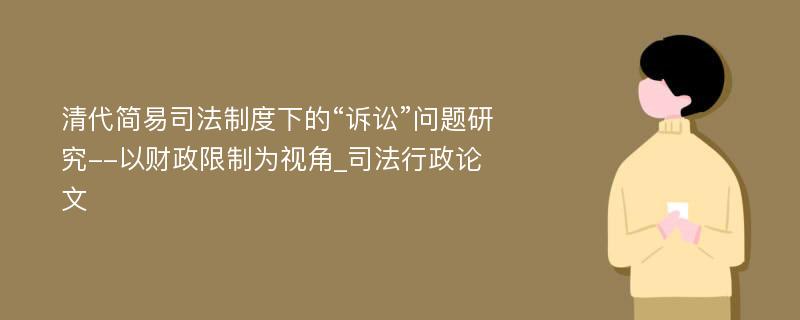
清代简约型司法体制下的“健讼”问题研究——从财政制约的角度切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代论文,司法论文,体制论文,角度论文,财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清代我国的“健讼”之风
虽然“嚣讼”、“健讼”之类的词语早在宋代就开始出现在史料和一些司法文书之中,①但其在明清时期显然出现得更为频繁。对二十五史中出现的“健讼”、“好讼”等词语所作的统计结果显示,“好”“讼”两字连用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宋史》,其后呈现总体增多的趋势,即《宋史》之中出现3处,《明史》之中出现1处,《清史稿》之中出现9处(具体以“民好讼”、“俗好讼”、“民俗好讼”等字眼出现);而“健讼”一词在二十五史中总共出现14处,除《金史》和《元史》之中各出现1处外,其余的12处皆出现在《清史稿》之中,其中最为常见的是“俗健讼”之类的具体表述。②由此可见,“健讼”和“好讼”两词在《清史稿》中出现的次数远远高于清以前的诸部正史。虽然这些词语的出现频率可能与史书编纂者各自的语词使用偏好差异有关,但上述统计事实也说明清代社会受“健讼”之风的困扰尤为严重。
宋代以降,尤其是自明代中后期以来,我国疆域内那些纷纷涌入各级衙门的大量词状不断昭示着诉讼正在日益嵌入越来越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③与此同时,“健讼”、“好讼”之类的文字记载,也在各地方志之中俯拾皆是。道光年间山东省的一份县志曾描述了当地的“健讼”风气:“乡愚无知之民,一有不平,辄尔兴讼,不量事之大小轻重,竟罹法网。有竞毫末财利者,有逞一时小忿者,有自处浑昧受人主摆弄者,更有无良奸徒乐观他人败坏、唆民致讼、于中取利者,虽屡加惩治,种类终难断绝”。④而这不过是各种地方志之中关于“健讼之风”、“好讼恶习”的众多记载中的一则而已。一份根据来自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山东7省的150余部地方志(涉及200多个州、县)所做的研究显示,其中写明当地“健讼”的地方志有70多部,而在江南地区有诉讼风气记载的70多部地方志中,明确记载“健讼”的有57处之多。⑤另一份对清代江苏、上海、山东、广东四省(市)的284种府志和县志所做的统计显示,其中有95种谈及当地当时的好讼风气。⑥
在此必须指出的是,对清代的“健诉”之风我们必须有一个理性的认识。且不说由地方官绅主导编纂的地方志常常有粉饰太平的倾向,因而有可能对其地的讼风轻描淡写乃至避而不论,就说那些“寡讼”话语所描述的社会景象也未必皆属实情,实际上也可能是对当地“健讼”之风所做的一种文字掩饰。这一结论的得出并非毫无根据。例如,光绪年间纂修的福建《长汀县志》记载,虽然明代“天崇以来,凌夷殆甚,科名星落,城社烟墟,讼狱繁兴,奸宄迭见”,⑦但“幸我朝道德齐礼,俾斯民革薄从忠,男女严峻其防,廛无幸货之妇,穷乏犹知所耻,衢少伏地之乞,室无怨旷,子女不鬻外乡人,各治生丁男绝鲜游浪,奢汰不竞,凶讼少闻”。⑧然而,根据17世纪的汀州府(下辖长汀县等多县)知府王廷抡所言,汀州早在康熙年间便“越控之刁风实繁”:“汀属之劣衿势恶,皆藉刁笔以谋生,恃此护符,专以唆讼而网利,更有宁化、清流两邑之流棍,半皆驾舟于南台,上杭、永宁两县之奸徒,又多贸易于省会。此辈熟识衙门,惯能顶名包告,与讼师串通一线,指臂相连,辄敢遇事生风,便得于中诈骗。每有山僻之乡愚,以一日之微嫌,希图捏词以嫁祸,或因情词妄诞府县未经准理者,或因审出真情已经薄惩反坐者,或因自知理屈难以取胜未经控府告县者,一遇若辈扛帮,无不堕其奸术。内用讼师之簸弄,外有包棍之引援,遂饰小忿为大冤,或翻旧案为新题,口角争端动云捆锁吊拷,地界接壤指挖冢抛骸,田土之交易未清便言霸占,钱债之利息不楚捏告诈赃……”⑨从王廷抡所著《临汀考言》之中记载的案例看,长汀县民诬告缠讼成风,社会上呈现的根本不是“凶讼少闻”的景象。因此,“健讼”之风的区域分布很可能要比依据地方志之文字记载所做的统计更为广泛。当时的官员及其幕友们,更是对所谓的“健讼”之风耿耿于怀,纷纷在官箴书、官府布告和公务禀文中予以强烈谴责。而江西、湖南以及湖北等省的“健讼”之风尤为引人注目,被地方官员们视为臭名昭著的恶风陋习,甚至被拿来相互比较。⑩
二、清代州、县衙门的理讼能力
其实,“健讼”在官方的话语中被日益视为严峻的现实问题之一在很大程度上与清代州、县衙门处理讼案的能力直接相关。清代部分省份的省例和清讼章程之中关于清讼功过的规定透露了清代衙门理讼能力之概况。例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拟定的《皖省清讼功过新章》对“旧案期限功过”作了如下规定:“自本年三月十五日起,凡在十起以上者予限一个月,二十起以上者予限两个月,三十起以上者予限三个月,一律审结详报,果能按限清结,各予记大过或功一次。倘逾限一月者记过一次,逾限两月者记大过一次,逾限三月者详请撤任”。(11)以此观之,当时安徽省各衙门每月平均能够审结的案件约在10起左右。此外,同时期在江苏省担任知县的许文濬,在抵任尚未满一月的时间内审结5起“上控案”和29起“自理案”,被江宁府评价为“勤能可嘉”而计大功二次。(12)由此可见,在当时的江苏省每月平均能审结30起左右案件的县令非常少见。有学者曾根据乾隆至光绪年间浙江、江西、江苏、福建和山西等省份的省例和章程,对其中审理词讼功过的相关规定作了初步统计。(13)从此类省例和章程的规定看,虽然最为常见的是以结案成数作为衡量功过之概括性标准,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发现一些线索。根据同治年间《江苏省例》“一季二十案以上全结,三十以上结九成,五十以上结六成,一百以上结五成,计大功一次”的规定推测,当地州、县衙门每月平均能审结10起左右案件的便已属难能可贵。清代名臣刘衡曾自豪地声称,其在巴县任内处理民事词讼时能做到“并无逾期不到之案,有具呈之日即结者,有一两日即结者,至迟亦不过二十日之限”。(14)不过,从上至皇帝下至省级长官的抱怨声中可以得知,像刘衡这样善理词讼而能做到案无留牍、审不逾限的州、县官,在清代终究属于凤毛麟角。
在民间词状日益增多的情势下,清代州、县衙门处理讼案能力的有限性日益凸显。清代大量未决积案的存在,一直在不同程度上困扰各级衙门。例如,福建巡抚吴士功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奏报,在福建省,小县有积案200至300起,大县有积案500至600起,如果加上从1758年遗留下来的10 979起未结案件和1759年前10个月新增的案件,那么福建省当年估计有22 800起积压案件。(15)面对层层上报的大量积案,在上位者自然免不了要责备下级官员懈怠其职。1807年,当嘉庆皇帝从福建巡抚张师诚的奏报中获知福建巡抚衙门先前积压的未结词讼多达2 977起时,禁不住龙颜震怒,大发“该省吏治废弛已成积习”的愤慨,表示要惩治前任福建巡抚温承惠。(16)虽然这种对下属懈怠其责的怀疑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就当时的词讼规模和州、县的职责而言,事实上,即便州、县官都十分勤勉,但想要及时审结所有新、旧案件也几乎是痴人说梦。
作为清代最小行政单元的正印官,州、县官员们被赋予了各种琐碎的职责。以知县为例,《清史稿》简要地描述了其“靡所不包”的职责:“知县掌一县治理,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17)而用瞿同祖的话来说,州、县官集“法官、税官和一般行政官”于一身。(18)这种情形通常被人们概括为“行政与司法合一”或“行政兼理司法”。由此可见,虽然司法是州、县官最重要的职责之一,但由于他们并非专业性的司法官,因此,他们实际上无法将全部的精力都集中于司法,而是还需要履行其他的众多职责。
就司法而言,《大清会典》规定“官非正印者,不得受民词”。这实际上是要求州、县官不得将词讼批于佐杂审理,否则将对正印官予以惩处。(19)但是,在如此繁多的职责之下,再加上科举取士内在的“非职业性倾向”所造就的官员们在法律知识方面的先天不足,(20)州、县官们常常不堪重负,即便有心者全力为之,也往往疲于奔命,积案因此也就在所难免。乾隆、嘉庆时期的名吏汪辉祖在出任湖南省宁远县知县时曾与绅民相约,每旬之中除了两日校赋、一日处理文件外,余下的七日均用于坐堂理讼,甚至连原本用来校赋的两日也兼听讼。(21)并且,在其坐堂理讼之日,往往由晨至昏,有时甚至迟至深夜,常常疲不可支。即便将要退堂用膳之际,若又有民众到案求讯,汪辉祖为免其等候,亦勉应之。乾隆庚戌(1790年)春夏,汪辉祖处理讼事常至傍晚,询问两造之际甚至已然“气往往不续”,仍“不敢倦怠草率”。(22)即便汪辉祖如此废寝忘食地勤理讼事,在其四年后离任之时,虽然做到将本任所收之案全部审结,但对于前任积压的400余件旧案也仍有10余件未曾清结。(23)
因此,从实质上讲,清代官员们所称的“健讼”可被视为官方司法体制与民间诉讼需要之间张力不断拉大的话语体现。“健讼”之类的谴责之辞在官方话语中出现得愈频繁,从某种意义上讲,愈折射出当时的司法体制已无力满足不断增多的诉讼需要而日显故步自封的现实。
三、因循运作的清代简约型司法体制
既然现有的地方官无法卓有成效地及时处理讼案,那么为何不增加人手以助其事?或者对原有辖区面积再加细分(这意味着各辖区内的民众人数减少,治理压力将得到减轻),再相应地增设地方官?然而在清代中国的历史上上述看似美好的想法并未被付诸施行。美国学者麦柯丽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从未发现有任何一位省级长官向皇帝建议其治下需要更多的官员与行政机构来处理这些积压案件”。(24)
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对中国帝制时期县级区划进行历史考察后指出,从理论上说,当原先定居地区的聚落扩展、人口增加之时,县级区划数目也会不断增加而县的平均面积将逐步缩小,但中国史籍的记载却显示,在中国帝制时代,县的平均面积反而是逐渐扩大。其原因在于县级区划的数目极其稳定,各王朝极盛时期县的近似数,汉朝为1 180个,隋朝为1 255个,唐朝为1 235个,宋朝为1 230个,元朝为1 115个,明朝为1 385个,清朝为1 360个。这意味着,清代县官的管辖区域通常要远大于汉代县官的管辖区域。在辖区面积扩大的同时,清代各县的人口数较之以往也在不断增长。(25)人口的压力以及伴随而生的经济社会生活复杂化,必将导致包括讼案增多在内的治理难度增大。(26)
然而,清代我国的正式官员数目并未随着县级区划的扩大和治下人口的繁衍所导致的行政事务的增多而相应增加。美国社会学家韩格理的研究成果显示,1899年编的《大清会典》中罗列了两万名公职官员,根据与时4.5亿的人口数计算,每2万多人才有一个官员。即便再加上实际执行公众职务的150万名官僚体制底层人员(差役、胥吏、师爷、仆役等),每1万人中也只有3名政府的公职人员。这与欧洲历史上官员人数随着行政功能的扩充而增加的情形大相径庭。在1665年人口总数为2 000万的法国,国家官员就有46 000人,人口总数与国家官员的比例约为500∶
1。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夕,法国人口增加到4000万,但科层官员包括小城书记及城门守卫在内就有30万人。因此,在当时,每1 000人之中就有7.5人是受薪的政府雇员。这个比例在19世纪之后还急剧上升,延至20世纪之交,在欧洲国家中,在1 000人之中的政府雇员达到20名至30名。(27)
县级区划的扩大和治下人口的繁衍意味着治理难度的相应增大,而县级官员人数却在低水平上维持相对的稳定。在施坚雅看来,这一现象反映了“中国历史从中唐以后直到帝国结束,出现了政府效率长期下降、基层行政中心职能一代比一代缩减的情况”。(28)但是,法国汉学家魏丕信质疑这种观点。他指出,当我们论述整个国家机构的规模时,如果将未入流的官员和非正式的政府机构考虑在内,那么可以发现明清时期的国家机器其实是在扩展,其规模至少是与人口增长及经济增长保持同步,从绝对意义上讲是这样,从相对意义上讲也是如此。(29)不过,魏丕信所说的“国家机器的扩展”,其实也只是在肯定掌印官数目大致不变的前提下,着重强调胥吏和官员私人雇佣的人员(幕友、长随等)在明清时期有明显的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书吏、衙役、幕友、长随这些自明清以来数量明显增长的人员很少从国家受薪。书吏在清初尚可以“饭食银”的名义从国家获得一些薪金,但大约在康熙初年(1662),书吏享有的这种微薄的薪金被取消,从而变成没有国家薪酬的职位。官方定额之内的衙役虽然有平均为6两银子的年薪,但仅靠这笔收入往往难以生存。而通常为数几倍于正规衙役的所谓“白役”,则更因为不在官方的定额之内而无法从国家领取薪水。因此,书吏和衙役几乎完全依靠收受各种“陋规”维生。(30)至于幕友、长随因为完全属于地方官的私人雇员而非政府雇员,其薪水全由地方官本人支付。(31)因此,即便是所谓的“国家机器的扩展”,增加的也只是不从国家受薪的各种辅助人员,而并非从国家领取俸禄的正式官吏。从国家财政的角度看,这一特点意味着清代国家不必因为吏役和官员私人雇员的人数增加而随之承受相应的财政负担。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各种辅助人员大量进入明清行政体制不会直接给国家财政带来重负,但由于其造成“公务性”和“私人性”被异常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因此很可能会因为纠缠和内耗而导致衙门的实际效率越来越低。(32)
除了将集司法和行政等职能于一身的正式官员之数量维持在相当少的基本水平而不与时俱增外,清代简约型司法体制的另一个特点是,即便收到民众关于纠纷的呈控,衙门也尽可能将其交给民间来解决。只有当堂外解决恶化到极为严重时,衙门才将所收讼案的处理权全部揽回自己手中。清代采用简约型司法体制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地节约正式司法资源。
由此而形成的机制就是美国学者黄宗智所说的纠纷处理中的“第三领域”,这是一个半官半民的地带。(33)晚近发现于安徽省歙县的一张空白格式县谕显示了官府将所收讼案批回地保和族长、敦请其加以调解,从而强有力地直接证实了上述半官方机制的存在和运作。(34)如果将这一机制放置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之中加以审视,那么就可以发现其与下列趋势密切相关:宋代以来,尤其是在清代,随着宗族、行会、商会、宗教团体和其他一些组织逐渐成为基层社会的主要结构,基层社会的自治程度总体上在不断提高,而国家权力则相对向上收缩。
四、清代司法体制的财政制约因素
无论如何,清代政府始终都没有通过明显增设包括州、县官在内的常规官僚的方式,主动扩大其司法服务事项的范围,来积极应对当时主要由于经济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和人口渐繁而不断扩大的词讼规模。易言之,清代县的数量并没有被特意增加,仍然是以数量相对稳定的县官来应对总量激增的词讼规模。如果按现代西方国家的“司法能动主义”理论来衡量,(35)那么这种简约型司法体制的表现显然极其平庸。不过,清代坚持这一简约型司法体制除了受“集权的简约治理”这一治理理念的深刻影响之外,(36)还受当时国家财政状况的制约。(37)
如果以公元180年(汉朝)平均每县5万人(当时全国有1 180个县级区划)的人口密度为基准,那么,公元875年需要设1 600个县,1190年需要设2 200个县,1585年需要设4 000个县,1850年需要设的县数则达到8 500个。如果再按每6个县级区划之上设置1个府级区划以维护相当的监督水平的平均比例推算,那么,1 180个县级区划需要设大约200个府级衙门,而在1850年所需的8 500个县之上,至少要求相应设置1 400个府级衙门。这意味着,就晚清时期的情况而言,仅省级以下的衙门至少就需要设置近1万个,而这还没有将巡按计算在内。(38)这种预想中的行政规模势必压垮整个帝国,因为县数的增加意味着从国家受薪的常规官僚以及其僚属人员的人数膨胀,给国家带来根本无法承受的财政负担。
美国学者曾小萍的分析清楚地道出了其中的经济学关键:“在雍正朝,中国有1 360个县,依照清初通行的比例,若使行政单位与人口相适应,县的数量应增加到8 500个左右。如果我们假设为州、县官提供养廉并完成基本行政任务,那么每县至少要3 000两白银。就18世纪20年代县级人口水平而言,这意味着大约4 080 000两白银要用于地方管理,这是考虑到当时的经济所得到的数字。向足够多的县提供财政支持以确保对当地人口有效的控制,清朝的拨款将必然超过25 500 000两白银,这还不包括对州、县官和他们属下的活动进行监督的较高层的行政单位的拨款。就此开支而言,18世纪初整个王朝的几乎所有的地丁钱粮收入都要用于自身的征收之上”。(39)这意味着,如果要强行维持8 500个左右县的预想规模,那么就必须大大提高帝国现有的税率,以获得足够的税负收入作为支持。但是,如果要在清代落实这种设想,那么将远远超过清帝国稳定所能承受的极限,从而严重威胁到清帝国的治理。
美国学者王业键的研究成果表明,虽然在整个清代,田赋在整个税收中所占的比例呈下降的总体趋势,但其即使在清朝崩溃前夕也依然占到所有税收中的约1/3,而在清朝鼎盛时期田赋在所有税收中所占的比例高达3/4左右。王业键根据其对田赋这一始终在不同程度上占据着支配地位的税收种类所做的深入分析发现,在清代最后的25年中,在大多数地区和省份,田赋只占到土地产值的2%—4%,只有苏州、上海地区占到8%—10%。而在明治时期的日本,这一比例要达到10%左右。王业键在比较后因此认为,“清末的田赋负担实际上并不沉重”,甚至可以说呈现长期减轻的趋势。(40)以此来看,或许有人会认为清代中国尚存在收取更多税收的空间。
然而,将清代与民国的情况稍作对比便可发现上述设想几乎就是天方夜谭。日本学者对民国时期华北数个自然村所做的调查资料显示,在1930年的河北省丰润县米厂村,该村中农、富农和经营式农场主所付的税率大致相等,即约相当于总收入的3%—5%,在1938年该村被日军占领后,税率被提高到5%—5.5%,而在1941年的河北省顺义县沙井村,这个比例徘徊在6%—8%之间。(41)不妨粗略计算一下,如果将清代实际的1 360个县扩张到设想中的8 500个县,按照这个扩张比例,要想获得足够的税收支持,那么上述2%-4%的实际平均田赋征收比例也大致要求相应扩张6.25倍左右,即达到12.5%—25%。这将是一个高得根本无法想象的税率。要知道,民国时期地方政府的军事化和现代化造成其支出猛增,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从乡村汲取各种税源的程度要远高于清代的总体水平,而日本对华北村落的侵占更是以变本加厉的税额苛刻而著称,但即便如此全力汲取,如同上面的资料所显示的,也只能达到5%—8%。
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到1848年末,累积起来的田赋拖欠约相当于整个国库的储备数量”。(42)这与前述王业键的看法相矛盾。不过,如果细想一下清代的经济社会现实,那么这其实并不难理解。明清以来人口绝对数量激增而土地总面积相对有限(即使算上新开垦的土地)所导致的人地紧张关系,使得土地及其上产出的任何收入对于农民而言愈发显得珍贵,从而导致围绕土地的暴力冲突愈显常见。(43)由于农民对于税率变得更加敏感(遇到收成欠佳的受灾年份更是如此),因此明清以来的农民抗租抗税运动屡见不鲜。尤其是自19世纪以来,随着通货紧缩(具体表现为银价上涨而米价下跌)导致百姓生活状况的日益恶化,除了各种日常性抗争大量出现之外,大规模的抗税运动也以京控甚至暴动的形式,在浙江、福建、两广、两湖、江西等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不断上演,呈现此起彼伏之势。(44)由此可见,在清代中国,如果政府强行提高税率,那么既有可能引起农民的抵触,又会招致地方缙绅们的不满。两者的敌意被以某种形式叠加放大,其结果必将是一场场冲击政治秩序乃至动摇帝国统治的反抗和暴动。
五、结语
以往的研究通常是围绕儒家的意识形态来对照讨论清代官方话语之中的“健讼”问题,而正如本文所展示的,结合财政制约之下的清代司法体制特征详加分析,可以更为深刻地洞悉清代中国“健讼”话语日渐兴盛的另一种历史必然性。
正是在上述财政因素的制约下,面对词讼激增的社会情势变迁,清代简约型司法体制之中那些因循运作的“制度资源”最终遭遇到可被利用的极限,官方因而不得不愈发借重“健讼”之论,试图以此弥补正被现实所冲击的司法制度本身的正当性。易言之,清代中国的“健讼”之论,究其实质,既是官府理讼能力与民间诉讼需要之间张力不断拉大这一现实的话语体现,也是当时的司法体制在“制度资源”方面逐渐无法有效应对社会情势变迁之时用来弥补其正当性的一种“话语资源”。
对于任何一种司法体制的有效维护而言,“制度资源”和“话语资源”各有其不同的功用并应当互动配合。但是,如果在面对社会情势变迁之时,司法体制由于财政等因素的制约,本身缺乏与时调整的弹性,那么由于“制度资源”的功能日渐低下而引发的正当性危机绝非仅靠“话语资源”即可挽回。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其依托的这两类资源之中,如果“制度资源”日益衰竭而“话语资源”却愈发膨胀,那么意味着司法体制本身很可能已经深陷正当性危机之中。
就此而言,重新审视“健讼”话语在清代日益兴盛的深层原因,或许对于我们思考当代类似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例如,在当前我国中西部地区,当地相对羸弱的财政能力使得基层司法体制在面对诉讼案件日益增多的大趋势之时,“制度资源”在实际运作中经常处于应对能力的极限。因此,司法体制运作与司法财政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深思。此外,当我国目前基层司法体制的“制度资源”在实际运作中频频遭遇其应对能力瓶颈时,“话语资源”与司法体制之正当性维护的微妙关系也将成为我们不得不正视的现实问题之一。
注释:
①参见刘馨珺:《明镜高悬:南宋县衙的狱讼》,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6-217页;陈景良:《讼学、讼师与士大夫——宋代司法传统的转型及其意义》,《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②上述结果系根据南开大学组合数学研究中心、天津永川软件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的“二十五史全文阅读检索系统”(网络版)检索所得。
③有学者将当时伴随经济社会结构变化而兴起的“好讼之风”视为司法传统在宋代由“伦理型”转向“知识型”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参见陈景良:《宋代“法官”、“司法”和“法理”考略——兼论宋代司法传统及其历史转型》,《法商研究》2006年第1期。
④黄维翰纂修:《钜野县志》卷23,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513页。
⑤参见侯欣一:《清代江南地区民间的健讼问题——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法学研究》2006年第4期。
⑥参见徐忠明、杜金:《清代诉讼风气的实证分析与文化解释——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清华法学》2007年第1期。
⑦⑧刘国光、谢昌霖等纂修:《长汀县志》卷30,《风俗》,清光绪五年(1879)刊本。
⑨王廷抡:《临汀考言》卷6,《咨访利弊八条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三十九年(170 0)刻本。
⑩“兹蒙恩命,移节楚南,访得各属中刁诳虚诬之习,有较甚于湖北、江西者。”吴达善纂修:《湖南省例》,《刑律》卷11,《诉讼·诬告·严禁诬告讼棍》,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清刻本。
(11)冯煦主修、陈师礼总纂:《皖政辑要》卷83,《审断二·清讼》,黄山书社2005年版,第756页。该点校本指出,原书“各予记大过一次”中的“过”,应为“功”字之误。
(12)参见许文濬:《塔景亭案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13)参见王志强:《法律多元视角下的清代国家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页。
(14)刘衡:《庸吏庸言》上卷,载《官箴书集成》编撰委员会编:《官箴书集成》(第六册),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181页。
(15)(24)See Melissa A.Macauley,Civil and Uncivil Disputes in Southeast Coastal China,1723-1820,in Kathryn Bernhardt and Philip C.C.Huang,eds.,Civil Law 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87,p.120.
(16)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十二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影印版,第321页。
(17)《清史稿》卷116,《职官志三·外官·县条》。
(18)(31)参见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页,第78-84页。
(19)参见方大湜:《平平言》卷2,载《官箴书集成》编撰委员会编:《官箴书集成》(第七册),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626页。
(20)参见屈永华:《中国传统取士标准非职业性的历史成因与影响》,《法商研究》2003年第4期。
(21)(22)参见汪辉祖:《病榻梦痕录》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648页,第666-667页。
(23)参见张伟仁:《良幕循吏汪辉祖——一个法制工作者的典范》,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文化研究院编:《中西法律传统》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8页。
(25)See Hsiao Kung chuan,Rural China: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0,p.5.
(26)参见方志远:《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0-205页;邓建鹏:《清代讼师的官方规制》,《法商研究》2005年第3期。
(27)参见[美]韩格理:《中国社会与经济》,张维安等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第120页。
(28)(38)参见[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9页,第19-20页。
(29)参见[法]魏丕信:《明清时期的官箴书与中国行政文化》,李伯重译,《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
(30)参见郑小春:《从徽州讼费账单看清代基层司法的陋规与潜规则》,《法商研究》2010年第2期。
(32)参见尤陈俊:《清代地方司法的行政背景》,载朱腾主编:《原法》第3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7-16页。
(33)参见[美]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107-130页。
(34)这张光绪年间以雕版印制的县谕写有以下内容:“为此谕仰该__知悉此事,尔如能出为排解,俾两造息讼,最为上策。此谕仍交地保缴销。若不能息讼,即由该族长告知被告,令其于_月_日午前到城,本(衙)每日于未初坐堂,洞开大门,该原被告上堂面禀,即为讯结……此因该族长素来公正,言足服人,帮饬传知,并非以官役相待,亦不烦亲带来城,不过一举足、一启口之劳。想该族长必能本□□爱民如子之意,共助其成,实有厚望”。该批文由田涛收藏,原件为木版雕印单张。参见田涛:《徽州地区民间纠纷调解契约初步研究》,《法治论丛》2009年第1期。
(35)参见[美]克里斯托弗·沃尔夫:《司法能动主义:自由的保障还是安全的威胁》,黄金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36)参见[美]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载[美]黄宗智、尤陈俊主编:《从诉讼档案出发: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99-427页。
(37)参见[日]夫马进:《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王亚新等译,载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19页。
(39)[美]曾小萍:《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董建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5-286页。
(40)参见[美]王业键:《清代田赋刍论(1750-1911)》,高风等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5页。
(41)参见[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89-290页。
(42)[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39页。
(43)See Thomas M.Buoye,Manslaughter,Markets,and Moral Economy:Violent Disputes over Property Rights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44)参见罗丽达:《道光年间的崇阳抗粮暴动》,《清史研究》1992年第2期;吴琦、肖丽红:《清代漕粮征派中的官府、绅衿、民众及其利益纠葛——以清代抗粮事件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2期。
标签:司法行政论文; 清朝论文; 历史论文; 行政体制论文; 财政制度论文; 清史稿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北洋政府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