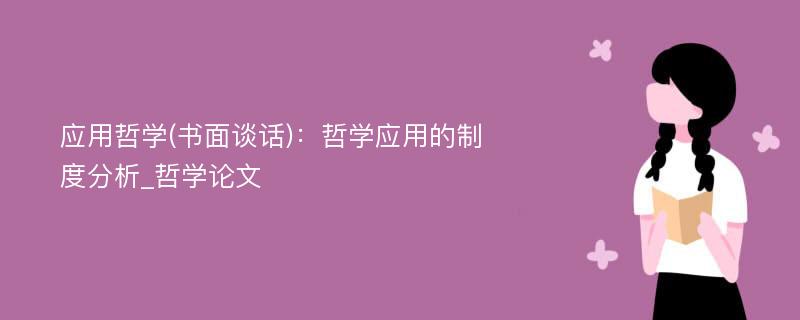
应用哲学(笔谈)——哲学应用的制度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笔谈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哲学应用的制度解析是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哲学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意识形态)应用于现实社会生活所具有的制度功能和作用的分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的哲学应用就是将哲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所蕴涵的“意识形态”特质引入人的实践活动中去,并对主体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及行为产生影响的过程。
哲学的制度特性
作为制度理解的哲学,其主要特性表现为:
1.公共性。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制度是一种“公共品”,它作为一种行为规则并不是为某一个人制定的,而是为大家所“共享”。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的理论存在,就其形式而言,它往往与某个人或少数人的名字相联系,而就其内容而言,则具有很强的社会性,甚至为一个时代所“享有”。马克思正是在后者的意义上指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种哲学的“公共性”是不言而喻的。当然,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和作为“公共品”的哲学又与其它“公共品”有一定的区别。这是因为,一般公共品都是有形的,主要表现为具体的实物或实体性的规范,而作为“公共品”的哲学则是无形的、抽象的范畴体系,是在人类认识与实践两个层面上展开的无数次的博弈的“公共选择”,即在一定的时空和社会条件下人人都可以享用它。
2.利益性。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哲学具有另一个鲜明的特性,即它是服务于一定利益集团的,所以,哲学在事实上也是人们的一种利益选择结果。历史上的任何制度,都是当时人的利益及其选择的结果,也就是说,人们只是选择符合自己利益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新制度经济学家反复强调,新制度经济学应该从现实的组织体制出发,同时也要从现实中的人出发。因为制度作为人的一种行为规则,本质上是人们利益关系的一种制度化形态。同样,哲学作为非正式制度,它的产生、存在和社会作用也离不开利益,也是人的利益关系的一种非正式制度的意识形态表达。作为一种制度(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的形成都是人们在基本利益基础上的“社会博弈”的结果,制度“公共性”的实质是利益的“公共性”。也就是说,人们建立在利益关系基础上的交往实践关系,是包含着利益的一致与冲突的辩证的相互关系的。人们为了达到既实现自身利益,又不至于在交往互动中因利益冲突而两败俱伤,就必须创造一种把冲突限定在一定范围的规则形式,这就是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是人们在交往实践中达成的“利益共识”。哲学的这个特性决定了哲学应用必须遵循利益原则,从利益的角度去审视哲学应用的方式和方法,评价哲学应用的成败。
3.相容性。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制度的均衡、作用和变迁都体现着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以相容为基本前提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制度均衡,发挥制度作用、推动制度变迁。具体地说,哲学的相容性特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与正式制度的相容,即正式制度与哲学的关系是作为“硬制度”与“软制度”的关系,从两者的产生与相互作用的角度看,又是“选择”与“适应”的相容关系。当正式制度被实践证明是“好”制度时,非正式制度要相容于正式制度;当正式制度被实践证明是“坏”制度时,则正式制度要相容于非正式制度。其二是哲学与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其它要素的相容,即与思维方式、习惯、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观念的相容,这主要表现为哲学与其它要素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实现哲学与其他非正式制度要素在意识深层处的一致性。哲学只有与非正式制度的其他要素相容时,哲学的指导性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哲学的应用才能合理有效。
哲学应用的制度功能
哲学的制度特性决定了它在应用中的制度功能。
1.批判功能。以反思方式表现出来的批判精神,是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批判功能的重要表现。从哲学与正式制度的双向相容关系来看,无论是正式制度相容于非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相容于正式制度,哲学都可以充分发挥其批判功能。就制度而言,哲学应用首先是以批判的精神考察正式制度的存在根据和价值论前提,指出它的片面性和狭隘性、保守性和暂时性,揭露它的内在矛盾。通过哲学批判,使正式制度在人的理性自觉指导下得到修正、完善或为制度变迁提供理性支持。其次,哲学在应用中还要进行自我批判,自觉地揭示哲学理论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辩证关系,改造现有僵化的思维方式,反思意识形态中的“合理性”问题,倡导与“好”的正式制度相适应的价值取向等。所以,哲学批判使非正式制度的其他要素也处于自我反省的状态。也正是哲学的批判与自我批判的制度功能,为人们划定了科学思维的框架和合理行为的边界。
2.建构功能。如果说哲学应用的批判功能是在制度的意义上回答什么是“不许或不应当”,侧重于对人们的观念和行为的约束作用;那么,哲学应用的建构功能则是对什么是“必须或应当”的回答,侧重于对人们的观念和行为的激励作用。因此,哲学应用的建构功能主要表现在:其一,为“好”的制度的经济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进行理论的“证实”;其二,为“坏”的制度的经济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进行理论的“证伪”,在“证实”与“证伪”的基础上构建新制度的“先验模式”,为新制度的诞生鸣锣开道;其三,为非正式制度中其他方面提供“是如此”的规定性和“应该如此”的价值导向和合理性的评价尺度。哲学应用的建构功能是由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辩证相容性决定的。
3.化约功能。所谓制度的化约功能主要是指制度以其自身的特质,具有把复杂的事物简单化,使无序的状态有序化的功能。哲学应用通过发挥特有的批判和建构功能,对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产生影响,使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对其客观对象也具有化约的功能。首先,哲学作为高度理性的非正式制度,以其特有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导向作用,确定了社会生活中人们的观念和行为边界,建立相应的观念形态的奖惩机制,为人们提供一套借以预测行为过程和结果的信息,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们社会行为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其次,哲学既是一个观念理论形态的行为检测体系,也是一种认知理论,哲学在人们认识世界中也具有化约功能,也就是说,哲学作为人们认识世界的“思想武器”,运用它可以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在流动多变中发现永恒的东西,立足现实并能预测未来等等,这都是哲学在人们认识事物中化约作用的表现;再次,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哲学应用的化约功能主要是指哲学作为一种价值引导,减少执行制度规则过程中的运作成本,有效地克服“搭便车”行为。正如诺斯指出:“至为关键的是,任何一个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克服搭便车问题,其基本目的在于促进一些群体不再按有关成本与收益的简单的、享乐主义的和个人的计算来行事。”(注: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59页。)
总之,哲学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通过确定思维框架和行为边界,提供奖惩机制,化约复杂与不确定性,降低认识和行为交易成本,从而产生并提高人的活动的“适应性效率”。
哲学应用与制度变迁
哲学应用与制度变迁包含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哲学作为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关系;二是哲学作为非正式制度中的一种具体形式与其他要素的关系。这里主要是从第一个方面探讨哲学应用在正式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1.通过发挥哲学的批判功能,产生并强化制度需求和制度不均衡的程度,从而为制度变迁提供动力。通过对制度的反思式批判,运用辩证否定的观点和方法,对现存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进行深层次的重新审视,对社会生活中制度的需求与供给的关系进行辩证且务实的分析,使人们认识到,按照现有的制度安排,他们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或潜在的利润),而如果改变现有的制度安排,有可能获得现有制度下得不到的利益,由此产生改变现有制度的心理萌动,形成驱动人们进行制度变迁的社会心理动力。当获得这种新认识的社会个体人数达到一定程度时,便形成具有相当强度的“制度需求”,从而形成了制度变迁的必要性,并为制度创新提供了精神条件。
2.通过发挥哲学的建构功能,实现对制度变迁的建构性认同。某种制度变迁有无必要与是否可能并非完全是一回事,正如有必要做的事并不一定是可能做成的事一样,制度变迁的真正实现,还需要在有必要的情况下探讨它的可能性程度。哲学应用的建构功能有助于形成制度变迁如何可能的一致性认识。这个建构过程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通过建构新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进而改变社会行为主体的行为取向,营造有利于制度变迁的客观环境和主观氛围。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人们必然面对观念上“解构”与“建构”并存的局面,完成思想上“破”与“立”的双重任务。价值取向是与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的核心,任何一种制度都必须以特定的价值取向为基础。换言之,特定的价值取向是特定制度得以形成与维系的逻辑前提,二者的相容与一致是“制度均衡”的基本条件。其二是运用哲学的反思特性与批判精神“扬弃”现存制度,克服其自身固有的“遗传”机制,有选择地保留那些有助于引起并推进制度变迁的文化价值观念与规范,使之成为新制度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哲学要对不适合现有正式制度的各种观念要素进行重新审视(解构),进而建构一种适合于正式制度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伦理道德,这是由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相容性决定的。
3.通过发挥哲学应用的化约功能,揭示社会变迁的复杂、多变的本质,把握制度变迁的基本趋势和方向。制度变迁的过程是一个现象与本质相互交织、变与不变相互并存、可能与现实相互转换的错综复杂的过程。要合理而有效地实现制度变迁,达到实现制度变迁的目的,把握制度变迁的本质方向十分重要。首先从认识上看,哲学的化约功能使人们对原有制度的“弊端”(如搭便车)看得更清楚,理解得更深刻,并将这些认识从感性直观升华到理性抽象;其次从实践上看,哲学的化约功能可以使人们推动制度变迁的行为取向,不偏离正确方向而更有成效,使人们的行为真正体现合目的与合规律的统一。正所谓认识明、行动快、效果好,这就是对制度变迁的认识与实践在“化约”的基础上达到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