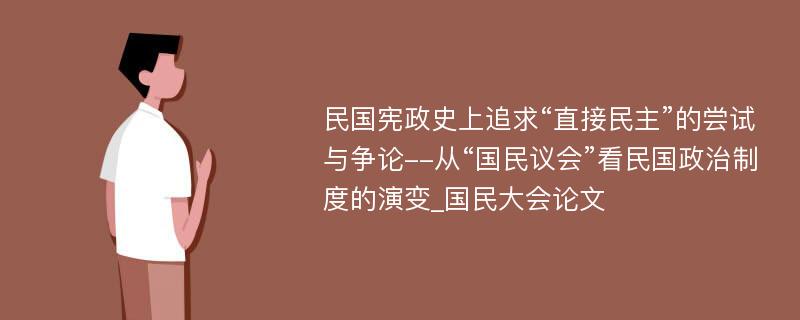
民国宪政史上追求“直接民主”的尝试及论争——从“国民大会”观民国政制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国论文,政制论文,宪政论文,史上论文,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4)02-0140-06
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孰优孰劣,是世界宪政史上聚讼纷纭、见仁见智的问题。直接民主起源于古希腊文明中。雅典的公民大会对城邦事务发表直接意见,是行使直接民主的方式。瑞士自13世纪以来即有直接民主。现代民主的主要形式是间接民主,即议会政治,亦称代议制,是西方政治的基本制度,指人民定期选举组成议会,作为全国的民意机关,行使立法权负责对政治的监督。作为间接民主,体现于普通民众有数年一次的选择执政政府的权利。历史上,它不仅是打破君主专制的产物,也是防止所谓多数暴政的产物,因此它是协调民主与自由之间的关系的思想的制度性表述。18至19世纪,议会政治的理论与运作逐步在欧美确立。
19世纪末20世纪初,直接民主在欧美有一度猛烈的复兴。这源于议会信用的堕落、阶级利益的分化、社会主义浪潮的兴起、人民政治教育的需要。现代的直接民主指公民直接行使创制权、复决权、罢官权。创制权指公民达于若干人数,得提出关于法律或宪法的建议案,其目的在于防止议会违反民意而不制定某种法律。复决权系指议会所通过之法律案或宪法草案,公民有重行投票表决之权,其目的在于防止议会违反民意制定某项法律。罢官权是公民以投票方式直接决定公职人员的继任与免职。不过,多数采用直接民主制的国家,目的不在废除议会,而在运用创制、复决诸权补救议会的缺点。人们倾向于认为,政治的腐败来源于公众对于政治的冷淡和麻木,直接民权的运用可以用来防止贿赂、腐败。因此,直接民权对于间接民权只是一种补充而不是替代。
近代西学东渐的大潮中,中国是被迫卷入世界现代化的进程的。各种西方学说纷至沓来。数百年的西学,都在短短数十年间涌入。早在清末的政制辩论中,革命派的思想家章太炎就表现出对于议会政治的强烈不信任。清末经由日本介绍到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中,都有着将议会政治看成是虚伪的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的因子。中华民国的建立意味着对西方制度的直接移植。但试行代议制的结果却是议会政治的破产。中国人试验议会政治的时候,也正值西方资本主义危机,反思议会政治弊端、直接民权在部分欧美国家大行其道之时。直接民权在西方的再度复兴,也深刻影响了北京政府的政治。
一
“国民大会”最初源自五四运动中知识界发动群众就外交问题向政府进行政治抗议的活动方式,逐步发展成以行使“直接民权”来代替国会立法功能的组织方式。1920年8月1日,自诩“进步”色彩的直系军阀吴佩孚通电提出《国民大会大纲》,提出“国民自决主义”,由“国民公决”制宪,引起强烈反响。《晨报》、《益世报》都发表文章讨论“国民大会”应该行使的职权。各地纷纷集会,成立召集国民大会的筹备组织,如国民大会协进会、策进会、筹备会等,上海、安徽、江苏、浙江等处尤其热烈。各省的教育会、农会、商会不乏积极参与者。总之,人们认为国民大会“合于世界最进步之直接立法主义、及直接复议主义,并民治主义之原则”。(注:严建章:《国民大会及国民代表大会之得失之申论》,《申报》1920年9月12日。)显然,“国民大会”运动,是与世界范围内直接民权的高涨相呼应的。
不过,时人对国民大会的理解不一致。梁启超主张以“国民动议”、“国民投票”制宪;李大钊认为国民大会应随时随地自由集合;标出解决时局的办法交给南北政府去办,“竖起民众万能的大旗”;彭一湖认为国民大会应宣告南北统一,制定国会组织法选举法、人民自由权利保障条例、地方制度,决定全国兵额、组织国民法庭审判祸首。(注:梁启超:《国民自卫之第一义》,《晨报》1920年8月1日;李大钊:《要自由集合的国民大会》,《晨报》1920年8月17日;彭一湖:《关于国民大会之提议》,《晨报》1920年8月2日。)尽管人们赋予国民大会的职权有广泛与狭窄的差异,但它意味着人民的直接参政权则是一致的。
“国民大会”是国民自决思想的产物。南北议和的流产使国人对南北政府失望,安福国会的祸国也预示着议会政治的失败,废除督军的呼声是对军阀们的憎恶。知识界对于解决国是的希望转而寄托在人民身上。1923年底、1924年初的国民会议运动也是一种追求直接民主的运动,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反映了北京政府合法性正在逐渐丧失的现实。
国民大会作为一种不定期的公众政治集会,其作用与议会的功能是很难相互取代的。议会与政府之职权互相对峙而牵制。议会最大的权力是立法权,通常还具有议决预算案和决算案的财政权,以及质询、查究、受理请愿、建议、弹劾、不信任投票、对政府机关活动进行调查的监察权。政党制度也是与议会制度互为表里的制度,多数党执政是议会政治的游戏规则。20年代的国民大会运动、国民会议运动,是带有激进民主色彩的民粹主义运动,是一种追求直接民主的运动。
孙中山直接运用“国民大会”来构思他改造代议制的方案,是在中央政府代行直接民权的机构。不过,国民大会的职权在《孙文学说》与《建国大纲》中的表述有不太一致的地方。《孙文学说》规定训政时期,“国民大会职权,专司宪法之修改,及制裁公仆之失职”,五院向国民大会负责,监察院向国民大会弹劾各院人员失职,监察院人员失职由国民大会自行弹劾而罢黜;宪政时期,国民大会代表人民行使对于国家政治的创制、复决、罢官权。(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205页。)《建国大纲》所设想的国民大会,一是制宪的国民大会,一是宪法施行后的国民大会。后者是民众在中央一级代行直接民权的机关,即“对于中央政府官员有选举权、有罢免权,对于中央法律有创制权、有复决权。”(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129页。)国民大会由各县选出一个代表组成。
孙中山对于国民大会的设想是较为粗略的。国民大会由两千人规模组成,如果作为集会议事的机关,人数太多,无法作为有力量的民意机构代表人民监督政府。如果作为直接民权的代表,人数太少,而且间接的行使直接民权,直接民权也就失去本来的意义。自“国民大会”的构想提出后,一直成为国民党人制宪活动中的一个难题。
二
从北京政权到南京政权,不仅是最高统治者的转换或首都的更变,更是一场深刻的体制变迁。“国民大会”最初是作为国民党人制定“五五宪草”、试行孙中山的宪政方案而进入其制度设计的。宪法草案前后七易其稿,“国民大会”及其引发的立法机关的设置问题是引发争论的焦点之一。如当时参与讨论的学者所言:“‘国会大会’为新款的机关,故争论亦最烈。大概不立宪则已,立宪则必须有国民大会;不然便无须立宪。”(注:钱端升:《评立宪运动及宪草修正案》,《东方杂志》31(19),1934年10月1日。),钱端升不主张此时立宪,即因他认为人民政治程度太低,国民大会绝无成功的希望。
在各稿宪法草案中,国民大会的职权有重大修改,其常设或执行机构的存留始终是一个有分歧的问题。
最早的宪草稿本是吴经熊所拟的稿本,他提出国民大会职权10项,既包含孙中山勾画的诸直接民权,也包含修宪、解决国民政府提请解决之事项、对于国民政府提出质问等若干国会的权利。但吴稿没有为国民大会设立一个常设或执行机构。
1933年11月主稿人会议通过的宪法草案初稿规定,国民大会闭会期间设“国民委员会”,委员名额定为21人,并对委员资格作了限定,此项委员不以国民大会代表为限。这一“国民委员会”有受理弹劾等权。1934年3月发表的宪法草案初稿中,“国民委员会”增加了候补委员,并增加对行政权的制约,“国民委员会”兼有受理立法院对行政院不信任投票案之职权。与吴经熊稿相比,宪法初稿增加了“国民委员会”,且立法权也有所扩张,在国民大会闭会期间,以国民委员会行使一部分的最高权并有权调剂各院间的对抗。有的论者认为,这种设计的毛病在于,国民大会闭会期间人民四种政权当如何行使的问题未能解决;国民委员会的职权兼含有权与能两方面的性质,立法院亦被认为人民代表机关,与国民大会将成为两个人民代表机关。(注:林家端:《宪法初稿中关于政制问题之商榷》,《东方杂志》31(8),1934年4月16日。)也有论者对国民大会的地位也提出异议,直接民权交付代表机关行使也就失去了意义,认为或则取消,或者增加实权,延长会期。(注:陈受康:《宪法初稿的国民大会》,《独立评论》99号,1934年5月6日。)
1934年7月公开的初稿审查修正案中,“国民委员会”改称“国民大会委员会”,取消受理不信任案的职权,只有受理弹劾案的权力。宪草修正稿中的立法系统仍受到不少批评。修正稿中有三个立法机关:国民大会、国民大会委员会、立法院。宪草初稿中,国民委员会有受理弹劾、不信任投票权,审查修正案中,国民大会委员会的权力取消了不信任案,只有受理弹劾案的权力。同时有复决预算、宣战、媾和、解决总统与各院提请事项等权限。三个立法机关受到批评,《大公报》指出,“这种三个立法机关相峙对立的情形,实是任何政治制度下所没有的”,这种立法体制施用起来的弊端是,立法责任将无专归,国民大会委员会与立法院的关系难以协调。《大公报》提出两个修正办法:一是完全抛弃现有的庞杂思想,别立简易体系,尽量采取立法与行政打成一片的内阁制度;二是将国民大会当成选举团,国民大会委员会的职权还要扩大,使之变成苏俄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总揽立法行政两大权,然后再由国民大会委员会产生内阁处理各部事务。(注:《修正宪草中之立法系统》,《大公报》1934年8月10日。)陈之迈也认为修正稿中的三个立法机关职权重复,提出“行政立法的体制”,并认为国民大会的职权应该大为削减,“使它的职权只限于选举及罢免政府的重要官吏,创制立法,复决法律案及法律,收受总统及各院的报告”(注:陈之迈:《评宪草修正稿的行政立法体制》,《东方杂志》31(19),1934年10月1日。)。
初稿、修正稿的特点是国民大会之下设立了常设组织,国民委员会或国民大会委员会显然是代表国民大会行使政权。按孙中山的构想理解“国民大会”的学者主张取消国民委员会或国民大会委员会。陈茹玄认为,代表人之不能转授代表权,已为近世行代表制度国家之铁则,“国民委员会何为者耶?留之则两伤。去之则双美,吾故曰可去之矣。”(注:陈茹玄:《国民大会中之国民委员会问题》,《时代公论》132号,1934年10月5日。)涂允檀也认为,国民大会应减少代表总额,增加会次,延长会期,“国民大会委员会以间接选出,不能代表人民,又不受国民大会支配之寡头组织,赋以如此庞大权力,真所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注:涂允檀:《评宪草修正案》,《国闻周报》11(36),1934年9月10日。)
立法院所三读通过的草案与以前各稿的重大差别是取消了常设的国民大会委员会。实际是回到了孙中山以国民大会在中央代行直接民权的路子。如果说,初稿、修正稿走的是“重回代议制”的路子的话,三读草案实际又回到“改造代议制”的思路。按照西方国会的功能来理解“国民大会”的学者则反对取消国民大会的常设机构。钱端升认为,三读通过的草案远不及修正案,二读、三读案取消常设的国民大会委员会,“将国民大会的创制权复决权大加扩充是极不妥当的,取消国民大会委员会则等于促成国民大会的失败”。(注:钱端升:《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东方杂志》31(21),1934年11月1日。)陈之迈也认为取消国民大会委员会不妥,一是国民大会闭会期间将无从行使政权,二是人民失去了监督政府的机关,三是总统不受监督。(注:陈之迈:《评宪草》,《独立评论》129号,1934年12月2日。)显然,陈强调的是政府外民意机关的监督,而不是体制内的监督。
孙科捍卫了孙中山关于直接民权的构思。对于“国民大会”的性质,孙科的解释是:它是宪法会议,外国革命之后、建国之初的Constituent Assembly,但外国只开一次会,中国变成常设机关;其次它的性质是“国家政权行使的最高机关”,人民行使四权,“可以说完全是一种创作的新制度,现代各国都没有这种制度的”。孙科反对将国民大会理解为西方的国会,反对设立常任委员会,反对行政院、立法院受国民大会节制的“国会一权政治”,认为与孙中山权能分治的主张相背离,“国民大会之政权,决不能与政府之治权相混淆;而其界限,则惟返求诸政权——四种直接民权之本义而已”。(注:孙科:《中国宪法的几个问题》,《东方杂志》31(21),1934年11月1日。)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孙科坚持孙中山的原意。
“五五宪草”所规定的国民大会的职能,主要体现的是孙中山“直接民权”的构思。稍后,南京政府公布了国民大会组织法与选举法,并在部分地方进行了国大代表的选举。在这前后,国民大会的运作再次受到关注,有关国民大会的职权、选举、期限,仍成为讨论的热点。即便国民党人有关国民大会的制度设想已进入实践层面,不少学者仍坚持直接民权是过于遥远的理想,在当时不切实际,不啻画饼充饥。胡适即主张宪政从限制的选举权入手,创制、复决,罢免的民治新方式都是在代议制的民主宪政长久实行之后用来补充代议制之不足的,“我们此时应该从一种易知易行的代议制下手,不必高谈一些不易实行的‘直接民权’的理论”(注:胡适:《我们能行的宪政与宪法》,《大公报》1937年7月4日。)。而国民大会的主要职能是在中央政府代表国民行使直接民权,这种间接的“直接民权”引起学者们的质疑。张佛泉认为:“国民如不能直接行使创制复决罢免等权,即是不能行使,在此只能放弃直接民权说。由代表替人民行使创制、复决、罢免,便不能再称为创制,复决,罢免,此种名词意义已很固定,未容再加滥用。”(注:张佛泉:《政治现状如何打开》,《国闻周报》13(21),1936年6月1日。)。钱端升认为,人民没有政治能力,2000人的国民大会浪费且低效,因此国民大会只能行使选举权。上述反对意见,表达了对以直接民权的“国民大会”取代议会政治的深切怀疑。
不过,正式召开国民大会的期限却因抗战的爆发而数度延期。
三
抗战时期的宪政运动是中国人追求民主的历程中的一个高潮,关于政治制度改革的讨论再次掀起。人们迫切关注政府行为法律化、政府设施制度化、政治体制民主化。“国民大会”问题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其职权也出现了“重回代议制”与“改造代议制”之间的反复,这体现在民主派人士制定的期成宪草、政协会议决定的宪草原则与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决议之间的争论与分歧。1947年宪法最后成了两者之间的妥协。
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第一届四次会议通过《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决议案》,“请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由议长指定参政员若干人,组织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协助政府,促成宪政”(注:《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决议案》,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第593页。)。各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组成的宪政期成会于同月成立。以此为契机,宪政运动在大后方蓬勃开展起来,各地纷纷召开宪政座谈会、组织宪政协进会,以重庆、成都、桂林、昆明等地尤其热烈。宪政运动有力地批判了国民党内盛行的抗战与民主对立、“军事第一”、“胜利第一”而民主不关紧要的错误舆论。
1940年3月,宪政期成会提出了针对五五宪草的修正案,是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修正草案》,也即“期成宪草”。这一草案以罗隆基、张君劢为主力在昆明改成,也被称为“昆明案”。“期成宪草”共8章138条,其37、41、44条规定了国民大会的常设组织“国民大会议政会”。国民大会闭会期间,设置国民大会议政会,设议政员150-200人,由国民大会代表互选产生,任期三年,不得兼任公务员。议政会每6个月开会一次,其主要职权是于国民大会闭会期间,议决戒严、大赦、宣战、媾和、条约案;复决立法院所决议之预算、决算、法律案;创制立法原则;受理监察院依法提出之弹劾案;对行政院正副院长及各部会长官有不信任权;得向总统及各院部会长官提出质询,并听取报告。(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修正草案》;杨纪:《宪政要览》;沈云农:《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8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49-50页。)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期成宪草对五五宪草中国民大会与立法院的设置原则的修正是根本性的,“它所要实现的是一种议会至上的议会政治体制”。(注:张学仁、陈宁生主编:《二十世纪之中国宪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92页。)在这种体制下,立法权对于行政权的监督是有力的。
国民党人力图约束宪政运动中的“越轨”倾向,反对这种重回代议制的倾向。蒋介石斥设立国民大会议政会的主张是袭取西欧之议会政治,与总理遗教完全不合。孙科也认为议政会的设立违反了孙中山权、能分治的原则。对于“国民大会议政会”的指责还包括“太上国民大会”、“太上政府”、“寡头政治”等。1940年4月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宪政问题集会结社言论暂行办法》,规定人们研究宪法仍必须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大纲等有关宪政法令为依据。
抗战胜利后,政协会议在举国一致的和平呼吁声中召开。政协会议确定的宪草修改方案进一步突破了“国民大会”的框架。政协会议通过的宪草修改原则12条,规定“全国选民行使四权名之曰国民大会”;“立法院为最高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之,其职权相当于各民主国之议会”;“监察院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由各省级议会及各民族自治区议会选举之,其职权为行使同意、弹劾及监察权”。(注:《宪法草案案》,孟广涵主编:《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482-484页。)上述原则是张君劢提出的。
根据孙中山的学说批评《五五宪草》的国民大会制只是间接民权而非直接民权,主张把国民大会化有形为无形,公民投票运用四权就是国民大会,不必另开国民大会。在立法院成为民意机关即行使西方议会的功能时,国民大会的存在也就不必要了,否则“徒使两个机关对立,既然给了立法院,便不能再给国民大会”。(注:张君劢:《政协宪草小组中之发言》,《再生》176期,1947年8月9日。)如果说期成宪草是“修正”国民大会的话,政协会议提出的宪草修正案是直接放弃了国民大会的形式。
1946年3月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是国民党顽固派对于政协会议所制定的宪草原则的反弹。会议决定:“一、制定宪法,应以建国大纲为最基本依据。二、国民大会应为有形之组织,用集中开会之方式,实行建国大纲所规定之职权,其召集次数,应酌予增加。三、立法院对行政院不应该有同意权及不信任权,行政院亦不应该有提请解散立法院权。四、监察院不应有同意权。五、省不应制定省宪。”(注:《中国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对于政协会议报告的决议》,《国民参政会纪实》下卷,第1506-1507页。)这五项决议,实际是推翻政协决议关于国会制度、内阁制度的精神,坚持《五五宪草》的内容。
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的制定,是由“改造代议制”到“重回代议制”的相互斗争的结果。1947年宪法规定的立法权,与五五宪草有很大区别。1947年宪法中,“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共同行使西方国会的职权。国民大会与西方议会相同的在于:全国大选产生,拥有最高立法权,制定与修改宪法。政府五院中的立法院同西方国会一样,有议决预算、决算、宣战、媾和、条约案等,但没有西方国会对于政府官员的弹劾权、国家财政的审计权,弹劾与审计权由监察院来承担。这实际是欧美式民主的主张与孙中山的宪政方案妥协的结果,而成为代议制与直接民权混合、行政部门部分行使国会功能的奇特体制。1947年宪法规定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及修改宪法,虽是有形国大,但选举虚位的元首,且修宪也是多年不遇之事,事实上跟一般国家的议会政治,只是形式上的差异了。
不过,国民党人公布这个宪法已经是其兵败大陆的前夕。此时,共产党人已经放弃了“联合政府”的主张,相信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只能靠武力来打破,历史并没有为实践这个宪法留下空间。
四
国民大会的出现及围绕这个问题发生的争论,反映的是民国宪政史上制度设计由“移植代议制”到“改造代议制”,从“改造代议制”到“重回代议制”之间的反复选择与比较。议会政治只是资产阶级民主,还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在西学东渐后已是缠绕着民国知识界的重要问题。“国民大会”的制度化,正是以改造议会政治的愿望作为驱动力的。人们围绕“国民大会”发生的争论及不同的制度设计,表现出政治精英们在下述两个方面的深刻分歧:
学理上,是如何处理直接民权与议会政治的关系。在民主政治发源地的西方,民主理论虽已从古典形态发展到现代形态,但仍出现在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的反复摇摆。对于代议政治的批评是,民主意味着政权操诸公民全体、公民直接行使政权,代议制本身并不是民主精神的产物,而是等级制的产物,更多地保证少数精英的参政权。对于直接民主的怀疑,一在于普通人民的知识程度是否能够理解与创制法律,是否有充分的兴趣与闲暇不断地过问政治问题;一在于公众过多的参与政治过程会带来政治肥大症,刺激起过高的政治欲望,对政府施加更高的社会压力与政治期待,使民主制度的稳定性难以维持。中国政治精英在追求民主的过程中,也卷入了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选择中。
从国民党的历史上看,是如何对待孙中山的宪政设计。孙中山不满意议会政治而主张直接民权,这给他的继承者们带来的问题是:如何处理直接民权与议会政治的关系;如何处理遗教与事实。直接民权在民主经验十分丰富的美国也只是在州一级实现,在中国人民的民主经验十分幼稚的情况下,指望直接民权发挥作用是不切合实际的。孙中山追求驾乎欧美的结果是他的宪政方案缺乏可操作性。孙中山树立了很高的民主理想,而国民党人执政后事实上连低调的民主都还谈不上。国民党人将三民主义视为政治宗教的结果,只能是解经、注经,“总理遗教”本应成为丰富的政治遗产,却成为难以承受的政治负担。
长于民主理论研究的美国学者萨托利认为,人民主权论意味着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只能是多数人的同意与授权,并不是简单字面上的多数人或全体人民的统治,否则可能带来“假人民之名而行使的绝对的权力”。(注:萨托利:《民主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77页。)国民党人试验“国民大会”的最后失败,表明政治理想与现实政治之间无奈的张力。
标签:国民大会论文; 孙中山论文; 代议制论文; 日本宪法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宪法修改论文; 议会改革论文; 宪法监督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