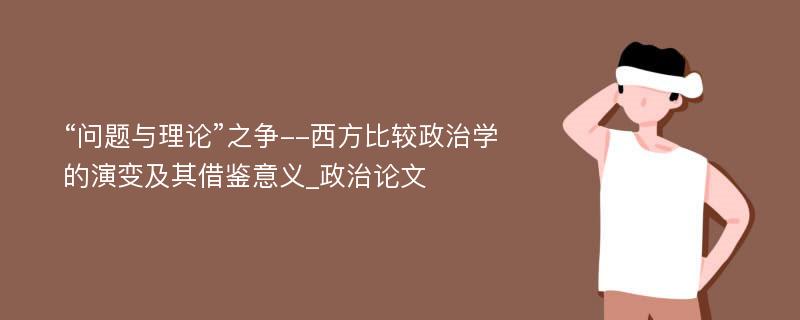
“问题与主义”导向之争——西方比较政治学沿革及其借鉴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沿革论文,政治学论文,之争论文,导向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比较政治学在西方政治学领域具有悠久的历史,其兴起几乎与政治学科的创立同时。亚里士多德被视为第一个具有典型特征的西方比较研究学者①。此后,许多著名的理论家皆为该学科的创立与发展作出了贡献。随着研究内容的深入与研究领域的拓宽,西方比较政治研究逐渐向多元方向发展,其研究类型除了原有的比较宏观的国家间的比较研究外,还涵盖了区域和跨区域的比较研究、全球治理、特定的专题研究等多方面。而在此过程中,其研究范式和方法论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20世纪末,由于世界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化及多种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引入,西方比较政治研究迎来一个新的高潮,其方法论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逐渐由基础理论构建阶段转入运用日臻成熟的理论工具对特定领域或命题进行系统分析的阶段,并以概括性描述即“问题导向”逐步取代了“主义导向”。
相对西方而言,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对其重视程度还是研究水平都有待提高。其中有两个主要问题需引起我们关注:一是对国际政治学界比较政治研究前沿课题追踪不够;二是如何处理比较政治研究的中国本土化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已形成共识,即照搬西方发展模式无法满足中国社会发展需要。但同时对过分突出中国政治特殊性对于比较政治研究的负面作用亦重视不足,时常忽视西方理论在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中可能具有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在当今西方比较政治学领域,有三种主要的方法论体系,即理性选择理论、结构主义理论和文化主义理论。它们的理论体系建构已趋于完备,并被广泛地运用到各种比较政治研究中。
1.理性选择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发端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衰落。20世纪50年代,邓肯·布莱克、肯尼斯·阿罗等学者尝试建立一种以经济人假设(即行为体行动以个体利益为基本导向)为基础的理性选择理论②。至20世纪90年代初,该理论成为比较政治学的主要方法论。理性选择理论本质上是一种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它的理论构架相对简单:其所有推论几乎都基于“理性假设”,即个体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永恒诉求。该理论认为,行为体行为的主要依据和目的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相应地,个体的政治行为亦可追溯至其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而群体行为、选择和制度的构建则一般被视为行为个体诉求的累积,这就忽略了在由个体行为向群体行为转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异向或异质变动的可能及相应影响③。这一理论同时认为这一“普适性的”理性标准不仅是理论性的,更是经验性的。这种理论的威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它指明了个体在政治活动中进行选择的“基本依据”;(2)它构建了“具有明确界定条件的可验证理论”,并由此提供了对社会政治现象进行量化研究的可能与依据;(3)它揭示了政治研究中“因果机制在自变量与变量之间产生的普适效用”④。
可以说,该理论的高度简约性和可验证性是其强大解释力的根本来源。理性选择论者也着力于在构建理论、组织论证体系和解释论题等方面显示这种优越性。该理论尤其强调,“因果机制”是人类社会最基本也是最普遍的逻辑,因此也就包含了“普世原则”,具有普适性。而在理论构建和应用过程中,为了体现这种普适性,理性选择论者更是常常不惜牺牲次要的概念差别和逻辑细节。同时,基于政治活动多为群体性行为的现实,理性选择理论同样关注群体行为取向,只不过多将之视为个体选择的集合。
但理性选择理论的高度简约性与所谓普适性,也导致了其在反映和解释真实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上的局限性。譬如,认知心理学家指出对行为结果的理性预期在人类社会现实中并不具有普遍性。个体对行为结果的判断不仅需要很强的经验支持,还会受到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这就意味着即使“进行理性选择”的意识是普遍的,但选择结果会由于经验、外在因素的影响而各有不同。许多政治实践也显示,理性选择行为本身无法在操作层面上提供确定性。由于在信息的获取上可能不确定,所谓理性的选项也可能不止一个。在这个意义上,行为体的行为仍是无法预测的⑤。这些均体现了理性选择理论失效的情况,也直接导致了对理性选择理论所标榜的“普适性”的质疑。此后出现了对理性选择理论的两种修正:一种修正被称为理性选择理论“实用主义姿态”;一种修正则是将理性选择理论视为一种对历史的“分析性描述”工具。虽然二者表述上略有差异,但本质上是相同的,都对原有的“普适性”理论进行了“条件”的限制,所以无论是否继续坚持理论的“一般性”内涵,他们均强调了由于条件的不同导致理论模式运行方式和结果的差异。笔者认为,这可以视作“主义导向”向“问题导向”过渡趋势的第一种表现,即从对一般性理论的诉求到对特定条件的重视。同时,我们还发现,第一种修正使理性选择理论与政治文化产生了关系,而第二种修正则借鉴了结构主义关于外部条件对行为体影响的观点。这样一来,原本相对独立的方法论体系,在针对特定问题的研究中建起了沟通的桥梁。这是“主义导向”向“问题导向”过渡趋势的第二种表现,即在特定问题域原本相对独立发展的方法论体系实现联系和合作。这两种表现在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方法论的发展过程中同样有所体现。
2.结构主义理论。结构主义理论最早形成于马克思和韦伯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组织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作为一种历史主义视角被引入比较政治研究⑥。相对于侧重微观的理性选择理论而言,结构主义理论是一种宏观的方法论体系。结构主义论者反对将社会视为基于个体意识与行为形成的社会关系与文化理解的总和;相反,他们认为特定区域内的社会生活与活动是由互动过程、关系及形式构成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⑥。但对于比较政治研究而言,这种宏观理论实际上可操作性不强。它并没有说明在宏观视角下可以比较什么,如何比较以及何种案例适合比较。对此,比较政治学者曾进行过多方面的探索。
莫尔比较分析了英、法、美、中、日、印等国的现代化路径,将结构主义的宏观理论系统地运用到对不同社会的政治体制发展的比较研究中。莫尔试图将宏观的历史分析与具体的案例研究结合起来,将特定的历史时期置于常态政治下进行考量,脱离所谓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简单划分,将欧亚国家放在同一理论标准下进行对比分析。在分析过程中,阶级关系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被凸显出来。另外,莫尔将总体的历史视角与现实主义和韦伯的组织理论融合,使结构主义方法论对比较政治议题具有更强的解释力⑧。由此,结构主义理论从一种“一般性”的方法论,被改造成适合进行案例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论工具。换言之,在这种理论被引入比较政治研究的同时,它亦开始由“主义导向”向“问题导向”进行转变。
这种趋势在斯科波尔的研究中得到进一步强化。她继承了莫尔的比较研究传统和结构主义视角,但认为莫尔在强调阶级统治和阶级关系的结构和过程对社会变化影响的同时,忽略了政治机制这一社会变革中的关键因素。概括地说,斯科波尔为结构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做出了三个重要贡献:超越了马克思直线式的历史唯物主义,代之以截面式的和静态组织式的唯物主义;具有一种极强的倾向,即对政治机构而言,将结构引导下的发展趋势视为一个执政的着眼点而非一个选择;完成了一种从框架式向案例式的比较政治研究策略的提升⑨。在这一理论基础上,结构主义理论进一步细化到对宏观结构与特定阶级间联动机制的研究。
此后,结构主义理论完成了由“主义”向“问题”转变的第三步,这一进展的推动者可归功于新历史制度主义者,如玛丽·道格拉斯等。他们同莫尔和斯科波尔一样坚持结构主义的宏观分析框架,同时亦突出个体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因此,新制度主义的最大特点是“在完成宏观分析的同时,至少并不排斥将经过极度净化和理性化的个体主义视为具体的微观基础”⑩。显然,这种发展将宏观的结构主义与微观的个体主义结合,显示了在特定问题域与其他方法论之间建立有效的联系与合作关系。
3.文化主义理论。文化主义理论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孟德斯鸠关于地理与民族性格的研究。后被马克斯·韦伯和加塔诺·莫斯卡继承发展。相对于理性选择理论,文化主义理论和结构主义理论属于宏观方法论,文化主义理论试图理解生活方式、意义系统和价值观在人类社会发展和变化中的作用。但与上述两种理论不同的是,由于文化本身即是某特定群体独有的内在特征,因此文化主义理论自始就对理论的“普适性”持保留态度,而对特定案例进行细致入微的解读,以求从中发现文化作用于人类社会的某些体现,即克利福德·格尔茨所称的“深厚描述”(thick description)(11)。但由于历史条件和学者偏好等限制,早期的文化主义理论视角较为单一,多局限于对西方文化与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内在联系的研究上。阿尔蒙德和维巴实现了文化主义理论的第一次飞跃。他们比较研究了英、美、德、意及墨西哥等国公民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诉求,试图通过抽样问卷和访谈的定量分析方式揭示政治文化与民主政体之间的关系(12)。这使文化主义的政治研究得以摆脱狭隘的文化视角,开始从宏观视角寻求文化与社会发展和制度建设之间的广泛联系。但在这个阶段,欧洲一些国家或所谓“现代文明”仍然被置于“标杆”地位,借以衡量不同社会的发展程度。同时,文化概念的模糊性也引起重视,而文化的定量研究方式遭到不同程度的质疑。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文化主义的比较政治研究视野逐渐开阔。文化主义理论进入新的阶段,笔者称之为文化本质主义阶段,其代表人物包括白鲁恂、罗伯特·帕特南和弗朗西斯·福山等。这些学者认为,一个社会的文化背景最终决定了该社会的政治特点和制度构建模式。这暗示了,一种文化背景下的规制构建方式是无法移植到另一文化背景的社会中的。文化本质论者至少在以下几点上推动了文化主义方法论的发展:首先,他们开始真正关注西方发达国家以外的广阔区域里文化在社会塑造过程中的不同作用,由此将文化主义由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关注,转向对文化与社会发展这一比较政治议题的关注。其次,他们将文化影响与社会规制构建相联系,弥补了早期文化主义对结构要素的忽视。再次,描述性分析、定量分析、历史主义分析等研究方法被相继引入,为文化主义理论与其他方法论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条件。简言之,在这一阶段运用单一标杆框定不同社会发展的观点已渐式微,而跨理论的合作逐渐成为政治文化研究的重要手段。但仍有两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即文化概念和范围的界定问题,以及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的界定问题。
这两个问题在“文化条件主义”阶段得到解决。文化条件主义认为,文化主义者认识到文化范畴界定上的特殊性,“解决(文化研究单位)问题最好的方式或许是对文化认同的分层和分情境定义”(13)。同时文化被视为社会发展的一种限制条件而非决定性因素。文化条件主义强调文化、社会结构与社会发展结构三者间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的关系。
综上所述,在西方比较政治学三种主要方法论的构建和完善过程中,蕴含了西方比较政治研究发展的某种内在规律。这种规律在对“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的比较政治研究过程中同样有所体现。
二
对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特点和趋势的分析一直是西方比较政治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发展理论的比较政治研究进入全盛时期,并随之涌现了大批研究成果。总体上它们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以欧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为国家发展的最佳途径;二是这个时期的发展理论与美国的对外援助政策密切相关(14)。
我们可将这一时期的发展理论依然定义为“主义导向”:一方面他们将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视为普适的社会形态加以推广,另一方面这一理论本身在冷战背景下被赋予了一定的意识形态因素,由此同样具有“主义导向”理论常见的一系列问题和缺陷(15)。首先,这一阶段的发展理论对某些重要中间行为体,如贸易和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缺乏深入理解,对政党在政治体制中的作用和行为规律也缺乏深入理解。其次,对政治寡头和统治阶层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的研究并不深入,且被认为是非必要的,因为,西方模式被认为是适合国家发展的唯一模式。由此也就忽略了非西方政治体制模式长期存在的可能。再次,没有将异化的民主规制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形态作为一种发展途径进行研究。本质上对于“政治发展”的内涵没有明确界定,单纯认为尊崇西方模式就是发展,但至于发展是如何体现和衡量的,并没有完善的解释。
这个时期还相继出现了依附理论、新政治经济学理论、统合主义理论以及新制度主义理论等。它们通过对第三世界国家不同政治层面、行为体和政治关系的分析,对发展理论进行批判,以求获得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方向和过程的新理解。从以欧美模式框定发展中国家到对这些国家自身特有条件的研究,笔者以为,这是比较政治研究由“主义导向”到“问题导向”过渡的重要变化。其中一个典型例子是发展主义国家理论。该理论1982年由美国学者约翰逊基于对日本的考察提出(16)。这一理论根据对一些新兴国家的考察,认为发展主义国家就是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但同时建构一系列社会政治条件以最终实现其发展目的。它将研究视角放在取得惊人发展成绩的亚洲新兴国家之上,试图建立一种有别于原有发展理论设计的以国家为中心、以经济发展为重心的发展模式。
当然,由于研究多是建立在对特定国家的特定条件的理解之上,这一理论无法对条件不同的国家的发展特点进行十分有效的诠释,换言之,它们都不是普适的,或主义导向的。而这一点亦为西方比较政治学界所接受,即鲜有一种理论能够囊括所有的分析层面或解释所有问题,而将现有各种理论综合起来对同一特定问题域进行分析,则可能得到一个更为完善的认识。由此在发展议题上经由“主义”到“问题”的转变趋势得以进一步明确。
通过对以上两种视野的梳理,西方比较政治研究中由“主义导向”到“问题导向”的发展趋势凸现出来。这种趋势并不是单纯的由总体到细节的变化,而是从“建构理论”到“解决问题”的研究理念的转变,也不意味着理论综合的销声匿迹,相反理论联合和合作的趋势同样明显。更重要的是,这种联合与合作的目的不在于建立某种大一统的普适理论体系,而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在对问题领域全面了解的基础上以解决特定问题为目的”的实用主义倾向。
本土化问题,一直是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一个有争议性的问题,因为它关乎如何处理中国政治和文化条件的特殊性与“政治运行过程中普遍规律性”两者之间的关系(17)。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本土化或有两条路径可以选择:一是构建完全独立于西方的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体系;二是集中于对某问题域的探讨,在借鉴西方现有理论成果的同时,注重对中国特有条件的研究对于整个学科建设的贡献。
西方比较政治研究也曾经历较长时期对普适性或“主义式”理论的探索,但并没有成功,最终导致了向“问题导向”的转变。那么,对于中国比较政治研究而言,再重复西方学界的路径并非明智选择。我们还应考虑到中国社会发展对比较政治研究的急迫需求——解决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也是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核心所在。那么,建构“主义”式理论既无法保证解决中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现实问题,从西方的发展实践来看,亦会摸索较长时期。
“问题导向”是建立在对西方比较政治发展经验的认识和对当前国际比较政治研究发展趋势的把握之上的,同时也考虑到了中国政治社会的发展实际。这种选择至少有三种优势:(1)可以参考借鉴西方相对完善的方法论体系和研究经验;(2)中国的现实问题将被作为研究重点,有助于对中国社会政治发展中的问题进行多角度的认识;(3)可以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与世界接轨提供平台。一方面,相同的问题域,使西方学者可以“旁观者”的视角对中国问题提出看法,再与国内学者交流,可对某问题领域得出较为全面、客观的理解;另一方面,由于问题域的通约性,对于特定领域内中国特性的研究,亦可为其他国家政治实践以及该领域的理论构建提供借鉴。
由此可见,“问题导向”的本土化道路或许更有利于中国比较政治研究和实际问题的解决。为此我们还需要做好以下三项工作:
第一,选择合适的问题域与理论。如上所述,当今西方比较政治学界致力于将现有理论运用于多个问题域,但确定中国的政治社会问题具体应归哪一领域研究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许多问题都具有极高的复杂性,涉及多层次、多领域。这虽然为我们从各种角度审视同一问题提供了条件,但也为对问题本身的全面认识和寻求妥善的解决方案带来了困难。
第二,选择适合的切入点。适合的切入点往往是现存理论能否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甚至是该理论能否被用来解释中国问题的关键。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看似与西方理论格格不入,但如果找到恰当的切入点,则会对该问题域的理论建设作出贡献。切入点会因理论特性的不同而各异,但至少应具备两个要素:在理论层面上,由之切入能够较好地规避西方理论假设与中国现实的巨大差异;在实践层面上,由之切入的理论宜考虑到在中国现实政治环境下的可操作性。
第三,对“中国特点”进一步加以界定。有学者指出,许多所谓“中国本土化”问题其实只是某些普遍性问题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显示,过分强调中国本土化会削弱与其他社会的可比性,进而削弱了比较研究的意义和效果。那么,确定什么条件是中国特有的,什么可以被视为社会发展的普遍性阶段,成为能否适度实现比较政治研究中国本土化的一个重要议题。但笔者认为,所谓“中国特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根据特定的问题域和特定的研究角度而定。
注释:
① Howard J.Wiarda & Esther M.Skelley,Comparative Politics:Approaches and Issues,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2007,p.17.
② S.M.Amadae & Bruce Bueno de Mesquita,“The Rochester School:The Origins of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2,1999.
③ Mark Irving Lichbach & Alan S.Zuckerman (eds.),Comparative Politics:Rationality,Culture,and Structure,Cambridge &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6.
④ Ibid.,pp.20-22.
⑤ Ibid.,pp.170-174.
⑥ Ibid.,p.5.
⑦ Ibid.,p.83.
⑧ Mark Irving Lichbach & Alan S.Zuckerman (eds.),Comparative Politics:Rationality,Culture,and Structure,Cambridge &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87-90.
⑨ Ibid.,pp.9O-94.
⑩ Ibid.,pp.102-107.
(11) See Clifford J.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New York:Basic Books,1973.
(12) Gabriel A Almond & Sidney Verba,The Civic Culture: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
(13) Mark Irving Lichbach & Alan S.Zuckerman (eds.),Comparative Politics:Rationality,Culture,and Structure,Cambridge&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52.
(14) Howard J.Wiarda & Esther M.Skelley,Comparative Politics:Approaches and Issues,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2007,p.57.
(15) Ibid.,p.58.
(16) See Chalmers Johnson,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1925-1975,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
(17) Yang Zhong,“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in China,”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Associa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Studies,vol.3,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