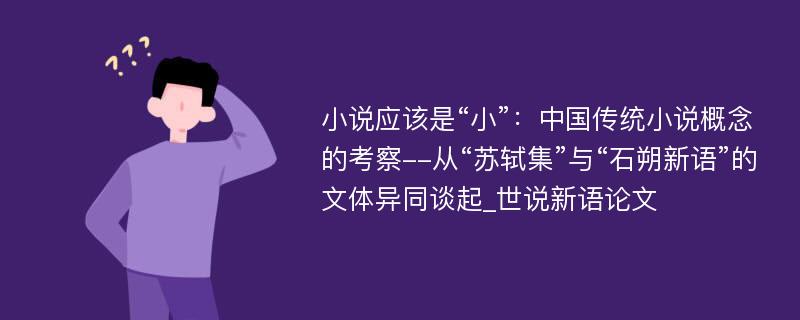
小说应“小”:中国传统小说观念的考察——从《搜神记》和《世说新语》的文体异同入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异同论文,小说论文,中国传统论文,文体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86(2006)12-0049-04
现代学术史上,《搜神记》和《世说新语》一直被当成六朝志怪小说与志人小说的代表。然而,考察《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世说新语》见录于子部小说类,而《搜神记》却见录于史部杂传类,也就是说,在《隋志》的编撰者看来,《世说新语》是小说而《搜神记》却不是。这不仅表明《世说新语》和《搜神记》有着文体上的差异,也由此反应出了不同历史时期小说观念的演变。
一
鲁迅论六朝志怪之书说:“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1](P28)虽然是把志怪之书纳入到小说史的整体框架中谈论,但也告诉我们不能简单地以现代小说观念去看待它们,一方面,从这些志怪之书的编撰者来说,并没有进行小说创作的自觉意识,即“非有意为小说”;另一方面,从社会心理说,在当时人看来鬼怪和人恐怕都是实存的,“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不存在“妄”与“诚”的区别。
干宝自序《搜神记》云:“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亦安敢谓无失实者哉!……仰述千载之前,记殊俗之表,缀片言于残阙,访行事于故老,将使事不二迹,言无异途,然后为信者……今之所集,设有承于前载者,则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这里谈到了《搜神记》的材料来源,一是“考先志于载籍”、“承于前载”、“缀片言于残阙”,即转录前人的著作;一是“收遗逸于当时”、“采访近世之事”、“访行事于故老”,即搜集民间的口头故事。干宝申说《搜神记》的材料来源,实际上是强调所记之事的真实性。值得注意的是,两种材料中尤以前者为主,有学者研究指出:“《搜神记》二十卷共四百六十余则故事,其中有前代典籍可据,或有当代及稍后其他著作可资相互参证者,竟占十分之八、九。”[2](P479)《搜神记》的内容多有所本,诚如鲁迅所言“非有意为小说”。
由于讲求资料的信而有征,《搜神记》的内容往往被人当成史料,具有了补充正史的重要作用。裴松之为陈寿《三国志》作注,广泛搜辑史料补充陈书,其中引用了《列异传》、《异林》、《博物志》、《神仙传》等多种魏晋志怪之书,干宝《搜神记》亦在其中。裴氏《上〈三国志注〉表》云:“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征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这里列举了四种作注方法,即“补阙”、“备异闻”、“征其妄”及“有所论辩”,可见他对资料的引用相当谨慎,并且时时注意以真实为出发点。那么,《搜神记》中的材料在裴氏看来也是真实可信的。除裴氏外,别的史学家也有持相同看法的,刘昭《续汉志注·五行志》、刘知己《史通》对《搜神记》中的材料都有多次征引。
考察《搜神记》的材料来源,我们发现该书具有尚实的史书性质;再考察《搜神记》文本的艺术表现,就会发现它又具有虚构的文学特征。它的文学性是由书中部分民间材料所决定的。干宝说自己“收遗逸于当时”、“采访近世之事”、“访行事于故老”,从而在书中著录了不少奇闻异事,比如人鬼婚配、奇遇异梦、人死复生、人兽互变等等,这些故事,题材怪诞,事无可考,只能是作者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发挥艺术想象的结果。
干宝自序说:“今之所集,设有承于前载者,则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幸将来好事之士,录其根体,有以游心寓目而无尤焉。”干宝承认他的作品有一定程度的“虚错”,也就是指书中有不真实、不合符事实的地方,尽管他从史书传统说起,认为《左传》、《史记》也难免有“虚错”之处,目的在于强调《搜神记》的真实性,但毕竟承认了不可能完全真实。我们认为,这些不真实之处就是作者在反映真实的生活情状与真实观念时所进行的艺术想象与细节虚构。正是这一切,使《搜神记》从纯粹的史书中脱离出来,从而具有了“游心寓目”的文学魅力。
从史书实录的原则来看,《搜神记》的史学因素并不充分,其中夹杂着不少虚构的成分。这也是六朝志怪之书的共同特征。《隋志》将六朝志怪之书列入史部,而在小序中说:“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传》,以叙圣贤之风。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3]“史官之末事”这一概括,反映了《隋志》的编撰者对这些志怪书文体特征的认识。
二
《世说新语》自其问世,流传至今已有一千五百余年的历史。《隋志》将其录入子部小说类,自此以降,历代目录大多如此归类,但也有个别书目将它录于史部,如《孙氏祠堂书目》便是将它著录在史部传记类。这说明,《世说新语》和《搜神记》一样,在文体上也体现着文学与历史的交融。
《世说新语》是一部以记人事为主的书。据余嘉锡统计,书中涉及的各类人物多达一千五百余人,[4](P2)其中有曹操、曹丕、司马氏等帝王;有王导、谢安、桓温等将相;有阮籍、嵇康等名士;有何晏、王弼、孙绰等清流;有支道林、慧远等高僧;甚至还有班婕妤、谢道蕴等女性,可以说,描绘了一幅生动的人物画卷。这些人物绝大部分活跃在魏晋的历史舞台上,他们是现实中实有的人,其生活年代和主要生平事迹往往有史可查。这使得《世说新语》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史学的意味。宋人董弅刊《世说新语》,跋语中称:“今人雅尚清谈,唐初史臣修书,率意窜定,多非旧语,尚赖此书以传后世。”嫌《晋书》未能尽依《世说新语》原文,可见是以《世说新语》的记载为史实了。
《世说新语》记人,主要是记人物的逸事传闻,虽不入正史,却能与史书相发明。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注,多次引用《晋阳秋》、《续晋阳秋》、《殷浩别传》等书中的内容,以补充《世说新语》的故事或纠正《世说新语》中记载所不合史实之处,表明在他的心目中,《世说新语》具有史书一样的价值和地位。实际上,《世说新语》一直为治史者所重,一方面它提供了补充正史的资料,正如刘知己在《史通·杂说》中所说的那样,“皇家撰晋史,多取此书”;另一方面,它是后人了解魏晋社会的重要文献,在研究魏晋时期的政治、文学、哲学思潮、时代风尚等方面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尽管《世说新语》有着某种史学意味,但与史书却有着很大的差异。史书的写作,是在充分占有真实材料的基础上,再现历史事件和人物,使读者对于相关事件和人物获得客观、全面的了解。但《世说新语》记人事,在于通过对人物行为举止、言谈笑貌的描写凸现人物的个性、神采与风度。如“王戎有好李”条:“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俭吝》)仅用“恒钻其核”四字,就把王戎铿吝的本性刻画出来。又如“王澄出荆州”条,记述王澄离京赴任之际,在送别人群的众目睽睽之下,脱衣上树去抓雀子,“神色自若,旁若无人”(《简傲》),显示出王澄的任诞放达。
《世说新语》不虚构人物、不杜撰离奇情节,但为增强作品的感染力也进行了细节加工,比如为人所熟知的“周处斩蛇”故事,文中写道:“处即刺杀虎,又入水击蛟,蛟或浮或没,行数十里,处与之俱。”(《自新》)描写如此细致、生动,好像作者身临其境目睹其事,显然带有想象和虚构的成分。再如《惑溺》:“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夫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这类闺房私语不可能有人听见,但这里却写得绘声绘色,自然也是艺术加工的结果。
《世说新语》中的材料为史家所重,而表述材料的手法又极具文学性。宋人秦果序孔平仲《续世说》云:“史书之传信矣,然浩博而难观;诸子百家之小说,诚可悦目,往往或失之诬。要而不烦,信而可考,其《世说》之题欤。”[5]认为《世说新语》既有小说的可读性,又有史书的真实性,指出了《世说新语》亦文亦史的文体特征。
三
《搜神记》与《世说新语》都体现出文体的驳杂性,这是中国古代文体发展的必然结果。六朝时期正是各类文体的蜕变与转折时期,就小说而言,一方面,虚构性因素在杂史中得到加强,表现出小说对史书的渗透;另一方面,小说又还没有完全脱离对史书的依赖。刘知几在《史通·采撰》中云:
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谈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虽取悦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6](P287)
所谓“诙谐小辩”,是指《世说新语》等志人类作品,而“神鬼怪物”则指《搜神记》等志怪之书,刘知己出于史家的责任,从捍卫史学纯洁性的角度出发,对《搜神记》与《世说新语》同时加以挞伐。这表明,在刘知己的认识中,《搜神记》与《世说新语》都具有史学价值,所以他才以史书的标准要求它们;另一方面也是看到了二者并非纯粹的史书,所以加以贬斥。无论刘知己如何褒贬,他的论述恰恰指出了《搜神记》与《世说新语》文史兼容的特性。
《搜神记》和《世说新语》同时兼有史学性与文学性,为什么《隋志》小说类著录《世说新语》而弃《搜神记》呢?实际上,《世说新语》还有不同于《搜神记》的文体特征,这主要可归纳为一个“小”字。《世说新语》之“小”有两重含义:一是体制小,言其篇幅短小,不具备完整的故事情节;二是功用“小”,言其缺乏宏大主题,远实用而近娱乐。
《世说新语》分三十六门,每门又记载逸事趣闻若干则,各则之间彼此独立、互不依赖,全书以及它的每一门都不具有系统的叙事模式,各则记事多由精彩片断和隽言妙语组成,各则之间也没有必然的逻辑关联,呈碎珠散玉状。《搜神记》也是由多则故事组成,篇幅一般也不算长,大多一百多字,其最长的篇目也不过八百来字。但比较起来,《世说新语》中的作品则更为短小,有时才几个字,通常都只有几十个字,最多也只有二百来字。《世说新语》是上千余则故事片断的联结,唯其因为单篇的短小,全书才不至于冗长散乱,反而简约有致、意蕴淳厚。日本学者菅原长亲说:“《世说》之书,玄旨高简,机锋俊拔,寄无穷之意于片语,包不尽之味于数句。”[2]高僧竺常禅师也说:“片言以核理,只词以状事,体简而意渊,语微而旨远。”[7](P178)“片语”、“只词”、“片言”、“数句”等都是看到了《世说新语》篇制上的特点。
因为篇幅短小,《世说新语》的绝大部分篇目就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搜神记》故事,一般都讲究结构布局,叙事中的人物与人物、人物与环境之间往往有着曲折、复杂的关系。而《世说新语》的记人记事,不重视交待时间、地点、环境,不重视事件的全过程,如“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赏誉》),“裴令公目王安丰:眼灿灿如崖下电”(《容止》),没有对话,没有动作,没有人物出场的背景,只是用自然景物作比喻捕捉人物的风采神貌。有时甚至连比喻都不用,如“嵇康身长七尺,风姿特秀”(《容止》),“周侯说王长史父形貌既伟,雅怀有概”(《容止》),直接对人物形貌下一断语,既没有形貌的具体描述、景物的呼应衬托,也没有修辞手法的运用。这类篇目在全书中最为常见。
由以上分析可知《世说新语》在体式上是“小”的,这是着眼于作品外在形式而得出的结论。再考察全书的主要内容与艺术表现,我们发现,《世说新语》在文学功能上也可以用一个“小”字来形容。功用之“小”,言其缺乏宏大主题,远实用而近娱乐。
前文已述,《世说新语》以记人事为主,但它的记人事,重点在于通过对人物行为举止、言谈笑貌的描写凸现人物的个性、神采与风度。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写道:“《世说新语》津津有味地论述那么多的神情笑貌,传闻逸事,其中并不都是功臣名将们的赫赫战功或忠臣义士的烈烈操守,相反,更多倒是手执拂麈,口吐玄言,扪虱而谈,辩才无碍,重点展示的是内在的智慧,高超的精神,脱俗的言行,漂亮的风貌。”[8](P94)这也就是说,《世说新语》关注的是人的个性而不是人的社会角色。
与此一致的是,《世说新语》不重视对社会功能的承载,而是追求趣味性,大抵是要自娱或者娱人。《世说新语》尤其擅长记一些畸形琐事,从而形成了一种幽默、诙谐、机智的美学趣味,如《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著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辗之,又不得。嗔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忿狷》)通过吃鸡蛋这样一件小事,刻画了王述的急躁性格,读来让人捧腹。再如《刘伶纵酒》:“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短短两句话,显得机智俏皮。书中还运用了不少生动的方言口语,如“阿堵”、“伧副父”、“溪狗”、“乃可”等等,也增添了行文的活泼、幽默。
刘知己《史通·书事》指出:“自魏晋以降,著述多门。《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载调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悦。”[6](P514)刘知己以史学家的眼光来评价《世说新语》等“志人小说”,故出以贬词,但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调谑”二字,正暗示了文本的趣味性和幽默感,而一个“悦”字,则指出了它们的愉悦功能。鲁迅说:“记人间事者已甚古,……若为赏心而作,则实萌芽于魏而盛大于晋,虽不免追随俗尚,或供揣摩,然要为远实用而近娱乐矣。”[1](P42)“远实用而近娱乐”实为中的之论。
四
《隋志》著录《世说新语》于子部小说类,却著录《搜神记》于史部杂传类,对二书的异部著录,体现出了《隋志》编撰者的小说观,即在他们看来,《世说新语》更切合他们对小说文体的认识。
何谓“小说”?这是难以下定义的。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小说是一种虚构性的叙事作品,如韦勒克、沃伦认为:“想象性的文学就是小说(fiction),也就是谎言”,[9](P237)巴尔扎克也把小说称为“庄严的谎话”。[10](P68)都指出了小说文体的虚构性;而作为叙事作品,通常认为“情节”是小说不可或缺的要素,如刘安海、孙文宪等学者就认为小说“必须有完整、复杂、曲折、生动、典型的情节”,[11](P148)如果持这样的小说观念,很显然,《世说新语》不适合列入小说类,胡适就批评《世说新语》:“虽有剪裁却无结构,故不能称作短篇小说”。[7](P174)
但这些都是今人的小说观念,而不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小说观念。在中国古代,“小说”一词,最早由《庄子·外物》道出:“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小说之名,昔者见于庄周之云‘饰小说以干县令’,然案其实际,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1](P3)这里的“小说”是与“大达”即大道、大言相对的琐屑浅识之言,还未具备文体性质。此后,小说逐渐演变成一种“记琐屑之言”的文体。东汉桓谭在《桓子新论》中说:“若夫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丛残”即聚集琐屑之事,“小语”即小言、小道,小说家采摭“丛残小语”以为“譬论”,而成“可观之辞”,这里的“小说”始有文体性质,其文体特征仍是一脉相承的一个“小”字。
其后班固作《汉书》,在《艺文志》中著录“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但同时指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认为小说家无甚可观,评价不高。班固对小说的认识是这样的: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班固这段话从两个方面对小说进行了界定,首先从成书过程来看,小说是市井乡野、街头巷尾的谈资、闲话、杂说或异闻被知识分子(“稗官”)记录加工而成的一种文体,小说的材料取自日常生活的谈资之类;其次从小说的价值定位来看,它无异于“君子弗为”的“小道”,是游离于正统政教文艺观的,但因它是采缀“闾里小知者之所及”、“刍荛狂夫之议”而成,保存了来自民间的材料,所以也不应废而不存(所谓“弗灭”也)。
分析庄子、桓谭、班固对“小说”的认识,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古代的小说文体,在它形成、发展的初期,就是指那种集合琐屑之言而成的、与高品大雅相对的文学样式;它的题材多为日常琐屑杂谈,不讲求虚构;它的篇制短小,不重视故事情节;它采缀民间谈资异闻,不追求文以载道的功能。正如顾青所言:“我国最初的小说不但形制简短,而且内容在当时被认为是浅薄的小道,具言之,于史则为民间流传的不可尽信的传说,如《伊尹》、《黄帝》、《周考》;于礼则为流行于平民口中或生活中的礼法风俗;于子则为偏于耳目所及的譬喻杂谈,与治国安邦的大道自然无涉。”[12](P3)
如前所述,《世说新语》篇幅短小,一般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可谓“琐屑之言”;它也不重视“道”的承载,远实用而近娱乐,可谓“非道术所在”;所写皆为人事,少有虚构与想象,记载魏晋士人的琐事名言,材料来源是谈资、笑柄。按中国早期的小说观念考量,《世说新语》正是典型的小说文本。《隋志》以《世说新语》入小说类而弃《搜神记》不取,意味着《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切合《隋志》编撰者对小说文体的认识,这就表明《隋志》编撰者对小说文体的认识与中国早期的小说观念一脉相承。
由以上分析可知,在唐代至少是到《隋志》成书之时,人们还是秉承传统的小说观念,也就是说,作品的体式篇幅、材料来源、文学趣味、价值取向几个方面体现出来的那个“小”字,是衡量其是否为小说的主要标准。在中国小说史上,文言笔记小说在六朝就涌现出了《世说新语》等一批志人小说,无疑是中国小说的正宗,但宋元以后随着白话通俗小说的兴起与繁荣,它最终失去了小说的主导地位。与之相应,中国传统的小说观念也就为讲求情节、虚构、叙事等要素的小说观所取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