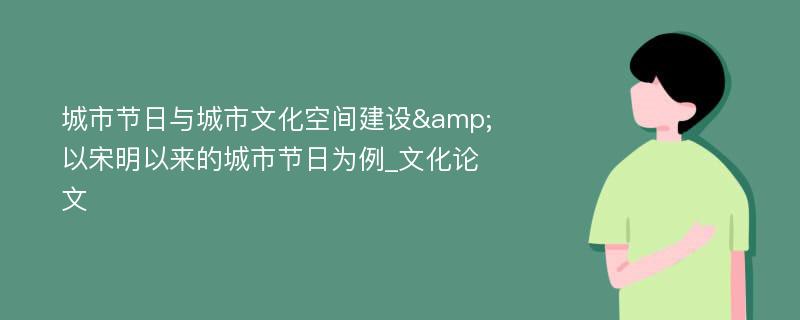
城市节日与城市文化空间的营造——以宋明以来都市节日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节日论文,城市论文,为例论文,文化论文,都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58(2010)04-0099-12
中国城市有着久远的历史,从考古发现中可知,上古三代已经形成了政治军事性城市,此后历代的大小政治层级中心都是人口集中的都市。这些都市虽然与现代城市在社会功能与空间形态上有明显差异,但其与农村社会相对区分的性质大体一致。中国的城市在早期是政治军事的都邑,居民是以有身份地位的贵族为主体。中古之后,城市性质发生变化,在商业消费动机的驱使下,城市成为经济活动中心,城市居民的主体是工商阶层等一般平民,因此城市生活形态也就发生重要变化,城市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得到重视,城市空间不再是上层阶级独占的空间。既然城市的普通人是城市人口的多数,那么他们的利益与需要、情趣与欲望,自然要在城市社会生活中显现出来。
一、传统城市节日的历史文化特性
城市生活是一种与乡村生活迥异的生活形态。虽然我们从中国农业社会的总体上看,中国城市是农业文明的花朵,但花朵毕竟与枝叶有不同的结构与色彩,长期的城市发展过程形成了城市生活传统。城市的日常生活传统这里先不去说它,我们来看城市的节日生活传统。
从历史民俗资料看,城市早期没有自己的节日,城市贵族依靠传统农业时令生活,他们的生活资源都来源于农村,他们只是城居的领主。随着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因商业、服务业与加工业的需要,聚集了众多离乡离土的非农业人口,这些人不是以熟悉的家族群居的方式生活,而是以家庭的形式或单个个体的形式聚集在相对陌生的社会中,他们居住是紧密的,但职业是分散的。城市居民在生活中逐渐因为城市五方杂处的聚居状态,形成自己的生活习性。城市有了自己的社会循环系统与生活节律,城市节日就是城市社会时间循环系统的重要环节,是城市时间节奏的重要体现。
唐宋时期的城市节日已经初现特色,明清以来城市节日愈益突出。虽然我们从城市节日的时序看,它依然遵行大的民俗传统,一年四季的节日与农业地区差异甚小,但是,值得充分注意的是,其中具体的节俗内容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虽然同样是传统节日,但过节的方式与内在的情感需求有了显著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城市生活模式的固定化,城市形成自己的节日传统。
在城市节日传统中,公共性是其根本特性。人们为公共节日需要而组织起来,人们为了公共社会文化空间的建立而聚集各种精神与物质资源。以农业地区为主的中国传统节日,主要是家庭性的节日。一般中国传统节俗是围绕着家庭伦理与家族生活展开,祖先祭祀与家庭亲人团聚、节日中的亲族往来是主要表现形式。而城市节日因为居民的居住紧密与人际关系的分散性(导致这种分散性的原因,是居民来自不同地域与他们不同的生计方式),虽然仍保留一定的家族成员的内聚性,但这种内聚性比较于节日其他要素来说相对次要,人们更看重的是户外、街市、庙会上的公共集会活动。城居百姓为了公共的利益与兴趣,重视彼此的联系与结合,以实现城市社会公共秩序的协调。城市节日的公众参与性与公共性仪式表演体现了城市节日文化空间民俗的本质特征。而城市节俗的历史文化特性集中体现在城市节日的娱乐性、宗教性及消费性三大方面。
(一)城市节日的公众娱乐性特征明显
城市节日公共性的标志之一是城市各阶层依照传统或新型的节日的时间定期举行吸引全城居民参与的公共性娱乐活动,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所说:“时节相次,各有观赏。”①
娱乐性是城市节日的重要特征之一。节日是生活的华彩乐章,节日的娱乐因素虽然未必是节日起源的原始动机,但在早期历史阶段的节日中娱乐已经是节日重要功能之一。如果从文明进程的角度考虑,那么城市节日较之乡野节日应该更加强调节日的娱乐性,因为节日的主体城市居民更重视感性的、与公共场所有关的娱乐活动,人们通过公众参与的娱乐活动,实现城市社会成员的沟通与交流。传统城市节日的娱乐性伴随着城市军事功能的消退与商业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由此产生的世俗化成分的扩大而愈益增强,顺应天时的岁时节日在隋唐之后日益成为城市生活节奏与城市信仰的社会时间,在城市节日生活中娱乐成为节日的重要特征。
集会游观与广场性娱乐是城市节日的主要内容。早期城市由于管理方式与社会功能的限制,人们较少自主性的公共活动,汉晋以前的大型城市活动都与宫廷有关,如岁末的宫廷驱傩仪式,由骑士军人充当仪式队伍。南朝以后,随着城市政治职能的逐渐消退、经济社会职能的不断增强,城市平民的公共活动逐渐活跃,城市居民利用城市节庆,举行集会游观与广场性娱乐活动,满足自身的精神与社会生活需要。
元宵节是城市节庆中最能体现城市公共生活的节日。作为中国的民俗年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元宵节在城市、农村都受到重视,但元宵节俗在城乡有不同的侧重,农村重在祈年,城市重在街市巡游、集会娱乐。从节日公共性角度看,农村元宵节也跨出了家庭,有走村串户的社火表演,但在城市里,公共参与更加热烈,习俗也更加丰富。
城市元宵的早期记载见《隋书·柳彧传》。隋朝官员柳彧在一封请求禁止正月十五侈靡之俗的奏疏中说:“近代以来,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装异形。以秽嫚为欢娱,用鄙亵为笑乐,内外共观,曾不相避。”京城与外地州城的人们利用正月十五日夜集会娱乐,鼓乐喧天,火炬照地,化妆游行的队伍填满街巷。这在当时是新起的城市节俗,因此受到保守官员的抨击可以理解。事实上,隋朝以后,正月十五上元节夜的集会娱乐成为社会上下普遍参与的活动。隋炀帝时“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②节日中的帝都街市有绵延数里、供人游观的戏场,节日成为显示太平盛世的日子。
唐宋时期,元宵节更为喧闹,元宵灯火、游人成为节日的突出的人文景观,有唐诗为证,苏味道《正月十五夜》:“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因为节日,官府取消了通常的宵禁,人们彻夜娱乐游赏。唐景龙四年(710),在正月十五夜,中宗皇帝放宫女数千人出外看灯。③当时的东都洛阳、江南扬州、西北凉州,元宵节同样热闹。宋朝将观灯的时间由三晚延至五夜,元宵灯火及游人更盛。《东京梦华录》记载,元宵节期间,皇帝登宣德楼看戏,并打出“与民同乐”的金字招牌,“万姓皆在露台下观看,乐人时引万姓山呼。”城市到处燃灯作乐,“万街千巷,尽皆繁盛浩闹。”④元朝大都的元宵花灯也吸引着游人,人们于灯市流连忘返。⑤
明清时期,元宵节依然是城市的公共性表现最强的节日。明代,京城百官放假十日,在东华门外形成灯市,卖灯的商贩、买灯的顾客、观灯的游客,络绎不绝,热闹非凡。“天下繁华,咸萃于此。勋戚内眷登楼玩看,了不畏人。”⑥明代,南方元宵灯会同样热闹,福建人尤其重视灯会。明人谢肇淛说:“富贵之家,曲房燕寝,无不张设,殆以千计,重门洞开,纵人游玩。”“游人士女,车马喧阗,竟夜乃散。”⑦明人张岱记述杭州龙山放灯的情景:“山无不灯,灯无不席,席无不人,人无不歌唱鼓吹。”⑧明朝后期江南元宵盛况,可见一斑。
清代的元宵灯市依旧热闹。清中期前,京城正月十三至十六日四晚灯火通宵,“金吾不禁”。⑨晚清,北京元宵灯火以东四牌楼及地安门为最盛,其次是工部、兵部,东安门、新街口、西四牌楼,“亦稍有可观”。⑩天津上元日,号为灯节,“通衢张灯结彩,放花炬,遍地歌舞。”(11)清代苏州闹元宵,元宵前后,家家户户的锣鼓依曲调敲起来,人们“或三五成群,各执一器,儿童围绕以行,且行且击,满街鼎沸,俗呼走马锣鼓。”(12)元宵的喧闹透出民众节日欢娱的心情。
寒食清明,是祭悼祖先的日子,但在城市生活中,人们有诸多娱乐活动。隋人所著《玉烛宝典》称:“此节,城市尤多斗鸡、斗卵之戏。”(13)这种游戏活动,在后代城市节日习俗中仍有传承,如开封清明斗鸡,一直是当地的节俗传统。从宋朝开始,城市居民借扫墓踏青郊游,庄严肃穆的祭悼演变为热闹的公众娱乐,这就是城市的节日文化。明代,杭州依然保持清明娱乐传统。扬州亦为明代重要城市,扬州清明因为有张岱的记述,让我们获得难得的节庆娱乐资料:“是日,四方流寓及徽商西贾、曲中名妓,一切好事之徒,无不咸集。”(14)扬州清明,成为城中百姓娱乐集会的节日。
七月十五中元节,在乡村是烧纸钱祭悼亡人的日子。城市的七月十五,不仅佛道俗三家各有祭仪,而且它成为城市居民出外观赏娱乐的机会。在北宋东京,“目连救母”杂剧自七夕开演,直到十五日,“观者增倍”。(15)明代,七月半杭州城市居民涌往西湖,杭州人到西湖观赏风景,自己也成了西湖的风景,如张岱所说:“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16)节日看人,是城市节日的传统。在拥挤中,在时空浓缩的节日里,人们从面对面、摩肩接踵中体验着城市人特殊的亲密关系。
中秋节在城市节日生活中也引人注目。宋代东京“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闾里儿童,连宵嬉戏。夜市骈填,至于通晓。”(17)不论贵族平民,不论成人儿童,人们都在公共场所欢度中秋之夜。明代杭州,中秋夜,人们在“苏堤之上,联袂踏歌,无异白日。”(18)虎丘是明代苏州人中秋聚欢的公共空间。“虎丘八月半,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傒僮走空之辈,无不麟集。”(19)中秋节在这里成为城市各群体、各阶层共同享用的公共时间,人们不是庭院式的私家赏月,而是在一个开阔的城市风景区娱乐聚会,这样一个公众参与的聚会,跟农村中秋的亲人团聚宴会大异其趣。清代,苏州虎丘赏月之俗虽不及明代,但其游观之风依旧,妇女有“走月亮”之俗,“妇女盛装出游,互相往还”。(20)中秋节成为城市妇女展演的舞台。可以说,节日解放了城市的妇女,盛装的妇女同时装点了节日的城市。
其他如新年、城市庙会、行业祭祀日等都是城市居民公共活动日,人们习惯在城市街头、广场、寺庙等公共文化空间聚集,热衷于行游与民俗展示活动。
(二)城市节日的宗教性集会活跃
城市是人口与物资聚集之地,也是寺院庙宇林立之区。由于经济的关系与人们密集活动的需要,城市既有适应全城甚至更大范围的人们祭拜需要的规模宏大的寺庙,也有同一街区或仅为行业崇拜的中等规模的寺庙,当然街角也会有一些影响范围更小的小庙。寺庙林立反映了城市各阶层的精神生活需要,城市节日通常都以寺庙为公共活动中心,烧香拜神、逛庙看会是传统城市居民节日生活的方式之一。
我们以宋代东京开封,元明清的北京、苏州为例。北宋东京开封城,正月十六除皇帝亲临的相国寺外,“其余宫观寺院,皆放万姓烧香”。(21)新年上庙烧香,是城乡共有的民俗习惯,但在京城,百姓只有在节日这样特定的时间才能够进入官家寺院。浴佛节,十大禅院“各有浴佛斋会”。(22)六月六日州北崔府君生日,人们“多有献送”,二十四日为神保观神生日,人们夜晚五更“争烧头香”,“天晓,诸司及诸行百姓献送甚多”。(23)“二十四日交年,都人至夜请僧道看经,备酒果送神。”(24)
北京是元明以来的国家都城,不仅有帝王的宗庙,而且是全国宗教信仰的本庙所在地,其中白云观、东岳庙、都城隍庙、都土地庙、关帝庙、雍和宫、广化寺、广济寺等尤为著名。北京人的宗教信仰常常通过岁时节日活动体现,不仅帝王要在岁时节日中举行盛大的祭天礼地敬祖、迎四时之气、祭祀山川诸神、追悼为国捐躯的将士的节日仪式,而且普通的北京居民,他们的岁时节日生活同样有着浓郁的宗教色彩。北京除一般传统节日外,也有自己的城市节会,而这些节会都与寺观庙宇等宗教空间发生关系。如元代,正月十九北京人称为“燕九节”,燕九节是为纪念长春真人丘处机诞辰所设的节日,此日,倾城士女拖着竹杖,前往南城的长春宫、白云观,“蒇扬法事烧香,纵情宴玩以为盛节”。(25)明代以后,正月十九日这一具有宗教纪念意义的节日,仍是北京的特色节日。虽然民间有节日起源的种种解释,但白云观宗教圣地的影响依旧,“京师是日不但游人塞途,而四方全真道人,不期而集者不下数万。”(26)清代白云观仍然是正月烧香赛会所在,晚清成书的《燕京岁时记》记载:“每至正月,自初一日起开庙十九日,游人络绎,车马奔腾,至十九日尤盛,谓之会神仙。”正月十九日成为北京人会神仙的佳节,有缘相遇,则“却病延年”。(27)城市节日中的祈福信仰与乡村殊无二致。
北京还有一个盛大的城市节会,那就是农历三月东岳庙会。元代,东岳庙会是京城朝野的盛会,“自二月起,倾城士庶官员、诸色妇人,酬还步拜与烧香者络绎不绝。”二十八日是岳王庙会的正日子,人们在给岳王庆生的日子里,亲近偶像,虔诚报赛,还愿许愿,盼望获得神灵的恩宠。(28)明代东岳天齐圣帝的岁时祭祀属于国家祭礼,在三月二十八日,“设有国醮”。(29)当然最兴盛的是民间香会组织的神像巡游活动:“三月廿八日帝诞辰,都人陈鼓乐、旌旗、楼阁、亭彩,导仁圣帝游。帝之游所经,妇女满楼,士商满坊肆,行者满路,骈观之。”(30)清代中期,在东岳诞辰时仍然“导驾出游”。(31)这样有着广泛市民参与的具有宗教意义的集会行游仪式是城市节日宗教性的生动体现,它促动城市居民卷入宗教庆典之中,让他们在同一节日中获得共同的情感体验。到了晚清,在东岳诞辰时已经不举行游神活动,人们将二十八日视为掸尘会期,“士女云集”东岳庙,(32)东岳庙已经成为节日期间信众游人会聚之地。从圣像巡游的仪式表演到庙中聚会膜拜的变化,虽然我们没有看到直接的说明材料,但很可能有外在与内在的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统治者对城内控制趋紧的需要,担心圣驾出游引发城内治安问题;二是人们信仰心态的变化:圣帝威严,他安居庙宇,接受信众顶礼膜拜,人们到庙中给圣帝掸尘,为的是乞求圣帝赐福。当然无论是游神表演还是到庙宇膜拜,三月二十八日是北京人的重要节日,它的宗教信仰意义始终如一。
江南苏州新年,“诸寺丛林各建岁醮,士女游玩琳宫梵宇,或烧香答愿。”苏州“男妇修行者,年初皆往烧香,必经历十庙而止,谓之‘烧十庙香’。”(33)鲜明体现苏州城市节日宗教性特征的节日是四月十四吕仙诞,俗称“神仙生日”。传说此日仙人变身乞丐,混迹人群中,烧香的人们互相挨挤,可祈福佑,民间称为“轧神仙”。(34)时至今日,苏州人仍将此节视为地方代表性节会,不过名称改为“轧蚕花”。杭州自南宋以来,就是江南繁盛地,寺观林立,城中人节日生活自然与信仰发生着密切联系。如南宋时期,二月十一日霍山神祠,“其日都城内外,诣庙献送繁盛”。(35)三月清明,“官员士庶,俱出郊省坟,以尽思时之敬。”(36)二十八日东岳圣帝诞辰,杭州有吴山庙等五处香火地,献祭之人,充满道路。(37)佛诞日,除寺院的浴佛会外,士民放生西湖,“舟楫甚盛”。六月六日是崔府君生日,“是日都人士女,骈集炷香”。七月十五中元节,“茹素者十八九,屠门为之罢市”。冬至,“岳祠城隍诸庙,炷香尤盛”。(38)明代,杭州节日民俗传统依然传承着浓厚的宗教信仰,有代表性的是二月十九日的观音会:“十九日,上天竺建观音会,倾城士女皆往。”(39)浴佛节、七月半等,市民“持斋诵经”成为节日常态,佛教信仰影响杭州甚深。清代,杭州节日中的宗教性特征仍然明显,看看晚清范祖述的《杭俗遗风》,自然就会得到以上认识。限于篇幅,此不具说。
从宋元以来的南北城市节日内容中,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明显地感受到城市节日中神圣空间的魅力。一方面,宗教场所是城市居民节日活动的重要场所,节日上庙烧香、祈福迎祥成为城市居民必不可少的节俗内容;另一方面,城市居民围绕特定宗教空间与信仰对象,形成具有城市特色的民俗节会,人们定期聚集庆祝。以寺庙神灵为中心的祭祀活动,是传统城市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寺庙都有开庙祭祀的时间,庙祀活动成为了城市节日生活的特色。
(三)城市节日的消费性特色突出
城市人口密集的程度与城市相对富裕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城市的消费性特征。节日是城市消费的重要时机,节日市场的消费行为又构成传统节日的重要内容。如果从时间过程看城市节日的话,城市节日就是一个精神消费与物质消费的过程,而且两种消费往往纠结在一起。城市节日的重要消费场所是庙会、庙市,进香、娱乐、物质消费等都可在熙熙攘攘的节日庙会、庙市中完成。
我们仍以宋代的开封、元明清的北京、明清的江南城市为例。先看宋代东京开封。正月初一为年节,自此后三天,开封府“放关扑三日”,坊巷以食物、果实、柴炭、用品等“叫关扑”。人们在城内耍闹处,搭建彩棚,买卖衣饰玩好之类。(40)立春时节,为配合鞭春节俗需要,在立春前一日,在“府前左右,百姓卖小春牛”。(41)元宵节是各种食品节物展示的佳节,如宣德门下“两边关扑买卖”,“诸般市合,团团密摆。”(42)清明,节日市场上最兴旺的是纸马铺,“纸马铺皆于当街用衮叠成楼阁之状”,(43)以此招徕顾客。浴佛节,“在京七十二户诸正店,初卖煮酒,市井一新。”(44)端午,市场上有百索艾花、花巧画扇、香糖果子、粽子、桃等。七夕,在一些瓦子及主要商业街区“皆卖磨喝乐”,磨喝乐是小的泥塑人偶。人们精心装饰人偶,“或饰以金珠牙翠,有一对值数千者”。各色节物,均当街售卖。七夕前三五日,“车马盈市,罗绮满街”。(45)中元节,是祭祀用品发卖的时机。(46)立秋日,“满街卖楸叶”,瓜果梨枣上市。(47)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市人争饮”,螃蟹、石榴、葡萄“皆新上市”。中秋夜饮酒娱乐,“夜市骈阗,至于通晓”。(48)岁末交年,“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卖乾茄瓠、马牙菜、胶牙饧之类,以备除夜之用。”(49)宋代东京节日市场丰盈,不同时节有不同的应节消费食品与用品,人们节日生活的物质性特征明显。
自元以来,北京是中国政治权力中心所在,也是物资消费的中心地区,城市节日消费性特征突出。年节是消费大节,元大都时期,从正月初一日开始,“车马纷纭于街衢、茶坊、酒肆,杂沓交易至十三日”。商人们在年节时期,在正常的市场之外,以芦苇编搭临时棚屋,售卖应节食品、物件,直到十五、十六日方止。(50)二月八日镇国寺庙会,“寺之两廊买卖富盛太平,皆南北川广精粗之货,最为饶盛。”众多商贾借皇帝与大佛出游之机,在南北二城内聚集起来,“多为江南富商,海内珍奇无不凑集,此亦年例故事。”这样铺排的年例故事,一以见“京师极天下之壮丽”,二以见皇帝与万民同乐之意。(51)端午节,南北二城赛关王会,小商人在街头喧闹处,如年节一样架棚做买卖。市场上的节日消费品,与江南略同,也是艾虎、彩线符牌等。(52)九月九日重阳节,一如端午、七夕,市场上又搭起席棚,叫卖重阳糕,还有流动的商贩推车“上街沿叫卖”。冬至,市场上开卖新历书。(53)
明代后期是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北京节日市场也体现着这样的时代特征。我们看到,北京节日消费继承着元代以来的传统,在与城市生活节律相应的民俗节日中,节日消费引人注目。元宵节依然是北京节日消费的亮点。明代,北京元宵灯市繁盛,元宵游灯市,成为一景。明人沈榜在《宛署杂记》中说:“每年正月初十日起至十六日止,结灯者各持所有,货于东安门外迤北大街,名曰灯市。灯之名不一,价有千金者。是时四方商贾辐辏,技艺毕陈,珠石奇巧,罗绮毕具,一切夷夏古今异物毕至。观者冠盖相属,男妇交错。”(54)由时人记述可知,灯市不仅是灯具的展示交易会,同时也是域内域外古今珍奇异物的交易博览会。其他节日依然有应节物品出售,清明日开始卖冰,七夕市面卖巧果,八月中秋食肆卖月饼:“市肆以果为馅,巧名异状,有一饼值数百钱者。”(55)纸店卖月光菩萨像。这些节日虽然没有元宵节热闹,但节日物品的消费依然烘托了节日气氛,饶有情趣。
清代北京节日消费仍为城市商业关注的内容。除夕之夜,伴随着迎年的鞭炮声的是各种应节商品的叫卖声,“卖瓜子的解闷声,卖江米白酒的击冰盏声,卖桂花头油唤娇娘声,卖合菜细粉声,与爆竹之声,相为上下,良可听也。”(56)元宵灯市虽然因为灯展与市易分离,没有明代繁盛,但也吸引着城市游人,其中出现了新型的冰灯。各色焰火“竞巧争奇”,“富室豪门,争相购买”。市场上的食物“干鲜俱备,而以元宵为大宗”。(57)正月二十五日为填仓节,京师居民以此日为年节消耗之后的物资补充节日,“于是日籴米积薪,收贮煤炭”。(58)二月一日中和节,京师人做太阳鸡糕,“绕街遍巷,叫而卖之”。(59)清明节琉璃厂有风筝市。闲园鞠农编的《燕市费声》对北京岁时节物消费情形,记述甚详,此不罗列。(60)清代北京围绕着寺庙形成的庙市甚多,各庙市有固定的开市日期,都城隍庙市在五月初一至八日,“百货充集,拜香络绎”。“至于都门庙市,朔望则东岳庙、北药王庙,逢三则宣武门外之都土地庙,逢四则崇文门外之花市,七、八则西城之大隆善护国寺,九、十则东城之大隆福寺,俱陈设盛夥。人生日用所需,以及金珠宝石、布匹绸缎、皮张冠带、估衣骨董,精粗毕具。”来京旅居的人,只要进入庙市,顷刻就能备办齐整所需之物,“富有完美矣”。(61)由此可见庙市货物的充盈。定期的庙市消费虽然与传统节日消费不尽相同,但它是对节日消费市场的重要补充。由于传统节日毕竟有一定的时间间隔,它不能完全满足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因此,就需要定期的庙市来满足市民购物娱乐的需要。直到民国时期,北京定期的庙市庙会仍是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清时,江南城市节日的消费特性引人注目。首先我们看杭州。从南宋开始,杭州节日消费就十分兴旺,明代杭州西湖香市尤为著名。西湖香市自花朝节开始,至端午节结束,长达四月的节日市场,可谓罕见。参与香市交易的人群来自南北地区,香市货物荟萃,“数百十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拥于寺之前后左右者,凡四阅月方罢。”(62)在杭州其他城市节日中,节日消费特性同样明显。清代杭州节日消费延续前朝,据《杭俗遗风》记载,香市虽然没有明代之盛,但春季“赶香市”的传统依旧。其次,看苏州。清代苏州新年,人们聚会玄庙观,买卖春牛图,庙内没有店铺的空间,人们支起布幕,搭建临时货棚,“晨集暮散”。(63)苏州灯市繁华,苏灯自宋以来闻名天下。苏州人自腊月开始就卖灯,“货郎出售各色花灯,精奇百出”,至正月十八日方止,这段时间号称“灯市”。(64)二月有观音香市,清明节卖清明团,端午市肆卖秤锤粽、健人,七夕前卖巧果等。岁末年市尤其丰盈,“市肆贩置南北杂货,备居民岁晚人事之需”,服务年节消费活动,“总谓之年市”。(65)
近代以后,中国城市节日形态开始有所变化,出现了许多新型的社会政治节日,但是中国传统节日在城市生活中的格局依然没有改变,虽然民国政府曾经一度想废除传统节日,但以妥协告终。
从中国传统城市节日消费的历史看,我们对传统城市节日消费特点有如下几点印象:第一,节日期间城市居民消费欲望显著增强。人们以节日习俗的方式为非日常消费找到正当理由,比如节物的备办、群体性娱乐消费、宴席的铺陈、衣饰的光鲜等等,人们在传统节日的特定时空中,有着竞赛性的消费欲望。第二,适应人们群体消费需要,城市市场空间显著扩张。节日都市市场空间异于平常,从经营时间看,一般节前数天,就进入了节日消费状态,节日当天是消费高潮,有的节日通宵达旦长时间营业,消费时间明显延长。从节日经营空间看,不仅有日常店铺进行买卖活动,又在街头增添临时性货棚、货摊,以扩大销售,适应居民消费需要。游走街巷的商贩将节日物品直接送至家户门口,这样的流动的消费方式,无疑也扩大了城市的节日市场。同时节日市场拥有大量的奢侈品与来自各地的新奇物件,这也是扩大城市居民消费空间的有效方式。第三,节日有特定的消费品。传统节日都有特定的物质符号,城市对于这些物质符号的生产与消费通常是由商家推动完成。在节日商业活动的推动下,社会出现基本统一的消费趋向,这种社会全方位的超阶层消费,其实就是在节日经济中实现的一次城市传统文化的认同。节日消费活动与消费品密切关联着城市居民的身心,物质消费与文化消费在城市节日中同步实现。
城市节日中城市居民参与的活动大多具有群体性特点,人们的节日活动除了家庭部分外,大多围绕着特定的传统街区与寺庙展开,人们在出游、进香、购物中将娱乐、宗教与消费活动融为一体。节日活动的开展过程就是一次消除人际关系的间隔、增进人们相互了解的城市认同过程,城市民俗的公共性特点较传统乡村要鲜明得多。
总体来说,传统城市有自己特定的文化空间,这种文化空间一般依托公众认可的习惯性场所或者是人们最易于聚集与参与活动的特定地点与路线。城市文化空间具有固着性与流动性,可见的文化空间与感知的文化空间有着密切配合的关系。城市文化空间有着复合的文化功能。传统城市文化空间标志鲜明,人们知道在节日时间中到哪里找到自己的精神寄托与物质享受。
二、当代城市节日与城市文化空间的营造
当代城市节日同样服务于城市居民,不过浓烈的社会政治生活,对城市节日的文化特性有着较大的抑制与消解,人们并不能通过民间组织开展自己的节日生活,城市文化空间相对狭窄与单一,城市节日的许多传统因素不复存在。但随着政府管理体制的逐渐开放,民间生活的自由度越来越大,人们希望城市有更多的传统节日,这就是近年来城市庙会复兴的因由。同时在中国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型城市,它们本来没有自己的城市文化传统,包括节日文化传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它们为了提升城市影响,人造了许多新型节庆活动,这些活动一般是以经济为中心的,跟人们的文化需要并不直接相关,所以一般没有延展的生命力。那些有文化传统的都市,即使打起了复兴城市节日传统的旗号,在当代经济浪潮与政治社会环境下,这些传统节日也发生了变化,跟传统的联系比跟当代的联系要少很多,往往是有名无实,有形无质,对城市民众的精神需要服务不够,城市民众参与的热情也有着相应的局限。这样,城市民众所需要的文化空间并没有真正完整地建立起来。
我们知道,人类学的空间概念,包括地理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三部分。人们对地理空间与社会空间的概念是明确的,而动态的组合的文化空间,容易被人忽略,其实它是重要的、需要我们用心灵与身体去感觉的空间。这种文化空间从性质上看,有神圣与世俗两类。在城市传统中,两种性质的文化空间往往结合在一起,在那里人们会实现人际的交流、与神灵的精神互动,从而使精神得到完善或更新。我们的传统节日在建设城市文化空间过程中有着重要而积极的作用。人们在同一时间,围绕着同一节日主题,以公众参与的形式,展开公共性活动,城市节日文化空间赖以形成。以传统节日为契机的城市文化空间,一般说来具有信仰与娱乐两种文化特性。
城居者在特定的时日,通过特定的线路与组织方式,在特定区位聚集,表达自己的特定信仰,城市神灵信仰是传统城市文化空间的核心要素;而城市的世俗游戏娱乐是城市文化空间的活跃力量,它以诙谐、有趣的形式吸引人们的观赏或参与,如通常所说的“行香走会”。在当代中国城市生活中,民众真正自足的文化空间还十分有限,但在一些城市有了发展的趋向,如北京的妙峰山庙会。这一文化空间虽然在地理区位上离北京中心市区较远,但它确是地道的北京城市文化空间,它是北京人精神释放与聚合的场所,传统香会通过花会的形式在此复兴。当然因为种种原因,它跟民国或更早的庙会有较大的差异,形式与内容都有许多新的变化。
此外,北京东岳庙也是民众文化空间重建的一例,虽然我们的名义是第几届民俗文化节,但普通民众正月初一上庙,还是要祈福求祥。这里,端午节的粽子都要比别的地方卖得好,不是质量更好,而是有人们认可的文化内涵。虽然我们赋予这些城市特定文化空间相当多的新文化的内涵,但最贴近人性的还是它的传统意义。可惜的是,我们对这些活跃文化空间的传统因素较为忽视。如北京琉璃厂的厂甸庙会是明清以来北京春节的著名庙会,每年春节期间人如潮涌,被国家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2010年北京春节厂甸庙会,就因某些领导从经济收入与管理方面考虑,被人为地挪到陶园亭公园内,那里收起了门票,结果引起北京市民强烈不满。文化空间虽然具有流动性特色,但传统的文化空间是不可以随意更动的,人们的习惯与心理认同是有一定指向的,对文化空间简单粗暴的挪移与改变,是对民众情感的重要伤害,更不会得到民众的接受与认同。
从城市文化运行逻辑上看,营造城市文化空间的积极力量是精神信仰,这种信仰可以是传统的神灵信仰,也可以是泛化的对未来幸福的期待。这种信仰大都通过节日仪式表现出来,所以我们说传统节日在营造城市文化空间上具有独特的作用。
我们用日本、韩国的例子,来说明类似的问题。日本京都有三大祭,即五月的葵祭、七月的祗园祭以及十月的时代祭。祗园祭还是日本三大祭之一(另外两个是东京的神田祭、大阪的天神祭)。祗园祭以八坂神社为中心,祭礼在京都的四条行政区划带展开,时间是从6月初到7月下旬,主要日期是7月17日。它起源于9世纪末,最先是为了驱除瘟疫而游街祈祷,后来演变为市民文化的一部分,成为展示京都传统文化的重要方式,至今盛行不衰。它的活动是完全由市民自治会组织的,成为京都最大的节庆活动,几十万人参加。京都人为此自豪。(66)
韩国江陵端午祭,是以端午神灵祭祀为中心形成的大型城市祭祀活动,1967年就成为韩国无形文化遗产。江陵端午祭期间,除指定的祭礼、巫祭、官奴假面戏、农乐竞赛、儿童农乐竞赛、鹤山奥道戴歌谣外,还有众多的民俗活动,如乡土民谣竞唱大赛、拔河、摔跤、荡秋千、射箭、投壶、烟火游戏、端午放灯以及艺术表演等,此外还有被称为“乱场”的商品交易。每年的端午祭活动吸引国内外上百万的观光游客。(67)在政府与民间的共同努力下,端午传统节日不仅充实、丰富了城市居民生活,成为“尝试新文化、探索新生活方式”的现代庆典,(68)同时也成为江陵城市的文化标志。江陵端午祭成为传统文化空间与现代社会成功对接的重要范例。
这些城市文化活动都以传统节庆为中心,以大型街市传统风俗展演活动为主体,以有效的民间组织为方式,构成当代城市独特的文化景观。我们可以从这些成功的例子中得到启示,即传统节庆活动,是我们培育发展城市文化空间的重要时空基础,我们完全可以结合现代经济实力与科学技术手段去扩大节日活动的规模与影响,以吸引更多的市民自觉自愿地参与其中,将城市传统节日变成当代社会生活的绚丽风景。如近年各地利用传统节日复兴的传统庙会,以及利用城市所在地区的资源兴办的新型城市歌会(如南宁歌会)与灯会(如自贡灯会)等,都是城市文化空间的生动呈现。
在当代城市节日的复兴与重建过程中,我们要注意传统与创新、中体与西用、文化遗产与商业追求的关系处理,既让城市节日成为城市民众的文化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让城市传统节庆活动成为城市名片,成为展示城市个性与城市魅力的窗口。城市传统节庆活动还可以影响甚至引领乡村文化(通常我们看到农村影响城市,但实际上常常忽略了城市文化对乡村的导向作用),从而铸就当代中国文化的精神品格。
注释:
①(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自序).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1.
②《隋书》卷15,音乐志[M](下).北京:中华书局,1973.381.
③《旧唐书》卷7,中宗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5.147.
④(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卷6“元宵”).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38.41.
⑤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组辑.析津志辑佚[M]“岁纪”.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213.
⑥(明)刘若愚.酌中志[M](卷20).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178.
⑦(明)谢肇淛.五杂组[M](卷2).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20.
⑧(明)张岱.陶庵梦忆[M](卷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71.
⑨(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M]“正月、上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10.
⑩(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M]“灯节”.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48.
(11)乾隆《天津县志》,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C](华北卷).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47.
(12)(清)顾禄.清嘉录[M](卷1).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33~34.
(13)(隋)杜台卿.玉烛宝典[M](卷二).丛书集成初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127.
(14)(明)张岱.陶庵梦忆[M](卷5)“扬州清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48.
(15)(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卷5).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55.
(16)(明)张岱.陶庵梦忆[M](卷7)“西湖七月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72-73.
(17)(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卷8).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56.
(18)(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M](第20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61.
(19)(明)张岱.陶庵梦忆[M](卷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46~47.
(20)(清)顾禄.清嘉录[M](卷8).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164.
(21)(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卷6)“正月十六日”.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40.
(22)(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卷8)“四月八日”.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52.
(23)(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卷8)“六月六日”.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52~53.
(24)(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卷10)“十二月”.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69.
(25)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组辑.析津志辑佚[M]“岁纪”.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213.
(26)(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补遗卷3)“淹九”.北京:中华书局,1959.902.
(27)(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M]“白云观”.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51.
(28)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组辑.析津志辑佚[M]“祠庙”.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55.
(29)(明)沈榜.宛署杂记[M](第17卷)“民风一”.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191.
(30)(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M](卷之二)“东岳庙”.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64.
(31)(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M]“三月”,“东岳庙”.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17.
(32)(清)让廉.京都风俗志[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1.
(33)(清)顾禄.清嘉录[M](卷1).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12.15.
(34)(清)顾禄.清嘉录[M](卷4).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96~97.
(35)(宋)吴自牧.梦梁录[M](卷1)“八日祠山圣诞”.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6.
(36)(宋)吴自牧.梦梁录[M](卷2)“清明节”.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10.
(37)(宋)吴自牧.梦梁录[M](卷2)“二十八日东岳圣帝诞辰”.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12.
(38)(宋)周密.武林旧事[M](卷3).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46~50.
(39)(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M](第20卷)“熙朝乐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58.
(40)(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卷6)“正月”.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36.
(41)(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卷6)“立春”.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37.
(42)(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卷1)“正月十六日”.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41.
(43)(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卷7)“清明节”.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43.
(44)(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卷8)“四月八日”.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52.
(45)(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卷8)“七夕”.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54.
(46)(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卷8)“中元节”.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55.
(47)(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卷8)“立秋”.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55.
(48)(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卷8)“中秋”.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56.
(49)(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卷9)“十二月”.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69.
(50)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组辑.析津志辑佚[M]“岁纪”.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213.
(51)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组辑.析津志辑佚[M]“岁纪”.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215.
(52)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组辑.析津志辑佚[M]“岁纪”.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219.
(53)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组辑.析津志辑佚[M]“岁纪”.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220.223.
(54)(55)(明)沈榜.宛署杂记[M](第十七卷)“民风一”.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190-191.
(56)(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M]“正月”,“元旦”.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7.
(57)(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M]“灯节”.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48.
(58)(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M]“正月”.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12.
(59)(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M]“二月”.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14.
(60)参看双肇楼丛书,闲园鞠农编,张次溪订.燕市货声[M].1938.
(61)(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M]“五月”,“都城隍庙”.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22.
(62)(明)张岱.西湖梦寻[M](卷1)“昭庆寺”,“西湖香市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7.
(63)(清)顾禄.清嘉录[M](卷1).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12.
(64)(清)顾禄.清嘉录[M](卷1)“灯市”.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30.
(65)(清)顾禄.清嘉录[M](卷12)“年市”.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224.
(66)年中行事·记念日事典[M].日本东京:学习研究社,初版第2次印刷.2005.144~145.
(67)参见百度百科词条“江陵端午祭”。
(68)贺学君.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以江陵端午祭为例[J].民间文化论坛,2006(1).
标签:文化论文; 元宵习俗论文; 元宵节的习俗论文; 中国节日论文; 城市公共空间论文; 消费文化论文; 传统民俗论文; 娱乐活动论文; 消费社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