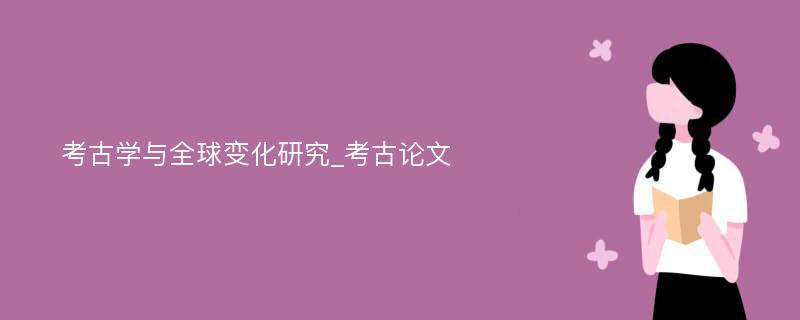
考古学与“全球变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考古学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731(2002)04-0004-03
苏秉琦先生晚年不无感触地指出:“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以地球 濒临毁灭为代价的”,“考古学应有能力来回答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协调关系问题”(注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这一论断不仅深 切地指出了农业文明发生以来人类活动对整个地球系统所造成的巨大破坏,而且也向考 古学家提出了一个新的义不容辞的研究命题。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面临的环境问题日趋尖锐,诸如环境污染、温室效应、 森林锐减、水资源短缺、土地沙漠化等问题,无不严重制约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在此 形势下,国际科学界于20世纪60年代组织了“国际生物学计划”(IBP),70年代组织了 “人与生物圈计划”(MAB),80年代组织了“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至20世 纪80年代后期,人类所面临环境灾难的规模之大,程度之重,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 都必须用“全球性”方可概括。于是,“全球变化研究计划”(Global Change Study) 这项由70多个国家参与的超级科学计划应运而生。
“全球变化”(Global Change)一词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为人类学家所使用,当时主 要是用来表达人类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愈来愈不稳定,特别是国际安全和生活质量逐 渐降低这一特定意义。至80年代,自然科学家借用并拓展了这一概念,将生态系统的各 个圈层纳入了“全球变化”的范畴,突出强调地球环境系统及其变化。由于该计划的目 标是针对整个地球系统,包括其演变过程和人地关系,所以,它包括“过去全球变化计 划”(PAGES)和“全球环境变化的人文因素计划”(IHDP)两个主要的子计划。所谓的“ 变化”,具有“恶化”或“有恶化趋势”的含义。目前,有关全球环境变化的研究已经 形成了一门新兴的科学——“全球变化科学”(Global Change Science)(注:潘家华、 庄贵阳:《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应该联手——合作开展全球变化科学的研究》,《可持 续发展研究》,2002年1期。)。
我国有关全球变化研究的权威机构所制定的“优先领域”(“九五”期间至2010年), 将“古气候、古环境研究”列为第一项。并提出目前有关“过去全球变化研究”应当关 注下列问题(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全球变化: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高等教育出版社、施普林格出版社,1998年。):
1.过去发生过什么重大全球变化事件
(1)冰期和间冰期存在什么样的温室气体以及地表温度如何变化?
(2)如何恢复定量化的高分辨率的环境要素变化记录?
(3)近千年来区域和全球地表温度是如何变化的?
(4)恢复过去千年尺度全球或区域环境变化的图像。
2.地球系统的自然反馈在何种程度上对温室气体有贡献
(1)过去的人类活动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了气候和全球环境?
(2)过去的人类活动对全球变化影响的表征量分析。
3.气候变率问题
(1)过去年代的气候突变事件的揭示;
(2)气候变率分析。
中国是全球变化研究的发起国之一,在全球变化研究方面已取得可喜的成果。但目前 也存在着严重的缺憾,其主要表现在:研究队伍几乎由清一色的自然科学家组成;在“ 过去全球变化计划”方面,则主要由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进行。这种状态导致了两个 严重不足:其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结合极为薄弱;其二,在“过去全 球变化计划”方面,数千年到数万年尺度的研究极为薄弱。而这两个方面恰恰是全球变 化研究的重中之重。
考古学对于前述“过去全球变化计划”的重点问题以及目前所存在的缺陷,都可以发 挥其他任何学科难以替代的作用。
夏鼐先生曾经指出:在社会科学各学科中,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最为密切,也最 易于和自然科学相沟通(注:夏鼐:《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考古》1979年第7期 。)。一门科学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特定的任务所决定的,而各门科学的任务又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特定的研究对象所决定的。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人类所遗留 的文化遗存,也包括与人类有过直接或间接关系的自然遗存。由于早期人类的生产活动 无不直接与大自然发生联系,因此,考古学实际上是一门介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 的交叉学科。考古学的这一学科特点和性质,决定了其在研究近1万年来的环境变迁和 人地关系机理方面均可发挥重大作用。
中国的考古遗存具有两大优势,其一是空间分布广阔,且堆积丰富;其二是时间序列 长,尤其是作为中国古代文明核心区域的中原地区,人类活动延续近万年不曾中断,且 文化发展一脉相传,从而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占据无与伦比的独特地位。中国考古学文 化赖以形成和发展的环境背景也具有独特性,例如,中国有各种类型的生态过渡带,这 些过渡带不仅对于全球变化的反映敏感,而且是探讨人地关系机理的典型区域。又如, 亚热带在世界其他地区多为副热带高压带,降水稀少,土地荒漠化严重。而中国由于青 藏高原的隆起和独特的海陆分布条件,亚热带地区的水热条件优异,除了西南地区的干 热河谷等局部性地带外,不仅基本上不存在“回归线荒漠”现象,而且成为人类和其他 多种生物的理想生存环境。这些人文和自然因素的独特性,决定了在中国进行过去全球 变化研究的典型性。
遗憾的是,本可在科学的广阔天地中大有作为的中国考古学,其学科功能却未能得到 充分的施展。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来自学科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就外部而言,包括大 多数知识界人士在内,很少有人了解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而仅仅将考古学视为研究古 物的学问。怀着如此认识的人们,自然不会考虑如何发挥考古学的学科功能。就考古学 本身而言,近几十年来,不仅其学科性质和研究任务被限制在狭义的史学领域,而且“ 关于文化分期、文化谱系亦即所谓‘文化史’的研究几乎主宰了20世纪前半期的考古学 ,并至今在中国盛行不衰”(注:韩建业:《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北 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0年。)。当然,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文化类型 丰富多样,中国考古学的基础性研究需要持之以恒、深入细致地进行。问题在于,以往 不少考古工作者几乎是将这类基础研究视为自己研究工作的终结,而对考古学在其他领 域可以发挥的作用却很少考虑。上述背景使考古学的学科功能在我国远未得到应有的发 挥。以环境变迁研究为例,田野考古发掘中遇到的大量环境信息如动物骨骼、植物残体 、考古遗址的分布状况与古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环境演变过程等,很少在研究成果中 得到必要的体现。事实上,近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学同自然科学结合的深度,在有些方面 尚不及它的初创时期。那时参与田野考古工作的学者中,不少具有地学、生物学或人类 学的背景,由他们进行的考古发掘,学术视野要开阔许多。
环境演变和人地关系机理这样的命题向来被学术界所重视。司马迁著《史记》,志在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中国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竺可桢先生在 82岁时,分析长期积累起来的资料,完成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 文,发表以后,立即得到国内外科学界的普遍赞扬,也引起了敬爱的周总理的重视和关 怀(注:《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而竺可桢的这一不朽之作,正是以 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中的物候资料为依据的。20世纪60年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所 进行的上海成陆年代研究(注:谭其骧:《关于上海地区的成陆年代》,《文汇报》196 0年11月15日。)和侯仁之所进行的沙漠考古研究(注:侯仁之:《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 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考古》1973年3期。),80年代叶笃正所进行的环境变迁研 究(注:Ye Duzheng,Lin Hai et al.,China Global Change Report No.2:China contr ibution to Global Change Studies.Beijing:Science Press,1995.),也都充分显示 出考古学在环境变迁和人地关系研究领域的重要作用。
考古学在“过去全球变化计划”研究中的优势十分突出。例如,传统的第四纪环境变 迁研究的常规手段是从自然剖面中提取环境信息,通过年代测定,建立环境演变模型。 但由于自然剖面的形成往往经历了漫长的地质历史时期,因而传统地学对自然剖面年代 的认定,大多是以千年、万年为尺度的。目前的精度虽有所提高,但几乎所有测年手段 仍以百年为尺度。然而,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在一般情况下却可以提供较自然剖面精确 的地层年代。尤其是我国许多地区现已初步建立了全新世以来前后密切衔接的文化谱系 以及全新世环境变迁的时空框架,这为考古学介入“过去全球变化计划”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又如,考古学所涉及的文化遗存不仅可以反映当时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 状况,而且同样包含或折射出多方面的环境信息。就一般遗址所包含的文化遗物而言, 如果一个文化层中出土大量的捕捞工具和人类食用后的水生动物遗骸,即可证明当时该 遗址附近存在着较为丰富的地表水资源,也可反映出当时的生物多样性状况。豫鲁苏皖 邻境地区的龙山—夏商时代遗址中鱼鳔、网坠等捕捞工具比比皆是,用蚌壳、鹿角等制 作的生产工具几乎替代了石器的作用,而中全新世期间那一带碟形洼地所形成的湖泊的 确星罗棋布;如果某个遗址的房屋建筑是干栏式的,或者坐落于泥炭层之上,可证明当 时该聚落处在多水的环境中,高邮龙虬庄和驻马店杨庄遗址的环境考古研究结果即其例 证。这两个遗址所发现的大量炭化水稻和水稻植硅石,可印证这一推论。
令人欣慰的是,近十余年来,日益众多的考古学者已经认识到中国考古学所存在的缺 憾,开始致力于完善考古学体系,拓展考古学功能。而与地学和环境科学的结合,尤为 大家重视。在最近短短的几年里,数部由考古学和自然科学工作者合作完成的“环境考 古”发掘报告集相继面世(注:例如,北京大学考古系等编著的《驻马店杨庄——中全 新世淮河上游的文化遗存与环境信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舞阳贾湖》、 南京博物院等单位编著的《龙虬庄——江淮东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都在考古 学与环境变迁研究领域作了积极的探索。),相关研究论文在考古论著中的比例也日益 提高。考古学的多重意义正在被不同学科的人们所认知,并开始在诸多学科领域发挥独 特作用。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局面,既是考古学自我完善的体现,也是科学一体化趋势对 考古学界影响的结果。当然,应该看到,我国的“环境考古”研究起步甚晚,力量微弱 ,在地学、环境科学界和考古学界都缺乏固定的支持渠道。环境考古研究队伍也面临着 拓宽学术视野、提高研究层次的要求。那种将气候的冷暖干湿变化与文化的发展演变机 械对应所得出的研究结论,虽可作为参考的依据,但也面临着“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的危险。
无论中国的学科隔离状态何等严重,科学管理体制如何僵化、滞后,随着学科交叉时 代的到来,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变化和提高(注:《全球变化: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这本权威著作在谈到中国全球变化研究“存在问题”时,首先承认存在“学科交叉与 综合不足”,指出“其综合通常只表现在课题的设计上,而不体现于实际操作过程中” 。“尤其是当研究内容涉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领域时,由于自然科学研究者与社 会科学研究者在过去的研究中很少沟通,所以这种缺陷更为严重。目前,虽然大多数全 球变化研究者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已着手改善,但离全球变化研究的科学 要求差距甚远。”),考古学在“过去全球变化计划”中所具有的其他学科难以替代的 作用必将日益显现出来。在此情况下,考古学家应迅速提高认识,主动将自己的研究工 作与“过去全球变化计划”这一历史性命题结合起来。
收稿日期:2002-03-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