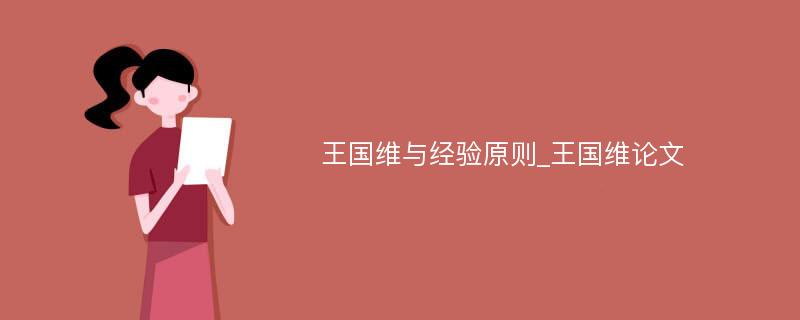
王国维与实证原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原则论文,王国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5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34(2001)05-0096-05
王国维是继严复之后传播西学、研究西学、并力图把中西学融会贯通的学术大师。与严复相比,他能更为深刻地领会实证方法,更为熟练地运用实证方法,并且在哲学、教育、史学、艺术等方面都有创获。他比严复前进一步,试图把实证方法提升到实证原则的高度,并且努力从哲学的角度领会实证原则的理论基础。他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第一个使用“实证”这一哲学术语的人。
一、王国维对实证原则的认同
王国维从未接触过现代西方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斯宾塞等人的著作,他的实证原则的领会不是来自于西方的实证论者,而是来自于实证者的共同祖师康德。
王国维没有写出论述实证原则的专著,他对实证原则的了解主要表现在他对实证科学的态度上和对西方哲学思想的诠释中。他的哲学著作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介绍西方哲学名家;一类是运用西方哲学观点评述、诠释中国哲学,谋求中西哲学的融会贯通。
王国维对实证原则的认同主要表现在《说理》,《释性》,《论命》三篇论文中。他运用康德哲学所体现的实证原则,重新诠释“理”、“性”、“命”这三个在中国哲学中带有本体论意味的哲学范畴,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实证论倾向。
(一)论性
在认识论方面,康德把知识分为两类:一类经验的知识,来自后天的积累;另一类是先验的知识,如空间、时间的形式和悟性的范畴等等,它们并不依赖经验而产生,但经验必须依赖上述的形式和范畴才能形成知识。先验的形式和范畴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后天的经验知识是因为经过先验的形式和范畴的加工整理之后,才获得必然性和普遍性。王国维接受了康德的这种说法,并且根据康德的这一观点指出,“因果之相嬗,质力之不灭,无论何人,未有能反对之者。”[1]他认为人们关于经验世界(现象界)的知识之所以具有必然性,是因为这种知识一方面得到经验事实的证实,另一方面以先验的因果范畴作为依据。但是,人们关于意义世界(本体界)的知识却不可能具有必然性,因为这种知识既得不到经验的证实,也没有先验的范畴作为依据。
从康德的认识论出发,王国维考察了中国哲学家关于“性”的种种有代表性的说法。他指出,中国哲学家在论及人性的时候比较武断,“不但得容反对之说而已,且一人之说中,亦不得不自相矛盾”。孟子立性善说、荀子立性恶说,若性“如数及空间之性质然,吾人之知之也既确,而其言之也无不同。”他们的看法虽然相互对立,但都犯了相同的错误,那就是用认识经验世界的办法去认识意义世界的问题,没有分清二者之间的界限。依据康德的观点,王国维分析说:“先天中所能知者,知识之形式,而不及于知识之材质,而性固一知识之材质也”,而“吾人经验上所知之性,其受遗传与外部之影响者不少,则其非性之本来面目。”[1]先验的范畴只适用于现象界,关于人性一般的问题属于本体界,因而先验范畴对于这一问题不适用;人们在经验层面对于人性的了解属于后天的,并不能代替对于人性一般的了解。所以,关于人性一般的讨论是没有办法得到大家都能接受的结论的。在这里,王国维依据实证原则,宣布中国哲学史上关于“性”的种种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王国维分析说,既然关于人性的认识不属于经验认识的范围之内,那么关于“性”的讨论就不能不驰于空想、揣测。在宋代以前,哲学家们不自觉地以经验认识的方式去推断“性之本然”,不懂得经验意义上的性,并非是“性之本然”,于是便反复于善恶之间,争论不休。告子主张无善无恶说,孟子主张性善论,荀子主张性恶论,董仲舒主张性二元论,杨雄提出善恶混说,这些都是在经验层面上就性论性,没有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考察“性之本然”。宋代以后,诸多哲学家开始从本体论的层面讨论“性之本然”问题,但也没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周敦颐的太极说,张载的气论,程朱的理学,都是在经验的层面说善恶,而无法在本体的层面把善恶统一起来,无法解决形上的“至善”同形下的善恶怎样沟通的问题。这样,他们在经验层面上的善恶之论与在本体层面上的人性至善说相去甚远。可见,从本体论的角度探讨“性之本然”,也是徒劳无益的。这种分析反映出,王国维实际上主张依据实证原则取消关于“性之本然”的问题,因为在本体层面上讨论,已是无意义和不可能的;而在经验层面上更无法弄清楚“性之本然”。
(二)释理
在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理有种种说法,王国维对这些说法的正确性表示怀疑,要求依据实证原则重新审视“理”的确切含义。关于“理”,在王国维看来,应当有两种意义:一是“理由”,二是“理性”。就广义而言,“理”就是理由。万物存在必有其理由,知识存在必有其前提。理“‘就客观而言,为世界普遍之法则;就主观上言之,乃吾人之知力普遍之形式也’。世界各事物,无不入此形式”。“天下之物绝无无理由而存在者,其存在也必有所以存在之故,此即物之充足理由也”。就狭义而言,“理”就是理性,即人心的认识能力。“理性者,吾人知先天的原理的能力是也”,“而汗德以后之哲学家,遂以理性为吾人超感觉之能力,而能直知本体之世界及其关系者也。”[2]从理由的意义上“理”是一个客体性范畴;从理性的意义上“理”是一个主体性范畴。按照康德哲学,前者关涉本体界,因而是不可知的;后者关涉概念的世界,因而是有限制的。
由于传统的哲学家没有分清楚“理”的两种含义,有时把“理”当作客观的假定,认为理可以独立存在。在西方哲学与中国理学中都存在着这样的看法。在中国,理学家往往强调“理”的理由之义,而忽视了它的理性之义,把它视为带有本体论意义的“太极”。在西方,一些哲学家虽然注意到理的两层含义,却从中转而生出“宇宙大理”之义。实际上,“太极”、“宇宙大理”所表示的理,只是一个幻影而已。
王国维的结论是:“以理由而言,为吾人知识之普遍之形式;以理性而言,则为吾人构造概念及定概念间之关系之作用,而知力之一种也。故理之为物,但有主观的意义而无客观的意义。易言以明之,即但有心理学上之意义而无形而上学上之意义也,然以理性之作用为吾人知力作用中之最高者,又为动物之所无,而人之所独有”。理“不存于直观之世界,而惟寄生于广漠暗昧之概念中。易言以明之,不过一幻影而已矣。”[2]从他的这种看法中反映出,他在本体论方面认同“本体不可知”的观点,在认识论方面认同理性不可脱离感觉经验的观点,而这两点正是实证论者信奉的基本原则。
(三)原命
关于“命”,他的理解也与传统的哲学家不同。他认为,“命”有两种含义:一是《论语》中所说的“死生有命”的“命”,这是从人生论的角度上讲的,乃是宿命论意义上的“命运”之义;二是《中庸》中所说的“天命之谓性”的“命”,这是从存在论的角度上讲的,乃是决定论意义上的“必然”之义。他说:“命之有二义,其来已古,西洋哲学上亦有此二问题,其言祸、福、寿、夭之有命者谓之‘定命论’;其言善恶贤不肖之有命而一切动作皆由前定者谓之‘定业论’。‘定命论’也就是宿命论,‘定业论’就是决定论。而‘定业论’与意志自由论之争尤为西洋哲学上重大之事实,延至今日而尚未得最终之解决。”[3]
在王国维看来,在中国哲学史上关于“命”的讨论似乎没有全面把握住这一范畴的内涵,“通观我国哲学上,实无一人持定业论,故倡言意志自由论者,亦不数数觏也。”除了墨子外,尽管大多数哲学家都从命运的意义上谈论命,可是在他们眼里,“命”没有“必然规定”的意思。王国维指出,由于中国哲学家所讲的命缺少“必然规定”的意义,没有像西方哲学那样充分地讨论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在中国哲学史上,没有人主张决定论,大都有意无意地倡导意志自由论。王国维与中国传统哲学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着重强调“命”的“必然规定”之义,并且深入探讨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
由于接受了西方哲学的影响,王国维深深感到自由与必然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相对复杂的哲学问题。按照决定论的观点,人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任何负责,因为行为为一个动机所决定,而这个动机又为某种不可抗拒的原因所决定。按照意志自由论的观点,支配行为的动机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在两个动机之间,人有选择的自由,所以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由此可见,决定论与意志自由论是两种完全相反的价值观:若“从定业论之说,则吾人对自己之行为,无丝毫之责任,善人不足敬,而恶人有辞矣”;而“从意志自由之说,则最普遍最必然之因果律,为之破灭,此又爱真理者之所不接受也。”康德试图化解决定论与自由意志论之间的对立。康德给自由一个消极的定义:“意志之离感性的冲动而独立”;又给自由一个积极的定义:“纯粹理性之能现于实践也”。但康德认为自由仍然同因果关系有关,只是意志自由的因果与自然界的因果不同而已。王国维不同意康德的说法,理由是自由有了原因,就不成其为自由了。他认为康德为自由所下定义“大不然者也。吾人所以从理性之命令而离身体上之冲动而独立者,必有种种之原因。此原因不存于现在,必存于过去;不存于个人之精神,必存于民族之精神。而此得表面的自由,不过不可见之原因,战胜可见之原因耳,其为原因所决定,仍与自然界之事变无异也。”[3]
在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上,王国维离开了康德而转向了叔本华。他表示赞同叔本华的观点,认为意志进入经验界后,就要受动机的摆布。意志本体究竟有无自由,我们无法得知,而在经验世界里,自由是一个空洞的概念,无实际内容。意志在经验世界里表现为动机;人求生的欲望是生命的基础,它支配意志,所以意志是不自由的。但人的行为若是必然,责任由何而来呢?因为人为一些自己不觉之原因而决定,当现在的行为不适于人生的目的时,人就会有责任及悔恨之情,这种感情会成为日后行为的原因,所以,对于以后的行为,人还是应该有责任感的,不能用意志自由论来辩解。尽管王国维关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的看法与康德有区别,但他把自由同本体界联系在一起,把必然同现象界联系在一起,仍然沿袭了康德的基本思路,仍然体现了实证原则。
《论性》、《释理》、《原命》三篇论文写于1904-1906年间,是王国维运用西方哲学理论诠释剖析中国哲学范畴的代表作。关于“性”,他认为已超越人的知识范围,无论从经验或本体两个层面都无法把握;关于“理”,他认为理作为理由或理性,并不在直观的世界中,不过是幻影而已;关于“命”,他认为在经验世界中自由是一空虚的概念,在本体世界中其性质不得而知。王国维强调“性”、“理”、“命”都有非感性、非经验的一面,以此对实证原则表示了认同的态度。
二、在“可信”与“可爱”之间
尽管王国维曾对实证原则表示认同,但他并没有成为一个实证论者。至于他为什么没有成为实证论者,他自己作了这样的说明:“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可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4]他之所以陷入矛盾的境地,同他接受康德的影响有关。对于王国维来说,人们以现象界为认识对象,可以得到确切的实证科学知识,所以他觉得“可信”,然而这种知识只是陈述经验事实,并不能满足人们对意义的追求,所以他又觉得“不可爱”。本体界可以满足人们对于意义的追求,所以他觉得“可爱”,可是人们又不能借助纯粹理性证明本体界的实在性,所以他又觉得“不可信”。他找不到走出矛盾境地的路径,只好徘徊于“可信”与“可爱”之间而无所适从。
在王国维生活的时代,实证科学已经传入中国,并且威信越来越高。王国维本人也有一段痴迷实证科学的经历。然而王国维又是一个人文素质比较高的学者,他没有被实证科学的具体知识淹没,而是去追问实证科学之所以“为最确实之知识”的理由,于是走上了哲学研究之路。在认识论方面,他受康德的影响较大,而在本体论方面受叔本华影响较大。康德哲学使他觉得实证科学知识确实“可信”,但不能满足他对于意义的追问;叔本华向他展示了“可爱”的意义世界,却不能满足他对理性的喜好。他徘徊于“可爱”与“可信”之间,其实正是徘徊于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之间,他深切地感受到了现代西方哲学中两大哲学思潮的矛盾和对立。在“可爱”与“可信”之间挣扎了一段时间后,王国维放弃了哲学,而把研究的目光投向文学和史学。
虽然王国维放弃了哲学研究,但他没有因此而改变对实证原则的认同。在他的治学生涯中,重视事实、重视证据是他一向遵循的基本原则。他十分注重事实,强调“事物必求其真、道理必求其是”[5]。辛亥革命后,王国维专门从事文字学、音韵学、考古学、金石学等方面的研究,在整理、考释、研究的实践中,他一方面根据文字,一方面根据地下资料进行佐证,提出在史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两重证据法”。王国维治学的这种独到之处,正是他努力贯彻实证原则的具体体现。
虽然王国维没有成为实证论者,但他在中国现代实证哲学思潮发展史上仍然占有重要位置。他继严复大力介绍实证方法之后,对实证方法作了认真的哲学思考,将其提升到实证原则的高度。如果说严复拉开中国现代实证哲学思潮的第一道序幕,那么,可以说王国维拉开了第二道序幕。
收稿日期:2001-0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