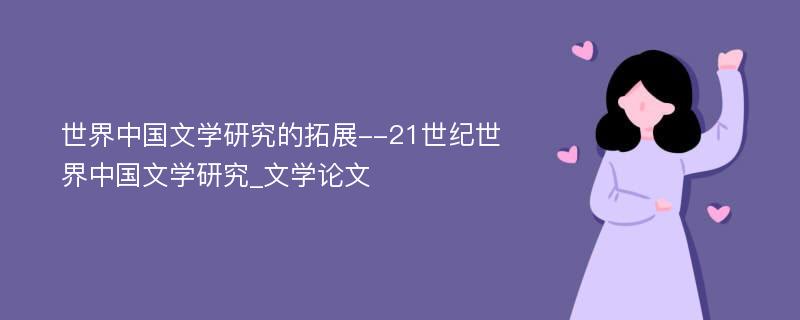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拓展——走向21世纪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论文,文学论文,走向论文,世纪论文,华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大陆以外的华文文学研究,最先称“台港文学研究”,附属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之下。还在1979年,北京的《当代》杂志率先发表了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当时把白先勇当作旅美作家,但也有人视他为台湾作家,或两者身份兼而有之。1982年在羊城召开的首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研讨会,讨论的重点均是台湾文学,从收入论文的17篇文章来看,真正论述香港文学的只有《论刘以鬯在小说艺术上的探求与创新》一篇。而后来的香港文学研究,仍扮演着陪衬台湾文学的角色。
可过了一年之后,随着中国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研究者们越来越感到“台港文学”乃至“台港澳文学”难于适应形势的需要,因而“海外华文文学”的概念开始流行起来。1984年汕头大学“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的筹建及次年《华文文学》试创号的问世,便是一个明显的标志。关于“华文文学”的概念,秦牧在《代发刊词》中指出:“华文文学”是一个比中国文学内涵要丰富得多的概念。即是说“中国文学”只限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华文文学,而“华文文学”除包括中国的华文文学外,还涵盖中国以外的华文文学。秦牧还将华文文学与英语文学、西班牙文学并列为一种语种文学。同期的《编者的话》,在界定“华文文学”的概念时说:一、凡是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而创作的作品,都可称为华文文学。二、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文学包括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文学,以及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台湾和香港文学。而华文文学除了中国文学之外还包括海外华文文学。华文文学与华人文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华人用华文以外的其他文字创作的作品,不能称为华文文学,但非华裔外国人用华文创作的作品,可称为华文文学。
秦牧虽然是作家,但他由于不是一般的中国作家,而是一位归侨作家,因而他对“华文文学”有感同身受的体会,经常思考这方面的理论问题。到了1986年2月,他在北京出版的1986年第1期《四海》上,正式打出“世界华文文学”的旗号。在题为《打开世界华文文学之窗》一文中,他指出:以中国为中坚,华文文学流行范围及于世界,我们应该打开窗口,关心世界华文文学的动向,“在世界范围内,加强华文文学的交流”。但对“世界华文文学”这个概念,学术界并没有马上接受。1991年在广东中山市召开的第五届研讨会上,仍沿用“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讨会”的名称,所不同的比上一届多了一个“澳”字。一直到1993年在庐山召开的第六届会议上,才正式使用“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的名称。即使这样,对这个名称仍有争议,这可从《四海》1994年第1期组织的“热门话题”中的四位作者对“世界华文文学”概念的理解不一致可看出。1994年在昆明召开的第七届会议上,在小组讨论中对会议名称仍有不同的意见,仍有人主张沿用“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旧名。理由是无论是第六届还是第七届会议,都没有把“世界华文文学”的主体中国大陆文学列入研讨范围。
但在台湾、香港,由于没有“大中原”心态的束缚,他们早就使用了“世界华文文学”的名称,先是在1991年7月在香港召开了“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后是1992年11月在台北成立了“世界华文作家协会”——尽管这个“协会”代表的广泛性严重不足,但他们将“新华文学、马华文学、菲华文学、泰华文学,甚至亚华文学、欧华文学、美华文学”与作为母体的中国文学沟通起来的做法,不能不认为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到“台港澳文学”,到“海外华文文学”,直到“世界华文文学”名称的使用,标志着从课题性的命名到一门学科的蓝图初绘。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首先是中国大陆及台港澳文学,可第六至第八届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没有一篇论文研讨中国大陆文学,这是跛脚的表现。这一偏颇到了1997年北京召开的第九届会议,已有所改变。当然,为了同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加以区别,“世界华文文学”在研究中国文学时,不以大陆为重点,而以台港澳文学为主体应是顺理成章的事。这门学科另一个研究对象是中国以外的华文文学。但海外华文文学与“台港澳文学”也有交叉的情况。像旅居北美的聂华苓、陈若曦、白先勇、欧阳子、於梨华以及北欧的赵淑侠,他们作品的选材以及蕴含的中国文化内涵,使人们容易把他们的作品看作是台湾文学。至于新加坡的黄孟文、泰国的司马攻、马来西亚的云里风,由于他们落地生根认同了当地文化传统,作品还有浓郁的南洋色彩,因而他们用中文创作的作品,已不属中国文学或侨民文学,而是地地道道的东南亚华文文学。
必须再次强调“世界华文文学”与“世界华人文学”的区别。前者是从“语文”、“语种”方面着眼的。后者是从“种族”、“华裔”方向规范的,是专指中国人及其后裔用中文或其他国家的文字创作的文学。有人认为:“广义的华文文学,除了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的华裔作家与非华裔作家外,还包括用外文作为表达工具的华人作家与汉学家。”又说:“就广义的华文文学来说,印尼华人的马来语文学是十分重要的特殊现象。”(注:刘以鬯.世界华文文学应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香港文学,1991(80).)这里把用其他语种创作的华人作家的作品包括进“华文文学”,为的是扩大“华文文学”研究范围。但作为一个科学定义,则欠严谨。像印尼华人创作的马来语文学,既然是用马来语,当然是马来语文学而非华文文学。如果要与“华”字沾边,那“华人文学”的概念正好适应这种特殊情况。不过“华文文学”与“华人文学”确有交叉之处。“华人文学”包括“华文文学”,但“华文文学”决不等同于“华人文学”。前者主要从文字使用上来划分,后者主要从作者的民族上区分。
“世界华文文学”亦不同于“世界文学”。前者是属概念,后者是种概念。即前者范围小于后者。后者是指不用华文写作的文学,作者多为非华裔的外国人。前者的文学语言一定是华文,作者亦多为华人。
“世界华文文学”当然更不同于“海外华文文学”。前者着眼于世界,后者则从中国本位着眼,容易引起中国以外华文文学作家的反感。与此相关的“世界华文文学”有无中心的问题。有人认为“中心”是客观存在,中国文学就是“中心”。《新加坡作家报》有人撰文表示不同意见,认为各国华文文学是兄弟关系,而不是母体与子媳的关系。如果承认“中心论”,就会出现狂妄自大与妄自菲薄两个极端。也有人认为,如果有“中心”,也是多中心,而不能只有一个中心。关于这个争论,其实意义不大。对中国作家来说,不应以主流自居歧视别的国家的华文作家。别的国家的华文作家也不应以本土性为名完全脱离中华文学这个“根”。各国华文文学应互相取长补短,共同繁荣。
关于“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命名的科学性及这门学科建立的必要性,已先后有饶芃子与费勇、许翼心与陈实、赖伯疆等人论述过。这些学者认为:“世界华文文学”既具有世界性,又有本土性;既有延续性,又有交融性。它是一门考察语种的学科,是一门探讨民族文学、研究文学关系的学科。具体来说,是研究世界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关系、华文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各国各地区华文文学相互关系的学科。在研究前一个问题时,着重研究中国文学如何在世界各地传播和演变,研究世界各地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共同性与差异性,研究中国文学对世界各地华文文学的影响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交融渗透。(注:许翼心,陈实.作为一门新学科的世界华文文学.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1996(2).)
世界华文文学的命名——尤其是“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包含着丰富的内容,至少有四种影像:“一是海外华人史,二是海外华文文学,三是居住国的历史,四是中国本土的历史;这四种历史,以‘海外华文文学’为纽结产生关系,对于海外华文文学本身有重大的制约作用,而海外华文文学又从文学的观点补充一般通史的见解。由这样的具体例证,我们又可引伸出文学与历史之间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的提问,从而达臻某种文学理论的形成。”(注:饶芃子,费勇.论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意义.文学评论,1996(1).)
作为一门学科,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方法应多种多样:既可用社会学的方法,也可用历史学的方法;既可以是民族的,也可以是地域的;既可以是文学的,也可以从语言学角度入手。目前较多人用文化视角,用这种视角去研究华文文学的“文化身份”,去探讨华文文学的文化旨归;或去研究华文文学作品中的“他者”形象,把握华族文化与别族文化在文学相遇的反差。有的则用符号学或结构主义的方法,去阐述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一些问题。
为了拓展学术视野,饶芃子一再强调用比较的方法去研究世界华文文学:比如在华文文学整体的观照下,将中国本土文学同其他国家的华文文学相比较,在比较中探索其发展的脉胳以及不同民族文化相遇时碰撞和认同的过程及其规律;也可能将本土以外的其他国家、地区的华文文学相比较,研究不同国家、地区的华文文学特殊的存在方式、美学模式、文学风格以及作为语言艺术的衍变史;还可以将同一国家不同群体的华文文学作比较,探讨它们在居住国主流文化碰撞所采取的不同态度以及作出怎样的反应与选择。(注:饶芃子,费勇.本土以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6.)不过,这里要说明的是,世界华文文学虽然重视文学的关系和比较,但它本身不是“比较文学”,“世界华文文学”是只“研究同一民族语言、同一文化传统的文学之间的关系和影响。比较,只是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的方法。”(注:许翼心,陈实.作为一门新学科的世界华文文学.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1996(2).)
从80年代以来出版的研究成果看,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开始多为作家作品介绍和赏析,后发展到作家论、作家评传;开始是国别文论,后出现整体性的海外华文文学概观、海外华文文学史或文体史,另还有辞典和研讨会论文集。
在这些著作中,最值得重视的是陈贤茂等人撰写的四卷本《海外华文文学史》(注:鹭江出版社1999年版.)。该书有下列特色:
一是理清了华文文学的内涵。研究华文文学,首先碰到基本概念的理解。对此,该书开宗明义地认为:“凡是用华文(即汉语,海外华人多称华文)作为表达工具而创作的作品,都可称为华文文学。”这就划清了“华人文学”与“华文文学”的界限,不至于把海外华人用华文以外的文字(如英文、马来文)创作的作品,混同于华文文学。如果像有些论者那样将“华文文学”的概念搞得过于宽泛,显然不利于华文文学特色的形成及其自身的发展。
二是突出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特点。海外华文文学到底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支流(或曰“华侨文学”),还是具有海外特色的独特文艺品种?对此,著者们作了具体分析。他们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多数海外游子是以华侨身份漂流异国的。他们与祖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海外华人作家也一直受着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可视海外华文文学为中国文学的支流。战后,“政治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绝大多数华侨已加入了侨居国的国籍。这种状况反映到文学上,就是作品本土色彩的增强,并且逐步脱离了”中国文学的轨道,“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这种分析显得十分辩证,特别是当今世界华文文学运动在不断推进的今天,强调海外华文文学的本土色彩,十分有利于确立海外华文文学的独特性和主体性的地位。如果不强调这一点,让海外华文文学像过去那样亦步亦趋中国大陆或台港作家的风格,即跟在中国作家后面走,而不在本国的社会和生活的土壤中扎根,那海外华文文学就注定会死亡。
三是覆盖面大,几乎凡有华文文学的国家都有涉及。其中“新马华文学”占了全书四分之一多的篇幅。这一方面是编著者对这一地区文学资料掌握较多,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新马华文学比别的地区远为发达兴旺。此外,该书还对文莱、越南、柬埔寨、缅甸、毛里求斯、厄瓜多尔等地华文文学作了资料整理和作品分析,极大地扩充了华文文学研究领域。
四是对海外华文文学发展过程的叙述,建立在丰厚的史料基础上。搞当代文学研究的人,常常鄙视史料的收集和整理,认为这种“笨”功夫不能显示自己的学术水平。这是一种偏见。学术研究如果不建立在过硬的史料基础上,这种研究就难免空对空。“文学史”的作者们,十分明白自己所从事的是海外华文文学史的编纂工作。他们坚持论从史出的原则。无论是哪一卷,均注意史料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还从中引出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动辩证关系,从而提炼出自己的史识。
《海外华文文学史》对著者们原先写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注:鹭江出版社1999年版.)来说,不仅是量的扩大——从原来评论的66位作家增加到260位,从原来的一卷本扩充为总计200万字的四卷本,而且是质的提高。这集中表现在由吴奕锜执笔写的《新移民文学》一章中。这触及到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新问题。作者论述时,注意了“新移民文学”的界定,尤其是“新移民文学”与五、六十年代白先勇等人为代表的“留学生文学”的创作主体与作品风格的不同,指出“新移民文学”所叙述的更多的是倾向于对生存的艰难与对不同文化价值观念的碰撞所产生的震撼,这均十分符合所评对象的实际。《新移民文学》一章的描写,使《海外华文文学史》的研究材料显得新鲜、灵动,并扩展了读者对海外华文文学新走向的认识。
为海外华文文学写史,牵涉面极广,要驾驭这样一个宠大的写作素材,实属不易,该书有些章节也可见到著者的力不从心之外。至少有些地方写得不够概括,还有个别重要作家的遗漏(如澳洲华文作家协会主席黄雍廉),把刚移民不久的陈少华称作厄瓜多尔华文作家也欠典型——至少书中论述的大部分均是他在香港时期的作品。但这些弱点实际上反映了当前这门学科建设所存在的不足。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相信下一个世纪会有更完善、更理想的海外华文文学史著作的出现。但就目前而论,陈贤茂等人著的《海外华文文学史》,确是本世纪总结性的著作。它的长处和短处,均反映了海外华文文学现阶段的研究水平。
黄万华独立完成的《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注:山东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则是第一本海外国别华文文学文体史。它以“现实主义兴盛和‘误读’(1919—1960)”、“现代小说的自觉和探寻(1960—1980)”、“双重传统和典律构建的艰难实践(1980—1998)”三篇论述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华文小说产生、发展的近百年历史进程,并由此呈现出20世纪华文文学,在南洋落地生根的坎坷历程。此书在分期依据、观照角度上均有自己的特色。如从生存困境角度考察海外华文文学,不仅切合新马华文文学的实际,而且也能在20世纪华文文学的整体格局中更明了马华小说生存形态的来龙去脉。
要将海外华文文学建设成一门学科,必须做好学科“底部”的理论奠基工作。饶芃子、费勇《本土以外:论边缘的现代汉语文学》(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对海外华文文学所做的学理式探究,对回答海外华文文学何以能成为一门学科以及怎样才能加快学科的建设,无疑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本土以外:论边缘的现代汉语文学》一个特点是非常注意在求“同”中明“异”。求“同”,是为了探索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规律;明“异”,则有助于丰富和整合世界华文文学的整体形象。无论是求“同”还是明“异”,《本土以外:论边缘的现代汉语文学》一书均借助于比较方法的运用。他们在华文文学整体的观照下,将中国本土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相比较,在比较中探索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发展脉胳:或像《欧洲华文文学简论》那样,将同一地区的不同国家的华文文学加以比较,在比较中看出不同国家华文文学特殊存在的方式和美学模式;或像《澳门当代汉语诗歌的本土性与当代性》那样,将同一地区的不同群体的华文诗歌进行比较,探讨他们在和主流文化碰撞时所采取的不同态度及其作出不同的反应和选择。这样做,不只是求“同”和明“异”,而是使读者对研究对象的存在方式的认识更加全面和深刻。
把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相结合,是饶芃子和费勇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又一特色。他们著文不就作品论作品,而是将海外华文文学放入文化的传播与影响中去研究、考察,如《中泰文化融合与泰华文学个性》,用比较的方法围绕中泰文化交流这种现象,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相互比较和阐释,使其研究更具开放性和丰富性。《菲华女性写作的文化精神》,则注意到性别与文化的结合,即用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去考察菲华女作家作品,探讨其文化身份的共同性、差异性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上述论著,为提高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理论水准,改变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存在着的偏颇,逐渐成为一门学科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十多年来,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经历了“命名”的讨论、对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研究对象的界定、世界华文文学历史状况和区域性特色的探索、海外华文作家“文化身份”的确认,乃至如何编撰“20世纪华文文学史”的研讨,进而转入对世界华文文学学科草创历史的描述,均取得了众多的成果,但还不能说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正式建立。目前的研究还多停留在资料的整理和发展线索的初步勾划上。表象的研究多,深层次的研究少;作家作品评论多,探讨发展规律的论文少;概观的描述多,经典性的研究著作则还未出现。要从目前的课题性研究而形成一门学术界广泛认可的学科,即实现从“无”到“有”,从“潜”到“显”的飞跃,尤其从这单一性学科繁衍成密集的学科群落,还有一段较大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