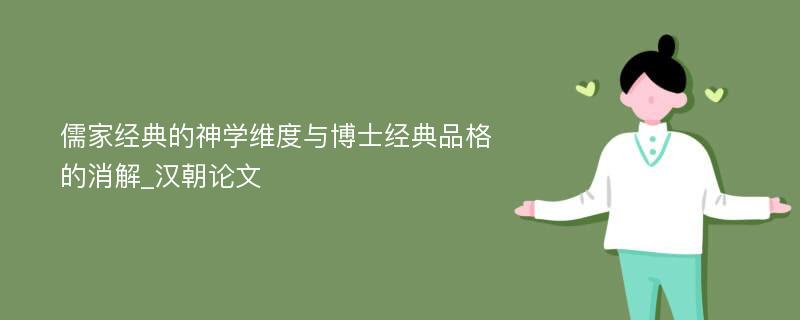
经学的神学向度与博士经典性格的消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学论文,神学论文,性格论文,博士论文,经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09)01-0113-06
五经博士制度建立以后,汉代的今文经学雍容自信地走上汉代政治舞台,以区别于诸子杂说的完整的政治价值体系,博得了汉代统治者的青睐,将其作为帝国的指导思想,并进行了由上而下的普及化教育。当经学成为进入庙堂的手段,儒家士人对于经典阐释展现了炽烈的情怀,“一经说至百余万言”不乏其人。《汉书·艺文志》曰:“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1](p.1723)经学成绩的取得直接关系到政治利益的获得,儒家经学客观而宏正的思想体系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就某一经的自我润色逐渐以繁复相高,后来者毫不相让又示其能,复现繁难,最终形成煌煌巨说,白首才能修习明晓。儒学的精神意旨固然已面目全非,依赖修习今文经学谋求政治利益使生命和智慧的成本不断增加,急功近利之徒在探索中发现了谶纬的政治价值。“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图谶兴,遂盛行于世。”[2](p.32)王莽以谶纬兴,又以谶纬亡;汉光武帝“颁布图谶于天下”,汉章帝白虎观会议将谶纬入于“国宪”,东汉政治被涂抹上神秘主义色彩,汉代经学在统治者意志的指引下,开始了新的转化——经学神学化,汉代经学博士们开始了新的精神炼狱。
谶纬即谶书和纬书的合称。东汉张衡云:“立言于前,有征于后,故智者贵焉,谓之谶书。”[3](p.1912)《四库全书总目》曰:“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4](p.47)关于谶纬的合流,《四库全书总目》也给出了合理的解释:“盖秦汉以来,去圣日远,儒者推阐论说,各自成书,与经原不相比附。如伏生《尚书大传》、董仲舒《春秋》阴阳,核其文体,即是纬书。特以显有主名,故不能托诸孔子。其他私相撰述,渐杂以术数之言,既不知作者为谁,因附会以神其说,迨弥传弥失,又益以妖妄之辞,遂与谶合而为一。”[4](p.47)任继愈先生告诉我们:“谶纬是封建神学和庸俗经学的混合物”[5](p.104),也是汉代政治现实的在思想领域的体现。西汉末期,汉代经学的发展已经无法逾越谶纬的藩篱,在政治的主导下,儒家的学术精英们欣然拥抱了发自民族内心的神秘,这种带有极端目的性的神秘思想弥散开来,笼罩在整个帝国的上空,约束和规范着一个民族的心灵。
一、“受命之符”:倾听神明的政治召唤
谶纬的兴起和哀、平之际混乱、动荡的社会现实息息相关,然而,统治者根据个人好恶的价值取舍也决定了谶纬的进退方向。汉昭帝时,有大石自立、僵柳复起,眭弘上书,言有从匹夫为天子,宜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霍光恶此论,诛杀眭弘。汉宣帝起于民间,征召眭弘之子为郎。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可伪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1](p.3192)。刘向奏其“假鬼神罔上惑众”,甘忠可入狱而病亡。以此观之,谶纬具有很高的政治依存度,尽管正直经学士大夫予以全力阻击,谶纬已经投入王莽热情的怀抱中。在末世经学怂恿下,王莽操起了谶纬的政治武器,与经学士人共同谋划了权力禅让的滑稽闹剧。
汉哀帝崩,元后拜王莽为大司马,拥立9岁的中山王即位。“太后临朝称制,委政于王莽”,不久。册封王莽为安汉公。此时的王莽邀名买誉,拔擢附顺,诛灭异己,并没有窃国的政治意图。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甚至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汉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太皇太后王政君“授王莽宰衡太傅大司马印”;元始五年(公元5年),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列侯902人,奏请太皇太后赐予王莽“九命之锡”,王莽小心翼翼的权力意识得到了彻底解放,他终于看到了占据帝王宝座依稀微茫的曙光。当朝公卿士大夫虽已洞悉王莽的政治野心,折服于王莽身上所体现的优秀政治家气质,以及暗怀对于汉代君主的失望,汉末的经学士人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下集体失语,一任王莽为所欲为。而散处于民间不甘寂寞的经学士人或方士,狡黠地观察着庙堂上发生的一切,彻晓了王莽的政治命意,他们无视于道德的约束,利欲熏心地制造符命,向王莽邀功请赏,汉代政治刮起了阴冷的谶纬之风。
元始五年(公元5年)十二月,汉平帝崩,孺子婴即位。“前辉光谢嚣奏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圆下方,有丹书著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1](pp.4078-4079)元后同意王莽“摄行皇帝之事”,次年改元居摄。然而,王莽逐渐不再满足于周公的政治美誉,摆脱汉代政治的假面,实现真实的权力梦想,促使王莽制造了一系列上应神迹的异闻符命。
王莽居摄三年(公元8年)七月,齐郡临淄县昌兴亭长辛当一暮数梦,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长曰:‘摄皇帝当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当有新井。”[1](p.4093)辛当早晨起来,赫然看到了深有百尺的一口新井。居摄三年(公元8年)十一月,先前发现的巴郡石牛、雍石文运到了未央宫之前,执殿大臣与王莽的从弟太保安阳侯王舜等前来观看,这时“天风起,尘冥,风止,得铜符帛图于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献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1](pp.4093-4094)大臣们忆起了甘忠可及其弟子夏贺良的赤精子之谶,恍然大悟,谶语上承天命的应符之人无疑指向了王莽。王莽谨慎小心地处理了上天的暗示,只是变“摄皇帝”为“假皇帝”,他等待着更大的机会,期待着更有政治说服力符命的出现。
在长安求学的梓潼人哀章,素来无行,好大喜功。“见莽居摄,即作铜匮,为两检,署其一曰:‘天帝行玺金匮图’,其一署曰:‘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某者,高皇帝名也。书言王莽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图书皆书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兴、王盛,章因自窜姓名,凡为十一人,皆署官爵,为辅佐。”[1](p.4095)居摄三年(公元8年)十一月,哀章闻知齐井、石牛等事宜,知道时机来临。当晚黄昏,哀章“衣黄衣,持匮至高庙,以付仆射”,闻之此事的王莽,急至高皇帝庙,拜受金匮神嬗。于是,王莽“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1](p.4095)
王莽执孺子之手,泣涕连连,感叹上天安排,将孺子送下金殿。“百僚陪位,莫不感动。”今天看来,非常滑稽的一场政治游戏竟然演绎得如此庄严而神圣。其后,王莽按照金匮的指示拜将封侯,擢升公卿凡数百人。其中,一介布衣哀章任为国将,封美新公。西汉君主在符命面前结束了自己二百多年的统治地位,滋润了帝国的精神世界、控制着帝国政治走向的汉代儒生博士们,鲜有人提出正义的告诫,而是随着王莽的政治节拍起舞,“当王莽居摄磷弑之际,天下之士,莫不竞褒称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3](p.956)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王莽的权力欲望,也触动了自身道德和正义底线,为中兴的统治者所诟病。始建国元年秋,王莽遣五威将王奇等12人班符命42篇于天下,使百姓人人知符,从而理解新朝代替刘汉是天命所归,增加社会的稳定。《汉书·王莽传》曰:
是时,争为符命封侯,其不为者相戏曰:“独无天帝除书乎?”司命陈崇白莽曰:“此开奸臣作福之路而乱天命,宜绝其原。”莽亦厌之,遂使尚书大夫赵并验治,非五威将率所班,皆下狱。[1](p.4122)
王莽得益于符命,也受制于符命。甄丰、刘歆、王舜本为王莽腹心之臣,歌功颂德,极力表彰王莽的不世功勋,内心却不是让王莽居摄、称假皇帝,然而,王莽羽翼丰满,非甄丰、刘歆、王舜等人所能控制,只好一任事态发展,又心中充满恐惧:畏惧刘汉宗室及天下豪杰。甄丰之子京兆大尹甄寻作符命,言“新室当分陕,立二伯,以丰为右伯,太傅平晏为左伯,如周召故事”。王莽明知其诈,还是拜甄丰为右伯。甄寻尚未履新,再作符命,言“故汉氏平帝后黄皇室主为寻之妻”。王莽以欺诈立国,心疑大臣怨谤,欲立威以惧下,收捕甄寻。甄寻亡命,甄丰自杀,坐及刘歆之子棻、泳以及刘歆的门人等公卿列侯数百人。
成为天帝诏命的凭证,谶纬是神圣的、凛然不可欺的。王莽正是利用了人们的这种期待心理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谶纬的神秘性一旦被臣子所利用,王莽不惜戳破自己的政治神话,清除面临的政治威胁,防止苦心经营的良好政治信誉破产,毅然断臂自救,诛杀了自己的爪牙,维护自身的政治权威。
西汉末期,谶纬的政治价值被普遍接受,光武帝刘秀清醒地意识到了谶纬的重要性,应和李通“刘氏复起,李氏为辅”的图谶,毅然在宛县起兵,逐鹿中原。群臣劝进为帝,刘秀迟疑未决,在长安时一起受经的同学强华从关中带来了《赤伏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3](p.21)刘秀大喜过望,以为是受命之符,拜祭天帝,正式登上皇帝位。远在河西的窦融得知汉光武帝即位,与众将议云:
智者皆曰:“汉承尧运,历数延长。今皇帝姓号见于图书,自前世博物道术之士谷子云、夏贺良等,建明汉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故刘子骏改易名字,冀应其占。及莽末,道士西门君惠言刘秀当为天子,遂谋立于骏。事觉被杀,出谓百姓观者曰:‘刘秀真汝主也。’皆近事暴著,智者所共见也。除言天命,且以人事论之:今称帝者数人,而洛阳土地最广,甲兵最强,号令最明。观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当也。”[3](p.798)
于是,遵建武年号,以示臣服。显然,谶纬发挥了巨大的政治威慑力,汉光武帝的良苦用心终于奏效,不费兵矢之力,而获天人之功。
其时,对谶纬寄予厚望者,尚有王莽末自称蜀王的公孙述。公孙述曾经夜梦有人语之曰:“八厶子系,十二为期”[3](p.535),又有龙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公孙述认为,这些都是符瑞,建武元年(公元25年)四月,遂自立为天子。公孙述对符命也是深信不疑的,他以为:
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尽也,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录运法》曰:“废昌帝,立公孙。”《括地象》曰:“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谓西方太守而乙绝卯金也。五德之运,黄承赤而白继黄,金据西方为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3](p.538)。
这些符命都出自巴蜀之地,故公孙述“数移书中国,冀以感动众心”。上承天命的再世之主只能有一个,对《赤伏符》深信不已的刘秀,大为恐惧,在无法也不能拆穿公孙述政治把戏时,回复公孙述说:“图谶言‘公孙’,即宣帝也”[3](p.538),责怪公孙述“王莽何足效乎”。刘秀将自己置于两难的境地,如果相信公孙述的符命,就要承认公孙述上应符谶的君王地位,如果申斥符命之伪,自己也难逃造伪的嫌疑,王莽的尴尬处境又一次在刘秀的身上体现出来。所以,符命是政治家自我神圣的工具,利益主体沉浸在虚妄的荣光里,感受着来自于上天或圣人的耳提面命,导演着现实世界的政治结构,以此求得臣民的神圣政治崇拜和心灵的神秘屈服。
光武帝即位之后,议选大司空,见《赤伏符》言“王梁主卫作玄武”[3](p.774),即拜野王令王梁为大司空。以谶文有“孙咸征狄”[6](p.141),拜孙咸为平狄将军,行大司马事,众将不悦,推举吴汉和景丹,卒用吴汉为大司马。光武帝以谶立事、决疑,也经常读谶。《东观汉记》津津乐地道讲了一个故事:汉光武帝勤勉好学,“十七年,帝以日食避正殿,读图谶多,御坐庑下,浅露中风,发疾,苦眩甚。”[6](p.76)班固也告诉我们:“三十二年正月,上斋,夜读《河图会昌符》,曰:‘赤刘之九,会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于承。诚善用之,奸伪不萌。’感此文,乃诏(梁)松等复案索《河》《洛》谶文言九世封禅事者。松等列奏,乃许焉。”[3](p.3163)汉光武帝对于谶纬的崇拜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中元元年(公元56年)初,起明堂、灵台、辟雍及北郊兆域,汉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6](p.78)。汉明帝时,诏令东平王刘苍“正五经章句,皆命从谶”[2](p.32)。建初四年(公元79年),汉章帝依宣帝故事“亲制临决”,召开白虎观会议,以谶纬衡定经学,完成了谶纬的国教化形式。侯外庐先生深刻指出:“所谓‘亲制临决’的钦定的法典形式,企图使皇帝成为国家的本质,使上帝成为宗教的本质,并使二者的关系固定化起来,这也如恩格斯指出的‘国王一词乃是君主制的完成,这犹之乎对上帝一词的崇拜是宗教的完整。国王一词是国家的本质,犹之乎上帝一词是宗教的本质,尽管这两词毫无意义’。”[7](pp.225-226)东汉政权许久没有像董仲舒这样的经学大师给予合法政治的定位,而今文经学在西汉末期的拙劣表现,使汉光武帝无法相信儒家思想的权威性,所以,必须找到经学以外的确保汉代政治合法地位以及保持政权神圣性的理论支撑,汉光武帝紧紧抓住了已经深入人心的谶纬观念,借鉴了王莽成功的政治经验,把自己描画成上应天命的真龙天子,在臣民诚惶诚恐的膜拜中顺利完成帝王大业。汉光武帝以及后世之君将谶纬制度化和法典化,不过是保证汉代政权得以永久延续的政治策略,即人君的神圣化,宗教的政治化。
二、谶纬决疑:朱紫错用的政治发明
今文经学家一直声称:“《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增加了经学阐释的不确定性。随着经学作为工具理性而存在的意义增加,追逐时代政治的颦笑成为今文经学的暗疾。谶纬主动投入汉代政治的怀抱,西汉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绝对的君主权力,予以毫无回旋余地的痛击。随着统治者权力的极度削弱,蕴含上天意志的谶纬成为权力演绎不可抗拒的依据,于是,体现了崇高和神圣。今文经学家们看到了谶纬的政治价值,在阐释经学过程中,主动接受谶纬的影响,做出了适合于现实政治需要的思想调整。“俗儒趋时,益为其学。篇卷第目,转加增广。言五经者,皆凭谶为说。”[2](p.32)以谶纬说经是东汉主流经学的价值追求,是一个时代政治特点的经学映射。
建武四年(公元28年),尚书令韩歆上疏欲立《费氏易》《左氏春秋》博士。《梁丘易》博士范升,认为“左氏不祖孔子”且传授不明,不宜立博士。又上疏奏言:“《左氏》之失,凡十四事”及“《左氏春秋》不可录三十一事”[3](p.1229)。古文经学名家陈元上疏谏争,凡十余次,光武帝卒立《左氏春秋》博士。从《后汉书·儒林传》中我们得知:“陈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图谶,不据理体”[3](p.2582)。显然,争论的双方为了说服汉光武帝,投其所好,论辩之中采用了大量谶纬作为取信于皇帝的手段, “才高名著”的陈元获得了最终胜利,《左氏》立于学官,旋即复废。贾逵云:“光武皇帝奋独见之明,兴立《左氏》、《谷梁》,会二家先师不晓图谶,故令中道而废。”[3](p.1237)可谓一语中的。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8](p.407)一些紧随风潮的儒生纷纷研治谶纬之学,寻找政治介入的最佳途径。建武二年(公元26年),光武帝以尹敏“博通经记”,拜为郎中,辟为司空掾,参与校定图谶,即汰去崔发为王莽所制图谶。尹敏以真诚的学术风格,诚恳地建议光武帝:“谶书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辞,恐疑误后生。”尹敏见光武帝并未认真听取他的意见,自制谶文“君无口,为汉辅”,光武帝见而怪之,责问其故。尹敏从容对曰:“臣见前人增损图书,敢不自量,窃幸万一。”[3](p.2558)光武帝虽未加罪于尹敏,却也不再升迁其官职。
薛汉世习《韩诗》,以章句著明于世。“尤善说灾异谶纬,教授常数百人。建武初,为博士,受诏校定图谶。”[3](p.2573)建武七年(公元31年),太仆朱浮越职上书倡言“广求博士之选”,最后说“臣浮幸得与讲图谶,故敢越职”,得到了汉光武帝的认可。光武帝时期,朝堂之上讲解图谶应该是一种经常性行为。《后汉书·儒林传》称:京师盛赞“解经不穷戴侍中”[3](p.2554)的戴凭,不肯恭陪末座,与诸儒论难,颇得汉光武帝的赏识。“正旦朝贺”,诸儒相互难诘,理义有不通,辄夺其座席,戴凭重坐五十余席。朝会主角是汉光武帝,评价尺度由他把握。诸儒讲经论道,即便不是讨论谶纬,论说者不可避免地将谶纬作为辩论依据。投君主所好,才能获得经学论辩上的胜利,政治利益便接踵而至。
建初四年(公元79年),汉章帝诏“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宫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3](p.138)。《后汉书·儒林传》也记载了此次盛事:“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史臣著为《通义》。又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3](p.2546)考之于史籍,参加白虎观论经的有太常楼望,少府成封,屯骑校尉桓郁,卫士令贾逵,广平王刘羡,五宫中郎将魏应,侍中淳于恭,校书郎班固、杨终,《公羊春秋》博士李育,博士赵博,郡吏鲁恭,儒生丁鸿。从儒生博士成为白虎观会议主角来看,汉章帝的目的非常明确,即整合朝野学术思想,力求统一于谶纬。从古文经学家的政治表现层面看,汉章帝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汉明帝时,贾逵上疏称《左氏春秋》也合于图谶。白虎观会议上,贾逵竭力辩称:“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其所发明,补益实多。”[3](p.1237)贾逵虽然不能代表古文经学者的全部,但古文经学者随波逐流的政治意识却给古文经学带来了政治的回报,“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建初八年(公元83年),汉章帝又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 《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3](p.1239)。而贾逵选拔的20名学修习《左氏春秋》的弟子及贾逵门生,选为千乘王国郎,“朝夕受业黄门署,学者皆欣欣羡慕焉”。古文经学虽未列于学官,但在帝国君主大力倡导下,获得了梦寐以求的政治地位和看似绚烂的学术辉煌,为今古文融合创造了学术条件。
对于汉代政治来说,古文经学走上政治舞台,有利于将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思想统一到谶纬的学术高度上。贾逵有关《左传》创造性的阐释不仅暗合了统治者的利益需求,也使古文经学落入汉章帝彀中。庙堂之上的古文经学从此失去了独立的学术精神,这是政治的胜利,学术的悲哀。随着今古文经学思想的整合,帝国统治内部形成了君权神授、天命所归的集体意识,儒学仅存的理性精神被谶纬侵蚀和瓦解,士人的学术精神在迷茫的神秘里逐渐倦怠,并且在疲惫中消失。
其后,汉章帝以谶纬为指导思想,对于国家的礼仪大典也进行了指导和修正,也就是说,改革帝国的政治结构,使其更符合于上天的意志,从而体现汉代政治的神圣性,增加神秘性,巩固汉代的神器而不至于鼎移。章和元年(公元87年),章帝以叔孙通《汉仪》12篇多不合经,命其“依礼条正,使可施行”。曹褒既受命,“乃次序礼事,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3](p.1203)会汉章帝崩,未及施行。永元元年(公元89年),汉和帝拜樊儵为长水校尉,“与公卿杂定郊祠礼仪,以谶记正五经异说”[3](p.1122)。
谶纬之风横扫帝国上下,于是,汉代经学士人大胆进行了学术创新,将谶纬作为专门的教学内容,形成了图谶学,或者称内学。《后汉书·方术列传》云:“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驰骋穿凿,争谈之也。故王梁、孙咸名应图录,越登槐鼎之任。郑兴、贾逵以附同称显,桓谭、尹敏以乖忤沦败,自是习为内学,尚奇文,贵异数,不乏于时矣。”李贤注曰:“内学谓图谶之书也。其事秘密,故称内。”[3](p.2705)“东汉之世,以通七纬者为内学,通五经者为外学。盖自桓谭、张衡而外,鲜不为所惑焉。”[9](p.1537)
经学士人是学术或文化精英,应该保持清醒的学术意识和敏锐的学术思维,然而,政治依附性造成的人格丧失,体现在学术上则是思想的屈服。将谶纬作为学术内容,作为精神思想传播,经学士人丧失的不仅仅是灵魂,而是对于一个民族的责任感。在东汉,谶纬作为教学内容显然是光明正大的,由于统治者的需要,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进而出现了方术群体。《后汉书·杨厚传》载:杨春卿善图谶学,为公孙述的将领,公孙述僭命称帝的符谶似乎和他不无关系。辞世之前,嘱咐其子杨统:“吾绨帙中有先祖所传秘记,为汉家用,尔其修之。”[3](p.1047)杨统修习家学,又从同郡郑伯山受河洛书,及天文推步之术。官至光禄大夫,国有灾异,朝廷多访之。杨统作《家法章句》及《内谶解说》二卷。杨统子杨厚,承家学,“晓读图书”。邓太后临朝,拜为郎,“问以图谶”,不合邓太后意旨,免归。同郡任安从学图谶,时人称曰:“欲知仲桓问任安”[3](p.2551)。
将作大匠的汉顺帝时,拜翟酺,四世传《诗》,“好《老子》,尤善图纬、天文、历算”[3](p.1603)。马融“集诸生考论图纬”[3](p.1207)景鸾“能理《齐诗》、《施氏易》,兼受河洛图纬,作《易说》及《诗解》,文句兼取河洛,以类相从,名为《交集》”[3](p.2572)。樊英习《京氏易》,兼明五经,又善风角、星算,河洛七纬,推步灾异,“以图纬教授”[3](p.2724)。桓帝时,牂柯郡人尹珍来洛阳求学,许慎、应奉授之“经书图纬”。尹珍学成,还乡里教授,“南域始有学焉”[3](p.2845)。
上有统治者郑重其事的政治宣传,下有谶纬之学的研习和传播,谶纬在东汉成为主导汉代政治、汉代士人思想乃至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绝对力量。由于士人阶层对于谶纬的屈服,随着经学的传播,谶纬思想逐渐下移,深入到汉代民众的文化心理之中,形成了汉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这也是儒家文化的一种悲哀。
三、“一禁绝之”:古文学家的谶纬批判
西汉的统治者选择了今文经学,抛弃了古文经学。古文经学因祸得福,保持了承自于孔子的以道术自命的传统儒学精神。沉浸于古文经学之中的儒家士人,不逢迎趋势,不屑于利禄之途上的随声附和,心无旁骛地自守于学术寂寞,呈现了清纯的学术气质和独立自持的学术人格,颇有隐逸的风格和精神,所以,修习古文经学的士人大多寂寂无名,古文经学的授受系统即便是史学家也难以明晰的原因就在于此。汉成帝末年,刘歆校中秘书,发现了《左氏春秋》、《毛诗》等古文经,颇好之。汉哀帝即位之初,提倡立古文经于学官,以失败告终。汉平帝时,古文经立于学官而复废;新莽朝,刘歆贵盛,古文经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空间。西汉末期,古文经学已经引起了有识之士的重视。经学大师杜林善古文经学,在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如获至宝,虽颠沛流离,却须臾不离于身。他曾经对卫宏说:“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意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也。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3](p.936)古文经与世道寡合,在热衷于利禄之途的经学士人眼中缺乏吸引力,作为通儒,杜林深深担忧古学的前途和命运。反观西汉经学士人,仕途上络绎不绝走来意气风发的儒学英俊,几乎都在西汉帝国的官僚体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实施自身的儒学理念。古文经学士人的孤独和寂寞,为汉代经学保持了一个纯净的学术空间,一片温馨的精神家园。
西汉晚期,古文学派的扬雄,“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为,少耆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1](p.3514)。王莽篡汉之后,“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扬雄不以为意,潜心于道术之中,欲以文章显名于后世。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1](p.3583)。刘歆对于扬雄求诸内心,而不旁观于外的治学精神颇有微词:“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1](p.3585)同为古文学家的桓谭,对于扬雄赞誉有加:“今扬子之书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若使遭遇时君,更阅贤知,为所称善,则必度越诸子矣。”[1](p.3585)此言诚为知人之论。扬雄以“默默独守吾《太玄》”的避世态度,与世俗富贵擦肩而过,虽不免于时代政治的附和,却保持了特立独行的学术品格,成为西汉末叶儒学成就最高的经学士人。
刘歆是西汉末期大儒,古今兼通,尤长于古学,对于古文经的传播用力甚深。与王莽关系密切,被王莽拜为国师,其二子以图谶要挟王莽,被王莽所杀。王莽利用谶纬篡汉,刘歆没有推波助澜,也没有予以制止。刘歆弟子们反对谶纬态度鲜明,成为东汉政治思想领域的精神财富。
《后汉书·杜林传》曰:“河南郑兴、东海卫宏等,皆长于古学。兴尝师事刘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兴等固谐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见林,暗然而服。济南徐巡,始师事宏,后皆更受林学。”[3](p.936)
《后汉书·郑兴传》曰:郑兴“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天凤中,将门人从刘歆讲正大义,歆美兴才,使撰条例、章句、传诂,及校《三统历》。”[3](p.1217)又曰:“兴好古学,尤明《左氏》、《周官》,长于历数。自杜林、桓谭、卫宏之属,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于兴,而贾逵自传其父业,故有郑、贾之学。”[3](p.1223)
《后汉书·贾逵传》曰:“父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又受《古文尚书》于涂恽,学《毛诗》于谢曼卿。”[3](p.1234)
杜林、郑兴、贾逵的古文经学皆起于刘歆,却彰显了不同的学术性格。范晔云:“郑、贾之学,行乎数百年中,遂为诸儒宗,亦徒有以焉尔。桓谭以不善谶流亡,郑兴以逊辞仅免,贾逵能附会文致,最差贵显。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3](p.1241)
桓谭遍习五经,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扬雄辨析疑义。汉光武帝即位之后,笃信谶纬,“多以决定嫌疑”。桓谭上疏指斥谶纬的虚妄:“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光武帝览奏,大为不悦。《后汉书·桓谭传》载:
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欲以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3](p.961)
范晔有言:“郑兴、贾逵以附同称显,桓谭、尹敏以乖忤沦败,自是习为内学,尚奇文,贵异数,不乏于时矣。”[3](p.2705)检阅《后汉书·郑兴传》,我们并没有发现郑兴有附同嫌疑,相反却能够理解在周遭谶纬悬疑的氛围中,一个儒者无奈的沉默。
帝尝问兴郊祀事,曰:“吾欲以谶断之,何如?”兴对曰:“臣不为谶。”帝怒曰:“卿之不为谶,非之邪?”兴惶恐曰:“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帝意乃解。兴数言政事,依经守义,文章温雅,然以不善谶,故不能任[3](p.1223)。
谶纬挟持了东汉的最高统治者,帝国君主意志的坚决贯彻,又屈服了那个时代博士文人的思想。西汉博士文人政治依附性中尚有自由命意成分,所以,我们还能看得到东汉初期博士儒生对于谶纬束缚的思想挣扎和意识反驳。白虎观会议之后,今古文经学慑服于统治者的玉阶丹墀之上,颂声不绝于耳,鲜闻榷诂之声。章帝之后,男主幼弱,女主恃强,外戚蜂拥而起,汉代政治再次呈现出动荡迹象,我们终于又听到了久违的科学和自省精神的呐喊,那一声宏亮呐喊不仅振动了汉代的政治基础,也给沉迷于谶纬中无力自拔的经学士人以自我认识的勇气。
永平末年,大儒王充造作《论衡》一书,他说:“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其本皆起人间有非,故尽思极心以讥世俗。”[10](p.280)对于当世流行的谶纬之说和充斥于社会的迷信思想,王充以科学的精神逆天下而动,“讥世俗”,“疾虚妄”,向经学士人在不知不觉中已经体认,并作为制度的常态——共同遵守的虚伪的政治理念发起了挑战。他说:“今吾不得已也。虚妄显于真,实诚乱于伪,世人不悟,是非不定:朱紫杂厕,瓦玉集糅,以情言之,岂吾心所能忍哉”[3](p.280)迫急的救世情状,拨乱反正的气魄,着实令人感佩。但是,无论王充怎样大声疾呼“如天瑞为故,自然焉在?无为何居?何以天之自然也”[10](p.177),没有回响,没有应对,也没有喝彩,哪怕是死水微澜,依然“月自当空,水自流”(苏轼《次韵徐仲车》)。
汉顺帝时,太史令张衡对谶纬发起了挑战。他认为,图纬虚妄,非圣人之法。又证之种种虚妄不经而无验之事,来说明谶纬出现较晚;他道出了谶纬出现的真是原因,即“殆必虚伪之徒,以要世取资”。所以,张衡上疏建议汉顺帝:“宜收藏图谶,一禁绝之,则朱紫无所眩,典籍无瑕玷矣。”[3](p.1912)张衡是清醒的,而清醒即预示着孤独的存在。张衡直言不讳的冷静以及刻薄的公正,注定了不被当时的统治者所欣赏;安于现状,已经习惯于通俗思维的儒生博士们也向他投来忿恨的目光,宦官们更是恐惧张衡讽谏左右的刚正个性,“恐终为其患,遂共谗之”[3](p.1914)。
汉武帝建国之后,直至东汉中叶,儒家的社会批判精神几近荡然无存,皇权重压下形成的附同的群体性格,使儒生博士的所有智慧,几乎耗费于毫无理性可言的谶纬,用天命观念极力证明皇帝是受命于天的,以此建构统治者理想的社会秩序。国家意志能够深刻地体现出来,但是儒生博士的自我消失了,如果没有王充的激烈反驳,如果没有张衡的清醒批判,东汉初期的思想史就会变得一片黑暗,博士文人亦无个性可言。我们听到的曾经那样熟悉的讴歌赞美声,即宫廷文学呈现出的灿烂祥和的微笑,遮蔽了一切悲伤、哀怨、叹息,一派盛世景象无节制地演绎着。歌者却在内心深处典数着谶纬的神秘,期盼着丰厚的利益回报,细数达则兼济天下的幸福。
[收稿日期]2008-08-20
标签:汉朝论文; 经学论文; 西汉皇帝论文; 博士论文; 王莽论文; 公孙述论文; 西汉论文; 光武帝刘秀论文; 古文尚书论文; 王莽篡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