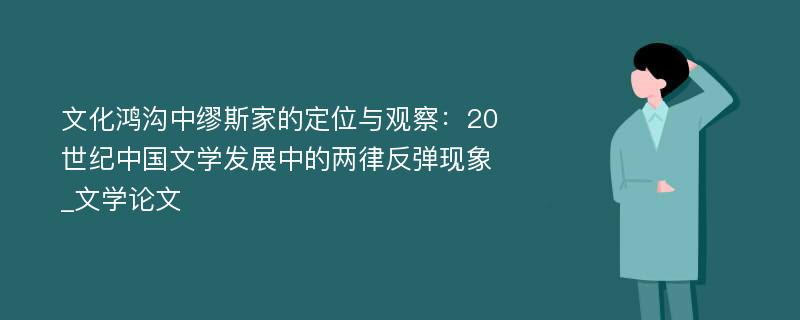
文化夹缝中缪斯家园的定位与守望——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的一种二律背反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夹缝论文,中国文学论文,现象论文,缪斯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站在世纪之交的分水岭,很自然就会回顾所来之路。在当下急遽转型的现实语境中,这种文学范畴里的世纪意识对于一个文学史研究者来说是份属当然的。前瞻的热望离不开回顾的清醒。因此,在无数个案的条缕清晰的微观研究之外,也很需要以一种综合的思维方式来进行思考,从种种文学现象的追踪进入到对文学性格和命运的深层把握。换言之,是要具有深度的宏观把握。一个相当诱人的话题,但却难以对之涵括,一不小心下言就易失去分寸。确实,百年文学史的现象极其纷繁复杂,其覆盖面之广阔,内容之深邃,牵涉之错综,非我之笔力所能轻易解析得清楚。这里试从文学所处的特殊的文化境遇及其文化心理这一角度回眸,对百年文学进行不自量力的梳理。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以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矛盾为主导线索,对文学中的“离家”与“还乡”、“终极价值”与“世俗化”、“多元化”与“统一性”等一系列二律背反现象加以论述,找出其规律、表现、根源,总结经验,以昭示中国文学从古典到现代最终转型的文化重构时期的到来。
一、中西文化夹缝:现代化的梦想与民族化的执著
文学与文化是不可分的,文学反映社会的特点决定了它既是文化的一个构成要素,又反映着社会的文化本身。因而,有着悠长历史的中国古典文化必然是与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化相伴相随,共生共灭的,它们在虽封闭却繁荣昌盛的封建时代曾享有值得自豪的辉煌灿烂。但当历史翻到19世纪中期,其命运就开始改写了。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之下,中国文化及其文学开始了一种被动的开放和交流的历程,因为被动,这历程是异常艰难而痛苦的,于是,造就了一道道深刻而异彩纷呈的矛盾烙印。
当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大范围的文化交流与比较成为可能,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开始形成。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中,各国各民族之间互相借鉴学习,照理,对双方有益,是皆大欢喜的事情。但中国文化自近代以来被强加的半殖民地化的文化地位注定了其进退两难的尴尬命运;被迫纳入到异族文化轨道这一事实决定了其文化心理构造的悲剧感。
首先,“落后就要挨打”这一以惨痛经历换来的真理,使中国人对西方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和民主国家制度注目。因为富国强民之心愿的急切,所以没有人去留意或者是故意忽视了现代化的时空局限性。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和价值,现代化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是与其整个文化体系相联系的,有其优胜面也有其差劣面。因而没有立足于民族传统,缺乏卓有见识的分析、批判而一味盲目地移植西方观念,是不切合实际的。但是,在民族存亡的忧患中,这一切都无暇顾及了。随着“德先生”、“赛先生”以昂然的姿态走上中国的舞台,其内涵所指向的“现代化”就成为了中国人的宏伟蓝图和最神圣的梦想,至今仍追求不息。与此同时,作为对另一文化屈从的弱小民族,深切体味到西方文化权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压迫,凝聚起民族自尊心,为了卫护自身文化的根基,于是屡屡呼唤回归民族传统,流露出对“民族化”(这里指沉淀着更多传统成分的民族化)的执著。出于民粹主义的怀旧情怀,他们往往把所有民族化的东西都盲目美化,而缺乏一种世界性的接受外来影响的目光,显得较为狭隘保守。由此,现代化的优胜面与民族化的落后面,民族化的合理面与现代化的差劣面之间(本文更多的是指前者),形成了尖锐的冲突,其冲突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广泛的。
这表现在百年文学史,便是文学创作趋向在这种文化夹缝之中的左右突围。可以说,几乎每一次文学“现代化”的努力,都会引起一次“民族化”的热潮。世纪之初,“五·四”新文化主将们以激进的态度来展开文学革命,倡导反帝反封建的平民文学,推行白话文运动,自觉地深化对民族文化价值和文化心理层面的反思,如鲁迅以《狂人日记》猛烈抨击封建传统的吃人制度,以《阿Q 正传》等开拓批判国民性的主题。而在30年代开始,民族危机的加剧,又触动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文化思潮的勃发,以拒斥西化影响。我们可以看到,从周作人沉回中国传统文化情境的散文创作,废名沉迷于唐诗宋词式的田园小说创作与沈从文回归湘西民族传统的创作倾向等的对西化的部分反拨开始,到抗战期间展开通俗化和民族形式的讨论,都是对民族传统的审美趣味实行热情洋溢的回归。其时对古典文学和民间艺术的学习也成为一种风尚。如老舍学写快板、鼓词;张恨水的章回小说走红;赵树理的一系列民族化作品出现等。而建国17年时,这种民族化的趋势和一元化的思维模式又进一步增强。直至到了文化大革命,所谓“完全民族化”使中国文化陷于保守、专制、僵化的境地,其文学道路是对“五·四”文学以西方文学为参照的现代化努力的全面背叛。这必然会引起另一场新的启蒙运动,由此,“现代化”梦想从内心隐蔽处重新走回到中国人的视线内。这就是70、80年代的文化开放与自省,反映在文学上便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兴起。而在对文化的反思过程中,寻根派发现了民族传统审美文化的价值。像《棋王》、《爸爸爸》等寻根小说一时蔚然成风。这表现了“民族化”的回潮。但在80年代中后期,“现代化”的潮流又席卷了一切。最引人注目的是先锋派,在浮躁的局面中带着对意义怀疑的心态,接受博尔赫斯等当代欧美作家影响时,努力体现创造性和个人风格,醉心于语言的实验……
这样,为了与世界接轨,接纳现代西方文明的先进面,于是,在对物质世界、精神世界变革的基础上来重构新的文化框架和文学观念的过程中,“现代化”成了中国人的最高梦想;而又痛感文化断裂,不愿因割断民族传统而失去中国文学自身品质和特征,从而执著于“民族化”的努力。此二元对立因为各执一端成为焦虑所在。优劣面之间,激进和保守之间,难以取舍,中庸则沾上了不中不西、不伦不类的味道。从而循环往复,不断摇摆,在痛苦的二律背反中辗转翻覆,无处安身。在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中国文学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某种横向错位、纵向断层的无根情境中,并在中西文化的撞击和整合中启动了它艰难的人文旅程。
二、缪斯家园的定位:“离家”的惆怅和“还乡”的破碎感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过许多家园意识很浓郁的作品,但其文化内涵与本世纪的是不同的。那时的家园感是在一元化的文化境遇中产生,是与家国一体的社会经济结构和伦理至上的儒家文化相联系的。而本世纪文学的家园感却是在二元对立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中生发出来的,从而拥有了独特的意味。
在现代作家们的许多作品中,正是天然地选择了在西方城市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包括持有乡村价值标准的古城文化和乡村文化)相交这一临界点,在逐步走向现代化的城市文化氛围中再现文学的困境。他们面对传统意义上的家园,或背离或回归所表现出来的正是二律背反的特质。“城市与乡村的对峙与相衡,构筑出谈不尽的现代中国的文化景观。这里,不但恩格斯说的历史与伦理的二律背反及判断有效,而且尤能见出中国人文精神中那种悲壮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分量”〔1〕。 显然,这种景观是源于独特的文化境遇,是从现代化与民族化的深刻矛盾中衍生出来的。
当中西文化较量的结果是中国沦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单一而固有的自然经济、农业格局被逐步打破,那么,一向被信守的传统文化分崩离析,中国文学也就失去了其精神的强大支撑力,而陷入了多灾多难的文化夹缝中。这个时候,现代对传统的影响已不容抗拒。中国知识分子茫然四顾之余,终于带着文化自觉,直面由遥远地域而来的这崭新的时代精神。我们可以看到,那是一个在沉睡中被惊醒的迷乱状态,一代代的人在世纪之初微露的曙光照耀下,开始四处寻求去路。从江南绍兴的乡绅破落户(鲁迅)、从四川成都的封建大家庭(巴金)、从湘西的军旅家庭(沈从文)、从浙江镇海的商业之家(王鲁彦)、从湖南洞庭湖的农民之家(叶紫)……,他们从四面八方各个阶层纷纷涌向都市。都市在他们眼里,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代表着物质的繁盛和社会的前进,是科学民主,是西方文明的象征。这种离家的热潮暗含着他们对现代化的梦想。很长一段时间,在“五·四”文学西化创新的光辉笼罩下,“离家”的中国作家们在创作中流露出对都市的盲目热情与憧憬。发展到海派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他们以崇洋鹜新的心态对半殖民化的现代都市,赞美多于批判,“认同多于反思”。正如杨义所指出的:“他们并未能深刻地剖示在两种异质文化反差的夹缝中心灵世界炼狱般的惨痛”〔2〕。这一点却在乡土作家的笔下得到体现。 他们对于都市的看法与海派是截然相反的。他们痛苦地感到所奔向的这个都市被现实褪掉了梦中的色彩,完全是陌生而疏离的,是并不属于他们的。都市的机械和商业文明对人的异化、损害及所造成的种种丑恶现象,又使他们深深厌恶,从而回望起封闭落后却纯朴美丽的故乡。于是他们的笔触从对都市的惆怅又返回了对故乡的文化描述。而对故乡的观感看法,在早期乡土派与后来的京派之间又有些差别。前者是写实的,更带批判性地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乡土生活,展现故乡的沉滞、落后,农民的不幸,社会的不合理。还乡的热切中有清醒。而后者是抒情的,对故乡更多主观性的赞美,但其行文中最终也难以掩饰对家乡道德沦丧、文化寂灭的渐近状况的破碎感和无家可归感。
由此,从以上勾画中我们发现了:现代文学史上在“离家”与“还乡”的彷徨中形成了城乡对立的命题。城市与乡村,在其作品中是一组“具象化的文化符号”,并以互相对立的形式出现,并非简单的地域概念,而是具有强烈的文化取向和价值意味。在城市梦想与乡村情结之间,其内涵实质上正是奔向西方文明与回归民族传统相悖反的反映。当然,“离家与还乡”,这现象在世纪初期文学中表现得最为显著,但在当代并非不存在,如寻根派与先锋派的先后崛起就是明证。而近几年来南方大城市广州、深圳的“打工仔”文学也隐隐透露出城乡对立的问题。
那么,在“离家”奔向西方文明与“还乡”回归民族传统之间,缪斯家园又该如何定位呢?有人是前瞻、追逐型的,深知自己的落后,奋勇追寻,虽然具体目标不明确,而始终立足于传统朝着世界性的方向前进。如鲁迅的《过客》便体现了这种精神。但其末流却容易陷入对西方的盲目崇拜中。又有人是怀旧、追忆型的,虽迎视崭新的外来文化,但对本土文化保持着相当的崇高感并对传统文学情有独钟,于是在创作中营造出浓郁的文化乡愁感。如沈从文的《边城》便是以抒情笔墨来展现田园诗人式的民族乡愁。但其末流却又易陷入保守、死守传统的困境。这两种方案都有其值得肯定的一面又有其偏颇的一面,不期然地体现出文化冲突的深刻影响。
总之,随着历史的推进,中西文化的冲突也从更广泛的层面构成了本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一种基本内涵。现代意识与民族传统之间的张力,推动着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前进。于是,不“离家”无以跟上世界潮流,涵纳新的时代内容,不“还乡”无以保持民族的独立品格,在“离家”与“还乡”之间,中国作家们对缪斯家园的追踪定位从未间断,或者中西文化冲撞的漩涡有时也使他们处于撕裂的痛苦和奔波的疲乏中,但他们始终不懈地执著于两者的沟通和融合。正如闻一多所说的那样,他们渴望在文化夹缝中的恰当地方建筑起美丽神圣的缪斯家园,以迅速向世界奉献出中西文学联姻后生下来的“宁馨儿”。
三、精神逃亡:终极价值关怀和世俗化倾向
缪斯家园需要有精神来支撑,两千多年来历来如此。20世纪却是中国文化意义危机和价值重建的时期。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现代化呈加速度行进,中国陡然裸露在世界面前。商业飓风席卷一切,于是人文环境的世俗化成为政治功利主义瓦解之后不可避免的产物。但问题的症结却在于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文化失范,欲望膨胀,精神价值和理想信仰退位以及文学创作的制作化。由此,文学上“精神逃亡”这一极具悲剧内涵的现象便出现了。
这首先是起因于文学所处的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正处在转型时期,市场经济法则的确立,商业方式的运作,文学的发展无法不受其牵制。其次是文人自身价值身份或文化身份的转变,从高高在上的精英知识分子变成了无甚特殊的普通人,为了获取世俗性的物质需求,也难免会逐渐放弃了曾被自己视为精神向导的人文立场。但说到底,在深层次上,恐怕还是源于二律背反的文化境遇所造成的吧。“五·四”时,对文学的改革“只着眼于文艺改造国民性的社会功利作用,忽视了文艺的形而上的审美意义,致使新文学缺乏西方近现代文学所具有的超越内涵,以后又向政治功利主义蜕变”〔3〕。可见, 在对文学现代化的进程中一直是缺乏形而上的文化层面引入,只一味注重功利主义。而且,“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造成了文化传统的断裂,旧价值失落,新的价值缺少终极价值的支持难以确立,于是陷入长期的文化失落中,不能有序、平稳地过渡”〔4〕。
其实,这种世俗化的现象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从世纪初的鸳鸯蝴蝶派、黑幕派,其商业性已初露端倪。到现代海派文学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虽然新时期的所谓“伤痕文学”、“改革文学”体现了一种人文精神和对个人终极价值的关怀,但因为艺术上的粗糙和思想上相应地流于浅显,很快就受到了后来人的摒弃。只是这些后来人也并未能从精神上真正超越他们,而相反地走上了另一条道路。80年代末期以来的当代文坛,随着商业文化的大范围泛起,文学深深地卷进了商业的运作中,其市民化和媚俗性更是一发不可收拾。神圣被肆无忌惮地嘲弄,理想主义悄悄撤退。对信仰的缺失,使人耻谈使命和责任。对于商业价值的追崇和对世俗的盲目迎合使文学迅速的庸俗化。这种猛烈的世俗化倾向具体地既表现在文人的商人化上,也表现在文学作品的商品化上。不少文人直接了当地投入了经商大潮,像陆文夫、张贤亮等。也有许多人只是为了销售自己的作品,通过传媒、广告大肆宣扬。而文学的商品化之赤裸裸的呈现就是如北京、深圳的文稿拍卖。其后果使文学作品在内容上流露出低级趣味、渴望堕落、俗不可耐的一面;而在形式上即使有所创新,也通常是以精神、价值的下坡为代价。另外,严肃文学也不断地向商业性靠拢。先锋派与通俗文学接轨,新写实小说对现实中的烦琐事务式的世俗价值认同,都透露出知识分子已逐渐丧失独立的人格精神和价值标向。到《废都》,这种世纪末的颓废情绪流露得更淋漓尽致。这样,商业大潮下,文学在普及和世俗化的过程中不断蚕食自己的本质,从而远离了它曾经令人目眩的精神属性。崇高的精神仿佛从此逃逸了,庸俗和浅薄成为时尚。
面对这种状况,全国各地到处展开了人文精神的讨论。有人指出:“(文学)走向了肉体乌托邦、感性乌托邦,导致了价值的崩溃”;有人说:“‘文以载道’曾成为文人们悲壮的祭坛,而‘文以载钱’则成了文人们悲凉的末路”;有人则提出所谓的“文学复位说”,承认现状,以平定人心。这都是对文学身处危机的种种表述。文化的失落、失语,真正信仰的缺乏,终至对文学本性的迷失。究其实,在对现代化事业的追求中,在商业飓风的席卷下,文学的部分沦落也许是无法避免的,但整个文坛的世俗化趋向和文学的大规模沦落却是必须努力避免的。文学的精神必须宏扬,人类直觉情感的最后一块生存领地必须捍卫,这是出于对文学本性的准确认识:“文学天生带有一种终极关怀的鲜明特性,它是人类为了拒绝沉沦走向超越而保留的唯一的一块精神净土。这类终极价值无法进入交换状态,文学价值永远也不可能转化成为商品的价值。”〔5〕
当代作家中部分人的创作就一直信守这样的信条,执著而昂扬地奏响了肃穆崇高的主题,向商业化、世俗化大潮展示了傲岸的姿态,以维护文学的精神属性。他们的这种寻求以其精神寄寓之所来划分,似可分为三类。一是对自然的追慕:张炜的创作总是使人“感到一个无时不在的人物,那就是大自然”〔6〕, 他“融入野地”的《九月寓言》中月辉照耀下的小村万物,后出的《柏慧》中美好和谐的葡萄园,《家族——你在高原》中那只飞翔的鸥鸟,自然在他的笔下如同海德格尔的“大地”,可“诗意地栖居”,是滋养人类精神的家园。二是对宗教的膜拜:张承志在向西部大陆迈进的精神朝觐之后,写出使人震撼的《心灵史》,表达了对精神的渴求,并试图把人生和文学引向宗教信仰,只可惜他在这宗教的超功利的彼岸性和不息的理想追求中所找到的灵魂皈依,因为流于教义的艰深而疏离了大众。三是对世俗生命新的人文价值的呼唤:新写实作品曾初露端倪,企求在烦恼人生的叙述中建立一种反映物质生存意识、更具人性色彩的平民式的人文价值观,可是精神的建构远未拉开帷幕,已被世俗所淹没而走向对意义的麻木。余秋雨、梁晓声的创作则力图在浩瀚的民族文明史中开掘出健康的人文精神,以之为世俗生命作新的注解。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表达了对“人本困境”的通透思索,从而真正面对自我,达到对个体生命的超越。
总之,在世纪末的颓废情绪大范围蔓延之时,仍有精神的捍卫者在,文学的良知仍未泯灭。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也必须看到,世俗化趋向虽不被精英文化承认却已成为一种时代潮流。其实,只要适俗而不是媚俗,世俗化文学也自有它存在的价值,假如能提高到对人的终极价值层面上的一定程度的追问固然更好,假如不能也无须当洪水猛兽。毕竟生活在当今时代,文学须和世俗的人们不停地对话和沟通。关键之处在于当代作家们应有长远的目光,对现实有明澈而机敏的认识,加上较为良好的尊重知识分子的机制,才能使文学肩负起文化关怀的使命。也就是说,在现代市民主义和传统乌托邦之间,文学在立足于现实人生的基础上,应寻找自己的信仰以之为生命的依托,这是摆脱媚俗与背时这一悖论的真正出路。
四、漂泊者在世纪之交的守望:多元化存在与世界性的最终流向
匆匆百年,洋洋大观。在20世纪中国的文学世界中分明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漂泊者”无地可栖的主体形象。这个大写的主体形象,在中西文化撞击、摩擦、挤压之下,长期陷入了种种二律背反的困惑中。如今新世纪的脚步已渐近,这个历尽磨难,曾执著追求、曾失意逃避的精神“漂泊者”,将在何处守望它的缪斯家园呢?
转型时期的当代社会有着深刻的复杂性。国际上冷战结束,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语境仍然存在,如前段时间西方哲学精神、艺术理论、现代主义潮流和更为庞杂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曾一度汹涌而入。国内则是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商业意识等,已渗入到社会生活的一切方方面面。这样一种社会氛围,意味着文学将要接受一种新的本质规定,带上新的时代属性和新的文化表征。而文学的一切变化,包括在形式上的叙述革命、语言实验、技巧与风格的变异等最终要回到思想和精神的追求上。作家们应站在为新时代创造新文化的理性峰巅上,俯览顺流而下的民族文化大河,以百川归海的信念,肩负起创造新文学的重任。
其实,在一个迅速发展与变化的社会中,不但不会冷落文学,而且比任何时间都更需要文学提供一种更为持久稳固的精神价值以抚慰人们疲惫的灵魂。文学将在新的时代发挥它新的抚慰作用。当然,它首先必须从二律背反的困境中突围出来,获得自由,赢得信念,才得以倡导多元化观念和多元化的精神,适应读者的需求。这需要有对文化融合的清醒目光,从而在中西文学及其范式的互补与筛选中,使文学的现代意识获得充分地发展,在不失落传统的血脉和时代的要求下,力求以自我的特质与整个世界历史对人类个性的要求相呼应。因为在商品经济的社会中,是以承认人的个性、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多样化为条件的,尤其在当前的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中,随着文化中心的进一步解体,文学更应该相应地建立一个有序的、充满生机的多元化格局。这样,既可从民族传统的诗性智慧中吸取养分,也可以从西方由古至今不断衍生繁殖的现代意识中茁壮成长;既可从回顾的目光中,寻找繁华旧梦的温暖记忆,也可从奋发向前的追寻中营造尚不可知的缪斯家园;既可在与世俗人们不断对话沟通中,描述现实展现世俗幸福的向往,把个人欲望转化为使人向上的艺术力量和较为纯粹的境界,也可把精神信仰寄寓在自然、宗教、历史、生命等各种各样的形式中,对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进行追问……总之,一统局面必须打破,专制化必须丢弃,多元化存在成为势所难免。
当然,多元化并不是杂乱地拼合,而是有序地形成文学发展的合力。文学的发展有其特定的总的流向,正所谓“百川归海”。多元化只是表明了文学发展的横向状态,而不能说明其纵向的动态,即统一性所在。这统一性的指归便是二元对立的文化夹缝中对现代化的偏向。不过,20世纪中国文学一直魂牵梦萦的关于文学现代化的努力,虽然从世纪之初就开始了,但由于没有一个持续的对文化理想、人文价值的关怀和建构,或激进或保守,都只是一种姿态,跳不出那个怪圈。尤其在新时期的作品中,仍然局限在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中,成了西方评论家韦勒克所说的一种只算作历史性的文献,而不能以不朽的著作走上世界,这使当今的中国作家们极为焦虑。况且,文学的现代化是有赖于政治——经济——文化整体格局的现代化。而当今社会的现代化仍未实现,文化上的启蒙仍没有完成历史任务,因而文化保守主义的合理性便大大削弱,现代化作为世界潮流仍是首要倡导的,而且任重道远。在文学创作中具体表现为一种现代性的要求,即以现代意识透视,以现代形式表现现代人的民族灵魂。深入地说,正如一位论者所言“是一个民族超越现实对于自我生存状态的反思能力,以及理性批判的基础上,进行终极价值追问的能力”,要求“文学回到人类生存的诗性智慧中”,“回到人性的根柢”中〔7〕,以此来确定人类艺术的世界性的根本内涵。 这正是被置于百年忧患背景之上的中国当代作家们所必须进行的对文学自身的思考。现代性的问题,如何与国际接轨的问题,是中国文学最终流向之所在。
可见,在“漂泊者”的眼里,现代化的希望之光仍在远方闪烁。一个单纯回归民族传统或终守田园文化立场的人是无法创造出一流的现代意义的作品;而一个盲目沉浸在所谓的商业文明里,在世纪末颓废中掏空灵魂内涵的人也同样开辟不出一片纯净的精神领地。其实,不在意“离家”还是“还乡”,“终极关怀”还是“世俗化”,关键是两者的最终追求一致。当世纪之交的钟声即将响起,面对着依然存在的二元对立的文化困境,在对死守传统者的不满与对拍卖者、逃遁者的诘难中,当今时代热情呼唤执著于缪斯家园的坚守者!
注释:
〔1〕刘淑玲:《乡村梦影里的城市批判》载《中国现代文学》,96,1。
〔2〕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第59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88,10。
〔3〕〔4〕杨春时:《文化转型中形而上的缺失及其代价》载《文艺评论》,96,5。
〔5〕〔7〕王进:《中国文学的当代命运——论文学的现代性》载《文艺争鸣》,95,3。
〔6〕张炜:《你的树》收入《散文精选》,山东友谊书社,93,8。
标签: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二律背反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艺术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现代化论文; 还乡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