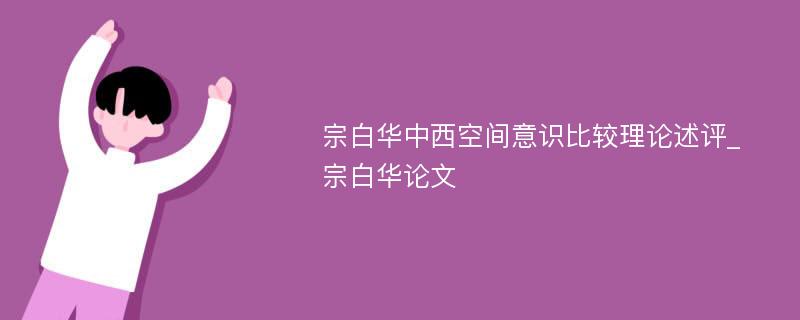
宗白华中西空间意识比较论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述论文,中西论文,意识论文,空间论文,白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西两种不同的空间意识与双方迥然有别的观照法密切相关,宗白华先生对中西空间意识的比较研究迄今无人可与之比肩。建基于“人与世界对立”哲学的西方人的空间意识,固守着心物截然两分的观照立场,因而形成的是静止的、几何式的、“一远”境界的透视空间;而建于“天人合一”哲学的中国人的空间意识,独独青睐“俯仰往还、远近取与”的流动照法,因而形成的是虚灵的、音乐化了的、“三远”境界的艺术空间。
在近现代中国美学家中,宗白华第一个将中西空间意识作为研究对象并加以分析、比较和探讨,他在这方面的成就迄今无人可与之比肩。分析这一内容,我们将会明白,宗白华之所以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是因为审美空间意识问题,集中反映了中西不同的宇宙观、人生观,从而表现了中西文化的不同特色,乃至相互歧异的民族心理。通过空间意识问题,我们可以更透彻地认识中西美学审美理想的根本差别。宗白华自己就说过,“空间感的不同,表现着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阶级,在不同的经济基础上、社会条件里不同的世界观和对生活最深的体会。”(注:《宗白华全集》第3卷,第411页。)所以,从30年代到80年代,空间意识问题在宗白华的研究中都居于突出地位。
西方人的空间意识,指的是以追寻、控制、冒险、探索的态度对待无穷的空间,是对空间的秩序、和谐之静止的意识。中国人的空间意识却是用心灵的眼睛观看空间万象,是对大自然整体节奏的流动的意识,它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艺术如书画中所表现的空间境界。
我们的空间意识的象征不是埃及的直线甬道,不是希腊的立体雕像,也不是欧洲近代人的无尽空间,而是滢洄委曲,绸缪往复、遥望着一个目标的行程(道)!(注:《宗白华全集》第2卷,第440页。)
宗白华试图从哲学根基上寻找中西空间意识的不同渊源。他通过分析认为,心与物,主观与客观问题始终支配着西方哲学思想,无论古希腊的哲学观是将有限的具体世界包涵在和谐宁静的秩序中,还是近代西方哲学观在无尽的交流关系里容纳了一往无穷的力的系统,它们的态度都是一致的,即心与物,主观与客观的对立相峙。中国哲学思想的兴趣在“天人之际”,不是把物看成是和人相衡相峙的异己对象,而是把它看成是与人息息相通的生命本体,这种“天人合一”的文化意识建构在体异性通的深层的文化心理之上,它不仅成为许多哲学伦理思想的逻辑起点,也成了中国美学中许多论题的立论基石。“料得青山应似我”,可能是中国艺术家经常萦然脑际的问题。中国人抚爱万物,与万物同其节奏,自然成为人一个永恒的参照对象,启发人类以真知,又赋予人类行为“天经地义”的神圣意义。钱钟书先生说:“即我见物,如我寓物,体异性通。物我之相未泯,而物我之情已契。相未泯,故物仍在我身外,可对而赏玩;情已契,故物如同我衷肠,可与之契会。”(注:钱钟书:《谈艺录》第53页。)按照杜维明先生的说法则是,西方人认识世界的方式是“认知”,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方式是“体知”。这种“体知”的认识形式强调内在的心灵体验,不太重视视听等感官契机的作用。西方人用“物理学的眼光”看待世界,侧重于对自然形体的科学感知;中国人用“生物学的眼光”看待世界,不太重视对自然物外在形态的感知,物是一种生命形态,它的形体只是内在生命的外在显现。因此人们对物的感知是要领会它的内在精神,而不是它的载体。对这种缥缈难定的生命感的把握,当然不能科学地个别地对待,而要直观整体地把握,这种把握显然只有心灵能胜任,以心灵去体悟外物,是中国人把握世界的根本方式,道家谈心灵驰骛,儒家谈内在省悟,玄学谈心归万有,禅宗谈体验,理学谈心性,都强调心灵体验有认识方式。
建基于“人与世界对立”哲学的西方人的空间意识,自然就体现于由近及远的层层推进中,到达目极难穷的远天,之所谓“向着无尽的宇宙作无止境的奋勉”,其中暗示着物与我之间的一种紧张和分裂。“东方的智慧却不是飞翔于‘自然’之上而征服之,乃是深潜入于自然的核心而体验之,冥合之,发扬而为普遍的爱。”(注:《宗白华全集》第2卷,第298页。)因此,中国人的空间意识,深深植根于《周易》的宇宙哲学观:“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二气化生天地万物,天地万物皆由阴阳二气相摩相荡交感而成,而人的内在心理结构正与之相契合,即“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宇宙间普运周流的勃勃生机使心物交相浑融,生生不已的阴阳二气又织成一种有节奏的生命。因此中国人的空间意识,不去奋力追求那无尽的宇宙,而是“网罗天地于门户,饮吸山川于胸怀”,流变的空间随着心中的意境可敛可放,空间延伸与时间节奏相交汇,回旋往复的空间流荡着一阴一阳、一虚一实的生命节奏,之所谓“无往不复,天地际也”。
中西两种不同的空间意识与双方迥然有别的观照法密切相关。西方人用数学、几何、物理的科学眼光看待空间。按照宗白华的说法是,西方哲学的象征是“测地形”之“几何学”,有“不懂几何学者勿进哲学之门”(注:《宗白华全集》第1卷,第602页。)的说法,因此,从古希腊开始,西方人就津津乐道几何透视法,站在空间外面来营构他们的审美空间,固守着心物基本对立的观照立场:艺术家由一固定的主观立场观察客观世界,主客截然两分,形成静止的、几何式的三进向立体空间,这是“一远”境界的透视空间。这种空间意识是西方文化自觉追求艺术与科学一致的产物,体现了西方传统的科学精神。在这种精神影响下,艺术家们竞相研习透视法、几何学,以建立合理的真实空间,甚至达到“令人几欲走进”的地步。这种透视空间,其“境界层”为写实的、物我对立的。西方的建筑、雕刻、油画同属这一境层。
中国哲学的象征不是西方的“测地形”之“几何学”,而是“本之性情,稽之度数”的音乐。因此,中国的艺术家“不愿在画面上表现透视法”,而独独青睐节奏鲜明的“俯仰往还,远近取与”的流动观照法。早在先秦时期,庄子就说过:“其疾俯仰之间,而再抚四海之外”。《易经》也曾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于是八卦得以产生。《说文解字·序》又把它作为汉字的创造方法。至魏晋南北朝时,发展、形成“俯仰”之说。宗白华列举了《诗经》以来许多著名的诗句,从创作实践上突现出俯仰宇宙的审美观照法。值得注意的是,“俯仰”观照,并非只是简单的观上看下,而是摆脱了西方数理、几何式的透视原理,以服从于艺术原理的“以大观小”(注:沈括:《梦溪笔谈》。):艺术家不是从固定的角度集中于一个透视焦点,而是“提神太虚”,用“心灵的眼睛”从世外鸟瞰的立场观照全整律动的大自然,在流动中把握全境的阴阳开阖,高下起伏。其空间立场在时间中徘徊移动,游目周览,犹如鸟之拍翅、鱼之泳水,在此过程形成“三远”境界的艺术空间,它集合了数层与多方视点,“滢洄委曲,绸缪往复”,遥望着中国艺术意境的最高目标——道!这种艺术空间不是以几何学的透视法表出,而是由流动观照的方法视空间如一有机生命境界的产物。它是音乐化、诗化的节奏在视知觉领域的流动,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生命精神。这种艺术空间,其“境界层”的特点为虚灵的、物我浑融的,中国的诗、书画同属这一境层。
中国诗人对宇宙的俯仰观照由来已久。汉苏武诗:“俯观江汉流,仰视浮云翔”。晋王羲之《兰亭集叙》:“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大诗人、大音乐家嵇康亦有名句云:“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凡此种种,都从不同角度描述了目视神游、俯仰宇宙、流连忘返的审美境界。当诗人直面生机流荡的感性对象时,有俯仰以对,使视点无限扩大,从而使其不再斤斤于物象,不再拘泥于个人身世之叹,也不为自己所处的狭小空间所拘限,而是让精神腾挪开去,由近及远、由远及近,“优游”于大自然的生命节奏中去“游心太玄”,以心灵去领悟宇宙,将自我全身心地融入到艺术空间中去。中国画家也十分钟情这种观照法,从而使中国画空间境界的表现与西洋画大异其趣。中国最早的山水画家宗炳曾言,山水画家的要务是:“身所盘桓,目所绸缪。以形写形,以色貌色”。这就是说,画家以流盼的眼光绸缪于身所盘桓的形形色色,所看的不是透视焦点,所采的不是固定立场,因而所形成的不是几何空间,而是由数层视点所构成的、具有音乐般和谐的艺术空间。
为什么会形成如此音乐般和谐的艺术空间呢?《形上学(中西哲学之比较)》这篇中国文化哲学的经典之论纲,集中表述了宗白华对这一问题的深刻见解。他认为,源于“历象授时”之悠久传统的中国哲学,铸就了“时空合体”的时空观,四时之序与空间四方(东西南北)形成合奏,迥异于西方的“几何空间”或“纯粹时间”观念。按这一历律哲学,时间作为生命之绵延,示人以宇宙生命的无声音乐。空间是生命之定位,它和时间因生命而沟通,于是空间得以“意象化,表情化,结构化,音乐化”。历律哲学的时空观,支持了宗白华的基本论点:“中国生命哲学之真理惟以乐示之!”(注:《宗白华全集》第1卷,第604页。)“我们的宇宙是时间率领着空间,因而成就了节奏化、音乐化了的‘时空合一体’。”(注:《宗白华全集》第2卷,第440页。)
这种节奏化、音乐化的时空合一体,反映了古人对主体与自然的生命精神的体悟,体现了主体对宇宙生机的把握方式。中国人总是将审美对象视为一个生命的有机整体,而审美的时空,便是这个生命整体生存的感性氛围。庄子曾言:“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其中,将空间(宙)视为生命不受外物约束的感性存在氛围,而不究定处;将时间(宇)视为万物成长的生命力的活动过程,而不究首尾。感性生命就实现在融贯一体的时空中。正是在这种感性氛围中,主体心灵的无限与太玄的无限豁然贯通,整个宇宙与主体心灵的时空遂浑融、契合。也正是在这种感性氛围中,主体才能实现其审美的最终目的,即主体精神突破了现实时空的束缚,从有限中获得无限,从瞬间中获得永恒。在主体眼中,一小池,一园林,都可感悟到整个宇宙的生机,一山庄,一别业,竟是生意盎然的全部世界。
宗白华认为,在俯仰观照中,既要注重静观默察,又要重视生命的飞动。由于万物在虚空中流动运化,因而审美时就必须有静有动。光动不静,则躁而不宁;光静不动,则止而沉寂,应该遵循“动静有常”的原则。正如宋代周敦颐《太极图》中所说:“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在静观默照中,神驰物外,尽情领悟自然的奥妙;在俯仰往返中,远近取与,采撷钟灵毓秀之气,寄托飞动鲜活之情思。既有“仰”、“窥”、“望”视觉直观的动,又有“高远”、“深远”、“平远”的静;并在动静结合中谛听到宇宙大化生命节奏的跳跃与飞扬气韵的流动。
宗白华认为,这是“用心灵的俯仰的眼睛来看空间万象”。因此,他很赞赏“《易经》上说:‘无往不复,天地际也’。这正是中国人的空间意识”(注:《宗白华全集》第2卷,第426页。)!可见,静观默照,不仅要用眼,更要用心灵。以冲淡、平和、宁静的心灵,去观照飞动的宇宙,从中领略宇宙的永恒,体察万物的变易,并在万物运动中创造静默的心灵。这不仅符合易理,也符合《道德经》中“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的精义。
必须指出,宗白华对动静观的理解,与易传动静观相比,毕竟是同中有异的。如果说,在动静之中,易传侧重于动,宗白华则侧重于静。这和他所受道佛二家动静观影响较深的原因是分不开的。道家提倡虚静、静笃;佛家提倡虚空、静寂,宗白华则兼收并蓄,提倡空灵、静默。所以,他在《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一文中,特别从理论上强调“忘我”、“静照”、“空诸一切,心无挂碍”、“静观万象”等等,用他的话说,“静不是死亡,反而倒是甚深微妙的潜隐的无数的动,在艺术家超脱广大的心襟里显呈了动中有和谐有韵律,因此虽动却显得极静。”这是一种静中之动,在这个“静”里,潜隐着静穆观照所带来的艺术飞腾。陆机说过,由静穆观照能获得“情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的效应,情思悠悠,物色纷呈,艺术意象由是熔铸而成。宗炳也说过,在审美中“澄怀味象”,便可“万趣融其神思”,产生极大的艺术激荡。孙过庭则欣赏那种经过“容与徘徊,意先笔后”的静观默照而得来的“潇洒流落,翰逸神飞”的审美效应。刘大櫆所谓“管弦繁奏中,必有希声窈渺处”,亦指生命运动的节奏,是在其感性形态及其物我关系的动静相成中形成的。由此可见,这个静里,不但潜隐着飞动,更是表示着意境的幽深。而“唯有深心人才能刊落纷华,直造深境幽境”(注:《宗白华全集》第2卷,第380页。)。在宗白华看来,象陶渊明、王摩诘、孟浩然、韦苏州、苏东坡这些第一流的大诗人便是此“深心人”,他们的诗如“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等都是能写出这种蕴含无数飞动的“最深的静境”的。
中国艺术偏爱以静为基础,静中生动,动静相成,以体现生生不息的生命整体。
在宗白华那里,动静被视为中国艺术俯仰观照的体用特质,而“三远”说则集中体现了中国艺术的审美观照与空间境界的一般特征,照我看,可以理解为中国艺术空间意识的特殊表征。宋画家郭熙于此说贡献最大,他的《林泉高致·山水训》云:“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高远之色清明,深远之色重晦,平远之色有明有晦。高远之势突兀,深远之意重叠,平远之意冲融而缥缥缈缈。其人物之在三远也,高远者明了,深远者细碎,平远者冲澹。明了者不短,细碎者不长,冲澹者不大。此三远也。”“三远”说的内涵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山水画构图法,这是“三远”说最基本的内涵,涉及到笔墨技法诸问题,不是我们的研究重点。二是作为中国山水艺术观照法的系统总结。画家面临山川景物,不是从一个固定焦点出发,而是“仰山巅”(高远),“窥山后”(深远),“望远山”(平远),其视线是流动的,转折的,有节奏的。三种不同的视线又可会通交替,对同一景致从不同角度远观。画家的视线由高转深,由深转近,再横向平远,视点不断变化,视线的往复流动使对象形成生命之波,于是自然的空间就活了起来,成为活泼泼的生命实体。这种“三远”式观照法正实现了传统美学的“游”观精神。
基于“道”的哲学,中国人欣赏山水和艺术,都落实于一个“游”字。“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庄子语),“精骛八极,心游万仞”(陆机语),“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刘勰语)。“游”可谓中国审美精神的真宰。“游”是一种没有外在负担,没有功利目的,来去自如、俯仰自得的审美活动,是一种摆脱羁绊,超然物外的精神状态,即物而不拘于物,观景而不滞于景,始终保持着精神的流动和畅达。可以这么说,“游”一方面表明了中国人的审美方式是时空一体的动的观照方式,即“游观”,另一方面表明了中国人的审美精神并不凝聚于对审美客体具体形象的把握,而是凝聚于自我生命与客体生命的交响合流,即“神游”,这两个方面是互为表里的。宗白华曾言,审美观照的实现即是继“心斋”而来的“神游”(游观)。因此,这种“游”的审美方式和审美精神不仅带来了“无往不复、天地际也”的艺术意境,也带来了人与自然的契合无间和亲切应会。在此精神状态下,画家对自然山水的高远、深远、平远作“俯仰往返、远近取与”的流动观照,则完全可以突破静止观物的局限,从而使画面所容景物更多、更广,场景更为博大、境界更为高深,这就形成“三远”说的第三层内涵,即作为中国山水艺术空间境界的表现。
“远”作为山水艺术理想境界的理想源远流长。魏晋时代,对中国山水画产生深刻影响的玄学就十分重视“远”。(中国艺术所重在于惟恍惟惚的“道”,自老子所言“逝曰远,远曰反”之“远”,到王弼《老子指略》以为“绵邈不可及”之“远”等等,与“玄”、“深”、“大”,“微”一样,所指均与“道”相近)。此后历代山水画家相继承袭这一思想,讲究“咫尺万里”、“平远极目”,讲究“远景”、“远思”、“远势”,极力追求“远”的境界。至郭熙,对这种思想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并概括为“三远”境界说。“三远”式观照法是“三远”境界得以产生的阶梯。画家通过“三远”的观照方式,“提其神于太虚而俯之”,以心灵之统观的“眼”抚慰山河大地、草木虫鱼,在“以大观小”的过程中,突破尺寸画幅,化有限空间为无限,从静止画面寻出流动,将自然感性与宇宙纵深联系起来,从而进入“大人游宇宙”的超越境界,最终实现中国画家、中国艺术家孜孜以求的开阔胸襟、陶冶情性、俯临万物之上而与宇宙同在的宏愿。这与西洋透视法构筑的“一远”境界可谓大相径庭。
西方绘画起源于建筑与雕塑,重视体积,以几何透视为构图法则,因而创造出的是“令人几欲走进”的三进向空间。而中国绘画起于甲骨、青铜、砖石的镌刻,主张舍形悦影,以线示体,甚至主张“无线者非画”,线条成为绘画的主要手段;它“以大观小”,采取的是“提神太虚”、“三远”式审美观照法,其结果,不是西方如何走进实景,而是“灵的空间”。正如宗白华所说:“由这‘三远法’所构的空间不复是几何学的科学性的透视空间,而是诗意的创造性的艺术空间。”(注:《宗白华全集》第2卷,第435页。)
既然中国艺术超脱了数理的几何式的空间意识,需在诗意的创造中体尽生命律动的变化,故而诞生一种特殊的审美特点——虚实相生。“我们的宇宙既是一阴一阳,一虚一实的生命节奏,所以它根本上是虚灵的时空合一体,是流荡着的生动气韵。”(注:《宗白华全集》第2卷,第441、442页。)宗白华对艺术中“虚”与“实”的论述很多,有几篇文章还专门论述了“虚实”问题。在他看来,空灵(虚)和充实(实)是艺术不可缺少的两大要素。艺术需要“充实”,需要反映人生、社会,然而更需“超凡入圣,脱尽尘滓”之“空灵”,空灵是人类最高心灵的外在表述。“空”是无边无际的空间,是艺术的空白;灵则是空中活跃的生命律动,是有机的审美心理场。“空灵”就是一种宇宙无极之境与人的生气的和谐。宗白华研究发现,中国诗词、绘画里都有空中点染、抟虚成实的表现方法,从而使诗境、词境、画境中有空间、有荡漾,形成空灵之境。如王维的《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四句诗中的形象可谓简之又简,春山、夜月、桂花、鸟鸣,但它们既显示了幽静与空寂,又昭示寂静中无限的生机,表现出诗人心境与环境的互相契合,因此,它如同无限的广阔宇宙,万事万物,尽可于其中生生不已。物与空间,灵气往来,溶成一片,显示出无尽的生动气韵,即所谓一天的春色寄托于数点桃花、三二水鸟启示自然的无限生机。
宗白华特别叹赏中国书画中的“空白”,认为这种“空白”,不再包举万象位置、万物轮廓,而是潜入万物内部,参加万象之动的虚灵的“道”,“空白”即“道”,即万物的源泉、万动的根本、宇宙生生不已的创造力。在他眼中,中国“哲人、诗人、画家,对于这世界是‘体尽无穷而游无朕’。……‘而游无朕’,即是在中国画的底层的空白里表达着‘道’(无朕境界)”(注:《宗白华全集》第2卷,第441、442页。)庄子曰:“瞻彼阙(空处)者,虚室生白”。宗白华认为中国诗画中的空白即是庄子所说的虚白,这个虚白“是创化万物的永恒运行着的道”,“这‘白’是‘道’的吉祥之光”。(注:《宗白华全集》第2卷,第441、442页。)所以书法家抒写的自然生命,都集中在一片无边的空白上,空中荡漾着“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道”。中国画也将“空白”作为真正的画底,“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画家的用心所在,正是这无形无迹而又无往不在的虚空,借着它而传达出“一片神游的意境”:空灵流荡、超旷幽远。“唯道集虚”,此一“虚空”并非真正的空,并非僵死的空间间架,而是灵气往来、生命流动之处,是最活泼的生命源泉,一句话,是宇宙生命的最深意义“道”,艺术境界由此获得“充实”。艺术家涵泳在这种虚灵而又充实的艺术空间中抚爱万物、澄怀观道,进入艺术创造的理想境界。
从宇宙生成论的角度理解,老庄的“道”是指派生万物的宇宙本体。但是,对于“道”是什么样子,即“道”以什么形态存在,老庄的回答却是“虚无”。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庄子亦说,“万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又说,“唯道集虚”。正是基于老庄对于“道”的存在状态的给定和描述,宗白华逆向推论,把艺术中的虚无解释为对“道”的追寻,“(诗人、画家)用太空、太虚、无、混茫,来暗示或象征这形而上的道,这永恒创化着的原理。”(注:《宗白华全集》第2卷,第441、442页。)在这里,宗白华将中国哲学中的宇宙本体论及宇宙生成论引入艺术空间,把艺术空间看作只是宇宙空间的位移或者微缩了的宇宙空间,艺术空间中的虚空、虚白就是超验的宇宙本体“道”的显现。中国人对“道”的体验,是“于空寂处见流行,于流行处见空寂”;当诗人、画家将自我跃入虚无、涵泳在虚灵中时,就是进行着将自我与宇宙中某种超验价值相结合的精神体验。所以,中国诗人、画家对艺术中的虚白、虚空精有独钟,数千年来始终不已地将它崇拜、神往、追寻,将它视为精神升华和艺术表现的理想境界。
虚实相生与整个中国艺术的审美特点也是相通的。如诗歌中有意象的跳跃与间隔,音乐中有“此时无声胜有声”,书法中有“计白当黑”,园林中有“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等等,而绘画的本质即在于虚实,借用郑绩的话则是“生变之决,虚虚实实,实实虚虚,八字尽矣”。其实,绘画比写诗更难表达“虚”的东西,唯一的办法是紧紧抓住对“实”的逼真描写,这是因为“实者逼肖,虚者自出”、“实景清而空景现”、“真境逼而神境生”。清雍正时画家邹一桂在《小山画谱》中,把这个问题论述得更清楚。他说:“人言绘雪者,不能绘其清;绘月者,不能绘其明;绘花者,不能绘其馨;绘人者,不能绘其情;此数者虚,不可以形求也。不知实者逼肖,虚者自出。故画北风图则生凉,画云汉图则生热,画水于壁,则夜闻水声。谓为不能者,因不知也。”由于虚与实存在着这样的辩证关系,所以中国绘画,都努力追求着真景实境的逼真描绘,力求从实境的真实感中能诱发人们更多的想象,从而生发出广阔的虚境空间。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实境可谓是一个具体的审美空间,虚境则是一个由实境诱发的想象空间,实由虚而生,虚因实而成。无实则不能表现出虚的生命力,无虚则实也无以生存,惟虚实相生,方能体现出空间的生命形态。从审美的角度而论,宗白华更倾向于以这种虚实结合的艺术空间作为空间意识的典型。
中国式的艺术空间超脱了西方几何化的透视空间,它所呈现的不再是西方的立体雕刻,流荡其间的是诗,是音乐,是舞蹈,总之一句话,是“生动的气韵”。宗白华通过对中西画法的比较分析指出:西方画家竭力向无穷空间奋勉,往而不返,其视线失落于无穷,驰于无极,或偏于科学理智,或过于彷徨不宁,物我之间仍存某种对峙而未能相契。中国画家对无尽空间的态度却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人生在世,如泛扁舟,俯仰天地,容与中流,灵屿瑶岛,极目悠悠”(注:《宗白华全集》第2卷,第440页。)。审美主体以抚爱万物的情怀,目极无穷而又返回自我深心,俯仰往还,远近取与,成一回旋节奏;宇宙生命空间,也呈现为由近及远,返归于近,由有限至无限,又复回归有限的“无往不复”的回旋节奏。于是,宇宙生命节奏与自我深心节奏得以和谐共振,通过点线交错的自由挥洒,化为一种音乐谱构。由此,宗白华认为“气韵生动”是中国绘画创造的最高理想,也是中国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所谓“气韵”,就是宇宙中鼓动万物的“气”的节奏、和谐,“生动”则体现了热烈的生命飞动,中国艺术正因为有了这种“气韵”,所以才给人以鲜明的音乐感。通观绘画、书法、诗词、建筑、雕塑以及园林艺术等等,无不潜伏着这种动人的音乐感。而飞动与生气则隐寓在艺术形象之中,给人以强烈的生命感,由此使得中国艺术意趣盎然而神韵超妙。但宗白华又独具匠心地告诉我们:“气韵生动”并非只是中国艺术的专利品,“西洋画表现气韵生动,实较中国色彩为易。”(注:《宗白华全集》第2卷,第107页。)
西洋画源于希腊的雕刻与建筑,其形体的凹凸光彩利用油色晕染移入画面,明暗的光彩及鲜艳流利的颜色构成画境的气韵生动。因而这种“气韵生动”可称之为“色彩的音乐”,是一种“华堂弦响之韵”。
中国画则另辟蹊径,不在刻划凹凸的写实上下功夫,不愿描写从“一个光彩”所看到的光线与阴影,而是舍具体、趋抽象,将全幅意境谱入一种明暗虚实的节奏之中,“神光离合,乍阴乍阳”。轻形似而重神似,所谓“得其形似,则无其气韵。具其彩色,则失其笔法”(张彦远语)。因而,中国画于点线皴擦的表现力上用力尤勤。既然,笔墨的点线皴擦从刻划实体中解放出来,就更能自由表达艺术家自心意匠的构图。画幅中每一丛林、一堆石,皆成一个意匠的结构,笔情墨韵中点线交织,丰富的暗示力与象征力代替了形象的写实,气韵生动,由此产生。因此中国画的气韵生动可称之为“点线的音乐”,是一种“明月萧声之韵”。
虽然一切艺术都趋向音乐,但“华堂弦响”与“明月萧声”韵调自别。照我看,宗白华更倾心于“明月萧声之韵”。他曾无限深情地指出,“中国画趋向抽象的笔墨,轻烟淡彩,虚灵如梦”,其气韵生动为“幽淡的,微妙的、静寂的、洒落的,没有彩色的喧哗炫耀,而富于心灵的幽深淡远”(注:《宗白华全集》第2卷,第107、108页。),而这,正符合他潇然洒落的艺术式人生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