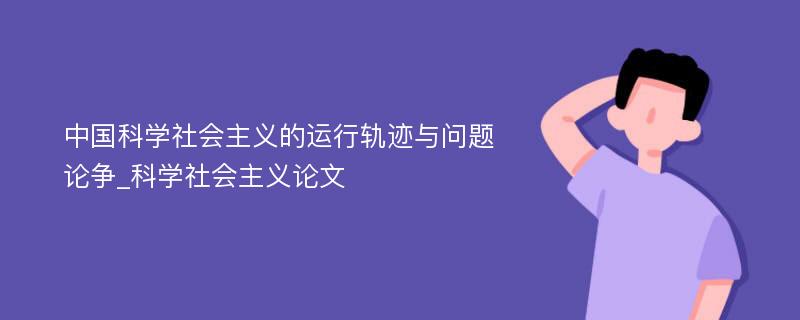
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运行轨迹及问题论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轨迹论文,科学社会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33.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00)09—0020—02
一
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正式传播始于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时期。八十余年来,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不仅要战胜西方传来的资产阶级思潮,还要同中国本身的文化传统碰撞、斗争和论争。影响全局的重大论争有四次:
“五四”运动到建党初期是第一次。这次大论争包括三场具体的争论:一是1919年7月由胡适挑起的“问题和主义”的争论;二是1920 年马克思主义者同“研究系”张东荪、梁启超的争论;三是1920年开始的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三场争论主要涉及两大问题:中国的真正出路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中国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整个问题的大前提,决定着中国现代社会的基本走向。所谓“历史的选择”最早就发生在这个时期,李大钊、陈独秀、胡适、梁启超、张东荪的争论就是选择。既然选择了社会主义方向,就有个通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根据马克思学说和俄国经验,必须首先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在这个政党的领导下,进行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对无政府主义斗争的胜利最终表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在中国被正式确认,这是第一次大论争所取得的基本成果。
第二次大论争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实际贯穿大革命失败到新中国成立前的整个过程。三十年代的大论争主要是“新思潮”派和“动力”派的对峙,焦点是中国社会的性质。“新思潮”派潘车周、王学文等人力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来研究和探讨中国社会的性质、结构及社会发展的历史,他们认为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一方面使得中国的商品经济获得了某些发展,促进了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生长;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同封建势力相勾结,竭力维护中国的封建生产关系。所以他们认为中国当时的经济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半殖民地的封建经济,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动力”派严灵峰、任曙、胡秋原等人则坚持认为:在帝国主义的推动下,现时的中国已经是十足的全称的资本主义,大革命失败以后,在托洛茨基的影响下,陈独秀、彭述之等人成为“取消派”,其基本的错误结论就是认为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蒋介石所建立的政权代表的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国家。为此,毛泽东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 ”(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33.)毛泽东正是在吸收了这场中国社会性质论争的积极成果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和阐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这次大论争的巨大功绩在于促使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在中国最终找到了现实的形式和途径,对于克服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可以说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第三次大论争。这是我党历史上遭受挫折时间最长的时期。大挫折有两次:一次是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另一次是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前一次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后一次主要表现在政治思想领域,但有内在联系。论争贯穿其全过程,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主要分歧点有两个:一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应不应放在经济建设上。二是经济建设要不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尊重客观经济规律。这次大论争是我党执政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由于党内民主集中制遭到损坏,论争不能正常地进行,特别是正确的观点得不到充分表达,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在中国的演化和发展,这也是使论争长达二十余年之久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尽管论争被失常的党内生活所扭曲,常常只能听到一个方面的声音,但绝不能因此否认论争的存在,某些场合论争和分歧还是比较明显的,如1959年庐山会议、1976年“天安门事件”及其后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等。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大论争的结束,其后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争论了二十余年的社会主义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总结。
第四次大论争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党和国家实现了工作重心转移,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问题开始了全面的实践和探索。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成为国民的共识。由于一方面长期“左”倾错误的余毒短时间内难以彻底消除,另一方面迅速到来的改革开放的实质一时难以为人民普遍认清,对于经济生活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人们又缺乏精神准备,加上国际上阶级斗争的复杂化,人民内部、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出现了新的分歧和论争。主要分歧点是改革的实质问题,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还是放弃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没有从“左”的思潮中解脱出来的人,不理解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把改革当作复辟资本主义而加以抵制;站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把改革歪曲成私有化和全盘西化。他们对社会主义前途完全丧失信心,实际上并不赞成社会主义改革,而是以改革为名放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彻底改变数十年来中国人民选择的社会主义方向。于是,当代中国应当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老问题又一次以十分尖锐的形式提到国人面前。这次论争和斗争同上一次是不同的,在党的领导核心中正确意见始终占统治地位。故斗争和争论的过程也是科学社会主义迅速发展和深化的过程。许多上次大论争中以被歪曲的形态或以萌芽状态出现过的问题,现在逐个地得到了实事求是的辩证的解决。例如,既要确认社会主义制度,又要承认社会主义还不完善;既要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又要承认一定范围内阶级斗争长期存在;既要搞物质文明,又要抓精神文明;既要改革开放,又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如果第三次大论争已经接触到科学社会主义深层次的问题,那么第四次大论争表明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开始走向全面解决。
二
四次大论争覆盖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系统地研究这些争论可从中观察到科学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运行的轨迹。例如,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理要在落后国家见实效,就必须转化为一定的民族形式。“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民主革命的一般原理在中国的民族形式。“农村包围城市”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一般原理在中国的民族形式,“人民民主专政”是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一般原理在中国的民族形式。一般说来,科学社会主义在任何民族都有个与该民族的实际相结合的问题,都要找到一定的民族形式。但是落后国家同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欧洲环境差别更大一些,科学社会主义的一定民族形式更为重要,矛盾更为突出。再如,关于两条战线上作战问题,落后国家也有自己的特征,既反“左”,又反右,坚持两条战线上作战,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普遍规律,任何民族运动的指导者都不能忽视这个任务。但落后国家这个任务更重。
上述特点虽然都能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的运行轨迹。但是笔者以为这条轨迹上还有更典型的特征,那就是落后国家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在内容上不同的部分会出现不同的情况,表现出层次差异,有易点,也有难点。
从历史上看,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比较快的,对“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容易理解。二十年代初期,对无政府主义者不要任何政权的谬论,蔡和森就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进行过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仍然是很正确的论述:“无产阶级革命后不得不专政的理由有三:无政权不能集产,不能使产业社会有。换言之,既是不能改造经济制度。无政权不能保护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阶级而复起,革命将等于零……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注: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一卷,723—734.)中国共产党在经过大革命失败的挫折之后,比较快地找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民族形式;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一刻也没有犹豫地把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运用到社会主义时期,直到今天在任何严重危险和挑战面前都没有动摇过这一真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革命和专政的学说之所以容易在中国扎根,主要是中国拥有近代的革命传统。旧中国广大人民长期处于无权状态,在各次变革和政治动乱中受害无穷。但也能从中看到国家政权的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启发下较容易理解和消化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原理的道理。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无疑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但它还只是科学社会主义一个方面的原理。如果我们把这个原理称之为社会主义国家原理,那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碰到的主要是另一个方面的原理,即社会主义生产力原理。相比之下,社会主义生产力原理在中国运用起来就显得困难得多、吃力得多、笨拙得多。最明显的表现是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延续了二十多年才转上正轨,其间主要精力被用于指导理论斗争。但深究一下,为什么一直把阶级斗争当作中心任务?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的原因,也有内部原因。应当承认党内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长期存在着分歧。根源就在于把某些本来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意见看成阶级斗争的表现,而在这里所涉及的深层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原理问题。由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原理根据不稳,“重心转移”的策略可以正确地提出,也可以错误地抛开。建国后一系列急于改变生产关系的失误是很典型的:三年完成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几个月内实现人民公社化,三二年完成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一面是物质生活十分贫乏,一面批“唯生产力”论,把商品生产、等价交换乃至按劳分配当作资本主义和产生资本主义的基础来批……所有这些错误的提法和作法,明显的倾向就是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看作纯生产关系的东西,似乎只要不停顿地提高公有化水平,就可以加快实现共产主义,这是自觉不自觉地离开了科学社会主义轨道。马克思恩格斯考察社会主义,不是把社会主义看成事先设想好的某种平等原则,而是看成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所必然出现的某种客观趋势。其主要逻辑是:资本主义发展造成了社会化大生产,而只有社会化大生产才能对私有制提出最后挑战,才能造就推翻资本统治的社会阶级力量,才能提供满足全体社会成员普遍需要的财富。他们也曾设想生产力很低的时候办社会主义是一种什么情况,但他们断定:“那就只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然会重新开始争夺必须品的斗争,一切陈腐的东西要死灰复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39.)在大搞穷过渡的年代里,中国人不仅看到过“贫穷的普遍化”,一面“斗私批修”,一面“争夺必须品”的事也不曾少见。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奇迹,之所以在社会主义生产力原理面前几经曲折,不能不使人联想到中国的国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民多半不熟悉不了解社会化大生产,视现代机器为异物,生产环境使人习惯于用小生产的平均主义的眼光看待社会主义,以为只要有了政权就可以消灭人世间一切不平等,只要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就可以达到理想境界。而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才有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同生产力的内在联系,这些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却容易被忽视,贯通在马列经典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原理也没有被真正挖掘出来。
能不能从社会主义生产力原理引出落后国家社会主义注定没有前途的结论呢?不能。这个问题列宁早已做了回答,那就是在生产力还不算很高的情况下先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然后利用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再来发展生产。但是这样一来社会主义国家解决生产力的任务更重了。我们应该看到,列宁的这一思想是对社会主义生产力原理的重大发展,其基本精神是结合落后国家的情况,更坚定地贯彻科学社会主义。如果用小生产者的心理片面地理解列宁的思想,就会以为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到来,就会忘记我们在生产不足的情况下建起来的社会主义只是一种不成熟的、不完善的因而也是不稳固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生产力原理的实现,是落后国家的难点,当然解决起来就要费更多的周折。从中国来看,第三次大论争时间太长,代价太大,不过它也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和丰富经验,故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迅速出现的新局面,故有第四次论争中一系列问题的全面辩证解决。
标签:科学社会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文;
